航空畫報卷首集《活著,走著想著》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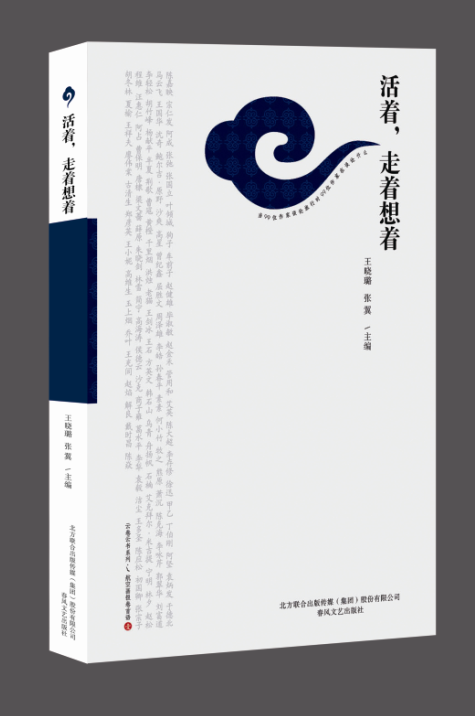
當99位作家談論旅行時,99位作家在談論什么?
由南航文化傳媒航空畫報社策劃、編輯的航空畫報卷首集《活著,走著想著》,近日由春風文藝出版社出版。該書收錄99位作家四年來應約為《航空畫報》卷首欄目撰寫的99篇旅行隨筆,包括陳嘉映、畢淑敏等,可謂名家云集,精品薈萃。另有99位作家素描畫像、簡介,11幅黔西南美麗風光圖片、11幅黔西南少數民族風情雕塑作品及40余幅遼寧桓仁農民版畫,作為插頁、配圖。
中國南航集團文化傳媒股份有限公司黨委書記、副總經理、南方航空報社總編輯蔣旭斌,中國科學院青藏高原研究所研究員、著名地質學家、探險家劉小漢先生,應約為本書撰寫了序言。
附:
書籍信息:
書名:《活著,走著想著》
主編:王曉璐 張翼
執編:程遠
責編:姚宏越
設計:王冉
開本:150mm×230mm
頁碼:254頁
出版:春風文藝出版社
上市:2015年3月
定價:48.00元
【書評】
人生就是一場旅行
——評《活著,走著想著》
文/ 趙志明
在《紅樓夢》中,賈雨村陪送林黛玉投奔賈府外祖母和親舅舅,從淮陽地區坐船,途經大運河,到達京城需要一個多月。古人或假輿馬者,或假舟楫者,以致千里之外,若是完全憑借腳力,晃晃悠悠豈不是要花費更長時間。所以在前人筆記小說中,一個書生赴京趕考,伴著一個挑擔書童,從蜀川到京師,總要經歷數月光景。因此之故,在一生中,一個考生自然很難三番兩次地赴考。在途中停停歇歇,走走看看,不外乎“雞聲茅店月,人跡板橋霜”,偶爾遇到“墻外行人墻內佳人笑”“人面桃花相映紅”,為著音容笑貌而駐步踟躕,不免長吁短嘆一番。
換成“無事一身輕”的閑人雅士,擔風袖月,訪山問水,“行到水窮處,坐看云起時”,更是觸目皆景,一切景語皆情語了。比如像詩人歐陽修、姚鼐之流,訪幽靜之所,登泰山之巔,更是游目騁懷,“思接千載,神游萬里”了。
這是古人的游歷,所謂“讀萬卷書行萬里路”,不可能一蹴而就,很可能讀書讀成了范進,腳掌磨破也抵不上十分之一個徐霞客。放到今天,交通便利,縮短了空間,節省了時間,以致每個人都覺得“世界很大,我想去看看”,來一場“說走就走的旅行”。然而,去的地方多了,看的景色多了,記住的反而少了,不過是走馬觀花,囫圇吞棗,這樣的“旅行”意義不大。當然,不一定非得來一次“朝圣”,來一場“苦旅”,那也是矯情。
“人在旅途”,旅行不是目的,而是過程。一個人滿世界飛行,也可能一無所見。一個人即使身處陋室,也能“坐地日行八萬里”。博爾赫斯雙目失明,但閱讀讓他無所不知。卡爾維諾借助讓人驚嘆的想象力,像魔術師一般讓“看不見的城市”一一呈現。一個行者,不管是為了攬勝獵奇,還是為了消遣放松,去往一個風景名勝;不管是為了打撈過去的回憶,還是為了獲得更多路上的體悟,讓人生飽滿酣暢;都要為每一次“旅行”準備一些必要的裝備,除了藤杖、帳篷、防雨衣、登山靴之類,還要有思想意識上的準備。否則的話,身體上路了,靈魂卻下落不明,眼睛看到了,心靈卻一片空白,這是多么遺憾。而是要“身體和心靈結伴上路”,這樣的旅行才圓滿。
我個人很少旅行,從一個地方過渡到另一個地方,也并不覺得是“旅行”,而是“他往”而已,不光是受制于經濟能力、時間,更主要是自己毫無旅行的準備和意識。就像著名小說家曹寇說的,“旅行是一種能力。不僅涉及語言能力、交際能力、經濟能力、體能,還包括性格能力”。就像哲學教授陳嘉映說的,雖然“無緣那種偉大的旅行”,然而只要對“自然之美比較敏感”,“看著風光,我就覺得自己風光”。
無論是曹寇,還是陳嘉映,說的都是一種投射效應,自我投射于風景,風景投射于自我。這是一種相融,也是一種相得,讓我想起兩句詩,一個是李白的“相看兩不厭,唯有敬亭山”,一個是陸游的“何方可化身千億,一樹梅花一放翁”。中國古人的旅游觀景的心態,物我兩忘兩相宜的境界,或許有些太理想化太文人氣,但今天的中國,碌碌眾生欠缺的可能正是這樣一種生活一種心境,悠然自得,不被太多身外事物所綁縛。
這是我讀《活著,走著想著》這本書的大致觀感。此書收錄了99位詩人、小說家、導演、畫家等的旅行感悟,里面有很多耳熟能詳的名字,比如張弛、狗子、阿堅、畢淑敏、高星、何小竹、烏青、唐棣、潔塵、王小妮。他們不一定都是旅行達人,也沒有給我們帶來路上的明信片,但他們對于旅行的感悟卻遠較攝影圖片更值得玩味。它山之石可以攻玉,更何況這些智者的吉珠之言,一定可以讓我們對旅行、對風景的認識更立體、全面和深入。
就拿我來說。我本來以為,對于在路上的人,給他風景就可以;對于宅人而言,給他一個地球儀,大不了再給他一個天文望遠鏡就行;其實這是不對的,是有失偏頗的。風景是永遠相對觀者而言的,不說“仁者樂山智者樂水”,至少也存在詩人楊黎的“冷風景”之類。“風生水起”也好,“波詭云譎”也罷,都要被看到,才能完成這種雙向的激發。世界千變萬化,時間轉瞬即逝,何謂長相憶的風景,何謂過眼云煙,這中間的區別大了去了,完全因人而異。
我還想到“活著”。粗淺的看法是,“活”由“三”“舌”組成,意味著對談和交流,“著”由“羊”“目”組成,意味著觀看和欣賞。這里面沒有“人”什么事情,人只是其中的一個物種而已。“活著”是關乎宇宙萬物的,是它們之間的互相欣賞和交流,指向的是一種物種之間的“和平共處”。“活著”是前提,萬物都活著,都活得好好的,這樣的世界才更值得去走走,去看看,去想想。“走心之旅”,才更值得向往。
趙志明 朋友們叫他小平,70后,常州人,小說家,壞蛋文學獨立出版發起人,小飯局局主,“十九點”文學沙龍第一批成員,2014年獲第12屆華語文學傳媒大獎“最具潛力新人獎”,2015年獲第五屆后天雙年度文化藝術獎“后天小說獎”。喜歡踢足球,打臺球,看NBA,喝酒,吹牛,做白日夢。出版書籍《我親愛的精神病患者》《1997年,我們買了螺螄,卻沒有牙簽》《青蛙滿足靈魂的想象》。現居北京。
沉重的肉身
文/ 李黎
我有一位爺爺,六十年來都生活在村子里,對眼前的丘陵樹木房屋道路了然于胸,對幾只中華田園犬、成群的雞鴨和兩頭水牛也都像親人一樣熟悉。再算上季節變化,他對這個生活期間的四維空間了如指掌。我覺得這樣很好,雖然閉塞,但是有一份沉重和穩當在他的每分每秒之中。這兩年,旅行成為人們的生活方式之一,和電視電腦手機一樣,無聲卻也無情地侵入每個人的生活,這位爺爺也隨團去了很多地方。每一次回來,他都大呼小叫,哪里都好,任何地方都好。我有時難免同情地看著他:維持了六十來年的自得在幾天的旅行之后就被摧毀了嗎?確實是被摧毀了,人一旦離開故土,哪怕只是驚鴻一瞥,世界的精彩就會在心中烙下印記。何況,這位爺爺先后去了西藏、新疆和內蒙,完全不同于丘陵地帶的景觀讓他有了一種類似于飛向太空的震撼,積淀在內心深處的探究世界、窮盡宇宙奧妙的愿望被徹底激發出來(如劉慈欣所說,幾萬幾十萬年前,地球上第一個抬頭仰望星空的那個人,就已經開啟了人對宇宙萬物的探尋之旅)。雖然,這位爺爺必將在某天停止外出,在溫馨和疾病的包裹下走完一生,但晚年的外出還是讓他想到了很多。在我們所不了解的時刻,他一定一邊看著親如家人的小狗、雞鴨一邊想,出去轉轉,能不回來就不要回來了。
人應當外出,離開熟悉以至溫暖、自得和甜膩的環境,讓所有不熟悉的事物成為坐標,這時,或許會自知自省一些。每一次外出都是一次放棄所有常見的依賴,以血肉之軀直面未知世界的一個過程。《活著,走著想著》一書,就是以走出去為思路選編的一本隨筆集。這不是一本游記匯編,因為本書提供的走出去的方式,遠遠超過了旅游(出差)這一現代社會才有的概念,它包含了探險、朝圣、追尋、訪古、離家出走、說走就走、隨便走走、逃避、漫游等各種方式,它以悍然的篇目(共99篇之多)和無所不容的外出方式,成為了一個指南,一個如何離開日常生活的指南,更是一個如何安于生活、如何蓄勢待發的指南。
除了數目寥寥的職業旅行家,每一個人都受制于各種社會事務;而就算加上極端純粹的旅行家,每一個人都受制于沉重的肉身,受制于它的無能、它的必然衰敗和死亡、它有限的能力和無盡的欲求。外出旅行是告別日常生活的方式之一,這層意思,即便是最庸常的旅行廣告也操練得很熟悉了。外出也是擺脫沉重的肉身的過渡形式,或者說,前奏。只有在一些極端的行走之中,才可能感受到無可抑制的震撼和靈魂出竅的感覺。當我們歷經一些極端疲憊、極端兇險的過程,面對一些極端恢弘的景觀,或身處一些超出視覺經驗和思維模式的情境時,才有可能在或長或短的時間里,忘卻那個煩人的肉身,進入人仙交界之處,更有可能的是,只有在那些時刻才真正思考以自身存在為依據的歸去來兮這樣的大問題,思考為何存在。
或許我們的存在毫不重要,但在如此決絕之前,我們更希望給自己一個妥帖的答案,一個滿意的過程。那么就走出去吧,《活著,走著想著》說得很明白,活著,就得走著而且想著。當然,這不是一本外出事物指南,如孤星系列那樣。這是一本讓你拋下很多事物,包括這本書本身,毅然走出去的書。99位名作者基本窮盡了外出的方式和趣味,但畢竟都是別人的,你的還得你自己去走。
李黎 1980年2月生于南京郊縣,2001年畢業于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現供職于鳳凰出版傳媒集團江蘇美術出版社。業余寫作,1998年開始發表作品。著有詩集《在手指以外的虛無里》,長篇小說《雞的遷徙》《獅子樓》等。
靈魂的行走與吟唱
——讀《活著,走著想著》
文/ 趙虹
讀這本書,貌似看天上閑云一朵,無須定位,隨風導航。圖,畫,文,信手翻來,處處有景。因為閑看,便不時放下,不時拿起,慢酌細品,一小口一小口,不忍牛飲。
身體和靈魂總有一個在路上,是我與書里九十九位作家神交后的啟示。從這個維度去掂量,世上人大約可分為兩種,喜歡在路上的,不喜歡在路上的。
我見過的最不喜歡在路上的人,沒有之一,是我曾經的上司。多年前某一陣子,公費國內國際考察學習,理所當然。作為雜志社老總,他接到的通知邀請無數,不懷好意的、懷好意的統統被他擋駕,不是因為廉政,只因不喜歡在路上。他說家里第一好,辦公室其次,別處都是受罪。有一回到北京開會,會務組安排爬長城,他在長城腳下的電影館看了一場關于長城的立體電影,看完便溜回旅館,等著調侃我們這些爬得氣喘吁吁的好漢。
他的理論是,一生不出門是個福人。
那時,他的不可理喻達到我不敢笑也笑不出來的地步。詫異的是,談到各地的風物民俗,他不亞于東跑西顛的我,好像哪里都去過。不行萬里路,多讀幾卷書,他踐行著自已的理論。車到頤和園,不進大門,在門口書攤買一本頤和園的畫冊就打道回府,這種人少見。
多年以后我不得不承認,他是另一種在路上。取舍萬殊,靜躁不同,皆欣于所遇。讀書寫作,是靈魂的行走。不走路算不算是他的一個偏執呢?讀萬卷書與行萬里路是大智慧的匹配,這大約是《活著,走著想著》編者的立意,也是印證了華文大詩人洛夫的理論:用腳步思考。
我居住的江城漢口,還有些老里弄幸存,1932年建成的老巷子同興里就在家附近。老巷子居民已新,氣息依舊,常有拍電視電影的班子在這里取景。父親和我有事無事,沿巷子北頭到南頭來回溜達。誰家蜂窩煤爐上土罐子煨著藕湯,誰家一桌麻將打得噼里啪啦響,誰家罵孩子“個板麻養的”——經典漢罵。老人們坐在墻跟閑話,冬曬日頭夏乘涼。四百一十二步,父親方步丈量,故意踩上誰家故意潑在路當中的藥渣子,幫忙一樣。二十一根,我細數飄動萬國旗的晾衣桿,躲著從濕衣服上落下的水。短短巷子,萬千世相,像我在書中讀到的九十九篇短文,作者以身體行走,用靈魂吟唱,無不善哉美哉。
寫下這些文字時,珠穆朗瑪腳下發生強震,震散了我的云淡風清。活著,走著想著,原是沉沉甸甸的主題,如生命質地。我們都是幸存者,已無可選擇的在路上,一呼一吸,有常無常,生命呼嘯而過。活著就好,永不放棄就好。
“向之所欣,俯仰之間,已為陳跡”。蘭亭不在,羲之的吟唱猶在,我們的行走還在,走著想著的方式還在。目標在哪里?走到遠方還有遠方。過程而已。而已而已。
趙虹 女,生于小城安陸,畢業于湖北美術學院。愛旅行,愛公益,多年在繪畫、文學、音樂領域游走。現居武漢,任職期刊副主編。
來源:程遠微信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