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岸之觀》序言
洪子誠
“中國新詩研究叢書”已經(jīng)出版的著作中,孫曉婭編著的《彼岸之觀——跨語際詩歌交流》有點“另類”。它不是嚴謹、系統(tǒng)的研究論著,里面的主要篇幅,是首都師大中國詩歌研究中心這些年舉辦的外國詩人講座,和中外詩人、翻譯家交流、對話的現(xiàn)場實錄(書中也收入若干詩人、翻譯家有關(guān)中外詩歌交流、翻譯的論文)。講座、對話這些活動,由孫曉婭博士單獨主持或與其他學(xué)者、詩人合作主持。現(xiàn)在,她將這些實錄匯集出版。這本書內(nèi)容豐富,富有啟發(fā)性,值得細心閱讀。下面是我的幾點讀后感。
首先是有關(guān)新詩合法性方面的。其實,《彼岸之觀——跨語際詩歌交流》沒有任何篇幅討論這個問題。中國新詩已經(jīng)百年。百年雖是歷史一瞬,但對“當事人”來說也足夠漫長。令人尷尬的是,百年“老叟”常常陷于身份未明的危機之中,有時還擔(dān)心報不上“戶口”。這個情況現(xiàn)在有了改變,即使懷有偏見的也不得不承認:它就在那里!詩人和讀詩者這方面的焦慮得到緩解。這個判斷,從《彼岸之觀——跨語際詩歌交流》中也能得到間接支持。中外詩人、翻譯家的這些對話,他們對中外詩歌寫作和翻譯問題的探討,側(cè)面顯示的信息是:新詩已經(jīng)有了豐厚的藝術(shù)積累,確立了自身的傳統(tǒng),出現(xiàn)了成就卓著的詩人。新詩的存在,既無須以是否“繼承”古典詩歌作為前提,也不必征引外國(西方)詩歌作為依據(jù)。就如有的詩人指出的,它的評價標準,由新詩自身的“傳統(tǒng)”給出。從書中的對話實錄中可以看到,中國詩人在中外詩歌交流中已不再總處于被動、仰仗影響的弱勢位置。他們中的優(yōu)秀者已有足夠心理能量、知識儲備和藝術(shù)才能,來參與這種平等的對話。在成為域外詩歌創(chuàng)造的參照物上,不僅中國古典詩歌能夠承擔(dān),新詩也已加入其中。
另一個感想是,在詩歌批評、研究(包括詩歌史寫作)上,除了系統(tǒng)、嚴謹?shù)膶W(xué)者論著之外,詩人、翻譯家的談?wù)撛姼鑼懽鹘?jīng)驗的文字,也值得重視。這里說的重視,不僅指它們?yōu)檠芯空咛峁┍尘靶缘馁Y料。2014年10月在臺灣清華大學(xué)舉行的兩岸詩歌研討會上,我的發(fā)言談到,由于詩歌這一“文類”的性質(zhì),詩歌批評、研究,包括詩歌史寫作應(yīng)該有多種方式。沒錯,尋找規(guī)律、條理化的研究論著自有它的價值,但是,更多基于詩歌寫作實踐的,能容納并有效處理感性細節(jié),呈現(xiàn)為抽象概括遮蔽的情景、思緒、精神氛圍的著述,也十分重要。對于詩來說,我們解說的方向不僅需要聚攏,也需要開放擴散;不僅要談?wù)摗氨厝弧焙汀爸行摹保残枭婕氨姸嗟呐既缓退槠Wx著《彼岸之觀——跨語際詩歌交流》,印象最深的就是鮮活的現(xiàn)場感,和不避偶然和碎片的獨特發(fā)現(xiàn)。這個特點,既來自演講、座談、對話的方式,也來自參與者的詩人、翻譯家的身份,他們那種“置身其中”的視角。比起小說等來,現(xiàn)代詩是一種特殊,甚至是更“專業(yè)”的手藝和知識;詩歌寫作經(jīng)驗,是有成效的詩歌批評和詩歌史寫作的重要條件;因此,出色的詩歌評論家和研究者,應(yīng)該也是夠格的詩人。這個想法很可能被認為是偏見,但它卻既為歷史證實,也是我在新詩研究上屢陷困境的自省。
第三,新詩自它誕生之日起,與外國詩歌就關(guān)系緊密,“跨語際交流”一直在進行。自然,由于情況發(fā)生的變化,交流的性質(zhì)、方式也相應(yīng)不斷發(fā)生變化。從本書的交流實錄可以看到,在當前,有兩個方面的問題得到了詩人和學(xué)者的重視。一是在對話中發(fā)現(xiàn)差異的重要性,另一是詩歌翻譯的位置。詩歌翻譯在當前中國詩界得到特別關(guān)注,和中外翻譯的不對等情況有了某些改善,也和對翻譯性質(zhì)的理解有關(guān)。王家新引述巴赫金的話說得很好:“自我是一個禮物,他從他人那里得來。”而且,翻譯不僅是溝通的媒介,也是創(chuàng)造。人們越來越認識到,戴望舒不只寫有《望舒草》 《望舒詩稿》,還寫有《洛爾迦詩抄》。
至于說到交流對話,正如本書編著者孫曉婭說的,交流是一種融合;不同事物在“相遇”中互相發(fā)現(xiàn),互相支持;因為交流創(chuàng)造了“空虛”和“饑餓”。卡夫卡說,“讀一本非常重要的書,這本書在我們身上挖出了一個空虛”(本書中法國詩人克洛德·穆沙的引述)。“空虛”感是融合得以產(chǎn)生的前提。不過,在“全球化”的今天,交流也是在發(fā)現(xiàn)差異,以保護、發(fā)展文化、詩歌的多元性。了解陌生的對方,吸取滋養(yǎng),同時返回“本土”,返回自身,返回自身的語言、文化傳統(tǒng),返回寫作者內(nèi)心,以認識我們生存、創(chuàng)造的可能與意義,“讓生命在詩歌中重生”。斯洛文尼亞詩人阿萊什·希德戈談到,歐洲看起來是一個整體,其實像馬賽克一般,是由許多不同的小環(huán)境、小氣候構(gòu)成。首都師大詩歌中心這幾年對東歐詩歌的側(cè)重關(guān)注,對其中一些詩人的重點推介,體現(xiàn)了他們對詩歌一體化、同質(zhì)化趨勢的警惕,也體現(xiàn)了對哪些詩人、哪些詩歌傳統(tǒng)能與當前的中國詩歌建立更有效對話的識見。我們從這里得到的啟示還在于,當我們談?wù)摗⑻幚碇T如“華文詩歌”“現(xiàn)代漢詩”“中國新詩”等范疇下的事物的時候,如何也能警惕某種同質(zhì)化的思維方式,而細心發(fā)現(xiàn)、保護,并推動因地域、族群、語言、文化傳統(tǒng)形成的特殊性的成長。
要感謝首師大中國詩歌研究中心,感謝孫曉婭,這些年來他們做了這么多扎實、有意義的工作。可以想見,組織這樣的中外詩人、翻譯家的講座、交流對話活動,需要付出怎樣的精力。而論題的設(shè)計,對話的引導(dǎo)、闡發(fā),更體現(xiàn)了孫曉婭在深入把握中國新詩基礎(chǔ)上,對詩歌現(xiàn)狀的那種問題意識。“寫自己的故事”與為集體發(fā)聲之間究竟是怎樣的關(guān)系;“象牙塔”的說法是否是一種“政治上的發(fā)明”而“在藝術(shù)上并沒有價值”;主流社會追求贏利,崇尚迅速接受的知識,并非一目了然的詩歌對此是要抵抗,還是采取妥協(xié);多媒體、視覺詩歌、跨界寫作將給詩歌帶來生機,還是讓我們輕忽語言、文字的力量;網(wǎng)絡(luò)導(dǎo)致的自立門戶、自設(shè)標準的“文字共同體”的出現(xiàn),是開拓詩歌多樣性,還是破壞了建立共識的需求;在信息爆炸和交往頻繁的今天,人是否還有屬于自己的內(nèi)心空間,又如何定義這個空間;溝通、傳播的便捷,也加速語言陳舊化的速度,詩人將如何面對為“過時”寫作的恐懼……講座和對話中提出的種種問題,是當前我們所面對的,相信也是我們所關(guān)心的。
洪子誠,北京大學(xué)文學(xué)院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
多種聲音的奇妙混合
——關(guān)于《彼岸之觀——跨語際詩歌交流》
張清華
從1916年新詩的誕生至今,整整一百年了,詩歌在我們的時代,早已不再是天朝中土自我封閉的田園牧歌,而是不同文化互相激蕩和吸納的結(jié)果,詩歌的豐富與復(fù)雜,觀念的互滲與穿越,早已成為一種無法回避的新常態(tài)。
在設(shè)想歷史敘述的修辭構(gòu)成時,米歇爾·福柯提出了一個“多種聲音的奇怪混合”的說法,這一構(gòu)想原本是要體現(xiàn)歷史本身的具體性和多雜性,但其實用在理論和詩歌的總體性上,也同樣適用。《彼岸之觀——跨語際詩歌交流》便是這樣一部著作,它幾近為我們呈現(xiàn)了一個關(guān)于當代中國詩歌、關(guān)于世界和西方詩歌、關(guān)于詩歌史、先鋒派、經(jīng)典作家、詩歌翻譯學(xué)、詩歌寫作與交流等等在內(nèi)的一個“奇妙混合”著的學(xué)術(shù)場和思想流的集合,匯集了眾多中外詩人、翻譯家、學(xué)者們的講座、對話和交流的現(xiàn)場實錄,可謂是今年詩歌界、批評和翻譯界關(guān)于詩歌話題的一個思想的匯合。只消看一看這些名字,就知道它的豐富:凡爾日·佩、克洛德·讓克拉斯、克里斯提昂·杜麥、克洛德·穆沙、弗朗索瓦·德布津、阿萊什·希德戈、賀麥曉、喬治·歐康奈爾……他們的聲音幾乎涉及了關(guān)于詩歌和翻譯的全部領(lǐng)域,共同構(gòu)成了一個話語的棱鏡,發(fā)散著豐富的思想光芒與藝術(shù)色澤。
這本書的來源,是青年批評家,首都師范大學(xué)詩歌中心的孫曉婭,作為學(xué)術(shù)的組織者和總策劃人,在近年中組織的數(shù)十場中外詩歌交流活動的學(xué)術(shù)結(jié)晶,她開闊的國際視野和矢志不移的學(xué)術(shù)抱負,也已贏得了詩歌界和批評界的認可,以及高度的贊譽。當然,值得贊佩的還有她出眾的學(xué)術(shù)調(diào)度能力,參與這些活動的樹才、高興、李金佳、明迪,還有王家新等,也都是重量級的詩人和翻譯家,他們既是參與者,當然也是最好的媒介,可以將以往橫亙著語言和文化溝壑的中外詩歌界,密切地聯(lián)通起來。
進入這個棱鏡的世界,我們會更強烈地感到,中國新詩已經(jīng)可以確證地獲得了它存在和發(fā)展的邏輯。不同語際的思索與對話,正碰撞出更加寬闊的界面,和意想不到的啟示,無論是契合還是反撥,我們都可以近距離地在對方的文化鏡子中看到新的可能,并重新認識著我們自己。這種交流既是相遇和尋找,同時也是自我的再度發(fā)現(xiàn)和確認。除此,該書還給出了一個啟示,即有關(guān)詩歌的理論和批評,可能最終都無法與寫作脫節(jié)——書中幾乎所有批評與翻譯家都是詩人,而所有的詩人也都擁有著理論的見地與建樹。這不止使得他們的見解更具穿透性和魅力,也使此書更具有話語的彈性、詩意與可信度。
幾年前在一次訪談中我曾經(jīng)提到,我們現(xiàn)在面臨的是一種外觀上真正的“大亂”局面,但不同層面和方向的寫作者們,也正是在這樣一種“失序”的狀態(tài)中找到了自由,新詩在誕生一百年之后,終于迎來了多元和自在的生態(tài),而且在語言、形式和內(nèi)在的美學(xué)觀念上都孕育著新的變化。我樂觀地認為,一個漢語詩歌的繁盛時代就要來了。
對那些視野寬闊的人來說,《彼岸之觀——跨語際詩歌交流》自然值得一讀,對那些想了解詩歌的現(xiàn)狀與邊際的讀者來,更不失為一個憑借和契機。
張清華,北京師范大學(xué)文學(xué)院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副院長
無限啟迪的張力
——關(guān)于《彼岸之觀——跨語際詩歌交流》
羅振亞
中國新詩萌生的引發(fā)模式,和眾多詩人匯入世界詩歌潮流的事實,雙向證明全球化語境中“對話”的重要,賦予了《彼岸之觀:跨語際詩歌交流》集束式成果展示以非同尋常的價值,而講座、交流、隨筆等充滿細節(jié)又極具現(xiàn)場感的蒙茸、鮮活狀態(tài),則使一個一個“問題”研討落到了實處。
論著抓取的詩與傳統(tǒng)、詩與語言、詩與翻譯、詩與民族及地域等話題,均為中外詩學(xué)體系建構(gòu)的核心之維,其中的一些觀點雖非定論,有的還不無商榷的余地,卻能夠在觀念和方法上進一步引發(fā)讀者的思考,而這恰恰是學(xué)術(shù)研究最重要的魅力所在。
擺脫過度倚重西方的“移中就西”的研究立場,一改影響研究、平行研究為中外跨語際平等對話的交流方式,并在交流中堅持主體個性的自覺,與擴大漢詩研究的視角和疆域同步,力避中外對話時“失語”的思維,也使論著獲得了無限啟迪的張力。
羅振亞,南開大學(xué)文學(xué)院教授、博士生導(dǎo)師、副院長
《彼岸之觀》后記
孫曉婭
立足跨語際交流的全球化視野,將六年來在首都師范大學(xué)中國詩歌研究中心主持的講座、研討會錄音以及相關(guān)隨筆整理出來,以期更多讀者分享,是我多年的心愿。
本書分三編,上編為我主持的中外詩人講座:外國詩人講座的主題多為命題或半命題,中國詩人的講座系近年在首都師范大學(xué)組織的“外國詩歌與我”系列成果。來自不同國家和地區(qū)、經(jīng)歷迥異的詩人從個體的詩歌際遇、精神向度、深切的生命體驗談起,主題各有側(cè)重并自成體系,涉及詩歌功能、審美旨趣、技藝策略、詩性機制、生產(chǎn)閱讀、出版?zhèn)鞑ァ嶒灨镄碌戎T多方面。每場講座生動可感、風(fēng)格迥異,本土與異域比照、傳統(tǒng)與現(xiàn)代兼容、規(guī)范與創(chuàng)新交織。主講人多立足此岸觀瞻彼岸,從不同維度彰顯了他們的主體情懷、宏富的詩學(xué)儲備,對詩歌意涵與形式的理解與創(chuàng)造,對時代生活、哲學(xué)文化、地緣生態(tài)、民族宗教等焦點議題的探察。上編猶如不同小宇宙的匯合體,個體智性的光芒熠熠于詩歌澄明遼闊的星群之列。
中編收錄了我近年在首都師范大學(xué)中國詩歌研究中心舉辦的三屆 “北京國際詩會”和首屆“國際駐校詩人”討論會、以及幾場中外詩人主題對話的錄音整理,它們均屬國際協(xié)同合作。召開這些研討會的初衷出于如下思考:吸納盡享跨語際交流的文化資源與互動空間;梳理挖掘中外詩人共同的精神血統(tǒng)與差異訴求;促進中外詩人之間的溝通,搭建多方位比較研究的平臺。為保證討論的有效性,每場研討有針對地邀請二十余位嘉賓,圍繞設(shè)定的元話題,但是不拘囿于此,議題的復(fù)雜性、觀點的個性化、思想的深度在活躍而緊張的氛圍中被激發(fā)出來。從這些討論中我們感受不到影響的焦慮,鮮見翻譯的隔閡與語言的障礙。略有遺憾的是,部分議題因為現(xiàn)場時間所限,未及深入展開,有待讀者繼續(xù)探討。在場感、后延性、開放的姿態(tài)、前瞻的眼光是本編的獨異之處。
下編收錄的是與前兩編相關(guān)的隨筆和論文,側(cè)重外國詩歌的中譯和中國詩歌的外譯等翻譯問題,偶有兼顧中外詩歌的品鑒與評論。在中國現(xiàn)當代譯詩界,外國詩歌的中譯自陳獨秀1915年在《新青年》第1卷的翻譯始,歷時百年,各方面都比較成熟,相形之下,中國詩歌的外譯顯得薄弱,始終不見格局。漢語的結(jié)構(gòu)與西方語言差別很大,中西方詩人的思維方式也不盡相同,由此,自新詩發(fā)軔以來,少有外國詩人、學(xué)者熱衷并投入中國詩歌的外譯工作。在本編擇錄的三篇研究中國詩歌外譯的文章中,來自德國、美國、克羅地亞的詩人、學(xué)者、翻譯家分別論述了漢詩在目標語環(huán)境中接受與變異的內(nèi)外因由,關(guān)涉到文體因素、思想因素,語言因素、時代因素,以及原語與譯語的結(jié)合。本編實為拋磚引玉,以期引起學(xué)界對漢詩外譯及相關(guān)研究的重視。
本書旨在為當代漢語詩歌的創(chuàng)作與研究提供新異的經(jīng)驗、豐盈的思想資源、流動的審視維度,活躍并擴展新詩的研究與建設(shè)工作。在整理書稿的過程中,我盡量剔除口語的重復(fù)、跳躍、錯雜,討論中的語義散失、無邏輯、零碎不連貫等問題,盡可能再現(xiàn)講座與對話的精義和主脈。此外,本書呈現(xiàn)了首都師范大學(xué)中國詩歌中心這些年為開展中外詩歌交流所做的工作,每場學(xué)術(shù)活動都貫穿著明確的學(xué)術(shù)理念——古今詩歌并重,中外詩歌互動,置身國際前言領(lǐng)域,深化中國詩歌研究。作為這些活動的組織者,很幸運能將我個人點滴的學(xué)術(shù)理想,對中外詩學(xué)粗淺的思考滲透在講座的開場與結(jié)語之中。
經(jīng)由北京大學(xué)洪子誠教授的推薦,本書得以納入“北大·中國新詩研究叢書”,特此表示感謝!誠然,本書凝聚了一批同仁的心血與汗水,銘感多年來切實支持、協(xié)助過我的師長、詩友、責(zé)編、學(xué)生,在此一并致謝!
截至目前,我個人或與詩友合作組織的詩歌講座、討論遠不止本書收錄的內(nèi)容。鑒于篇幅等因素,僅挑選有代表性的一部分先整理成文,至少可以避免它們遺失于虛空的片影中,留存住過往的詩歌記憶和有價值的資料。從工作的持續(xù)性看,這不是本書的終點,我們相信,經(jīng)由跨語際的交流、啟示與滋養(yǎng),詩歌必將遒勁地生長,我們?nèi)栽谛羞M中。
孫曉婭,首都師范大學(xué)中國詩歌研究中心副主任,碩士生導(dǎo)師,《中國詩歌研究動態(tài)》執(zhí)行主編。出版學(xué)術(shù)專著《跋涉的夢游者——牛漢詩歌研究》、《讀懂徐志摩》。編撰《中國新詩研究論文索引(2000-2009)》,主編《中國新詩百年大典》(第7卷)、《新世紀十年散文詩選》、《牛漢的詩》等。曾在《新華文摘》、《文藝研究》、《人民日報》、《光明日報》、《中國現(xiàn)代文學(xué)研究叢刊》等刊物上發(fā)表論文數(shù)十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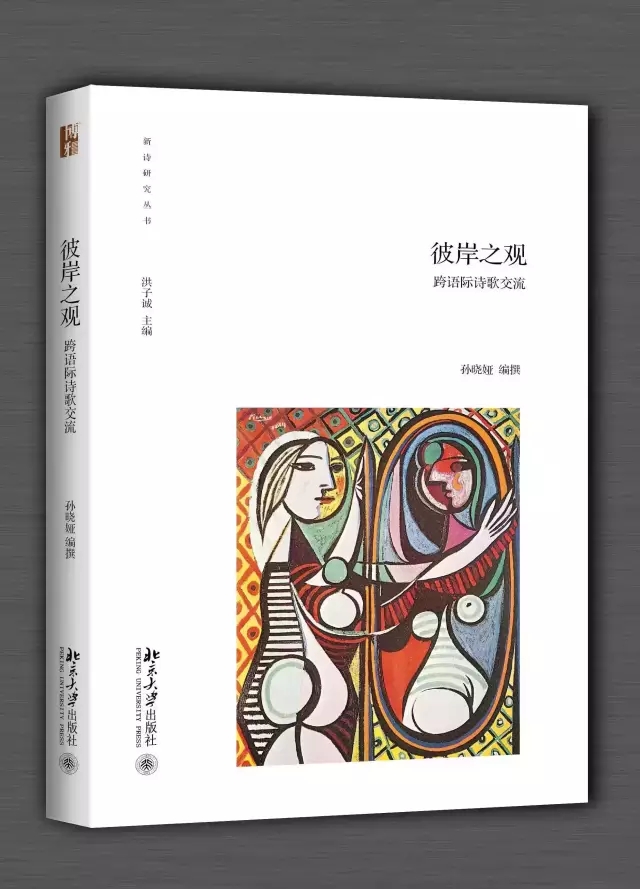
《彼岸之觀——跨語際詩歌交流》,孫曉婭編撰,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2016年1月第1版。
來源:詩刊社


 純貴坊酒業(yè)
純貴坊酒業(y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