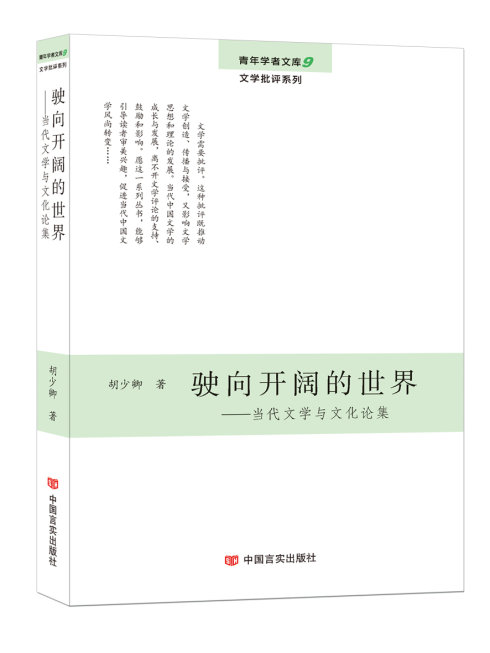
后記
胡少卿
通讀此書,會發現其中對于“漢語的手工藝人”這個說法近乎絮叨的強調。我看文學作品,若發現語言粗疏,便提不起興趣再讀。這種對文字的要求,也貫穿在自己的寫作中。不特寫詩,我之于著文,也算個“苦吟派”,總是力求語言的精當,概念的準確,行文的清晰簡潔,內容的言之有物。往往總是確實對自己的主張有了把握方才下筆,力戒粗暴浮泛、人云亦云。收入本書的文字,除掉寫作時間較早的三兩篇(2003年,2007年)語言還嫌輕率,其余部分(大部分完成于最近的五、六年)是經過了精心打磨的。不論前期準備之繁瑣鋪張和吹毛求疵,即具體到行文,亦往往推敲至自己都不堪忍受方止。盡管這些文章從高處俯視,意義有限,但具體到每一篇的誕生,說是嘔心瀝血也不為過。曾經在深夜著文時,寫下自傷自憐的詩句:在下雪的晚上/像一根蠟燭/讓人心疼又虛無地燃燒著。學者亦當如工匠,制作的器具應追求牢靠、耐用,歷久彌新。這是我理想中的作品形態。
曾有人問我學什么專業,答曰中國當代文學,又繼續追問:研究哪一段?我只能撓頭。這樣的問話體現出,研究者專注于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似乎已成常態。但我卻一直很恐懼這樣的細分,像恐懼高樓上那些密密麻麻的小窗格子。人文科學與自然科學很不同的一點是,自然科學以專精為要,而對于人文科學來說,廣度就是深度。陸游說“汝果欲學詩,功夫在詩外”,《紅樓夢》里的對聯是“世事洞明皆學問,人情練達即文章”。文學是人文學科中尤其不應該被專業化的,它應該沾染生活、生命、歷史、時代的精氣神兒,成為有源之活水。顧城有一本詩集的名字叫“海籃”,文學也像是海水做成的籃子,它有自己的疆域,同時,又和廣大的海水連成一片。在本書中,我嘗試打破文學與政治,文學與幾何,文學與電影,文學與大眾文化,當代文學與古典文學、外國文學的界 限。文學絕不是專業、圈子內部的事情,而是關涉每個普通人的精神生活的元素性存在。在各種現代細分讓人變得越來越傾向于機器的時候,文學和文學研究應該跳出藩籬,“駛向開闊的世界”。
我在大學時的導師是曹文軒教授,他同時是一位作家。他的文學批評事業充滿了對審美、直覺和感性的推崇,他復活了中國古代印象式批評的傳統。在校的時候,并不知道從老師那里究竟學到了什么;離開學校近十年,才發現學問風格的影響還真是潛移默化。對文學作品的眼光、感受力,是我唯一還有些自信的地方。本書滲透了對各種作品文本的感性認知,它的短板在于缺乏理論提升。因為一直寫詩,我簡直是有些偏執地想保護自己的感性,避免養成“分析癖”。我曾經被干癟枯燥的理論文字折磨,但思辨的力量、理性之美對于學術文字必不可少。理想的學術文章應該是蘇東坡評陶詩那般“質而實綺,癯而實腴”,既有骨力又有豐沛的感性基礎。這同樣是未來的追求。
對語言表達的在乎,對開闊的向往,對感性的借重,是我能想到的本書文字的共性。
感謝老友師力斌,感謝出版人王昕朋老師和責編肖鳳超老師,是你們的支持與細致工作,使本書得以誕生。感謝每一個目光落到這行字上的人——讓我們一起用思考與言說穿越生命的長夜。
2016年4月12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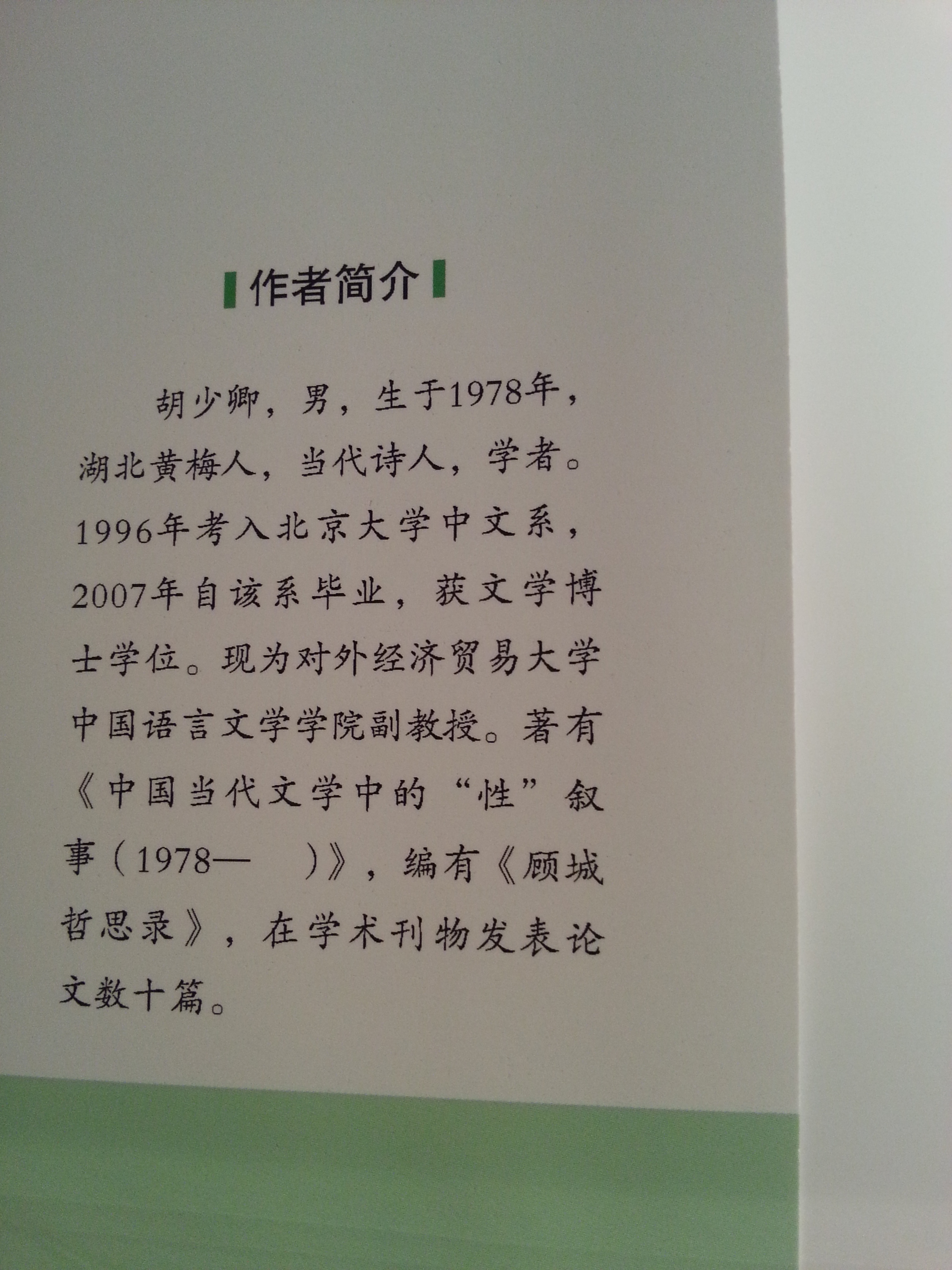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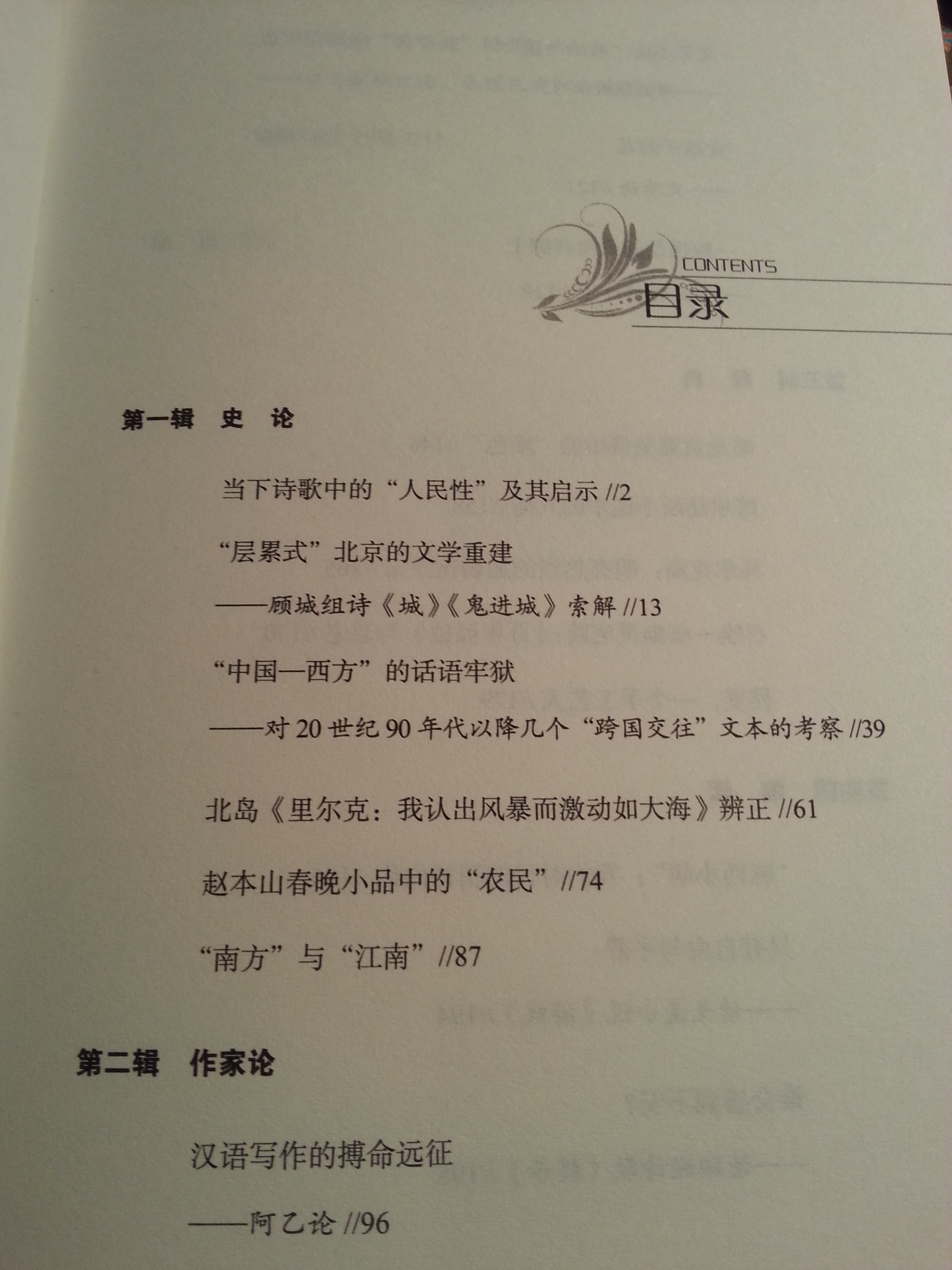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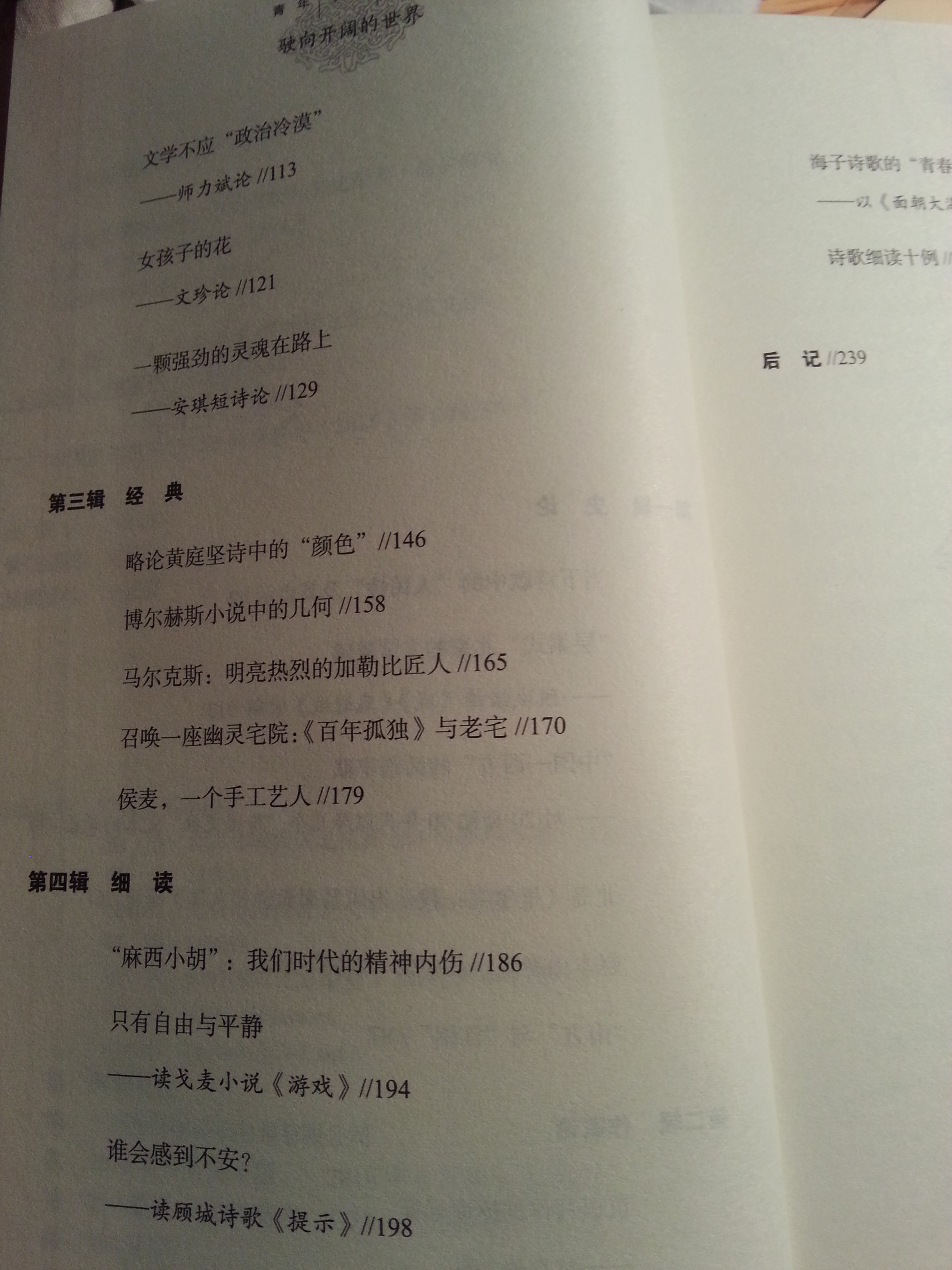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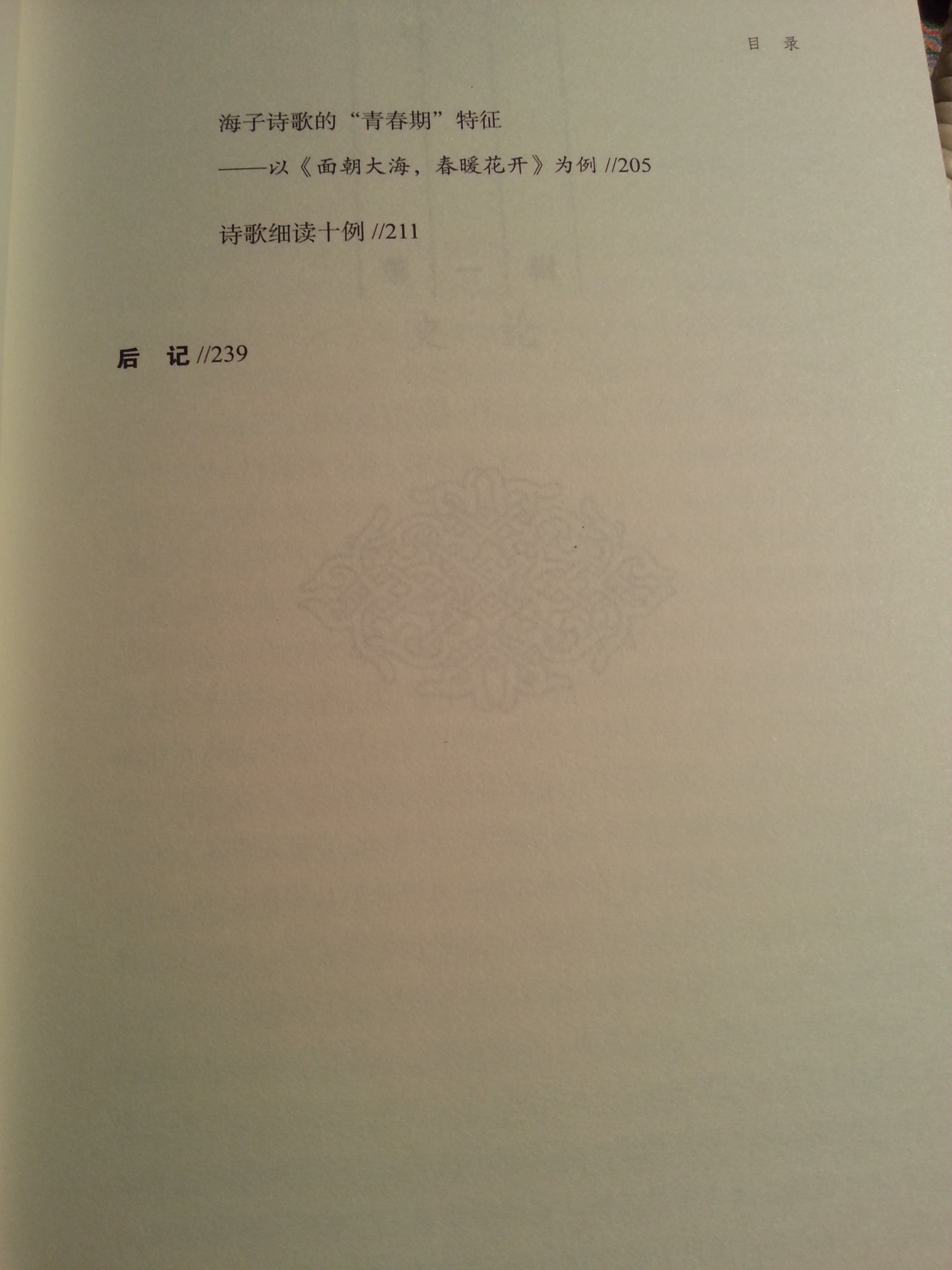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