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詩歌來感受巴蜀地理 著名詩人梁平詩集《家譜》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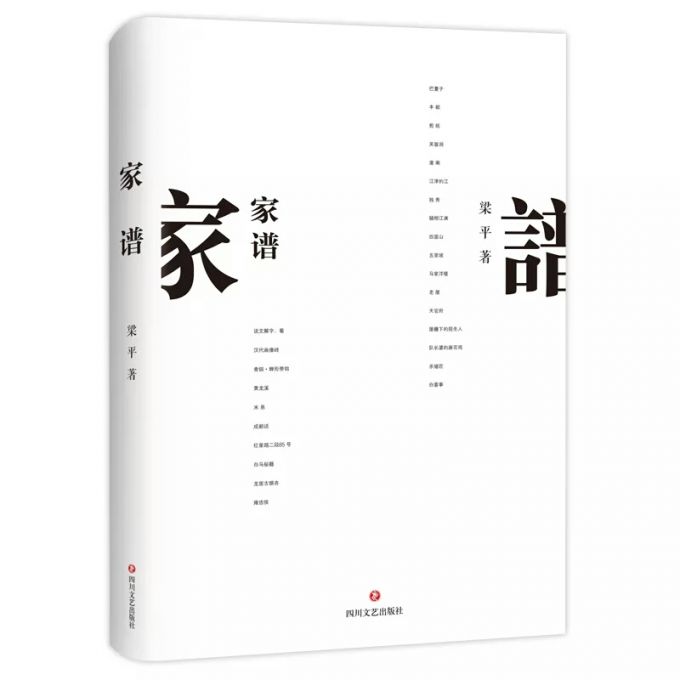
導(dǎo)讀:寫故鄉(xiāng)的作品幾乎占了梁平所有創(chuàng)作的二分之一。而在書寫故鄉(xiāng)的詩歌中,他比較刻意地把著力點(diǎn)用在正在消弭的那些人文記憶上。
“從殷商一大堆甲骨文里,找到了‘蜀’。東漢的許慎說它是蠶,一個(gè)奇怪的造型,額頭上,橫放了一條加長的眼眶……”近日,著名詩人、《青年作家》主編、成都市作協(xié)主席梁平的最新詩集《家譜》出版,這本詩集中收錄了梁平近年來對家鄉(xiāng)重慶和目前生活地——成都的詩樣解讀,“我的寫作有很強(qiáng)的地域性,我是希望構(gòu)建我自己的詩意地理學(xué)。我很多作品會(huì)刻意地寫重慶,寫成都。我這些年‘流竄’于兩個(gè)城市之間,已經(jīng)忽略了家鄉(xiāng)的概念,成都、重慶都是我的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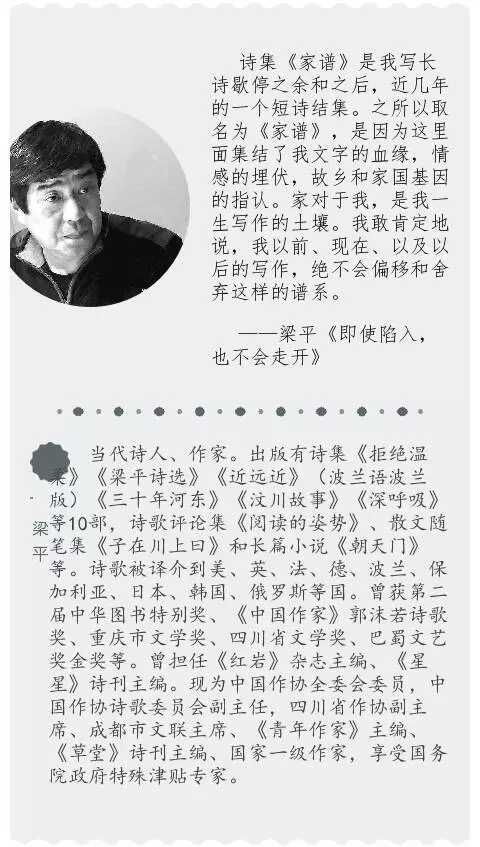
美國詩人布羅茨基說,詩歌是對人類記憶的表達(dá)。梁平用他的作品印證了這一結(jié)論。在他被列為很多大學(xué)科研課題的《重慶書》、《三星堆之門》、《三十年河?xùn)|》中,在眾多詩人網(wǎng)友中廣為流傳的諸多短詩《成渝高速》、《棉花街》中,都無一例外深深地烙著故鄉(xiāng)的印記,“這個(gè)不奇怪,作家的寫作來自自己的生活經(jīng)驗(yàn)。而我的故鄉(xiāng)就是巴與蜀。”
他曾經(jīng)在《重慶:城市血型》中解讀巴,也在《說文解字:蜀》中解讀蜀,寫故鄉(xiāng)的作品幾乎占了梁平所有創(chuàng)作的二分之一。而在書寫故鄉(xiāng)的詩歌中,他比較刻意地把著力點(diǎn)用在正在消弭的那些人文記憶上。比他在寫《棉花街》時(shí)寫道:等到我在棉花街上走的時(shí)候,已經(jīng)見不到街了。一條青石路油亮光滑,那是清末遺留的一條長辮,順坡而下的民房,就像一地倒扣的黑色瓜皮帽,一百年忘了撿拾……
《家譜》中,收錄了梁平近年來150余首詩歌,全書分為“為漢字而生”“蜀的胎記”“巴的血型”三個(gè)部分,“大部分是關(guān)于成都、重慶的詩歌,也有一些其他城市、景點(diǎn)的作品,有一種家國情懷。”梁平說,之所以取名為《家譜》,是因?yàn)檫@里面集結(jié)了自己文字的血緣,情感的埋伏,故鄉(xiāng)和家國基因的指認(rèn)。“家對于我,是我一生寫作的土壤。我敢肯定地說,我以前、現(xiàn)在、以及以后的寫作,絕不會(huì)偏移和舍棄這樣的譜系。”
一個(gè)人的出生地和成長地是這個(gè)人一輩子的印記。梁平出生于重慶,從小在山城長大,寫詩、生活。2001年春天,梁平來到成都,擔(dān)任了《星星》詩刊總編,又在2013年當(dāng)選了成都市作協(xié)主席。在梁平看來,自己的寫作有很強(qiáng)的地域性,并以此來構(gòu)建自己的詩意地理學(xué)。雖然重慶和成都相隔不過幾百公里,同屬巴蜀文化的一脈,但梁平認(rèn)為,這兩個(gè)城市卻是兩個(gè)風(fēng)格完全不同的,重慶陽剛、率真、大氣;成都陰柔、含蓄、滋潤。從文化意義上講,成都更適合做文化,成都的土壤也更適合文化的生長和繁衍。
如果說重慶是梁平的故土,而成都則是他的樂土。梁平說,在成都寫作像拐棍一樣,成為他精神和身心最大的滿足和支撐。
正是這樣的土地情懷,梁平的許多詩作都跟地域有關(guān)。他曾在詩集《深呼吸》中專門寫“成都詞典”,寫成都的《紗帽街》《惜字宮街》《爵版街》等10首。
又比如他寫《成渝高速》:“成渝高速/是我惟一不能感受飛翔的速度/橫臥在成都和重慶之間/混淆我的故土……”;
《回家》:“成都有一把鑰匙在手/重慶有一把鑰匙在手/往往一腳油門踩下以后/以為人在家里,手機(jī)卻開始漫游……”;
《成都:紅星路二段85號(hào)》:“站在窗口,看得見天上的三顆星星/一顆是青春,一顆是愛情/還有一顆,是詩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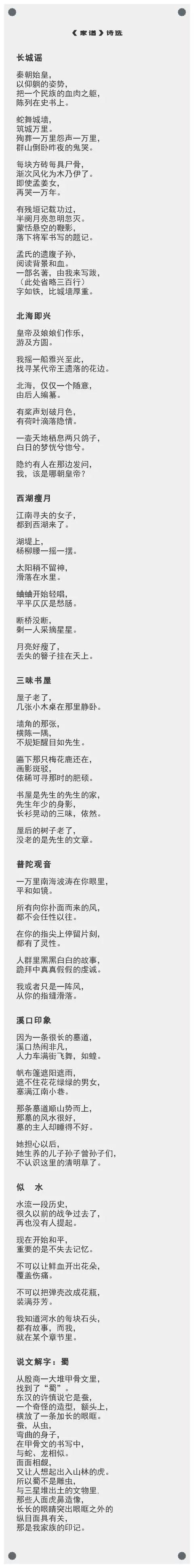
作者: 邱峻峰 伍文韜
來源:成都商報(bào)
http://www.yzs.com/zhongshibaodao/2017/10/26/5613.html


 純貴坊酒業(yè)
純貴坊酒業(y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