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在》詩訊‖胡亮詩話集《琉璃脆》近日由陜西人教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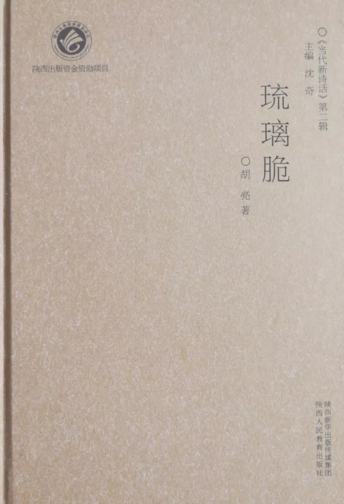
胡亮新著《琉璃脆》近日由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精裝出版。該書分為兩卷,上卷《屠龍術》,乃是詩學札記;下卷《窺豹錄》,乃是詩人叢論(論及六十六位當代詩人)。全書一百八十七頁,定價二十九元。
該書由茱萸博士作序。序稱:“胡亮兄此書,卷上內思,卷下外觀,又在此兩種類型之外,另開一條熔鑄古今、指點中外的路徑。”
該書由沈奇教授作跋。跋云:“胡亮此書語雖玄妙而自有來去,橫生逸出而思精慮細,看似散發亂服,實則正襟危坐,古今混搭,中西交嵌,復于分延與變奏中自成一家。”
該書乃是“當代新詩話叢書”第二輯之一種。“當代新詩話叢書”由著名學者沈奇教授主編,目前已經出版兩輯。第一輯收錄于堅《為世界文身》、趙毅衡《斷無不可解之理》、陳超《詩野游牧》、耿占春《退藏于密》和沈奇《無核之云》。第二輯收錄楊匡漢《長亭聽云》、簡政珍《苦澀的笑聲》、臧棣《詩道鱒燕》、泉子《詩之思》和胡亮《琉璃脆》。
包括《琉璃脆》在內的五部新著,不日即可在各大書店和網站購買。遂寧將在席殊書店等處舉行簽售活動。

胡 亮
huliang簡介
胡亮,生于1975年,詩人,文論和隨筆作家。出版論集《闡釋之雪:胡亮文論集》(言實,2014)、《闡釋之雪:現代詩人評論集》(臺灣秀威,2015)、《琉璃脆》(陜西人教,2017)、《虛掩》(安徽教育,2017),編著《永生的詩人》(北岳文藝,2015),主編《出梅入夏》(北岳文藝,2015)、《力的前奏》(白山,2015)。創辦詩與詩學集刊《元寫作》(2007)。參加第2屆青海湖國際詩歌節(2009)、第1屆洛夫國際詩歌節(2009)。獲頒第5屆后天雙年度文化藝術獎(2015)、第2屆袁可嘉詩歌獎(2015)。現居遂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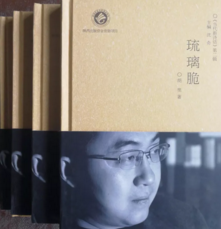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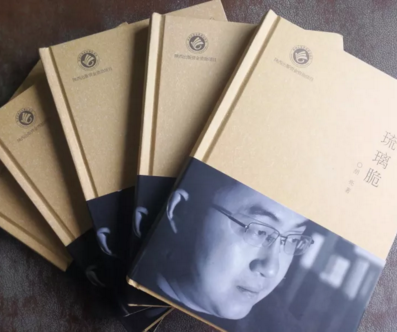
書 名:琉璃脆
作 者:胡 亮
出 版: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
目 錄
序言/茱萸
卷上
屠龍術(777則)
卷下
窺豹錄(66條)
1.孔 孚(1925-1997)
2.木 心(1927-2011)
3.商 禽(1930-2010)
4.痖 弦(1932-)
5.林 子(1935-)
6.昌 耀(1936-2000)
7.張新泉(1941-)
8.啞 默(1942-)
9.食 指(1948-)
10.北 島(1949-)
11.多 多(1951-)
12.胡 寬(1952-1995)
13.周倫佑(1952-)
14.嚴 力(1954-)
15.于 堅(1954-)
16.王小妮(1955-)
17.柏 樺(1956-)
18.夏 宇(1956-)
19.藍 馬(1956-)
20.歐陽江河(1956-)
21.劉以林(1956-)
22.王家新(1957-)
23.馬 莉(1959-)
24.莫 非(1960-)
25.吉狄馬加(1961-)
26.崔 健(1961-)
27.孟 浪(1961-)
28.王 寅(1962-)
29.虹 影(1962-)
30.麥 城(1962-)
31.普 珉(1962-)
32.凸 凹(1962-)
33.車前子(1963-)
34.西 川(1963-)
35.李亞偉(1963-)
36.鄭單衣(1963-)
37.馬 松(1963-)
38.楊 子(1963-)
39.草 樹(1964-)
40.榮 榮(1964-)
41.田 禾(1964-)
42.樹 才(1965-)
43.阿 吾(1965-)
44.杜馬蘭(1965-)
45.李青凇(1965-)
46.雷平陽(1966-)
47.余 怒(1966-)
48.伊 沙(1966-)
49.魯西西(1966-)
50.陳先發(1967-)
51.楊 鍵(1967-)
52.桑 克(1967-)
53.趙思運(1967-)
54.杜 涯(1968-)
55.安 琪(1969-)
56.朱 朱(1969-)
57.宇 向(1970-)
58.周云蓬(1970-)
59.孫磊(1971-)
60.譚克修(1971-)
61.李小洛(1972-)
62.唐 果(1972-)
63.葉麗雋(1972-)
64.韓 博(1973-)
65.王 敖(1976-)
66.鄭小瓊(1980-)
后 記 / 胡 亮
編后記/ 沈 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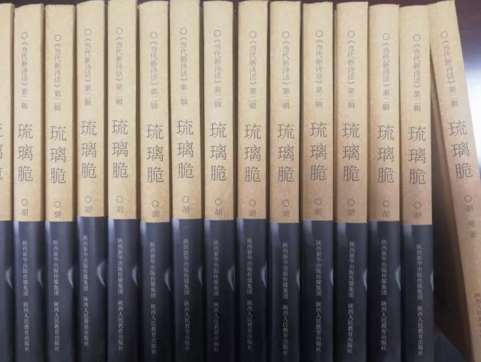
序 言

茱萸,
生于1987年,同濟大學哲學博士,研究方向為文化哲學、漢語詩學與現當代文學。著有評論集《盛宴及其邀約》,詩集《花神引》《爐端諧律》《儀式的焦唇》,隨筆集《漿果與流轉之詩》。曾為日本東京大學文學部訪問學者,兼任同濟大學詩學研究中心研究員。
可使“建安作者”相視而笑
——序胡亮《琉璃脆》
茱萸/文
胡亮大兄與我的文字之交,到目前為止,時間并不算長。他編同仁刊物《元寫作》,曾向我約過幾件手稿(《元寫作》有影刊詩人手稿的傳統),并多次接受我的推薦,選用過好幾位我看重的青年詩人之作品;我亦曾為之引介旅日詩人兼譯者虛坻,使她翻譯的兩位日本當代詩人,得以與該刊結緣。我曾向不少詩人、批評家和學者推薦這份刊物,倒不是因為與編者的這些交誼或往來,而是因為,客觀以論,它雖誕生于西南一隅之地,趣味、視野和胸懷卻皆足以列于當代之前沿。每次拿到《元寫作》,我最先翻看的是《編后記》,它們綜述當期內容,品評諸位作者,向各路詩人、學者和批評家的支持表示感謝,總能道來娓娓,溫情脈脈,毫無頭巾氣,但見淋漓的爽氣與豪氣,又有對詩之深情。這些文章,原擬收錄在《琉璃脆》中,稱為“讀象記”,許是因作者欲自謙此事為“盲人摸象”,在我看來,實在可視為“目無全牛”之后的游刃有余。由于體例原因,此部分內容在本書定稿付印時終未得附入,若有機緣,諸君或可徑看《元寫作》各卷。
當然,胡亮的長處不止在編輯這樣的一本刊物上,否則的話,未免太大材小用。他還是近年來崛起的詩歌選家(一句題外話:當代詩界盡多“主編”,而少有選家,實因此等人士只知蒐集諸家作品,印制成冊,冠以時髦之名目,而實無真正的編選思路與甄別之眼光),憑藉自身良好的詩學修為和判斷力,貢獻出不少別出心裁的編選集:以“英年早逝”之詩人為線索,編著《永生的詩人:從海子到馬雁》;以整理、保存當代一流詩人之作品為旨趣,遴選陸憶敏散落于各處之佳作,輯為《出梅入夏:陸憶敏詩集1981-2010》;以梳理地方文脈、考察百年川蜀詩人之創作成就為鵠的,主編《力的前奏:四川新詩99年99家99首》。如此這些,可見他的勤勉與專注,亦可見他在盡一名批評家的職分。
蜀中多人杰,尤其在文字一道,簡直占盡山川奇氣。單是胡亮所居的遂寧,就曾出過陳伯玉(子昂)和張船山(問陶),而這兩位都是我私心篤好的大詩人。前者于綺麗六朝流風余韻之中,初開盛唐之調,元遺山(好問)說,若論歷史功績,以黃金鑄其像都不為過;后者為乾嘉間蜀中第一詩人,所謂“性靈派”的殿軍,亦堪稱中國詩于清代臻于極致時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但胡亮并不像他的這兩位先賢那樣以詩人名世,我甚至都沒有拜讀過他的詩作(如果有的話)。不過,不自限于詩人身份未必是壞事,因為這樣的人杰地靈之地,并不缺足夠多的好詩人,做一名批評家,或許是當代詩更需要、也令他適得其所的角色。
川籍文人中不乏博學多才之奇士,不止是古代,觀之以當世,亦所在皆是,譬如鐘鳴和敬文東。前者是成名已久的優秀詩人,也是一位全能型的文人,以我觀之,他作為批評家和隨筆作家的那一面,對年輕一代的影響似乎更大;后者亦是第一流的批評家,雖也兼詩人身份,終是學者面目,他對其同代川蜀詩人的觀察與跟進,幾與他們的崛起、成名和逐步經典化相始終。與中原人士普遍之保守持重、穩打穩扎不同,蜀人中又多劍走偏鋒之士,神思飄蕩,路數玄妙而奇詭。蜀中才子也不同于江南軟糯風雅型的俊才,而是兼具博學與奇思的逸才。此一類逸才,早已無法用現代意義上之分類法——如詩人、學者或批評家之類——以限定之,他們自古以來亦不滿足于守成與循規蹈矩,往往能融匯貫通,于辭章文學一道,開破舊創新之局。除陳伯玉外,前有司馬長卿(相如),后有李太白,莫不是此等大人物。胡亮得巴山蜀水之滋養,仰先賢耆舊之高風,雖不以詩人名世,對與詩相關的諸多門類,卻用力甚勤,并浸淫于西學新知與國故交雜的思想之海,樂而忘倦。至于其批評之語體,亦能雜糅文言、白話、口語與翻譯體之特色,而成自家格調與面目。他非學院中人,無需靠學術論文來為稻粱謀,所以更容易反思并拋開“現代學術工業”中所形成的那套穩妥路數,而以一名傳統層面的文人或博雅意義上的知識人自居,無視體制的“繁文縟節”,直面問題的核心。
《琉璃脆》由兩卷組成,分別被稱為“屠龍術”和“窺豹錄”。前者是詩學札記,后者則是對具體詩人的點評;這是吾國詩學傳統中詩話之體的余脈。所以,將《琉璃脆》列入沈奇先生所主持之“中國新詩話叢書”,正得其宜。叢書首輯有耿占春、陳超諸先生之作,是大雅之聲;此一輯內,亦有唐曉渡、臧棣等一流批評家加盟。眾人齊以詩話為詩歌批評之形式,或可視為對吾國固有的印象式、點評式乃至感興式批評傳統的復活?此一路批評方式,乃是漢語詩界獨具特色、源遠流長之體例,甚至是中國談藝一脈之基本形態:從曹子桓(丕)之《典論·論文》,到鐘仲偉(嶸)之《詩品》、劉彥和(勰)之《文心雕龍》,至于司空表圣(圖)之《二十四詩品》、歐陽永叔(修)之《六一詩話》,再到《滄浪詩話》和《人間詞話》等等。投射在新詩領域,就有限的視野來說,除了這兩輯十位作者的大作外,無論是世紀之交出籠、戲謔中含嚴肅意思的“中國詩壇108將排行榜”(百曉生),還是針對同代詩人發言的《七零詩話》(秦曉宇),也同樣具有鮮明的個性。前者為清季盛行之“點將錄”體于網絡時代之新變,點評毒辣;后者更是才子文章,斑斕成錦繡,視角文辭俱佳,堪稱戛戛獨造。胡亮兄此書,卷上內思,卷下外觀,又在此二種類型之外,另開一條熔鑄古今、指點中外的路徑。
書中《屠龍術》的體例,介于詩學文論、札記與辭典/條目式書寫之間,而更近于雜感。若說是文論,少有具體論述和展開;若云為札記,卻無具體語境之依傍,只是隨興寫來,興盡而止;若說是詞條體(此體裁或可追溯到塞爾維亞作家米洛拉德·帕維奇的名作《哈扎爾辭典》,但那是小說;賈勤在前幾年出版的《現代派文學詞典》,則是辭典式批評集的典型),每則之前又不冠之以關鍵詞,但以數字標號而已。體例上與之相近的要屬臧棣的《詩道樽言》、《詩道鱒燕》系列,以及陳先發的《黑池壩筆記》,只不過這三位所關心的問題、切入的角度和行文的語氣均各有區別。此體文字,介于詩與學術札記之間,比前者理性一些,復又比后者感性。它的好處在于,只言片語皆可予人以啟迪,又為作者平日里的思考和靈感承擔著記錄的功能。它的問題則在于,因為缺少前后文的準備,這種體例的文字會對讀者提出一種更為私密的要求:語境的共享和理解的會心。它們往往引起爭議:步調合拍的人將之視為天籟而有知音之感,知識結構、語境和氣質迥不相侔的讀者,則常視此為囈語而將之打入另冊。功過之間,倒也難說得緊了。它更傾向于在打磨技藝過程中獲得的自我充實之感,一種書寫的快慰,或羅蘭·巴特所謂的“文之悅”。或許這才是作者將之命名為“屠龍術”的用意?
我對“屠龍術”的另一層理解,是更為常規的說法:世上已無龍之蹤跡,故而所謂“屠龍術”,早已是務虛之術。基于這層理解,《屠龍術》或許更應該屬于哲學而不是詩,它談論得更多的,實質上是思想,而不是詩的技藝或具體內容。倘若這樣來看,那么我們就能更好地理解此種體例之意義:它近乎哲學上的語錄體,譬如尼采的《蘇魯支語錄》,或者黎靖德集朱熹言論編纂而成的《朱子語類》。當然,胡亮關心的話題和行文的氣質,和朱熹、尼采這兩位大哲并不相侔,我們也不必要求批評家如真正的哲人那樣,參與對理念世界的建構與反思。亦有人將尼采這部極具狄奧尼索斯精神的著作,視為文藝色彩濃厚的散文詩,而《朱子語類》中也不乏讀之令人如沐春風之言,所以類似于此之文章(包括胡亮《屠龍術》中的這777則雜感),我們究竟是將之視為批評、札記、詩話還是散文詩呢?然而,這種分類并不見得有那么重要,我們完全可以將《屠龍術》視為一個跨文體裝置,它綜合了筆記、語錄、散文詩甚至思想碎片等諸多文體的特質。
列于卷下的《窺豹錄》,占了本書最大的篇幅。觀此命名,作者大概是取“管中窺豹,可見一斑”的意思,并不煩惱于論述的周全性,而只看某個瞬間的靈犀一指。這種篇幅不長、同樣近于詩話的評點式論集,與莊周(周澤雄、周實和張遠山的合用筆名)出版于世紀初的《齊人物論》相仿,只是篇幅整體更長一些,并且以稱美各位詩人為主,少有莊周此作中那種辛辣犀利的“酷評”——話說回來,對于漢語新詩而言,或許正應該如臧棣所提倡的那樣,好的批評應該多道人之善?《窺豹錄》以詩人為核心展開論斷,片語點睛,高論迭見,精彩之處令人擊節。從孔孚(1925-1997)、木心(1927-2011)、商禽(1930-2010)諸人,寫到我之同輩、作者之同鄉的詩人鄭小瓊(1980-),時間跨度極大,涉及詩人眾多——其中有廣為人知的,也有即使是內行讀者、若無特殊機緣都未必熟悉的詩人,如林子(1935-)、啞默(1942-)和胡寬(1952-1995)——亦可從中窺見作者涉獵之廣博與取舍之用心。篇幅和格式雖與《屠龍術》有別,卻是另一種辭典/條目式書寫,一如該輯原來的名目——“詞條”。
相比于《屠龍術》的汗漫無涯,我對《窺豹錄》中精審而細致的落實更感興趣,因為作者的哲思、洞見和會心,在這66篇文章中得到了更為切實的體現。其中論及韓博(1973-)的部分最契我心:“流俗有多寬,才賦就有多高。才賦有多高,賭注就有多大。韓博一邊永懷修辭的渴意,一邊飲鴆,即便最后淚灑意義的‘廢墟’,他也算得上一個傲眄流俗的試驗者和探險家。”韓博近十年來的寫作漸入險怪之途,固然淵源自蕭開愚等人,仍屬當代漢語詩中之變格,不為大多數人所理解。胡亮兄卻能作解人,足見眼光。其余如視柏樺為“身懷致幻術的罕見的文體家”,雅謔歐陽江河為“修辭學的老狐貍”,對姜濤以“嘟囔的儀式”來界定桑克詩風的抗辯,以及對詩人嚴力之詩歌史地位的重新界定,都給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不過,我并不知道《窺豹錄》的寫作背景為何,是出自于整體性的批評計劃,還是具有某種在批評對象選擇上的隨機性、偶然性或趣味化?目前呈現出的這66篇文章,應該只是某個龐大的批評計劃之“冰山一角”。
這部帶有強烈個人語調的“談藝錄”得以印行,實在是一樁可喜之事。出版方及編輯委員會對“新詩話”的倡導,也可見一番苦心:在現代學術體制日趨嚴密、人文學科愈加社會科學化的趨勢下,以這種古老的“中國文體”為標榜,整合一批同氣相求的批評家和學人,推出此套叢書,可稱功德無量。胡亮兄將他的這一冊取名為“琉璃脆”,又另見他的一番苦心:詩道久衰而嗣響微弱,如今我輩重拾古老的“詩話”之體,接武古人之精神,而對基于現代性的漢語詩歌進行分析、評斷和闡發,并不是一件易事。此事如白樂天(居易)《簡簡吟》中所謂,“大多好物不堅牢,彩云易散琉璃脆”,故而需要我們的格外呵護和持守。然而,琉璃豈止是脆,最終大抵也是要碎的,耶律晉卿(楚材)就在一首長詩中感慨道,彩云易消散而琉璃易碎,眾生則有四相之無常,而天人終受五衰之苦。這或許能作“琉璃脆”之說的別解。不過,正因為這樣,讀詩談藝才成為無常世界中我們能夠把握住的一點慰藉。這種慰藉,既見諸論者對詩人的闡釋,亦參證于論者與論者之間的相契:譬如我對胡亮兄此書的認同。這種情形,一如作者的鄉賢陳伯玉在《與東方左史虬修竹篇序》中說的那樣:“不圖正始之音,復睹于茲;可使建安作者,相視而笑。”
茱萸
公元2016年春夏之交寫定
《琉璃脆》后記
胡 亮 / 后 記
2015年,從秋天,到冬天,我準備了大量的水果和干果,——來自阿克蘇的駿棗,來自奉節的臍橙,來自煙臺和茂縣的蘋果,還有來自本地鄉間的核桃、花生和沙田柚。小箱,大箱,小筐,大筐,讓我犯了嘀咕:什么時候才吃得完啊?
恰恰就是在此前后,我較為正式地啟動了這本小書的寫作。本書各卷的某些段落或篇章,寫作時間還要更早。比如,《窺豹錄》,可以追溯到2007年的秋天;而《屠龍術》,則可以追溯到2014年的秋天,——那個秋天,我避居于閬中古城,窗口石榴高懸,伴了好些日夜。
《屠龍術》的寫作,始于某個朋友的諷諫,——在他看來,新詩研究就是“屠龍術”。“屠龍術”似乎最早見于《莊子》,這個朋友的原話,其實亦是莊子的原話:“技成而無所用其巧”。當這個朋友——曾經的詩人——深陷于美孜孜的生活,我卻較了真,偏要寫出《屠龍術》。世間本無龍,詩或如龍,——就讓我來白下些功夫。這篇詩學札記,想要端出幾小碟修辭論詩學,后來走了神,不免又羼入幾滴生態主義詩學。字里行間,西洋,古典,也有一點兒有意思的交錯。如果有讀者從中嗅出了劉勰、鐘嶸、司空圖、嚴羽、袁枚、劉熙載、王國維或民初學衡派的香味兒,我將樂于承認,并樂于與大家一起向他們致敬。他們代表了中國詩學正脈,留下了不廢的江河,——而我們,瞎了眼,斷了腿,分了心,已經取不回一瓢兩瓢。
我的老派的詩學立場,在《屠龍術》,已有顯現,而在《窺豹錄》,將有更加充分的顯現。《窺豹錄》,最初名為《詞條》,——到了現在,我仍然很喜歡這個標題。如果說《屠龍術》是詩學札記,那么,《窺豹錄》就是詩人叢論,共包括六十六個詞條:起于孔孚,訖于鄭小瓊。六十六個詞條,就是六十六篇小型詩人論,最短,僅有二百五十字,最長,也僅有二千五百字。用這么局促的篇幅來寫詩人論,似乎有點輕浮,但又那么值得一試。為此,我瀏覽了數以百計的詩集,閱讀了數以千計的詩篇,最后寫出了七萬五千字,——亦如一部小型的當代新詩史。民謠,搖滾,以及非主流音樂的文字腳本,向來是新詩史研究的盲區,這次論及崔健和周云蓬,或亦算得上是一個怯生生的提醒。當然,限于個人能力,寫作時間,此書篇幅,還有很多詩人尚未論及,擬于日后不斷增補,直到寫出可以單行的《窺豹錄》。
連年寫作,累次修改,終于完成這本小書,——當我走出書齋,才發現已是2016年的夏天。從秋冬,到春夏,時間過得又慢又快。那些駿棗,臍橙,蘋果,沙田柚,都已經慢慢吃光,只剩下來一點兒花生和核桃。這個寫作和修改的過程,高強度,高密度,鐫肝鏤肺,給我帶來了很大的焦慮,當然,也帶來了更大的歡暢。
這本小書定名為《琉璃脆》,典出白居易的一篇歌行:《簡簡吟》。琉璃脆,琉璃脆,既切詩話之體例,亦切詩人之命運,更切作者之立場:從一點兒西學,轉向一點兒古典學。雖然甚是泥古,卻已顧不得,——我不能化歐,更不能化古,那就先來泥古吧。
最后,必定要感謝沈奇教授和茱萸博士,——這兩位師友,前者著述宏富,可謂宿儒,后者頭角崢嶸,堪稱新星。茱萸博士惠賜序言;沈奇教授則玉成出版,——他將這本小書列入了《當代新詩話叢書》。這個叢書很快將出齊兩輯,共計十人十種,除我外,其他皆是當世名家。大河前橫,高山仰止,——忝列其間,不免頗為忐忑。多虧了沈奇教授的勉勵,讓我除了心虛,還能有那么一點兒膽大……
胡 亮
2016年4月19日
主編后記

沈奇,1951年生,陜西勉縣人;1970年代開始現代詩寫作和文學活動;已出版詩集《沈奇詩選》、詩學文集《沈奇詩學論集》(三卷)、詩話集《無核之云》及文藝評論集《文本與肉身》《秋日之書》等15種,編選《西方詩論精華》《現代小詩300首》《當代新詩話》(叢書)等9種。迄今在《文學評論》《當代作家評論》《文藝爭鳴》《詩探索》《二十一世紀》(香港中文大學)等海內外學術期刊發表詩歌評論及文藝評論一百余篇,代表詩論《角色意識與女性詩歌》入選《中國新詩大系》(謝冕總主編);部分詩歌作品和論文被翻譯為英、日、德、瑞典、捷克、拉脫維亞等國文字。現為北京大學中國詩歌研究院研究員;陜西美術博物館學術委員;西安財經學院文學院教授。
主編后記
沈奇/文
時隔兩年,“當代新詩話”叢書順遂出版第二輯共五卷,可謂“更上層樓”而佳話有續。
兩年前的2015年初夏,由趙毅衡《斷無不可解之理》、于堅《為世界文身》、陳超《詩野游牧》、耿占春《退藏于密》、沈奇《無核之云》聯袂亮相的“當代新詩話”叢書第一輯,歷經近三年選題策劃、約稿及編審,終于如期結集,全部精裝印制,由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隆重推出。
叢書出版發行后,雖因詩與詩學畢竟小眾且邊緣化,一時未能“盛名天下”,但也以其獨得之秘而“填補空白”【注】的“底氣”與特色,引起詩界、學界及出版界不小的反響,并入選“陜西新華出版傳媒集團2015年度十大好書”,進而榮登全國“2015年度好書榜”。
隔年五月,著名青年學者、詩評家劉波,在中文核心期刊《南方文壇》2016年第3期,發表《再造漢語詩學傳統——由“當代新詩話叢書”觀詩話寫作傳統的拓展》書評論文,認為“這種新詩話的創造,應當是對古典詩話精神最好的傳承與拓展。”并且,“讓這一文體充滿新的魅力”,“為我們帶來了令人耳目一新的再造漢語詩學傳統的別樣體驗”,而“成為這些年來,現代漢語詩人和批評家們,重新探尋詩話這一文體的集約型亮相,同時,也填補了近二三十年當代新詩話出版空白,以期促進對詩話的研究,實現其學術價值的拓展。”
由此,本套叢書從編選到出版,所秉持的“對當代中國詩歌美學景觀和精神圖譜,作另類文體解讀而創新說,成為承正脈而別開一界的重要文本”的核心理念,及其“促進現代漢語詩話之研究,現代詩學之發展,及相關學科研究方向與視野的擴展。同時,也為廣大詩歌與文學研究者和愛好者,提供一份別具參考意義與閱讀趣味的特色文本”(本書“選題策劃”語)的價值期許,得到了初步有效的實現。
詩雖小道,國魂所系。
時值新詩百年,革故鼎新、與時俱進中,如何于全球一體化大潮拍岸間立定腳跟,重新找回并確認我們的文化身份,實為功在后世千秋的大事。于此,內化現代,外師古典,重樹典律,再造傳統,正成為當下學界業界之共識。
同時,“轉基因”之新詩及其新詩詩學,經由百年“移洋開新”的“現代化”歷程,也終能得以在新的歷史節點,于部分學人和詩人的思與詩中,反顧漢語傳統,倡揚漢語氣質,更是值得珍重和守望的事情。
當此關口,“當代新詩話”連續結集出版,以求由個案之經典而成譜系之經典,板塊呈現,集約展示,“既填補歷史之缺憾,又經營目前之務實”(第一輯《主編后記》語),可謂得風氣之先,并由此開啟了一扇朗逸遠致的“窗戶”,而厚望可期。
第二輯“當代新詩話”叢書,還是以五卷結集。分別為楊匡漢《長亭聽云》、簡政珍《苦澀的笑聲》、臧棣《詩道樽燕》、泉子《詩與思》、胡亮《琉璃脆》。其“陣容”排輩,依序為1940年代、1950年代、1960年代及1970年代,“老中青”三代佼佼者,濟濟一堂而氣象分呈,各顯千秋。
同時,依循前例,各卷皆以序言開軒,或可添彩導讀美意。其中,臧棣、泉子、胡亮三位,各自邀約同道好友敬文東、耿占春、茱萸為文,皆是當代詩學界名家,且占春還是第一輯之《退藏于密》的作者,難得再續佳話。楊匡漢、簡政珍兩位,一者年邁,一者海外,遂由主編代為邀請云南大學王新教授、三峽大學劉波教授兩位新銳青年學者為序,如期斐然,成其圓滿。
本輯卷一,系楊匡漢先生歷時兩年,特別輯錄和補寫的詩話專著。先生資深,而文心謹重,一部《長亭聽云》,既與古典通合,又與現代呼應,格高思逸,不落凡近,如王新序文所言,無愧為“有性情、有品味,有識見的現代詩話”,且“特別葆有了古典詩話鳶飛魚躍、披美繽紛的人文生態”。同時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匡漢先生原本就是這套叢書最初動議及選題策劃人之一,最終復以作者加盟,玉成全局,實在堪可珍重。
卷二《苦澀的笑聲》,為臺灣著名詩人、詩學家簡政珍教授的精深之作。猶記二十年前初次拜讀政珍先生賜寄詩學新著《詩的瞬間狂喜》,以簡篇而約無窮之致,及其富于收攝與整合力的學者風范和超凡才具,確然不虛盛名而令人折服!二十年后,耿耿中隔海約稿,先生如期賜達而精深如故,正如劉波在序言中所指認的,“既有技藝的錘煉,又有深厚的人文情懷,精短的文字,在異質性轉換中帶著解析詩歌的普適性美學”。
卷三《詩道樽燕》,乃近年蜚聲海內外的北京大學詩人學者臧棣之作。機緣湊巧,二十二年前赴北大拜謝冕先生門下訪學時,得以結識臧棣,一握如故。此后雖來往不多,卻念念在心。“當代新詩話”第一輯選題申報時,原本六卷,其中就有《詩道樽燕》,后因臧棣忙中不及修訂,這才推至本輯。結集之前,此書內容已多有刊布,影響廣泛,其“對于現代漢語詩歌獨有的思考方式”,及其“在力度、深度上的巧妙性”,卓然有致,而“看似散漫、隨意,實則頗為考究、謹嚴,具有深遠洞察力的見解俯拾即是。”(敬文東語)
卷四《詩與思》,為青年詩人泉子潛沉多年、近于“病蚌成珠”式的詩學札記,深心靜力,博思約取,斷續發表,得同道矚目。此次結集,從原稿兩千多則中精選集萃,以“探究詩‘得以發生的秘密’為核心主題”,“植根于修辭轉義結構中的思想方式,”“以差異與等值替代思想的同一性,用轉義和生成性替代本質論,以悖論的修辭取代容易被誤解的概念體系”,“因此它不能被否定,也不能輕易證明對與錯,就像詩歌本身那樣,成為思想自由的象征。”(耿占春語)
壓軸卷五,系以民間學者而一舉全票斬獲第二屆“袁可嘉詩歌獎”之詩學獎的青年才俊胡亮,新就詩話專著《琉璃脆》。識胡亮多年,其集淵雅與謹嚴于一身的少年老成,及其在批評文體方面的孜孜以求,每每令人感佩。此次特約專候得之,“卷上內思,卷下外觀,又在此二種類型之外,另開一條熔鑄古今、指點中外的路徑。”(茱萸語)細讀之下,語雖玄寥而自有來去,橫生逸出而思精慮細,看似散發亂服,實則正襟危坐,古今混搭,中西交嵌,復于分延與變奏中自成一家,特地亮眼。
至此,二五一十,五載畢其一功,“當代新詩話”叢書竟得十卷集成,別開一界,略備格局,實在不勝欣慰!
—— 俗語說“好事成雙”,實則學問之道,“成三”許得方能筑基;兩輯行世后,竊想后續步程,或可“逗引”新知加盟,終成大觀,也未可知。
最后,代表所有作者,再次深切感謝堅持這套冷門叢書連續出版的陜西人民教育出版社!感謝從選題策劃動議到具體編校發行操煩,在在付諸愛意與辛勞的田和平總編、馬曉俠編審、各卷責編校對與裝幀設計家們!
—— 想來所謂“為他人做嫁衣”者,亦如著書立說做學問者一樣,事功于日常之外,總還是惟愿能有一二 “代表性”作品,足以立身入史,以釋理想與情懷所在,尤其對身處“邊緣地界”的出版人來說。但愿這套叢書的編輯出版,不但能實現這一“邊緣與中心對話”的愿景,還能為所有參與其中者,留下一份山高水遠的美好記憶!
是為“主編后記”。
沈奇
2017年3月20春分日
【注釋】 這里所指的“填補空白”,大體就近二三十年出版界而言。之前,自1985年1月至1991年5月,北京三聯書店出版社曾斷續出版過“今詩話叢書”共計11冊,按其出版時間先后排序,具體分別為羅洛《詩的隨想》、荒蕪《紙壁齋說詩》、流沙河《隔海說詩》、鄒荻帆《詩的欣賞與創作》、邵燕祥《晨昏隨筆》、綠原《蔥與蜜》、公劉《亂彈詩弦》、牛漢《學詩手記》、曾卓《詩人的兩翼》、謝冕《詩人的創造》、彭燕郊《和亮亮談詩》。特此補綴說明。
往期鏈接精選
《存在》詩刊‖發星:四川,中國詩歌發動機——30年來四川詩潮史綱 (末定稿)
《存在》詩訊 ‖ 《漢語地域詩歌年鑒》 征稿啟事
《存在》詩刊‖李村詩歌——所有的悲哀都緣于與石頭的距離(二十二首)
《存在》詩刊·陶春評論‖“禮”失之辭,鳴有七哀—— 關于宋光明組詩《一聲嘆息》及其它
《存在》詩刊‖張杰詩歌——重返不能逆行的辰光之河(十二首)
《存在》詩刊•張衛東評論‖重塑詞語生命的的尊嚴與榮光——淺談劉澤球的詩寫與文本
《存在》詩刊‖李永才新作速遞——千古一人蘇東坡 (組詩)
《存在》詩訊‖陶春文論集《品飲一滴詞語之蜜傾瀉的輝光》近日由北京燕山出版社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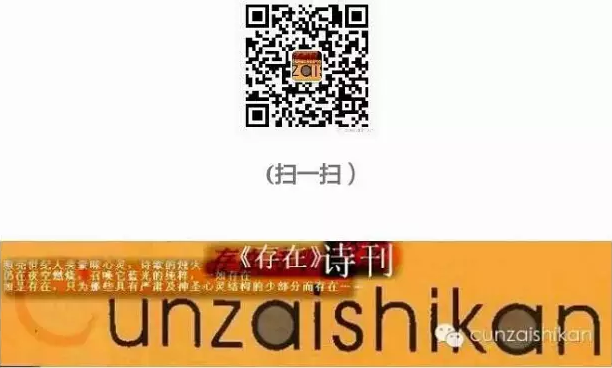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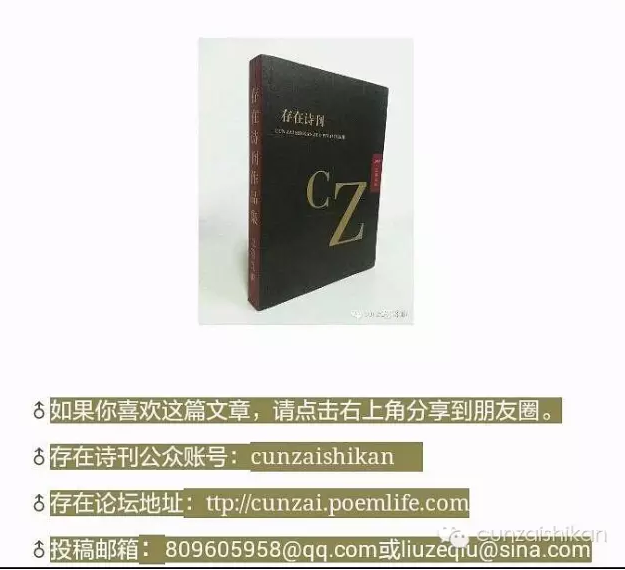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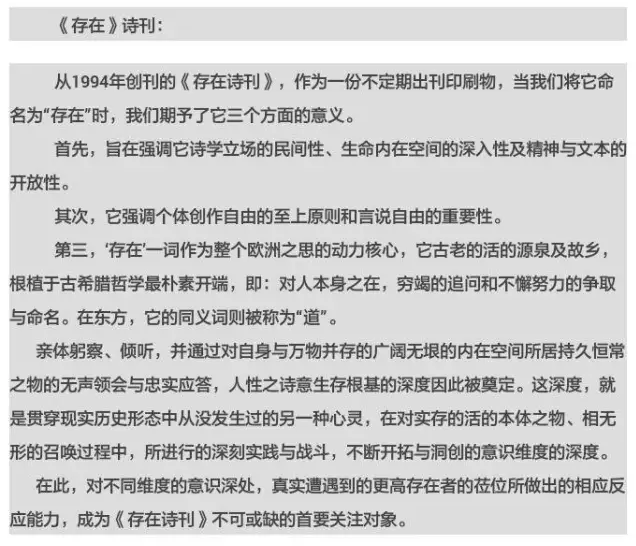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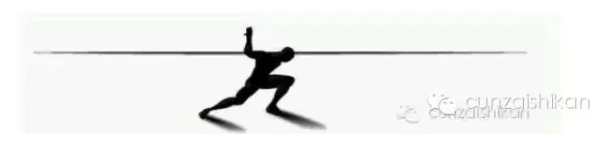
作者:存在詩訊 (原創)
來源:存在詩刊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A5ODY4NDAwNw==&mid=2652152704&idx=1&sn=a032d885c2dc3545866074934c214d62&chksm=8b6dde88bc1a579e8e72c79fa1060d71e85ba916b75e4e3b658b64c5fb86b059ff5ea72c722a&mpshare=1&scene=1&srcid=1031sWbMrHG3k88bxjzKho2O&pass_ticket=PH3n4x4s2vqsm6rAegTvIVcIKUsxu30ZAYKVHhs%2BTTDgap6kj0bJgXBivsMjSpZ0#rd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