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母親節,我又想起了媽媽
作者:冰 峰
一、推著媽媽的輪椅
又是一個節日。
我推著媽媽的輪椅走在客廳里,走在一段人生的路上。媽媽坐在輪椅上,輪椅上的兩個輪子安靜地轉動著,時光一圈一圈被甩到了身后。我想和媽媽說一些知心的話,可是媽媽答非所問。媽媽自顧自地說著她想說的話,從很久以前到很久以前,我一句也沒有聽懂。我想起了媽媽年輕的時候,勤快,麻利,不知辛苦……可是,媽媽老了,病了,沒有力量了。她斜靠在輪椅上,像一棵傾斜的樹,立在生命的荒野中。
媽媽坐在輪椅上,我停下了腳步。看著媽媽僵硬的表情和恍惚的目光,好像看到了家鄉的老房子,風刮著,房子在雨中搖晃。我問自己,如果媽媽沒了,我的“老家”還在嗎……已經九年多了,媽媽先是拄著拐杖,之后又坐上了輪椅。輪子轉動著,一圈一圈,好像要把所有活著的人都轉到另一個世界去。媽媽沒有害怕,也沒有哭,因為媽媽已經不會哭了。姐姐、姐夫、弟弟、弟媳一直攙扶著媽媽,像使盡力氣扶著一棵即將倒下的樹。他們氣喘吁吁,身體已經被壓彎。我站在北京,不能靠近樹,只能遙望媽媽,并在每個月的10號,向媽媽匯去一些生活費和看病的費用。為了讓媽媽這棵大樹不倒下,兒女們日夜消耗著身體里的能量。
我推著媽媽的輪椅,腳步沉重地走著。媽媽偶爾被身體的疼痛喚醒,她痛苦地呻吟著,宛如悲情的音樂從房間里響起。我被媽媽的呻吟聲扯得心痛……媽媽已經很少出門了,偶爾出去一趟,也只能坐在車里,包裹著厚厚的衣服。因為媽媽怕風,風會吹破媽媽的皮膚,會讓她更加疼痛。媽媽一直躺在臥室的病床上,煩躁的時候,也會被姐姐、姐夫、弟弟、弟媳、護工艱難地抬上輪椅,然后推進客廳。接下來,便是輪子的轉動,像鐘表一樣,一圈一圈的轉動……我雙手握著輪椅的把手,有節奏地抬起左腿、右腿,向前走。媽媽的滿頭白發和傾斜的身體在我的視線里晃動,我的腦際忽然浮現出兩個詞匯:監獄,酷刑。
推著媽媽的輪椅,望著媽媽傾斜的后背,我的體溫忽然開始下降……我想起了爸爸,想起了爸爸臨終前的一刻……爸爸是一個愛喝酒的男人,一輩子好像都沒有離開過酒。2010年11月13日,爸爸酒后摔倒,傷了肋骨。兩天之后,爸爸住進了醫院,這是他有生以來第一次走進醫院的病房,當然也是最后一次。爸爸很安靜,在醫院里輸液之后,就平靜地去了。他與這個世界告別的過程不到兩分鐘,簡單,快捷,沒有痛苦,來不及搶救,不麻煩兒女,沒有受一點罪……想到這里,我似乎不敢往下想了,否則,好像我在慶幸爸爸的死,似乎在說爸爸的死是一件好事,是一件讓兒女們高興的事情。我知道,這樣的想法是惡念,是不可饒恕的犯罪。
推著媽媽的輪椅,任憑時間一圈一圈向后轉動。媽媽疼痛的呻吟聲傳來,宛如屠刀飛起,一片一片,刺進了我的身體……我的假期結束了,可媽媽身體上的疼痛卻沒有結束。我多么希望我的媽媽像從前一樣,拉著我們姐弟三個人的手,哼著老舊的歌曲,走著,跑著,把快樂拋向天空,把時光一點一點甩在身后……
恍然間,媽媽好像已經從輪椅上站起,她又回到了年輕的歲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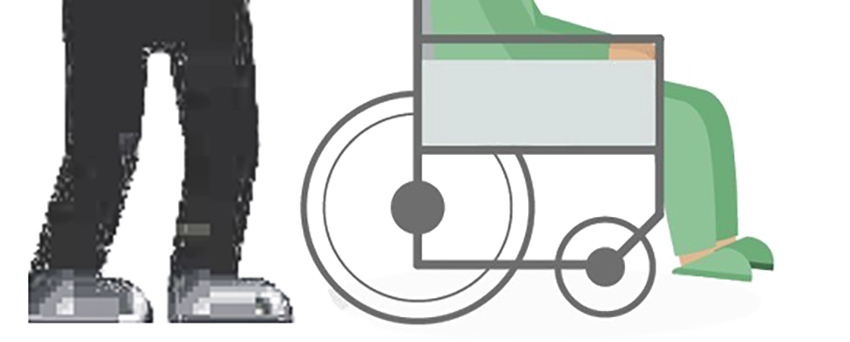
二、人世間再也找不到我的媽媽了
媽媽去了,她是乘著一縷青煙離開人世間的。她去的時候,我正站在殯儀館的門口,望著天空里飄動的云朵。云朵是黑色的,媽媽的靈魂就站在上面,揮著手,戀戀不舍。我知道,從現在開始,人世間就再也沒有我的媽媽了。
我曾經與媽媽有過無數次的告別,不過,之前的每一次告別,都是因為我的離家出走。記憶最深的,是我上高中時與媽媽的第一次告別。媽媽曾經說,我走的那天正好下著小雨,媽媽看著我遠去的背影,眼眶里忍不住流出了眼淚。那時候,我不知道媽媽為什么要給我講這件事情,而且每次講起,她的眼睛總是濕潤的。今天我懂了,那是媽媽經歷的第一次心碎。慢慢的,媽媽習慣了我的離家出走,告別變得沒有那么傷感了。我去外地上學,去外地工作……無數次與媽媽告別,最后留下的,只有一句句溫暖的嘮叨:多吃飯,注意安全,不要太勞累……
而這一次,不是我離家出走,而是媽媽要離我而去。2022年2月25日的早晨,媽媽躺在一張鋪滿鮮花的床上,體溫已經消失,眼睛微閉,好像漂在很深很深的夢中。媽媽的表情很安靜,面容是凝固的,仿佛一尊蠟像,一動不動。我想和媽媽說話,可是媽媽已經聽不到我的聲音了。
記得那天,我和弟弟、姐夫推著媽媽僵冷的身體在殯儀館的長廊里走過,身后變成了一段模糊不清的膠片,之后的很多天,我都想不起來那段路是怎么走過去的,好像整個身體都空了,只有一種幻覺在腦子里游蕩。
其實殯儀館的長廊并不長,只有幾十米。可是,在我走過的人生旅途中,這段路卻顯得格外漫長……因為媽媽要離我而去,她去的地方很遠很遠,沒有歸途。在幽靜的走廊里,我看著媽媽僵硬的身體,腦子里浮現出一個場景……五十六年前,媽媽躺在床上,隨著一陣嘹亮的哭聲,我從媽媽的身體里走了出來。之后的歲月,媽媽呵護著我,讓我一點點長大,從牙牙學語,直到兩鬢出現白發……
在殯儀館的長廊里,我看見,時間的腳步退了回去,時空出現了錯亂。年輕的媽媽拉著我的手,在村口的小河邊走著,炊煙裊裊,整個世界變得清澈明亮起來,蔚藍的天空下,茁壯成長的莊稼覆蓋了整個視野,只有一頭懶散的牛和幾只覓食的麻雀在田間的小路上走著……在牛和麻雀的身后,我的手被媽媽的手緊緊抓著,牛的背影搖晃著,從我的視線里漸漸遠去……恍惚間,恬靜的畫面里飄過一絲霧霾,天氣漸漸轉涼,冷風吹了過來,晦暗的色彩涂滿了田野。媽媽病了,身體開始癱軟。
后來,媽媽失去了力量,時光被燃燒成灰燼……黑暗中,我的手從媽媽的手中滑落了,我呼喊著,瘋跑著,想找到媽媽的手,找到媽媽的溫暖。

在殯儀館的長廊里,我在低聲哭泣,但聲音已經渾濁,沒有了當初的純真……我撩開被角,用顫抖的手抓住了媽媽的手。頓時,冰冷的血液從我的身體里穿過,媽媽的體溫已經沒有了。我知道,今天之后,這只撫摸我成長的手,就再也無法傳遞細如棉麻的母愛了。
在殯儀館的長廊里,媽媽的身體是安靜的,疼痛已經從她的身體里消失。媽媽松弛的表情顯出了安詳的樣子。因為殯儀館的工作人員已經為媽媽化了妝,病魔的殘骸已被清掃干凈,媽媽恢復了健康的容顏,臉上的疼痛凋謝了,露出了紅潤的光澤。
我看到媽媽慈祥的表情,內心忽然有了一絲無法名狀的傷感。媽媽老了,走了。接下來離開這個世界的又是誰呢?在媽媽面前,我一直是個孩子,因為在家庭的隊列里,有前面的媽媽擋著,我就什么也不怕。而現在,媽媽去了,飄向了另一個世界……走在前面的媽媽不見了,我站在了懸崖的邊緣。
是啊,生命輪回,誰又能逃離衰老、死亡。既然走在我前面的爸爸、媽媽已經不在,身后又有兒女們在趕路,他們的腳步聲時時刻刻都在逼近我,我除了放緩腳步,緩慢靠近懸崖,又能有什么選擇呢?
在灰暗的燈光下,我的目光停留在了媽媽的臉上,我仔細端詳著媽媽的臉,試圖看到什么……隱約之間,我好像看見,躺在床上的是我,而不是媽媽,身邊是我的子女,他們的眼睛里流著血一樣的疼痛。整個世界都在塌陷,只有我,安靜地躺著,想著很久很久以前的事情……
時間好像過了很久,我們來到了火化車間的火化爐旁。我知道,媽媽的肉體,將會在這里化作一縷青煙和一小堆白骨,從今以后,媽媽的肉體,將會從這個世界上永遠消失。
此時,媽媽的面容是安靜的,好像一直等待著今天的涅槃……我們將媽媽推進火化爐的瞬間,我似乎覺得我的身體里也出現了熊熊烈火,我的青春和童真正在被燒成灰燼……頃刻之間,我的青春不在了,站在媽媽的骨灰旁,我身體里的銳氣和骨氣消失了很多,我的面容也衰老了很多。
我知道,媽媽已經永遠永遠離開了我,離開了她的兒女……但我不知道媽媽離開我們之后會去哪里,她去的地方是否有溫暖、親情和掛念她的兒女。我無法想象,因為媽媽去的地方確實太遙遠了,人類目前還無法進入媽媽所處的空間。在媽媽的宇宙里,人類的靈魂和夢想已經變成了一連串數據……這樣的感覺讓我對生命有了新的認識。一代一代人排著隊,緩慢地走向遠處,走向另一個看不見的世界……我想,遠處的那個世界一定是存在的,因為,媽媽還活著,她正在另一個世界里微笑著,看著她的兒女在慢慢成長,慢慢老去。
已經是正午,我看見,殯儀館上空的云朵飄走了,陽光正在撕開我身體里的哀傷。我站在殯儀館的門口,揮揮手,與年輕的我進行了告別。我知道,從今以后,我的青春跟著媽媽的身體一起走了,人世間再也找不到我的媽媽了。
作者簡介
冰峰,男,本名趙智。曾在人民文學雜志社等單位工作。現任作家網總編輯、北京微電影產業協會會長、世界華文微型小說研究會副會長等。作品散見于《人民文學》《人民日報》《詩刊》《詞刊》《中國作家》《十月》《隨筆》等報刊。雜文《嘴的種類與功能》入編《大學語文》(2008年3月,北師大版)。曾獲中國電視藝術家協會“十佳制片人”、“優秀編劇”等獎項。2014年,獲美國世界文化藝術學院榮譽博士學位(在秘魯頒發)。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