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見油鹽豌豆飯
作者:徐業君
小孫子從城市里來,跟隨我到農村姥爺家,大概是晚上睡覺不習慣,我正愁無法哄他睡,他突然聽到“豌豆八哥”鳥叫,便問:“爺爺,這鄉下還有鳥說話?”我說:“鄉下晚上比城市區別大,城里除了路燈就是汽車,再就是來往上下班的人群,鄉下是靜靜地的夜,鄉村和大自然融為一體。”
我爸見我們爺孫倆沒睡意,大概是喜歡他的重孫子,隨手拉亮電燈,披著衣服,瞇著眼,點燃一只煙,給我孫子講起了“豌豆八哥”的來歷。
從前山上有個寺廟,廟里很多和尚,一個有智慧老主持,他帶領眾僧嚴守佛門戒律,贏得許多佛門弟子不遠千里慕名而來,他見僧多粥少,于是對和尚們提出了訓條:“善于事,勤于耕”。他帶領眾僧在山上山下墾田千畝,像農家一樣,春種夏管秋收冬藏。四周的山坡溝崖都栽滿了松柏果樹,象一座花果山。從此,這座寺廟的香火很旺。
后來,老主持圓寂了,一個歪嘴和尚奪了寺院大權,他說“嘴要香當廚匠,人要懶當和尚。”把個寺院鬧得開始敗落了,連寺廟周圍的莊稼都無人割了。一年六月,四周百姓的麥子已收完上垛,寺里種的豆子無人拔,麥子熟的快掉地上了,原來安葬在寺廟對面山上的老主持,見了氣得要命,但無奈天堂難管人間事,最后他化作一只鳥,飛到寺院后的樹上叫:“快收快割,快收塊割!”因為這鳥來時正是拔豌豆的時節,人們就叫它“豌豆八哥”。
小孫子聚精會神地聽完姥爺的故事,更加興致勃勃,還纏著姥爺講,姥爺繞不過他又給他講了關于春未夏初的故事,最后以天明做青皮豌豆油鹽飯才罷休。
小孫子進入了夢鄉,我想起老爸的青皮豌豆油鹽飯,我的心底有些意味無窮。記得我年幼時,母親一聽到“豌豆八哥”鳥叫,就告訴我們兄弟姐妹們,要我們聽話,田里馬上有青皮豌豆,我來給你們做青皮油鹽豌豆飯。我們一聽都高興得手足舞蹈。那些天,我們特別聽母親的話,連我那最不聽話,整天哭著喊著要跟著母親“趕路”的三妹,老實呆在家里。
一天,母親從自留地里,扯來一捆豌豆桿,我們一群孩子三下五除二,摘的摘青皮豌豆夾,剝的剝青皮豆,很快有一大筲箕。母親將我們剝好的青皮豌豆用清水淘洗后瀝干水,然后將灶火燒旺,將適量的油鹽放入熱鍋中,等鍋中冒出油煙,便將瀝干水的青皮豆倒入鍋中,用鍋鏟快速反復的翻炒,等待青皮豌豆變色之后,迅速的用鍋鏟盛一大碗放在一邊。然后將做好的米飯個到入鍋中,和青皮豌豆同時悶,蓋好鍋蓋,退小火悶十分鐘,隨即又大火,翻炒,讓青皮豌豆與米飯拌均勻,而且還帶一種焦味。這時按人口先一人一大碗端上桌。
飯上了桌,我們聞著帶著焦味的豌豆和飯香,一個個口水直流,端起飯一個狼吞虎咽。特別是飽滿青皮豌豆進了口,牙齒一咬,象雞蛋黃,味道又爽又下喉。吃起來只聽扒飯的筷子聲和吞咽聲。母親見狀,心疼地說:“孩子們,慢點吃,鍋里還有。”三妹笑著說:“媽,我要盛碗明天吃。”母親回答:“明天還有,我繼續做。”這時大家吃飽了,才放下筷碗。
母親還繼續在鍋里忙碌,她將先盛的一大碗豌豆,用青辣椒炒好,用上香麻油一淋,真象香過了五湖四。吩咐我請來鄰居張叔和李叔繼續圍上一桌喝青皮豌豆酒。一會兒,我們家里好熱鬧……
往事歷歷在目,我又象回到了童年。
“豌豆八哥,豌豆八哥,婆婆炒菜,爹爹燒火;豌豆八哥,豌豆八哥,犁田耙地,割麥插禾”一一這是夢里的童謠,是刻在心尖上的鄉愁。
小孫子在鄉村的姥爺家住上了幾日,天天吃著姥爺做的青皮豌豆油鹽飯,睡得香,賴在姥爺家不愿回城里去。
作者簡介:徐業君,男,漢族,出生于1958年,中共黨員,大學文化,中國微型小說會員,中國鄉村雜志認證作家,文學欣賞雜志副主編。文學作品發表在全國大刊上。代表作中篇小說《苦菜花兒香》。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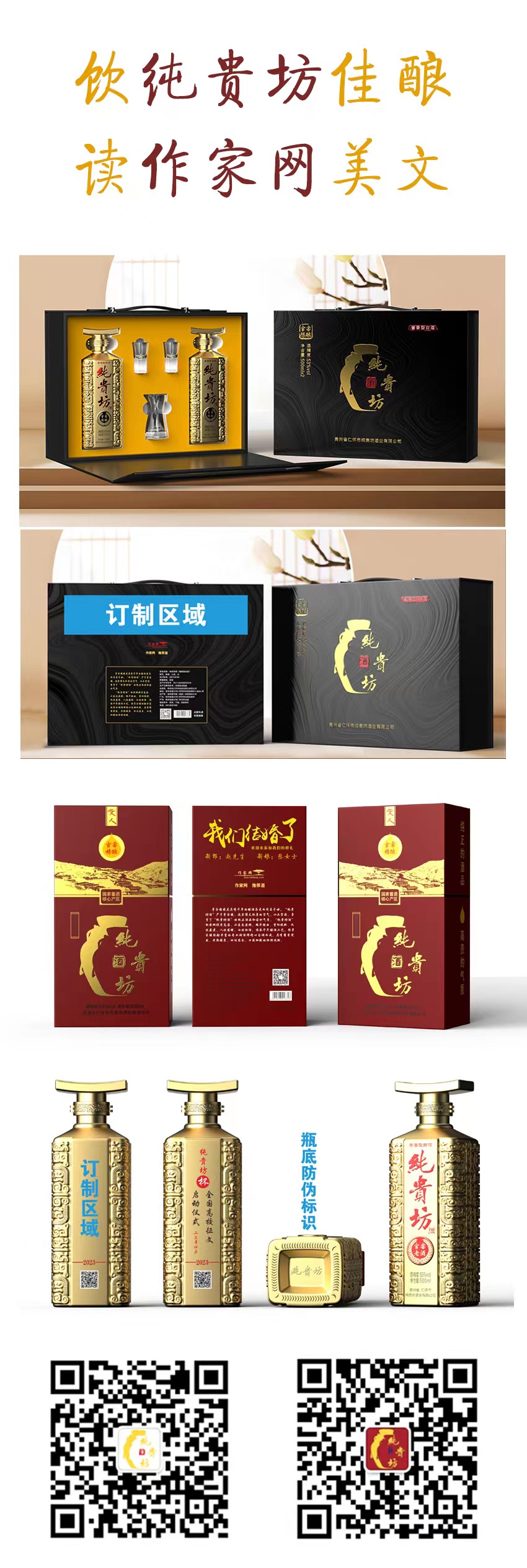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