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歌同行(隨筆)
作者:董勤生
秋天的午后總帶著點懶怠,陽光穿過窗簾縫,在手機屏上投下一道細窄的光帶。本是隨手點開短視頻,想打發(fā)一段零碎的時光,卻沒成想,李小萌開口唱出那曲《探清水河》的瞬間,指尖的滑動忽然頓住 。整個世界好像被按下了慢放鍵,唯有她的嗓音攜帶著老北京胡同里的槐花香,不稠不稀,正好漫過耳際。
那純正的北京琴書調子,不是時下流行的快節(jié)奏,沒有電子樂的轟鳴,也沒有刻意炫技的轉音,就只是“桃葉兒那尖上尖,柳葉兒那遮滿了天”,一字一句都踩著胡同里的青石板路。她的聲音清得像剛從什剎海取上來的水,帶著點涼,卻又暖得熨帖。比如“日思夜想的六哥哥”那句,尾音輕輕往上挑,不是撒嬌,是姑娘家藏在帕子里的心事,軟乎乎地飄出來,落在人心里就化了。旋律更妙,京胡的弦一拉,像胡同里蹬著二八自行車的大爺晃著車鈴,一頓一揚都踩著日子的拍子,板鼓敲得 “咚咚” 響,不慌不忙,正好把老北京的煙火氣都敲了出來。就這么坐著,手機擱在膝頭,聽她唱完一段又一段,等回過神時,窗外的陽光已經歪了,原本只打算 “聽兩句” 的,竟偷偷溜掉了半個下午。
聽著聽著,就想起這些年某些變化。 不知從什么時候起,竟越來越喜歡一些過去討厭的北方戲曲了。小時候總覺得京劇節(jié)奏太慢,京韻大鼓格調顯得沉郁。聽《蘇三起解》里 “蘇三離了洪洞縣”,一句能拉老長,急得我總想替蘇三把話說完;聽駱玉笙唱京韻大鼓《重整河山待后生》,那低沉的調子壓得人喘不過氣。可如今再聽,倒覺得這份 “慢” 里藏著大乾坤。
傳統(tǒng)京劇里的吟唱,從來不是急匆匆的趕路,是閑庭信步的琢磨。比如梅派的《貴妃醉酒》,“海島冰輪初轉騰” 那句四平調,梅蘭芳先生的傳人唱起來,聲音像云一樣飄,繞著戲臺的梁子轉,不是飛,是游,每一個轉音都像貴妃手中的團扇,輕輕一扇,就帶出了大唐的風。京韻大鼓更甚,駱玉笙的嗓子像老紫檀木,敲一下能發(fā)出綿長的回響,唱 “千里刀光影,仇恨燃九城” 時,那調子不是喊,是沉,沉得能砸進歷史里,讓你跟著想起老北京城墻下的悲歡。這些戲曲里的不急不慌,像極了原始深林中的白發(fā)樵夫 —— 他背著柴捆走在腐葉上,腳步沒半點急燥,手里的柴刀偶爾敲在樹干上,“篤” 一聲,倒比戲里的板眼還準。你跟著他走,聽他偶爾哼兩句不成調的曲子,走著走著,就走進了一片蒼茫 。但沒有蒼涼,是歲月沉淀后的開闊,好像所有的急脾氣、煩心事,都能被這慢調子磨得軟下來,跟著白發(fā)樵夫的腳步,一步一步踏進歲月的深處。
可年輕時候,我偏不喜歡這份 “慢”。那是恢復高考后的第二年,我揣著錄取通知書,來到黃河故道旁的一座城市求學。一到秋冬季,故道里的風沙就裹著土腥味撲過來,打在臉上像沒磨過的砂紙,連教室的窗戶都灰蒙蒙的。風一吹,“嘩啦嘩啦” 響,像誰在窗外扯著嗓子喊。唯有夏天不一樣,一場暴雨過后,空氣里滿是樹葉和著泥土發(fā)酵的甜香,連故道里的緩慢流淌的河水都清澈了,河邊的楊樹林里,葉子上掛著的水珠能亮一整天。
那時候我總愛早起。天剛一亮,就揣著《古代文學》走出校園,踩著沾了露水的青草,往小河邊的樹林里去。晨霧是從河水里蒸出來的,薄得像紗,沾在睫毛上涼絲絲的,一眨眼睛就零落成小水珠。找棵粗點的槐樹靠著,開始背誦《詩經 · 氓》。“氓之蚩蚩,抱布貿絲。匪來貿絲,來即我謀”,嘴里念著,眼睛盯著河面,看著霧慢慢散開,太陽慢慢爬上來,把光灑在水珠上,樹葉上的亮斑就跟著晃,像撒了一把碎金子。
就在我念到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 時,忽然學校隔壁省運輸公司六十六車隊的大喇叭響了起來 。那是 “每周一歌” 的欄目,前奏剛過,一個甜美的女高音就飄了過來:“同志哥,請喝一杯茶啊,請喝一杯茶!”
那聲音太干凈了,像剛從井里打上來的泉水,帶著井壁的清涼,順著耳朵往下流,流到胃里時,連早上背書時的口干舌燥都化了。手里的書忘了翻,耳朵跟著那調子走,聽她唱 “井岡山的茶葉甜又香啊甜又香”,連空氣里都好像飄著茶葉的清香。那時候廣播里的歌多半是 “雄赳赳氣昂昂” 的硬氣,要么就是 “學習雷鋒好榜樣” 的激昂,突然冒出這么軟乎乎、帶著南方茶山水汽的調子,就像在滿是糙面饅頭的桌上擺了碟白糖糕,讓人忍不住多嘗幾口。后來才知道,這是《請茶歌》,因為帶著井岡山的紅色基因,才能在中央人民廣播電臺連播一周 。可那時候我不懂什么基因,只知道每次聽到這歌,就像在悶熱的夏天喝了碗冰鎮(zhèn)綠豆湯,渾身都透著爽利。
《請茶歌》之后,廣播里的調子漸漸軟了。沒過多久,就聽到了李谷一的歌。她唱《鄉(xiāng)戀》時,聲音里帶著股 “氣”,不是喊出來的,是嘆出來的 ——“你的身影,你的歌聲,永遠印在我的心中”,那口氣繞著 “身影” 轉,像春風拂過麥田,麥浪都跟著晃。之前聽的歌,多半是 “直來直去” 的,調子是調子,詞是詞,可李谷一的歌不一樣,她的聲音里有 “情”,唱《難忘今宵》時,“無論天涯與海角”,尾音輕輕落下來,像朋友在耳邊說悄悄話,暖得人心頭發(fā)熱。后來才明白,李谷一的出現(xiàn),不是偶然 —— 那是一個藝術新時代的標志,就像冬天過后的第一縷春風,吹醒了之前緊繃的旋律,也吹開了人們心里對 “抒情” 的渴望。
可真正讓我覺得 “時代變了” 的,是鄧麗君的磁帶。在那之前,偶爾能在半導體收音機里擰到 “敵臺”,里面會飄出鄧麗君的歌 ——“甜蜜蜜,你笑得甜蜜蜜”,信號忽強忽弱,像隔著一層棉花聽人說話,還得豎著耳朵防著旁人聽見,生怕被人說 “聽靡靡之音”。可后來,不知是誰先把鄧麗君的磁帶帶到了學校,再后來,連鄉(xiāng)村中學的供銷社里,都能偷偷買到她的磁帶了。
那時候我剛畢業(yè),分配到一所鄉(xiāng)村中學教書。學校給我安排了一間小臥室,冬天漏風,夏天漏雨,可我一點都不覺得苦 。因為我有一臺二手的錄音機,還有好幾盤鄧麗君的磁帶。周末的時候,同事里的幾個單身青年會湊到我屋里,有人帶一瓶啤酒,有人揣一把炒花生,我把錄音機放在桌上,按下播放鍵,“小城故事多,充滿喜和樂” 的調子就飄了出來。
鄧麗君的聲音太軟了,像剛曬過太陽的棉被,裹著人就不想動。她唱《月亮代表我的心》,“你問我愛你有多深,我愛你有幾分”,不是直接的表白,是嬌嗔的詢問,每個字都像撒了把糖,甜得人心里發(fā)顫;唱《我只在乎你》時,“如果沒有遇見你,我將會是在哪里”,調子輕輕的,帶著點委屈,卻又滿是依賴,聽的時候總想起自己的心事 —— 那時候剛談戀愛,跟對象隔著幾十里地,只能靠書信聯(lián)系,每次聽這首歌,就好像鄧麗君在替我說話,把心里的想念都唱了出來。啤酒瓶碰得 “叮當” 響,鄧麗君的聲音混著啤酒的麥香,連窗外的月光都變得軟乎乎的。那時候覺得,日子就該這么過 —— 有歌聽,有朋友,有盼頭,哪怕住的是不到十平方的房子,也覺得滿屋子都是亮堂的。
后來,國內的音樂也開始 “不一樣” 了。先是杭天琪的《黃土高坡》,一開口就震住了人 ——“我家住在黃土高坡,大風從坡上刮過”,那聲音里帶著股沖勁,像黃土高原上的風,裹著沙粒,刮得人心里發(fā)顫。那時候日子還緊,買塊肥皂都要算著用,鎮(zhèn)里的路還是土路,一下雨就泥濘不堪,可《黃土高坡》里的 “喊”,不是怨,是較勁 ——“不管是西北風還是東南風,都是我的歌”,唱的是多少人心里的勁兒啊。我在電視上看杭天琪唱這首歌,她穿著紅色的上衣,頭發(fā)甩得高高的,眼神里滿是倔強,好像在跟生活叫板。那時候覺得,這歌就像一把火,能把人心里的憋屈都燒沒了,聽著聽著,就想跟著她一起喊,喊出心里的勁兒。
再后來,就聽到了崔健的《我是一只小小鳥》。那是搖滾,跟之前的歌都不一樣 。 沒有甜美的調子,沒有抒情的歌詞,只有崔健抱著吉他,甩著頭發(fā),嘶吼著 “我是一只小小鳥,想要飛卻飛不高”。那聲音里滿是迷茫,卻又滿是不甘,像剛走出校門的年輕人,看著偌大的世界,不知道該往哪兒走,可又不想停下腳步。那時候我已經在小城定居了,有了家,有了孩子,日子過得安穩(wěn),可心里偶爾也會有 “飛不高” 的失落 —— 想換個好點的工作,想讓家人過得更好,可現(xiàn)實總有些牽絆。每次在電視上看崔健唱這首歌,都覺得心臟跟著跳得快,好像自己心里的那點不甘,都被他喊了出來。雖然沒機會去首都的萬人劇場感受那種氛圍,可光是在電視上看,就覺得渾身的血液都在沸騰。
不過要說我最喜歡的,還是朱哲琴。朱哲琴的《一個真實的故事》,我第一次聽是在收音機里,前奏剛響,就覺得自己站在了蘆葦蕩里 ,到處都是鶴鳴,水鳥掠過水面,“嘩啦” 一聲,濺起一圈漣漪。“有一個女孩,她從小愛養(yǎng)丹頂鶴”,朱哲琴的聲音一出來,就像丹頂鶴的翅膀掠過藍天,清凌凌的,帶著點空靈感,能把人從柴米油鹽的日子里拉出來。她的嗓子高,卻不尖,唱到 “走過那片蘆葦坡,你可曾聽說” 時,聲音慢慢往上揚,像鶴群飛向云端,帶著點悲壯,又帶著點圣潔。我總想起歌里的那個女孩,為了救丹頂鶴掉進沼澤,那么年輕的生命,卻跟蘆葦蕩、丹頂鶴永遠留在了一起。每次聽這首歌,都覺得心里軟軟的,好像自己也變成了蘆葦蕩里的一縷風,陪著那些丹頂鶴,陪著那個女孩。
除了國內的歌,還有一首外國歌,我記了一輩子。那是日本電影《人證》的插曲《草帽歌》,“媽媽,你可曾記得你送給我那草帽”,喬山中的旋律一出來,就帶著點澀,像秋天的柿子,甜里裹著酸。那聲音是嘆,嘆時光,嘆離別,嘆那些回不去的日子。“突然狂風呼嘯,奪取我的草帽耶!”歌者吟唱到此,突然轉入高音,更是母愛失落無法追尋的哭泣和哀嚎,那是一種撕心裂肺、肝腸寸斷的痛,聽者的靈魂則漸漸被抽走,落下的就是一腔空殼。何為長歌當哭?此歌便是。我第一次聽是在鄰居家的黑白電視上,電影里的男主拿著草帽,站在懸崖邊,調子慢慢飄出來,連電視里的雪花點都好像跟著靜了。那時候我剛失去母親,母親生前總戴著一條白地藍花毛巾,夏天在地里干活,秋天在院里曬玉米,那毛巾陪著她走過了多少日子。后來母親走了,毛巾也不知丟到了哪里,每次聽《草帽歌》,就想起母親的樣子,心里空落落的,卻又覺得溫暖 —— 至少還有歌,能幫我記住那些日子。
前幾天,我在電視上偶然看到了現(xiàn)代京劇《智取威虎山》的片段,楊子榮唱《打虎上山》,“穿林海,跨雪原,氣沖霄漢”,那熟悉的調子一出來,我手里的茶杯都差點沒拿穩(wěn)。五十年前,我還是個孩子,家里的磁石喇叭掛在墻上,天天放這首歌 —— 早上放,中午放,晚上也放,那時候覺得吵,嫌楊子榮的調子慢,嫌京胡的弦拉得刺耳,總想把喇叭的開關擰小。可現(xiàn)在再聽,卻覺得親切得不行 —— 楊子榮的長吟像老熟人敲門,“吱呀” 一聲,門開了,小時候的日子就涌進來了:我趴在門檻上寫作業(yè),喇叭里的調子跟著筆尖走,媽媽在廚房做飯,煙筒里的煙飄得慢悠悠的,鄰居家的小孩跑來喊我去玩,我們追著跑著,笑聲混著喇叭里的歌,飄得滿院子都是。
可高興勁兒沒過,心里又有點酸。現(xiàn)在的年輕人,愛聽的是電子樂、說唱,節(jié)奏快得像打鼓,歌詞也多半是 “潮流”“個性”,很少有人再聽京劇了。上次孫女來,我放《打虎上山》給她聽,她皺著眉頭說 “爺爺,這歌太老了,不好聽”,轉身就拿出手機,放起了我聽不懂的調子。我不怪她,每個時代有每個時代的歌,就像我們小時候不愛聽京劇,他們現(xiàn)在也不愛聽我們的歌。只是覺得有點可惜 —— 這么好的調子,這么有味道的詞,怕是以后聽的人會越來越少了。這種慢節(jié)奏的音樂,好像只剩下我們這些老人還當個寶,因為我們經歷過那樣的日子,能聽懂歌里的故事,也能在歌里找到自己的回憶。
可轉念一想,又覺得沒必要難過。人生不就像一張唱片嗎?每個時期都是一段曲子,有激昂的,有舒緩的,有甜的,有澀的,可哪一段都少不了,哪一段都有它的精彩。年輕的時候,愛聽《請茶歌》的甜,愛聽鄧麗君的軟,那是因為我們心里滿是憧憬,滿是熱情;后來愛聽《黃土高坡》的沖,愛聽崔健的吼,那是因為我們在為生活奮斗,在為夢想較勁;現(xiàn)在愛聽京劇的慢,愛聽《草帽歌》的澀,那是因為我們開始回憶,開始懂得珍惜。
沒有哪個時期的喜好是 “錯” 的,也沒有哪個時期的人生是 “差” 的。就像我現(xiàn)在,午后曬著太陽,聽李小萌的《探清水河》,聽楊子榮的《打虎上山》,偶爾也會聽孫女放的流行歌,雖然聽不懂,卻也覺得熱鬧。音樂就像一條河,陪著我從年輕流到現(xiàn)在,以后還會接著流,它不會嫌棄我老,也不會催促我趕時間,只是安安靜靜地陪著我,走過每一段日子。
與音樂同行,聽著歌,想著事,念著人,日子就不會孤單,也不會乏味。不管是過去的歌,還是現(xiàn)在的歌,只要能讓心里暖,能讓日子甜,就是好歌。至于時光嘛,慢慢來就好,反正有歌陪著,每一段都值得享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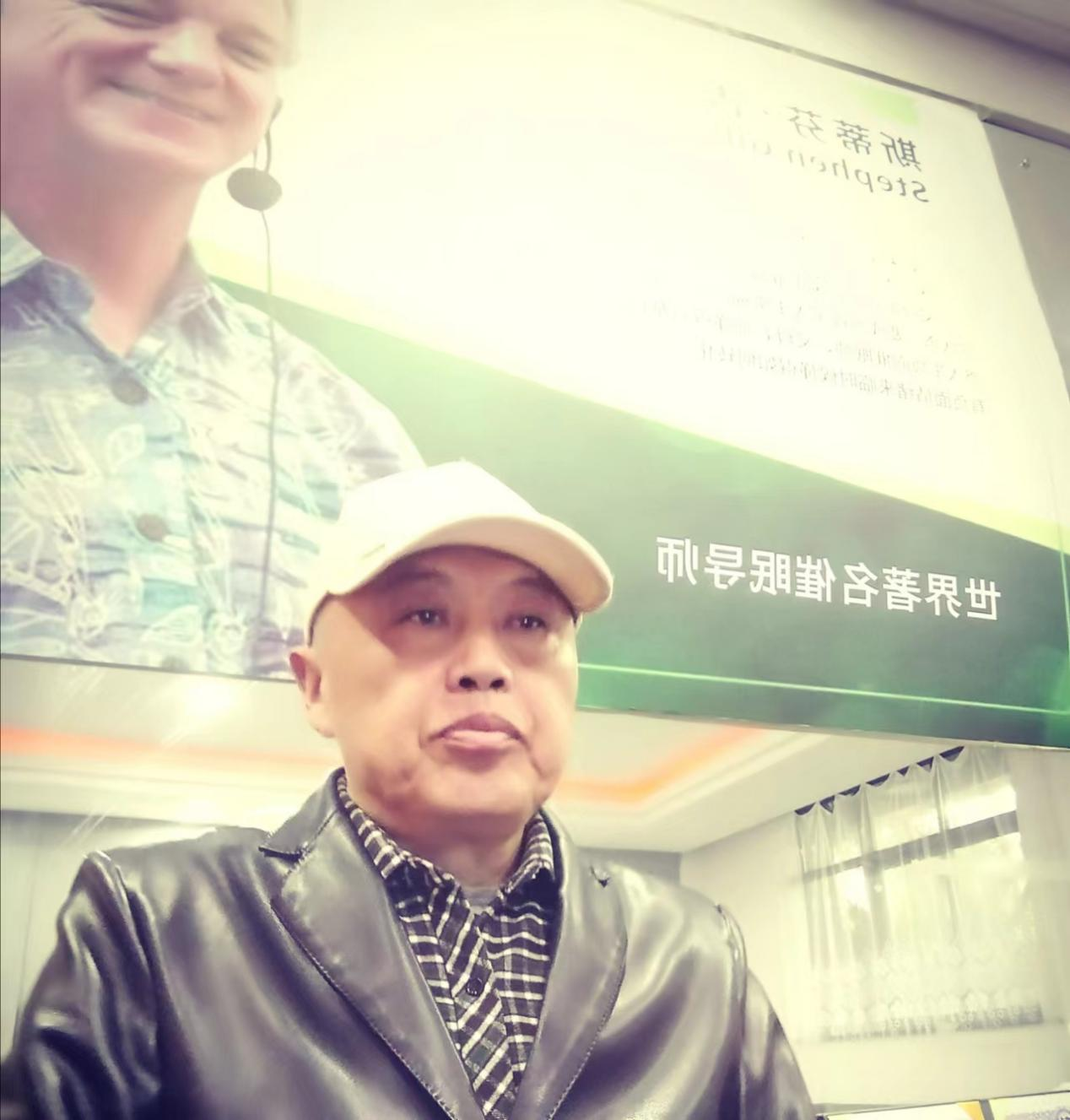
作者介紹:董勤生,江蘇淮安,退休中學教師。早年有散文、小說見刊于《小說報》(吉林)《伊犁河》(新疆)《崛起》(淮安)《揚子晚報》《淮安日報》《江蘇教育報》等刊物。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fā)布)


 純貴坊酒業(yè)
純貴坊酒業(y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