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價(小說)
作者:羅銀湖
一
雨滴答滴答地下著。風嗚嗚地嘶嚎不停。
屋子里,暗黃的燈光下,幺妹跪在水娃的面前,她抬起那張滿是淚水的臉,不住地給水娃磕頭。她的頭發長而凌亂,讓人看到的不是美,而是如披頭散發的瘋子。
“水娃,求求你。求求你看在我們夫妻十年的份上,求求你看在秀兒和剛兒的份上,放我一馬吧……”
“幺妹,不是我不肯留你啊!“水娃流著淚,他也跪倒在地,抱著失聲痛哭,渾身凍得篩糠一般的幺妹,哽咽著說:“我也不想讓你走啊!可是,你叫我情何以堪啊?我的兄弟姐妹,我的叔子伯爺,還有全村上上下下的人,哪個不是搗著我的后脊梁在罵我啊?他們罵我是個不中用的男人,他們罵我連個女人也管不住的廢物啊!我是個男人,你叫我這張臉往哪擱啊?叫我往后還怎么做人啊?”
水娃抱著幺妹,泣不成聲,“幺妹啊,你真得太不該了啊!你為什么要這樣啊?那個矮胖子比我水娃哪一點強啊?你為什么要一次又一次地去纏他?想到這些,我連殺人的心都有……”
水娃說不下去了。他把幺妹拉起來,抱在懷里。兩只手不住地拍著幺妹的后背。頓了一下,水娃把牙一咬,狠下心來說:“走吧!趁現在天黑,下雨,沒人看見,車子我叫好了,在門外。兩個孩子我會好好的照顧他們的。”
水娃跑到房里,把早就裝好了的一大包衣服提出來,拉開大門,往外面走。
天一片漆黑,冷冷的風,嘩啦啦的雨,還有痛不欲生的幺妹。他們就這樣,鉆進了水娃叫好的一輛麻木三輪車。
“我的孩子,”幺妹起身往地下跳,“我連最后一面都不能見他們了嗎?”她的心要碎了。“你不要再連累孩子了。秀兒和剛兒都睡著了,你就放心走吧!我會照顧好他們的。”水娃死死地拽住幺妹,不讓她往下跳。
“快開車,師傅!”水娃向駕駛室里大吼了一聲,“小心一點開車,注意安全!”
車子啟動了。在風里,在雨里,在無邊的黑暗里,在兩顆痛苦的心靈的煎熬中。
“到了你娘家,就好好過吧!”水娃含著眼淚叮嚀著。“如果萬一過不下去了,就遠走高飛吧!總比在家里被人唾死要強!”
看著眼前這個與自己同床共枕近十年的女人,水娃心里又怎么舍棄得下呢?雖然有過磕磕絆絆,有過吵吵鬧鬧,但也有過恩恩愛愛,有過纏纏綿綿啊!
而且,幺妹有一張讓男人神魂顛倒的嬌媚的臉。雖然自己個頭不高,臉頰瘦削,人也不是長得很英俊,但幺妹卻從沒嫌棄過自己。要不是幺妹做得太過分,讓自己顏面掃地,在眾人面前無地自容,水娃還真的舍不得趕幺妹走啊!
幺妹也的確是做得太過分了。前幾次她和那個矮胖子朱細茍做了茍且之事后,被細茍的老婆當面逮住,還打了她幾個耳刮子。可幺妹卻不思悔改,不知怎么的就和細茍又湊到了一起。
山娃本在廣州打工,廠里忙得不可開交。可家里出了這事,他能安心嗎?哥嫂一個電話打過去,把正在上班的水娃氣得半死。他急匆匆跟老板請了假,還向老板借了五百元路費,便火急火燎地坐班車趕回了家。
起初水娃根本不相信幺妹會做這種丟人現眼的事,他認為是有人在中傷幺妹。可回家見到的事實卻讓他的心涼了半截。
他坐了十五個小時的班車。趕到家的時候,將近凌晨三點鐘。天上的星稀稀朗朗,路兩旁的大樹,在月光下顯得灰朦朦一片。走在路上,有一種冷冷清清地感覺。水娃的心里忐忑不安,他有些害怕。他來到了自己的家門口。隔著窗戶玻璃,他向屋里望去,屋子里頭黑不溜秋的。他輕輕地敲了敲門,忽然門吱呀一聲開了一個逢。他一摸,一把大鐵鎖鎖在大門上。“這么早,幺妹會上哪兒去呢?”水娃自言自語道。“不會是帶孩子們走家家去了吧?”他想。但他馬上又否認了。往日里,只要幺妹帶孩子們去走家家,總是要把父親或母親叫過來守夜的。不管怎么說,家里多少還有些值錢的東西。
“孩子們呢?”水娃想叫他們幾聲,可他又止住了。從小他聽父母講,夜里是不能叫孩子名字的。怕被神鬼聽到了,循著聲音來找孩子。可家里就兩個孩子,她放心得下嗎?
水娃放下背包,坐在門口,由于長時間坐車的顛簸,疲憊不堪的他,竟一頭睡著了。
待他醒來時,天差不多快要亮了。門口的梧桐樹上,立著幾只洋雀,在秋風中嘰嘰喳喳地吵嚷著,太陽的臉已躍出了東邊的地平線。頭頂上的天空,散著一片一片五彩斑斕的云霞。秋天的早晨讓人心曠神怡。路上開始有人走動的聲音了。水娃怕被人看見,他趕緊折回到屋子后面。后門叉得很緊,他叫了幾聲幺妹的名字,沒人應聲。他又叫了幾聲秀兒的名字,只聽見秀兒迷迷糊糊地嘀咕著:“媽媽,你怎么還不回來啊?媽媽,你上哪兒了呀?我好怕怕!”
原來哥哥嫂嫂說得都是真的。水娃心里有一種無名的怒火,在升騰,在燃燒,他恨不得拔了那矮胖子朱細茍的皮。也想狠狠地扇幺妹的幾個耳刮子。
水娃沿著屋后那條小路走著。他忽然記起來了。屋后那一塊河灘上,有一個池塘,那是村里人挖土挑臺挖出來的。那個池塘有三四畝的樣子,村里一直包給朱細茍種蓮藕養漁的。為了守護蓮藕和魚兒被人偷竊,朱細茍在池塘邊上搭了一個棚子,長年在那里守護。
會不會在那里呢?水娃不敢往下想。水娃越是這樣想,心里越是緊張和害怕。他害怕幺妹真的會在那個棚子里面。
快到棚子跟前了。水娃屏住呼吸,但他的心卻跳得好厲害,快蹦出來一樣。他輕輕地湊到棚子跟前,立起耳朵,凝神聽著從里面發出的聲音。
“嗯……”是矮胖子發出的一聲長噓。“幺妹,我的心肝寶貝,”聽得到悉悉索索的聲音。“真想永遠這樣,與你日日相擁,夜夜纏綿……”矮胖子用上了不知從哪個電視劇里學來的臺詞,怪聲怪氣地說,還不時發出幾聲滿足的笑。
“我也是啊。細茍哥!”聽得到幺妹柔情似水的聲音。
“你不怕你家水娃知道?他會拔了你的皮的!”朱細茍輕輕嘆息一聲。
“誰讓他對我不聞不問的?”幺妹嗔怪地說,“一個大男人,只知道賺錢。一年半載,也不知道回趟家,我可是個女人哪!”
“好呢!”矮胖子又油嘴滑舌地說,“他不回來,有哥哥我陪你啊!”
水娃聽到這里,禁不住怒火中燒!他大吼一聲:“朱細茍,劉幺妹,你們這對臭不要臉的狗男女!”說完,從地上撿起一塊磚頭,向棚子的鐵門猛地砸去。
幺妹被帶回了家。她披散著頭發,低垂著頭,象個犯人似的,在水娃的押解下,幾乎小跑似的走回了家。
“幺妹,你,你太不是東西了!”水娃坐在堂屋里,怒視著幺妹,“老子在外面累死累活,舍不得吃,舍不得穿,賺的錢一分不少地寄給了你。圖的是什么?還不是為了你和孩子?你不但不曉得知恩圖報,還,還給老子戴綠帽子!你,你是人嗎?”水娃罵完,語氣平緩了些。他見幺妹不吱聲,臉上也滾滿了淚水,忽然心一軟,有些自責地說,“也怪我沒替你考慮。”
幺妹撲通一聲跪在地上,雙手緊緊地抱住水娃,痛哭流涕地說:“水娃,以后我再不敢了。是我賤,是我對不住你!你打我吧!”水娃聽幺妹這樣一說,哪還下得了手?他怔了怔說,“你起來吧幺妹,我可以原諒你這一次!但從今以后,你要保證改邪歸正,重新做人。看在孩子們的份上,我也不計較了!你發誓!”
幺妹信誓旦旦地說:“水娃,看得到你是真的對我好!我發誓,如果再有第二次,我劉幺妹遭天打五雷轟,不得好死。”
那天晚上,水娃和幺妹象回到了初戀的時光,他們相擁著度過了一個美好的夜晚。
幾天后,水娃的假期也到了。幺妹把山娃送到車站,分別時,幺妹拉著水娃的手,深情地說:“水娃,你就放心去吧!孩子和家里的一切就交給我了。我會沒事的。過年的時候早點回來吧!我等你!”
水娃心里的一塊石頭總算落地了。水娃沒想到,自己去了才多久,幺妹又鬧出那些傷風敗俗的丑事。水娃是恨鐵不成鋼,又惱又氣,才決定把幺妹送回她娘家,隨她怎么折騰去了!
二
水娃個頭不高,大概一米六的樣子。臉頰瘦削,一雙眼睛有些細小,總是不住地眨巴眨巴著。
水娃平時說話總是柔聲細語,看上去,一副文文弱弱的樣子,給人一種軟弱可欺的感覺。
水娃是二十五歲那年娶的幺妹。說實話,水娃娶幺妹還是頂住了很大壓力的。
水娃家境一般,幾個哥哥姐姐相繼成家立業了。父母看他對婚姻大事貌似無動于衷,有些急了,便托人四處打聽,最后媒人把幺妹的情況說給了水娃和他父母聽。水娃父母起初有些反對,后來看水娃態度很堅決,便答應了。
水娃跟幺妹見面,是在媒人家里。
幺妹扎著一個學生頭,她的五官長得很勻稱,臉上有一對深深的小酒窩。幺妹穿著一套鮮艷的連衣裙,看上去很調皮很活潑的樣子。一見面,她用火辣辣的眼盯著水娃的臉,把水娃看得不知所措。幸虧媒婆出來圓場,“幺妹啊,水娃可不是一般的人物啊!他做了五年水手,漂洋過海去過好多地方。因為長年漂泊在外,人很孤單寂寞,所以才辭了那份工作,現在,到廣州打工去了。”
幺妹聽媒婆這樣一說,自然對水娃有了一些敬佩。她想,如果水娃有能力賺錢養家,就跟了他!
其實幺妹也有過一段非同尋常的經歷。不過那不是浪漫的經歷,而是痛苦和辛酸的。
那是幺妹十八歲那年。她還是一名高二年級的學生。
那是充滿天真和美好的時代!幺妹對外面的世界充滿了好奇,充滿了向往。因此,一有閑暇,她就來到網吧,在網上尋找自己最感興趣的文化娛樂活動。
一名叫紅色妖姬的網友,闖入了她的視線。他經常和幺妹在網上聊天,視頻。他告訴她,他在上海華夏文化娛樂有限公司做經理。他們公司專門培養各類影視人才,并負責向影視圈推薦。從小就非常崇拜影視歌星的幺妹,這下心里可樂開了花。她為自己能夠結識一位這樣有才華的經理而高興。她仿佛看到了美好的未來向她在招手。他告訴幺妹,她是他長這么大以來,結識的最漂亮大方,最有潛力的一位女孩,前程無量。最后他問她是否想到上海去發展?機會對人只有一次,一定要好好把握住。
幺妹真是喜極而泣。他告訴了他的電話。并告訴了他接她的時間和地址,再三囑咐她不要告訴任何人,以免別人冒充她行事。
一個星期天的上午,學校放假了。好久沒有回家團聚的同學們,有說有笑地走出校門,朝市汽車站的方向走去。
幺妹也在這些同學中,她背著一個紅色的背包,里面裝著幾件換洗衣服,內心無比激動地來到了市汽車站。
車站里人來人往,熙熙攘攘,售票窗口,很多出門或是回家的人,排著長長的隊伍在等待購票。
幺妹來到5號窗口,這里就是出售邊城市至上海的班車售票口。
幺妹排好隊,心急如焚地等待著,她希望能盡快買到車票。
“幺妹,你好啊!”一個牛高馬大的男子突然出現在幺妹的面前。“我是上海華夏文化娛樂有限公司在邊城地區的招生代理。受我們經理紅色妖姬的委托,專門來接你的。”
“你……是真的嗎?”幺妹有些半信半疑,她猶豫不決。
“別瞎想了。先跟我過來。”高個子男人拉起幺妹,直往車站廣場走。“我們的專車在那里,去那邊看我的工作證!”
車站廣場上,停滿了各種各樣的車。但大都以出租車為主。
“這就是我們的車。”男人指著一輛白色柳州五菱面包車說,“我們車上還有一個女孩。也跟你一樣,到上海去參加我們公司的培訓。”他掏出一個紅色的小本本來,遞到幺妹眼前:“這是我的工作證,你看好了?”
幺妹拉過工作證,左看右看,不舍放下。“去了,你也會有的,做了我們公司職員,就才會有人生的精彩。祝福你!幺妹!”
幺妹上了車,車上還真有位十七八歲的姑娘,她坐在座椅上正在打盹。幺妹挨著她坐下來。車在公路上急速地奔跑著。公路兩邊的村莊,大樹,田野,都在向后退去。望著這些她那么熟悉的故鄉,她心里突然有一種失落和不舍!
“爸爸媽媽,女兒是為追逐自己的理想而去,等女兒有出息了,一定回來看你們!”幺妹想著,淚水不知不覺流了下來。
經過八九個小時的顛簸,車子穿向了一條大山中的黃色泥沙公路!幺妹把臉貼在窗口,她望著窗戶外那一片緊緊相連的大山,心里忽然又升起一種恐懼來。
鄰坐的那個女孩叫曉雪,是幺妹同一個鎮上的人。她也是在網上認識的紅色妖姬,“我們都是好姐妹,到了,咱倆一定要互幫互助啊!“曉雪期待地望著幺妹笑笑,“好的好的!咱們就是好姐妹!”幺妹忙不迭地說。
天黑下來了。幺妹和曉雪都被顛簸得沉沉睡去。
“到了,下車!”高個子男人吼叫著。
被車顛得有些暈頭轉向,渾身無力的幺妹和曉雪,被架下了面包車。
“來,這是兩個新鮮貨,沒開苞的。”高個子男人叫著。“每人三萬,不能少一分錢。要的,就快數鈔票。”
“完了!!!上當了!!!“幺妹在心里哭喊起來。她抓住曉雪,就要往外走。這是緊靠山崖邊的一個小鐵棚,里面只有兩張床,和幾條矮凳子。門外擠了二十多個看熱鬧的男子。他們紛紛伸出大拇指,顯出贊美的口氣來。“這個,我要了。”一個三十歲上下的男人,從懷里摸了許久,摸出一沓鈔票來,遞給高個子。“可以帶走了嗎?”他看看高個子,又望著幺妹白皙的臉,一雙淫蕩的眼睛在幺妹身上移上移下。
“好!你可以帶她回家了!”高個子甩甩手,“去吧去吧!記住,別讓人跑掉了。那樣我是沒錢賠你的。”
曉雪也被帶走了,只聽見她大聲嚎啕的聲音。
這個男人叫小堂,他的家在大山深處的一間土坯房子里。屋里幾乎沒有任何值錢的東西。幺妹象一只落入虎口的小羊羔。在這個哭天天不應,叫地地不靈的深山老林里,她任憑小堂如虎似狼的蹂躪和遭踏。
她想逃離這個令她心驚肉跳的地方。可是周圍除了一眼望不到盡頭的大山和森林,她看不到任何東西。小堂的母親是個跛子,父親是個聾啞人。兩個姐妹已遠嫁他鄉。小堂靠到井下挖煤幾年,苦苦攢下幾萬塊錢,才從高個子那里買到了幺妹。
他當然會把幺妹牢牢看住。他想幺妹給他生個大胖兒子,給他傳宗接代,延續香火!
幺妹在無盡的黑暗和痛苦中度日如年。她的淚已干涸!她在無盡的懊悔和仇恨中苦苦掙扎。她不知道自己該怎樣做,才能得到上蒼的恩典?
小堂每次對幺妹施暴后,都要捏著幺妹的鼻子,恨恨地說,“你啥時給老子生兒子啊?你可是老子花三萬塊錢買回來的啊!再不下嵬,老子就把你賣出去了!”說完,小堂又是一陣狂笑,還用雙手狠狠地掐幺妹的雙乳。
這不人不鬼的生活,把幺妹的銳氣幾乎蝕盡!她已然如一具行尸走肉。沒有思想,沒有言語,沒有笑容,她的世界沒有晴天。
這樣的日子過了兩年。其實幺妹是根本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時的。而這兩年的時間里,盡管小堂隨時隨地對她施暴,而幺妹竟然沒有給他產下一男半女。
曉雪則不一樣。她被鄰村的王顛子買去后,給他生了一對龍鳳胎。王顛子喜出望外,對曉雪逐漸信任,放心。春節前,曉雪纏著王顛子,要他和自己回娘家去,看望一下自己的父母親,王賴子同意了。
下班車后,曉雪讓王顛子在侯車廳的座椅上坐會兒,自己以買東西為名,偷偷地跑到了車站民警室。向值班民警哭訴了當年在車站廣場,自己和幺妹被人販子販賣的經過。就這樣,在公安干警的巧妙周旋和英勇無畏的營救下,幺妹得以逃離魔爪,與日思夜想的親人團聚。
回家后的幺妹,完全變了個人似的。不吃不喝,不說不笑。整天把自己禁錮在與世隔絕的世界里。
父母親看到過去活潑愛笑的女兒變得如此模樣,不禁老淚縱橫,他們四處求醫問藥,燒香拜佛,可幺妹的狀況卻毫無改變。
后來,多虧公安干警和婦聯的心理醫生們多次進行心理治療,才使幺妹逐漸擺脫陰影,重又變得活潑開朗起來。
水娃得知幺妹的所有情況后,十分地同情幺妹的悲慘遭遇,他想,自己因身材矮小,家境條件差,多次戀愛未果,這次能遇到幺妹,也算是緣分,況且,幺妹人也生得秀氣,若能與幺妹攜手白首,豈不是天賜良緣?
兩個同樣渴望幸福和愛情的年輕人,在特定的條件下,走在了一起。
新婚燕爾,水娃和幺妹有說不完的話。他們一起上街,一起下地。他在耕田打藥,而她則在水田埂上坐著,看她喜歡看的愛情小說和雜志。他累了,她則把從家里帶來的井水遞到他面前,讓他甜甜地喝上幾口。
下雨天,水娃則坐在床沿,向幺妹講他當水手時候的故事,歐洲,非洲,太平洋,印度洋,好望角……他所有去過的地方和所有經歷過的故事,都要繪聲繪色地講給她聽。
幺妹有時候會插上一句:“你這么牛,怎么不弄個洋妞回來呢?”還故意向水娃笑笑,擠擠眼。水娃有些不好意思地說:“好好好,下次不吹了。”
最初幾年,他們的生活是甜蜜和諧的。秀兒和剛兒的誕生,把這個家庭的幸福指數幾乎提升到了最大值。隨著孩子們年齡的不斷增長,家里的負擔也逐漸加大。
一天,水娃對幺妹說:“幺妹,你在家好好帶孩子。我出門掙錢養你們。”幺妹有些不忍地說:“你一個人養我們仨,不累死你才怪呢?”頓一下幺妹又說,“你在外打工攢點錢,我帶倆孩子,種幾畝田,里里外外都有收獲,那不更好?”
水娃在外不抽煙不喝酒,不賭不嫖,都說他很能顧家。幺妹則把孩子們的吃喝拉撒全部拾掇好,才能到地里去勞動。
三
常言道:好事不出門,壞事傳千里。幺妹的娘家雖然和水娃的家相隔二十多里地,然而幺妹與朱細茍茍且的事,卻如長了翅膀一樣,很快便傳到了娘家人的村子里。
幺妹的哥哥嫂子聽到村里人對幺妹說三道四,對自己指指點點,覺得低人一等,回到家里,嫂子板著臉對幺妹說:“幺妹啊幺妹,你不只禍害你一家人,還要禍害娘家人,你,你還讓不讓人活啊?你趕緊走吧!別說你哥嫂不給你面子!”幺妹是家里的老幺,平常父母親和哥哥姐姐們都是很疼自己的。現在自己這樣子了,他們不厭煩才怪呢!
父母親雖然是滿腹的牢騷,但幺妹畢竟是自己的親閨女啊!父親緊皺著眉頭,苦不堪言地說:“孩子啊。是爹媽從小沒教好你,才讓你落得今天這個樣子……”話沒說完,已老淚縱橫。“兒啊!這人生哪,就象下棋子兒一樣,一步走錯,滿盤皆輸啊!你已經一錯再錯了,這以后的日子啊,你該怎么過啊?”
母親抱著淚水嘩嘩的幺妹,哽咽著說:“你快別說了啊!孩他爸!難不成我們讓孩子去死嗎?”
幺妹覺得自己丟人丟得太大了,不但讓水娃在人前抬不起頭,還讓自己的親人們個個受盡旁人的白眼,她覺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大的罪人。
“我為什么會變成這樣啊?我為什么要這樣寡無廉恥啊?”幺妹在心里哭喊著。她恨自己,她恨自己的軟弱,貪婪,她恨自己一次又一次地犯賤。她更恨那個把她變成今天這個樣子的朱細茍……
那天,幺妹早早地起了床,她來到菜園子里,弄了些豌豆,青筍,然后理好洗凈,準備做早餐。這些都是孩子們喜歡吃的菜肴。她升燃灶火,放了幾把木材,灶蹚里的火便劈劈啪啪地燒起來。她炒好了菜,炸好了豌豆粉,又煮好了兩碗雞蛋面,便叫孩子們吃早餐了。
秀兒和剛兒吃著幺妹做好的飯菜,直叫好吃好吃。隨后便和隔壁的盼盼桐桐姐弟結伴上學去了。
幺妹走進里屋,將孩子們晚上洗澡換下的臟衣臟褲裝進膠桶里,又從床上扯下枕頭被套,準備拿到小河里去洗。
幺妹從屋后的一條便道向小河走去。便道上長滿了輕輕搖曵的蒲公英和車前草,走到大約二百多米的地方,就是朱細茍守護漁塘的棚子。
這個棚子是用鐵皮建成的,頂上蓋著幾塊青色的石棉瓦。棚子四周長滿了絲爪藤和南瓜藤。這些爪藤都相互纏繞著,攀爬在棚子頂上,絲瓜細小的黃色的花朵,和南瓜黃色的如喇叭一樣的花朵,也互不相讓,在盡情地吐著各自的芬芳。幾只早起的蜜蜂,在花朵叢中忙碌地飛來飛去。棚子南邊,就是朱細茍承包的村里的那方小池塘。此時正是初夏,氣候宜人,池塘里的荷葉已經長得枝葉蔥蘢,幾只剛出水的蓮花,上面還閃著晶瑩的露珠,已有蜻蜓在蓮花和荷葉間追逐著。
在經過朱細茍的鐵棚子時,幺妹加快了步伐。前幾次每次經過這里時,都被正在池塘絞雜草的朱細茍看見。朱細茍每次同她打招呼時,她都懶得理睬他。此時,正坐在棚子前抽煙的朱細茍看見幺妹一個人,便伸過頭來,兩眼盯著幺妹,向她打招呼:“好早呀幺妹。要不要坐一下?”
幺妹看見他眼里有一種饑渴的光,便馬上縮回眼光,也不理他,飛也似地跑到河邊去了。
幺妹洗完衣服轉回來時,見朱細茍還在那里一個人抽煙。朱細茍笑著說:“幺妹子,怎么不說話啊?是看不起細茍哥啊?”“沒有的事啊!你誤會了!”幺妹笑笑,準備走過去。“等下幺妹,我這有一袋西瓜,是我這灘涂地上種的早熟品種,帶回去給娃們嘗個鮮。”朱細茍從鐵棚子里搬出一蛇皮袋子西瓜來。“我幫你扛回去。”“不要,我有。”幺妹回絕,“別太生分了,鄉里鄉親的。”朱細茍說著就往幺妹家里走。幺妹拗不過他,只得由他了。
到家后,朱細茍打量了一下幺妹家的擺設,贊不絕口。幺妹從房間拿出二十元錢,遞給朱細茍:“這是西瓜錢,細茍哥。”“不要不要。”細茍推辭,但幺妹硬是要塞給朱細茍,一不小心,把他的臉撞了一下。細茍說:“不如這樣吧!我家的耕牛明天有空,我幫你去棉花地里中耕培土,這二十元就當是你付的工錢怎么樣?”幺妹想,這樣也好,就笑著答應了。
朱細茍個子雖說只有一米五左右,但人生得肥頭大耳,顯得很有精神和力氣的樣子。他長著一副四方臉,眼睛也頗有神彩,而且嘴角總是掛著笑。不過這種笑,總是讓人感覺到有一絲虛情假意的樣子。不過既然他硬是要幫自己,那就由他吧!反正又不是沒付工錢給他。幺妹這樣想著。心里也就平衡了。
第二天一大早,朱細茍便已放牧歸來,他把自家那頭老黃牛套上格頭,拉上板車,來到幺妹門口。朱細茍幫幺妹把幾袋復合肥搬上板車。然后來到了幺妹的棉花地里。
初夏的早晨,天氣很涼爽愜意。田里的棉花,將近一尺多高了,枝葉一片挨著一片,掛滿了露水。田野上空,有輕輕的薄霧在飄逸。
幺妹將復合肥用膠桶裝好,彎下身子,左胳膊挽著膠桶提手,右手則抓起肥料,往棉花的根部撒去。幾分地撒下來,幺娃累得氣喘吁吁,汗流浹背了。
朱細茍已經趕著牛,在中耕覆土了。牛兒在前面吃力地拉著犁鏵,朱細茍左手牽著牛繩,右手扶著犁把,一拐一歪地往前面走。有些棉苗被牛腳踩倒或是被犁鏵掀起的泥巴壓倒,幺妹便趕緊過來扶正。兩三畝棉花地的施肥和培土,在幺妹和朱細茍的配合下,半天就完成了。
幺妹對朱細茍感激不盡。她擺好了飯菜,酒杯里倒滿了酒,勸朱細茍不要客氣,隨便吃。酒過三巡后,朱細茍有些恍惚了。他瞟了一眼幺妹,打了一個酒咯,說道,“水娃出去這么久了,連個電話也不來,肯定是在外邊有女人了。”
“你別胡說,水娃可不是那號人!”幺妹攔住了朱細茍的話。
“信不信由你。你看我家大侄兒洪亮,老不老實?還不照樣在外面有了女人。”
洪亮的老婆在家帶孩子,人生得很漂亮。洪亮在廣州做衣服,半年不給家里來個電話,廠里七八月份歇熱的時候,冷不丁帶回來個女人,說要和她結婚,把家里的老婆氣跑,跟了別人。這件事,不只幺妹,就是全村人都知道。
難不成我家水娃也會這樣?幺妹聽朱細茍一慫恿,心里還真的對水娃有些擔心了。
“幺妹,人這一輩子,不要太死心眼。”朱細茍借著酒勁,開導幺妹,“今日有酒今日醉,明日愁來明日愁。你何必……”話沒說完,朱細茍便忽然站起初,往幺妹身上靠。
“細茍哥,你別亂來啊!”幺妹臉頰變得通紅,結結巴巴地說,“我可是正經人家來的!”
“幺妹,你,你別哄人了。哪個不曉得你的事啊?還有一個什么叫曉雪來著的?電視上都播過的。”朱細茍的話,象一根針插進了幺妹的心里一樣。本來,這是她最切深的傷痛。讓他這么一掀,她心里感到好難受好委屈。幺妹一下子嚶嚶啜泣起來。
“我,我不該傷害你……”朱細茍不知所措,忙從墻上的衣架上扯下一條毛巾,遞給幺妹。當他陡地看到幺妹那張姣美的臉蛋,嗅著她身上散發出的那種成熟女人的體香時,突然渾身的血往上噴涌,他不顧一切地把幺妹抱在了懷里……
就這樣,幺妹在朱細茍的誘惑下,一次又一次地與他發生了肉體的碰撞。她感受到朱細茍的那種陽剛之氣,是水娃從未有過的。她完全成了他的俘虜。而朱細茍也從幺妹身上,體會到了女人的嬌嫵和溫存。他極盡挑逗,奢靡之能事,以至后來終于釀出命案,兩人都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
四
朱細茍的妻子名叫召群,與他同庚。他們也是經由媒人掇和的。召群的父母去世的早,跟著大哥大嫂長大。人都說“長哥長嫂當爺娘”,可召群卻在大哥大嫂的家里受盡了委屈。
因為家里窮,大嫂不肯讓召群上學,她很小便學會了洗衣做飯,放牛養雞。稍大些,還下地幫助哥哥嫂子栽秧割麥,挑谷打場。什么臟活累活她都能做。召群是個懂事的苦命的孩子。更是個種田過家的好女子。到了談婚論嫁的年齡,上門說媒的也有幾個。但男方一聽說召群不識字,又沒有手藝,所以就沒有了下文。大哥大嫂為此很是有些著急,而召群自己也是焦急萬分。生怕自己成了嫁不出來的老女人。這也為日后她的悲劇埋下了禍根。
有一天,媒人帶來一個又胖又矮的男人與召群見面。這個男人,不是別人,正是朱細茍。朱細茍因為人生得矮,家境也不啥樣,所以很長時間沒能找到媳婦,與召群見面,他也沒有抱大太的希望。然而召群的哥嫂卻對這個未來的妹夫很是看好。嫂子瑛子對朱細茍說,“我家小姑子無所不能,人也好,心也好。誰娶誰享福。只要你答應,我們立馬給人。”朱細茍可是求之不得。
當晚,朱細茍便帶上召群一起,到鎮上的電影院看了一場電影。散場后,召群便隨朱細茍來到朱家,兩人在一起過了一個激情四射,纏綿悱惻的夜。
召群出嫁的時候,是臘月初八,那時候農村青年結婚,很少穿婚紗的。召群穿著一件紅色的中長毛絨昵子大衣。頭上扎著紅色的蝴蝶結,在一片敲鑼打鼓聲中,和劈劈啪啪的鞭炮聲中,她終于與朱細茍喜結連理,成為夫妻。
婚后一個月,召群就臨產了,并順利產下一名男嬰。他們給他取名來福。一年后,他們的小兒子來順也平安降生。這段日子,朱細茍和召群過得確實很恩愛。
朱細茍喜歡抽煙喝酒,閑暇時候,也喜歡斗斗地主,打打麻將什么的。不管是輸是贏,召群都不會說三道四,完全是一副賢妻良母的形象。但朱細茍卻不以為然。他認為是自己幫了召群,他想,如果不是自己和她結婚,她說不準真的成了一個嫁不出門的老女人。所以后來每當為了某種小事,與召群吵鬧的時候,朱細茍總是極盡所能地挖苦,嘲笑,譏諷召群,讓她難堪,甚至發怒。
有一次朱細茍在外面打麻將輸錢了,心里一肚子火。回到家看到召群還沒燒火做飯,便氣不打一處來。罵召群是個懶婆娘,連丈夫都不好好伺候。召群不服,頂了幾句,這下可捅了馬蜂窩了。朱細茍一邊摔東西,一邊破口大罵,“你這賤人,不要臉的騷婊子。”聽到自己的丈夫竟用這樣惡毒的話詛罵自己,召群忍無可忍,她指著朱細茍的眼角說,“朱細茍,你把話說清楚了,誰是賤人,誰是婊子,今天不說清楚了,我跟你沒完!”
朱細茍哼哼哼地哼了幾聲,一字一句地說:“你拿起棉花紡一紡,這天底下,有哪一個女人,嫁出門才一個月,就生兒子的?不是野種是什么啊?!”
原來朱細茍拿這事在做文章。召群怒不可遏。她哭著說:“朱細茍啊,你不是人。你竟這樣罵你的孩子,你小心遭報應啊!”
以后的日子,召群成了朱細茍砧板上的肉,要她圓就圓,要她癟就癟。召群對他們的婚姻不再抱有奢望,她只求兒子們能健健康康的快樂成長。
而自從朱細茍與幺妹發生了茍且之事后,召群面臨的是前所未有的打擊和侮辱。
那天下午兩點多鐘,召群頂著高溫,把最后一塊棉花地的葯水打完,當她拖著疲憊不堪的身軀回到家里,看到的是一幕讓她不齒的齷齪場景。朱細茍和幺妹赤身裸體,正在廚房的涼床上裏在一起。她憤怒了,為這兩個毫無廉恥,禽獸不如的畜牲而蒙羞。
她跑上去,扯起幺妹的頭發,伸出手來,對準幺妹的臉就是幾個耳刮子。隨后,對準朱細茍的臉也是一陣猛抽。
可完全喪失了理智和人性的朱細茍依然我行我素,只要一有時間,就與幺妹纏在了一起……
還有一次,朱細茍與幺妹儼然一對夫妻似的,公開在鎮上的照相館拍照。并且把照片公開鑲嵌在召群和朱細茍結婚買來的相框里。召群質問朱細茍:“你究竟跟她過還不跟我過?”哪知朱細茍毫無夫妻之情,他冷冷地說:“你死了最好!”性急中的召群,哪里聽得了這樣的話。一氣之下,她來到屋后的一片小樹林,用一條小繩子,結束了她的生命,也結束了和朱細茍之后的所有恩怨!
來福和來順這兩個沒有娘的孩子,則象一根斷了線的風箏,他們四處漂泊,流浪,乞討。在他們眼里,父親朱細茍不過是一抔糞土,他們寧愿去死去流浪,也不愿與他生活在一個屋檐下。幺妹呢?水娃是不會再要她了。娘家人也為她傷透了神。
一天,父親對幺妹說:“兒啊,父母老了,你也不可能在娘家呆一輩子!我有一個結拜的老弟兄,是我在修鐵路時認識的。他們在大山里生活。不知你適應不適應?去了,他就是你的父親。他會幫你找個好人的。你一定要好好地過日子……”
水娃還在廣州打工。他的兩個孩子秀兒和剛兒,分別交由大姐和二姐撫養。水娃心里還時時念起幺妹。但他決定,這輩子不再娶了。
每一個人,無論何時何地,都不能逾越道德的紅線。為了自己的無知,愚昧,和一己私利,為了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會付出代價。甚至于以生命來殉葬。
人們啊,該醒醒了。
作者簡介:羅銀湖,男,湖北省仙桃市作協會員,荊楚網版主。散文《山鄉之夜》、小說《山妹的心思》入選作家出版社《大地上的燈盞?中國作家網精品文選2018》一書;報告文學《熊坤和他的棗紅馬》榮獲《今古傳奇人物年鑒》2022年卷全囯有獎征文二等獎。散文《圓匠外傳》獲第二屆“三亞杯”全國文學大賽金獎。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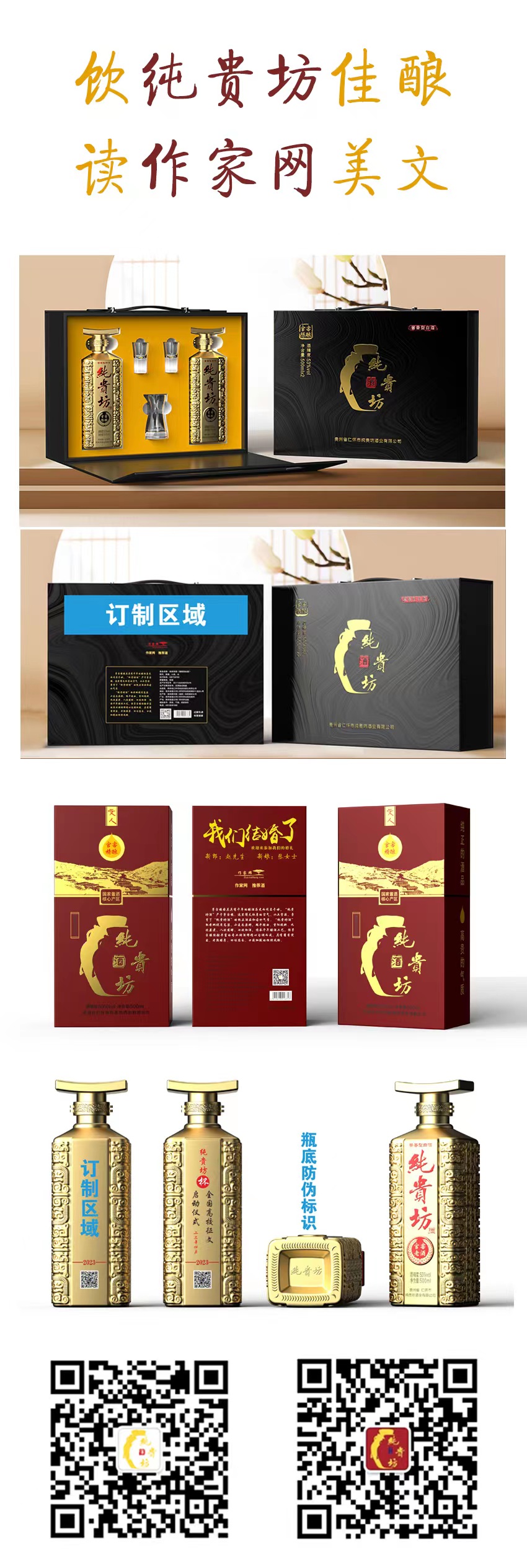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