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日報》撰文認為,王雄被譽為中國第一位倡導和實踐漢水文化小說創作的作家。他精心選擇了漢水岸邊的一座古城(襄陽)、一條古巷(馬背巷)、一個古渡口(襄陽渡口),作為漢水文化小說的敘事載體,以濃郁的漢水文化風情和楚風楚韻為背景,十二年磨一劍,相繼推出了長篇小說《陰陽碑》《傳世古》《金匱銀樓》,形成了具有獨特地域文化魅力的“漢水文化三部曲”,向讀者展示了一幅幅精神守望地的美麗畫卷和漢水流域民眾的心態史和生存史。
《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文藝報》等媒體曾相繼刊發評論文章,評價王雄的小說填補了漢水文化小說創作的一塊空白,展現了中華民族豐富多彩的地俗文化和河流文化。近日,本網記者采訪了漢水文化學者王雄。
記者:您是中國第一位倡導和實踐漢水文化小說創作的作家,對于許多讀者而言,漢水文化這個概念還比較陌生。您能否給廣大讀者介紹一下什么是漢水文化嗎?
王雄: “文化”是有廣闊領域和豐富內涵的。目前包容量最大的定義叫做“文化是人類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總和。”歷史的沉淀產生了文化,人們的生活習慣、風土人情、婚喪嫁娶、祭祀禮儀、服飾刺繡、音樂舞蹈等經過歷史這個發展過程后,就凝聚成文化。其內核是一個民族的無意識和有意識,是一個民族文化的基因。它反映的是一個民族文化中共同的層面,表述的是一個民族共同的心理意愿。我國晚清愛國學者黃遵憲先生認為,民俗是一種歷史的因襲。它的形式主要是由不同地域民眾的生活習慣逐步發展而約定俗成的。這種約定俗成的生活習慣一旦形成,并經過傳播,民俗文化也就形成了。
我曾在長篇小說《傳世古》的代后記中,給“漢水文化”下過一個定義:即漢水兩岸人民為了自己的生存,在與大自然的搏斗中積累的經驗和形成的生活方式,是漢水兩岸人民共同創造的物質財富和精神財富的總和。顯然,這個研究對象包括整個漢水流域的地理、歷史、文化、民俗、宗教等。這是一個厚重博大的研究對象,是一部上下幾千年的“河水百科全書”,它值得專家學者深入研究。
記者:對于這樣一個課題,我想知道您最初研究它的動因是什么?
王雄:我最初研究漢水文化的動因應該說純粹是一種水文化情結。1982年的春天,我來襄陽工作后,在一個傍晚時分,第一次登上襄陽小北門的古城墻。漢水從腳下匆匆而過,碼頭的石階一級一級地伸入水中,我仿佛被電擊一般,心里有種說不出的沖動。我出生于美麗的洪湖岸邊,家門后面就是長江,按說,漢江遠比不上洪湖水面的寬廣、秀美,也比不上長江的洶涌、彪悍。踏在厚重的古城墻上,前面是逝者如斯的漢江水,身后是車水馬龍的鬧市。在這靜與動、新與舊的交接處,讓我生發出探究這座城市歷史文化的濃厚興趣。
不久,由于《隆中對》小型張郵票的發行,引發了“諸葛亮出生地襄陽南陽之爭”。我采訪了事件的全過程,寫出了長篇報告文學《爭奪諸葛亮》。為寫好這篇文章,我認真翻閱了襄陽歷史,悉心發掘漢水文化遺物,搜集整理漢水民風民俗,掌握了大量的歷史資料。一種凝重的漢水文化情結就這樣無孔不入地浸透到了我的骨子里,我產生了要給我所在的這座古城寫點東西的強烈愿望。也許從那一刻起,我開始真正地走進這座城市,走近漢水文化。
如果說,在創作之初 ,我的漢水文化意識還不是特別清晰的話,隨著創作的深入,我的創作意圖越來越明確。當我知道這是一片無人涉足的領域時,我更是帶著一種興奮的情緒,將倡導和實踐漢水文化小說創作作為己任。
記者:您剛才講了漢水文化厚重博大,您在研究過程中有哪些重大發現?
王雄:我在襄陽工作18年,后調任鄭州鐵路局機關工作。因當時的鄭州鐵路局管轄陜西、河南和湖北三省鐵路,而漢水正好流經這三個省。由于工作需要,我經常往返于漢水兩岸,順便考察漢水歷史、尋覓漢水遺存也成為我出行的必修課之一。
隨著研究的不斷深入,我的研究由感性逐漸走向理性,視野也日益開闊,收獲了許多意想不到的驚喜。我有三個重大發現:
第一,漢水的歷史早于黃河、長江。多年來,我們一直認為只有黃河、長江是中華民族的母親河,但是,在地質界和考古界有一種說法,漢水形成于地球早期的造山運動之始,早于長江、黃河7億年。1975年,考古工作者在漢水中上游地區的湖北鄖縣發現的 “鄖縣猿人”比“北京猿人”要早 30萬年左右。考古界從漢水流域發現近百處舊石器時代、新石器時代和商周時期的文化遺址,這些都證明,在數十萬年前至六七千年前,漢水流域就已有人類生息。可以說,漢水和長江、黃河一樣,是中華民族的搖籃之一。越來越多的考古證明,漢水流域是最早有人類活動的地方,漢水文化是漢文化的發展源頭,人類文明有可能發端于漢水流域。
第二、漢水是漢文化的直接發祥地。中國漢民族學會副會長、歷史學家何光岳認為,中華民族的始祖伏羲氏的后代炎帝、女媧后代黃帝均出生于漢水流域。這與《淮南子·時則篇》中的古籍記載不謀而合,它證明了中華民族、華夏之邦起源于漢江。從漢水的縱深腹地莽莽林海走出了一代神農炎帝,成了中華農業、醫藥、紡織的開山祖師。從堯舜禹,到夏商周時期,漢水流域成為匯聚南北與東西文化的大熔爐,冶鑄出了魅力無窮的秦文化、巴楚漢文化;隨國曾侯乙墓中精美絕倫的大型編鐘,已被國內外考古學界公認是代表春秋音樂文化的絕響;春秋戰國時期,一部《鬼谷子》,揣摩天文地理、世風人情,窮盡人心機變,讓諸子百家及諸侯國將目光聚焦到漢水流域。西漢的張騫,從漢水邊的城固踏出了第一條通向世界的絲綢之路;東漢的蔡倫封侯于漢水邊的龍亭鋪,發明了造紙術;張衡發明了渾天儀,率先揭開了中國地震科學和遙測技術的篇章;三國的諸葛亮躬耕漢水邊的襄陽隆中,寫下著名的傳世之作《隆中對》,鞠躬盡瘁死而后已。在漢水這個大舞臺上,曾經上演了“三分天下”氣勢恢弘、波瀾壯闊的歷史活劇,形成了兩漢三國文化一脈相承的歷史軌跡。
第三、由漢水衍生出神奇的“漢”字系列。因為有了漢水,所以有了漢中這座城市。因為秦末那場戲劇性的龍爭虎斗,讓劉邦成了漢中王。他借漢水之靈光,以漢中為基地,筑壇拜將,明修棧道,暗渡陳倉,擊敗項羽,一統天下,成就帝業,定國號為“漢”,于是有了漢朝。在劉邦創立漢朝之前,尚沒有漢族之說。劉邦起家于漢中,漢中也就成了漢民族稱謂的源頭。漢朝的臣民自然是漢人,漢人使用的語言自然是漢語。由此可知,漢族、漢人、漢字等稱謂,都源于漢朝。
西漢末年,劉秀政權同樣興起于漢水中游的南陽地區,依靠南陽潁川豪門大族支持起家,建立東漢王朝。由此可見,漢水流域在兩漢王朝建立與漢民族文化整合中所起的作用非同小可。可以說,離開了漢水流域,漢王朝、漢文化將無從談起。
在當今,3500個常用漢字中,“漢”字的頻度為0838,可謂高頻字。目前,漢語正以前所未有的蓬勃姿態走向世界,全球超過1億外籍人士學習漢語,漢語熱正在全球不斷升溫。
記者:聽了您的講述,我感覺漢水文化真的是源遠流長。請問您為什么會選擇小說創作的方式來展示漢水文化的厚重與博大?
王雄:最吸引人的表達方式,就是講故事。在所有文學表達方式中,小說是信息容量最大、表現方式最靈活、故事性最強、最受讀者歡迎的文學體裁,而漢水流域的人文底蘊很深厚、文化寶藏很豐富、民風民俗很特別,只有小說才能承載得起這么厚重的內容,只有小說才能包容得了這么豐富的內涵,只有小說才能將漢水文化轉化成故事表達出來,只有小說才能活靈活現地展現漢水流域民風民俗趣聞,也只有小說才能通過讀者更好地弘揚漢水文化。所以,我選擇了用小說創作的方式來展示漢水文化的厚重與博大。
記者:您是什么時候開始小說創作的?您能簡要地介紹一下“漢水文化三部曲”的故事梗概嗎?
王雄:我是1989年開始小說創作的。其實,我的文學創作源于一次偶然的采訪經歷:1987年,我在襄樊鐵路分局黨委宣傳部負責新聞工作,在一次采訪身患癌癥的鐵路工程師老宋時,意外地發現他抗癌的鍛煉方式竟是每天徒步行走幾里路去漢江邊上撿古錢幣。
襄陽古渡口起源于戰國時期。古人過渡,為求平安,乘渡船時都要向江水里拋擲錢幣,名曰過渡錢。這樣,襄陽古渡口的漢江底就成了一個天然的“古錢博物館”。
上世紀80年代末,由于襄陽城市建設需要,挖沙船開到古渡口挖沙石。轟鳴的挖沙船,在古渡口晝夜不停地挖著。猛然間,民工們發現出水的沙石中夾有好多“窟眼錢”,消息轟動了襄、樊二城。每天傍晚,民工們都會揣著濕潤的古幣,在江邊叫賣。常見的古錢開價一毛錢,少見的也就五毛錢。就是這個時候,我跟著老宋跑起了古渡口,成為一位古錢收藏者。
1989年,定居杭州的湖北籍作家楚良來到襄陽,我與他談起了古錢收藏。楚良對我的古錢收藏十分感興趣,建議我以中國古錢文化為題材,嘗試寫小說。我接受了楚良的建議,一氣寫了3萬多字的處女作《男錢》。半年后,湖北省作家協會主辦的大型文學刊物《長江》隆重推出了這部作品,在文學界產生了較好的反響。從此,我的文學創作一發不可收。此后的十二年間,我的長篇小說《陰陽碑》《傳世古》《金匱銀樓》相繼問世,這就是漢水文化小說三部曲。
《傳世古》是一部以中國古錢為中心意象的漢水文化小說。它著重反映一個家族的精神追求。光緒年間,錢學昌盛。杭州祥符鎮大戶人家祥符必魁玩古成癮,棄官為民,致力錢學。豈知江湖險惡,遭人算計,被人用一枚贗品“國寶金匱直萬”錢騙走了半條街的房產。臨終前叮囑兒孫:定要覓得“國寶金匱直萬”錢,以雪家恥。祥符后人秉承遺志,顛沛流離,苦苦追尋。嫡孫祥符得坤落腳襄陽,歷練成“襄陽錢王”,譽滿漢水流域。他看重名節,卻誤入花船;他暗戀沈氏,卻不提婚配;他寬容仇家,卻屢遭陷害……雖命運多舛卻矢志不渝,執意要找到魂牽夢縈的“國寶金匱值萬”錢。后經專家考證,“國寶金匱直萬”乃王莽時“金銀入庫憑證,非錢也。”祥符家族幾代人尋索與追求,乃是一個美麗的夢幻和泡影。
《金匱銀樓》是一部以中國銀樓為中心意象的漢水文化小說。襄陽金匱銀樓,流金淌銀,富甲一方。賈皮兩家,原本為莫逆之交,后反目成仇,由此拉開了綿延幾代人的恩仇故事。美麗聰慧的丫頭彩鳳走進銀樓,面對世道的黑暗和家族內外的爾虞我詐,以其睿智和干練,勇敢地沖殺出一條生路,讓奄奄一息的金匱銀樓重現昔日的輝煌。然而,在一個夕陽秀美的黃昏,已是東家太太的彩鳳卻被前夫賈二少爺砍殺于銀樓之中……銀樓賈老爺、煙館皮二爺、煙鬼賈大少爺、花癡賈二少爺,還有眾多的賣藝人、花船女、老板商人、軍政要人、地痞江匪,在銀樓內外上演了一幕幕扣人心弦的悲愴故事。
《陰陽碑》是一部以漢江碼頭為中心意象的漢水文化小說。馬背巷鞭炮鋪少老板權國思誘奸了小巷丫頭女貞,由此埋下了仇恨的種子。女貞走進權府當奶媽,卑賤之身,飽嘗恥辱和歧視。她含垢忍辱,以其干練多智,一步步實施著復仇舉動。鞭炮作坊起火爆炸,太太被炸死,權國思成了植物人,孫子權六子的小雞雞被狗咬掉……權六子憤然出走,浪跡天涯,偶結奇緣,承接了稱霸江湖的“龍鞭”,榮登襄陽丐王寶座,人稱六爺。他盤踞古渡口碼頭,仗義疏財,口碑載道。然而,鋪子杠里卻怪事迭出,大太太被人砍頭,二太太拋尸漢江,三太太遭強奸染性病爛死,管家相繼身亡。清匪反霸中,六爺被處極刑。失蹤十多年的瞎眼婆女貞竟然還活著,她一直被關在六爺杠子鋪后院的地窯里。有人說,這個故事就是中國版的《王子復仇記》。
記者:在漢水文化三部曲中,您是如何利用講故事、環境描寫、人物性格刻畫等來巧妙展現漢水文化的?又展現了漢水文化的哪些方面?
王雄:這種展現可以分為兩個層面,一個層面是自然展現。小說的故事本就發生在漢水流域,那兒的人有自己的處事方式,有自己的民俗民風和生活習慣。我在講故事的過程中,自然而然地展現了漢水文化的瑰麗色彩。比如,在《傳世古》中寫道,小翠出嫁時,她的母親要親自用兩根紅絲線給出嫁的女兒纏絞臉上的汗毛、剔眉毛,讓女兒的的臉變得光潔如玉,并在這個過程中給女兒講許多做新娘的話題。在《金匱銀樓》中寫道,銀根娶新娘時,吳媽與苗嫂則忙著鋪婚床。吳媽在床的四角被子底下放了不少的棗子、筷子、花生、核桃、藕等物,預示小兩口早(棗)得貴子,快(筷)得貴子,有兒有女花著生,孩子長得圓頭大腦(如核桃一般腦子里皺紋多,聰明),孩子的胳膊、腿長得猶如藕一樣粗壯。苗嫂有著一副好嗓子,邊鋪邊唱:“床兩頭摸摸,五子登科 ;床兩頭按按,得個狀元。”這是為圖個吉利。類似這樣的當地習俗,都是在故事中自然流露的。
另一個層面就是有意刻畫。讓人物出現在特殊的時間和地點,讓人物的生存環境多一些文化韻味。比如,在《金匱銀樓》中,我故意安排彩鳳在天貺節這一天,帶著貓咪洗澡掉入漢江,被小武子救起,引出了一段纏綿的愛情故事。而借此就將漢水流域獨有的天貺節寫進了小說。在《陰陽碑》中,我特意安排了身為寡婦的女貞在“穿天節”這天到漢江邊撿小白石,犯了大忌,遭到一幫婦女圍攻。因為相傳“穿天節”是鄭交甫與漢水女神相遇定情的日子。這天,襄陽城有情男女就會不約而同地來到城外的萬山,乘船沿江而下,在漢江邊聚會玩樂,婦女們則在沙灘上撿拾有孔竅的小石子,用彩色絲線穿起來,戴在脖子上,以祈求早日獲得美滿的婚姻,祈求早生貴子、全家平安。這樣,既動態展現了穿天節文化,又推動了故事情節的發展。
在漢水文化三部曲小說中,我深入挖掘漢水流域歷史積淀下來的人文底蘊,用心開采漢水流域的文化寶藏,對漢水流域的民俗文化進行了動態的描繪。展現了漢水流域先民堅定勇敢的精神追求、剛柔相濟的生活秉性、樂觀向上的生活情趣、五方雜處的生活習俗。有學者統計,在我的漢水文化三部曲中,漢水流域的民俗文化趣聞有117種,家族慶典文化趣聞23種、佳節文化趣聞21種、飲食文化趣聞23種、民居文化趣聞11種、服飾文化趣聞14種、茶樓文化趣聞13種、戲曲文化趣聞12種等等。這些文化趣聞通過小說人物表現出來,形成一道道獨特的民俗文化景觀。另外,還有歷史事件116件。
記者:您在三部曲中是如何塑造小說人物形象的?您認為哪些人物形象比較成功?在他們身上是如何體現漢水流域民眾文化心理的?
王雄:塑造好人物形象是小說創作的藝術使命。有學者統計,漢水文化三部曲中共有各種人物572位,其中歷史人物 260位、小說人物312位。在塑造人物形象時,除了常用的肖像、語言、行為、心理等傳統的描寫等手法外,我還十分注重用故事起伏表現人物的復雜多變,更注重用內心追求展示人物的精神氣質,更注重用細節描寫展現人物的性格特征,更注重用方言俚語來體現人物的地域特色,讓這些生長于漢水流域、生活于漢水流域、追求于漢水流域、成敗于漢水流域的人物既有著自身鮮明的個性特征,又散發著濃郁的漢水文化氣息。
《陰陽碑》中的鞭炮鋪老板權國思、奶媽女貞、丐幫六爺等;《傳世古》中的古錢收藏家祥符先生、沈氏茶娘、王鑒先生等;《金匱銀樓》中的銀樓老板賈哲義、丫頭彩鳳、小武子、卓氏等,他們都是小說里的主要人物,我塑造他們時花了許多心思,用了許多筆墨,總想他們活靈活現,栩栩如生。
由于漢水流域處于南北兩大文化板塊的結合部,人物氣質具有融合性。我試圖讓小說中的人物,在南方人纖弱的氣質中融入北方人的剛健之美,使之既有南方人溫文秀美、機智開朗的品性,又有北方人不畏艱險、豪放剛強的氣質,形成了漢水人勤勞樸實、淳厚善良、崇尚禮義、熱情好客的流域性格。他們像山一樣的堅硬、水一樣的坦蕩,成為漢水流域的文化意象和漢水文化的基因密碼。
當然,還有眾多的碼頭杠子、商行掌柜、販夫走卒,文人墨客、軍人湖匪、船工伙計、花船妓女等人物,雖然他們只是小說中的配角,但他們的身上既有正直、善良、勇敢的美德,也時而流露出自私、落后、狡黠的弱點。這些人物充滿著智慧與質樸,也有失去理性的丑陋與殘酷,彌漫著流域性格的多變與傳奇。
記者:莫言曾說:“一個作家必須要有一塊屬于自己的地方。”您寫的漢水文化三部小說地域背景都是襄陽古城,請問“襄陽”屬于您的地方嗎?
王雄:我十分贊同莫言這句話,每個作家都應有一塊屬于自己的地方。襄陽就是屬于我的地方。我人生最美好、最有朝氣、最富創造力的青春年華在這里度過,我以好奇之心、熱愛之情,沐浴在漢水文化的濃厚氣息中,感受著漢水文化的厚重博大。我用心挖掘著古襄陽的故事,描繪著古襄陽的模樣,有意識地打造了一個具有古韻古味的古襄陽。創作過程中,我將古襄陽馬背巷的店鋪畫了一個排列圖,讓小說人物在這些店鋪里出出進進。有不少北京的朋友,特地跑到襄陽,對照我的小說找故事。他們問,襄陽的馬背巷在哪?我告訴他們,就是襄陽小北門外的老龍堤,唐代詩人劉禹錫、李白、孟浩然經常去的地方,有唐詩《大堤行》《大堤曲》作證。他們問,襄陽小北門是原址嗎?我說完全正確。他們問,古渡口在哪?我說就在襄陽鐵路大橋下游500米處……這樣,襄陽的歷史故事和景點就在現代人的追尋中有了新意。
記者:我們知道,您還有大量關于漢水文化研究的散文、隨筆、學術筆記問世,能簡單為讀者朋友介紹一下嗎?
王雄:我還有一部漢水文化研究專著,名為《漢水文化探源》,書中收錄的是我的“漢水文化”博客上的文章。我曾一度很喜歡寫博客,幾乎一天一篇。我將流行的博客寫作手法運用于文學隨筆寫作,從挖掘和弘揚漢水文化的角度,積極與網友互動,對漢水之源、漢民族之源、漢文化之源進行了深入溯尋;對漢水文化的源流性、多元性、包容性和傳承性特征,進行了深刻闡述。書中還特別搜集了網友的跟帖,形成了一定的互動效應,在當時產生了較大的反響。還有一部錢幣文化專著,書名是《古錢收藏筆記》,收錄了我玩錢的心得和體會,主題緊扣漢水流域的生存與發展,只不過是以古錢幣為作引線,借題發揮而已。另外還有散文集《走過的》、《守望我的河流》等,收集了我考察漢水的感受與感悟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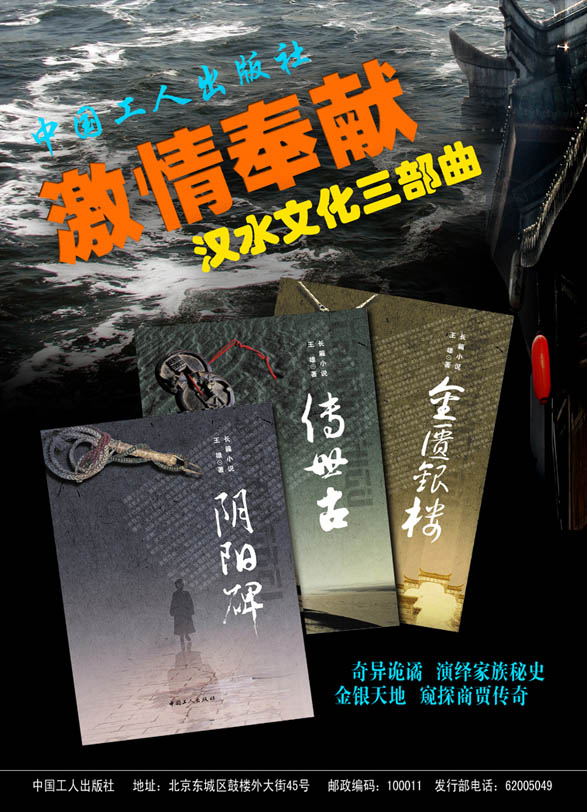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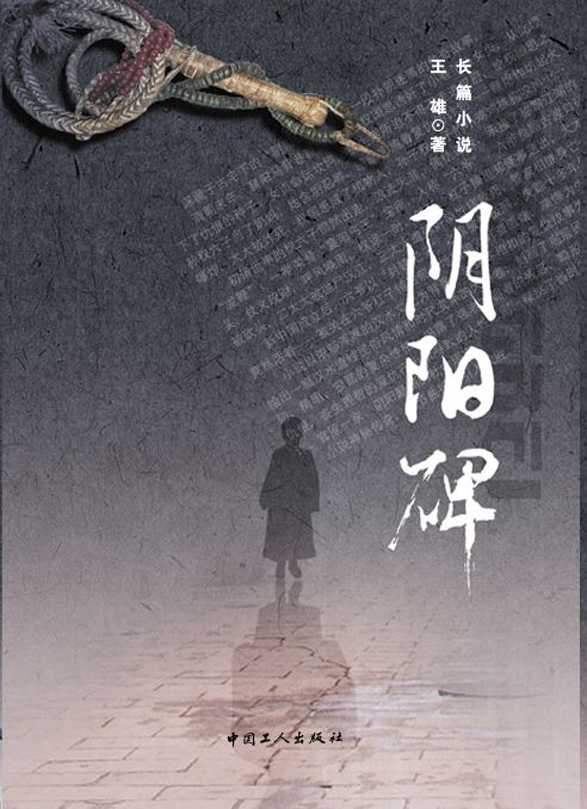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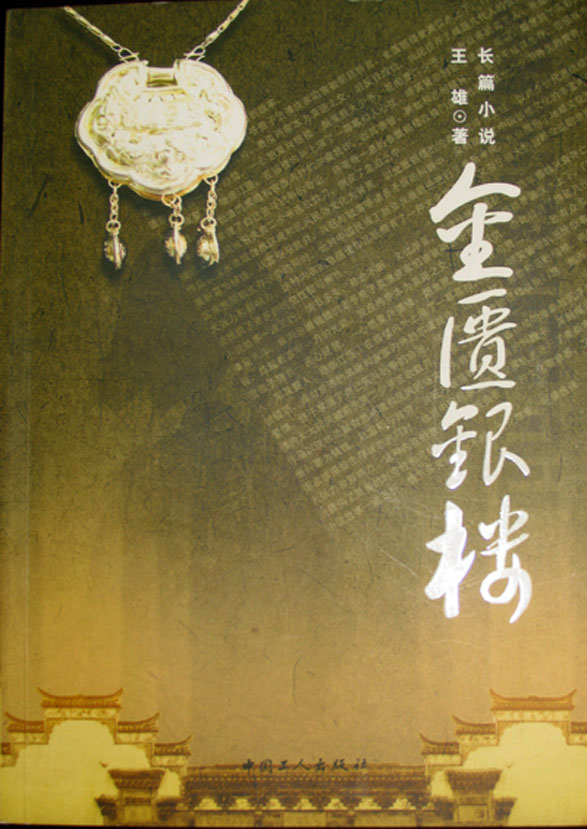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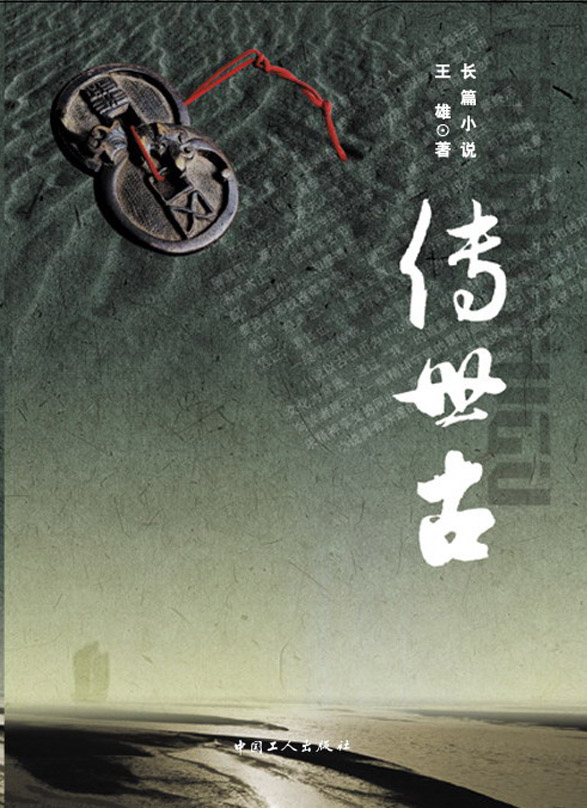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