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雕塑般的詞語鑲嵌每個詩節”
——詩人趙卡讀講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沃爾科特的《白鷺》

現場

現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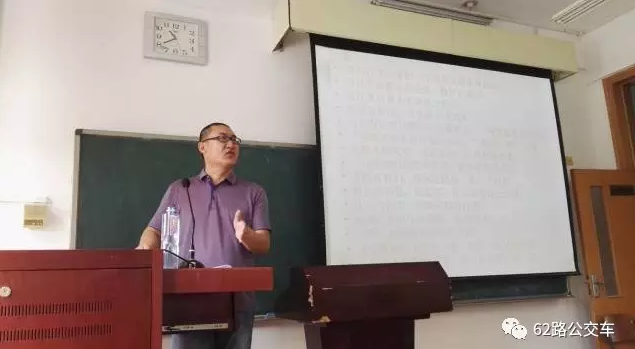
作家、詩人趙卡
“用雕塑般的詞語鑲嵌每個詩節”
沃爾科特《白鷺》
趙卡讀講(錄音稿)
地點:內蒙古大學
主持人:遠心
今天我們非常榮幸的邀請到了趙卡老師為大家講課。首先,用熱烈的掌聲歡迎他;另外,我們也有非常高級別的,應該說卡哥的粉絲來了,這是我們內蒙古著名的民族文化刊物《傳統》的主編黑梅,她也是全國著名的小說家;而且我們曝光一下,她是我們內大文研班的學生,但是她說念三年以后寫不出東西來了。這個我有時候也很無語,但是她算得上大家的大學姐,早一點進這個學校,也早一點畢業。我也是內大的學生,本科碩士都在這里。我覺得今天很慶幸,后面還會有人來聽,遲到的我們就不管了。
我們首先給大家介紹一下趙卡老師。我們發的通知你們也都看到了,邀請函中已經寫到了,他最早是寫詩的,然后這些年也在寫小說,尤其近兩年,小說的產量不少,也寫了好多評論。我這樣的開課方式,就是把外面的老師請過來,其實是我的一種理念。你們會發現學校里面都是科班出身的老師在教學生,而趙卡他是獨立批評家,也是獨立的詩人、小說家。僅在這一方面,我和他相比的話,他就更加自覺。另外,他自己經商,還在一直寫作,而且時間非常的長。包括我們內蒙古的好幾位詩人都是這樣的,三個男詩人,廣子、趙卡、溫古,我覺得這三個人都是值得我學習的作文老師,尤其是趙卡,他的評論寫的令人很佩服。我只給大家講一個細節,因為我們是寫詩的,今天早晨我又專門把網頁打開,因為我搜集你寫的在內蒙古比較著名的詩人敕勒川的時候,我看到,趙卡在2016度各大詩歌刊物,我們中國知網上能搜到的文章13篇。我給大家讀一下,這13篇中有評論,有小說,有詩歌。我現在無法判斷他的題材,我跟大家說一下這些刊物有哪些,正好也是一個普及,一個詩歌月刊,是我們詩歌界的權威刊物,還有《長江文藝》,還有《青春》,這個雜志70年代能看到,不知道圖書館現在有沒有,去翻一下;《海燕》、《紅巖》、《青島文學》、《草原》,《草原》這是目前我們內蒙古文學界級別最高的刊物;《青年作家》,這都是有先鋒性質的雜志。《新民周刊》、《駿馬》、《山花》、《新文學評論》,還有《華夏時報》。十三個是吧?你看看他發表的量,這其中有評論,小說,而且他的小說現在很熱門,很搶手,很多人和他約稿;那天中午我們預約,和他聊了一下,我一聽他小說創作的思路,讓我覺得非常接地氣。就寫他們村的事兒,他們村兒能寫一本書;然后這樣的一個發表量,我覺得請過來給我們同學講課,其實他也是在給我講課,我覺得非常有說服力;不是說只是去年發表,這是個長期的過程,他會在這樣的時間,2015年和2016年達到他的一個高峰,非常成熟的一個作家和一個評論家,所以,我們再次以熱烈的掌聲歡迎趙卡老師開始他的課。
主講:趙卡
那就開始吧。
我和你們的老師趙博士是好朋友。我沒上過大學,所以我來大學講課覺得有點兒壓力山大。在這里,我要事先說明一下,我不是來講課,是來作分享的,這樣的話,我壓力會小點,大家也能讀到更好的東西。剛才趙博士對我的介紹過獎了,我不是寫作量最多的,我是閱讀量最大的,多少年來我堅持一個原則——每天閱讀量不低于一萬字,這是我自己給自己做的基礎任務。我所說的閱讀量只是指正經書,報紙上、雜志上、微信上的、網絡上的,這些都不算,純粹的書,專指文學藝術方面的,一天不低于一萬字。上周有個朋友到我家做客,看到我沙發床上的一本,以為是什么好玩的書,拿起來一看是《堂吉訶德》,對,80萬字,一天一萬字,80天就能讀完。我的床頭放的都是這樣的書,所以說我不是寫作量最大的,而是閱讀量最大的。而且,只要是從事文學的,我一直有個建議,就是加大你的閱讀量,當你讀的多了,見得多了,什么樣的作品你都知道怎么回事了。
來之前趙老師和我說,大家現在開的課是《現代詩歌的審美》,是關于現代詩的。大家都知道,我們今天所說的詩,一般都叫新詩,咱們古典詩歌都是格律詩歌,這是相對區別說的,一百年前,忽然出來新詩了,但那個剛出來的新詩套用長者當年流行的話說是“Too young Too simple”,意思就是太年輕太膚淺了,所以現代詩這個概念是很重要的。什么樣的是新詩?什么樣的是現代詩呢?“輕輕的我走了,正如我輕輕的來。”這就是新詩。
今天分享的一個著名詩人是德里克·沃爾科特。沃爾科特1930年出生在西印度群島的圣盧西亞,以前是英國殖民地的一個詩人,這個國家,這個地區,我到今天也不知道在哪個地方,可能是太小了。沃爾科特他不僅寫詩,他的劇作也很著名,而且當過導演。他出了很多很多詩集,最著名的就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那部長詩,然后就是今天分享的《白鷺》。沃爾科特是1992年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他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品不是《白鷺》,是《奧梅羅斯》,寫他的出生地的歷史的一部宏偉的書。
沃爾科特是一個寫海洋的大師。到今天為止,我們記住了各種各樣的詩人,有寫鄉村的,有寫城市的,有寫命運的,有寫歷史的,寫海洋的這個是無可爭議的,沃爾科特是公認的大師。他寫海洋得天獨厚,他就出生在加勒比海,西印度群島是他生活的地方,第二是他詩歌的啟發就來自這個地方;但是我們不能把沃爾科特認為是地方詩人,為什么需要特意強調地方詩人呢?地方詩人和地域作家,這些年來一直很流行。比方說福克納,福克納也是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他是教練級的小說大師。我認為,大家以后要寫小說的話,有兩個師傅需要拜訪,一個是海明威,一個是福克納。你要是從他們那里學到東西,寫小說很快上手。我呢,就把福克納暗暗認為是我師傅,我認的另外一個師傅是胡安·魯爾福,寫《佩德羅·巴拉莫》那個。福克納主要是寫美國南方的,他那個地方叫做“約克納帕塔法縣”,這個地名太拗口,不知道我謅對了沒?他這個里面的東西中國很多人就受了影響,比方說莫言,他就寫高密縣東北鄉。他的小說像《紅高粱》系列,《豐乳肥臀》《檀香刑》等,包括他獲諾貝爾文學獎的《蛙》,還有《生死疲勞》都是以這個地方為原型寫的。再舉一個例子,著名的《白鹿原》,陳忠實寫的,把一生的賭注放到一個叫白鹿原的地方。所以說很多人就寫一個地方,專注即成功,我后來就寫土匪鄉,不知道行不行?我老家薩拉齊土匪太多了也出名了。但作為地方詩人地域作家有他的局限性,這個放到后面說。就是說,沃爾科特靠了三樣東西寫,他所生活的加勒比海,英語和他的非洲祖先。這三樣東西集中在沃爾科特身上,這就是說花里胡哨的,而他一生都在探索這種花里胡哨的關系。為什么是這三樣呢?加勒比海,是他的出生地,英語是他創作的語言,非洲的祖先是他血液里的東西,就是說寫成他作品的風格。所以,諾貝爾文學獎頒給他時,授獎辭說的很準確。因為幾乎每一個作家寫作都離不開這三樣東西,就是你在什么地方,那個地方就會影響你,比如內蒙古,內蒙古的某個老實巴交的作家,像鄧九剛先生,祖籍山西的,然后生活在呼和浩特,他寫的是著名的旅蒙商大盛魁,但很一般了,我也在寫一個大盛魁小說,凡是和犯罪有關的東西這里面都寫了,殺人,放火,偷竊,違法,等等都有,這是題外話。
我尊敬的詩人、翻譯家黃燦然老師他主要翻譯詩歌,是這些年來翻譯詩歌的最好的,黃燦然老師也翻譯過沃爾科特的其他詩,他在他的評論中介紹沃爾科特就說,“具有歐洲和非洲血統”,他這是說,歐洲人和咱們中國人有一點不一樣的是他的血統非常復雜,尤其他們有殖民地,他就很復雜;又有信教的傳統,所以在一個人身上就弄不清楚他的血統是來源于哪兒,種族來源于哪兒,他到底說什么話。有的人生于非洲,說著英語,然后生活在亞洲。所以沃爾科特是棕種人,并不是黑人。我們平時介紹時,大部分說沃爾科特是黑人,實際上不是,他是棕色種族。他是講英語的,當地人講方言,所以說沃爾科特身上自帶另一種生命,“被分割的孩子生錯了膚色”,這句詩我覺得他自己說自己說的很準確。沃爾科特的詩是英國詩歌式的風格,什么是英國式詩歌風格呢?大家看這個伊麗莎白一世女王時代的詩歌就知道了, 伊麗莎白一世女王時代是英國文學輝煌也就是歐洲文藝復興的那個時代,像莎士比亞就是活躍在那個時期,就是說英國的詩歌有一個特點,優雅。優雅有時候也不準確,估計都是被朱生豪給譯雅了,我看莎士比亞的語言挺野蠻的。包括華茲華斯那些人,也是詩人,今天看來一般了,或者說被譯一般了。當時這些詩人的詩歌地位是什么樣的?我們平時說標準英語,什么是標準英語?就是說你讀華茲華斯,你讀完他們的詩歌就知道了,英國標準的純正的英語就是這樣的。所以說沃爾科特繼承了英國標準的純正的英語。我呢,是當過一個學期的英語老師,我那會兒是剛出學校后沒事干就跑去鄉中學當英語老師了,連半瓶醋都算不上,瓶底兒吧,后來走上社會把當時學的那點英語全給忘掉了。學英語的特點是如果你不是每天說英語就忘得很快。又跑題了,再說沃爾科特。沃爾科特在他的《飛翔號縱帆船》中說:“我只不過是一個喜歡大海的紅種黑人,我受過良好的殖民地教育,我身上有荷蘭、黑人和英國血統,所以我要么不是任何人,要么是一個民族。” 這樣的表達是在中國的作家身上不會出現的。為什么呢?因為沒有一個中國的作家會說,我是一個雜種。所以你看,外國人很誠實。比如博爾赫斯,博爾赫斯是阿根廷的,有人采訪時說你這個傳統來自阿根廷,博爾赫斯糾正說:“不,我的傳統來自歐洲。”有人問,趙老師,您傳統來自哪兒?我會說我的傳統來自《詩經》,其實這是胡說。我學的第一首正兒八經的詩是中國的,但第一部小說絕對是外國的,我看過外國的才發現,我這個崇洋媚外非常正確,看中國的我估計會很麻煩,眼界不開闊。所以沃爾科特這種嘗試,我也不知道他是什么種族,所以表明他非常誠實。我的朋友、詩人草樹,我剛才來的路上和他打招呼,跟他說我一會兒要和大家分享沃爾科特,會引用他一篇文章里的觀點,他表示很榮幸,當然是謙虛了。草樹是這兩年中國寫的非常好的詩人,他也主要讀外國詩人,他對沃爾科特的喜歡不是一般的語言能夠表達,他說:“無意中從網上看到了詩人兼翻譯家明迪上傳的一段沃爾科特的詩歌朗誦視頻。83歲的老詩人雖然行走要依靠輪椅了,但他站著朗誦,聲音底氣十足,毫無老態,明亮里夾帶著重濁。他的姿態讓我聯想起《珍珠港》中的羅斯福總統,而聲音的延時部分又太像甘地,只是比甘地更有力量,目光也更犀利。”哈哈,就是喜歡一個詩人,對他的動作和姿態都要喜歡上。
趙娜老師做了兩張圖,這圖還沒選好,網上有沃爾科特和馬爾克斯的黑白的對比圖,長得太像了。因為馬爾克斯是我非常非常喜歡的作家,寫《百年孤獨》和《迷宮里的將軍》那個,你們一定要看。他倆的照片太像,有時候看到沃爾科特又想這是不是馬爾克斯?
介紹完沃爾科特本人,接下來接觸一下《白鷺》,也就是今天我們分享的這首詩。《白鷺》是本詩集,我買回來不知道怎么回事找不到了,要不今天就帶來了,我們現在讀到的《白鷺》是一個從網上解壓下來的。中文譯本是我尊敬的一個朋友,詩人、翻譯家程一身先生翻譯的。我們見到的《白鷺》應該有兩三種吧。我認為,程一身先生的《白鷺》是我目前讀到的最好的譯本。流暢,就是你把外國詩翻譯成中文流不流暢是個很重要的標準。很多人為什么發憷外國作品呢?地名和人名之外,主要是國外的句子,長句,倒裝,在閱讀上很不習慣。這個很考驗翻譯家的功底,所以程一身翻譯的非常流暢,而且很中庸。中庸就是合適,適度,正好,再恰當不過了。實際上,我們再舉個很形象的例子,中庸就是最好的白酒,酸甜苦辣的味道都有,但每一種味道都不露頭,這就是中庸。所以程一身教授翻譯的《白鷺》,盡顯中文之美。
《白鷺》出版于2010年,沃爾科特憑借《白鷺》獲得了艾略特獎。別小瞧這個獎,入圍的10位作家中,包括詩人謝默斯·希尼,希尼也是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你看希尼的詩,希尼和弗洛斯特都是農民詩人,人家寫農民詩和中國的不一樣,咱們中國的農民詩,都是孩子們讀的,什么收割麥子啊太陽光芒啊,你看弗洛斯特和希尼時就知道外國詩人比中國詩人更技高不止一籌了。
我們今天分享的是《白鷺》的核心章節《白鷺》。《白鷺》是一本54首詩組成的詩集,最核心部分是里面的11首組詩,組詩內含金量最高的就是這個。拿到這本詩集你就明白了。《白鷺》是其中核心中的核心部分,就是說這部詩集給它增加光彩,能讓它一舉成為全球大家都很服氣的一首詩。所以主要就是講《白鷺》這本詩集中的一首詩《白鷺》。他這些詩都沒有注明創作時間,不知道什么時候寫的,但是有一點是透明的,就是沃爾科特老年時期的作品,詩集出版時沃爾科特已經80歲了。這國外的詩人到了80歲還在寫,這和國內的詩人是不一樣的,你們誰能給我舉個例子,中國的詩人別說80歲了,60歲以后還能好好寫作的?中國的詩人,青春期靠才華寫作,中年寫作,中年寫作的概念出自羅蘭·巴特,被歐陽江河引用最厲害的那個概念,中年時期靠經驗寫作,60歲以后已經寫不過他中年時候的作品了,創作能力明顯下降。但說老年寫作的厲害,除了沃爾科特之外,另外一個詩人是葉芝,葉芝是愛爾蘭詩人,也是獲得過諾貝爾文學獎的,葉芝這個人很了不起,他的秘書是龐德,龐德有一個厲害的地方,艾略特的《荒原》,那也是獲過諾貝爾文學獎的主啊,他改的。艾略特寫完《荒原》之后找龐德看看他寫的作品,龐德直接砍掉一半兒,砍完一半兒后成了世界名作了。同時期,詩歌里是《荒原》,小說里是喬伊斯的《尤利西斯》,這些都是進入文學史的東西。當年海明威也好,還是菲茨杰拉德也好,大家的小說都要找龐德看看。所以我很懷疑,他是葉芝的秘書,是不是葉芝的很多詩他也都改過。因為我們大家讀到的葉芝最熟悉的詩,比如《當你老了》,還有《駛向拜占庭》《麗達與天鵝》這些都是名噪一時的名作,到今天都是經典。就像葉芝這樣的作家后來也遇到了問題,就是不想寫了或者說寫不動了。但葉芝和別人不一樣的地方就是,他到晚年的時候寫出了《人與回聲》也是非常厲害的名篇,他寫人的一生的命運是什么?終生的勞役。所以說這都是真正的大詩人。終生寫作的最著名的應該是歌德,我們今天看到的《浮士德》實際上是一部未完成的作品,他年輕時寫三部曲作品,最著名的就是拿破侖行軍打仗時帶著那本《少年維特之煩惱》,那是盡顯年輕時的才華,炫耀的東西。到了晚年他覺得這個東西不對了,所以寫了《浮士德》。《浮士德》就很少有技巧,就是說一個人一生經驗的結晶。他不是一首詩,是一個劇,這個劇恐怕下輩子也搬不到舞臺上了,終生無法在舞臺上上演的劇,寫了一輩子,到死還沒寫完。這就是國外的大作家,終生寫作。所以我和我的朋友廣子在搞《中文》雜志時,最后定下的標語就是向終生的中文寫作者致敬。我們年輕時候寫過一兩部好作品這不算什么,老年時候寫過一兩部好的作品,這也無所謂,最重要的是做一名終生的、持續的中文寫作者,這才是作為一個職業作家、職業寫作者的一個終極意義。很多人獲得了諾貝爾文學獎之后還能寫出大作,沃爾科特就是獲完諾貝爾獎十年后寫出《白鷺》的。這個就是說,像馬爾克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作品是《百年孤獨》,之后又寫出了《霍亂時期的愛情》。很多人是看過《百年孤獨》的,大作家的大作品,那不是影響中國,而是影響全球的很多作家,但是《霍亂時期的愛情》,在技巧上和細膩程度上要超過《百年孤獨》的。為什么外國人寫愛情寫的好呢?咱們中國人寫愛情是寫年輕人的愛情,中年人的愛情,馬爾克斯寫的是老年人的愛情,寫做愛。看完之后你目瞪口呆,什么叫做巨大的才華,無法超越這個。在這兒不能用語言描述,用語言描述就褻瀆了,我建議大家看一下,就是說好的文學作品會讓你終生難忘。
人們是怎么對沃爾科特評價的呢?沃爾科特是1992年憑借《奧梅洛斯》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的,這是一部長詩。國外有傳統,他們的希臘英雄主義傳統太強大。國外有兩個傳統,一種是希臘傳統,一種是宗教傳統,所以說很多人寫東西喜歡拿他們的希臘傳統和宗教傳統寫東西。沃爾科特也是借鑒中國人所說的抄襲仿照的意思,但是人家水平高。借鑒荷馬史詩《伊利亞特》和《奧德修紀》的長詩,寫完了《奧梅洛斯》,然后獲得諾貝爾文學獎,被譽為“加勒比史詩”,沃爾科特也被譽為“當代的荷馬”。這個稱號是無上光榮的,為什么呢?假如有人說我,趙卡是當代的莫言,那我就會感覺到無上榮光。荷馬,這個是歐洲文學的源頭之一。歐洲哲學的源頭來自蘇格拉底、柏拉圖、亞里士多德,文學的希臘源頭來自一個是荷馬,二是古希臘的戲劇家。所以說創作,我為什么剛開始就強調閱讀呢?沒有閱讀就不會有資源,你要大量閱讀才能利用資源,你越有強大的資源,就能寫出強大的作品。我們說抄襲,今天這個抄襲,明天那個抄襲,我說我也抄襲。你抄襲的哪兒?我說,我告訴你我抄的誰,我說了一串名字,你沒讀過,你想指責我抄襲都沒辦法,我覺得是我抄的好。我有個中篇小說,給廣子看,問這篇小說寫得怎么樣?他說:“這是我目前看到你寫得最好的小說。中國幾乎沒有超過的。”這就是抄的好,但他反手說,“要不是我剛看完《佩德羅·巴拉莫》”,就被你騙了!”哈哈!當然抄也不是一個字一個字抄,你明明知道我抄,卻又說不出我哪個字是抄的,所以說這是我提倡的寫作的投機取巧的辦法。
羅伯特·格雷夫斯是英國的詩人、希臘學家,他說:“沃爾科特處理英語時,對英語內在魔力的領悟要比他大部分(如果不是所有)生于英語地區的同代人來得深刻。”國外有個很奇怪的現象,像納博科夫是俄羅斯的,他到美國之后用英語創作,寫得比美國人還像美國人,這就很厲害了。布羅茨基,那也是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被流放后到了美國,他的大量散文是用英語寫的,寫的比英國人和美國人都好,就像我們見到老外時,中文說的比中國人都好。咱們著急還滿嘴大茬子味兒,我這個武川莜面土豆味兒,外國人說的那么好,就這個意思。沃爾科特說:“我無風格可言。”這個沒風格不是自謙了,是自夸了。沒風格就是他的風格,為什么呢?剛介紹里說過,他的背景,他受的教育,包括他祖先的來源,讓他把各種風格容納于一身。所以說,布羅茨基非常推崇沃爾科特,他說:“你可以說他是自然主義的,表現主義的,超現實主義的,意象主義的,隱逸派的,自白派的,等等。”這些都是當時美國、法國那些國家非常著名的文學流派,像自然主義,華茲華斯他們都是自然派的,意象主義就是龐德他們。意思就是說,沃爾科特,我們所知道的這些著名詩人風格在沃爾科特身上都有,但是都不冒頭,就是我剛舉例白酒那個說法,都不冒頭,這就是水平。但是這里有什么問題呢?出現個人身份危機。你到底是誰?批評家首先說:“一位西印度群島詩人”或“一位來自加勒比海的黑人詩人。”一般都是這樣介紹的。就像趙卡是內蒙古的詩人,黑梅是來自通遼科爾沁的小說家。有時候這么介紹時,心中很不爽。我是內蒙古籍的全國著名作家,不是內蒙古作家。這是個人膨脹,當然這是開玩笑的。來自加勒比海的詩人,加勒比海范圍太廣,應該說我是英語世界詩人,所以說給人的定義不準確讓人很不爽。布羅茨基在一篇評論沃爾科特詩歌的文章《濤聲》中認為,這種定義之短視和誤導,并不亞于把救世主當做一位加利利居民。“這些顯然要把他視為一個地方作家的企圖,是一種思想上和精神上的怯懦,這種怯懦可進一步歸因于批評界不愿承認這位偉大的英語詩人是一個黑人。”的確如此。中國也是這樣,賈平凹寫的挺好,農民,莫言也是,自己不懂的東西還要胡亂評價,以后要遠離這種人。什么叫遠離這種人?一定要遠離你們身邊懂文學的人,你身邊人太容易影響你,什么也不懂還要評價。
關于沃爾科特的特點, 美國批評家斯文·伯克茲 在《指定繼承人——評德里克·沃爾科特的《仲夏》》一文中說,“他的引導者包括伊麗莎白一世和詹姆斯一世時代的詩人,華茲華斯,丁尼生,葉芝,哈代和羅伯特·洛威爾(此人也曾嘗試把這一序列的傳統合并到他自己的作品中),我們可以聽到他們的聲音象織機上的緯線一樣在他的詩行中穿梭。與之相應的是,從中也可以聽到本地的影響,譬如加勒比地區的方言語匯和句法”。這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把當代和前一代最優秀詩人的營養價值拿來,然后結合自己的本地方言寫出非常好的作品。特別一提的是莫言,莫言學的是誰呢?是馬爾克斯和福克納。福克納是寫南方的嘛,他把這兩個人的特點學到之后呢,寫高密東北鄉。山東的本地方言,語言和故事,拿出去后就傻了,怎么中國還有這么好的作品呢?所以說莫言的小說《紅高粱》,張藝謀拍完之后在柏林電影節上拿了獎。我在北京現代文學館參加麥家的一個講座,邀請的嘉賓中有莫言。當時我就感到龐大的氣場,坐著坐著聽說莫言來了。麥家是今天的主人吧,莫言進來的時候自帶光芒,所有人的照相機往他身上打,我就和旁邊的朋友寧夏的詩人阿爾說:“兄弟,咱們啥時候要是能這樣就沒問題了。”有老人沒座位,就坐在地下聽,他也聽不懂講什么,就是去看,這就是氣場。莫言為什么有這么大的成就呢?他在中國是最聰明的,最自覺,最勤奮的人,把國外的小說和文學作品容納到自己的文學作品當中,然后創作了獨樹一幟的莫言小說。今天這么多人寫小說,當把莫言的小說拿到手的時候,你看到的根本不是和其他人一樣的作品,和中國所有的作家都不一樣。這就是莫言。
毫無疑問,沃爾科特是一位英語的大師。我很奇怪,國外的任何一個國家一旦用英語寫作時,他的英語水平就超過他本國的人,所以很多人特意強調英語大師。在這兒想強調什么問題呢?就是翻譯的重要性,翻譯中的缺憾。每次翻譯一定是把原著中的一些東西丟掉了。所以說你怎么才能把它留住?舉例子,龐德等翻譯中國詩文,現在在想用外語怎么翻譯?比如“床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這是一個字一個字對的啊,英語的這幾個單詞對上,怎么翻譯啊?中國的漢語是抑揚頓挫,窗前/明月/光,疑是/地上/霜,英語不知道怎么對。所以說肯定在翻譯過程中丟掉了一些東西。“他灰溜溜的跑了。”“灰溜溜”怎么翻譯這個味兒?就存在這種問題。因為我不懂翻譯,我知道的好多詩人朋友他們也是翻譯家,王家新老師啊,黃燦然老師啊,像草樹啊,李以亮啊,他們也有些困惑。水平挺高,我估計是用其他方法轉換過來了。詩人、翻譯家黃燦然老師認為“他這種風格,剛好適合用來表現加勒比海生活的豐富性和多樣性,西印度群島也因此找到一位能夠賦予它不朽魅力的偉大詩人。他的語言明亮練達,他的詩句充滿陽光和空氣,海灘,海島,沾在皮膚上的沙粒和海鹽,而這種鮮明的色彩是與他那畫家的眼睛分不開的。他不僅是一位詩人,戲劇家,還是一位水彩畫家和油畫家。”
為什么今天講沃爾科特呢?沃爾科特這個名字對中文讀者來說應該是很陌生的,我們很多人熟悉的是奧登、里爾克、葉芝、艾略特、史蒂文斯、弗羅斯特、布羅茨基、特朗斯特朗姆、博爾赫斯、波特萊爾、惠特曼等等,荷馬、但丁、莎士比亞就更不要說了。所以,講沃爾科特要比講這些詩人輕松的多,你們不熟悉嘛,好講,因為講錯了也不知道。要是講奧登、里爾克、艾略特大家都知道咋回事,就不敢講。所以這也是投機取巧的事兒。大概就是說,關于沃爾科特,關于《白鷺》,關于英語詩歌的一些特點,剛才已經說了,雖然講不全面,大家知道一點兒。今天為什么說不是講課,而是分享?因為講課不是我的專長,我是寫評論的,斯坦納說評論家是太監,哈哈,現場給大家評論這首詩,也沒多大意思,估計你們也不愛聽,還是分享吧。分享詩歌的方式最好是閱讀,只有閱讀才能感受到詩歌之美。整個《白鷺》不讀,但是核心章節要讀下來。我的普通話不好,但是課堂上一定要讀。我在北京的時候,歐陽江河老師講課,講著講著就覺得沒意思了,就開始讀。他是技藝好,他讀詩會聽的如癡如醉。
程一身老師這個譯本翻譯的非常好。我雖然普通話不好,咱們還是讀一遍,感受一下中文之美。我給大家一個提示,就是朗誦詩歌切忌朗誦腔。我說的朗誦腔是以中央電視臺的主持人為標準的裝腔作勢的朗誦。朗誦是詩人怎么寫的怎么朗誦就行。沃爾科特怎么寫的呢?他老年了,以我本人的理解能力,讀一遍吧:
1
細察時間的光,看它能有多久讓
清晨的影子拉長在草地上
潛行的白鷺扭著它們的脖子吞咽食物
這時你,不是它們,或你和它們已消失;
鸚鵡在日出時咔噠咔噠地發動它們的船只
四月點燃非洲的紫羅蘭
面對鼓聲陣陣的世界,你疲倦的眼睛突然潮濕
在兩個模糊的鏡頭后面,日升,日落,
糖尿病在靜靜地肆虐。
接受這一切,用冷靜的判決
用雕塑般的詞語鑲嵌每個詩節;
學習閃光的草地不設任何籬笆
以免白鷺被刺傷,在夜間呻吟不止。
剛才我朗誦的第一節。
我們今天分享的作品好在哪里呢?現代詩好在哪里?我說的現代詩不是新詩,新詩是民國的詩,70年代末以前的詩,屬于不怎么成熟的。現代詩好在哪里?就說咱們今天的主題。這首詩的第一句“細察時間的光”,這就是老年之作,因為年輕人不寫時間,因為他不缺時間,所以這一看就是老年人。“細察時間的光”起句不平凡,關于詩歌的主題一目了然。這就是我們傳統語文教育中經常被問的一個弱智問題,也是我本人從事文學寫作以來最為困惑的一個問題,你寫的是什么意思呢?也就是說中心思想。文學作品為什么要有一個中心思想呢,沒有中心思想不能嗎,來,你給我說說卡夫卡和博爾赫斯每一篇小說里的中心思想?后來我也不得不妥協這個中國語文式問題,我得回答,文本是有中心思想的,比如說,所有的文學作品里有一個共同的中心思想:時間。把時間作為中心思想是很安全的。一個詩人或作家的偉大首先在于他如何感受、處理“時間”這個主題,比如但丁的《神曲》,普魯斯特的《追憶逝水年華》,比如艾略特的《四個四重奏》,包括卡夫卡的《城堡》,都是在處理時間的問題。在讀的時候我們就能感受到他處理的問題就是“時間”。
2
這些渾身潔白,鳥嘴發紅的白鷺多么優雅,
每只都像一個潛行的水壺,在潮濕的季節
茂密的橄欖樹,雪松
撫慰咆哮的急流;進入平靜
超越欲求擺脫悔恨,
或許最終我會達到這種境界,
在陽光下,棕櫚葉像轎子一樣低垂著
影子在它們下面狂舞。在我充溢著
所有罪孽的身影進入遺忘的
綠色灌木叢以后,它們就會到達那里,
一百個太陽在圣克魯什山谷
上升又下沉,而我的愛如此徒勞。
3
我看著這些巨樹從草地邊緣騰空而起
像膨脹的大海,卻沒有浪峰,竹林陷入
它們的脖子,像被繩子拴著的馬匹,黃葉
從震蕩的枝條被撕下來,雪崩般塌落;
所有這一切都發生在暴雨驟降之前,
天空如同被浸透的帆布,在絕望地航行
風在亂紙中猛吹,完全籠罩了山巒
似乎整個山谷是一枚安然度過風暴的豆莢
而森林不再是樹木,而是奔騰的海浪。
當閃電炸裂,雷聲吱嘎作響如同咒罵
而你是安全的,躲在圣克魯什深處的
一間黑屋里,電光一閃,當前突然消失,
你暗想:“誰會為顫抖的鷹,完美的白鷺
和云色的蒼鷺,還有連看到黎明虛假的火焰
都感到恐慌的鸚鵡提供住房呢?”
我們從第一節開始一直感受它的美,另外就是說,他處理時間的方式是“細察時間的光”,這幾句你會想到什么,《圣經-創世紀》的開篇,“神說,要有光,就有了光。”(呂振中譯)這就是偉大詩篇的開頭格式,也就是我講營銷課時說的起手式。
剛才我們讀第二節第三節感受到了什么?第一個特點是時間,第二個你看他的修辭,剛才讀的時候估計大家都感受到了,《白鷺》如鉆石光芒四射,也就是說織錦般的繁復華麗的修辭太強大了。中國的新詩太膚淺,太簡單。你看它的比喻裝飾句子,沒錯,我說的是修辭裝飾,而且我始終認為,那些能夠流傳下來的詩主要是依靠修辭裝飾過的力量,包括中國的許多古典詩詞也一樣。“這些渾身潔白,鳥嘴發紅的白鷺多么優雅,/每只都像一個潛行的水壺,”“白鷺”優雅得像“水壺”太新鮮了,以前沒見過。
我們強調詞句,就是說你的詞語、句子要怎么運用。一定要把最合適的詞語安排到最恰當的句子里。這樣的話,一首詩讀出來就和別人不一樣了。這樣的句子在《白鷺》里面,天衣無縫的綴滿了全詩,美到極致。像“有時像保齡球瓶一樣直立,”“當閃電炸裂,雷聲吱嘎作響如同咒罵”等等,正如詩中的一句:“用雕塑般的詞語鑲嵌每個詩節”。就是每個句子里,他的用詞都像鑲嵌的,有雕塑的美感,建筑感。如果用一些很普通的詞語,就沒有了美感。
咱們繼續再往下讀兩節:
4
這些鳥持續為奧特朗充當模特,
在我年輕時,一本書中雪白的白鷺
或白色的蒼鷺會像圣克魯什翡翠綠的
草地一樣打開,深知它們看上去多么美麗,
完美地昂首闊步。它們點綴著這些島嶼,
在河岸上,在紅樹林的行列或養牛的牧場里,
在池塘上方滑翔,然后在小母羊光潔的
脊背上保持平衡,或者在颶風天氣里
逃離災難,并用它們令人震驚的戳
啄出記號,似乎在它們神話的高傲里
研究它們是完全的特權
它們撲扇著翅膀從埃及飛越大海
伴隨著法老的朱鷺,它橙色的嘴巴和雙腳
呈現出安靜的輪廓,裝飾著教堂的地下室
隨后它們展翅起飛,翅膀撲扇得很快,
當它們撲扇翅膀時,當然像一個六翼天使。
5
那永恒的理想是驚奇。
陰冷的綠草地,安靜的樹木,那邊山坡上
的叢林,接著,一只白鷺白色的喘息使
飛行進入畫面,然后用它笨拙的腳步
搖搖晃晃地站立,那么筆直,白鷺的象征!
另一個想法令人驚奇:站在樹稍的
一只鷹,悄無聲息,像一只獵鷹,
突然沖入天空,用那種和你相同的高度冷漠,
在贊揚或責備之上盤旋,
此刻它落下來,用爪子撕扯一只田鼠。
草地的事件和這種公開的事件是相同的,
一只白鷺驚奇于這個事件,高處的鷹在嗥叫
沖著一具死尸,一種純粹是虐待的愛。
當我們知道了它的主題和修辭,有主題,有修辭后,詩的好還要看氣息。我們讀一首詩時,氣息不順就會特別難受。假如讓我們讀福克納、喬伊斯的小說,為什么很難讀?除了特殊的句式設計之外,有種意識流的成分,我特別不喜歡意識流,意識流這種東西讓人上氣不接下氣,感覺氣息不好。真正的好作品,首先要好讀。如果有讀過美國詩人金斯堡《嚎叫》和法國詩人圣-瓊·佩斯《遠征》的,一定會被詩人的高亢剛猛的氣勢所震懾和折服,但你們見過平時人們會朗誦嗎?不會。真正的好句子,舉個例子,大家見過最多的是像葉芝的《當你老了》這樣的詩口口相傳。這里面的奧秘就在于氣息,所以你看《白鷺》的氣息,均勻、平衡,有古典音樂般的節奏感,所以程一身翻譯《白鷺》譯出了中文之美。每一行詩都會給人帶來巨大的愉悅感,和其他的英語詩人比如艾略特、史蒂文斯、迪蘭·托馬斯、西爾維婭·普拉斯等都不一樣,和英國浪漫主義的偉大先賢們如雪萊那種尖銳、渾身似火的明亮也不一樣,沃爾科特是將高音的嘹亮和中音的渾厚結合起來的一種獨特的發聲,這個時候我們就會覺得他的來自加勒比海地區獨特的殖民文化和本土文化的出身給予了他詩的獨特魅力。簡單來說,就是你出生在海洋地區,你的嗓子里都帶著潮氣.
繼續讀詩:
6
圣誕節這周過了一半,我還不曾看見它們,
那些白鷺,沒有人告訴我它們為什么消失了,
而此刻它們和這場雨同時返回,橙色的嘴巴,
粉紅的長腿,尖尖的腦袋,回到了草地上
過去它們常常在這里沐浴圣克魯什山谷
清澈無盡的雨絲,下雨時,雨珠不斷落在
雪松上,直到它使這里的曠野一片模糊。
這些白鷺擁有瀑布和云的
顏色。我的一些朋友,已所剩不多,
即將辭世,而這些白鷺在雨中漫步
似乎死亡對它們毫無影響,或者它們像天使
突然升起,飛行,然后再次落下。
有時那些山巒就像朋友一樣
緩緩消失了,而我非常高興的是
此刻他們又回來了,像記憶,像祈禱。
7
伴隨著落入林中的一片悠閑的葉子
淺黃對著碧綠旋轉——這是我的結局。
不久將是干枯的季節,群山會生銹,
白鷺上下扭動它們的脖子,彎曲起伏,
在雨后用嘴巴捕食蟲子和蠐螬;
有時像保齡球瓶一樣直立,它們站著
像從高山剝下的棉絮似的果皮;
隨后它們緩緩移動,用雙腳張開的指頭和
前傾的脖子移動這么一只手的寬度。
我們共有一種本能,那種貪婪供應
我鋼筆的鳥嘴,叼起扭動的昆蟲
像名詞那樣吞咽它們,當它書寫時
鋼筆尖在閱讀,憤怒地甩掉它的鳥嘴拒絕的食物。
選擇是這些白鷺的教導
在寬闊空曠的草地上,安靜而專心地閱讀時
它們不斷點著頭,這是一種難以表述的語言。
“鋼筆尖在閱讀,憤怒地甩掉它的鳥嘴拒絕的食物。選擇是這些白鷺的教導”。這個很有意思,這就涉及到技藝。主題和語言確定之后,能不能寫出令舉世折服的詩篇其實就看一個詩人的技藝了,注意,是技藝而不是技巧,技藝貫注的人生的閱歷和經驗,技巧要等而次之;我們剛才讀過一遍,《白鷺》感情充沛,令人驚嘆的高音和渾圓的中音恰到好處的調換共鳴,一生的時間都奉獻給了詩歌。這樣的句子出來我一點兒都不奇怪。風格化的描述服從于內心起伏的激情,你能想象一個80歲老人體內洶涌熾熱的激情嗎?修辭雄辯而精確、用詞驚心動魄而準確、語調哀而不傷,斷句舉重若輕,這個是我個人的總結。譯者程一身說,“他是一位平衡大師,準確地計算好了每一個詩節中杠桿的比例,并服從于內心的涌流和生命的經驗。”太有魅力了。作為一個世界級的詩人,寫詩的時候,和我們初學者寫詩是不同的。技藝高超。這就是我們說的老師傅.
我們再看最后這節:
8
我們在圣克羅伊一個朋友家的游泳池邊
約瑟夫和我正在交談;他停止談話,
這次來訪我本希望他會快樂,
喘息著指出,并非靜立或闊步
而是固定在這棵巨大的果樹上,一種景象使他震動
“就像某種來自博施的東西,”他說。那只大鳥
突然飛到這里,或許是同一只鳥把他帶去,
一只憂郁的白鷺或蒼鷺;說不出的話
伴隨著我們,像歐邁俄斯,第三個同伴
什么得到他,他愛雪,什么就會讓它呈現,
這只鳥泛出一種幽靈似的白光。
此刻正值中午或傍晚,在草地上
白鷺一起靜靜地向高處飛翔,
或者航向海綠色的草地,如同一場劃船比賽,
它們是天使般的靈魂,像約瑟夫的靈魂一樣。
這是《白鷺》這本詩集的核心,詩共8節。所以讀完之后,我們最后要說感受。《白鷺》是一部老年之詩,沃爾科特寫《白鷺》的時候,已經是享譽世界的大詩人了,意味著不再有身份焦慮和精神壓抑這種情緒了,年輕的作家有種焦慮,生命的焦慮和寫作焦慮。沃爾科特當時有了名譽地位,寫《白鷺》是毫無焦慮感的。所以你看《白鷺》的語調、語速、語感都平和和寬闊無比;這個時候我可以說一下這首詩的中心思想了:表達了沃爾科特對時間流逝和死亡迫近的一種思考。這種思考不是那種難以抑制的悲傷,而是如我的朋友、詩人草樹所說的:悲而不傷。所以你會看到詩人嘆息美之將凋零但更珍惜現時的時光,不到一定境界根本達不到這種洞悉人類命運的水平。所以沃爾科特就是寫了這些,詩歌寫了什么是最難回答的問題,因為很多詩只能放到中國的語言源頭上,我們才能知道寫了什么。這首詩主要是寫老年,時間在流逝,我感到很悲傷,但是沒有傷到那個地步。我很坦然的接受這一切,時間已經流逝了,但是我們還要珍惜這沒有流逝的時候,我們要珍惜現在。所以說,這是一首非常豁達的一首詩。
基本上分享《白鷺》就到這里了。
最后,額外說一句,趙博士說要在內蒙古大學開現代詩歌審美的課程,這個課在北京沒問題,在內蒙古可能是破天荒的。我覺得內蒙古大學,包括內蒙古的其他學校,如果要進行語文教育,要是回避詩歌的話,這個語文教育,我相信不會好到哪里。為什么?因為在世界上的所有文體中,詩歌是所有文學、所有文體的老祖宗。世界上第一流的詩歌作品就是《荷馬史詩》,戲劇作品就是古希臘的三大劇作家,哲學作品就是柏拉圖,就是說文字高于一切。文字高于標準,高于音樂,文字當中高于一切的就是“詩”。所以開詩歌課,我覺得這很有想象力,很及時,應該會讓很多人受益的課程,尤其是我們說的現代詩。我今天和大家分享目前翻譯成中文最漂亮的詩,而不是講詩歌理論,就是想讓大家感受,為什么要開現代詩課程?好在哪里?這就是我們今天分享的,所以不用中文學術語言,我平時也是做文學理論批評的,一會存在主義,一會兒表現主義,結構主義等,講這就沒意思了。就用平常的口語,所以大家感覺趙卡老師沒多大水平,這是為了讓大家互相都能聽懂。
為什么講現代詩?幾乎所有人都知道,中國的新詩自胡適1916年寫完那首《蝴蝶》后就誕生了,之前的都是格律詩,四言、五言、到七言就不再往前踏一步。格律詩,無論你的水平多么高深,就只在四言、五言、七言之內。當然這是中國古典文學,像唐詩的輝煌,它是沒問題的,但是今天我們沒法那樣寫,所以今天我的好多朋友,當他寫古體詩的時候,我的話很難聽,中國古典文學的格律體是種死去的文體。所以說新詩也是用口語破的局,經過五四的不成熟期和四九年后的歌德體,真正確立了現代意識應該是從七十年代末北島顧城開始啟蒙,經八十年代洗禮到九十年代終成大熟,誕生了中國當代漢語詩歌諸多大詩人,比如西川、于堅、歐陽江河、李亞偉、王家新、韓東、臧棣、余怒等等,當然了,你們熟悉的可能也是熱愛的席慕蓉,海子。
那到底什么是現代詩?這個三言兩語說不清楚,屬于理論家們和寫博士論文的同學們研究的事兒,我作為一個作家、詩人,我參考的是波特萊爾和惠特曼的標準,畢竟他倆算是開現代詩的鼻祖:
1、自由;
2、反動。
自由是說形式的,反動是說內容的,也就是說,什么形式都敢用,什么內容都敢寫。
今天分享沃爾科特的《白鷺》,一是的確大師之作,二是比較安全。如果我講艾略特的《荒原》,估計會被你們轟下臺的,太復雜也太晦澀。
謝謝!
作者:趙卡
來源:62路公交車
本期編輯:周野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