苗雨時:論詩歌的生命形式
苗雨時/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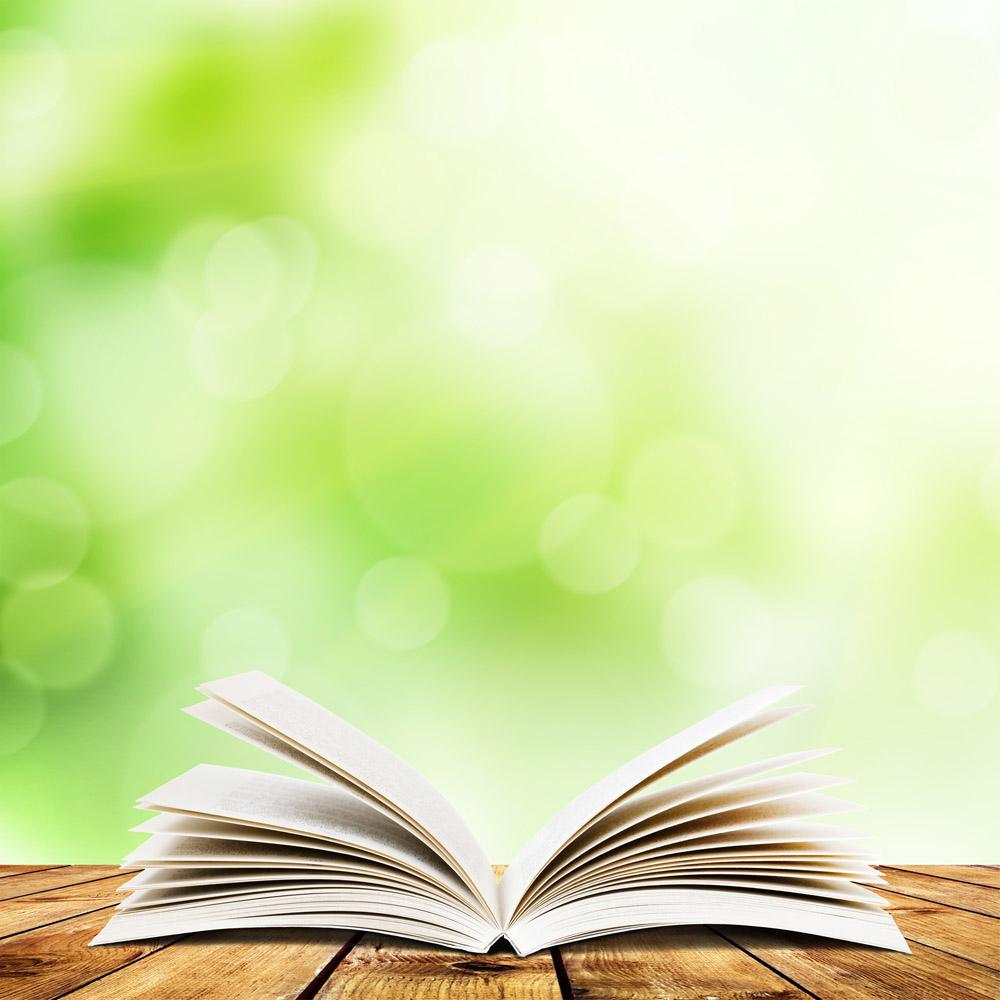
資料圖
一切藝術的共同特性,就是“表現性”。一件詩歌作品,就是一個表現性的形式。這種表現性形式,供人們的感官去感知,或供人們的想象去想象。而它所表現的東西是人的生命的情感。
關于“形式”,是一個相對的概念,有多種含義。比如說,中國詩歌有四言詩、騷體詩、古詩、律詩、詞、曲、新詩等多種體式,這只是“形式”含義中的一小部分,或者說只是外形式。如果當我們說,“形式取決于機能”,或者說“這是有意味的形式”,這種形式就是廣義的形式,或者叫內形式。內形式主要指某種結構、關系、各種特征的組合或通過相互依存的因素構成的整體。內形式與外形式,相互為用,諧調統一,就形成了詩歌的表現性形式。
表現性形式,不是一類具體的事物,它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實際上,它是一種知覺和想象的特定的邏輯關系模式。以此種關系模式,就可以表現具有同構關系的某種情感或事物。某種情感與某種表現性形式能夠動態同構,表現形式就成了“情感生活”在藝術的時間、空間或詩中的投影。因此,詩歌的形式,就是情感的形式。
詩的情感的形式,是生命的形式。當我們欣賞一部詩作的時候,往往能從中看到“生命”,看到“生機”和“活力”。這種精神,并不是詩人的創造精神,而是作品本身的性質。一個詩人在創作中,應該給自己的詩作以“生命”。一件“死”的作品肯定是毫無價值的。那么,一件作品為什么需要有生命的形式?而生命的形式又是指什么?
詩歌的表現性形式,應該是一個有機的形式。而且,這里的有機性,不只是借用生物學上的比喻。它是指一部優秀詩作的典型特征。有機的形式就是生命形式。所以詩歌的表現性形式應該是一種生命的形式。
我們知道,情感和情緒的組合不是物理性組合,而是精神性組合,它們所呈現的運動狀態和生命有機體有某種相類似之處。事實上,它們有如生命湍流中的波飛浪涌。它們的產生和消失的形式也就是生命成長與死亡過程所呈現的那種形式,而決不是機械的物理活動的形式。也就是說,這些情感和情緒之間的關系與組合,和有機的生命形態具有一種邏輯相似性。所以,生命的形式能夠很好地傳達詩人的感情,生命形式也就是詩的情感的表現形式。
詩的表現性形式和生命體的機能之間有哪些類似的地方呢?
一個生命的形態永遠是一個運動的形態。一個生命體也如同一個瀑布或一條河流,只有不停地運行才能夠存在。它們的固定性,并不是由材料本身的永久性造成的,而是由它們生生不息的機能造成的。生命體的運動實際上是一種機能的發揮。
當然,生命體和瀑布與河流又不完全相同,它比它們要復雜得多。生命體雖然是一個運動的事物,但它不象流水那么簡單,因為它其中包含著由各種互相之間性質不同的活動所組成的持續性的結構,結構中的各種因素的活動,互相制約,互相補充,從而形成一個有機的統一體。這個統一體就是生命存在的基本形式,生命之所以能維持持久的動態式樣,其中一個重要的原因是生命運動的節奏性,例如人,呼喚、脈搏、走路、劃船、騎車……都是有節奏的活動。在所有的有機體中,它們的一切活動都是有節奏的運動。生命在于運動,運動在于節奏。
關于生命形式的特征,蘇珊·朗格在《藝術問題》中總結四點:第一,它必須是一個動力形式。它那持續穩定的式樣必須是一種變化的式樣。第二,它的結構必須是有機結構,它的構成成分不是互不相干,而是通過一個中心互相聯系和互相依存。第三,整個結構都是由有節奏的活動結合在一起的。第四,它隨著自身的生長與消亡而辯證發展。
如果說,詩歌以藝術的形式傳達詩人的情感和意識,那么,我們所說的生命形式的一切特征,都可以在詩的表現性形式中找到。諸如它的各個要素組合的動力性,有機結構性、脈動節奏性,以及開端與終結的完成性等。這一切在詩中都是一種類似生命的存在。但是,我們也必須清楚,“類似”不是等同。一個與生命相類似的事物,不一定與生命本身的圖式絲毫不差,一個用來引起變化感受的創造式樣,其本身不一定發生變化,一種用來引起明顯生長感受的創造式樣,其本身也不一定逐漸生長。藝術形式是一種生命形式的投影,而不是生命的復制。因此,一件詩歌作品的構成要素和一個生命的構成要素之間是沒有直接關系的。藝術形式有它自身的規律。所說的詩的表現性形式是生命的形式,我們在這里所強調的是藝術形式的特征與生命本身的特征這兩種特征之間的象征關系。這正如托爾斯泰所比喻的:“在真正的藝術作品——詩、戲劇、圖畫、交響樂中,我們不可能從一個位置上抽出一句詩、一場戲、一個圖形、一小節音樂,把它放在另一個位置上,而不致損害整個作品的意義,正象我們不可能從生物的某一部位取出一個器官來放在另一個部位而不致毀滅該生物的生命一樣。”這就道出了表現性形式的生命特性的真諦。
試分析艾青的《搏動》:
心的搏動,能衡量
這病的博動么?
都市的,夜的光之海,
常給我以太重的積壓;
積壓的縱或不是都市的
繁雜的音色也吧;
積壓的而是回想的
音色的都市也吧!
但是,心的搏動果能
衡量我這病的搏動么?
這首詩表達詩人內心的痛苦和憂患。全詩是一種循環式結構,起句與結句重復,中間三節在現實與回憶的回環中,析解“心的搏動”無法衡量“病的搏動”的原因,從起句到結束,構成了一個螺旋形深化的有機整體。第一節兩次出現“搏動”,但這個“搏動”的含義不同,其間以能不能“衡量”,把“心”引入到“病”。“搏動”是這一節的關鍵詞,它的轉換開啟了詩人的心路。第二、三、四節是一個“之”字拐的聯想曲線。那“病的搏動”的原因是:現實的“積壓”——“縱”不是現實的“積壓”——也是“回想”的“積壓”。詩句一任情緒流轉而賦形,從而形成一種往返層遞式的有力結構。在這里,“都市”出現了三次,“積壓”也出現了三次,但由于在這特定的語言結構中地位不同,它們的意味和作用也不同:“積壓”一詞暗中作了兩個“都市”之間聯想的橋梁,而兩個不同“都市”的相互對應,更增加了“積壓”的份量。此處語言的編織,幾乎每一個詞都是不可更動的。在層層“積壓”的沉重之下,詩人把開頭的疑問一變而為結尾的反問,從不肯定到否定;詩歌雖然首尾園合,完成了一種思緒流程,但是它給人們的啟示卻是超越詩歌本身的“心的搏動”的無限深遠的沉思。
不難看出,你越是深入到詩歌作品中去,你就愈加清楚地發現藝術的表現形式與生命的有機性特征相似。正是這種相似性,使一首詩看上去充滿“生機”和“活力”,呈現一種“生命”的精神和形態。表現性形式就是生命的形式,而作品的意義就象直接包含在“生命形式”之中。“生命形式”,就是詩歌的感性存在,也是詩歌的現實存在。
分享:
來源:苗雨時新浪博客
作者:苗雨時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