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普希金那樣的愛情詩人
——序張后的愛情詩集《紙上玫瑰》
洪燭/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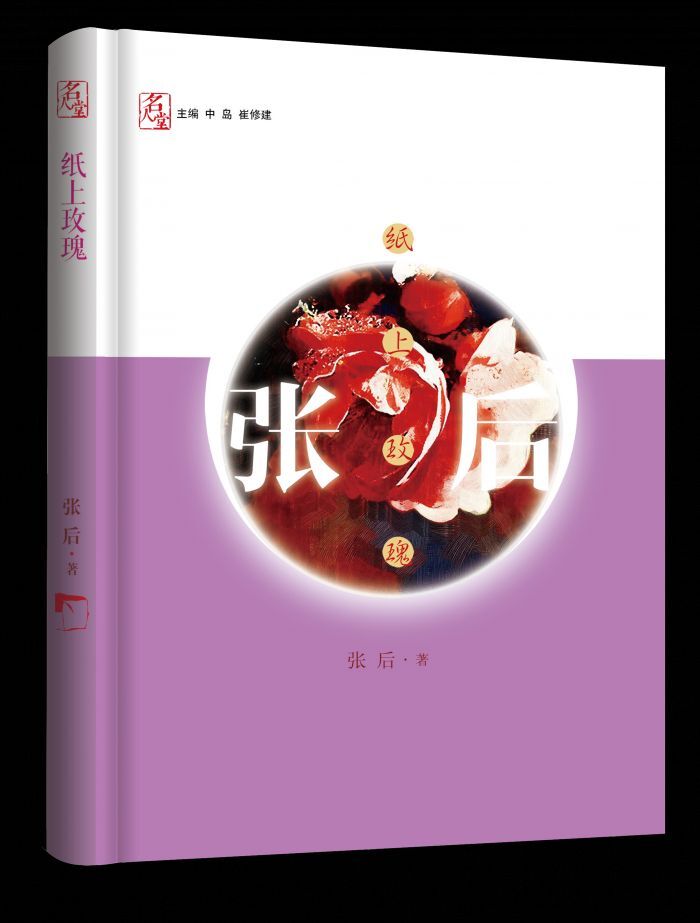
張后的情詩,有眾多的讀者。可張后的情書,寄出去過嗎?我指的是,會寄給自己情感世界的女主人公查收嗎?會捅破那層窗戶紙嗎?這是個問題。我擔心的是:窗戶紙一旦捅破,詩就沒法寫下去了。詩人若真的墜入愛河,眼里將只有愛神而不再有詩神。最好的選擇:坐在愛河的岸上寫詩。
我在少年維特的年齡,也把愛情與詩當成自己眼中最神圣的兩種美。跟張后一樣,跟大多數(shù)詩人一樣,我也是寫愛情詩起步的,在沒談過戀愛的時候就會寫愛情詩了。十八、九歲,在武漢讀大學,出的第一本書就是愛情詩集,名叫《藍色的初戀》(湖北青年詩歌學會叢書)。當時也有好多少男少女傳抄啊。
只是似乎沒過多久,愛情逐漸遠離我的詩歌主題。我更多地把愛情留在散文里,天花亂墜地在流行刊物上發(fā)表,賺錢,也賺讀者的眼淚。太無恥了!怎么能拿愛情來換錢呢?
張后比我純粹,只拿愛情寫詩。詩是不賺錢的,愛情也跟詩一樣屬于非賣品。所以,他才可能將愛情進行到底,將愛情詩進行到底。他才可能成為碩果僅存的愛情詩人。
張后寫愛情詩,從少年寫成了青年。想了解告別了少年時代的青年維特的煩惱嗎?那就讀張后的愛情詩吧。
我印象中有兩大愛情詩人,一個是外國的,一個是中國的,一個叫普希金,一個叫徐志摩。張后身上或許有著他們的影子。
普希金比徐志摩要多一些憤怒,也就多一些力量。普希金要為自己尋找一個情敵,為自己的女人同時也為自己的詩歌。否則他就沒有決斗的對象。情敵似乎比朋友更容易使人忘掉孤獨。愛神或詩神,都擅長替那些癡迷者樹立假想敵。為女人而決斗,這樣的事也只有普希金能做出來。尤其這個女人并不是一般的女人,甚至不是他妻子岡察洛娃,而是繆斯——他必須表現(xiàn)出加倍的勇氣。決斗時岡察洛娃不在現(xiàn)場,而繆斯并未缺席——她溫情脈脈地注視著走向槍口的詩人。普希金之死,并不僅僅為了維護他妻子的貞操,同時也在捍衛(wèi)詩神的榮譽。他的情敵丹特士,是否有沙皇撐腰?這不重要。普希金的身后,卻確實站立著流淚的繆斯。
張后也是有情敵的。那就是生活。他一定戰(zhàn)勝了自己的情敵。世俗的壓力并未能把他懷中的愛情奪走——他還在寫詩,還在捍衛(wèi)自己的夢,就是證明。他以詩面對生活的挑戰(zhàn)。
假如普希金沒有去決斗——或者說,即使他去決斗了,但沒有死,那么將會有怎樣的情況發(fā)生?他肯定會重新拿起筆,寫更多的詩篇,并且愛更多的女人。他會變成另一個歌德。然而長壽的歌德只有一個,短命的普希金也只有一個——他還是死了。這是詩神的損失,也是愛神的損失。有什么辦法呢?好在詩神還會呼喚更多的愛情詩人。張后也在響應冥冥之中的號召吧?
張后的情詩令我聯(lián)想到普希金的情詩。不知張后怎么看普希金?普希金曾是我年少時的偶像,我早期的情詩不無他的影響。屹立在皇村的普希金銅像,曾令遠方的我激動不已。我熱愛(甚至有點嫉妒)那位以塑像的形式永生的詩人。他戰(zhàn)勝了時間!這比戰(zhàn)勝沙皇要難得多。那時我剛剛寫詩,還是不諳世故的少年,卻有了這樣的夢想:但愿一百年后,我也會被塑成同樣大小的銅像,立于故鄉(xiāng)南京的新街口……我愿意用血肉換取一塊尚未冶煉出來的青銅。或許,那才是我來世的骨頭。
張后寫愛情詩這么多年,懷著怎樣的理想?與我的是否有幾分相似之處?
我?guī)啄昵霸陂L篇詩論《我的詩經(jīng)》里寫道:“我今年38歲,正是普希金死去的那個年齡。我意識到自己身上的雙重使命:不僅為自己,還要接替另一個人活下去。我要把普希金沒來得及寫的詩全部寫出來。包括他那些還沒來得及開始或完成的愛。我正在把虛擬中的普希金的下半輩子變成現(xiàn)實。這也是我的下半輩子:與另一個活著的死者同在。”今天,我發(fā)現(xiàn)了張后,發(fā)現(xiàn)還有個張后,在跟我做著同樣的事情。他哪來那么多的激情?
我在《我的詩經(jīng)》里還說過:“歌德八十歲了,還會愛上十八歲的姑娘,有火熱的情詩為證。他是一個很老很老的年輕人。我從不羨慕那些短命天才。我希望自己有普希金的青春,再加上歌德的晚年。”愿以此和張后共勉。兄弟,我們離八十歲還遠著呢,好好地活著,好好地愛,好好地寫詩。怎么過都是一生,還有比做一個詩人(尤其是普希金那樣的愛情詩人)更有意思的事情嗎?
即使夢想被拒絕或磕磕碰碰,也同樣有意思呀。在生活中的被拒絕,有時比被接納更能激發(fā)一個詩人的靈感。對于他的創(chuàng)作來說,痛苦比愉悅更有價值。葉芝終生都在苦戀女演員毛特·崗,這段極為漫長的單相思還是有回報的,那就是促使他寫出《當你老了》這首經(jīng)典的愛情詩。難怪毛特·崗真的老了之后仍不后悔當初的態(tài)度:“世界將會因為我拒絕了你而感謝我!”是啊,即使她與葉芝共結連理又怎樣呢?愛爾蘭不過多了一個幸福的丈夫,卻極有可能失去一位苦吟的詩人。至今,我們將讀不到如此深沉的詩句:“多少人愛你年青歡暢的時候/愛慕你的美麗,假意或真心/只有一個人愛你那朝圣者的靈魂/愛你衰老了的臉上的痛苦的皺紋……”我們在感謝葉芝的同時難道不應該感謝拒絕了他的女人嗎?葉芝所榮獲的諾貝爾文學獎杯,我覺得有一部分屬于毛特·崗的功勞,屬于折磨過詩人的愛神的功勞。
張后,我祝愿你的這部愛情詩集里,或未來的愛情詩創(chuàng)作中,有可能出現(xiàn)《當你老了》這樣的經(jīng)典之作。
裴多菲說:“詩人都是夜鶯,苦惱的夜鶯,折磨它吧,這樣它就能唱出美妙而苦惱的歌聲。”人類中惟有這一群體,會將命運安排的磨難視為珍貴的賜予,在刀刃上跳舞,使痛苦演化為一種美。我在北京參加詩歌活動,經(jīng)常遇見張后,總體上感覺他的生活不無滄桑,因而他的情詩也不只是單純的“甜品”,有復雜的回味。這是好事情!
在我已很少寫愛情詩,甚至快寫不出愛情詩的時候,多么愿意聆聽張后這樣的夜鶯的鳴叫。
作者:洪燭
來源:博客中國


 純貴坊酒業(yè)
純貴坊酒業(y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