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寮子背》:后工業(yè)時(shí)代的“結(jié)繩記事”
馬志良/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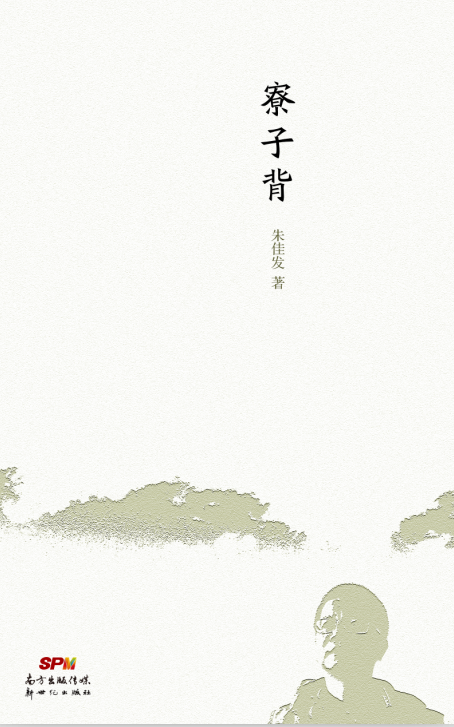

詩人朱佳發(fā)
那一天,來自北方的風(fēng)吹散了聚集在南方的霾。
黃昏時(shí)分,我從朱佳發(fā)的詩歌里抬起頭,竟然看見了清晰的地平線和遠(yuǎn)山起伏的影子。在十九樓的陽臺(tái)上,寒冷的風(fēng),帶著透徹的涼,穿過我的身體,穿過擁擠的城市,吹向一個(gè)遙遠(yuǎn)的村莊——寮子背。
對(duì)于朱佳發(fā)的詩歌而言,寮子背是一切的起點(diǎn)與終點(diǎn)。詩人在大地上行走,腳步如同飄忽不定的風(fēng)向,無論是南方還是北方,也無論是來路還是去路,都像是雨中的鷹,雪中的蟬,所有的漂泊都是不期然而然的使然。思想的鳥群在天際間飛翔,身體的腳步在大地上匍匐,兩者之間,永遠(yuǎn)都存在著一個(gè)巨大的悖論,并由此而造成了撕裂般的反向作用力,猶如一道溝壑被分裂為兩岸,猶如一道傷口永遠(yuǎn)的疼痛(這是詩中反復(fù)出現(xiàn)的意象,如《峽谷》、如《裂谷》 )。
說到底,此岸與彼岸的分裂、呼喚與交織,是一個(gè)詩人永遠(yuǎn)無法回避的生存狀態(tài)。它存在于精神和物質(zhì)之間,靈魂與現(xiàn)實(shí)之間,行走與回望之間,同時(shí)又對(duì)應(yīng)著城市與鄉(xiāng)村,繁華與孤獨(dú),精神與世俗。
由此而論,我認(rèn)為朱佳發(fā)的詩歌至少可以分析為三個(gè)維度的基本張力,即空間張力、時(shí)間張力和精神張力。這三重張力有時(shí)各自拉扯,經(jīng)緯分明,主導(dǎo)著詩歌敘事在某一方向上的力度;有時(shí)又互相作用,縱橫交錯(cuò),形成了一張疏而不漏的命運(yùn)之網(wǎng)。可以說,朱佳發(fā)的每一首詩,都是在這個(gè)三維交織的網(wǎng)羅上的一個(gè)“死結(jié)”,或可稱之為后工業(yè)時(shí)代的“結(jié)繩記事”。
需要說明的是:與先民們“結(jié)繩記事”的處境不同,漢語詩歌雖然已有三千年的深厚積淀,但我們所處的時(shí)代卻面臨著更多的問題、矛盾和不確定性。所以,閱讀朱佳發(fā)的詩歌,會(huì)讓人感覺到這些“以詩作結(jié)”的“疙瘩”倔強(qiáng)而又堅(jiān)硬,作者似乎是鐵了心的要傳遞給更久的未來,更遠(yuǎn)的遠(yuǎn)方,以及更加感同身受的同謀者。
一、城市與鄉(xiāng)村的文明之結(jié)
城市化進(jìn)程對(duì)鄉(xiāng)村的排斥與拉攏、掠奪與安撫,本身就是一個(gè)充滿悖論的矛盾。但三千年農(nóng)耕文明在中國人血液中注入的鄉(xiāng)村基因仍然根植于大部分人的心中。其中,由農(nóng)家子弟而進(jìn)入城市的詩人,也許是最具代表性的一個(gè)群體。在這條路上,從海子的北方“麥田”到朱佳發(fā)的南方“寮子背”,有著一脈相承的源頭和指向。
時(shí)至今日,空間關(guān)系上的城市與鄉(xiāng)村,是漢語詩歌在三千年文明進(jìn)程中遇到的一個(gè)新課題。雖然,關(guān)于鄉(xiāng)愁的主題由來已久,但城市與鄉(xiāng)村之間的關(guān)系卻從來沒有像今天這樣緊張和分裂,這樣充滿了粗魯和不義。僅憑這一點(diǎn),就足以讓手持漢語的詩人痛徹心扉。
一方面是城市生活對(duì)于生存空間的拓展。上世紀(jì)八十年代以來的這一代詩人,大多以知識(shí)精英的身份,參與了城市化進(jìn)程,是城市化的親身參與者和見證者,并已成功地在城市中安身立命。另一方面,城市的快速發(fā)展也反襯著鄉(xiāng)村的沒落,特別是隨著年齡的增長,當(dāng)一批一又一批的詩人們伴隨著清明、春節(jié)的返鄉(xiāng)潮流回到鄉(xiāng)下時(shí),思緒在童年的家國記憶與現(xiàn)實(shí)的蒼茫蕭條中凝結(jié)為無形的空虛,一切都似乎失去了根據(jù)。
可以說,是我們自己親手毀掉了鄉(xiāng)村,又親手?jǐn)財(cái)嗔伺c這個(gè)母體相連的臍帶。但是,當(dāng)初義無反顧地投奔而來的城市,并不是一個(gè)安放靈魂的所在;而“故鄉(xiāng)也已經(jīng)不是一個(gè)榮歸的去處了”(費(fèi)孝通《鄉(xiāng)土中國》)。
朱佳發(fā)的詩歌正是在這樣的背景下對(duì)故鄉(xiāng)的重新審視和自我懺悔。
“小溪流過寮子背/我,以及我的子孫們流過寮子背/小溪已經(jīng)沒有了小魚/我,以及我的子孫們/可是寮子背游走的小魚?”(《寮子背》)。
“一近一遠(yuǎn)的錯(cuò)覺中,山出現(xiàn)裂谷/我的傷口開始疼痛,幻覺透不過氣……鄉(xiāng)親們說,那是豁口,是山與山的夾縫/夾縫是一條河,緩緩流過城市和鄉(xiāng)村/流過我的身體”(《裂谷》)。
這樣的敘述方式并無詩意可言,因?yàn)樵?jīng)有過的詩意早已隨著村莊一同遠(yuǎn)去。留給詩人的只有無限蒼涼的山岡與堅(jiān)硬的巖石,那些山岡與巖石從來不會(huì)無病呻吟,但它們構(gòu)成了朱佳發(fā)詩歌在空間維度上的基本質(zhì)地——柔軟而又倔強(qiáng),卑微而又傲慢。
二、繁華與孤獨(dú)的生命之結(jié)
在時(shí)間軸上,對(duì)于生命意義的思考和回答,是詩人無法回避的另一個(gè)命題。正因?yàn)槿绱耍剂_茨基才會(huì)嚴(yán)肅地指出:“寫詩也是一種死亡練習(xí)”。
生命在時(shí)間中流失,其方式不外是兩種:繁華或是孤獨(dú),存在或是虛無。而在現(xiàn)實(shí)中,更多的是繁華中的虛無,孤獨(dú)中的存在。作為生存于現(xiàn)實(shí)中的詩人,朱佳發(fā)當(dāng)然屬于后者,正如他在詩中寫道:“光和聲音糾纏不休,我和自己糾纏不休/今夜,誰的影子拉不長,誰走不出宴席”。(《整個(gè)晚上我只看到一顆星星》)。
從衰敗的鄉(xiāng)村重新回到繁華的城市,如何審視生命的價(jià)值是每個(gè)人都不得不面對(duì)的問題。大部分人在短暫的傷感之后,重新回到了城市生活的滾滾紅塵。但詩人卻不可能這樣沒心沒肺,酒盡人散之后,只能沿著陡峭的臺(tái)階或者垂直的電梯離開大地,日復(fù)一日地回到高樓上的水泥格子里,重新思考生命的意義:飛翔還是墜落?背叛還是回歸?
這是一種巨大的孤獨(dú)感,而關(guān)于生命意義的思考總是出現(xiàn)在孤獨(dú)的盡頭。《山的那一頭》正是這種在孤獨(dú)中對(duì)鄉(xiāng)村生命狀態(tài)的懷念:“山的那一頭升起炊煙,人就該到齊了/我遲遲沒有動(dòng)身,是想找?guī)赘静?hellip;…”。在此,木柴可能代表著詩人記憶中某種美好的鄉(xiāng)村記憶或是人生意義。詩人雖然堅(jiān)信“只要有柴火,炊煙總會(huì)升起”。然而,在城市里尋找木柴的結(jié)果只能是自我身份的迷失和終極意義的迷茫,最終只能是更大的不可知:“我可能來自山的那一頭\ 我可能是山那一頭的背叛者”(《山的那一個(gè)頭》)。
如果說,柴火與炊煙代表了鄉(xiāng)村意義的自然場(chǎng)景,那么在詩中反復(fù)出現(xiàn)的“兄弟”則代表著鄉(xiāng)村意義的生命關(guān)懷。眾所周知,兄弟是中國傳統(tǒng)文化中除了父母、夫妻之外最重要的人際關(guān)系,也是人際關(guān)系從家庭走向社會(huì)的第一個(gè)圈層。其中既有血緣關(guān)系的紐帶,又有社會(huì)關(guān)系的溫情;兄弟既可以是血緣的,也可以是結(jié)義的,這是幾千年來中國農(nóng)耕社會(huì)最看重的人際關(guān)系。在朱佳發(fā)的詩歌中,反復(fù)出現(xiàn)的兄弟,既是詩人在巨大的孤獨(dú)中對(duì)城市冷漠的抗拒,也是對(duì)古老的人際關(guān)系和社會(huì)溫情的召喚。
“有兄弟已經(jīng)出發(fā),但不知道自已在什么方位”(《山的那一頭》)。
“而我的一生都茫然行走的兄弟/還在一步一個(gè)腳印地丈量/城市與鄉(xiāng)村的距離”(《種種跡象表明》)。
“沒有人知道,消逝多年的兄弟/與河流的走失有沒有關(guān)系……我的兄弟一直尋找的那棵樹/不知會(huì)不會(huì)從明天的河床長出”(《明天的河床》)。
與眾多的稱謂詞一樣,現(xiàn)代社會(huì)兄弟關(guān)系的泛濫與疏離,是對(duì)漢語的又一次侵犯。在傳統(tǒng)的鄉(xiāng)村社會(huì),兄弟既是構(gòu)成宗族實(shí)力的主要力量,也是一個(gè)人生命意義的最漫長的見證者和伴隨者,他們不僅提供生的意義,同時(shí)也提供死的關(guān)懷。某種意義上說,由于宗教的缺失,在傳統(tǒng)的中國鄉(xiāng)村,兄弟之間的平等關(guān)系為每一個(gè)人提供了宗教意義上的傾聽、訴說、懺悔的可能,也是唯一可能以平等的身份提供生前相伴,死后相送,患難相扶,困厄相助的人。
從這個(gè)意義上說,朱佳發(fā)詩歌中反復(fù)召喚的兄弟不僅是對(duì)這個(gè)語匯的復(fù)原,而且已經(jīng)脫離了平凡意義上的人倫關(guān)系,帶著某種神性的光芒,是一種對(duì)人生意義和終極關(guān)懷的召喚。
三、精神與世俗的詩歌之結(jié)
實(shí)際上,無論是空間維度上的價(jià)值追尋,還是時(shí)間維度上的生命反思,都不能解決一個(gè)最根本的問題,就是詩歌作為人類精神的高地,如何完成自己的生長。因此,詩人最終只能在精神與世俗的對(duì)抗中,回到詩歌內(nèi)部,重建自己的精神王國。
“讓我回到一粒米,詞的米,米的胃……家園日漸下沉,恐懼早已失語/而詞,一粒詞站立了!……我回到固定的中心,我把我固定”(《讓我回到一粒詞》)。
就是從一粒詞開始,朱佳發(fā)不僅以一個(gè)詩人的身份固定了自已,同時(shí)也重新塑造了屬于自己的空間和時(shí)間,“沿途撿拾傲慢的詩句,如同沿途撫慰/遺落的靈魂,以及草芥的生命”。
在這里,“我從不需要聽眾/時(shí)間就是我忠實(shí)的聽眾”(《聽眾》);在這里,“木質(zhì)的鄉(xiāng)村,以及鋼鐵的城市早已迷路/而我非常清楚來時(shí)的路,以及路上的橋”(《橋》)。
由此可見,通過詩歌,詩人不僅完成了自我價(jià)值的“固定”,同時(shí)也完成了從必然王國到自由王國的升華:“我為自己建造了一座城堡……我是自己的王……我要他們用一生去找我,世世代代去找我……我不讓自己悲傷,不讓自己憐憫”(《我的城堡》)。
至此,朱佳發(fā)的詩歌已經(jīng)完全擺脫了世俗的羈絆,并以詩歌的精神完成了對(duì)時(shí)間和空間兩個(gè)維度的跨越,形成了明顯的自我認(rèn)定與精神指向。
阿諾德說:“詩歌拯救世界”。但是,詩人首先必需完成對(duì)自己的拯救。如果把《寮子背》的書寫過程所涵蓋的十三年時(shí)間以2010年為一個(gè)分期標(biāo)志,對(duì)比前后兩個(gè)時(shí)期的作品,則可以發(fā)現(xiàn)朱佳發(fā)詩歌不斷走向自我拯救的種種跡象。
在前一階段,詩人行走的范圍很廣泛,豐富的題材中雖然已經(jīng)包含著向傳統(tǒng)和自身回歸迫切感,但詩歌在廣度上的鋪展掩蓋了主題的掘進(jìn),對(duì)他者與外在的關(guān)注是這一階段的主要特點(diǎn)。在第二階段,主題明顯集中于對(duì)故土家園的切身感受和城市生活的深刻反思之間,隨著自我生命意識(shí)不斷擴(kuò)展,這一時(shí)期的詩歌獲得了越來越充足的內(nèi)生力,從而使我們透過不斷變幻的意象發(fā)現(xiàn)一個(gè)更加真實(shí)的自我和更具真相的世界。
結(jié)語
我相信這是一次不自覺的嘗試,但詩歌既然是“語言存在的最高形式”(布羅茨基《文明的孩子》 ),則自有其本身的系統(tǒng)功能傳遞內(nèi)涵豐富的思想信息,等待著遙遠(yuǎn)的“聽風(fēng)者”。對(duì)此,現(xiàn)實(shí)中的老朱就是一個(gè)頑固或者說是傲慢的佐證。作為詩人,他從不談?wù)撛姼瑁坪跻矎牟黄诖姼璧母黝悺爸簟被蛘吒魃爸骸薄D陱?fù)一年,老朱在甲子路一帶的街頭大排擋里喝著冰鎮(zhèn)啤酒,看落英繽紛或者暴雨滂沱,忽而興奮又忽而傷感起來,卻也從不當(dāng)眾吟詩。
從寮子背而武平、從武平而龍巖、從龍巖而溫州,又從溫州而順德,二十多年來,朱佳發(fā)像風(fēng)一樣在東南與華南之間劃過三省四地,但是只劃了半個(gè)圈,剩下的半圈向著寮子背。
在詩集的自序里他說:“我在走,我就是方向”。也許,這就是詩人的宿命,盡管存在著各種各樣的張力和引力,但詩歌的方向永遠(yuǎn)是內(nèi)在的,也是不可預(yù)知的。
我之所以把朱佳發(fā)的詩歌稱之為“死結(jié)”,是因?yàn)樗环N不愿被人們輕易打開的決絕,也包含著內(nèi)心矛盾的壓力與沖撞,這是詩人內(nèi)心的絕望與傲慢,也是詩歌在消費(fèi)主義時(shí)代所面臨的困境。換句話說,對(duì)于詩人而言,最擔(dān)心的并不是自己的詩歌被誤解、被冷落、被封存,而是被消費(fèi)、被消化、被排泄。


 純貴坊酒業(yè)
純貴坊酒業(y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