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奇:“漢語詩心”與“漢語詩性”散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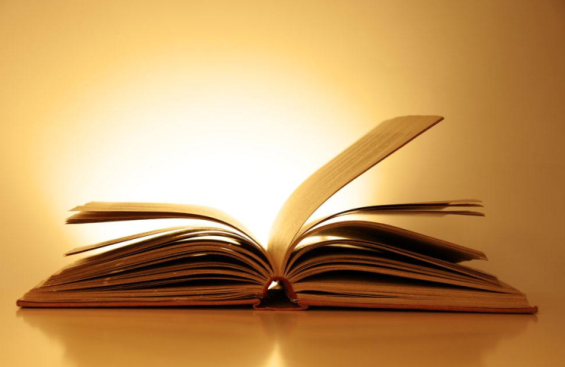
1
詩是詩人寫的。什么樣“存心”的詩人,寫什么樣的詩。同理,什么樣“存心”的時代,出什么樣的詩人。
這幾句大實話,至少在談論現當代漢語新詩詩人時,是個必要的前提。
“存心”,即“動機”,德國人哈貝馬斯講的寫作“心理機制”,即誰在寫、寫什么、怎樣寫之外,還得深入考察“為什么寫”的問題。愛爾蘭詩人葉芝說過一句話:“我們和別人爭論時,產生的是雄辯,和自己爭論時,產生的是詩。”[1] 可以看作對思考這個問題的一個注腳。
葉芝這里所說的“別人”,在本文語境中,大體作為指代所有的“他者”性存在,似乎會更明了一些。
百年新詩詩人及其作品,如過江之鯽,何其繁盛?但水落石出后,誰存留了下來?誰還會繼續存留下去?誰與時俱進繼之時過境遷而后廢之朽之不復存在?或者換句話說,誰爭了“當下”也便活了個當下,誰心存“千古”而不爭也成千古?如此等等,都和詩人的那點“存心”有關系。
這是“人本”。具體于新詩“文本”而言,“存心”不正,則詩體難正;“動機”不純,則詩性難純——無論古今,詩都是最見心性的,“用心良苦”,或“別有心機”,結果大不一樣。有關當下漢語詩歌創作諸多現象與問題的解析,其實都得從“心”說起。
2
深入反思與辨析新詩以及后來被正名為“現代漢詩”的“詩心”所在,有兩個心理機制慣性,一直或隱或顯此伏彼起而長期存在,需要認真檢討:一種可謂“創新情結”,為創新而創新;一種可謂“運動情結”,為“他者”而他者。前者,耽于變動不居,因變而益衰,而致優雅的缺失和典律的渙散;后者,樂于與時俱進,或從眾造勢,成為宣傳、時尚、乃至娛樂化的附庸,而至真純的缺失和初心的渙散。
兩者共同的“病根”,在于其創作心理機制中,總有一個“他者”的存在暗自作怪,缺少那種“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的心胸與氣格,所謂自若即失,唯有顧盼,是以大多為小家子成了點小格局,弱詩人寫了些弱詩歌而已。
由上文所引葉芝的說法,又想到孔子的一個說法。孔子談學問之道,指認“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論語》),并認為“為己之學”方為學問之正道。套用圣人這句話,似乎也可將詩人與詩的存在狀態,分為“為己”與“為人”兩個向度觀察之。
我們知道,自古以來,漢語詩歌的正根,或者說漢語詩歌的大傳統,在“為己之詩”而非“為人之詩”。古典漢語詩詞中許多傳世之作,大多出之或唱和或贈答之得,便是一證。此種單純“詩心”,可謂古典“漢語詩心”之要義——以己而發,為己而作,即或有一二“預設”知己,那也是另一個自我的對象外化,所謂“鏡像”作用,心理機制上還是為己之詩,而非“他者”式的攀附。
由此回頭看去,百年新詩新了百年,其實主要新了個“為人之詩”:預設受眾,預謀他用——現代文學意義上的啟蒙、新民、療救等,當代文學意義上的主旋律、新詩潮、實驗、先鋒、走向世界等——皆為時代、家國、民族、階級、大眾、小眾、以及“與國際接軌”等等所主導而發展變化,且慨而慷,發為各種思潮與運動,造勢爭鋒,與時俱進,形成一個小傳統,但若將其比之漢語詩歌大傳統,還是多少有些底氣不足。
說到底,“詩在開始就不是救世的工具或媒介,它是最有生趣的藝術,光輝而不實用,但也最屬必要。”[2] 故, “詩人的力量在于他的獨立”;(雨果語)而“詩,這是人的一切活動中最純真的”(海德格爾語)一種存在。按照漢語的說法,詩人乃“真語者”(《金剛經》,“修辭立其誠”(《文言》),非“自性圓明”(《圓覺經》)者難成正果。
尤其,現代化至今日之物質時代、后消費主義時代、碎片化時代、網絡與自媒體時代、以及“娛樂至死”的時代,詩,越發成為無用之用之時,浮華還是上升,更得看詩人的“存心”如何了?所謂自得其所,方有詩得其所。
——有必要引用尼采的一段話作參照,或許更意味深長些:
寧靜的豐收。——天生的精神貴族是不大勤奮的;他們的成果在寧靜的秋夜出現并從樹上墜落,無需焦急地渴望、催促、除舊布新。不間斷的創作愿望是平庸的,顯示了虛榮、嫉妒、功名欲。倘若一個人是什么,他就根本不必去作什么——而仍然大有作為。在“制作的”人之上,還有一個更高的種族。[3]
3
原本,人類世界詩人的“詩心”,應該都是相同且相通的,何以生出“漢語詩心”一說?
筆者生造“漢語詩心”的說法,在本文語境中有兩層意思:一是說漢語詩人該有漢語自性的詩心所在,不能總是翻譯詩歌主導的“范”;一是說漢語詩人為詩而詩時,多少還得操心點漢語的事。
一方面,如上述行文中所點到的,至少就古典漢語詩人之主體精神而言,其主要取向,盡可用那句“獨與天地精神相往來”概言之:真純朗逸,篤誠率性,出而入之,入而出之,有顧盼而不失自若,終歸自得而美,唯詩文“千古事”為是。這其中的深層心理機制所在,其實與漢語感知與表意世界的根性有關,亦即“詩意運思”(李澤厚語)的漢語本質有關——個中話長,此處點到為止。
另一方面,如T.S.艾略特所言:“詩人作為詩人,對本民族只負有間接義務,而對語言則負有直接義務,首先是維護,其次是擴展和改進。”[4] 作為漢語詩人,其“存心”所在,自然還得“操心”經由現代“詩性編程”后,對漢語的“維護”、“擴展”、和“改進”起了多大作用?尤其現代漢語,恐怕很難經由別的話語方式獲益于此,唯有現代漢詩責無旁貸——這可是個大問題,也是忙著與時俱進的當代中國詩歌創作與理論一再延宕荒疏的問題。
詩是語言的藝術,這藝術除了要盡詩的責任外,還得反轉來盡語言的責任。我們知道,現代漢語中尚留存使用的許多成語,多取自古典詩詞,從而成為現代中國人,各個層面的感知與表意中,常常畫龍點睛式的存在,其“穿越”性的“命名”效應,揮之不去,唯有眷顧,而功莫大焉,便是一個最顯豁的例證。
語言是人的起始,詩是語言的起始;詩由語言而生,語言由詩而生——這其中的相互關系及利害所在,實在大有說頭。
不妨轉而討論有關“漢語詩性”的命題,或可經由此關聯而另獲啟示。
4
新詩或現代漢詩,經百年“現代化”,由倚重字構、詞構之古典“編程”,轉而為依賴句構、篇構之現代“編程”,其外在形式,如當代詩評家葉櫓先生所言,只剩下“無限自由的分行”,另走一道,另成譜系,我們再回頭談論“漢語詩性”命題時,究竟要義為何?
先繞開來說。
古今漢語詩歌,若概要打通去看,大體可以“情”“義”“體”“境”四字,概括其原本可以共生共有的基本詩性——
其一,“情”者,可謂“精神詩性”;
其二,“義”者,可謂“思想詩性”;
其三,“體”者,可謂“形式詩性”;
其四,“境”者,可謂“境界詩性”。
此詩性“四維”,其中,前兩點關乎主體,在本文中主要關乎“漢語詩心”所在;后兩點關乎對象,在本文中主要關乎“漢語詩性”所在。前兩點普遍都明白,后兩點須略備細化說明:“體”之所在,包括語感、氣息、節奏、韻律等,從中見出文學及藝術修養的高低深淺;“境”之所在,包括文心、文脈、文字、文采等,從中見出文化涵養的高低深淺。
現代漢詩與古典漢詩,除開精神與思想方面,心系“時代愁”還是心系“萬古愁”的明顯差異之外,關鍵是后兩點“體”與“境”的差異,亦即“形式詩性”與“境界詩性”方面的差異,較為復雜和微妙。
順便一說:這多年的當代詩學,多熱衷于“思想詩性”和“精神詩性”的宏觀關注與言說,疏于切實有效的微觀研究,“漢語詩性”命題的提出,或可引發一點類似的話題,漸開風氣,而別具意義。
5
詩,以及一切文學藝術的存在,或為語種所限,或為材料所限,或為形式所限,總是以其類、種、個的局限為基本文體屬性。換言之,即以其局限為位格之所在,以及風格之所在,以免混同于他者。
局限即界限,類、種、個的“域”之所在。在具體創作或叫做文本生成的過程中,界限或可適當伸縮,或越過界限探求并擴展新的表現“域”。但總體而言,若過于擴張,則可能反而失去原有的“領土”而無所適從,造成屬性的含混不清而致典律的渙散無著。
百年新詩,其潛在“危機”正在這里——屢屢變動不拘,在在創新不斷,“滾動的石頭不生苔”(法國諺語),只剩下大眾化的、運動性的模仿性創新或創新性模仿。如此結果,只能是不斷“下行”而泛化,乃至連“分行”也只是一種表面性的存在,內里的文體意識亦即詩體意識,已經相當模糊。
道成肉身,這“肉身”之“體要”,是詩之“道”所以然的根本屬性。
記得上一世紀九十年代初,我在編選《西方詩論精華》一書時,讀到美國詩人學者喬治.桑塔雅納的一段話,至今印象深刻:
從形式的角度看來,詩歌的不嚴格的定義可以這樣表達:詩歌是一種方法與涵義有同樣意義的語言;詩歌是一種為了語言、為了語言自身的美的語言。正如普通的窗戶,其作用只在于使光透過,而彩繪的玻璃使光帶上色彩,從而使自身成為住宅里的物品,繼而又使其他物品帶上特殊的情調。[5]
回到常識性的再確認:詩(現代詩)是對涵泳于“分行”中的思想、精神、意緒諸“內容”的一種語言“演奏”,其本質不在演奏的“曲目”及“內容”如何,而在于其演奏的方式以及風格如何。
在這一方面,語感及其風格方面,以及有關形式要素之分行、斷連、跨跳、節奏、調式等方面,“筆墨當隨時代新”的新詩,以及無限自由分行的現代漢詩,似乎并沒有給出多少經典性的規律或范式可言。這樣說,不是要歸法于一,而不免會傷及以自由為靈魂的現代漢詩的根性,而是要擇善為流,于典律的意義層面發揮自由的精義,總比任運不拘及散漫無著要好些。
這是“形式詩性”的簡要討論,更要緊的問題,還在“境界詩性”上。
6
新詩百年,以“現代化”為由,唯“現代性”為上,是以又有以“現代漢詩”為正名之舉,從“定義”與“命名”上確立并強調其“現代性”屬性。
而現代性諸問題中,首要一點是人與自然的背離。這里的“自然”,不僅是指“生態自然”,也包含“心態自然”,或“自然心性”——現代詩人也不例外,而且現代詩人之詩寫的第一要義,正是要質疑進而填補這樣的背離。
不少詩愛者都體驗和發現到:讀古詩名作,明知是依循格律做出來的,卻常常感覺是從古人心里自然流出來的;反之,讀大多數現代漢詩,表面看去是自由瀟灑“流”出來的,一旦讀多了讀久了,卻反而感覺到是依循什么“預設”之維做出來的。若深入品味,再上升到理論性的認知,或可概言之:有詩形而乏詩味;有詩感而乏語感;有詩情而乏文采;有詩心而乏文心——“四乏”所致,或輕或重,影響及新詩以及現代漢詩的品質與位格,也是至今難以取代古典詩歌,在現代中國人相關感知與表意的必要位置的主要原由。
顧隨先生在比較宋詩與唐詩時有一個說法:“宋詩意深(是有限度的)——有盡;唐詩無意——意無窮。”[6] 若將此說法套用于新詩普泛之作與古典詩詞精華的比較,可謂“昭然若揭”。
這便是“境界詩性”的關鍵所在了——此“境界詩性”之有無及深淺,不僅取決于心理機制,也許更重要的還取決于語言機制。是以近年我總在講一個極而言之且自以為是的“歪理”:在現代漢語語言機制及其語境下產生的現當代文學藝術,說到底,擺脫不了模仿性創新或創新性模仿的局限。
那么,下一步就要問:如何走出這種“模仿”之怪圈?或者說,我們的現代漢語文學與藝術,何以能在當代世界文學藝術格局中,重新找到我們自己的“身份”定位?
大概唯有重返對漢語本質屬性的再認識,方能有所改觀。
7
顧隨先生有一句話:“詩人最要能支配本國的語言文字”。[7]
從古典漢語到現代漢語,語言變了,但文字大體沒變,不管繁簡,總歸還是“漢字編程”。漢語感知與表意世界的根本屬性在于“詩意運思”,而這一屬性的根本脈息,又在漢字。由這一根脈所在,決定了中國文學藝術的三大基因所在,即,一字一詩,一音一曲,一筆細涵大千(中國書法與中國水墨)。這三大基因,往深里講,幾乎已成為中國文化身份的“指紋”之所在了。
由此可以反思到,新詩及現代漢詩與古典漢詩在“語言機制”上的根本區別,在于基本放棄了“字思維”與“詞思維”這一“漢語編程”的核心要素,唯現代漢語之句構與篇構為是,流風所致,沿以為習,不做他思。這樣帶來的問題,其一是總難擺脫由翻譯詩歌影響下的洋門出洋腔調式,不免尷尬于復制與投影之嫌;其二即“漢語詩性”亦即“形式詩性”尤其是“境界詩性”的匱乏,難免不斷下行而落陷于差異中的同一與膚淺。
其實說來嚴重,正之也并非難事。關鍵在于,能不能擺脫過于信任和依賴現代漢語“編程”的慣性,多少加入一些古典漢語“字思維”、“詞思維”的理念,慢慢習慣了,自然會在語感、語境、乃至心境上,都有些新的感受和要求,隨之漸生變化,或許連氣息、節奏等技藝方面的問題,也會慢慢有所改善。由此,所謂“漢語詩性”以及“中國身份”的要求,也自會有所提升與改觀。
但最終的問題在于:百年新詩歷程,潮流所致,我們在在革故鼎新慣了,也在在與時俱進慣了,更在在從眾從勢慣了,又何以能認同這樣的反思與提醒?
同源基因,要“通”才能“同”。一個常理,何以在在難以落實?
說到底,還是“詩心不古”,唯新是問,唯當下是問,唯“走向世界”是問,顧不得“常回家看看”而泛濫無歸。
8
回首百年新詩,有過耀眼的開端,有過艱難的過渡,也有過輝煌的成就。尤其是,還有過作為主要“介質”,去“定義”一個時代的歷史功用——如胡適、郭沫若等,之于五四“狂飆突進”時代; 瘂弦、洛夫等,之于海外“漂泊族群”時代; 北島、楊煉、舒婷等,之于“朦朧詩”時代等等——這一點,是其他新文學新藝術所無可比肩的。
然而,時代賦予你的,時代也就可能轉而他就。當下的問題是,當這種“定義”效應,隨著整個文學藝術的“下行”趨勢,逐漸減弱乃至喪失后,或者這一效應遲早或已然被其他藝術或亞藝術“介質”所取代后,作為純粹意義上的現代漢語詩歌,又該如何“定義”自己呢?
大概,也只能從如何重新認識和定義“漢語詩心”和“漢語詩性”上來,尋求新的位格與走向——設若認同這一理論前提,而需求解于具體人本與文本的“定義”之所在的話,本文給出的臨時答案是:
其一,不可替代的生存體驗、生命體驗、生活體驗——獨得之秘的中國經驗:
其二,不可替代的語言意識、文化意識、文體意識——獨得之秘的漢語詩性。
按時下說法,即:一則拼“走心”、“接地氣”,二則拼“語感”、“接底氣”。“地氣”者,當下時代脈動之在場;“底氣”者,古今學養修為之在心。二者居其一,即可別開生面;二者兼而得之,或可別開一界。
——最后的狂歡后,是該回到最初的詩意,而種玉為月、朗潤天下的了。
2017年5月29日定稿于西安大雁塔印若居
附:
[注釋]
1 [愛爾蘭] 葉芝:《人的靈魂》,轉引自《西方詩論精華》第3頁,沈奇編選,花城出版社1993年版。
2 [美] J.M.卜潤寧:《我寫詩工作的幾個階段》,同上第88頁。
3 [德] 尼采:《出自藝術家和作家的靈魂》,同上第48頁。
4 [英] T.S.艾略特:《詩歌的社會功能》,同上第49頁。
5 [美] 喬治.桑塔雅納:《詩歌的基礎和使命》,同上第8頁。
6 顧隨:《中國經典原境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28頁。
7 顧隨:《中國經典原境界》北京大學出版社2016年版第122頁。
(原載《文藝爭鳴》2017年第5期“詩論”欄目頭條)
作者:沈奇
來源:中國詩歌網
http://www.zgshige.com/c/2017-07-14/3816329.shtml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