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旗手般的優(yōu)秀詩人,同時也是一位對推動和繁榮當代新詩發(fā)展有卓越貢獻的人。以其為統(tǒng)領的“新歸來者詩群”,在新世紀以一股勢不可擋的回歸大潮,給詩壇注入了一支成熟浩大的生力軍。
他還是一位詩歌預言家,能前瞻未來20年詩歌發(fā)展的走向。他提出和倡導的“新新詩”概念,以及大型組詩《西域》的試驗寫作,給詩歌文本提供了一種全新的體驗及可能。實際上,他的創(chuàng)作和作用,已使他擔當和肩負了未來詩歌潮流的制造和引導者的重任。
——古箏
【訪談家】洪燭訪談錄
眉批大師
——張后訪談詩人洪燭

你喊著詩的另一個名字:“子虛烏有”。
張后:最近我特別喜歡安靜的坐在地板上翻拾舊書,經(jīng)常有意外的收獲,很多原來只能在紙片上見到的人,在北京我都見到了,比如你,我早幾年就讀過你的眉批天空的散文集,我沒有想到會有一天見到你,這是不敢去想的,但我現(xiàn)在在北京常常能見到你,你為人為友的古道熱腸總給我一種感動的情懷,我相繼在1989年的12月21日這期的《詩歌報》(總第127期)讀到你的詩歌,《祈禱》(外一首)《作為一只鳥與世界的同在》,還有《詩神》雜志1993年2月號的第52頁上登有你的《失樂園》、《蘋果園》二首詩,我最喜歡最后一首《蘋果園》,因為我現(xiàn)在就住在蘋果園,“離城市最近的地方,也是離秋天最遠的地方//一場雪在千里之外落下,掛滿枝椏”,巧了的是,在你的《祈禱》中你也寫到雪“在冬天,積雪覆蓋了道路”,其實更巧的是,在我的窗外,北京的天空剛剛下過一場雪,雪不大,卻是今冬的北京第一場雪,有可能是最后一場雪,雪令人寂寞呀?“蘋果園地址不詳。姓夏的女孩下落不明”你在雪中找過誰?她是否真實的存在?以這個有點私人化的問題做開場白,可以談也可以不談?
洪燭:《失樂園》、《蘋果園》二首詩,蘋果園地址不詳指伊甸園,姓夏的女孩下落不明指夏娃,這是代替亞當寫的愛情詩。夏娃是否真實的存在?她真實的存在于虛無中。跟著魔了似的,我曾經(jīng)在夢中寫詩。確切地說,是夢見了一首詩,覺得它就是完美。醒來后使勁追憶,只記得片斷的字句。看來它并未跟我一起醒來,仍然沉睡在黑暗里。我知道自己在現(xiàn)實中只能寫一些充滿缺憾的詩。你喊著詩的另一個名字:“子虛烏有”。而我卻把它當真了。把詩當真并沒有什么錯,可怕的是我還把生活當成假的。我翻閱過去的詩稿,如同撫摸著用來結繩紀事的一個個疙瘩——再長再直的人生,也需要不時地繞一段小小的彎路,才能留下深刻的印象。在給記憶打結的過程中,我偏離了現(xiàn)實,卻離美更近了。我不承認這是一種暫時的迷失。生活是散文,我考慮的是如何從中提煉出詩來。恨不得把整座太平洋,曬成一把鹽——九個太陽夠不夠?不夠的話,再加上一個;我隨時準備扮演第十個太陽。后羿,你有本事就把我給射下來呀!
繆斯不僅是詩神,更是我的命運女神……
張后:我喜歡聽詩人講故事,詩人的故事都很動人,講講你少年才子的故事,是如何被保送大學的?這對當今的少年人很有激勵的作用?榜樣的力量是無窮的,當今哪還有榜樣啊,我想以你來激勵讀到我訪談的那些少年人?你那時寫了多少作品?你的第一部詩集叫《《藍色的初戀》,我注意到許多詩人的第一部詩集都似乎和藍色有關?比如林雪的第一本詩集叫《談藍色的星》、蘇淺的第一本詩集叫《更深的藍》、桑朵的第一本詩集叫《水和藍色》……這是否和少男少女時期的憂郁情懷有關聯(lián)?
洪燭:八十年代初我在南京梅園中學讀書。瘋狂地愛上詩歌,甚至上課時都偷偷在筆記本上寫詩。還曾以原名“王軍”在《語文報》、《星星》、《鴨綠江》、《詩刊》、《兒童文學》、《少年文藝》等一系列報刊發(fā)表大量詩歌散文,十幾次獲得《文學報》等全國性征文獎。在全國中學校園贏得一定的知名度。1984年《春筍報》刊登王建一先生所寫《這迷人而又痛苦的路啊!——記南京梅園中學小詩人王軍》:“他似乎是一個成功者了,他的面前似乎是一片光明了。錯了,他還嫩得很,一切都還是未知數(shù)……他將咬緊牙關走下去,他準備付出巨大的代價,他說:我也許因此而上不成大學,但文學創(chuàng)作的路我是要走下去的。你能走到底嗎?你在已發(fā)表的一篇作品中寫道:假若有一天,刀忍不住所受的痛苦,它擺脫了磨刀石,結果將怎么樣呢?哦,世上將多一片銹鐵!”可以說是這篇報告文學使我奠定了當個大詩人的幼稚理想。要知道,那是個幾乎人人都懷有所謂“理想”的年代。1985年,我面臨高中畢業(yè)。2月18日《語文報》,刊登了我畢業(yè)之前寫在同學紀念冊上的五首詩《獻給同學的心花》,以及創(chuàng)作談《感情:詩的生命》。這在那一年的全國中學校園里,喚起很多畢業(yè)生的共鳴。他們紛紛來信關心我:畢業(yè)后會去哪里?還寫詩嗎?由于對文學全力以赴,也造成嚴重偏科,除了語文,數(shù)理化乃至外語等經(jīng)常亮紅燈,每次考試總屬于年級倒數(shù)第幾名。不但上大學無望,就算想拿到最基本的高中畢業(yè)證書都很困難。數(shù)理化成績一塌糊涂,連高考預考都未通過,我只好準備做個“待業(yè)青年”了。但自己仍想像高爾基那樣到社會(“我的大學”)上繼續(xù)實現(xiàn)文學之夢, 闖蕩一番,說不定也能寫出個三部曲啥的。有個中學同學的哥哥是開照相館的,我甚至準備畢業(yè)后去那兒當臨時工……當時梅園中學只是普通中學,沒有保送名額,幸好覺得我給母校爭得些榮譽,想出了一招:把我發(fā)表的作品及獲獎證書復印許多份(感謝那個時代發(fā)明了復印機!)向全國二十多所大學寄發(fā)了推薦函。很快,武漢大學特意派來一位負責招生的老師,領我去武漢面試。華東師范大學也約我去上海面試(他們還答應給我的中學另外五個入學名額)。最終,我選擇了武漢大學,作為免試保送生,沒參加高考就跨進了大學門檻。哦,對于我而言,繆斯不僅是詩神,更是我的命運女神,她帶給我好運氣!
第一部詩集叫《《藍色的初戀》,我最早的詩寫在日記本里。跟日記一樣,不是為讀者而寫的,也沒想到會有讀者。是寫給自己的,把自己當成讀者來寫的。為了留下點記憶。為了不至于被忘記。為了未來的某一天能有點回味的材料——或者說為了很久以后的反芻。寫詩之后我不再寫日記了,也許覺得不需要了:還有比詩更含蓄、更隱私也更保密的日記嗎?我能清晰地追憶起寫每一首詩那天發(fā)生的事情與心情。我能站在很久以后看見寫每一首詩時的自己,那成長中的或衰老中的一個個自己。
即使作為商品的以小說為代表的那部分文學死了,一直作為非賣品的詩卻是不死的。
張后:你現(xiàn)在能寫多少本書了?我看很多書店里都有你的書,曾有人說,你是寫北京的專業(yè)戶,每十本寫北京的書中,有你三本,這話不算蝎乎吧?看來你的版稅一定不少?一般你一本書吃百分之幾的版稅?順便談談當今的出版行業(yè)是怎樣的一種情況? 談談當今的詩歌是怎樣的一種情況?
洪燭:1989年7月,分配到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工作,在全國范圍數(shù)百家報刊發(fā)表作品,進行“地毯式炸”,獲《詩刊》、《萌芽》、《中國青年》、《星星》等獎,1992年在北京臥佛寺參加《詩刊》社第十屆青春詩會。1993年——1999年,詩歌的低谷期,居京大不易,厭倦了租房及睡辦公室,僅僅為了有能力買一套商品房(多么世俗而無力抗拒的一個念頭),就狠心地改變了個人的創(chuàng)作史,以淡出詩壇為代價,轉攻大眾文化,狂寫為稻粱謀的青春散文,覆蓋數(shù)百家發(fā)行量巨大的青年、生活類報刊,成為掀起九十年代散文熱的現(xiàn)象之一,被《女友》雜志評為“全國十佳青年作家”。其間出版詩集《南方音樂》、散文詩集《你是一張舊照片》、長篇小說《兩棲人》、散文集《我的靈魂穿著草鞋》、《浪漫的騎士》、《眉批天空》、《夢游者的地圖》、《游牧北京》、《撫摸古典的中國》、《冰上舞蹈的黃玫瑰》。2000年——2002年,如愿以償?shù)刈∵M商品房,開始為回歸詩歌做準備,撰寫數(shù)十萬字解讀大師與經(jīng)典的評論,后結集為《眉批大師》、《與智者同行》、《晚上8點的閱讀》出版。出版《中國人的吃》、《明星臉譜》、《北京的前世今生》、《北京的夢影星塵》等暢銷書。2004年——2007年,出版《北京的金粉遺事》、《舌尖的狂歡節(jié)》、《頤和園:宮廷畫里的山水》等暢銷書十幾種,其中《中國美味禮贊》、《千年一夢紫禁城》、《北京AtoZ》等在日本、新加坡、中國臺灣出有日文版、英文版、繁體字版。2009年初,中國青年出版社的歸來者詩叢推出我由400首短詩組成的詩集《我的西域》。近期,應花城出版社之約,撰寫歷史文化大散文《北京往事》,這是我繼《北京的夢影星塵》《北京的前世今生》《北京的金粉遺事》之后又一部表現(xiàn)“北京心靈史”的文化專著。今年底或明年初,花城出版社將推出這本列入“名城往事”系列的圖文書。

洪燭(左四)與詩友在南京雞鳴寺茶樓(2008年2月)
當今的出版行業(yè)是怎樣的一種情況?談談當今的詩歌出版行業(yè)?憤怒的書商高呼文學死了。意味著商品化的文學死了,或文學商品化的失敗?我想,即使作為商品的以小說為代表的那部分文學死了,一直作為非賣品的詩卻是不死的。即使把文學當作飯碗的作家全都餓死了,自帶干糧投奔文學的詩人卻是餓不死的——他們早就適應了野外生存。非賣品從來就不怕市場經(jīng)濟。它沒占過市場經(jīng)濟的便宜,也就不畏懼它所帶來的危機。全社會都搞市場經(jīng)濟了,詩依然是非賣品,很難作為商品流通,它創(chuàng)造的稅收恐怕是最低的。但在精神層面上,詩卻是創(chuàng)收大戶,近乎貪得無厭地索取著讀者的眼淚、心悸與微笑。當你情不自禁地被一首詩感動,等于替它上稅了。在真正的好詩面前,又有幾個人能“偷稅漏稅”?除非他鐵石心腸……
談談當今的詩歌是怎樣的一種情況?每個時代都對詩人的身分有不同的理解。所以,不同的時代甚至會出現(xiàn)截然相反的詩人。新詩90年,徐志摩恐怕是惟一進入大眾文化的詩人。哪怕是以他的緋聞。他與林徽因的關系,與陸小曼的關系,乃至最后的空難,使他作為詩人的形象增添了浪漫色彩。正如俄國的普希金,娶莫斯科第一美女岡察洛娃為妻,并決斗而死,事件能夠產(chǎn)生跟作品一樣深遠的影響。志摩與小曼的故事改編成電影《人間四月天》,更說明他身上有著大眾文化所需要的元素。即使對于一些不寫詩的80后,可能不知道胡適、郭沫若,不知道艾青,不知道北島、舒婷,大都聽說過徐志摩。當代詩人對徐志摩評價不高,其實他還是對新詩的傳播起到特殊的作用。如果徐志摩不曾誕生,將有相當一部分民眾說不出一位二十世紀的詩人。你信不信?尤其新時期以來,現(xiàn)代詩似乎已與大眾絕緣,變成小圈子里的生態(tài)。這即使不算壞事,也不能說是好事。是詩歌先遠離大眾,還是詩人先遠離大眾?造成兩者被大眾遺忘的共同命運。一個時代的詩人失去影響力,詩歌也就失去號召力。倒不是說詩人非要成為巨人,詩歌界還應多出幾位社會名人,以證明詩人的話語權乃至生存權并未完全喪失。別說新詩只有90歲,即使從《詩經(jīng)》的年代開始算起,中國詩歌的歷史也是有限的,它還沒有擺脫青春期。我之所以這么說,因為詩的未來遠遠大于它的過去,還有更多的可能性尚未發(fā)掘出來。這等于肯定了一種假設:詩是永生的。你、我、他,哪怕寫出再偉大的詩篇,也不過是其瞬間的戀人。它很快就會把目光投向更年輕的一代,一代又一代……或許這正是詩永褒青春的秘密。
如果說實用是美,那么詩既不實用,又不美。如果說美來自于不實用,倒有點像詩的專利,它不是不實用,而是太不實用了——當然這只對無關的觀眾而言。對于寫詩的人,它比藥與酒乃至魏晉風度之類亂七八糟的東西都要管用,當你或者失意或者疼痛或者空虛的時候。一試就靈!豈止如此,它還使你油然產(chǎn)生某種難以言喻的幸福感、充實感、成就感……所以詩真正的讀者還是詩人本身(彼此閱讀)。雖然大都是寫詩的人在讀詩,但隨著寫詩的人越來越多(肯定比寫小說的人多多了),讀詩的人也越來越多,詩反而有可能比小說之類文體獲得更多的讀者群。詩畢竟還多多少少能夠撫慰心靈(這就是它最大的用處)。在這個精神普遍存在種種障礙的時代,與詩相比,虛構的小說容易虛偽,或只是隔靴撓癢,反而顯得不那么實用了。據(jù)我所知,連寫小說的人都沒心思讀小說了(等于不相信小說),它的讀者群激劇縮小。而詩的讀者隊伍則隨著作者隊伍的擴大而擴大。問問那些寫詩的人,誰敢說自己不相信詩?不相信詩還寫詩干嘛?既然它如此不實用還能存在,一定有某種非其它事物所能代替的“無用之用”。世間沒有真正的無用之物,無用,也會有用。
詩的生存之道:以制造更多作者的方式來制造更多的讀者。詩人多了,不僅創(chuàng)作活躍,閱讀也變得繁榮。讀詩的樂趣不亞于寫詩。讀詩甚至能激活寫詩的沖動。許多人都通過讀詩而開始寫詩的。許多詩人中斷創(chuàng)作了,仍然戒不掉想讀幾首好詩的癮。詩是一種隱(隱于朝隱于市隱于野都可以),也是一種癮。寫詩過癮,讀詩也過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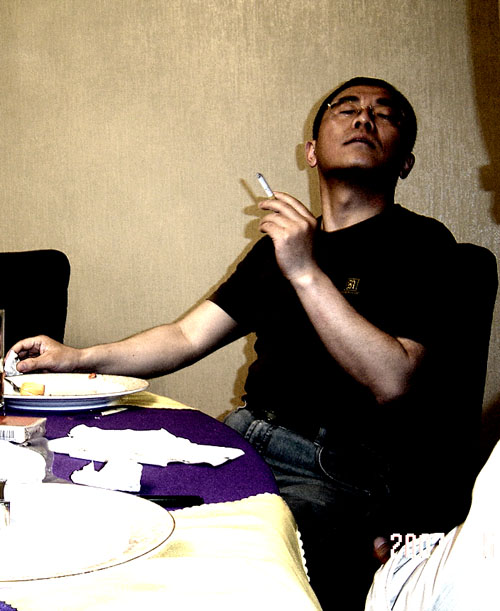
我太了解這一代人:屬于愈戰(zhàn)愈勇型,會活到老寫到老的。
張后:有人說我的訪談都是談些詩以外的漫不經(jīng)心的話題,其實我要的就是這個結果,我的訪談絕不是給寫詩人讀的,我希望更多的詩歌以外的人群透過我的訪談更多的了解詩歌圈中的人和事?2009-8-8我們在金寶匯上上國際藝術館過道里談得很激情揚溢,對了,還有安琪,三個六十年代人談了許多六十年代人和事,這種談話的方式似乎只有六十年代人才能做出來的事情,你能否對六十年代人這個“不可復制性”的群體再談些你的認知?
洪燭:60后詩人不是靠理論、而是靠作品說話的。也不是靠年齡,而是靠詩齡。在長征路上(八十年代詩歌運動),他們就是經(jīng)過槍林彈雨洗禮的老戰(zhàn)士了,至今尚未退役,并且體現(xiàn)出越來越強大的后勁。這些既有雄心、又有耐力的長跑運動員,把馬拉松的接力棒搶到手了,怎么也不舍得交出去……我太了解這一代人:屬于愈戰(zhàn)愈勇型,會活到老寫到老的。譬如我吧,也許不會號稱“先鋒到死”,但一定會“戰(zhàn)斗到死”——要知道,并不只有先鋒才算戰(zhàn)斗。先鋒固然能贏得戰(zhàn)術上的勝利,但不見得是惟一的戰(zhàn)略或最好的戰(zhàn)略。先鋒跟“60后”一樣,應該到被追認時才真正有效。60后的優(yōu)勢應該表現(xiàn)在:既不以先鋒、更不以傳統(tǒng)為門檻,它沒有門檻,如果有也只有一條——好詩!只要真的好,任何風格都可以。如果它也有什么風格的話,那就是包容性——建立在獨立性、獨創(chuàng)性的基礎上。包容先鋒,也包容傳統(tǒng),更要包容熔先鋒與傳統(tǒng)為一爐的集大成者。60后本身就誕生在傳統(tǒng)與先鋒的中間地帶,有容乃大。這是它區(qū)別于其他局域性的藝術流派的地方。60后是一代人的詩歌共同體而非詩歌流派。真正的大合唱就應該這樣:每個人都發(fā)出不同的聲音,而不是千人一面、千篇一律。有合唱隊,卻不需要隊長,更不需要打拍子的人。每個人都只服從于內(nèi)心的指揮。“林子大了,什么鳥都有”,反過來說更有力量——什么鳥都有,林子才顯得大。“60后”這個稱謂不是大籠子,60后詩人也不是圈養(yǎng)動物,他們恰恰是殺出一條血路,從不同的籠子里沖出來的——我從這一代人的孤獨與野性里看到更多的希望。
“北京,我是來征服你的。”
張后:最近我看到李犁的一篇文章《洪燭:物質(zhì)時代的活著的詩歌烈士》,他這樣評價你:“洪燭是這樣一種詩人,沒有宣言不用揚鞭,晨起開始勞作,日落依然不息。而且二十多年如一日。所以,洪燭不是那種以突然聳起的大廈來震驚詩壇的詩人,但他用成片成片的風格各異的村落悄悄地把詩壇覆蓋。”你認為他對你的評價過當嗎?我記得伊沙稱他自己是為全集而寫作的人,你呢?你是怎樣認知自己的?
洪燭: 二十年前,也就是1989年,從武漢大學畢業(yè)的我坐著硬板凳(火車硬座)來北京創(chuàng)業(yè),在老火車站重溫前輩沈從文初來時發(fā)的誓:“北京,我是來征服你的。”最近接受人民網(wǎng)采訪,說起這個細節(jié),主持人趙凝問我是否也發(fā)過什么誓,我說當時這么想的:“北京歡迎我,我來,不歡迎我,我也來。只要我來了,就趕不走了。”轉眼二十年過去了,我不在乎自己在這座城市里是否真有了一席之地,更希望精神上仍然坐著初出茅廬時的硬板凳、冷板凳,而不去搶那些安逸的沙發(fā)。那個二十二歲的文學“北漂”,如今已過了不惑之年,但愿他仍然對詩歌與人生保持著癡迷、困惑與好奇。2009年初,中國青年出版社的歸來者詩叢推出我由400首短詩組成的詩集《我的西域》。其中一首《向成吉思汗致敬》,證明了我的夢想還沒有老:“為了向成吉思汗致敬/我不說自己從北京來到新疆/我是從元大都來到西域/在荒廢的絲綢之路上/開始一個人的西征。什么時候/才能趕上/那消失了的大部隊?/正如詩人喜歡把西安叫做長安/我把北京叫做元大都,使自己/更像征服者/西域,同樣是新疆的乳名/成吉思汗就這么稱呼它的……”詩歌乃至文學,是繁榮還是蕭條,將漲潮還是退潮?我沒想那么多,它對我的影響不會很大。就像前面那二十多年一樣,我仍將做文學的“釘子戶”。誰想拆遷就拆遷吧,反正我就住這兒了,趕也趕不走。別說至少還有冷板凳、硬板凳可坐,即使是站票,我也要啊。二十年前,投奔文學理想,我已做好了自帶小板凳的準備。文學永遠不會攆她的追求者的,我干嘛攆自己呢?只要文學不死,我就不會成為喪家之犬。2009年,我對文學感情更深了,態(tài)度更虔誠了。文學活著,我愿意為她看大門。即使真像某些人預言的那樣——文學死了。她也會有守陵人的。不是還有我嘛,我會站好我的這一班崗。我知道能這樣想的,可不僅僅是我一個人。文學的鐵桿粉絲多著呢。即使文學真的死了,她的靈前也會點一盞長明燈,只要燈火不熄,就等于文學仍然活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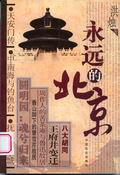
她可以使一個死去的詩人活過來,你信不信?
張后:西域一直在我的夢境里,那實在是遙不可及的夢魂,也許在我的夢境里,真正的西域是根本不存在的,但我發(fā)現(xiàn)你的西域很真實,“柵欄由干枯的樹枝編織,圈住了彼此還未熟悉的牛羊。從山坡上走來的,每一個都是陌生人。純粹靠圖案類似的服飾相互辨認……”從你的寫作中看得出來你對西域有很深的感情,你到過西域幾次?讓我們一同分享你的感受吧?
洪燭:2005年10月,我第一次到新疆,當時中坤集團邀請“中國詩歌萬里行”、“詩刊社青春詩會”、“帕米爾詩歌之旅”三支團隊,供赴新疆采風,近百位中外詩人結伴同行,以浩浩蕩蕩的車隊,從烏魯木齊出發(fā),走過庫爾勒、輪臺、庫車、阿克蘇、阿圖什、喀什、塔什庫爾干……我參加的是“中國詩歌萬里行”,有祁人、娜夜、趙麗華、北塔、李自國、雁西、周占林,張況等十幾位成員。我不知道別人怎樣,自己確實感受到強烈的震撼。畢竟是第一次來(就像展開和新疆的初戀)。但這第一次,就使我意識到:以后每次來都會這樣,都會像觸電了一樣。到目前為止,我只去過一次新疆。這惟一的一次旅行,還不到十天,僅限于烏魯木齊和南疆的庫爾勒至喀什一線。我卻寫出了由大約400首短詩構成的《西域》。新疆是我文學上的一次“艷遇”。就像轉瞬即逝的洛神會改變曹植,如果不曾遇見新疆,我可能只是個很平庸的詩人。在新疆,短短的十天,可從第一分鐘開始,我如同浮士德面對海倫:“美啊,請停留片刻!”對于歌德來說,海倫不僅是世界第一美女,更象征著不可一世的古希臘文明,是古典主義的化身。新疆之于我也是如此,凝視著她的美貌,我腦海里常常浮現(xiàn)出另一個人,下意識地念叨她的另一個名字:西域(這被無數(shù)古代詩人呼喚過的)。她已成為西域在現(xiàn)實中的替身。希臘有海倫,新疆有香妃。我慶幸自己找到了抒情的對象——她可以使一個死去的詩人活過來,你信不信?回到北京,我狂熱地寫下第一首詩《降落在月亮上》,一發(fā)而不可收,仿佛噴泉的開關被打開了,一年時間里,寫出了長達8000行的大型組詩《西域》。北京是我的現(xiàn)實,新疆是我的夢。一個光有現(xiàn)實而沒有夢的詩人,是行尸走肉,無法長期保持創(chuàng)作的激情。我是幸運的,找到了自己的夢,而且是最想做的一個夢。我以四十歲的年齡,進入西域,進入這個已做了兩千年的美夢——她奇跡般地保持著青春。對于我的詩歌,夢境才是最好的故鄉(xiāng)。我為一些我沒有去過的地方寫了詩,譬如羅布泊、樓蘭、吐魯番、巴音布魯克、和田、英吉沙、疏勒,譬如北疆的吉木薩爾、伊犁、和布克賽爾、阿勒泰、額敏……似乎比去過那些地方的人寫得還要好。只能說明我的想像力比他們更發(fā)達而已。想像力彌補了我生活閱歷的匱乏。惟一弄不懂的是:我想像出的這些場景純粹子虛烏有,還是確實存在?我甚至預感到:若干年后,真正去這一系列地點的時候,我會想到什么?我會覺得這些地方我曾經(jīng)來過,而且它在我來過之后沒有任何變化。我對未曾抵達的遠方的想像與其現(xiàn)實會是如此接近,也就是說我的想像似乎從來不曾欺騙我。難怪我這么喜歡生活在想像中或者在想像中生活呢。其實整部《西域》,都不能排除想像的功勞。它之所以不以新疆而以西域來命名,很明顯是為了增加幾分虛幻色彩,為了激發(fā)自身的想像或者給想像留下足夠大的空間。如果沒有這份足以炫耀的想像力,我去新疆,即使走遍天山南北,恐怕也只能留下幾篇蹩腳的游記。可我畢竟為它寫出在時空上更顯深遠的一大組詩《西域》,仿佛同時經(jīng)歷了它的前世與今生,想像是其中很重要的添加劑。對于詩人而言,除了直接經(jīng)驗,間接經(jīng)驗同樣可以激發(fā)想像;想像一旦被有限的經(jīng)驗激發(fā),甚至可能制造新的經(jīng)驗。體驗生活,莫如體驗自己的想像。

2012年,左起,張后、洪燭、周瑟瑟、王士強
……詩是一種童子功。
張后:你寫作題材廣泛,漫無邊際,我常常納悶,你哪來的那么多的激情和精力,我就是天天追趕著在你博客閱讀都趕不上你書寫的步伐,你更新的太快了,你每天的寫作時間是如何分配的?有什么秘訣保持創(chuàng)作的旺盛?
洪燭:對流浪的青年時代的寫照:我沒有屬于自己的房子,就像一架飛機(甚至可以說是一架戰(zhàn)斗機),卻沒有飛機場,因而只能日以繼夜地在空中盤旋、滑翔,連夢都不敢做,生怕打個盹就墜落了。可即使這樣,我也沒有停止戰(zhàn)斗啊,我不斷地寫詩,不斷地扔出精神炸彈——對想象中的文學界進行著“地毯式轟炸”。某些時候,還不得不跟狹路相逢的別的飛機展開格斗——它們意識不到,我正是因為找不到自己的飛機場才格外地勇敢。我已經(jīng)準備好把天空當成墳墓了。幸運的是,我沒有失敗,我擁有了天空,擁有了最為開闊的飛機場,我可以在戰(zhàn)斗中休息,在休息中戰(zhàn)斗……詩是一種童子功。詩人就該是赤子。我從少年時期癡迷上寫作,一鼓作氣地堅持到現(xiàn)在,童子功還沒破呢。夢也還沒有破呢。沒有夢又如何寫詩?如果說我的詩與眾不同,因為我做著的是原始的夢。我是一個保守的人,當周圍的寫作者紛紛追求另類,似乎只剩下我在原地踏步,我忽然發(fā)現(xiàn),自己反而成了另類中的另類,或真正的另類。
光靠吐口水很難完成長詩的,吐完了口水、胃液,終究要吐血的。
張后:這兩年你一直寫長詩,先后完成了《西域》、《李白》、《黃河》、《地震心靈史》,你對長詩的書寫方式很情有獨衷?其實長詩很考驗人的?才氣、激情、情懷、氣韻……等等?你對寫長詩有什么與眾不同的心得?
洪燭:詩人沒有長詩,是否會像小說家只寫中短篇、卻沒有長篇小說那樣遺憾?魯迅、博爾赫斯,都屬于沒有長篇小說的優(yōu)秀小說家。沒有長篇小說的小說家很難獲諾貝爾文學獎的。沒有長詩的詩人,照樣能成為大詩人。因為詩歌原本就不以長短來見短長的。但一位詩人如果能寫出長詩,無疑是好事情,證明他不僅有爆發(fā)力還有耐力,不僅會百米沖刺,還能跑馬拉松,是稱職的長跑運動員。長跑,屬于比較專業(yè)的訓練了,業(yè)余選手很難勝出。同樣,短詩屬于輕武器,百步穿楊固然是本事,但射程更遠的是重武器,譬如火炮。優(yōu)秀的長詩,應該有精確制導炸彈那樣的航程和命中率,甚至可以有像核武器那樣的威懾力。一個時代的詩人都把目光投向長詩,就像準備進行軍備競賽,誰不希望自己的武庫中能有一枚原子彈?詩人,不應該只滿足于小米加步槍的。尤其在口水詩泛濫成災的日子里,詩被看成了最無難度的寫作,詩人被當作唾沫制造者或段子發(fā)明者,提倡長詩有其積極意義。長詩之長,本身就構成客觀上的難度,以劃分專業(yè)選手和業(yè)余票友。這還只是形式上的,更大的難度一定來自內(nèi)容,“寫什么”將和“怎么寫”同樣重要。平地起高樓,可比挖一孔窯洞難多了,需要足夠的建筑材料和結構能力。長詩,在考驗著它的作者的知識儲備、情感儲備、智力儲備,運用技巧的能力,以及耐心、耐力。它是一座隨時都可能倒塌的巴比塔。哥們,你能把它托住嗎?口水淹不死人,也托不起船——尤其是噸位很大、吃水線很深的船。它太淺了。你要是有深水炸彈的話,不妨投進長詩里。光靠吐口水很難完成長詩的,吐完了口水、胃液,終究要吐血的。好的長詩都應該吐血完成,這是它比那些口水詩高貴的地方。我要在自己的血海里游泳。當然,我首先要找到一個傷口。它不應該是“無痛寫作”或無病呻吟。無病,也很難通宵達旦地呻吟。所有人關注的都是長詩之長(篇幅上的),常常忽略了另一個要素:重。它應該是重磅炸彈,是萬噸貨輪。它無法承受的是輕而不是重。構思一部長詩,你必須找到壓艙之物:無論題材上的,思想上的,或情感上的。光玩形式、玩技巧可不行。你不得不考慮到內(nèi)容的問題。短詩是輕量級的競賽,花拳繡腿也容易蒙混過關;長詩是重量級的,是硬功夫,硬碰硬的。它越來越嚴峻地考驗著一個人各方面的積累:你是否有實力發(fā)動一場立體化的戰(zhàn)爭?寫短詩是騎馬,寫長詩是駕馭馬車。我首先追求的不是速度,而是平衡。一旦真正地達到了平衡,血流的速度、閃電的速度自然應運而生。
……我不是花和尚,我是詩和尚。
張后:臧棣曾說“生活的深度,其實絲毫不值得我們?nèi)パ芯浚挥猩畹谋砻妫胖档梦覀優(yōu)橹畠A注如潮的心血”,所以在我的歷次訪談,我更關注的是詩人的當下生活,比如我就很想知道,你每天是怎樣生活的?你一直保持著“宿舍,自行車,背包,還有單身……”始終給人以在路上的感覺,很多人向我打聽過你,而我對你的實際生活形態(tài)其實也所知了了,你可以打開你的生活窗口,讓我們窺探一二嗎?
洪燭:理想才是詩人真正的祖國,他僑居于現(xiàn)實。詩人的生活比詩人的作品更吸引我。也就是說,生活才是他最隱蔽同時又最真實的作品。即使他有能力欺騙讀者,卻無法欺騙自己——無字的詩就這樣寫下了。而有形的詩充其量不過是其投影。在這過程中甚至可能被他本人做過一些善意的掩飾或歪曲。想了解詩人的形象,讀他的作品可能就夠了。但要想了解他的內(nèi)心,必須回到生活的現(xiàn)場——瞧瞧這個人是怎么放縱或克制自己的……我不是花和尚,我是詩和尚。對待詩,有時需要宗教般的虔誠,為自己的信仰作出犧牲。包括以世俗的歡樂,去換取精神的愉悅——并且要覺得很值!
真正的好詩都是做白日夢的詩人寫出的……
張后:我的詩歌寫作比較傾向于古人的“羚羊掛角,無跡可求,故其妙處,透徹玲瓏,不可湊泊,如畫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鏡中之象,言無盡而意無窮”這一理念的,你呢?你最理想的寫作形態(tài)是什么樣子的?
洪燭:詩人不是食肉動物,也不是食草動物,而是趨美的動物(像趨光的動物燈蛾撲火那樣趨美),美是他精神上不可或缺的食物。如果沒有美,詩人即使不會餓死,也會渴死。好在這個世界不可能沒有美的,所以詩人是不死的,作為人類文明的一個種族,是不會消亡的。缺少美的時候,詩人們饑渴難耐,痛不欲生。但哲學家說得好:“從來就不缺少美,而是缺少發(fā)現(xiàn)。”于是詩人即使置身丑陋的現(xiàn)實中,仍然努力去挖掘、去發(fā)現(xiàn)——美啊永遠在身邊。即使身邊的美像高原的空氣一樣稀薄,他也會憧憬遠方,遠方總會有美的。遠方這個概念本身就很美。這種憧憬,本身就很美。越是無法達到的遠方就越美,因為你的憧憬將無法實現(xiàn),幾乎快構成一場曠日持久的白日夢了。真正的好詩都是做白日夢的詩人寫出的(譬如李白的夢有著最遼闊的疆土)。夢是詩人的根據(jù)地。如果連一塊夢中的疆土都沒有,詩人比乞丐好不到哪里去。稍微有點野心的詩人,都想做詩的封疆大吏,都想有夢的自治州。恐怕只有詩這種“交通工具”,才能使時光倒流,幫助我上溯到這個美夢的源頭.
又一代人從市場經(jīng)濟中弄潮歸來,在克服了生存壓力后忘不掉初戀情人,攜帶著在其它領域里的種種戰(zhàn)果向闊別的繆斯獻禮。
張后:我看到古箏主編的《歸來者詩刊》你寫的序言,請詳細談談這個“詩歌寫作歸來者”現(xiàn)象如何?
洪燭:新時期詩歌經(jīng)歷了八十年代的繁榮、九十年代的寂寞之后,在新世紀又再度輝煌。許多“年輕的老詩人”在世紀末的塵囂中不得已中斷歌唱,持久的沉默之后遇見萬物滋長的詩壇“第二春”,又梅開二度、重續(xù)前緣,已經(jīng)形成陣容龐大的歸來者詩群。是日漸繁榮的詩壇吸引著更多的人歸來,還是更多的人歸來增強了詩壇的繁榮?或許兼而有之吧。這一不斷有人歸隊的景像使我聯(lián)想起新時期之初艾青等老詩人的歸來(一代人被政治運動打散了,待到冰消雪化時,重新唱起‘歸來的歌’)。又一代人從市場經(jīng)濟中弄潮歸來,在克服了生存壓力后忘不掉初戀情人,攜帶著在其它領域里的種種戰(zhàn)果向闊別的繆斯獻禮。更重要的,這些詩歌的游子還為詩歌寫作空間注入了酸甜苦辣、非同尋常的人生經(jīng)驗——他們用告別、孤獨、遺忘或思念換取的。這是新時期以來詩的第二次回歸,和重復的勝利。歸來者確實是近年來詩歌繁榮的中堅力量,他們有過八十年代的經(jīng)驗,而且保持著八十年代的激情。對于中國詩歌的發(fā)展,這批歸來者將成為很重要的力量。去各地參加活動,我都能邂逅重起爐灶的歸來者。他們用行動為自己命名。為自己重新命名。由于2006年以來,我和眾多詩友一起為詩歌界歸來者現(xiàn)象鼓與呼,我還執(zhí)筆寫了《歸來者:不是宣言的宣言》,中國青年出版社隆重推出《歸來者詩叢》,為詩歌的升溫,詩人的堅守或回歸提供支持。還是“歸來”詩人吳茂盛說得好:讓我們把詩歌進行到底。
我覺得詩還是要讓人感動。
張后:最后一個提問,乃是我的系列訪談中的終旨:“你為什么寫詩?”
洪燭:“你說他們?yōu)槭裁床粚懺姡俊薄澳悄闶紫纫f出你為什么寫詩?也許你寫詩的原因正是他們不寫詩的理由。”詩給社會帶去了什么我不知道,我只知道詩給詩人的內(nèi)心帶來無限的樂趣。這種樂趣非其他事物所能代替。妙不可言,詩偏偏要把不可言說的妙給表達出來。你應該理解詩人完成這一幾乎非人力所能完成的工程之后,臉上浮現(xiàn)出幸福的神情。詩人自以為是原創(chuàng)者,其實不過是世間一切奧妙的翻譯……有人認為所謂的“感動寫作”藝術起點不高,我覺得詩還是要讓人感動。首先要感動自己,如果自己都無法感動,怎么寫得出詩來?那你寫詩干什么?這樣的社會,難道還愁無事可做嗎?其次要感動別人,如果別人讀了跟沒讀一樣,干嘛要來讀你的詩呢?我寫詩的原始目的是自我感動,兼而能感動讀者,則實現(xiàn)了額外的價值,多多少少能滿足寫作上的虛榮心:感動,也是一種兵不血刃的征服啊。有點虛榮心沒啥不好的。

張后(左)與洪燭
洪燭簡介:
洪燭原名王軍,1967年生于南京,1979年進入南京梅園中學,1985年保送武漢大學,1989年分配到北京,現(xiàn)任中國文聯(lián)出版社編輯室主任。出有詩集《南方音樂》《你是一張舊照片》,長篇小說《兩棲人》,散文集《我的靈魂穿著草鞋》、《浪漫的騎士》、《眉批天空》、《夢游者的地圖》、《游牧北京》、《撫摸古典的中國》、《冰上舞蹈的黃玫瑰》、《逍遙》、《北京的夢影星塵》、《北京的前世今生》、《北京的金粉遺事》、《眉批大師》、《與智者同行》《中國人的吃》、《風流不見使人愁》、《多少風物煙雨中》《永遠的北京》、《晚上8點的閱讀》、《閑說中國美食》《拆散的筆記本》、《頤和園:宮廷畫里的山水》、《北京沒有風花雪月》等數(shù)十種。其中《中國美味禮贊》、《千年一夢紫禁城》、《北京AtoZ》等分別在日本、韓國、新加坡、中國臺灣出有日文版、韓文版、英文版及繁體字版。
古箏簡介:
現(xiàn)居南京。江蘇省作家協(xié)會會員。曾獲《芒種》2008年度詩人獎,“歸來者詩群”代表女詩人。作品散見各類省級報刊,并收錄《2008中國詩歌年選》等多種詩歌選本和年鑒。著有詩集《虛構的房子》(2007)、《濕畫布》(2009),詩合集《南京五人詩選》(1992)、《五味子》(2007),編著詩評集《品箏集》(2008),主編民刊《陌生》詩刊。
張后簡介:
中國著名獨立詩人、高產(chǎn)作家。曾被評為1917--2016影響中國百年“新銳詩人”。其作品以情詩為主,意象奇幻,視角新穎,充滿新唐詩之美。擁有廣泛的讀者,素有“夢幻之王”之美譽。并獲過多種獎項,2017年獲得網(wǎng)絡文學詩歌組銀獎。并著有歷史小說春秋三大霸主系列:《雄飆霸主齊桓公》《威凌霸主晉文公》《荊楚霸主楚莊王》(1998)、長篇小說《再紅顏一點》(2004)《像鳥一樣飛》(2003年)、詩集《少女和鷹》(2004)《夢幻的外套》(2007)《紙上玫瑰》(2008)《牙齒內(nèi)的夜色》(2005)《張后網(wǎng)絡詩選》(2005)《草尖上的蝴蝶》(2005)《獨自呢喃》(2012)及《三人詩選》(田力、張后、韓永合著2002)《叢林七子》(羅唐生、楊然、張后、趙福治、北塔、周占林、張嘉泉合著2013)、散文集《月光下的水影》(張后、海沫合著1995)、隨筆集《詩人之夢》(2015)。《張后訪談錄——訪談詩人中國》(2012)、訪談錄《詩人往事》(2015)。2012年自編自導自演中國首部以詩人海子拍攝的詩電影《海子傳說》。2016年創(chuàng)辦中國唯一訪談類專刊《訪談家》。現(xiàn)居北京。
來源:張后供稿
作者:張后 洪燭


 純貴坊酒業(yè)
純貴坊酒業(y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