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肯談李浩:他開始向上,讓身體有了信仰、天空

寧肯(作家,十月雜志常務副主編,本文為其在李浩詩集《還鄉》發布會上的發言)
李浩詩集《還鄉》出版,這個對李浩來講,是一個非常重要的開始,一個詩人能夠結集出版一本詩是個標志性的事件。這里應特別感謝我們的出版社,詩集的出版不是一個賺錢的生意,出版社著眼于詩歌和詩人,著眼于這種在當下非常重要的才華,表現他們一種自己的職守,值得尊敬。
詩集出版之前,他就把部分的詩歌給我看了,對于李浩這樣一個80后的詩人,我覺得他的特點還是非常的突出的,我讀他的詩歌里面給我最突出的印象是他打開了自己的身體,這個身體在李浩的詩歌中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身體寫作前些年并不陌生,我們知道詩歌有一個流派叫做下半身寫作,也是強調了身體,那個身體我覺得代表那個時代的特點。身體寫作經過這么多年發展沉寂之后,由李浩重新強調起來以后,顯示了一個非常大的不同。這個不同在于李浩更多強調的身體是上半身,不是下半身的寫作,下半身走向不是朝精神方面走,是朝著生活中的非常邊緣的方向走,甚至是一個驚世駭俗的、非常震驚的方向,到了李浩的身體寫作,則有了另一種精神的表現,他擺脫了90年代以來形而下的一種趨向,他開始向上,讓身體有了信仰、天空。
我們知道下半身寫作,當初經常攻擊詩歌寫作的一點是,詩人人們只強調精神、理想、心靈、靈魂,他們正相反,現在李浩回過頭來再次相反,再次強調靈魂,這個時候李浩強調靈魂和過去下半身詩歌寫作攻擊的靈魂已經不同了,我覺得是一個否定之否定,有一些事情在你否定了之后再去肯定才能顯示出價值,我覺得李浩重新肯定了身體寫作,或者身體和精神方面的寫作,這個是李浩詩歌的特點,也是一個他的意義。我沒有想到這么一個寫作由他這么一個年輕的青春的身體來完成這樣一個形而上的身體寫作,這是我沒有想到的。
讀李浩的詩,感覺李浩的由詩歌構成的身體感覺像一個樂器一樣,這個身體好像布滿了笛子的孔,每個孔都會發出自己的聲音,在他的不到10首詩里面用了和身體有關的詞語,我羅列了一下,就有這些:肥胖、身體、靈魂、腦子、手、衣袖、嘴唇、喉嚨、心,甚至包括智齒都寫進了詩歌里,還有耳朵、頭頂、頭顱、眨眼、鼻孔、心腸、胸口、下跪、叩頭、腦門等等。我們不但可以聽到李浩演奏的聲音,甚至我們還能看到他詩歌內部的構成,他如何敲打詞語,就像我們聽到鋼琴一樣,我不但看到他的手指在演奏,我們還看到琴蓋后面的木捶在敲擊,就是他的身體整從里到外都是個開非常好的打開的狀態,那么這個狀態又是而上的打開和發揮,某種意義上講,實際上李浩還是受到了整個身體寫作的影響,只是他的導向、朝向是往上的,這個是李浩詩歌非常重要的方面,所以我覺得上天創造了李浩身體性的音樂,這音樂性的身體來為我們演奏生活、演奏靈魂,這方面我覺得是李浩的詞語非常大的有特點,是李浩詩歌的一個標志。
另外,李浩的另一個特點,他這么年輕,他有一種信仰,這個信仰涉及到了宗教。我們過去的詩歌里面一些詩人也會經常涉及到一些宗教的詞匯,但是沒有像李浩這么堅定,這么扎實,這么誠懇。宗教、信仰和他的身體,和他身體打開的狀態結合在一起,是李浩特別明顯的一個特征。按理說,一般來講宗教和信仰是排斥身體的,甚至身體和精神和宗教是一個矛盾,是一個對立,是一個沖突,過去我們表達這方面的沖突比較多,而李浩的詩歌使這些是成為一個和諧的整體,他的那種和諧、洞穿,他的渾然一體,你可以感覺到他就在他的教堂里面一樣,在演奏自己的圣歌。
再有,還讓我驚異的是,李浩這樣一個敏感的身體和靈魂,他不僅僅關注自己的內心,他偶爾也關注身體之外的事物。我印象特別深的是李浩詩中有一個寫北京的場景,寫鼓樓的那首詩,那首詩描述生活場景,都市、時尚的拼接,信手拈來,類似于搖滾性的結構感,場景讓撲面而來。某種意義上來講,其實李浩這樣一個靈敏的身體有時候就應該放在那些喧囂的都市,讓他去感受,去反映,去演奏,反而對喧囂更有一種特別的把握。什么東西對巖石的感覺最強烈?我覺得應該是蝸牛,最軟的對最硬的感覺最強烈,蝸牛當沒有人的時候,當它的身體出來的時候,它在貼著路走的時候,對外界的敏感性是最強的。所以我覺得像李浩這樣極其柔軟敏感的身體當他寫北京鼓樓都市那種喧囂的時候,可以感覺到他的靈敏度已經達到了蝸牛的那種觸感,反映出來的都市特別有特色。所以我認為李浩除了他的敏感,我覺得他的敏感可以繼續表達他身體之外的世界,通過他的己有特點的來感知外部的世界,因此我看到李浩不僅僅是一個靈魂的詩人,一個身體向天空打開的詩人,他還是一個可以關照都市、可以關照大千世界的詩人,而他會給這樣的世界帶來了他的身體的特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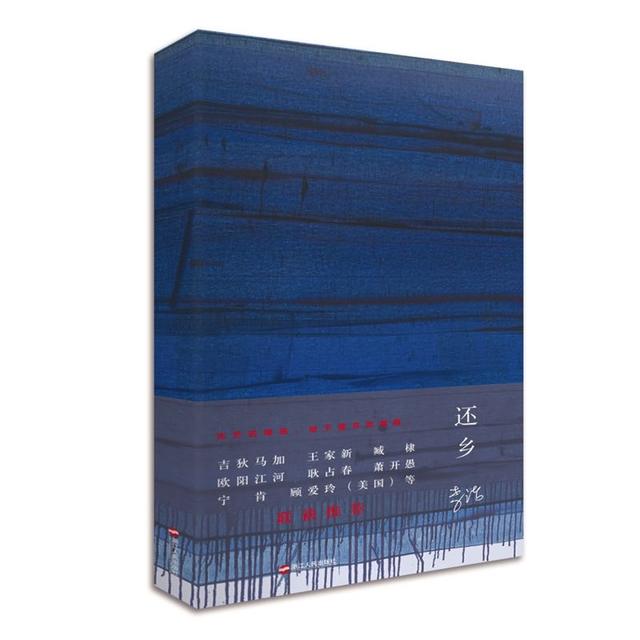
《還鄉》,李浩 著,浙江人民出版社
責任編輯:魏冰心 PN070
作者:寧肯
來源:鳳凰讀書
https://share.iclient.ifeng.com/shareNews?forward=1&aid=cmpp_060220000078681#backhead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