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詩學的倡導與實踐
——李少君論
趙思運/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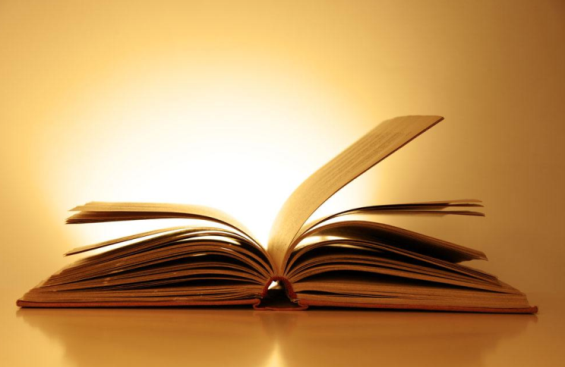
摘要:李少君既有鮮明的詩學思考力和強烈的理論驅動力,又具有較強的詩藝外化能力。李少君多年致力于“草根詩學”的倡導,并在持續的“自然詩學”創作實踐中彰顯出“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內涵。李少君的自然母題表達之中,融入了具有現代生命意義的沉思品質,在傳統與現代既博弈又和諧相處的辯證關系中,對古雅詩學范式進行了新的拓展。李少君的草根詩學理論及其創作實踐,有助于我們思考文化生態的可持續性發展以及傳統文化、傳統詩學在當下的命運,具有重要的本土文化尋根的意義。
李少君既有鮮明的詩學思考力和強烈的理論驅動力,又具有較強的詩藝外化能力。早在武漢大學讀本科的時候,李少君就發起了珞珈詩派。他不僅是一個活躍的詩人,還是一位叱咤風云的理論文章主筆。在主編大型雜志《天涯》的時光,由于雜志涉及到文學、文化、思想等多種綜合性學術背景,李少君研讀了大量政治、經濟、法律、社會學之類的著作,不僅激發了他的理論敏感性和問題意識,也為學術批評打下了扎實功底。他在21世紀倡言的“草根性”“新紅顏”都成為耳熟能詳的關鍵詞。他以扎實的詩歌實踐,將詩學思考呈現到詩歌文本之中。其詩集《草根集》[①]《自然集》[②]《詩歌讀本:三十二首詩》[③]等,充分展示出他的創作實績。他的詩學思考和創作實踐,都帶著鮮明的本土性色彩。
一、“草根詩學”的自覺
“草根性”在文學、藝術、文化、思想等領域,都是一個新的概念。進入21世紀,經過李少君的理論倡言和創作實踐,“草根性”成為一個重要的詩學關鍵詞。李少君還編選出版了《21世紀詩歌精選(第一輯)草根詩歌特輯》。[④] 并且把自己的詩集取名為“草根集”。
關于“草根詩學”的內涵,一般人往往顧名思義地理解為“底層性”。李少君給出了詩學的界定:“我強調一種立基于本土傳統,從個人切身經驗感受出發的詩歌創作,也就是‘草根性’。所謂‘草根性’,如果用一句話來概括,就是指一種自由、自發、自然的源于個人切身經驗感受的原創性寫作。”[⑤] 這種草根性詩學可以提煉出三大關鍵詞:本土性、自由自發自覺、原創性。他強調本土性,是相對于過度外來化的詩學傾向,主張關心民間底層、關注中國問題和中國現實;強調自由自發自覺,是基于移植而來新詩逐漸遠離了詩人的真誠,因而重新主張深入中國人心靈世界;強調原創性,是基于對西方模式的模仿,意在打破僵化、模式化的集團化寫作,而主張重回漢語起點,專注于個體生命體驗和漢語詩意空間的再發現。李少君對草根詩學的呼喚,其實是主張讓橫向移植過來的新詩在中國本土落地。
李少君對于中國詩學傳統根基——草根性——的觸摸,也是基于新詩歷史的反思。他清楚地知道,“新詩”(當時叫白話詩)從西方移植過來,源于“五四新文化運動”同人進行社會改造的急功近利思想,新詩就是文化運動和社會改革的武器。那場文學革命,徹底切斷了新詩與古典詩學的淵源。整個20世紀新詩史貫穿了兩條主線,一條是激進主義主導的革命思潮,切斷了傳統的本土文化之流脈,這是主線;另一條是西方現代主義詩學,這是暗線。新詩的本土性和草根性一直被懸置起來。
“草根詩學”在中國本土語境里最主要的表現就是“自然詩學”。自然詩學的文化基因在于漢語詩歌的載體漢字的自然性。漢字具有獨特的詩意,具有其他語言所無法具備的文化基因優勢。從漢朝以來,關于漢字造字法,流行的說法是“六書”。“六書”包括“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轉注”和“假借”。實際上,后兩種屬于用字法,而不是造字法。漢字的造字方法有四種,即“象形”、“指事”、“會意”、“形聲”。《說文解字》解釋道:“象形者,畫成其物,隨體詰詘,日月是也;指事者,視而可識,察而見意,上下是也;會意者,比類合誼,以見指揮,武信是也;形聲者,以事為名,取譬相成,江河是也。”“六書”之首即是“象形法”。漢字最初就是對自然物象給出的反映、印象、理解與認識,是始終不脫離具體的自然意象的行為呈現,所以,申小龍、石虎等文字學家和書畫家都十分重視“字思維”。李少君也清醒地認識到:“中國文化因為是建立在象形字的基礎上,就更能看出自然對中國文化的影響了。象形字里本身就藏著自然,是具有實指性的。” [⑥] 李少君還詳細論述過漢字的三大特性:實指性(與具體物象有關)、超越性(蘊含的多樣性能指以及宗教的超驗維度)、強大的適應性(隨著時代變化而進行自我重組的能力)[⑦]
“草根詩學”和“自然詩學”是李少君詩學思考的邏輯起點,也是他詩歌創作的母題和基調。中國文化傳統與西方文化傳統是兩條河流,中國傳統文化講究“和諧”,講究“詩可以群”;西方詩學則強調“個體”,強調“對抗”。西方以上帝為靈魂皈依,現代派喊著“上帝死了”,實質上是詩人自己取代了上帝,從而像上帝一樣去批判現實社會和社會中的人性,特別關注個體與社會的對抗以及由此產生的個體痛苦。他們聚焦于個體靈魂的孤獨、絕望、破碎、虛無、抗爭、失敗。中國則特別講究“詩教”傳統。所以說,西方有《圣經》,中國有《詩經》。李少君說:“重實用講世俗的儒家文明怎樣獲得生存的超越性意義,其實就是通過詩歌。中國古代依靠詩歌建立意義。因為在沒有宗教信仰的儒家文明中,唯有詩歌提供超越性的意義解釋與渠道。詩歌教導了中國人如何看待生死、世界、時間、愛與美、他人與永恒這樣一些宏大敘事;詩歌使中國人生出種種高遠奇妙的情懷,緩解了他們日常生活的緊張與焦慮;詩歌使他們得以尋找到現實與夢想之間的平衡,并最終達到自我調節、內心和諧。”[⑧] 李少君在中西兩種文化視野中,在對民族文化當下癥結的思考中,建立起自己的詩學理論。
李少君久居現代都市,為何在21世紀初期能夠生成“草根詩學”并且一直從事自然主題的詩歌創作?
從發生學的角度講,李少君最初的詩歌寫作完全是得益于大自然的啟蒙。他在《在自然的廟堂里修身養性》一文里有詳細述說。1967年出生的李少君,由于父母擔心城市的混亂給他帶來意外遭遇,把他送到鄉下的奶奶家,“在湘中的青山綠水間,我過上了真正的無拘無束的童年生活,奶奶行動不便,完全管不住我,就放任我在自然的懷抱里摸爬滾打。”[⑨] 后來,回到城市的父母身邊,“很長時間不能適應,以至由一個開朗活潑的孩子變得寡言少語,內向自閉,沉默與孤獨,并開始喜歡上了文字,且從中感到安慰。或許,那時候我就開始隱秘地領悟到了詩。”[⑩] 他在初一時創作了他的第一首散文詩《蒲公英》,“蒲公英這樣流浪的意象很適合我的心理,就這樣寫出了《蒲公英》。”[11] 李少君說:“鄉下是一個寬闊的天地,自然培養人的想象力和美感,尤其是對自由的追求。”[12] 可以說,是大自然成為李少君最初的詩性基因,并且成為他的文學啟蒙之源。
而后來他之所以從商海抽身而出,重新回到中止多年的詩歌,仍然是由于大自然的啟迪。2006年底,他在黃山開會,借著煙雨迷蒙的新安江觸發的靈感,創作出《河流與村莊》。這首詩還被選入多種詩歌選本。從此,他一發而不可收。他說:“黃山是一座偉大的詩山,歷史上有過無數關于黃山的詩歌,新安江是一條偉大的詩河,李白等曾經在這里流連忘返,所以,我的詩歌乃是神賜,冥冥中,乃是偉大的自然和詩歌傳統給我了靈感,是自然的回音,傳統的余響,是我內心的感悟與致敬使我重新寫作。”[13]
李少君提倡“草根寫作”的意義和價值,還需要置于特定背景來分析。進入21世紀以來,中國的詩歌語境發生了巨大變化。其一,網絡、自媒體以及民刊所代表的民間力量浮出水面,并且日益形成歷史性的力量,強烈地沖擊著傳統的出版發行體制,極大地解放了詩歌生產力;第二,資訊時代信息的交融,使得中心與外省、城市與鄉村、主流與邊緣、主旋律與多元化等諸種元素,以民主的方式共時性存在著,農民詩人、打工詩人等底層文化階層進入主流文化視野,并構成挑戰與互補;第三,“盤峰論爭”之后,知識分子寫作與民間寫作兩大陣營的壁壘森嚴,在彰顯詩歌內在格局與真相的同時,也造成了詩歌力量的嚴重內耗。因此,摒棄意識形態的域限,讓詩回到詩,讓詩學回歸詩學,就成為現代漢詩發展的必然趨勢。在李少君眼里,草根性并不是一種階級劃分和階層界定;不是強調詩人身份,而是強調詩學審美。因此,他提出草根寫作,強調本土性,強調創作主體的自由、自發、自然,回到詩寫的原點和原初,具有超越不同詩寫路向的清晰的整合意圖。
因此,在李少君看來,重提草根性,重提自然寫作,便具有了民族本土文化尋根的意義。新詩文體在社會急劇變動的“五四新文化運動”時期誕生;20世紀80年代以來的30多年,也是東西方文化劇烈交鋒期,產生的種種社會亂象也都在新詩中得到反映。因此,中國新詩越來越西方化的現代語境下,重提“道法自然”的中國詩教傳統,重提新詩本土性,就具有迫切的現實意義。近年,一大批具有本土性的詩人非常活躍,如陳先發、柏樺、雷平陽、潘維、李少君、向以鮮、飛廉等在本土性方向的詩學追求異常鮮明。本土性、草根性的理論促動,無疑會激活詩歌的生命力。正如李少君所言:“如果說朦朧詩是當代詩歌的第一聲春雷,那么,現在大地才真正覺醒,萬物萌發,競相爭艷,生機勃勃。”[14]
李少君的理論自覺,有效地轉化為他的創作實踐。他的代表作之一《傍晚》即是踐行草根詩學的經典之作:
傍晚,吃飯了
我出去喊仍在林子里散步的老父親
夜色正一點一點地滲透
黑暗如墨汁在宣紙上蔓延
我每喊一聲,夜色就被推開推遠一點點
喊聲一停,夜色又聚集圍攏了過來
我喊父親的聲音
在林子里久久回響
又在風中如波紋般蕩漾開來
父親的答應聲
使夜色似乎明亮了一下
這首詩本土性極其鮮明。它所傳達的父子之間的生命共振和情感共鳴,處理得含蓄蘊藉,完全是中國式家庭倫理的詩意表達。“我每喊一聲,夜色就被推開推遠一點點/喊聲一停,夜色又聚集圍攏了過來”與“父親的答應聲/使夜色似乎明亮了一下”,二者內在隱秘的生命關聯,具有穿越時空的強大生命力,永恒地擊中我們最柔軟的靈魂深處。人和自然的關系、人和人的關系,也是西方現代文學的母題,但是,西方詩歌中卻充滿了變形意象,傳遞出西方社會特定時代的絕望心理和人性畸變。在T·S·艾略特詩中,正在蔓延開來的黃昏是麻醉在手術臺上的病人;英國詩人迪蘭·托馬斯筆下的文明世界是一個荒原,天空是一塊裹尸布……每個人之間都是隔絕和禁閉關系,“他人就是地獄”成為現代人的基本信條。李少君為我們提供了極富民族特色的人與自然、人與人之間的雙重和諧。這是屬于中國人的草根詩學。
在李少君的《草根集》和《自然集》《詩歌讀本:三十二首詩》里,這種具有經典意義的作品還有很多。可以說,李少君關于“草根詩學”的理論思考和對“自然詩人”的踐行,在很大程度上講,接續了惠特曼在《草葉集》中開創的草根性,使之在中國本土語境下生根、開花、結果。
二、“自然詩人”創作的美學范式
李少君以《抒懷》、《四合院》、《南山吟》、《山中》等一系列以“大自然”為題材的充滿傳統詩學神韻的佳作,持續在詩壇吹拂一股清新之風,確立了當代漢詩的古雅美學范式。
歌詠大自然之魅力依然是李少君詩作貫穿始終的美學母題。“汽車遠去/喧囂聲隨之消逝/只留下這寧靜偏遠的一角/沒有噠噠馬達聲的山野/偶爾會有鳥鳴、泉響以及一兩聲電話鈴”(《山間》)。這種樸素靜謐的所在不僅為南方所擁有,同樣也出現在秋天的北方平原。剛剛收割之后的一望無際的田野里,一棟安靜的房子掩映在金黃的大樹下,陽光搖曳,迸濺出“雞叫聲、牛哞聲和狗吠”,“還有磕磕碰碰的鐵鍬聲或鋸木聲”。白天的交響鳴奏與夜晚的安寧靜謐,形成了鮮明對比:“夜,再深一點/房子會發出響亮而濃暢的鼾聲/整個平原亦隨之輕微顫動著起伏”(《平原的秋天》)。整首詩洋溢著動人的律動感,一如生命的呼吸,自然而酣暢。
李少君被稱為“自然詩人”,是有道理的。李少君說:“對于我來說,自然是廟堂,大地是道場,山水是導師,而詩歌就是宗教。”[15] 他有一首小詩《朝圣》,只有兩句:“一條小路通向海邊寺廟/一群鳥兒最后皈依于白云深處”,就像一則偈語,妙在兩句詩之間內在的隱喻關系:人尋找道路寺廟,與群鳥皈依白云,殊途同歸。“迎面而來的鳥鳴對我如年偈語”(《偈語》),“青山兀自不動。只管打坐入定”(《春天里的閑意思》),“至少,隱者保留了山頂和心頭的幾點雪”(《云國》),都極富禪意。在李少君的眼里,自然是比“道”更高的范疇。他說:“在我看來,自然,可以說是中國古典詩歌里的最高價值。老子說‘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在這里,‘自然’是比‘道’更高的價值。”[16] 他在詩歌《青海的一朵云》中寫道:“高人雅士總是遠離紅塵隱身山水/大德大道多半源自田野草間/我也愿意永遠棲居于一朵白云之下”。在李少君的詩中,很少看到沖突,大概與他的自然詩學有關。他清楚地看到,西方詩歌講究“個體”意義上的“對抗”與“沖突”,靈魂的分裂成為重要表現內容。而中國詩學講究和諧與超越。是“道法自然的”傳統詩教觀念,為中國人提供了超越性的精神解釋和價值系統。這是中國傳統文人的世界觀。在李少君的心里,自然詩學具有了某種宗教意義,以至于認為“詩歌是具有宗教意義的結晶體,是一點一點修煉、淬取的精髓。”[17] 《詠三清山》把三清山比作“云的領地”“鳥的故鄉”“俠與道的基地”“善與美的主場”,來此地的各色人等如“尋藥客”“狩獵者”“浣衣女”“采蓮妹”等,“都是善與美的守護者”。李少君的詩歌,大都體現出“三清山”的境界。
他的《自白》一詩幾乎可以看做李少君的生活宣言:
我自愿成為一位殖民地的居民
定居在青草的殖民地
山與水的殖民地
花與芬芳的殖民地
甚至,在月光的殖民地
在笛聲和風的殖民地……
但是,我會日復一日自我修煉
最終做一個內心的國王
一個靈魂的自治者
李少君接受了傳統的文化人格,但是與“內圣外王”的擴張型士大夫人格完全不一樣。他繼承的是另外一種傳統文化的流脈,他甘愿成為大自然的殖民,是內斂的“靈魂自治者”,是面向自然而求助自我靈魂完善的人格。同為傳統文化,而價值取向迥異。李少君以自然人格之王,置換了政統人格之王的價值觀。這個自然之王頻繁地出現在李少君的詩中:
只要擁有這滿庭桃花
我就是一個物質世界的富有者
(《春光》)
當我君臨這個海灣
我感到:我是王
……
我感到:整個大海將成為我的廣闊舞臺
壯麗恢宏的人生大戲即將上演——
為我徐徐拉開絢麗如日出的一幕
(《夜晚,一個人的海灣》)
我怎么看也覺得機場的出入口
修得像山寨寨門,還是只要一拉閘口
這小小的山間小城
就可以成為一個獨立王國
(《烏蒙山間》)
假如,萬嘉果莊園是我的領地
我會養三四條狗,七八個孩子
讓他們每天在莊園的野地里游戲玩耍
(《假如,假如……》)
多年來,這風花雪月的國度
在云的統治下,于亂世之中得以保全
(《云國》)
在李少君的詩中,只要有“自然”在,就一定有“人”在,“人”與“自然”和諧一體地存在。李少君最負盛名的一首詩《抒懷》,在“你”“我”的對話中,彰顯出一種“為山立傳,為水寫史”的文化情懷與詩學野心。他寫道:
樹下,我們談起各自的理想
你說你要為山立傳,為水寫史
我呢,只想拍一套云的寫真集
畫一幅窗口的風景畫
(間以一兩聲鳥鳴)
以及一幀家中小女的素描
當然,她一定要站在院子里的木瓜樹下
“當然”一詞,強調了二者的“必然關系”。正如《初春》一詩的結尾:“一位少年,安靜地坐在院子中央讀書/燕子門圍繞著他飛來飛去”,《疏淡》的結尾也是“人”的在場:“背景永遠是霧蒙蒙的/或許也有炊煙,但更重要的/是要有站在田埂上眺望的農人”。我們從這些詩作中發現了一種“人在自然中”的意象構圖范式。與現代主義思潮強調人的主體性不同,李少君的筆下,自然占據了畫面核心,人只是大自然的組成部分,自然是主體,是本體,自然才是中心。他復活了傳統文化中的“天人合一”境界,而這一境界不是所謂的“人的自我實現”,而是人在自然中的“消失”。正是這種“消失”,人們才能在更大的宇宙之境中找到真正的自我。他的“自然詩境”其實是經過了螺旋上升的否定之否定三個階段:傳統自然文化——現代自然文化——現代與傳統交融的自然文化。他的自然詩學是古典的,但又是現代的,因此,可以稱之為“新古典主義”的“自然詩人”。
李少君的自然抒寫,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美學論述的“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他常懷欽羨之心,主動融入大自然,并且成為大自然的一部分,如《自道》:“白云無根,流水無盡,情懷無邊/我會像一只海鷗一樣踏波逐浪,一飛而過/……海上啊,到處是我的身影和形象//最終,我只想擁有一份海天遼闊之心”。只有在大自然的懷抱里,詩人才找到自己的靈魂歸宿:“我那亂撞亂跳的心啊/在呀諾達,安靜如一只小鳥/包裹在原始森林的一團濃蔭里”(《呀諾達之春》)。“包裹”一詞,極其精準地傳遞出“人在自然”中的歸宿感。在李少君的筆下,大自然的萬事萬物都具有了“屬人”的本質,大自然被充分“人化”了。“水之府第,最高首長是一只白鷺/每臨黃昏,要最后一次巡視自己的領地”(《水府白鷺》)。這不是單純的擬人化處理,而是具有了人類學和哲學意義。一方面,這只“白鷺”將大自然視為自己的“領地”,另一方面,詩人愿做大自然“殖民地”的居民,二者之間是一種靈魂內在的呼應關系。
大自然成為人類存在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成為人類的鄰居。具有代表性的一首詩是《鄰海》:
海是客廳,一大片的碧藍絢麗風景
就在窗外,抬頭就能隨時看到
海更像鄰居,每天打過招呼后
我才低下頭,讀書,做家務,處理公事
抑或,靜靜地站著凝望一會
有一段我們更加親密,每天
總感覺很長時間沒看海,就像忘了親吻
所以,無論回家多晚,都會惦記著
推開窗戶看看海,就像每天再忙
也要吻過后才互道晚安入睡
多少年了,海還在那里
而你卻已幾乎不見。我還是會經常敞開門窗
指著海對賓客說:你們曾用山水之美招待過我
我呢,就用這湛藍之美招待你們吧
最理想的狀態是,“人的自然化”和“自然的人化”形成美好的相遇,最終“人”與“自然”完全融為一體,互為自己的有機部分。例如《七仙嶺下》一詩。大人小孩都以七仙嶺為家,人與自然和諧相處。“她家的園子 就有一泓溫泉/每一個月夜她都要在里面泡上一個時辰/她細嫩的皮膚、苗條的身挑,以及一副好性情/就這樣慢慢養成”。大自然養育了人的魅力和性情,人都具有天然的清純與干凈。李少君曾經與文成青山相遇。他明明知道自己身在異鄉,但是,他身心放松,融入青山,甚至幻化為“青山的倒影”,不分你我:
即使喝了酒,我仍清醒地知道這里不是故鄉
但又為何如此熟悉,莫非我前世到過此地、
此刻,青山正凝視的那個人
——那個端坐在酒樓上的人是我嗎?
還是那個低頭前行的僧人是我?
抑或,是那個垂手站立橋上看風景的第三者是我?!
(《文成的青山》)
他在亦真亦幻、“相看兩不厭”的山水審視之中,確認自我的精神存在。
在具體的詩藝處理方面,李少君也可圈可點。他特別善于對大自然做極富層次感的處理。他首先把鏡頭聚焦到一個具體的點,然后,鏡頭拉開,直到出現大全景。最有代表性的是《神降臨的小站》和《春》。《神降臨的小站》從特寫到近景到中景再到遠景,鏡頭一直拉開,最終呈現出氣韻蒼茫的闊大境界:“再背后,是神居住的廣大的北方”,那種自然的神秘感和宗教感,油然而生。再看《春》:
白鷺站在牛背上
牛站在水田里
水田橫臥在四面草坡中
草坡的背后
是簇擁的雜草,低低的藍天
和遠處此起彼伏的一大群青山
這些,就整個地構成了一個春天
從“白鷺”到“牛背”到“水田”到“草坡”到“雜草”和“藍天”到青山,鏡頭緩緩平移,從白鷺的特寫,鏡頭拉開,到近景,到中景,到遠景,到全景;從空中移到地面再到藍天和青山,畫面構圖完整、清晰,富有層次感,在靜態美之中顯示出和諧美。
三、古雅詩學的現代拓展
傳統詩學的古雅范式,并不是封閉僵化的。我們需要警惕的是將古典詩學視為靜態標本而對當下生存視為不見。在高度物質化、現代化的時代語境下,人們有理由懷疑,李少君的這種審美范式,究竟是一種進步性的反撥,還是一種古老意緒的回光返照?李少君的不斷探索,打消了這種疑慮。
假如李少君一直沉浸于大自然“殖民地”的居民身份,就有可能使詩歌的內涵變得單一乃至于單薄。而李少君之所以是李少君,就在于他在一以貫之的自然母題之中,融入了具有現代生命意義的沉思品質。他知道,作為一個現代詩人,不能僅僅認同“大自然殖民地的居民”身份,還需要轉型為理性的“田野調查的方志工作者”。李少君傳遞出在現代化進程中現代人生存的復雜性,在傳統與現代既博弈又和諧相處的辯證關系中,對古雅詩學范式進行了新的拓展。
他以生命沉思視角,形成了對自然母題內涵的拓展。如《渡》一詩,詩中的渡客在黃昏的渡口:
眼神迷惘,看著眼前的野花和流水
他似乎在等候,又仿佛是迷路到了這里
在遲疑的剎那,暮色籠罩下來
遠處,青林含煙,青峰吐云
暮色中的他油然而生聽天由命之感
確實,他無意中來到此地,不知道怎樣渡船,渡誰的船/甚至不知道如何渡過黃昏,猶豫之中黑夜即將降臨”,充滿了濃厚的命運感,令人產生形而上的思考。一塊石頭從山巖上滾下,引起了一連串的混亂,最終“石頭落入一堆石頭之中/——才安頓下來/石頭嵌入其他石頭當中/最終被泥土和雜草掩埋”(《一塊石頭》),這塊石頭的命運正是由于富有哲理思辨色彩,才得以在詩人的童年記憶中留下深深轍跡。《孤獨鄉團之黑螞蟻》也完全祛除了大自然的唯美性質,注入了人類生命的孤獨感。詩人從身邊物象出發,自然而然地富有層次地延展到無際的宇宙星球,“榕樹”、“檳榔樹”、“島嶼”、“月亮”、“星球”等意象一個一個全都是孤獨鄉團,最后詩思驟然拉回到眼前“老榕樹樹干上爬行的小螞蟻”,詩思騰挪跌宕之后,直逼“又黑又亮觸目驚心”的孤獨體驗。在《半山》中,“我逐級登高,滿耳開始灌滿蟬聲/滿目全是老人,三五幾個各自分散……/他們對路人毫不關注,仿佛只是在云游/目光木然,他們沉浸在太極和自己的心事里”,體現的是內蘊充盈的虛靜文化,而虛靜中夾雜著幽美,隔絕中夾雜著皈依,寫實中滲透著寫意,呈現中蘊含著象征。
由于沉思性的介入,李少君的自然抒寫常常具有鮮明的間離色彩。這種間離色彩,構成了他的獨特的抒情身份。在《鸚哥嶺》里,詩人自命名“一名熱衷田野調查的地方志工作者”。這意味著,詩人不再是融于大自然并且成為大自然的一部分,而是間離出來的一個“他者”,一個在審美距離中進行思考的抒情角色。《大霧》一詩中雖有田園風光:“屋后是叢林修竹,屋前有一條小溪”,但是,作為美的象征的“女人”出走之后,給詩人留下了“感到她還在山中,又好像已經不在”的迷惑。一場大霧完全隔斷了大自然之美的存在,從而具有了若即若離的虛幻色彩。這種沉思者的形象往往導致抒情主人公呈現“獨自一人”的形態。《江邊》和《山間》都是以獨體抒情來加強間離色彩。《江邊》結尾的反問“那么,誰又是這一場景的旁觀者?”與《半山》結尾的疑問“為什么老年才尋覓這么幽美的棲身之處呢?”如出一轍。他在這種自然現實之上,進行了形而上的思考,這種反思使抒情角色與抒情對象拉開了距離。最終,大自然的精靈猶如現時代的一個神話,成為“可遠觀而不可近觸”的超現實象征性存在:
伊端坐于中央,星星垂于四野
草蝦花蟹和鰻鱺獻舞于宮殿
鯨魚是先行小分隊,海鷗踏浪而來
大幕拉開,滿天都是星光璀璨
(《海之傳說》)
本來,“月光下的海面如琉璃般光滑/我內心的波浪還沒有涌動……”但是,“她浪花一樣粲然而笑/海浪嘩然,爭相傳遞/抵達我耳邊時已只有一小聲呢喃”,就是這么一小聲呢喃,竟然“讓我從此失魂落魄/成了海天之間的那個為情而流浪者”。這個“流浪者”的形象,豈不象征著現時代人在高度物質化、技術化的時代,靈魂的無根感?自然的精靈猶如形而上的超驗力量,誘惑著我們超拔于俗世的泥淖。《新隱士》其實也是一個隱喻性表達。“孤芳自賞的人不沾煙酒,愛惜羽毛/他會遠離微博和喧囂的場合/低頭飲茶,獨自幽處/在月光下彈琴抑或在風中吟詩//這樣的人自己就是一個獨立體/他不愿控制他人,也不愿被操縱/就如在生活中,他不喜評判別人/但會自我呈現,如一支青蓮冉冉盛開”。這種隱士并未人情寡淡,而是擁有常人不能理解的幸福:“我最幸福的時刻就是動情/包括美人、山水和螢火蟲的微弱光亮”。
正是這種內心世界的光亮,讓他能夠穿越世俗的黑暗,而保持自我的完整和溫度。
詩人的間離色彩具有二重性。李少君站在大自然與城市生存的中間來思考問題:他一方面站在如上所述的角度對大自然做間離性思考,另一方面,他又站在自然立場審視現代性城市化生存。他往往將“城市”生存與“自然”生存并置,引人深思。如《山中一夜》《夜晚,一個復雜的機械現象》《黃昏,一個胖子在海邊》。“我眼睛盯著電視,耳里卻只聞秋深草蟲鳴”(《山中一夜》),將現代科技的象征物象“電視”與傳統自然文明象征意象“秋深草蟲鳴” 對舉,借助萬草萬木、萬泉萬水散發出的自然氣息來滌蕩“在都市里蓄積的污濁之氣”。《夜晚,一個復雜的機械現象》抒發一對愛侶到一個異域場景下重溫蜜月的美好情愫,詩人以一系列自然意象隱喻愛侶生命激情的迸發。有意味的是,詩人將他們的生命感官自然綻放的行為置于現代意味十分濃厚的都市“酒店”,夜深人靜之時夢中醒來,聽見窗外空調驟停復響的運轉聲。此時,一對愛侶生命欲望的絢麗綻放與空調運轉的機械性重復,讓詩人產生了殘酷的比照性深思。李少君還經常將自然之美置于現代物質生存語境來審視。如《流水》中的那位“守身如玉”的“現代女性”其實構成了現代物欲環境下傳統之美消隕的命運隱喻。她以充滿原初生命的身體,不斷地讓我們保持生活的感覺的生命的“痛感”與“傷心”,她的隕落,猶如一場現代版“牡丹亭”,成為一種文化絕響。《春色》將“春色” 以“紅衫女子”來具現,置于“夜總會包廂”的現代語境,“在恍惚之間”“突然聽到一聲嬌滴滴軟綿綿的/蘇州口音”。虛實結合,現代與古典穿越,有效地拓展了詩意空間。在當下,“胖子”這個概念幾乎成為現代都市人的標本性意象。胖子大多數“神情郁郁寡歡/走路氣喘吁吁”,他“看到大風中滄海落日這么美麗的景色/心都碎了,碎成一瓣一瓣/浮在波浪上一起一伏”(《黃昏,一個胖子在海邊》)。詩歌的最后一句“從背后看,他巨大的身軀/就象一顆孤獨的星球一樣顫抖不已”,充滿巨大張力的比喻,觸目驚心,發人深省!
盡管李少君倡言不會以古典文化取代現代化進程,但是,城市文明和鄉村文明之間的巨大分野,在李少君的詩作中卻極其豁顯。一個代表性的作品是《某蘇南小鎮》。詩歌第一節為我們呈現了古老安靜的鄉村王國的魅力:
在大都市與大都市之間
一個由鳥鳴和溪流統一的王國
油菜花是這里主要的居民
蚱蜢和蝴蝶是這里永久的國王和王后
深沉的安靜是這里古老的基調
這簡直就是一幅現代世界之外的桃源盛景,“這里的汽車像馬車一樣稀少”,這個獨立王國宛如一個寓言,一個古文明的標本。多年的安靜之后,終于迎來了“過于慘烈的歷史時刻”,“青草被斬首/樹木被割頭”,讓這里的生命感到巨大的“驚愕”,“濃烈嗆人的植物死亡氣味經久不散”。對于自然界來說,這場“暴戮事件”是史上最黑暗的時期。“而人類卻輕描淡寫為修剪行動”。“自然”的生命自足性與“人類”虛偽的暴力,構成了怵目驚心的巨大張力。他在詩中不斷地表達一位“自然詩人”對現時代的擔憂:
我,一個遙遠的海島上的東方人
因對世事的絕望和爭斗的厭倦
轉向山水、月亮和故鄉的懷抱
但我也有隱隱的擔心,在新的大躍進中
青山會不會被搬遷,月宮在否終有一日拆除
而每一個人的故鄉,似乎都在改造之中(《虛無時代》)
高樓大廈之間尚余一處亭臺樓閣
微縮版的江南庭院,浮于水上
深密的竹林藏著幽暗的風景
(《蛇的怨恨》)。
這種隱憂不是意識形態層面“留住鄉愁”的那種宣傳,而是現代化進程中一種審慎的文化態度,一種生存哲學態度。李少君將自然文化人格與現代都市文化并置的時候,會產生一種張力和戲劇性效果,并引發我們關于人的命運的深思。《上海短期生活》就刻畫出一個自然文化人格在當下遭遇的尷尬處境。“我”在上海短期生活的周末保留節目是:
在尚湖邊喝茶,看白鳥悠悠下
到興福寺聽鐘聲,任松子掉落衣裳里
在虞山下的小旅館里安靜地入睡……
并且把這種生活視為“一個中產階級的時尚品牌”。但是,他周邊的環境卻是:
公路像毛細血管一樣迅速鋪張
縱橫交錯地貫穿在長江三角洲
滬常路上,車廂里此起彼落的
是甲醇多少錢一噸
我要再加一個集裝箱的貨等等
語氣急促、焦躁,間以沮喪、疲憊
于是戲劇性出現了,“我”本來的自然本真的生活狀態,在他人的“焦慮”圍困之中,卻感覺“自己生活的非正常”。這種現代生存環境的逼壓最終導致了人的生存轉向異化狀態:
她的焦灼干擾著我
讓我也無法悠閑下去
成了一個在長江三角洲東奔西竄的推銷員
還有一首極富文化沖突意味的詩作《一個男人在公園林子里馴狗》。它將“公園”“林子”“狗”“馴狗人”這些自然意象置放在城市里面,凸顯出現代都市生活里的異質性存在。一個孤獨的馴狗人,在寂靜的日子里,常常有樹葉子落在他的身上。由于長期在大自然中生活,他仿佛與自然完全融為一體:
從此,他就真的融入了這一切
白天他繼續馴狗 晚上則隱入都市深處
他離群索居 不再被同類關注
他好像成為了自然的一部分
全身披掛樹葉 成為了公園林子的一部分
人們對此見慣不驚 久而久之視而不見
就這樣,他和他的馴狗成為了公園林子里的一部分
自然的一部分,仿佛自然中的一副靜物
本來“天人合一”的境界,在現代都市場景環力卻變得十分突兀,“常態”與“非常態”的概念被顛倒過來,卻又十分具有警醒意義,令讀者去深思人與自然的生態關系。
李少君反復詠嘆大自然的超驗性的無窮魅力,讓我想起了T.S.艾略特的詩歌《空心人》。《空心人》表達的是高度物質化的現代文明瀕臨危機、希望渺茫、精神空虛的時代語境里人的主體性的潰散。“我們是空心人/我們是填塞起來的人/彼此倚靠/頭顱裝滿稻草。唉!/我們被弄干的嗓音,在/我們竊竊私語時/寂靜而毫無意義/像干草中的風”,艾略特勾畫的“空心人”,便是失去靈魂的一代人的象征。李少君的古雅審美范式,一直致力于重新恢復從農業文明時代向工業文明時代轉型過程中所丟失的抒情個體的質樸的人性力量。他的《自白》宣示了他的理想:“我會日復一日自我修煉/最終做一個內心的國王/一個靈魂的自治者”。這需要的不僅僅是詩學定力,更涉及到現時代本真人格如何葆守的問題。面對日益嚴峻的消費主義浪潮,隨著自然生態危機和精神生態危機的日益加深,生態文學和生態批評漸趨高漲。長沙理工大學的易彬稱李少君為“自然詩人”,北京大學的吳曉東教授稱之為“詩學的生態主義”,南開大學的羅振亞稱之為“生態寫作”,都是切中肯綮的。李少君在主持的《天涯》雜志曾經組織過一次關于生態主義思潮的大型學術討論,發布的《南山紀要:我們為什么討論環境——生態》被翻譯成多種文字,產生了積極影響。李少君也親自寫作過生態主義思潮方面的論文,但是,對于李少君來說,詩學的生態更多地源于他個體生命體驗和詩學實踐。他的經歷、教育、環境、個性,決定了他的詩學觀念和詩學實踐。他從小在美麗的湘鄉長大,大學就讀的武漢大學所在地在東湖和珞珈山之間,被稱為最美大學,畢業后在海南工作,亦具有最佳生態環境。所以,對他來說,大自然才是安身立命之所,都市乃過客之地。他說:“在我看來,自然不是一個背景,人是自然中的一個部分,是人類棲身之地,是靈魂安置之地。但自然若不為人所照亮,就會處于一個昏昧狀態,所以需要我們不斷去發現自然,探索自然,照亮自然。對于我來說,自然早已與我的生活融為一體,我只要呆在一片林子里或站在水邊,就會覺得很輕松,還會像李白說的‘相看兩不厭’。”[18] 李少君曾經不止一次地表達了他的詩觀:“詩歌是一種心學。詩歌感于心動于情,從心出發,用心寫作,其過程可以說是修心,最終又能達到安心,稱之‘心學’名副其實。在一個全球化時代,心學是指個人化的對世界的體驗、感受、深入理解和領悟的過程,是以心為起點,重新認識世界,重建價值 。”[19] 李少君的草根詩學理論及其創作實踐,是一個十分具有現實意義的典型個案,將有助于我們思考自然生態的可持續性發展以及傳統文化、傳統詩學在當下面臨的命運。
注釋:
[①] 李少君《草根集》,上海人民出版社2010年。
[②] 李少君《自然集》,長江文藝出版社2014年。
[③] 李少君《詩歌讀本:三十二首詩》,長江文藝出版社2009年。
[④] 李少君編選《21世紀詩歌精選(第一輯)草根詩歌特輯》,長江文藝出版社2006年。
[⑤] 《草根性與21世紀詩歌》,李少君《在自然的廟堂里》,西北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54-55頁。
[⑥] 《我與自然相得益彰》,李少君《自然集》,長江文藝出版社2014年,第119頁。
[⑦] 《草根時代》,李少君《文化的附加值》,安徽教育出版社2013年42-43頁。
[⑧] 《草根性與21世紀詩歌》,李少君《在自然的廟堂里》,西北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59頁。
[⑨] 《在自然的廟堂里修身養性》,李少君《在自然的廟堂里》,西北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頁。
[⑩] 《在自然的廟堂里修身養性》,李少君《在自然的廟堂里》,西北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1頁。
[11] 《我與自然相得益彰》,李少君《自然集》,長江文藝出版社2014年,第111頁。
[12] 《我與自然相得益彰》,李少君《自然集》,長江文藝出版社2014年,第111頁。
[13] 《在自然的廟堂里修身養性》,李少君《在自然的廟堂里》,西北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頁。
[14] 《草根性與21世紀詩歌》,李少君《在自然的廟堂里》,西北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55頁。
[15] 《在自然的廟堂里修身養性》,李少君《在自然的廟堂里》,西北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5頁。
[16] 《在自然的廟堂里修身養性》,李少君《在自然的廟堂里》,西北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2頁。
[17] 《在自然的廟堂里修身養性》,李少君《在自然的廟堂里》,西北大學出版社2010年,第5頁。
[18] 《我與自然相得益彰》,李少君《自然集》,長江文藝出版社2014年,第117頁。
[19] 《遂寧日報·華語詩刊》2015年5月29日第一版。
原載《當代文壇》2017年第5期
作者:趙思運
來源:趙思運新浪博客
http://blog.sina.com.cn/s/blog_54b574bb0102x66m.html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