趙卡:作為一種“小語種”修辭的地方主義寫作
(一個倉促的反對意見:本卷《明天》呈現的超級概念、邏輯和抽樣文本)
趙卡/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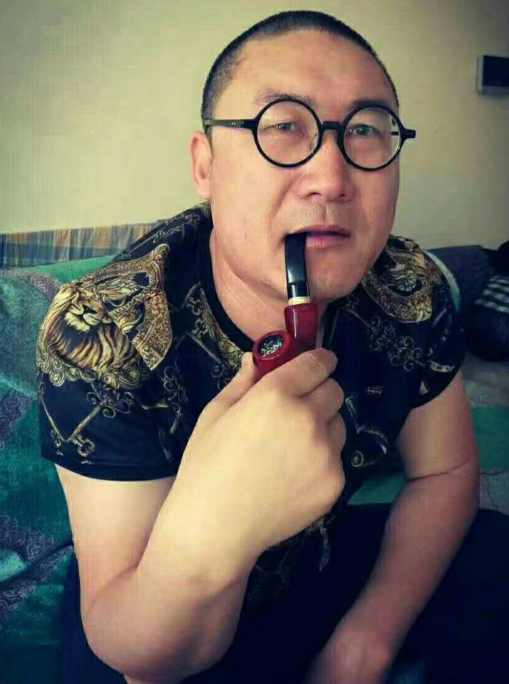
作家、詩人、評論家趙卡(資料圖)
對布萊希特式戲劇的疑問,也是地方主義寫作者要面臨的問題:中心在哪里呢?
就像一個傳統鐵匠在爐前對待一塊鐵一樣,我們稱贊的是他出神入化的淬火手藝,而不是因為他的來歷不明的籍貫。同理,一個詩人的首要職責是寫好詩,至于給他的詩貼上什么標簽他是無法阻止的,眾所周知標簽的出現不是為了詩,它幾乎就是一種工具,唯一的作用是批評家利于風格場景分類。風格看相術是批評家的核心技術,比如本雅明對病態的普魯斯特的精密觀察。有個絞刑幽默段子,拿過來可以說明詩人和批評家的現實關系:死刑犯不肯接受行刑人員遞上的最后一支煙,因為他正想戒煙。彼此心領神會,命名邏輯和文本出自必然。我只需要補充的是,詩不是寫給批評家的,詩人孤立于所有人,除了他的回聲,而回聲作為一種“小語種”腔調對應著詩的意義。
對于地方主義,恕我有點孤陋寡聞。出于從事的職業和閱讀興趣,第一次見到這個概念是在彼得·F·德魯克的一部重要著作《后資本主義社會》中,德魯克在這部書的“政體”部分第七章“回歸地方主義”中談到了“地方主義”,他說:“地方主義已經變成了全球性浪潮。”當然,德魯克作為一名教父級的管理思想家,他是從政治、經濟、組織和文化角度闡述地方主義的,不像吉爾茲在他的《地方性知識》中直接說,“法律與民族志,如同駕船、園藝、政治及作詩一般,都是跟所在地方性知識相關聯的工作。”
今天,再拿威廉·福克納的“約克納帕塔法世系”說地方主義已經顯得很沒意思了,作為反例,吳承恩可沒去過印度。現在,我就要談談我理解的地方主義和地方主義詩歌了。“地方主義”作為一種現代漢語詩歌的寫作概念是由譚克修提出來并從理論上加以確立的,他基于這樣一種擔憂,也是奧·帕斯指出的藝術被變成了消費品的境況。不過他撰述“地方主義”這個概念的時候,面對的主要是詩人特別是被定義成地方主義的詩人而不是其他讀者,他擔心人們不能很好地理解“地方主義”這個偏地理屬性的概念,由此,這種——安徽余怒、陜西伊沙、河北韓文戈、甘肅阿信……的地域+詩人的語法結構署名方式被觀念化了。譚克修在他的宣言性質的《地方主義詩群的崛起:一場靜悄悄的革命》一文中“突發奇想”“提出‘地方主義’詩派”,并引據加勒比島國圣·盧西亞詩人德里克·沃爾科特、約克納帕塔法的福克納以及加西亞·馬爾克斯的馬孔多、沈從文的邊城、賈平凹的商州、莫言的高密……,這個省略號應該還包括本卷《明天》 里的詩人。
“地方主義”的修辭仿佛是另一種使命的象征——流派份額的雄心,“今天派”以后的集體有意識(而非無意識)符號,而符號源于寫作的出發地。我想說,自1916年中國第一首白話詩誕生以來,“地方主義”于漢語詩學的確像一個學術的細節如私事般隱藏了。譚克修的闡釋讓我不太滿意的地方在于,他重“地方主義”的公共意義而弱“地方主義”的內部價值,而我始終認為地方主義詩歌不僅僅是(但包含了)一個地域(地理)寫作概念,而是一種非常個人化的超級概念寫作,每一個詩人的文本都可以單獨拿出來觀察,他們獨具的個人地理和歷史意識,他們嗓子里的方言口音,他們動用過的龐雜的技術,文字的自我保護功能,風格上的辨識度等等,我將之視為從一種日常走向另一種日常的“小語種”修辭。
比如,我先舉個余怒的例子。余怒的詩在閱讀時讓人處于一種難以捉摸的緊張狀態,這是他對詞語的專制結果,個人建立起來的一套闡述日常生活的方式,和權力濫用的絕對主義一樣,對讀者來說在體驗上不太令人愉快。依照地方主義的片面定義,情況正好相反,余怒不是一個地方主義詩人,就像顯而易見莎士比亞不像英國人一樣,惟此,他們才具有更持久的詩學價值。我所理解并定義的地方主義在內部,否則你無法將本卷詩人都歸入此類,說句極端的話,和莎士比亞一樣,余怒已經是一個世界性的詩人了,不能再從外部的研究和鑒賞確定他的地方主義性質。
之所以要說地方主義于百年中國新詩是一個超級概念,在于地方主義有它的理論上的普適性一面,就像紅綠燈是一組超級符號一樣,地方主義較之其它詩學概念更易獲得共鳴。對地方主義詩歌的樣本遴選,當視為本卷《明天》的一個伴隨它的實體的符號性動作,不論我們關注的是口頭的符號還是文本的符號,都以在場為基礎。
“現在醒著,是一座孤島。”(《雪夜獨步》)阿信的強烈的地方主義特征在于他設置并發展了一種適合他的孤島意識的文本空間,在自然主義抒情形式和神秘主義美學上他有著宏偉的風格,即使如《雪夜》這樣的寥寥五行的短詩傳達出來的寂靜都會讓人突然想到歌德的《漫游者的夜歌》,這是天才的神話,人生經驗的一次孤立的濃縮;但他傾向于持續做一個艱苦的匠人,“我更像一個匠人。使用很多工具:/鋸子、錘子、釘子、繩索、石膏……/我會花很長時間用鵝卵石打磨一塊粗布。”(《一個酥油花藝人與來自熱貢的唐卡畫大師的街邊對話》)所以你會看到阿信對詩的卓越地雕琢,我認為,這太奢侈了,不利于他的抒情性,而且妨礙了他的其他一些優勢。
草樹是那種將小調寫成交響樂的力量型詩人,他在詩中常常發出令人驟然暈眩的聲音,“像沉默,或怒吼”(《長笛》)。草樹給人的印象——用德語寫作的那個捷克人卡夫卡,或者用英語寫作的那個前蘇聯人布羅斯基,他的主格調是俄羅斯白銀時代式的囁嚅或咆哮,他在一種不為人所知的極限處開始顛簸,“一束光從黑暗的背面射來——”(《白光》)這是他的獨特音調。草樹在本卷《明天》里的詩不能代表他的地方主義性,《長壽碑》那種具有民俗和知識考古學意義的地方主義內容和表達的同時給出符號并用符號來指示的文本才夠震撼,不過,這很難說是一個偉大詩人的做法。草樹的詩作為一個局部的整體有一種抵制意識,他是后爆發力的那種詩性力量,粗俗的市儈氣式機智反襯了他的富于創造性的口吃。
從表達的形式到內容的形式,非亞一直在誠實而固執地描述個人在地方的生活。他幾乎是南寧人民意識的喉舌又是南寧的城市生活相面師,就時間而論,沒有一個詩人像非亞那樣影響了南寧或被南寧影響,我想我這說法應該不會有損他的聲譽。南寧這種城市,和西寧、銀川、呼和浩特差不多,在政治經濟學話語里是個三級城市,對詩人來說則是個嚴肅的小詞。“我,推開樓上的一扇窗戶/在又臟又亂的城市,獨自打量那個/又小又瘦的/靈魂”,在《霧》中,非亞像個奇怪的異國人,孤獨感被壓進了每一行機警地詩句中,這種孤獨感一直蔓延到自問的《我想干嘛》和《51歲該干嘛?》,仿佛示弱但讓語言自身——像《貓》里的那只貓——“又發出一聲怪叫”。非亞的哥特式——他自述“從與詩歌的關系上,我承認我時刻和它處于一種緊張的對峙之中”——幻覺風格將自我性視作一種缺席的在場之物,于弱勢中獲得了存在感。
橫幾乎就是一個奇異(歧義)的存在——于當代詩歌而言,他的無比強勢的迂回之術已達到了爐火純青的地步。作為一個深度喬裝的語言流氓,橫創造了一種專屬于自用的方法:在日常事物的背后分行。在別人那里,“分行”是詩的一種基本形式,而在橫的世界里則是一種公開的秘密,他說,“于我而言,一個寫作者的個人秘密是沒有必要對他的閱讀者提及的。”橫的詩是一種疏離的詩學,他所有的詩幾乎看上去都很單薄,但和策蘭的用詞觀念一樣,意象詭異飽滿卻又厲行節約,如同葉芝的晚期作品令我們偏愛;《悲傷》中的銀幣弧線,《跟蹤是第一課時。自我的感受力》中的饑餓對手,《關于痕跡》中的時間節點,《這個地方本來就很安靜》中分幾次飛走的鳥,《有人會記得星期五》中沉默的抬頭又低頭,《在雨中的汨羅江喝酒》飄逸,《黑拉望鏡子——寫給愛人小智》死亡辯證,在《對一只狐貍的觀察》中他寫出了一種張望的憂傷,《世界末日或祝你生日快樂》里散發出遺言的氣息,《那條橫在友誼河那里的堤壩及一個朋友》更像緬懷;如果不是一個深度抑郁癥者,沉默的像個家鄉的陌生人,絕不會寫出橫那樣的詩:在他自己的語言鏡像中雕琢出了一個旁觀自己的病人。我認為或沒想到橫的詩太感傷了,在使用口語的詩人中,他是死亡意識處理大師(尤其像《痕跡學》這種杰作),以至于達到了幽默的地步——本雅明在1916年寫到的那種幽默的必要性,語言不能達到的效果,“除非采用:幽默……留存下來的就是真實之物:灰燼。”
彼得·F·德魯克在《后資本主義社會》中的第八章“尋根的需要”中指出:“地方主義潮流的興起,還有一個重要原因,不是政治或經濟的需要,而是人存在的需要。在一個超國家化的世界里,人還是需要有個根,還是需要鄉土。”這個論斷和譚克修的“地方性詩學的第一個維度是,從‘這里’出發”是相契合的,“這里”即源頭。對于一般的中國詩人,尤其是對于從故鄉出發的詩人,寫作的源頭突然變成了一種對模擬的述行,這種現象似乎在告訴我們“故鄉”的定義需重新闡釋——詩連接了一種虛構敘事——地方主義在哪里發生的。
即使寫作“最終仍然回到了生養的土地”,黃沙子還是不無遺憾的說到了他的離開,“從那時開始,我就不能稱自己是洪湖人了。”他變成了另外幾個地方的人了,在這種作用力下,作為一個詩人,黃沙子經歷了一種雙重的過程:此地出發和重建故鄉。這個過程也是其他詩人經歷過的,其普遍意義在于此地和他鄉就是一個同類項,甚至不存在選擇的問題,正如黃沙子在他的《不可避免的生活》中寫的那樣,“這循環往復的過程/早已被我熟知”。黃沙子對故鄉的重新檢視是回憶錄式的,氣息拉長,語速放慢,意義簡單,仿佛一個人的早期作品,這符合他所說的“詩歌源頭從未改變”原則。
湯養宗的詩幾乎是“地方性寫作”的地標了,在他的自述中,他的詩歌起源于母親哼出的歌謠和鄰婦哭喪時發出的長短調,“我驚奇那些婉轉復沓的調子”。僅有四句的《禱告書》讓我們看到了湯養宗對史蒂文斯的回應,就像史蒂文斯曾在暗中回應惠特曼那樣;《釘子釘在釘孔中是孤獨的》由“天下的釘子”哀己命運,這種習慣性的“情感謬誤”又似情境反諷;《大米考》有吊詭的修辭學,《孤憤書》則區分無所不在的秩序,《大往》如偈咒,《尋虎記》重幻像,《路易十六王后》這種挽歌仿佛糾正歡樂。湯養宗的詩擅長下各種結論,這和艾略特精確他的隱喻主題的情形差不多,他還喜歡預言不可預見的事物;看起來湯養宗還會從出其不意的方式中處理軼聞式題材,《皇帝的心經》有著使人好奇的平行結構式怪誕空間,寫得既像是搞笑又像是呱嘴,在妙趣橫生之間插入了對權力質問的動機,特別是整首詩溢出的歡樂感。
姜濤為地方主義寫作貢獻了一個重要卻屢遭忽視的概念——“郊區”。作為城鄉互為過渡的灰色地帶,我們可以想象“郊區”語言的晦澀性,就像貝克特那種的喜歡用法語寫作的愛爾蘭人。《菩提樹下》的兩個時間觀念“此刻”和“彼時”相互指涉如同雙語同質,他這種漸進而非排他性質的恰到好處的敘述秩序,在我們的日常的閱讀中常常會得到鐘愛,尤其結尾令人震撼的一節:“包括刻了死者名字的石頭/齒輪一樣從青草中冒出/讓人恍然,那些夜間疾馳長街的坦克/其實也曾這樣被活埋過的”。《家庭套裝》瑣碎而幽默,《“小農經濟像根草”》諧趣但嚴肅,《蛇形湖邊》不敬又如釋重負,一個情境反諷高手在場景間離的可能性上給我們上了一堂場景間離的可信性課,看上去像兩種語言雜糅,但他在模擬中分清主次關系還能保持內在的連貫性;《夜行的事物》幾乎超越了言語的可能,詞一刻也不停歇,匯入逃逸般的語言疾行于詩句的每個分岔口,但絕不會相互混淆;很多人想問一個問題,密集的修辭對一首詩究竟會不會有利?毋庸置疑,在姜濤的詩里你看不到過剩只有詞被組合的豐富。
地方性詩學之“個我方言” 的發明確屬洞見。譚克修從對抗的角度觀察并提出了兩個問題:“個我方言”寫作是否可能?“個我方言”寫作是否有效?這屬于寫作資源的問題,令人信服的寫作資源的析取必然是排他性的,如果“個我方言”算一種;但方言入詩的困難性也是顯而易見的,就像歌德的不容反駁的教誨,悲劇絕不能使用方言。一個東北人聽不懂閩南話,溫州人都不懂溫州蒼南的語言,這樣的例子在中國是正常的,和譚克修一樣,很多人擔憂的是故鄉寫作的語言轉換問題,即方言翻譯,比方說,你如何用普通話把四川話翻譯出來,即面對自己的語言,不將別的語言和自己的語言混雜起來。語言一旦以紙頁的方式呈現,我們都有過這樣的經驗,那些曾經熟悉的字詞瞬間變得陌生了不可辨認了,這就是通用語言對“個我方言”的限制,不止譚克修,很多人擔心的事情還是發生了,按譚克修的說法:“最終,丟失的東西遠比捕獲的東西要多。”
針對這個比較棘手卻很現實的問題,李建春提出了“有效地變現”可能性策略。“變現”這個帶有濃重商業氣味的詞在詩學里的定義應該是從一種語言轉向另一種語言的幻覺,是晦澀的獨特感受喚醒普遍的言語能力,它不是一種方式對另一種方式的限制,而是翻譯式的一種重構——將一種陌生的聲音賦予普遍性原則:語言的物理性表現。
《等候蠻杵》里的“蠻杵”是個詞語的“視覺錘”。舉個例子,當你在一百首詩和一首詩里尋找一個詞的時候,你就會發現,只有在一首詩里才會準確辨識出一個詞的形象,比如“蠻杵”。如同埃及術士只需以一滴墨水為鏡向路人展現萬里之外的景象(艾略特小說《亞當·比德》的開場),李建春則以搗衣的“蠻杵”卜瑣屑命運之卦,這首詩的詞語排列適當,句型卻緊張到讓人不安,我們讀到的每個瞬間都像在遭遇:“她囁嚅些啥?沒有意義的詞語”。《啞巴大娘的訴說》里的“個我方言”特征明顯,有著精神聚焦的作用,比如這兩句:“‘啦啦當,啦啦當,’啞巴大娘歪歪扭扭/從廂樓崴到堂屋的竹椅上哭訴:/‘昨夜我不小心/又壓死了你們的一個兄弟/你爺沒有戴斗笠,侵早冒雨用箢篼抱到對面山。’”除了“昨夜”這個詞不當外,其它的詞句絕對會生出神秘的陌生感來。但是我想說,李建春的例子并不能印證譚克修提出的“個我方言”應用的“地方主義詩人的使命”,反倒讓人覺得“個我方言”在拯救詩的特殊性上不可信,除了偶爾起到一種意想不到的驚人效果。我喜歡李建春的《乙未年的秋氣》,這種技術上的“個我方言”出自武斷的個人風格,詞語的奇異位置令人信服,《護水》和《守土》是按“事物本來樣子”敘事的,間架松弛,節奏搖晃,如果將之視為地方性詩學的一部分,恐怕第一個不服氣的就是提出“地方性詩學”的那個人。
正如泉子的追問:“山水對人心的塑造從來緩慢而劇烈。如果不是這片土地,如果不曾生活于江南,那么,我會是誰?我會寫下一首或一些怎樣的詩歌?”地方主義的普遍意義在他鄉和故鄉所做的斗爭中凸顯出來,不只表現于生活方式和言語層面上,而僅僅如泉子的切身感受:“厭倦”。或許每個詩人都是故鄉的叛徒,沒有自我身體的背叛就沒有地方主義,從一個地方到另一個地方,他們所做的,除了轉換口音更多的是喚醒穿越的身體,就穿越自身而言,地方主義者賦予他們的作品符號的作用。
泉子的詩中有內含性因素的人生經驗和風格中始終堅持的儀式感,莊重、憂郁但不感傷,在那些被人詬病的大詞(如“民族”“國家”“時代”“大地”等)里他的空位置感非常恰當,一般而言,被大詞定義或描述的事物容易呈現庸常的特點,如果這是個假定的結構,在泉子這里卻成為了一種符號結構。《青山》和《圓月》里的距離感讓我們讀到了敬畏和悲傷,《詩人的心》有力量,《落日》則是這種力量延伸出來的一種場景;《偶然》傳達出來的絕望感令人驚心動魄,《盛年》則是對自己的一次辨認。泉子的詩短,短到或讓意義封閉,但聲音卻是連續的,《繁華是這一刻的》充溢了滄桑感,《瑪瑙寺》仿佛建立起了一種深層的悖論,從詩學上解釋,詩人或通往虛無的傳統。泉子的詩在哲學的層面上幾乎都有一種反思命運的普遍動機,像《凡心》中的“幽暗”、《不斷醒來的自己》中的“異質”、《空無的蜜》中的“多與寡”等都在《廣陵散》的“在我今天這個年齡”的追問中化約為呢喃的風格。
我特別愿意讀到韓文戈的詩,他試圖給故鄉立傳而建立起另一種通往死亡的傳統,也就是如譚克修說過的“從而實現拯救某種生命細微角落即將逝去的特殊感覺”。就技藝而言,韓文戈的《包漿的事物》和《手藝》可視為他的地方性寫作宣言,按他自己的說法,“這是一個對個體身份確認的過程。”專注于詩歌中的“勞動”因素,會讓我們想到《詩經》,韓文戈的寫作似乎被古典地規定了一種源頭,他的身體穿越了歷代的身體,力圖在詩中循環往復地展現“手藝”和“包漿的事物”;傳統本身亦隱喻本身,他為之辯護的某種現實主義——寓歷史于個人生命的寫作——地方主義寫作結果又像個眾所周知的文學史悖論;他的《遷墳》作為一種意指,以及伴隨它的生與死的思索,比恐懼本身還模糊。
詩的不可能性應該優于它的可能性,一首詩或一種詩太強調它的可能性時,我們會發現,詩在幾乎所有地方都離散了它的說服力。地方志或屬地方言式寫作其實既沒有自我性也沒有說服力,問題是,地方主義特別容易給人一種錯覺,地方主義是模擬性的。如何超越地域性概念,這是“地方性詩學”研究的一個重要問題。從語言的角度來看,“個我方言”的封閉的意義變得不再確定,如果通過分離的詞語間的距離來確認一種詩寫的屬性,這種不可能性必定優于它的可能性。
方言系統里最有生命力的是那些俗話、黑話、俏皮話、雙關語、順口溜、諺語、口誤、污言穢語等等,但俗話、黑話、俏皮話、雙關語、順口溜、諺語、口誤、污言穢語等等不是詩;必須重新發明方言,而不是憐憫方言,在我看來,方言是口語系統里的一個活躍的器官,也是“地方性詩學”最容易被貶謫的地方。
我們可以拿伊沙舉例說明重新發明方言的重要性。伊沙的身上掛滿了“口語詩”標簽,他的“口語詩”意識形態與語言的連接有關并超越了言語成為一種強大的風格。這么說吧,口語是伊沙系的方言(甚至,連口語中的口吃和臟話都成為了口語系詩人的一種語言力量)。《最后的長安人》已經是伊沙的舊作了,其對農業抒情的抑制和“故事”式的表意結構,到現在依然保持著硬朗無匹的語調,盡管這首詩帶著鮮明的地方性表意符號——“秦俑”,但它卻與“地方性詩學”的主張背道而馳,包括那首經典的《張常氏,你的保姆》,改變或重新定位了“地方性詩學”;在口語系詩人那里,進入到口語系統里的基于事實的意識形態表意習慣和當下的隱喻性觀念的寫作格格不入,以伊沙為例,作為現象級詩人,日常口語化的表述有著一種獨屬于他自身的專有結構形式,對讀者而言,文本幾乎成為了一種獵奇的對象,個人的軼聞趣事則帶來了最具娛樂性的談資。
余幼幼有個說法,“我與這片土地的關系幾乎就是我與日常生活的關系……因為我把它視為了生活中的一部分,置身其中,便成為了一種細碎瑣屑的東西。”這么看,地方性儼然直接成為余幼幼在顯意識中構造的一個詩寫前提,“細碎瑣屑的東西”應該具有代碼功能以及象征作用,也就是說,她在塑造一個類似于碎片狀態之中的“四川”符號。從《醉酒的人都有透明的心》《在膠囊里飛》《寡歡》觀察,余幼幼總是圍繞、橫貫對自己不利的位置感受和理解“細碎瑣屑的東西”,令我們相信這確實可能發生:“出租車進入隧道的那刻/我突然感覺偏離了城市的自尊/今夜我挨了一把刀”“兩粒膠囊/上膛/向我的頭顱開槍”。她把自己裝扮成了一個問題少女,她在《少數人》一詩中強調了自己幾乎與世隔絕一樣的身份:“我是誰不重要/就像許多人/只能經歷大多數人中/的少數人/少數的同性以及/更少的異性”;這種理念令人驚異,余幼幼在詩中表現出來的一個仿佛被上帝遺棄的任性孩子的形象,卻暗含著一種邏輯——個人與當代現實之間的緊張的想象性關系。
限于篇幅,諸例不再舉。
韓文戈認為“從某種寬泛意義上說,每一個詩人都是‘地方主義詩群’的詩人。無論他的那個‘地方’是在城市社區還是在廣闊鄉村。”這種看法屬于散漫性思維,就像譚克修試圖將“地方主義”視作一種新詩以來最大的流派,事實上“地方主義”作為流派是無法成立的。可以說每位詩人面對他所使用的地方性語言時,首先明確的是他個人的語言,語言即意識,詩人因“少數”意識而偉大——廖偉棠自認為是無政府主義和國際主義者,周瑟瑟排斥既定標準,伊沙根本不承認有一種普遍意義上的“地方主義”,他是“口語流”,就像福克納是“意識流”而不是建立在他那個“約克納帕塔法世系”的地方主義。地方主義寫作必然受出生地影響他的思維方式、腔調和方言習慣,但更多是一種個人風格、譜系,我將之視為一種“小語種”風格,是一種“小語種”技術,這樣我們就能清晰地發現地方主義詩人的另一個真相:每個詩人有他自己隱秘的寫作譜系、源頭、資源和地理。
重要詩學概念的建立和處理,歸納的復雜化似乎已成慣例,隨之而來的問題便是,何等形態的“地方主義”文本才稱得上“地方主義”文本?現在看,我傾向于將“地方主義”視為一個術語事件——確如其名的術語事件,只有將“地方主義”這個詩學術語孤立出來,我們才能明白“地方主義”的始作俑者為什么要非如此不可的原因。誠如德魯克發現并指出的,“地方主義”一直是全球化的,在文學這個領域,你比如說荷馬史詩中的古希臘或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彼得堡,但地方主義歸根結底是對統合力的削弱,以美國為例,地方主義“表現在愈來愈強調地方多樣性”。作為地方性詩歌寫作的“地方主義”,譚克修賦予了“拯救存在”的重大意義,我認為這不是一種認同思想,而是記憶幽默。可以這么說,如果“地方主義”試圖陳述一個事實,那現在看來陳述的事實經驗強烈但次要;如果“地方主義”試圖傳達一種統一性觀點,遺憾的是,這種觀點作為潛在的爭論對象自相矛盾;如果“地方主義”就是一種止于事實的想象,我相信在事實面前,人們一定看到了它的經不起推敲的主體性功能;但需要承認的是,“地方主義”觀點提供者譚克修,必將作為一種漢語詩歌溝通和解釋的形象為更多的人熟知。
2017-2-15呼和浩特
原載于《明天》2017年第6卷
來源:趙卡新浪博客
作者:趙卡
http://blog.sina.com.cn/s/blog_49c6b2f90102z6mr.html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