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中總會有一些不期而遇
——毛夢溪音樂專輯《我們在這里》欣賞
作者:朱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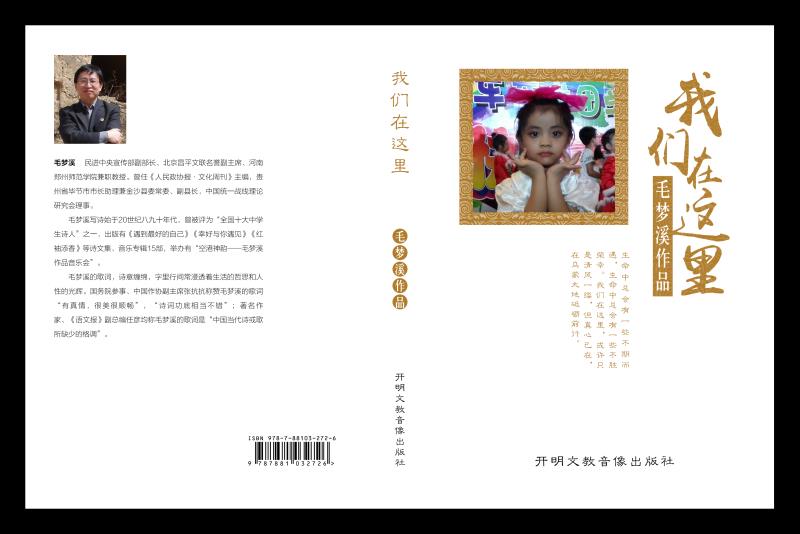
所謂詩人,就是能夠察于甚微而敏于極處,從平常的生活里發現異質,從事物的表象與內核或者從與之交集的土壤里發現特殊的光源,發現美,并且為這種發現提供語言。
多愁善感是詩人的共性,因此詩在攜帶著人文因素,自然因素以及社會生活因素的同時,也攜帶著詩人自身的眼界、悟性、品格與精神情懷。真正的詩人,都具有悲憫之心,有著無限的向上、向善、向美的品質和情懷。詩在詩人的靈魂之中閃電一般的形成,向世俗劈開一道裂縫,某些光源,就不自覺地破壁而出,并散發能量。這種能量能讓瞬間成為永恒。
身份不俗、文學造詣頗深的毛夢溪,當然也不例外。他生在依山傍水的湖南山村,畢業于北京師范大學,曾任貴州畢節市的市長助理兼金沙縣的縣委常委、副縣長,現任民進中央宣傳部副部長。無疑,他熱愛著那一片生養自己的湖南鄉土,熱愛那一片曾讓自己投入身心的烏蒙大地,也熱愛著祖國的山山水水、一草一木。他大量的詩與歌,都是寫鄉音鄉情,寫在觸動靈魂的每一次不期而遇和不勝榮幸。相遇,熱愛,感恩,悲憫,就是他詩意的源泉,寫作的原動力。
毛夢溪不但博古通今,精于文理,文字底蘊豐厚,而且對詩書畫頗有偏愛,因此字里行間自然而然的流露出些許痕跡。集詩書畫于一體,糅古典與現代詩風于一脈的詩詞格調,雄渾又清奇,高貴又洗練,典雅而絢麗,柔曼且自然。頗能觀古今于須臾,挫萬物于片言。
《我們在這里》,我們在哪里
心兒在支嘎阿魯,精彩演繹明天的憧憬;青春在花海鶴鄉,盡情放飛燃燒的激情。我們在這里,我們在這里,在烏蒙大地,金山玉水地穿行……生命中總會有一些不期而遇,生命中總會有一些不勝榮幸。我們在這里,或許只是清風一縷,但真心已在,在烏蒙大地砥礪前行。
這些帶著哲學視野與生活氣息的詩句,來自毛夢溪的“同心工程”之歌《我們在這里》。這首歌曲,詞曲優美獨特,歌聲婉轉清脆,可謂空靈優美,堪比天籟。它是沉淀在心底的聲音,充滿一種發自內心的豪情與博愛。
“‘生命中總會有一些不期而遇,生命中總會有一些不勝榮幸。’能聽上這樣詞曲優美的歌聲,我感到不勝榮幸!”,“好美的意境,詞曲十分優美,太好聽了。”“讓人久久不能忘懷的動人旋律。”“沉淀在心底的歌聲。”“這歌寫的充滿了一種發自內心的豪情與博愛”……《我們在這里》傳到網上,諸如此類的短評不絕于耳,不久便有了一百余萬聽眾。貴州詩人張開云不無感慨地說:“感動人心的歌,只有自己親臨體會,才能從血液中流出……”
《我們在這里》是從凱里到金沙幾小時一路放歌,是唱著《我們在這里》在烏蒙大地青山綠水間穿行,甚至去世前還在為他所幫扶的鄉鎮籌辦音樂會的已故音樂人鄭建安老師,留給我們最為珍貴的財富和最為動聽的旋律。《我們在這里》在各種演出中都頗受歡迎。在凱里,在金沙,在貴陽的現場,在中共中央統戰部的播放,還有2015年12月4日由著名歌唱家吳碧霞在慶祝民進70周年文藝晚會上的演唱,都引起了強烈反響。
一年畢節人,一生畢節情。毛夢溪曾在畢節掛職一年,有“洞天湖地”“花海鶴鄉”之稱的畢節試驗區已經融進了他的生命。當然,歌中的“我們”不僅僅是指他們這些掛職干部,更多的是指在中共中央統戰部、各民主黨派中央號召下,以及以各種渠道、各種方式前往試驗區參與扶貧攻堅的人們。毛夢溪說:“我們必須為他們歌唱,唱出他們的大美心境。有了真心、有了真情留在那里,就一定會生根,就一定就會成長,就一定就會花開不斷……”
有人說,世界是由兩個部分組成,一是自我,二是自我所面對的一切。毛夢溪正是在自我的意識之中,觸碰感覺自我,抑或社會生活,生命體系以及精神層面和人文情懷等諸方面帶給自己的震撼和沖擊力,并在這種感覺里提純接近理性的東西。
來到并生活在烏蒙大地,無疑是此生的不勝榮幸,那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都與自己有了必然聯系。“或許我們只是流星一雨,但真情已在,在烏蒙大地上同心同行。”柔曼自然的語境表達,不僅呈現詩性高貴闊遠的向度,而且彰顯低調、深沉、淳樸、敦厚的文人品質,和扎根烏蒙,改變烏蒙的決心。這一刻起,也許毛夢溪在自我面對的一切之中,找到了生命的支點與發射點。他把身心放在烏蒙大地,隨時準備發放出自身詩性的光和熱。
這樣的路走到山外,還要有多久多長,祖祖輩輩都在渴望,幸福的生活與夢想。泥濘的山路,拖住了日子和希望誰不想改變摸樣,找一個方向……我背條大路回故鄉,再苦再累也要扛;我背條大路回故鄉,讓山里山外一個樣。
這些帶著泥土芬芳,帶著濃郁的生活氣息以及底層勞動者心聲的詩句,來自毛夢溪的公益歌曲《背條大路回故鄉》。
這是一個真實的故事。貴州省織金縣雞場鄉雞坡村核桃寨的村民楊文學,帶著兒子在貴陽當“背篼”(民工),并把自己在貴陽當了8年“背篼”換來的13萬血汗錢全部用在家鄉的修路上。他的事跡感動了億萬中國人......
從生活深處挖掘詩意,毛夢溪以真誠、謙和、感恩、悲憫的心態觀察世界,以一個低層人的心理反應作底片,讓更多人看到了部分人生活的負重與樸實的高貴,也看到社會的某些不足,因此筆下的每一個字,都能成為底層勞動者最強烈的發聲。體察、關愛、悲憫,不單單是個體問題,更應該成為整個社會的共同責任與共同品質。
呈現即是讓讀者去覺醒的手段。通過具體的事物,給人們展現一個社會截面,從而得到更好的社會認知并產生社會效應,這也是毛夢溪的詩域擴張的一種潛在的、衍生的力量。
《喚一聲江南》,那叫一個美
一支長篙烏篷輕漾,青山綠水繞過白墻,秦淮燈影唱一曲流觴,綠了柳岸醉了時光。一折紙扇吳歌深巷,曉樓煙雨剪影在窗,百轉柔腸喚一聲江南,驚了水鄉醒了念想。
“我煙雨依舊的江南,我綠意盎然的江南,淅淅瀝瀝深深淺淺,仍是我魂牽夢繞的模樣。”《喚一聲江南》,江南之美,美得纖塵不染,甚至美成一種禪。古往今來,那些文人墨客無不對江南產生無限眷戀。仿佛江南自身就具有多愁善感永不衰老的青春氣息,帶著纏綿幽怨的愛情因素,無論何時何地,只要提及江南,便就不由自主的想起她濕漉漉的模樣,想起有關于她的烏篷船、青石板、雨巷、油紙傘。
有人說,寫詩形同談戀愛,起筆的那一刻,就已把自己融入其中,動了情的詩作才能給予人最好的感覺。毛夢溪既有成熟穩重的文人風范,也有多情浪漫的青春情懷。這首歌詞,深深淺淺的幾筆,就描出一個古意綿延、柔美多情的江南。
“我煙雨依舊的江南,我綠意盎然的江南。”一個“我”字,纏綿悱惻,暗含多少愛?多少癡情?像寫給誰的情書,有那種似是而非、若隱若現的感覺;讓人看一眼心跳,再一眼淪陷……
越曲撫不平一湖漣漪,裊裊的江南漫過蘇堤,還有輕抹淡染的胭脂,夢一般的眼神顧盼流離。煙柳牽不住青石逶迤,婷婷的江南一襲羅衣,還有清香淡雅的茉莉,綢一樣的身段隨風飄逸。
還有“嫣然春愁,烏篷依依,吳儂軟語,打濕郎意……你這江南江南奇女子,婉約在唐風宋雨的詩詞里。”(《江南奇女子》)毛夢溪筆下的場景,總是清晰又朦朧,似乎近在眼前,又恍若隔世。或濃或淡的文字線條,片段性的鏡頭穿插,立體而動感。
就像我們都熟悉的歌曲《纖夫的愛》,閉上眼睛都能感覺那種活生生的畫面來。而毛夢溪的著筆更趨于水墨色彩,不是把所有的境況寫得密不透風、水泄不通,也不是過于直白,失去詩詞本具有的含蓄性。而是,濃淡之間,情就顯山露水。他更多的留白,留給想象,這樣就使得自己的歌詞具有濃郁詩意和浪漫情感的繁衍空間。
不僅僅是提到的這些,其實毛夢溪的絕大部分作品都具有這種含蓄、優雅、纏綿、內斂、柔軟的風韻與水墨色彩,就仿佛總有那么一雙水汪汪的眼晴,看著你,還“說”著話,瞬間就擄走了你的心,讓你傾倒在那片刻的凝視里。
《十面青山》,青山依舊在
一溪流水,十面青山,你逶迤在烏蒙和婁山山脈攜手的地方。清水塘茶冷水河畔,你的容顏映現云水蒼茫。眉間赤水,足下烏江,你行走在過去與未來時光相逢的路上。東漢遺韻回沙酒香,你的歲月雕刻世代夢想。
這首《十面青山》寥寥120字,寫盡了貴州省金沙縣(原名打鼓新場)的天文地理。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作者筆鋒一轉:“且留心,慢回想,偉人當年,英明遙指打鼓新場……”就是這看似不經意的一筆,帶出來的卻是一場不小的風波------中國工農紅軍四渡赤水期間的一次重要事件,也是當年自遵義會議以來紅軍領導層在軍事路線原則問題上的一次重大分歧。
1935年3月10日,林彪發急電給軍委,提出消滅駐守打鼓新場一個師的滇軍。對這一建議,毛澤東堅決反對,但朱德認為可取。前敵司令部發生了分歧,毛澤東建議立即召集軍委會議,張聞天同意并主持召開了20余人參加的會議。由于大家絕大多數主張進攻打鼓新場,并一致通過了進攻打鼓新場的決定。毛澤東為了顧全大局,還是連夜設法說服中革軍委副主席周恩來緩發作戰命令,于3月11日開會重新決定集中全力打擊周渾元縱隊以實現戰略目標,避免了全軍覆沒的可能。這就是“打鼓新場風波”。
“打鼓新場風波”雖然未能立刻統一紅軍領導層的認識,但隨后魯班場之戰的失利,正是從反面證明了毛澤東的高瞻遠矚和深謀遠慮。
就像一幅懷舊版的滄桑水墨,清晰又朦朧的把一軸浩大而沉重的歷史拉開,推遠,再拉近,再推遠;就像一幀枯澀的書法,曲折而驚心動魄的烽火硝煙就在他落筆的輕重緩和之間,跌宕起伏,若隱若現;又似乎像一種無形劍,出于無聲而有聲,使于無形而有形,總可以扯著你的眼神心境,讓你跟隨境況而起伏不定。
再看毛夢溪筆下的婁山關:
千峰萬仞,雄詞只須一闕。英雄落寞愈是壯懷激烈。漫道雄關,旗鼓重振,遍地狼煙,霜晨月下,那西風也是,真烈……婁山關,霜晨月,聲豪邁,猶在耳,看今朝繁華盛世風生水起,婁山關上,已煥然一輪,新月。
毛夢溪最擅長的是那種婉約、纏綿、淳樸、自然的風格,但寫起壯懷激烈的沙場場面來,如此令人刮目。當一段歷史或濃或淡,斷斷續續地展現在讀者面前,那種時代感、距離感、滄桑感、緊迫感就突兀嶙峋。就像岳飛的《滿江紅》激越中藏著悲涼,悲愴中藏著力量。讀后有某種無法言喻的惋嘆與激情,久久不能平靜。復活一段歷史,實質上就是觸及生命與生活的真正意義,喚醒遙遠而被淡忘的疼痛,作為一種發奮的催生動力,才真正打開了詩性的本質。
毛夢溪不但具有卓越的藝術天分,而且是一位陽光向上知識淵博的思想者,既堪稱具有卓識才干的文人,又不愧為低調成熟的作家。總是能讓自身的哲思、遠見、卓識影響大眾,從而得到正能量的傳輸。
毛夢溪的歌曲,詩意纏綿,字里行間常浸透著生活的哲思和人性的光輝。國務院參事、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著名作家張抗抗稱贊毛夢溪的歌詞:“有真情,很美很順暢”,“詩詞功底相當不錯”。著名作家、《語文報》副總編任彥均稱毛夢溪的歌詞是“當代中國詩或歌所缺少的格調”。
對于毛夢溪的詩詞評價,有的說他具有哲學意識,有的說他頗有禪宗思想,有的說他具有普羅米修斯式的親和力,但也有的說他的詩作為歌詞太過含蓄。著名詩人、詞作家申林說:“我絕不認可有些人說的,毛夢溪的歌詞過于含蓄、文雅、清賞。這個時代,如果一味地附庸市場,書寫和歌唱同樣會失去應有的價值。我更期待歌曲像月光和大海,神秘、純凈、遼闊,充滿某種神圣引領的希冀。歌詞應該在簡約穩健的結構中充盈流動的氣血,回蕩著真實的情感。應該有真情的人文關懷,有微雕的表達,有時代的印記,有豐富的心靈。這樣,才能立體、真實、靈動地呈現更多人夢中的月光。我們有限的教養也許不能給予生活在底層的百姓絕對意義的平等,而我從他的歌曲里聽到更多的是傾聽、關愛與理解。”
我想,一個人的創作絕不是局限在某個風格特點上,他總會在不斷地探索之中不斷的進步。也許每一位評論家都只看到他其中的一面,還有更多沒有發現的東西潛藏在他的藝術創作中。就這本音樂專輯而言,他最大的寫作特質是動情,用心、真誠、自然。注重于以形傳神,似是而非。頗能把平面的語言,轉化為立體畫面,讓讀者直觀視角上有一定的概念。
有人說,一切藝術都通往音樂。正與毛夢溪的“詩源于歌,歌源于詩”觀點不謀而合。如果說詩中有畫,畫中有詩是一種境界,那么這種境界的最高抵達應該就是樂的升華。音樂往往又為衍生一種畫面、一種場境、一種氛圍,或者一種精神力量和情感濃度,提供更好的騰飛空間。音樂與詩相互融合,相互彌補,相互催化,相互向虛無縹緲的空靈意境趨近努力,才得以騰升為無與倫比的藝術境界。
詩書畫與音樂融為一體才是藝術的最高境界。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