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有弱之品格
敬文東/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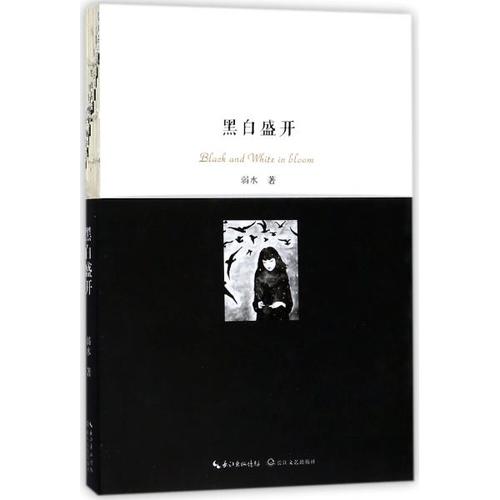
散文:《黑白盛開》
作者:弱水
出版:長江文藝出版社

弱水近照
自卡夫卡以來,對弱而不是對強的展現,似乎已經成為文學寫作中一道隱蔽的律令。康羅·洛倫茲據此認定:所謂現代人的歷史,就是自己反對自己的歷史。
如果文學刻意對強進行展現,就顯得既不誠實,又自不量力;而它對弱進行展現,卻很有可能當得起希尼的贊語:“文學是一種糾正。”
但1949年以來的中國當代文學卻另有特色。它更傾向于在高音量中,展現絕對的強,展現鐵拳。而傾心于弱,并試圖理解弱,以至于最終學會展示弱,乃是中國當代作家的必修功課,雖然至今都很難說已經成功。
在這個大背景下,去觀察弱水女士的散文集《黑白盛開》,就很可能別有一番意思。弱水宣稱:“我不喜歡我的生活中一切過于明顯的女性特征,除了我的相貌和衣著,我喜歡在自己能夠發揮的方面將自己打造得粗糲、堅強、豪放、有力。”(弱水:《與我們的性別和諧相處》)
這里似乎有兩點特別值得注意:
第一,這個自我宣稱乃是弱水在洞悉到女性的弱者地位后的刻意之舉。
第二,她意在強大起來的自我宣稱在語調上卻明顯是弱的。
但這一點都不矛盾。一個頗為有趣的人生三段論存乎于弱水的人生:她似乎在無師自通中,學會了對弱的體察與遵從;然后,在體察與遵從中愛上了寫作;最后,才在寫作中展現弱,就像那個一點都不矛盾的孩子。
秉承這種樣態的人生三段論,弱水有意把散文理解為對瑣碎生活的細心感受,對日常事務的用心體察。
她對自己因工作原因,長住外地賓館的狀態有過描述:“我不用計算時間趕路回去給孩子做飯,不用一邊走路一邊籌劃買什么菜,甚至連鋪床疊被擦桌拖地這類細致的活都由服務員做了。我只是必須回到那個房間而已,而不是它需要我。所以走在路上的我,顯得像一個真正的局外人,這個世界的旁觀者。懷著一種被遺棄般的空落落的心情,我忽然明白,被人需要有多重要,它幾乎就是我們活著的理由。”(弱水:《異地的房間》)
正如她在自我宣稱中暗示的那樣,她的文字在質地上,只有很弱的性別特征,不嬌氣,不柔弱,不嫵媚,沒有“颯爽英姿”,卻仍然有著個性鮮明的語言指紋,容不得被假冒、被張冠李戴。
理解了弱之品德的弱水女士做得相當徹底、相當堅決,一點都不“弱水”:她讓自己的文字屈尊于家長里短的市井生活,甚至將散文降低到“嚼”東家蘿卜西家糠的“舌頭”境地。但這并不是說弱水認同市井生活,以及市井生活中令人難以忍受的俗氣,也不意味著弱水熱衷于從“舌頭”境地提取啟示。前者是淪陷于生活的俗物才喜歡干的事情,后者則是“心靈雞湯”的熬制者的慣常動作——說經典動作可能更莊重,也更鄭重。
處于散文狀態的弱水自有其的目:將市井生活與東家蘿卜西家糠寫下即可,因為東家蘿卜西家糠與市井生活自有其深意。弱水于此之間暗中遵循的戒條,也許早已被保爾·瓦萊里一語道破:“最深的是皮膚。”也被奧斯卡·王爾德一眼洞穿:“唯淺薄之人才不以外表來判斷。世界之秘密是可見之物。”
得自弱之品格給予的教誨,也為了更好地對弱進行展現,弱水暗中擁有一套沾染了她體溫的詞語庫存,以及這套詞語庫存支持的句式和句型。一個成熟的作家,必有專屬于自己的詞匯,尤其是打磨和驅遣詞匯的方式,以及對句式和句型的操控,讓它和需要表達的主題緊緊綁在一起,并且環環相扣,不得有任何錯位和松動:
蘇州的一切,都和一個曠世美女有關。無論多遠,總要與她牽扯點故事。
這個叫木櫝的小鎮,是因為木材堵塞了航道,是為了讓我們知道,為美人而建的宮殿,需要多么龐大的木料,以及,比木料更龐大的,男人的愛。
雖然愛得有些盲目,但愛,哪有不盲目的。
在木櫝小鎮,想象木材擁堵河流的壯觀,如同美人心中的憂傷,流淌在每一條河流——脂粉香染寂寞的河,魚兒羞煞沉底的河。南方的河流太多,盡可以放縱想象,建構無窮的關系,任美人的美和憂傷,以及那最終砌成的宮殿,陷落的城池,在安靜的河水中一淌而過。(弱水:《南方日記》)。
詞語素樸、平常,像村姑,既水靈又有力,一看就是干農活或操持家務的好把式,每一個詞語都有春風拂面而來的那種體溫感,安逸、舒適,宜人心脾。句子短小,端莊、靈活,并且錯落有致,有女人腰間迷人的曲線,一看就是一副守身如玉的好氣度。而市井生活本身的意義,東家蘿卜西家糠自身的品相,不僅溢出了自身的外表,并且自在弱水動用的詞語、句子、句型之中。
但這一切,都跟個人心性的堅韌有關:散文呼應現代社會之真相去展現弱,恰好是為了獲取散文自身的強。《黑白盛開》就是對這個堅韌心性的堅韌實施。
作者簡介:
敬文東(文學博士,作家,文藝批評家,現執教于中央民族大學文學與新聞傳播學院
來源:北京晨報新聞中心
作者:敬文東
http://m.morningpost.com.cn/article/221826?from=timeline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