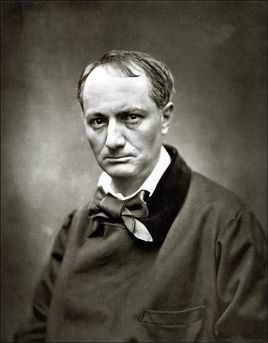
波德萊爾(資料圖)
文學(xué)和城市之間的淵源可以說與城市本身的歷史一樣久遠(yuǎn)。西方文學(xué)的歷史一直都伴隨著對于城市講述的歷史。從早期神話、史詩和《圣經(jīng)》對古代城邦、城市的講述,到現(xiàn)代文學(xué)對倫敦、巴黎、紐約等大都市的講述,文學(xué)敘事的發(fā)展始終與城市化的進(jìn)程相互影響,始終體現(xiàn)出與城市發(fā)展之間的密切關(guān)系。城市的發(fā)展在為作家們提供素材、語境和生活經(jīng)驗的同時,也深刻地影響著他們觀察世界的視角、反省人性的方式和評判價值的標(biāo)準(zhǔn)。
......
人類用了5000年的時間來建造城市,并且用了同樣多的時間來認(rèn)識城市的本質(zhì)和演變過程。但在這個歷史長河中的絕大部分時期,城市的發(fā)展速度和數(shù)量增長一直都非常緩慢。這種格局到了近代才開始發(fā)生改觀。中世紀(jì)晚期和文藝復(fù)興時期發(fā)生的農(nóng)業(yè)經(jīng)濟(jì)向工業(yè)經(jīng)濟(jì)的轉(zhuǎn)型和資本主義運(yùn)動的興起,拉開了歐洲近代城市化的帷幕。后來的工業(yè)革命浪潮更使城市化從18世紀(jì)末期開始以一種爆炸性現(xiàn)象呈現(xiàn)出來,并迅速向世界各地蔓延。現(xiàn)代城市就此成為這個世界上占支配地位的社會結(jié)構(gòu),代表著占支配地位的文明形態(tài)。整個現(xiàn)代世界都仿佛是在建造一座幅員遼闊的城市。短短兩百多年時間里,城市化在人類生活的各個方面引起的巨大變化超過了歷史上一切變化的總和。
在當(dāng)今世界,就人們所能夠直觀感受到的社會現(xiàn)象而言,城市化程度的高低在某種意義上代表著一個國家或地區(qū)文明程度的高低,被視為是“現(xiàn)代化”最明顯的表征。一般來說,工業(yè)化的快速推進(jìn)與城市化的快速推進(jìn)是齊頭并進(jìn)的,而工業(yè)化和城市化正是現(xiàn)代化過程中密不可分的兩個方面。所謂“現(xiàn)代”,不應(yīng)當(dāng)僅僅被理解成一個歷史性的時間概念,而更應(yīng)當(dāng)被看作是對一種全新文明類型的指稱,標(biāo)志著一個在諸多方面與那種以農(nóng)業(yè)文明為基礎(chǔ)的田園牧歌式的時代判然有別的新時代。而所謂“現(xiàn)代性”,是對這一全新文明類型及其特點(diǎn)的最凝練的表述。以這樣的視角來看,城市的劇變意味著現(xiàn)代性的劇變,反過來,現(xiàn)代性的劇變也就是城市的劇變。
在城市研究的發(fā)展過程中,現(xiàn)代性問題無疑是一個核心的理論問題。由于城市本身就是一個豐富而矛盾的存在,這也致使“現(xiàn)代性”成為一個意義復(fù)雜并且難以精確界定的概念。在對于現(xiàn)代性的多種解說中,最具代表性的是以下兩種同源而出、既相互關(guān)聯(lián)又相互抵牾的現(xiàn)代性。
一種是在西方近代資本主義工業(yè)文明中與時俱進(jìn)的現(xiàn)代性,它以科學(xué)理性為旗幟,以科學(xué)技術(shù)為手段,相信通過構(gòu)建新的理論和知識體系,可以促進(jìn)人類社會的進(jìn)步并達(dá)成人類自身的完善和自由。啟蒙精神是對這種現(xiàn)代性的直接體現(xiàn)和高度張揚(yáng)。現(xiàn)代的經(jīng)驗科學(xué)、社會規(guī)范、道德與法律理論正是在這種現(xiàn)代性的背景中各按其自身規(guī)律發(fā)展起來的。
另一種是以反思和審美為名而對前者構(gòu)成反叛和超越的現(xiàn)代性。就在資本主義意氣風(fēng)發(fā)、順風(fēng)滿帆地得到充分發(fā)展之際,一批眼光敏銳、思慮深遠(yuǎn)的先知先覺者基于自身的感覺經(jīng)驗,開始意識到理性的勝利并沒有為人類帶來預(yù)期的完善和自由,于是挺身而出,成為從“現(xiàn)代性”母體中產(chǎn)生出來的內(nèi)在批判力量和強(qiáng)大的自我超越力量,以反思和審美的現(xiàn)代性來對抗科學(xué)理性的現(xiàn)代性,揭露資本主義社會和文化中包含著的深刻矛盾性和悖論性。他們在捍衛(wèi)審美現(xiàn)代性的同時,又在物質(zhì)上拒斥現(xiàn)代文明,對現(xiàn)代文明的發(fā)展方向表現(xiàn)出深切的憂慮和懷疑。他們在這個時代找不到什么可以讓他們喜歡的事情,但他們卻又表現(xiàn)得像是極為著迷于這個時代,對這個時代最具特征的那些事物進(jìn)行反復(fù)的、不厭其詳?shù)拿枋觥N覀儗λ麄兊男袨橹荒軓南喾吹姆较騺砝斫狻K麄儗崉t是以嘲諷的態(tài)度去喜愛這個讓他們深為憎惡的時代,帶著批判的眼光去承認(rèn)它,為的是發(fā)展出一種在那里起著作用、正從內(nèi)部腐蝕它的既定價值的力量。如果說前一種現(xiàn)代性的主角是在經(jīng)濟(jì)和政治上都占有支配地位的資產(chǎn)階級,那后一種現(xiàn)代性的主角則是以資產(chǎn)階級的逆子和批判者面目出現(xiàn)且常常淪為社會邊緣人物的一批詩人、藝術(shù)家和文人。波德萊爾在他那個時代是后一種現(xiàn)代性最具代表性的,甚至也可能是最好的理論家和實踐者。后來的人們(如齊美爾和法蘭克福學(xué)派的本雅明、阿多諾等)以審美經(jīng)驗為武器進(jìn)行社會批判的思路,都可以在波德萊爾那里找到淵源。
審美現(xiàn)代性從本質(zhì)上說是心理主義的,其最顯著的特點(diǎn)就是從感覺的當(dāng)下性中去挖掘具有精神價值的收獲。波德萊爾就毫不猶豫地標(biāo)舉現(xiàn)代性的這一特點(diǎn),把當(dāng)下經(jīng)驗視為自己的情感和想象的起點(diǎn)和終點(diǎn)。他在自己的詩歌實踐中一如他在《現(xiàn)代生活的畫家》一文中所言,致力于從“過渡、短暫、偶然”中提取永恒,“從流行的東西中提取出它可能包含著的在歷史中富有詩意的東西”。波德萊爾的現(xiàn)代性綱領(lǐng)一方面得益于現(xiàn)代文明為他提供的巨大可能性,但另一方面,他所倡導(dǎo)的審美現(xiàn)代性本身又構(gòu)成對作為資本主義同義語的現(xiàn)代性的反動。他對精神價值的守護(hù)與對現(xiàn)代社會中粗俗的物質(zhì)主義的抨擊適成對照。美國學(xué)者卡林內(nèi)斯庫對波德萊爾審美現(xiàn)代性的悖論進(jìn)行了這樣的解說:
他(指波德萊爾)的現(xiàn)代性綱領(lǐng)似乎是一種嘗試,希望通過讓人充分地、無法回避地意識到這種矛盾來尋求解決之道。一旦獲得了這種意識,轉(zhuǎn)瞬即逝的現(xiàn)時就可以變得真正富有創(chuàng)造性,并發(fā)現(xiàn)它自身的美,即曇花一現(xiàn)的美。
美轉(zhuǎn)瞬即逝,但其“形式和神圣本質(zhì)”將在精神宇宙的空間中得到永存。
齊美爾被認(rèn)為是在波德萊爾之后第一個深入研究現(xiàn)代性問題的社會學(xué)家。他的研究可以說是在波德萊爾提出的審美現(xiàn)代性的框架下展開的。他對現(xiàn)代性本質(zhì)的定義基本上可以被看作是對波德萊爾審美現(xiàn)代性綱領(lǐng)的又一種解說:
現(xiàn)代性的本質(zhì)是心理主義的,即根據(jù)我們內(nèi)在生活(實際上是作為一個內(nèi)在世界)的反應(yīng)來體驗和解釋這個世界,在躁動的靈魂中凝固的內(nèi)容均已消解,一切實質(zhì)性的東西均已濾盡,而靈魂的形式則純?nèi)皇沁\(yùn)動的形式。
齊美爾以哲學(xué)家的稟賦,以審美的眼光和形而上學(xué)的思考,以帶有幾分親近又帶有幾分疏離的態(tài)度,考察日常生活中微不足道的現(xiàn)象和感性碎片,以揭示現(xiàn)代生活狀況對個體情感、人格和心靈狀態(tài)所帶來的影響,其所采用的方法與作為城市詩人的“閑逛者”在大街小巷發(fā)掘生活和詩歌碎片的方式頗相仿佛,十分契合于城市生活的異質(zhì)性、多元化、碎片化、開放性等特點(diǎn)。與波德萊爾一樣,他所關(guān)注的重點(diǎn)不是城市生活的政治經(jīng)濟(jì)學(xué),而是人們在日常生活中的看與被看的經(jīng)驗,即一種基于感受的審美經(jīng)驗,因而他的現(xiàn)代性理論也被認(rèn)為是一種審美社會學(xué)。
在被認(rèn)為是20世紀(jì)“最偉大的文學(xué)心靈之一”和“最偉大、最淵博的文學(xué)批評家之一”的本雅明那里,歷史哲學(xué)也已經(jīng)與美學(xué)理論難分彼此地融為一體了。本雅明懷著從歷史現(xiàn)象學(xué)角度走近社會的經(jīng)驗結(jié)構(gòu)的抱負(fù),部分借用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并以馬克思主義傳統(tǒng)中從未有過的方式探討“發(fā)達(dá)資本主義時代”人的內(nèi)在經(jīng)驗與外部世界之間結(jié)成的特殊共生關(guān)系。他與海德格爾一樣,在思考自己時代的核心問題時,把目光投向了藝術(shù)與文化領(lǐng)域。他認(rèn)為,經(jīng)驗結(jié)構(gòu)是社會歷史轉(zhuǎn)變的產(chǎn)物,而現(xiàn)今時代的顯著特征,首先而且最清楚地出現(xiàn)在美學(xué)經(jīng)驗之中。他所探討的現(xiàn)代性落腳在能夠體現(xiàn)時代精神的經(jīng)驗層面。他同波德萊爾一樣,把客觀世界的非精神狀態(tài)再造成精神,在體驗的層次上連接起現(xiàn)實經(jīng)驗和審美經(jīng)驗,連接起時代的生產(chǎn)方式(包括技術(shù)手段和社會組織等)和藝術(shù)作品的創(chuàng)造。按照他的思路來看,文化藝術(shù)領(lǐng)域依然具有反映社會現(xiàn)實的鏡像功能,只不過這種鏡像不一定是現(xiàn)實的物質(zhì)鏡像,而倒更像是現(xiàn)實的精神鏡像。他論述波德萊爾抒情詩的那些文字是對他自己的思想進(jìn)行形象演示的經(jīng)典范例。盡管他的思想中帶有一些“過于精明的唯智論”(布萊希特語)和神秘主義的傾向,但他第一次讓藝術(shù)作品真正地與生存方式建立起“直接”的聯(lián)系,讓“經(jīng)濟(jì)基礎(chǔ)”第一次以可見的(雖然是隱喻的、寓言性的)方式與“上層建筑”在同一個充滿寓意的空間中結(jié)合在了一起。物質(zhì)國度里的廢墟就此成為思想國度的資源,生活形態(tài)也因為轉(zhuǎn)變成為審美形態(tài)而獲得了價值。這也讓本雅明這位體驗的沉思者成為了現(xiàn)代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文藝?yán)碚摰拈_創(chuàng)者。
費(fèi)瑟斯通在《消費(fèi)主義與后現(xiàn)代主義》一書中把波德萊爾、齊美爾和本雅明三人并舉,指出他們都致力于通過探索感受、情感、心態(tài)、靈魂等在城市背景下發(fā)生的變化來捕捉現(xiàn)代生活的節(jié)奏,展現(xiàn)現(xiàn)代生活的能量。他并且還認(rèn)為,他們對自19世紀(jì)中期開始的大城市的“現(xiàn)代性”經(jīng)驗所進(jìn)行的描述,對促進(jìn)20世紀(jì)的后現(xiàn)代主義對現(xiàn)代性問題的思考和批判具有不可多得的啟示意義。誠然,在其最廣泛的意義上,現(xiàn)代性可以指與一個時間段和一個地理位置聯(lián)系在一起的現(xiàn)代社會生活及其組織形式,但在“審美現(xiàn)代性”的視角下,現(xiàn)代性更多是以一種態(tài)度、一種文化、一種思想、一種思潮的面目呈現(xiàn)出來的,其偏重于精神文化,把物質(zhì)視為人性的隱喻,把城市視為文化的隱喻,它不僅意味著行為和舉止的新方式,而且還代表著感覺和思想的新方式。
本文選自《波德萊爾:從城市經(jīng)驗到詩歌經(jīng)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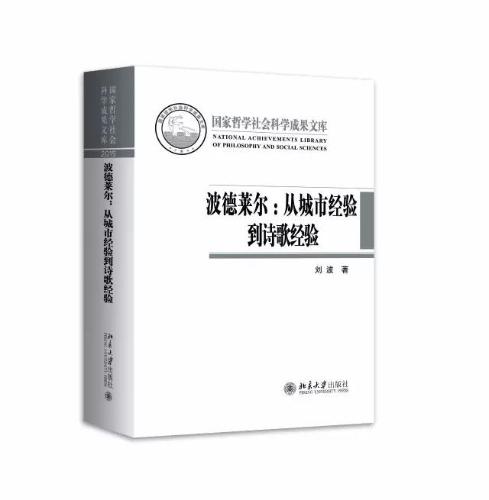
《波德萊爾:從城市經(jīng)驗到詩歌經(jīng)驗》 劉波/著
ISBN 978-7-301-26959-6 北京大學(xué)出版社 定價:139.00元
作者:劉波
來源:中國詩歌網(wǎng)
責(zé)任編輯:蘇豐雷
http://www.zgshige.com/c/2018-07-23/6700340.shtml


 純貴坊酒業(yè)
純貴坊酒業(y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