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少卿:評價昌耀詩歌的三個誤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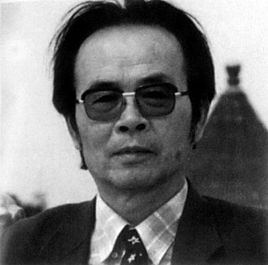
昌耀(資料圖)
內容提要:昌耀早期詩歌存在深度改寫、重寫的現象,不能通過他在詩末標注的寫作日期得出“他超出時代”的結論,他真正的特出之處是可以不斷自我更新;昌耀詩歌的黃金時代開始于1980年代中后期,寫于1980年代早期的《慈航》不宜作為昌耀的代表作;對于昌耀詩歌的“散文化”和音樂性問題,應結合具體作品辨析得失,不應籠統地褒揚或貶斥;以上是評價昌耀詩歌時應注意的三個方面。
自2000年詩人昌耀去世之后,研究昌耀的論文急劇增多。尤其是近幾年,說昌耀研究蔚然成風亦不為過。以同方知網論文檢索為例,按主題詞“昌耀”、“詩歌”組合搜索,共得200余篇結果,其中,約10篇發表于昌耀去世之前,約90篇發表于2000-2009十年之間,約100篇發表于2010年至今(2016年7月)。由此約略可見昌耀詩歌受關注程度的變化趨勢。
在這一研究熱潮中,昌耀詩歌獲得了高度的贊譽和經典化的位置。已故詩人駱一禾早在1988年即發表文章指出:“昌耀是中國新詩運動中的一位大詩人。”[①]昌耀去世后研究的主流基本上是對這一論斷進行印證。諸多研究者熱衷于從各個方面去發掘昌耀作為一個大詩人的特征。筆者無意挑戰這一結論,但在閱讀文獻的過程中察覺到,關于昌耀的評價還有許多虛浮之處。只有進一步夯實浮土,我們對這位命運多舛的詩人的敬意才能建筑在一個更真實、更牢靠的地基上。
一 不牢靠的詩歌編年
關于昌耀的杰出,一個較為常見的評價是:他的早期詩歌即超出了他所寄身的時代。這一判斷存在于教科書里,如“他的詩歌的重要價值,是從50年代開始,就離開當代‘主流詩歌’的語言系統,抗拒那些語匯、喻象,那些想象、表述方式”[②],也存在于一些知名學者的論文里,如“昌耀1953年開始寫詩,至1957 年因詩罹難。從早期的作品看,他即已背向詩壇,完全無視時人的寫作而獨辟蹊徑, 初步形成個人的風格”[③],“昌耀是一個特立獨行的人,不歸屬于任何流派社團,他從1950年代開始寫詩,他的創作就似乎沒有受到當時環境的影響”[④],“昌耀的創作一開始就以其獨特的背景和獨特的方式而卓然獨立于時代的主流詩歌之外,顯示出可貴的民間品格”[⑤]。
這些論斷統統都可以由昌耀的詩集資料支撐。昌耀自己編定的《昌耀詩文總集》[⑥](為行文方便,以下簡稱《總集》)里,標明寫于1950-1960年代的詩(為行文方便,以下簡稱“舊作”)共50首。在昌耀生前出版的詩集里[⑦],這些詩歌在結尾處都標明了寫作時間,如《邊城》寫于1957年7月25日,《高車》寫于1957年7月30日,《良宵》寫于1962年9月14日。標出寫作時間的慣例一直延續到《總集》里。在1950-1960年代,集體主義的頌歌、“政治抒情詩”寫作是詩壇主流,昌耀能寫出《邊城》、《高車》、《良宵》、《給我如水的絲竹》這樣個人色彩鮮明、充滿創造力的詩,當然超出了他的時代,即使被稱為天才也不為過。詩人西川曾這樣評價:“他早在1957年就寫下了非同凡響的詩篇《高車》。”[⑧]但實際情況并非如此。
文學史家洪子誠談到1950-1970年代的“地下寫作”時,提到一個研究的難點,即“地下寫作”的系年問題:“這些詩有的篇末注明了寫作的時間,如‘寫于1961年’,1972年等等,但是它們公開在刊物上發表,是在80-90年代……從寫作到發表期間,作者有沒有進行過修改?如果有的話,修改的程度怎么樣?如果做了修改,而且是重要的修改,這些作品的寫作時間還能定在61年和66年嗎?”[⑨]昌耀列為1950-1960年代寫作的詩歌,即存在這樣的問題。我們可以把《總集》里50首“舊作”的發表情況作一些歸納整理:
1.《林中試笛》(二首)發表于1957年《青海湖》第8期,按發表原貌收入《總集》,未收入生前的四部詩集。昌耀正是因為這兩首詩被打成“右派”,開始自己二十多年的流放生涯,并喪失了發表作品的權利。
2.《總集》的第一首詩《船,或工程腳手架》或是在《船兒啊》這首詩的基礎上修改而成。《船兒啊》這首詩作為組詩“高原散詩”中的一首,發表于沈陽作協主辦的《文學月刊》1956年4月號。
3.除以上三首詩外,其余47首詩歌的公開發表均在1979年昌耀復出后,發表時間一直綿延到1990年代。其中有些詩歌曾在雜志上發表,后保持原貌或修改后收入詩集,如《高車》、《邊城》、《群山》等,還有一些詩歌未在雜志上發表,直接收入詩集。
4.昌耀生前出版的四部詩集收錄的1950-1960年代詩歌的數量,依次是19首,36首,18首,15首,而且篇目不盡相同。這意味著,這些舊作是陸陸續續出現的,時間跨度很長,有些舊作第一次發表是在2000年出版的《總集》中。
那么,如何判斷昌耀修改了除《林中試笛》之外的那些舊作呢?首先,可以找到史料的線索。在昌耀1986年出版的第一本詩集《昌耀抒情詩集》里,一些(不是全部)1950-1960年代寫作的詩歌,不僅標注了原稿時間,還標注了修改時間,如《高車》標注:1984年12月22日刪定并序;《這是赭黃色的土地》標注:1983年12月22日刪定;《筏子客》標注:1981年9月2日重寫;《夜行在西部高原》標注:1982年12月5日刪定;《峨日朵雪峰之側》標注:1983年7月27日刪定;《天空》標注:1983年12月14日謄正。只是在后來的詩集中,這些修改時間的標注一律刪除,只保留了原稿時間。其次,可以將這些舊作與昌耀1950年代公開發表的作品對比。那些作品是昌耀排除在《總集》之外的,是昌耀不希望呈現給讀者的,但卻最真實地體現了昌耀在毛澤東時代的寫作水準。來自河南的研究者李海英搜集到昌耀1950年代公開發表的作品26件(計兩篇散文24首詩歌),通過分析發現,“昌耀早期的創作并沒有游離于主流之外,相反他一直都在時代的洪流中放歌”[⑩]。《總集》增編版增選了5首昌耀1950年代的詩歌,可以看出那就是社會主義建設之歌、生活之歌、戰士之歌,與廣受贊譽的《高車》《良宵》《兇年逸稿》不可能出自同一時期同一人之手,因為其世界觀、語言體系都迥乎不同。最后,還可以找到旁證。昌耀密友及傳記作者燎原在搜集比較大量材料的基礎上指出:“他早期的詩作,普遍地存在著1979年之后的改寫和‘深度加工’。”[11]
退一步講,如果修改只是一些無關緊要的修改,那么也不影響對昌耀早期詩歌價值的判定。如何判斷修改程度劇烈與否呢?可以將《船兒啊》與《船,或工程腳手架》兩首詩進行對比,還可以將《群山》1979年雜志發表版與收入《總集》版對比,可以發現改動帶有根本性,涉及語言風格、修辭手段乃至價值觀的調整。[12]
昌耀在《總集》后記里自述:“可嘆我一生追求‘完美’,而我之所能僅此而已。”他是一個精益求精的詩人。“他每編輯一部自己的新詩集時,都會對此前的一些詩作進行集中的改動。”[13]昌耀不可能坐視舊作中看起來已經不合時宜的痕跡。2000年由昌耀編定的《總集》,經過了他本人的篩選、審視,反映的是昌耀最晚近的關于詩歌的看法。對詩人來說,《總集》是帶有蓋棺論定性質的共時的存在,但由于它又清清楚楚地標示著寫作日期,對不明就里的研究者來說,就會把這些詩歌納入一個歷時的進程中考察,從而很方便地得出“昌耀超出時代”的結論。
概言之,《總集》里收錄的1950-1960年代的作品,除《林中試笛》外,都經過了昌耀復出后的重新審視和深度加工,體現的是昌耀1980年代以來的寫作風貌。只有理清了這一修改舊案,我們才能理解,為什么在五六十年代寫出《高車》《良宵》《給我如水的絲竹》《這虔誠的紅衣僧人》這種水準詩歌的人,還會在1978、1979年寫出像《致友人》《秋木》《啼血的“春歌”》這樣水準的詩作[14]。再延伸一下,《總集》中1979年之后的詩歌,其詩末標注的寫作時間也值得警惕,一首標明是1979年的詩作,也可能修改定稿于1980年代中期乃至1990年代。比如1979年的《歸客》是一首杰作,這首詩的水準大大超過了昌耀1979年作品的一般水準,體現的也不是昌耀在1979年對于歷史的認知,應該是經過了深度加工,加工時間甚至可能在1990年代中期(1994年的詩集《命運之書》沒有收入《歸客》,1996年的詩集《一個挑戰的旅行者步行在上帝的沙盤》才第一次收入)。按《總集》的編排順序閱讀昌耀詩歌,常會感到劇烈的質量起伏和風格的錯亂,應該是修改導致的結果。判斷昌耀作品大致的年代歸宿,從風格、水準出發可能比依據詩末所標時間要來得更為準確。
作為詩人,昌耀不是天才型的。他自述自己是“歲月有意孕成的琴鍵”[15]。他在詩歌上的成就很大程度得益于生活的磨難。并不需要把“超出時代”這樣泛濫的褒揚加之于昌耀。從歷時的角度考察,昌耀創造的真正的奇跡是他一直保持著自我更新的能力。他跟公劉、邵燕祥、流沙河、胡昭、周良沛、梁南、林希等一起被稱為“青春歷劫、壯歲歸來”的詩人,但當同代人的詩歌生命紛紛凋零的時候,他卻迎來了寫作的黃金時代,有能力與更年輕的詩人同臺競技,正如有論者注意到的那樣:“1986年出版的《探索詩集》中,昌耀是僅有的一位與新中國一起成長起來的首代詩人,同二、三代詩人相并列。它使我對這位詩人的不倦藝術追求深為嘆服。”[16]一個詩人的詩歌教養往往青少年階段即已奠定。昌耀年輕時代成長于社會主義政治抒情詩的環境之中,他本人早期寫作也是典型的集體主義詩歌。1980年代的寫作新浪潮對于五十年代、六十年代出生的詩人,接受起來是順理成章的。但對于昌耀這代“老詩人”來說,則不會那么容易。昌耀從一個早年的“政治抒情詩”詩人,轉變為80年代中期以后忠于自己的詩人。這種轉換,就論者目力所及,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中尚缺少其他范例。
昌耀有一種迫切跟上時代的愿望。在組詩《聽候召喚:趕路》中他寫:“我深感落伍已不可避免。”雖然僻居西部,他總能敏感到時代的中心命題,并用寫作實踐去呼應之。“傷痕文學”、“反思文學”發端時他寫《大山的囚徒》《歸客》《慈航》,“改革文學”盛行時他寫《印象:龍羊峽水電站工程》《邊關:二十四部燈》,“尋根文學”、“史詩潮”流行時他寫《青藏高原的形體》(組詩)《巨靈》,“先鋒文學”興起時他寫《斯人》《空城堡》《冷太陽》,“市場化”改革鋪開時他寫《烘烤》《意義空白》《堂▪吉訶德軍團還在前進》,“新左派”思潮抬頭時他寫《毛澤東》《一個中國詩人在俄羅斯》。與現實中的行動相對應,他在自己的詩歌中也創造了這樣的主體形象:挑戰,趕路,被太陽所召喚,一個永不停歇的“夸父”。強力的生命意志,使他沖破了習見和積習的包裹,拒絕了平庸和停滯。他的詩歌生涯幾乎保存了1949—2000年歷次文學主潮的浪花痕跡。他的自我更新能力是從詩歌史的角度去定位他時,需要特別褒揚的。
二 從鍍金到鑄金
在各類介紹昌耀的出版物上,最常提到的昌耀的代表作便是《慈航》。1991年的一篇評論文章中,論者將《慈航》與但丁的《神曲》相提并論:“《慈航》是二十世紀中期發生在中國大地上的一幕《神曲》。”[17]在一篇晚近的評論中,《慈航》也被推崇到無以復加的地步:“昌耀先生創作完成于1981年的長詩《慈航》,不僅是新時期文學三十年出現的巔峰之作,亦是整部詩史中堪與《離騷》《北征》并列的偉大詩章。”[18]昌耀臨去世前接受記者采訪,記者提問中的一個,即:“《慈航》被公認為是您的代表作,請您談談這首長詩的創作過程和作品的主旨。”[19]昌耀在隨后的回答中,并沒有表示異議,可見他也默認這種說法。《慈航》真有如此之高的價值嗎?且不論它是否能與歷史上的偉大詩篇并列,它能否作為昌耀真正的代表作都值得打上問號。
《慈航》標注的寫作時間是1980.2.9—1981.6.25,其最早發表于《西藏文學》1985年第10期。這是一首敘事長詩,共有12節。從情節來看,應該是以昌耀的個人經歷為藍本,加以想象、發揮改造而成。詩歌第一節講述詩人回憶的動因:“我不理解遺忘。/也不習慣麻木”,以及回憶的結論:“在善惡的角力中/愛的繁衍與生殖/比死亡的戕殘更古老、/更勇武百倍”。這個結論類似于詩歌的主旋律,在詩中反復出現了六次。詩歌的主體情節是一個落難者被荒原上的土伯特人(即藏人)拯救,成為土伯特女婿,重點描寫與土伯特女子相遇、成婚的經過,尤其是非常細膩地描寫了藏族的婚禮儀式。昌耀在上文提到的那次采訪中說,這首詩“基本上是以我為中心,寫出了我對藏族群眾的一種感激之情。……寫的是靈魂的棲所”[20]。
從誕生的背景看,《慈航》應該被歸入1980年代初期流行的“傷痕、反思文學”,它使用的象征性詞匯,是那個時期描述歷史災難時常用的,如“燈塔沉入海底”、“暴風”、“嚴冬”、“妖風”、“失道者”等。它的構思,屬于那個時期的一種典型敘事:咀嚼過往的苦難,并闡發苦難的意義。可以把它和這類敘事中當時最有名的一篇——張賢亮的小說《綠化樹》作一對比。兩篇作品發表時間相近,兩個作者年齡相仿,遭遇類似,可以說這兩件作品是類似的情緒呈現為不同的文學樣式,不同的是,《綠化樹》發表后被廣泛閱讀,而《慈航》發表后知者甚少。同樣是落難,同樣是被一個淳樸善良的底層女子拯救(這兩個女子都類似地散發著神性的光澤)[21];同樣是敘述者成為劫后英雄:《綠化樹》里寫“一九八三年六月,我出席在首都北京召開的一次共和國重要會議”,《慈航》里寫“摘掉荊冠/他從荒原踏來,/重新領有自己的運命”;同樣是把苦難理解為一種成就自己的必經階段:《綠化樹》開篇引用阿·托爾斯泰的名言“在清水里泡三次,在血水里浴三次,在堿水里煮三次”,《慈航》里則寫“你是風雨雷電合乎邏輯的選擇”;同樣充斥著一種男權中心主義的自戀:馬纓花豪言“就是鋼刀把我頭砍斷,我血身子還陪著你”,《慈航》里的土伯特女兒則表示:“我懂/我獻與/我篤行”;甚至他們最終得出的結論也是一樣的:張賢亮在小說結尾表達對像綠化樹一樣遍布大江南北的普通體力勞動者的贊頌,昌耀在詩歌中將“良知不滅的百姓”推崇為自己的“眾神”。——由此可知,《慈航》是那個時代帶有類同性特征的作品。
王安憶的名作《叔叔的故事》里這樣寫被打成“右派”的作家“叔叔”復出后的心態:
由于寫小說這一門工作,他的人生竟一點沒有浪費,每一點每一滴都有用處。小說究竟是什么啊?叔叔有時候想。有了它多么好啊!它為叔叔開辟了一個新的世界,在這個世界里,叔叔可以重新創造他的人生;在這個世界里,時間和空間都可聽憑人的意志重塑,一切經驗都可以修正,可將美麗的崇高的保存下,而將丑陋的卑瑣的統統消滅,可使毀滅了的得到新生。這個世界安慰著叔叔,它使叔叔獲得一種可能,那就是做一個新的人。
這段話概括了“叔叔們”在復出后的作品中所做的工作,即將過去的經歷浪漫化,在講述中將自我塑造為英雄,并將這個英雄安置在一個美麗新世界。《慈航》中的受難者是這樣登場的:“他獨坐裸原。/腳邊,流星的碎片尚留有天火的熱吻。”這儼然是流落人間的神子。在整首詩中都充滿了類似的驚人的浪漫化。“墻壁貼滿的牛糞餅塊/是你手制的象形字模。/輕輕摘下這迷人的辭藻, /你回身交給歸來的郎君,/托他送往灶坑去庫藏。”牛糞餅被比喻成象形字模和迷人的辭藻,這恐怕是陶淵明也難得有的田園逸致。“……一頭花鹿沖向斷崖,扭作半個輕柔的金環,瞬間隨同落日消散。” 慘烈的死亡,在觀察者眼中,竟然只剩下輕飄飄的“美”。在詩歌的抒情主人公和現實之間,仿佛隔了一層薄薄的簾幕,作者看不到現實的本來面貌,而是陶醉于簾幕上華麗而虛幻的煙云。這應該是得意者眼中的世界。這個時期,不僅《慈航》是這樣的,一批作品都具有類似的眼光。如《總集》中排在《慈航》之前的一首小詩《賣冰糖葫蘆者》:
他理解——
人們對春意的期望,
才將火紅的山楂
剪作一串甜蜜的蓓蕾,
綻放在扎靶。
于是,早春的集市
多了一樹裹著冰甲的紅梅。
在寒風中賣冰糖葫蘆者,當然首先是迫于生計。但在作者的眼中,卻是為了滿足人們對“春意的期望”。這首短詩之病也即《慈航》之病:作者用一廂情愿的虛幻的想象代替了對真實現實的體貼與逼近。昌耀在《慈航》中曾用“鍍金的騙局”[22]來形容之前的年代,而某種意義上,《慈航》的寫作不過是另一種規模略小的鍍金行為。這樣的寫作既可能是由于昌耀現實命運的改變所帶來的興奮感所致(“50年代的受難者‘文革’后‘冤情’得以洗清,他們受難的因由,連同受難的經歷,在‘新時期’轉化為榮耀”[23]),也可能與他經受的社會主義詩歌教育有關。寫作日期標注為1978、1979年的詩歌《秋之聲》、《秋木》、《啼血的“春歌”》等表明,重新登臺的昌耀仍然是那個社會主義時期的政治抒情詩人(主題先行,代言,概念化,圖解理念),他的詩歌基礎并沒有因為長期的流放而毀壞或改變。1979年的長詩《大山的囚徒》是那個時代“傷痕文學”的一部分。寫作《慈航》前后,昌耀本質上還是“老一代詩人”,習慣于生產宏大、空洞、充分意識形態化的敘事,習慣在詩歌中呼應政治結論,他并沒有和之前的詩歌積習實行切割。在描寫苦難時將苦難詩意化,同時自我圣化,用膚淺的思考得出泛泛之論,這很容易變質為對苦難的頌揚和掩蓋,而不是導向對苦難的反思。這正是《叔叔的故事》所致力于揭示的:如果我們持續生產虛幻的帶有自我麻醉色彩的浪漫故事,當真正的危機來臨時,就不可能有應對之道。
在具體的寫作技術方面,昌耀不加警惕地使用了“愛,良知,光明,道,善,惡”等帶有詩人歐陽江河所稱的“圣詞”性質的詞語。“圣詞先于尋常詞語。圣詞所指涉的是寫作中的絕對起源……從某種意義上講,圣詞的基礎是‘特許的檔案式預想’與二元對立邏輯的分析關系。這種關系事先假定有一個絕對支點(‘不可解釋的阿基米德支點’)來制約思想的形成過程、表達過程,以防不規范的語句突然出現。圣詞正是這種性質的絕對支點。”[24] “圣詞”起源于人類的假定,它們被頒布出來,就是為了讓人類無條件地遵守。所以,當詩歌中出現“愛、良知、光明、善”這些詞的時候,詩人的立場必是站在正面的一方,反擊居于對立面的一方,如“恨、無良、黑暗、惡”等。這些“圣詞”及其攜帶的“二元對立”的思維模式,使詩歌不再是“語言的冒險”,而成為對已知理念的一次多余的印證。它們關閉了朝向無限的語詞毛孔,切斷了本該豐富的想象神經,使詩歌一覽無余。正如詩人布羅茨基所言:“一個與邪惡斗爭或抵制它的人幾乎會自動地把自己當成是善良的,從而回避自我分析”[25],立場的自動獲得使作者不可能去挖掘人性深處的多樣性與復雜性。
《叔叔的故事》里,“叔叔”所講述的神圣莊嚴的故事不斷被瑣屑的實際生活的故事所瓦解,“叔叔”終究無法逃脫真實的過去對他的追捕,他的患有肝炎的兒子大寶找上門來便是這一追捕的最高潮,最終“叔叔”和大寶發生了打斗。盡管叔叔打敗了兒子,但卻一夜蒼老。他再也無法講快樂的故事了。在《叔叔的故事》發表之前好幾年,實際上昌耀已經感受到了虛幻的講述和真實的現實之間的差距。文化英雄的幻覺迅速消散,家庭關系在惡化,他的兒子也和他動過手[26],一些更具終極感的苦悶出現在他的視野,《慈航》所代表的早期寫作模式難以為繼。當他撕開虛幻的簾幕,“睜眼看世界”,一種真正有生命力的東西伸張出來。1985年,他寫下了詩歌《斯人》:
靜極——誰的嘆噓?
密西西比河此刻風雨,在那邊攀緣而走。
地球這壁,一人無語獨坐。
這首短詩里有著遼闊的時間和空間,它是靜觀和內視的產物。“斯人”獨坐,與天地精神相往來。第一行的“嘆噓”,仿佛千年一嘆,而后面的兩行,則在比對中凸顯出滄桑和命運感。有論者將昌耀的詩歌階段分為“斯人之前”和“斯人之后”:“《斯人》是昌耀詩歌寫作一個里程碑式的作品,它可以把昌耀的創作標識為‘斯人前’和‘斯人后’。”[27]昌耀發生轉變的時間并不一定就是1985年,可能要更早一些,但《斯人》的確是最為突出地展示了詩人新的精神形象:洗凈鉛華,徹底回到個人,靜觀世界。《慈航》和《斯人》可以作為昌耀創作生涯中兩個階段的標志。
《斯人》階段的作品,表現了對《慈航》的改寫和超越。《鹿的角枝》(1982)是對死去的鹿的追悼。《盤陀:未聞的故事》(1988年)不再洋溢著浮泛的樂觀,而是質疑:“生活總是一場敗局既定的博弈?”長詩《哈拉庫圖》(1989年)是昌耀重訪日月山牧地之后所作。日月山牧地是昌耀的流放地點,也是《慈航》的發生地。在《哈拉庫圖》里,昌耀發出這樣的詰問:
他勸我不要再尋思城堡的事,
他說那里很臟很臟很臟,
他說那處填滿卵石的坑穴刨出過許多白骨。
……
果真有過如花的喜娘?
果真有過哈拉庫圖之鷹?
果真有過流寓邊關的詩人?
是這樣的寂寞啊寂寞啊寂寞啊
《哈拉庫圖》實際上以另一種姿態重寫了《慈航》的故事,展示的是金粉凋落之后的斑駁圖景。1993年的《意義空白》里寫:“有一天你發現道德箴言變成了嵌銀描金的玩具。/有一天你發現你的吶喊闃寂無聲空作姿態。”這樣的表述可以看作是對《慈航》的宏大敘事的反省。
這些詩歌中的昌耀,和《慈航》時期的昌耀有著質的區別。在這個時期,他的詩歌運作方式不是鍍金式的,而是“鑄金”:鍛造一顆充滿力量的獨特的心靈,像太陽照臨萬物一樣,面對無限的虛空歌唱。詩歌《金色發動機》(1986)和《紫金冠》(1990年),便是這樣一種靈魂的自畫像。金所代表的溫暖力量,沒有被涂抹到世界的表層,而是變成內心堅守的動力源泉。他超出了階段性的社會歷史經驗,而與人類普遍性的困境遭遇:歷史的非連續性,自我的碎片化,荒誕感,災變意識,宿命。于是,我們在昌耀后期詩歌中看到了“烘烤”、“噩的結構”、“淘空”、“冷太陽”、“墳”(《謠辭》)“血跡”(《仁者》)、“化療者面部涂紅”(《風雨交加的晴天及瞬刻詩意》)、命運的猙獰之美,一如魯迅的《野草》那樣表現出內心煎熬的外在征象。
是什么決定昌耀成為大詩人的?燎原判斷自《斯人》之后,“昌耀強盛的精神形態開始從峰值向下回調”[28],而筆者的判斷恰恰相反:昌耀寫作最有價值的部分在《斯人》后階段。[29]《慈航》是昌耀作品中相對比較完整的長詩,但它只是昌耀過渡期的成果,絕不應作為昌耀的代表作。能代表昌耀詩歌最高成就的應是那種排除虛幻、徹底面對自身和意義空白的作品。
三 關于“散文化”及“不諧”
談到昌耀詩歌的外在形式特點,“散文化”、“滯澀”、“奇崛”、“拗”等斷語是常常被啟用的。文學史家洪子誠這樣概括自己對昌耀詩歌藝術形式的印象:“按照一般的觀念,詩應該與散文劃清界限,應該在音韻、節奏、句式上講究均衡和和諧,但昌耀似乎在回避、抵抗這些。而且,‘句子’的構造,常使用倒裝、修飾語后置等分割、安置方式,以造成總體上奇崛的散文式的外在形態。”[30]這一印象包含了兩層信息:1.昌耀詩歌的“散文化”傾向:他的詩歌和散文的邊界常常是模糊的;2.與散文化相關,其詩歌音樂性是不太和諧的。閱讀昌耀詩歌,這兩方面的總體印象是比較容易留下的,但如何對之進行評價,卻存在著較大分歧。
褒揚者將昌耀的這一形式特點解釋為對新詩的發展和創造。如:“語言創造有時有必要突破固有的語言模式……對某些習慣于文從字順的詩歌的讀者構成了冒犯……偏離于這詩壇的習氣和秩序,甚至偏離于這詩壇對于詩歌的惰性滿滿的習見。”[31]還有論者認為昌耀詩歌的形式特點,恰好對應于他的青藏高原體驗:“他在這里讀出了一種沉重的、滯澀的、古奧的、佶屈聱牙、塊壘崢嶸的語言和文體……相對于同代詩人相同時期的詩作,它們敘事的不流暢,以及語言的滯澀感,猶如礦石群在山體內的憋悶崛動。”[32]有不少贊揚者延續了這樣的思路,認為這樣的形式恰好對應于駁雜的生活感受,因此是必要的,是與內容相協調的:“由于生活的脅迫,緊張、混亂、沖突,這固有的悖反現象同時保留在他的詩中,于是有了差異、間離、駁雜、不和諧。”[33]“詩歌形式上的錯亂看起來泛濫無形,恰是基于詩歌主題表達的需要。”[34](這樣的說法其實經不起推敲,復雜凌亂的生活不一定要以復雜凌亂的詩行來表現。形式上的錯亂和表達內容的豐富性是兩碼事)
在盛大的褒揚聲中,一直以來,也有一股細小的聲浪對昌耀詩歌的表達形式提出批評。盡管這樣的聲音常常被淹沒,但它也是不屈不撓的。如較早的一篇關于昌耀的評論中,作者羅洛指出:“昌耀近期的短詩,結構、意境都比較完整,而長詩則顯得松散。”[35]詩人劉湛秋為《昌耀抒情詩集》所作的序里提到:“我們也可以說昌耀的詩偏于散文化,太不講究形式上的韻律,或者在內容和角度上有些什么。”[36]昌耀去世之后,亦有論者斷言:“音樂性、節奏和質樸恰是昌耀先生作品所不具備的特點。”[37]
如何看待以上兩方面的評判呢?昌耀詩歌的形式探索對于建設中國新詩的體式具有啟發意義。他的實驗已經沖擊到邊界地帶。籠統的褒揚和貶斥,都無助于我們深入理解昌耀實踐的意義,唯有具體問題具體分析,方可進入真正的詩歌現場。
“散文化”是新詩自誕生以來的一個大趨勢。白話新詩誕生之初,即是散文化的,如胡適《嘗試集》里的大部分詩歌、周作人的《小河》等。盡管在新詩發展的歷史上,不時有將新詩格律化或納入某種固定形式的沖動(如聞一多、何其芳、卞之琳、林庚等的探索),但“散文化”卻是不折不扣的主流,自郭沫若至艾青,新詩的形式更趨自由、舒展。廢名在上世紀三十年代即斷言:“我們只要有了這個詩的內容,我們就可以大膽的寫我們的新詩,不受一切的束縛,‘不拘格律,不拘平仄,不拘長短;有什么題目,做什么詩;詩該怎樣做,就怎樣做。’我們寫的是詩,我們用的文字是散文的文字,就是所謂自由詩。”[38]艾青也說:“假如是詩,無論用什么形式寫出來都是詩。假如不是詩,無論用什么形式寫出來都不是詩。真正的詩就是混在散文里也會被發現的。”[39]他們把新詩成立之依據不是放在形式上,而是放在內容上。這樣的觀念一直延續到當下,如詩人西川寫了很多不分行的詩,詩人張棗將魯迅的散文詩集《野草》追溯為現代漢詩的起源:“我們新詩的第一個偉大詩人,我們詩歌現代性的源頭的奠基人,是魯迅。魯迅以他無與倫比的象征主義的小冊子《野草》奠基了現代漢語詩的開始。”[40]
昌耀同樣主張決定詩之為詩的,不是詩的外在形式,而是詩的內核:“我并不強調詩的分行……也不認為詩定要分行,沒有詩性的文字即便分行也終難稱作詩。相反,某些有意味的文字即便不分行也未嘗不配稱作詩。詩之與否,我以心性去體味而不以貌取。”[41]他的這一觀念直承艾青。昌耀在詩歌寫作上受到艾青很大的影響。他曾有言:“艾青從巴黎帶回的蘆笛是我所珍重的,我不知當代前輩老詩人里還有誰對我更具這種長久魅力。”[42]和艾青一樣,他的許多詩歌都像是一個散文長句折行而成。不過他比艾青走得更遠。之所以在評價昌耀詩歌時,人們重提“散文化”,正是因為相對于新詩歷史上的散文化,昌耀的散文化表現得格外突出,在邊界上更具突破性。“散文化”本身并不構成評判優劣的標準,而是需要去具體區分哪些是成功的散文化,哪些是失敗的散文化,其決定之點在于是否具備昌耀所說的“詩性”,或者說“詩心”。詩心的螺旋槳一旦轉動起來,無論化諸怎樣的文字形式,它都是詩;而詩心的螺旋槳一旦停擺,即使采用了格律的形式,它也不是詩。
昌耀在詩歌散文化方面一個比較成功的例子出自《內陸高迥》(1988)。這首詩的第三節有一個長句子堆積成詩的一部分:
一個蓬頭垢面的旅行者西行在曠遠的公路,一只燎黑了的
鋁制飯鍋倒扣在他的背囊,一根充作手杖的棍棒橫抱在
腰際。他的鬢角扎起。兔毛似的灰白有如霉變。他的頸
彎前翹如牛負軛。他睜大的瞳仁也似因窒息而在喘息。
我直覺他的饑渴也是我的饑渴。我直覺組成他的肉體的
一部分也曾是組成我的肉體的一部分。使他苦悶的原因
也是使我同樣苦悶的原因,而我感受到的歡樂卻未必是
他的歡樂。
這些句子是一個散文式段落,在每一個版本的詩集里,其斷行位置和每行字數都不太一樣,都是跟著排版版式而發生變化。這表明它是一個徹底的散文段落,分行沒有意義。這樣的段落顯然是昌耀有意為之。它為一個旅行者畫像,也是為詩中的抒情主人公畫像。這樣的畫像是工筆畫的風格,作者采取了連貫的描繪性的句子。這樣一個龐大的文字塊出現在詩中,從幾何形狀上也呼應了詩題“內陸高迥”,這段話就是詩中的“內陸”,甚至和“迥”字字形中的塊狀部分也構成了呼應關系。用“塊壘崢嶸”來形容這一藝術創造的美感是恰當的。
從某種意義上說,寫自由詩比寫舊體詩更具難度。舊體詩寫得再差,至少還在表面上有一個形式撐住場面,而自由詩脫去了形式的依仗,一旦陷入平庸,就會簡陋得一覽無余。艾青對此深有體會:“自由詩所要防止的是平庸的敘述、蕪雜、凌亂、過分的散文化。我們采用寬大政策——反對過分的散文化。……有人認為自由詩好寫。大概是徐遲講的:‘自由詩難寫。’自由詩要反掉平庸的敘述、蕪雜、凌亂、過分的散文化這幾條,可不是那么容易的。”[43]如果要求自由詩剩下的是必不可少的具備“詩性”的內容,那么這樣的散文化其實是很難的。一旦詩歌的創造性減退,散文化的敘述帶來的就是繁瑣與平庸。在昌耀詩歌中,也不乏這樣的例子:
疏離意義者,必被意義無情地疏離。
嘲諷崇高者,敢情是匹夫之勇再加猥瑣之心。
時光容或墮落百次千次,但是人的范式
如明鏡蒙塵只容擦拭而斷無更改。
可見萬園之園在不遠的過去慘遭外盜火刑侮慢,
帝宮廢墟伶仃的柱礎蓋以國難而具奠祭之品格。
靈魂的自贖正從剛健有為開始。
不是教化,而是嚴峻了的現實。
——《意義的求索》節選(1995)
這些詩行采取的是散文的語調,并不新鮮的陳說內容顯示了詩人思想世界的單調與狹窄。第五行和第六行敘說的是圓明園遭焚毀的歷史,不僅表述得佶屈聱牙,而且用作論證材料顯得牽強、含混。這樣的寫作是昌耀詩歌中的敗筆。在不少詩歌、甚至代表作中,昌耀詩歌的語調往往是單調的,結構形式也往往是呆板的排比式。如果沒有強大的“詩心”、創造力來拯救或在結尾有一個高妙的破局,整首詩就會陷入不完美或徹底失敗的狀態。艾青所說的“平庸的敘述、蕪雜、凌亂、過分的散文化”在昌耀詩歌中也不少見。批評者指出:“在不少的作品中,詞語的羅列堆砌有時到了失去控制的地步。句子內部橫生的枝蔓在破壞了詩歌應有的速度和節奏的同時,消除了詞語和詞語之間的張力。”[44]這樣的意見值得重視。
與散文化相關的是詩歌的音樂性問題。音樂性是詩歌的基本質素,新詩亦概莫能外。只是新詩的音樂性范疇要寬泛得多,不僅指格律、押韻,還包括詩歌內在的節奏感、語流。好的新詩是可誦讀的,只是它所追求的朗誦效果并不都是那種標準化模式化的美聲朗誦,也可以是個人私語性的朗誦,“所謂詩歌的音樂性,不單是為了滿足這種討厭的朗誦腔(最好避開),詩歌也可以默讀,也可以一個人讀給另一個人聽,也可以自己讀給自己聽,也可以發瘋著讀,也可以嘔吐著讀”[45]。
昌耀本人并不否認詩歌的音樂性,在不同的場合,他多次談到音樂性和詩歌的關系。如:“我近來更傾向于將詩看做是‘音樂感覺’,是時空的抽象,是多部主題的融匯。感到自己理想中的詩恰好是那樣的一種‘流體’。”[46] “詩,不是可厭可鄙的說教,而是催人淚下的音樂。”[47]在昌耀趨于完善的作品中,音樂性亦是完備的,文氣連貫,一氣呵成,內在的節奏感非常好,如《良宵》《金色發動機》《紫金冠》等。昌耀會有意識地利用詩歌的形式手段來加強音樂性,如《冰河期》(1979)第一節:
那年頭黃河的濤聲被寒云緊鎖,
巨人沉默了。白頭的日子。我們千喚
不得一應。
第二行中的兩個句號,有利于制造停頓的效果。而將“不得一應”另起一行,也是為了拉長時間間隔,凸顯呼喚無果的絕望。在誦讀時,讀完“千喚”可以有較長的停頓,再讀“不得一應”,可以收獲良好的聲音效果與表意效果。
這樣的處理,是昌耀有意制造一種藝術效果,形成“滯澀”感。但在另一些情況下,昌耀詩歌讀起來磕磕絆絆,而這種磕絆本身并非出自表達的需要,而是由于作者才具的限制,它們應被視為昌耀詩歌中需要完善的部分,而不應被謬許為創造。如:
記憶的負重先天深沉。
人類習慣遺忘。
人類與任何動物無別都習于趨利避害。
而遵循快樂原則。
——《哈拉庫圖》節選(1989)
這是長詩《哈拉庫圖》中強行插入的幾句議論性的句子。這些觀點并不新鮮,它們出現在詩中,不僅沒有給詩歌增色,反而阻斷了詩歌的文氣,破壞了詩歌的“節奏感”和“內在旋律”。昌耀的一些長詩如《雄辯》《牛王》,是以犧牲音樂性來換取長度的,詩歌中突然的跳躍、轉換、插入,給人拼湊之感。他的許多詩并不具備貫通性與完整性。
如果不加分辨地肯定昌耀詩歌在“散文化”和“音樂性”方面的表現,會引起價值標準的混亂,使新一代的學習者無所適從。必須承認,在散文化和音樂性的處理方面,昌耀有自己的短板。有意為之的奇崛,與功力不足導致的不通暢是兩碼事。上文提到,昌耀曾臨終浩嘆:“可嘆我一生追求‘完美’,而我之所能僅此而已。”這表明他對于自己的不足有自我判斷。如此,我們就不能接受過于夸張的肯定,如在詩歌形制方面“自己給自己立法”[48]、“昌耀的詩隨便抽一首水準都很高”[49],也不能接受籠而統之的貶斥,如“昌耀的詩所缺不多,缺的只是音樂性和形式感”[50]。這兩種極端評價都無助于呈現昌耀詩歌的真實面貌。話說回來,沒有哪個詩人的詩首首經典。即使偉大如李白、杜甫,也存在大量平庸之作。十幾首或幾十首好詩已足以支撐起一個詩人的經典地位。
四 結語
由于昌耀一生命運多舛,承受了常人難以想象的厄運,研究者面對這樣的研究對象很少有不帶著敬意甚或景仰的。目前已經出現的研究論文基本上都是贊譽有加,鮮少具體地去辨析昌耀的得失。但道德感、主觀情感不能干擾正常的學術研究,明辨是非方是學術之正道。對一個詩人,生前的漠視與死后的造神,是同一種惡行的兩種表現。
在本文行將結束時,筆者偶然看到這樣一段話:
在昌耀去世后聲譽日隆的十年間,我也注意到了一些對于他表示不屑甚或是挖苦的文字和聲音。我當然清楚,它來自那些懷有特別心思、多少年來一直面目含混的中青年詩人和評論文字的操持者。一般而言,這是一些比較委屈的、執意要以不同凡響招徠詩壇注意的聲音,對此這里姑且不論。[51]
這樣的論調不應該出現。昌耀詩歌自有它的短板,不符合一些人的審美取向也是完全正常的。為什么“不屑”就一定別有用心呢?并進一步推斷發出不同聲音的人都是不得志的人。這種劃戰線、排立場、黨同伐異、學術道德化的思維方式,不正是當年昌耀被打成“右派”的厄運之始么?昌耀的追隨者成為昌耀敵人的化身,這是我們在評價昌耀時尤其要警惕的。
刪節版刊登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2017年第1期
注釋:
[①] 駱一禾、張玞:《太陽說:來,朝前走——評〈一首長詩和三首短詩〉》,《西藏文學》1988年5月號。
[②] 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修訂版),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26頁;亦見于洪子誠、劉登翰:《中國當代新詩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10年版,第172頁。
[③] 林賢治:《“溺水者”昌耀》,《當代文壇》2007年第4期。
[④] 張桃洲:《昌耀的詩歌成就及其歷史地位》,《武陵學刊》2013年第1期。
[⑤] 向衛國:《極地徘徊》,《當代文壇》2002年第3期。
[⑥] 昌耀:《昌耀詩文總集》,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7月出版,書面世時,昌耀已不在人世。2010年本書由作家出版社出版增編版,增加了77個頁碼的詩文,其中包含1950-1960年代的詩作5首。
[⑦] 昌耀生前出版的詩集共四部:《昌耀抒情詩集》,青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1988年出版增訂版,增加26首詩;《命運之書》,青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一個挑戰的旅行者步行在上帝的沙盤》,敦煌文藝出版社1996年版;《昌耀的詩》,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
[⑧] 西川:《昌耀詩的相反相成和兩個偏離》,《青海湖》2010年第3期。
[⑨] 洪子誠:《問題與方法》,三聯書店2002年版,第77頁。
[⑩] 李海英:《1953-2000年:昌耀詩歌創作綜論》,河南大學文學院2010屆碩士論文,第8頁。
[11] 燎原、王清學:《舊作改寫:昌耀寫作史上的一個“公案”》,《詩探索》2007年第1期。燎原和李海英的上述論文是目前僅見的對昌耀詩歌舊作改寫問題進行探究的研究,在它們相繼發表之后,“昌耀早期詩歌超出時代”的論斷仍然層出不窮。
[12] 在上述燎原、李海英的論文中有詳細對比,可參看。
[13] 燎原、王清學:《舊作改寫:昌耀寫作史上的一個“公案”》,《詩探索》2007年第1期。
[14] 這三首詩見于2010年增編版《總集》的增編部分,這個部分的文字是被昌耀排除在初版《總集》之外的,但被編者選入。
[15] 昌耀:《一份“業務自傳”》,收入《昌耀詩文總集》增編版,作家出版社2010年版,第857頁。
[16] 李萬慶:《“內陸高迥”——論昌耀詩歌的悲劇精神》,《當代作家評論》1991年第1期。
[17] 葉櫓:《〈慈航〉解讀》,《名作欣賞》1991年第3期。
[18] 莊曉明:《“愛的繁衍與生殖”的祭壇——昌耀〈慈航〉解讀》,《名作欣賞》2008年第11期。
[19] 昌耀:《答記者張曉穎問》,收入《昌耀詩文總集》,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81頁。
[20] 昌耀:《答記者張曉穎問》,收入《昌耀詩文總集》,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782頁。
[21] 黃子平在他的經典論文《同是天涯淪落人——一個“敘事模式”的抽樣分析》(刊于《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1985年第3期)中指出,《綠化樹》延續了“落難才子遇佳人”的敘事模式。《慈航》亦復如是。
[22] “鍍金”之語亦見于北島著名詩歌《回答》:“看吧,在那鍍金的天空中,飄滿了死者彎曲的倒影”。
[23] 洪子誠:《中國當代文學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7年版,第270頁。
[24] 歐陽江河:《當代詩的升華及其限度》,收入《如此博學的饑餓》,作家出版社2013年版,第280頁。
[25] 布羅茨基:《布羅茨基致哈維爾公開信》,黃燦然譯,《傾向》1994年第1期。
[26] 可參閱燎原:《詩人昌耀最后的日子》,《神劍》2007年第3期。
[27] 敬文東:《對一個口吃者的精神分析——詩人昌耀論》,《南方文壇》2000年第4期。
[28] 燎原:《高地上的奴隸與圣者》(代序),見《昌耀詩文總集》,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18頁。
[29] 可備一提的是,駱一禾賴以判斷昌耀是“大詩人”的四首作品,寫作日期標明為1986、1987年。
[30] 洪子誠:《點評〈鹿的角枝〉》,《詩探索》1995年第4期。
[31] 西川:《昌耀詩的相反相成和兩個偏離》,《青海湖》2010年第3期。
[32] 燎原:《昌耀評傳》,人民文學出版社2008年版,第271頁。
[33] 林賢治:《“溺水者”昌耀》,《當代文壇》2007年第4期。
[34] 易彬:《從穆旦到昌耀:新詩的語言質感論略》,《南京師范大學文學院學報》2013年第2期。
[35] 羅洛:《險拔峻峭,質而無華——談昌耀的詩》,《詩刊》1981年10月號。
[36] 劉湛秋:《他在荒原上默默閃光——〈昌耀抒情詩集〉序》,《文學評論》1985年第6期。
[37] 馬丁:《昌耀的悲劇》,《青海湖》2001年第1期。
[38] 廢名:《論新詩及其他》,遼寧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2頁。
[39] 艾青:《詩論》,《艾青全集》(第3卷),花山文藝出版社1991年版,第23頁。
[40] 張棗:《文學史、現代性與魯迅的〈野草〉》,《當代作家評論》2011年第1期。
[41] 昌耀:《〈昌耀的詩〉后記》,《昌耀的詩》,人民文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423頁。
[42] 昌耀:《艱難之思》,收入《昌耀詩文總集》,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407頁。
[43] 艾青:《談詩》,《詩刊》1996年5月號。
[44] 馬丁:《昌耀的悲劇》,《青海湖》2001年第1期。
[45] 西川:《西川回應:討論詩歌音樂性必須注意七點》,《遼寧日報》2016年7月21日第11版。
[46] 昌耀:《我的詩學觀》,收入《昌耀詩文總集》,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22頁。
[47] 昌耀:《與梅卓小姐一同釋讀幸運神遠離》,收入《昌耀詩文總集》,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656頁。
[48]燎原:《高地上的奴隸與圣者》(代序),見《昌耀詩文總集》,青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1頁。
[49] 韓作榮、胡殷紅:《大自然賦予的詩的器官》,《文學界》2008年第4期。
[50] 劉家魁:《缺失四分之三的新詩》,《星星》詩刊2001年第12期。
[51] 燎原:《多重語言類型景觀中的昌耀》,《青海湖》2010年第3期。
作者:胡少卿
來源:中國現代文學研究叢刊
責任編輯:蘇琦
http://www.zgshige.com/c/2018-12-12/7937546.shtml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