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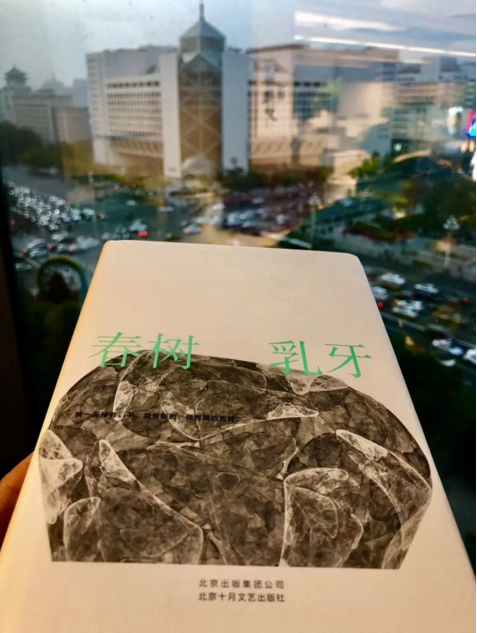
高星:直面人生或霧里看花
——評春樹小說《乳牙》
不知道誰給了阿堅一本去年的《世界哲學》雜志,他拿到德宏串吧,算是給我結賬的回扣。他還煞有介事地說,雜志中有幾篇文章特適合我閱讀,一篇是談福柯有關城市、空間與生態(tài) “空間批判”的啟示;一篇是論海德格爾與“土地倫理”;還有一篇是維特根斯坦論“世界圖像”的無理據(jù)性。阿堅還在有關海德格爾那篇文章上批注:“很像高星文論的風格,只是邏輯更明暢,但造句不如高生動。”
不管真假,阿堅知道我比較喜歡福柯、海德格爾、維特根斯坦論這三個哲學家,特別巧合的是,這三篇文章談到的城市、圖像、土地,都呈現(xiàn)著一種空間或環(huán)境的形態(tài)。
春樹新近出版了小說《乳牙》,這是她移居德國后的第一本小說。說是移居,其實她也隔三差五地回北京,甚至比她在北京時回山東老家的節(jié)奏還勤。
春樹是一位迷戀居所的女孩,她成名作是《北京娃娃》,后來有《光年之美國夢》,可見對地域環(huán)境的敏感。現(xiàn)在她在北京、柏林之間飛來飛去,翻來覆去,尋找或捕捉著她的“孤獨”——她的“生活在別處”。春樹說:“像年輕時候喜歡紐約一樣,巴黎像一座燈塔,每當我對生活無力的時候就會想起來。它也能刺激到我,讓我對此時的生活更加不滿。”
春樹說:“我想揪著自己的頭發(fā)呵斥自己活在當下,我像個小孩子一樣試圖從他者和世界那里獲取能量,卻不知道自己能做些什么。”
春樹確實是活在當下的人,從微信、微博、豆瓣等渠道可以看見她敞開式的生活,她不是和同一戰(zhàn)壕的詩人在一起,就是和發(fā)小或閨蜜在一起,在網(wǎng)上也經(jīng)常是和粉絲互動或互懟。
海德格爾認為,大地之“命運”從屬于“存在之命運”,從屬于形而上學之“遺忘”,所以在人類“主體地位”興起的時代,大地必然被“貶降”。他引用里爾克的詩表達了對現(xiàn)代工業(yè)的擔憂和對大地的深深的情感:“礦石懷著鄉(xiāng)愁/生計渺渺無蹤跡/一心離開錢幣和齒輪/離開工廠和金庫/鬼鬼到敞開群山的脈絡中/群山將在它的身后自閉”。
春樹當然不是迷戀田園或熱衷環(huán)保的人士,她甚至熱衷科學技術所產(chǎn)生的“光明”。但是春樹的內心總是存在“黑暗”的一角,如外人看不見她的孤獨。就像大地的黑暗,是光明的“居所”,更是成就生命之所。人除了在大地上固定棲居外,還要尋找思想漫游的家園。
春樹結婚、生子,是許多人想不到的事。這本小說,主要是懷孕到孩子(餡餅)長出乳牙的歷程,對于春樹來說,這個過程,不僅是她生活居所地域的變遷,也是她身體結構發(fā)生變化,特別是新的身份變更,一切到來的都恰到好處,又都有一點措手不及。
姑娘總是要長大的,女人總是要變老的。春樹也處在長牙的階段,所有的經(jīng)歷,全是收獲的素材。如她所言:“后來我也喜歡過許多男生,有些我記不清了,有些固執(zhí)地留在我的記憶里。那些如同噩夢般的試煉經(jīng)歷,讓我發(fā)誓以后盡量避免再出現(xiàn)這種情況。我慢慢訓練自己,反應遲鈍一些、感受力弱一些,不要沖動,不要偏激,與此同時,怦然心動的瞬間也減少了。我不再睹月思人,不再見花流淚。”
看春樹的小說,流暢自然,如面對面交流,特有的敏感如切膚之痛。她和狗子互稱戰(zhàn)友,他們都堅定直面人生,他們的豪言壯語是:“自己的真事還寫不完呢,寫什么創(chuàng)作!”
春樹把情緒化拿捏的行云流水,她平日的日記也是如此。“我的所有感官完全打開,情感變得細膩,乃至都到了人員受傷的程度。事物都呈現(xiàn)出它們本來的面目,像一片葉子上的脈絡般清晰、纖毫畢現(xiàn)。我才意識到這么多年,我一直都在克制壓抑著自己的敏感和情緒化的一面,一直在試圖讓自己的感受力變得粗糙。因為我意識到少年時期的那張面對面和處理問題的方式無法持續(xù)下去,那時候的我太容易崩潰、太追求完美主義。強大的感受力是我與生俱來的能力,讓我快樂,也讓我痛苦。我的情緒有如大海的潮汐,洶涌澎湃,席卷一切,甚至包括自己。”
我喜歡這樣的內心獨白。


 純貴坊酒業(yè)
純貴坊酒業(y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