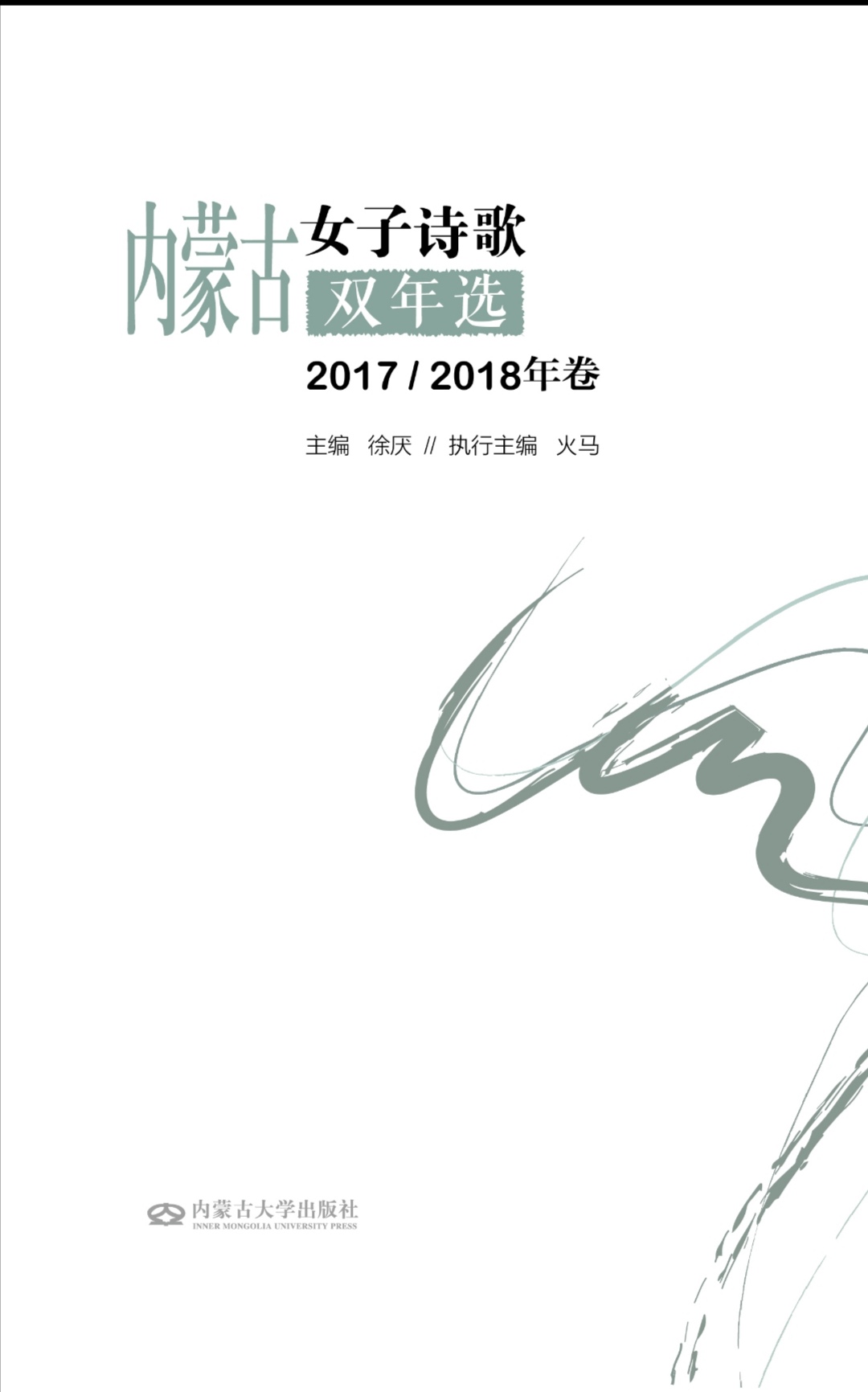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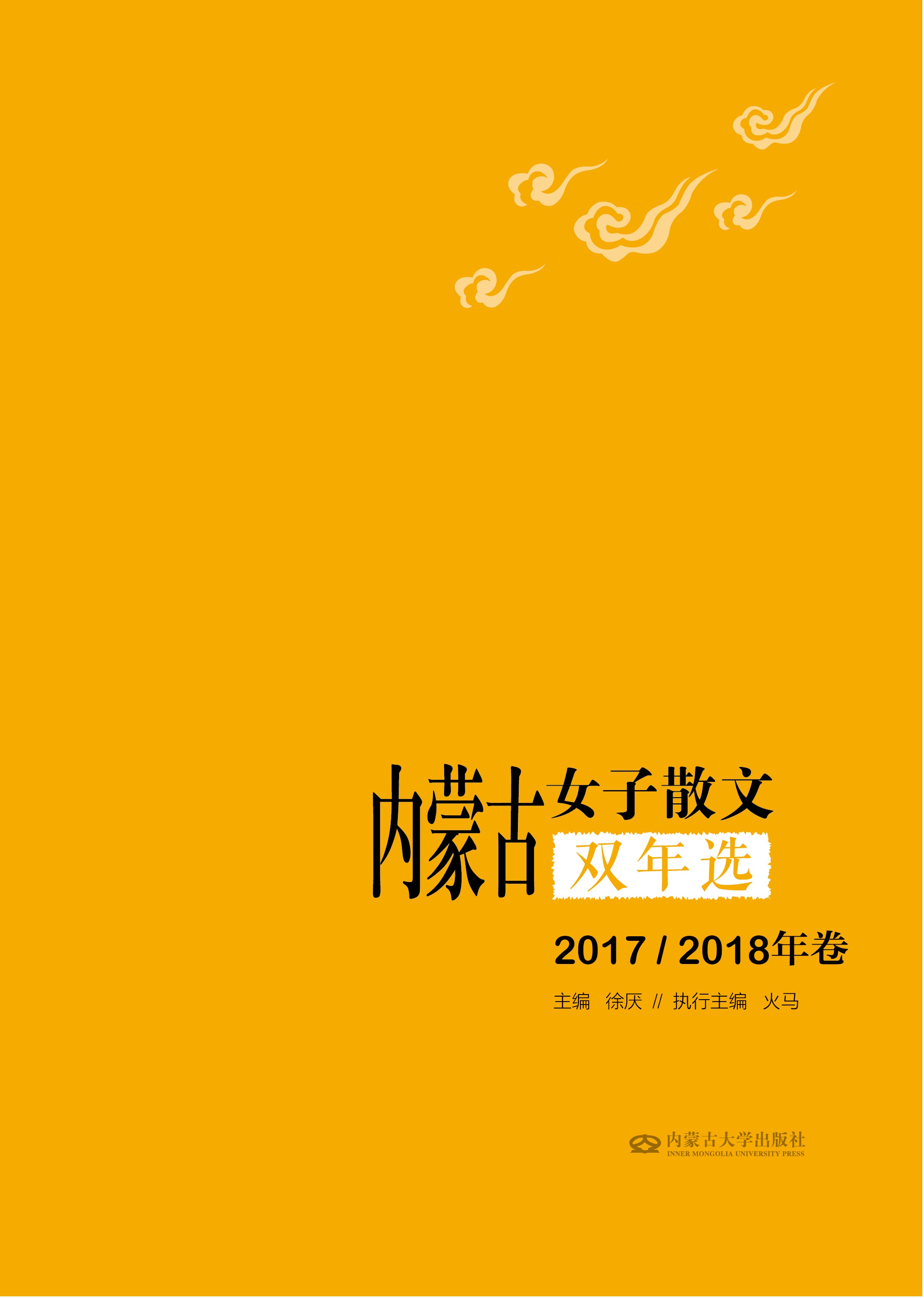
優秀選本的魅力:從私語抒寫到共同體的“復活”
——基于一套詩歌、散文雙年選的出版啟示
作者:王曉俊
作者:王曉俊
當下出版界一個比較繁盛的現象就是各種文學選本扎堆出現,尤在歲末年初更顯。多種選本紛呈,給讀者提供了選擇的多樣性和品鑒的豐富性,但所謂的“最佳”“精選”是否名副其實呢?細究之,我們會發現很多選本作品在藝術的感染力、審美的獨特性、思想的深邃性上并非實至名歸。或因標準模糊,缺乏顯著標識;或因擇選蕪雜,帶來泥沙俱下;或因功利驅使,導致魚目混珠。總之,“最佳不佳”“最精不精”的選本亂象屢見不鮮。
著名作家、學者顧隨先生曾說:“一個好的選本,等于一本著作。不怕偏,只要有中心思想。” 其言旨有二:一是說,優秀的文學選本具有元典的權威性和影響力;二是說好的選本具有明確的擇選標準,通過選本會傳遞出先進的文學觀念和審美理念。我國歷史上就出現過很多優秀的有影響力的文學選本,如我國現存最早的詩歌總集《詩經》、南朝梁代蕭統主持編選的《文選》,還有流行甚廣的《古文觀止》《唐詩別裁》《唐詩三百首》《文章正宗》,以及蒙學經典《神童詩》《千家詩》,等等,這些選本皆因整體的高品質、流傳的久遠性和受眾的廣泛性而成為文學史上經典的存在。
好的選本,會因為編選者披沙揀金的文學追求和眼不著砂的評判標準而讓其卓然而立,也會因為選本標準的新穎獨特、別具一格而讓其熠熠生輝。新近由內蒙古大學出版社出版發行,由詩人徐厭策劃、主編的內蒙古女子詩歌、散文雙年選(2017/2018年卷)被著名詩人、批評家霍俊明稱為“在‘選本文化’已經失范的今天具有重新校表的功能”,其擇女性視角觀照邊地文學新景觀的成功模式再次詮釋了選本的精品意識和精準定位對于文學選本實現自身文學價值和社會價值的重要性。
一、選本成功的表現
該套雙年選分兩卷本,一卷為詩歌,于2019年9月正式出版發行;一卷為散文,于2020年4月正式出版發行。兩卷雙年選從作家作品選擇的廣度和深度入手,重視選本的多元維度和嶄新向度,力圖用階段性的文學成果展示內蒙古女性作家在構建具有鮮明的地域特征和時代特征的邊地文學景觀過程中的個人體驗的抒發和公共體驗的共鳴。這種嘗試具有先鋒性質,正如執行主編火馬先生所言,它的出版將成為“內蒙古文學史上的一個重要事件” 。
1.因選本角度首立而引人注目
內蒙古文學作為邊地文學的一個分支,因浸透著草原泥土的芬芳、張揚著力與美的和弦而成為其中的獨特景觀。主編徐厭從“地理價值”和“美學價值”的角度深入挖掘出了內蒙古女性作者群體的別致所在,并用最能體現個人性靈和個性風采的抒寫文體來集中呈現這個創作群體的耀眼在場。這兩卷雙年選雖有些小眾情味,但因首創之功而嶄露頭角。詩人、評論家張清華說:“她們讓我們獲得了另外一個觀賞角度:塞外的粗獷,女性的柔美,兩種特質美妙地結合在一起,構成了一種稀有而珍貴的邊地詩學,穹隆之下文學生態的多樣性與異質性。”
這兩本雙年選從概念化的邊地文學中劈開一道亮光,用女性的別樣視域與豐沛情愫來折射遼闊邊地的細膩紋路。亦因選本角度的新穎獨創,內蒙古女性作者告別個體的淺吟低唱、私語獨寫而得以聚眾高歌。浪花朵朵,終匯溪流之勢,這恐怕是這套文學選本最成功的地方。
2.因選本標準精確而標識彰著
選本要想獲得成功,選本視角固然重要,選本標準也是關鍵。一個文學選本的誕生,不該是蕪雜作品的堆積壘砌,而應是精品的相互輝映;也不該是無章程的拼接湊數,而應是編選者文學觀念的集中體現;更不該是烏合之眾的嘶啞聒噪,而應是獨立靈魂的心聲吐露。
《內蒙古女子詩歌雙年選》收錄了174位詩人的372首作品,《內蒙古女子散文雙年選》收錄了100位作家的107篇作品,代表性、豐富性、在場性是這兩卷專題選本的擇選標準。從發聲伊始的校園寫手到技術成熟的文壇宿將,從隱忍柔情到剛健質樸,從廚房之近到遠方之遙,從精品至上的選編態度、開闊包容的文學視角到異彩紛呈的多元風格,編選者用小眾化的專題選本濃縮了一個稀有而別致的美學存在,真正做到了“聚眾凝神”,邊地特質與女性風采成為這兩本雙年選的雙重標識和美學標志。
3.因選本意義別致而耀眼在場
內蒙古地處北疆,“邊地”的地理坐標為其文學生態烙下了顯明的地域徽記,但也因此在人們心目中定格了先入為主的美學印象。內蒙古女子詩歌、散文雙年選于傳統的草原風骨之外,別開一面,擇女性視角觀照邊地文學的力與美,呈現了另外一種珍貴的美學景觀,它具有不可更替、無法取代的重要意義。耀眼在場的女性作家們很好地發揮了地域特質、性別優勢和個性魅力,她們的集體出場改變了邊地文學的傳統外觀和美學印象,她們也以群星璀璨的作品宣告了自己存在的價值和意義。
二、選本成功的意義
選取“她們”的吟唱抒寫,既呈現了邊地文學的全景態勢,又因性別因素和個體風格,增加了搖曳多姿的局部風姿。讓私語抒寫的薈萃成為一個共同體“復活”的契機,集地理價值與美學價值于一體,這是出版兩卷雙年選最有意義的地方。
1.邊地女性寫作群體耀眼登場
詩歌、散文是最容易流露個體情感體驗的文體,其鮮明的美學特質是獨抒性靈,更著意于“自然”狀態。把許多個性化的私語抒寫集結起來,置于獨特的地域背景下,無形中凝聚了一個創作共同體——她們以文學為旗幟,以邊地生活為寫作背景,以個人體驗為寫作對象,于高天厚土、粗糲遼闊中開辟出一款集萬千柔情與情感銳度的美學存在——姹紫嫣紅紛呈,多元書寫交織,文學的詩意與世俗的紅塵并現,一個新興的寫作群體被喚醒,被復活在邊地文學的浩渺星空之上。
從私語抒寫到共同體的“復活”,這是兩卷雙年選最令人稱道的文學貢獻。作家梁鴻評價道:“這些邊地書寫者以不羈的柔情與隱忍的鋒利呈現塞外生活的冰山一角,我看到雙彩虹與野馬群在字里行間閃閃發光,這光芒是女性的,也是人性的。”
2.邊地女性寫作群體風格多元
文學共同體的形成并沒有消融掉個性的光芒,兩卷雙年選沒有成為一個程式化亦或是概念化的文本代名詞。相反,因為在選本過程中更注重個性靈動的美學旨趣,所以我們在選本中看到的作品內容和風格是奇麗多姿的,真正做到了將地域文學與女性文學、群體水準與個人風格完美結合在了一起。個體在鮮明的地域背景中得到了文學的原動力和驅動源,又在個性化的情感體驗中尋覓到了屬于自己的美學特質和個性風采。因此,展現在讀者面前的內蒙古女子詩歌、散文作品是力與美的和諧疊加,是個性張揚的美學呈現,是融匯了地域特征與個別特質的稀有范本。
個性意識的蘇醒和個性風格的凸顯,使每一位作者都有獨立的標識。這一個個獨立的標識讓整部文本靈力流動,絕沒有因為選本的集結而陷入概念美學和僵化意念的泥淖里。
三、選本成功的啟示
1.在選本中要樹立與時俱進的文學觀
文學選本在一定程度上是編選者文學觀念和審美觀念的體現,若沒有明確的文學觀,選本勢必會因缺少靈魂而喪失掉引人矚目的特色。從這個意義上說,有靈魂的選本恰是編選者的二次創作。
這兩卷雙年選的靈魂,就在于編選者突破程式,敢為天下先,對選本多重校表功能的看重。這種校表功能不僅體現在編選者執念于通過小眾化的專題選本實現對文學、地理學、社會學的坐標重新定位,而且還體現在對整個邊地寫作的“在場性”的密切關注上。基于這種文學觀,我們在選本中可以看到個人經驗情感的直接性、無遮蔽性和敞開性的呈示,也可以領略到民族性、地域性和性別化的探索性書寫;既能讀到成熟作家在場堅守的力作,也能讀到年輕作者正在走向現場開始綻放的星光之作。選本呈現的是一群蓬勃成長的文學新貴,她們以群體的優秀而讓選本有一種文學的影響力量。
2.在選本中要貫徹始終如一的審美觀
主編徐厭一直反對任何形式的單向度價值,希望女性作家們“能夠擺脫集體性的特定時期,于有限處寫出無限性,最終順利進入個人化的在場期” 。因為重視選本作品的風格多樣性,所以我們在兩卷雙年選中可以讀到廣場作家陳慧明的沉痛追憶和人生感悟,也可以讀到自學成才的小作者曉角沒有書卷氣的質樸野趣;可以讀到母女及姐妹的家族式寫作,也可以讀到少數民族作家的神性寫作;可以讀到文壇宿將的獲獎作品,也可以讀到邊緣作者的智慧和能量;可以讀到個人對既定范式的反駁和揚棄,也可以讀到個體對公共語言體系的疏離。總之,無論哪一類寫作哪一種風格,我們都能品味到邊地文學的芬芳詩意,也能感動于個體情感體驗的細膩纖微。
3.在選本中要堅守寧缺毋濫的功利觀
文學選本最忌諱的是沒有原則性,若不良功利觀橫行,那么選本就必然會消損掉自身的美學特質。這兩卷雙年選忠實于文學追求的初衷,選本嚴謹而不失靈動,品質至上而風格多元,很好地踐行了編選者堅守的文學觀和審美觀。
以詩歌《雙年選》為例,編委會在短短36天的征稿期內共收到近300位作者發來的兩千余首作品,最終入選率不足15%,入選的詩歌只是內蒙古女子詩歌創作的冰山一角。但就是這冰山一角,既注意拓寬了作者的年齡跨度,沒有斷代現象,凸顯了邊地女性寫作的可持續張力,又看重在地域上的“泛內蒙古”,即通過本土作家與漂泊游子在文學創作上的并力齊驅,再現了更加獨立、自由、富有個性精神的邊地女性創作的宏大景觀。
內蒙古女子詩歌、散文雙年選也許在選本的規范和編排上會存在一些瑕疵,但瑕不掩瑜,由于編選者的用心著力,作為內蒙古首例小眾化的女子專題文學選本,其首創之功意義非凡,更因為其精品的選編態度和紛呈開闊的作品實力,讓“小眾”有了集體發聲的威勢,使之成為邊地背景之下獨一無二的美學影響。
這兩卷雙年選在選本失范的出版領域的成功嘗試,給執著于文學選本事業的編選者和出版者很多啟迪。文學選本的創新出版離不開編選者和出版者的協力合作:編選者用精品打造選本的品質和特質,出版者在選本上嚴格甄別,從而推波助瀾,規范選本的出版市場。二者的雙贏,恰是廣大讀者的福音。
(本文發表于《內蒙古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20年第6期,作者系內蒙古大學出版社編輯)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