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挖地域文化底蘊(yùn)的典范佳作
——壯族作家黃佩華散文集《生在平用》評(píng)述
作者:丘文橋
——壯族作家黃佩華散文集《生在平用》評(píng)述
作者:丘文橋
莫言說(shuō):“一個(gè)作家難以逃脫自己的經(jīng)歷,而最難逃脫的就是故鄉(xiāng)的經(jīng)歷。”故鄉(xiāng)的影像和經(jīng)歷成了很多作家豐厚的寫作素材,著名作家黃佩華的散文集《生在平用》更是直接用其出生地“平用”命名,可見故鄉(xiāng)是植根精神家園的。壯族作家黃佩華,曾兩度獲得全國(guó)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駿馬獎(jiǎng)”,出版有長(zhǎng)篇小說(shuō)《生生長(zhǎng)流》《公務(wù)員》《殺牛坪》《河之上》《五月病》和小說(shuō)集《南方女族》《遠(yuǎn)風(fēng)俗》等多部,著作豐厚皆以小說(shuō)聞名,《生在平用》是其首部散文集,由廣西民族出版社出版,全書由《生在平用》《行蹤履痕》《食色江湖》《文場(chǎng)暖事》四輯組成。
作家黃佩華飽醮著深情盡情地書寫著鄉(xiāng)土鄉(xiāng)情,正是這種農(nóng)人式寫作,讓他有了意想不到的收獲,由40篇散文精品以其如鳥鳴般純粹的清音吟唱出了原汁原味的鄉(xiāng)音鄉(xiāng)情,有來(lái)自家鄉(xiāng)的人和物,有壯鄉(xiāng)特色的景與像,也有打開味蕾的食色江湖,還有文壇的溫情記錄……。
平用是一個(gè)位于桂西北馱娘河畔的壯鄉(xiāng)小村寨,用《生在平用》這個(gè)書名,主要是為了紀(jì)念作家的出生地,幾十年來(lái),家鄉(xiāng)的父老鄉(xiāng)親、風(fēng)土人情、自然景致一直根植于作家黃佩華的記憶深處,從某種意義上說(shuō),平用這個(gè)小村莊就是作家黃佩華創(chuàng)作生涯的出發(fā)地和靠山。這部散文集,與作者的小說(shuō)相比可能技藝沒有那么高,展示主題沒有那么深,但卻是作家這些年的心路歷程,抒發(fā)內(nèi)心對(duì)家鄉(xiāng)對(duì)故土對(duì)親人無(wú)限的思念和眷戀,讀來(lái)令人感動(dòng),擊節(jié)叫好。
我毫不驚訝《生在平用》所具備的文學(xué)品質(zhì)。因?yàn)槭虑榈恼嫦嗍牵@本散文集絕非一個(gè)成功小說(shuō)家的臨時(shí)客串,而是一名優(yōu)秀作家的漂亮歸位。整部集子的散文語(yǔ)言平實(shí)、生動(dòng)、準(zhǔn)確,娓娓道來(lái),如數(shù)家珍,像拉家常一樣的記述方式極其耐讀。對(duì)家鄉(xiāng)平用的敬重、迷戀,與其文章的審美渾然一體,智性表達(dá)已然成為作家散筆的風(fēng)格。正如黃鳳顯教授在序言中說(shuō)“小說(shuō)創(chuàng)作上實(shí)力雄厚的黃佩華,這種看似“跨界”的努力,實(shí)則是跨越,代表了他們?cè)谖膶W(xué)創(chuàng)作領(lǐng)域的新開拓。”正是這種跨越,如《后記》中作者所說(shuō),這本散文集集結(jié)了作者“大半生的人生經(jīng)驗(yàn)積累,又是我奉獻(xiàn)給自己一份烈酒般的精神財(cái)富”。
美國(guó)詩(shī)人羅伯特•弗羅斯特說(shuō)過(guò)“文學(xué)始于地理”,這種文學(xué)的地理性寫作在散文集第一輯《生在平用》就得到充分展現(xiàn),整輯篇幅不長(zhǎng)的10篇精品里承載了平用鄉(xiāng)村的歷史、現(xiàn)代和未來(lái),寄托了作者對(duì)故土濃濃的鄉(xiāng)愁之情,是“望得見山、看得見水、記得住鄉(xiāng)愁”情懷。羅伯特還有一句名言:“作者不流淚,讀者也不會(huì)流淚”。我覺得,羅伯特的這兩句名言也恰好印證了第一輯關(guān)于故土的人和物的描摹。
在作家黃佩華眼里,15歲就離開家鄉(xiāng)去謀生活后,“平用”是有距離的,而“距離”成了《生在平用》《寄樹》《少年目光》等散文篇章里美學(xué)的關(guān)鍵詞。這個(gè)距離不僅是平面上的,還有空間上的,不僅有長(zhǎng)度,還有高度。故鄉(xiāng)風(fēng)物與人物在他筆端都成了他揣摩、省思和審視的對(duì)象,讓他的文字于抒情與描寫之外,多了極富辨識(shí)度的智性色彩:
“如果讓我選擇一個(gè)地方不能忘記,那我肯定會(huì)選擇平用。
平用不僅是我的出生地,而且給我留下了人生最初的印記,留下了童年生活難以磨滅的痕跡。縱然,這些印記和痕跡有快樂和幸福,也有悲傷和痛苦,但對(duì)于我的人生而言,那段時(shí)光依然是那般美好而有趣。
平用,是桂西北山區(qū)一個(gè)普通的地名,是一個(gè)小村子。這個(gè)依山傍水的小村,就像一顆散落的星星,深嵌在云貴高原南緣一個(gè)小小的皺褶里。”(《生在平用》)
《生在平用》,用蒼涼而又飽含情感的筆調(diào)勾勒出一幅平用人在粗獷、荒涼、孤獨(dú)無(wú)援的"絕地"中頑強(qiáng)"堅(jiān)守"的畫卷,展示了人類強(qiáng)大的生存毅力,那就是"堅(jiān)守"。推而廣之,我們每一個(gè)人都需要這樣的堅(jiān)守精神。本文對(duì)于讀者的意義"思想""精神"這些概念有了更為具體感性的認(rèn)識(shí),從內(nèi)心深處生長(zhǎng)人性的高貴。每個(gè)人都會(huì)有一處或多處屬于自己的精神家園或原鄉(xiāng),這是一個(gè)人的精神支柱,作家更是如此。
平用的象征意義,從地域文化象征看,又有多重意義。“把家安在高處”僅為了遠(yuǎn)離爭(zhēng)執(zhí),但又必須面臨“墾荒造田”的實(shí)際困難,盡管有來(lái)自時(shí)代社會(huì)歷史的,也有面臨生存和人性的,但是平用仍堅(jiān)定地讓父輩守住了自己的某些東西;盡管不是什么生命體,但似乎有靈魂,有品格和信念,就像人類一樣。平用是“驛站”,“對(duì)于我來(lái)說(shuō),老家的概念似乎到了平用就終止了”,作者書寫到這里的同時(shí)又僅僅感嘆匆匆過(guò)客,仿佛預(yù)言著人生的偶然性和必然性,人生遭遇的短暫性和記憶的深遠(yuǎn)性,無(wú)論如何“生在平用,是上天對(duì)的眷顧”。
“在云貴高原南緣,有一粗一細(xì)兩道大地的皺紋,粗的是紅河,細(xì)的便是馱娘河。
聽老人們說(shuō),平用這個(gè)地方原先并沒有人跡,是野獸們的樂園。是馱娘河給這片平緩的坡地帶來(lái)了靈性。這條源自云貴高原的河流,緩緩地從西南方向流下來(lái),在平用前面繞了一個(gè)大彎,便向東南方向踅去。馱娘河對(duì)于平用,就像一雙張開的巨臂。”(《馱娘河》)
顯然作家黃佩華對(duì)于河流的抒寫是濃墨重彩的,魂?duì)繅?mèng)繞的平用必定在馱娘河的臂灣里。世界文明最早誕生于尼羅河、恒河以及兩河流域,我國(guó)早期的文明主要在黃河、長(zhǎng)江流域,當(dāng)然還有珠江流域。河流既傳承文明,也承受更多的苦難。馱娘江則是右江的主要干流,是廣西兩條重要的河流之一。這里有作者幼小時(shí)候,每天到村前的馱娘江游泳捉魚,玩獨(dú)木舟,帶來(lái)了無(wú)窮的樂趣和思考。在這些有趣而充滿現(xiàn)場(chǎng)感的敘述里,也可見作家少時(shí)記憶里的獨(dú)木舟,這一道風(fēng)景里呈現(xiàn)的受人敬重的英雄好漢形象。
在第二輯的《行蹤履痕》里,作家走出西林的平用,《西行五百里》《冬天到長(zhǎng)春去看車》通過(guò)閱讀地圖揣摩世界又親歷去了解世界,作者寫了自己身處桂西北這種特殊的環(huán)境中的特殊的情緒感覺和思想意識(shí)。讓讀者深刻地感受到人的感覺意識(shí)與客觀環(huán)境息息相關(guān),這些感覺意識(shí)源于老家的環(huán)境;從文學(xué)原理來(lái)說(shuō),這些感覺意識(shí)與當(dāng)時(shí)當(dāng)?shù)氐目陀^環(huán)境相互映照,非常融洽。不過(guò),作家黃佩華筆下的這種感覺意識(shí)不是負(fù)面的,不只是被動(dòng)地為客觀外物所刺激、所促成,作者還將這些感覺意識(shí)加以升華,并生發(fā)出堅(jiān)韌不拔的心靈追求。
《生在平用》第二輯側(cè)重于對(duì)廣西乃至祖國(guó)名勝古跡,地方風(fēng)俗,傳統(tǒng)文化和人文景觀的解構(gòu)與詮釋。散文創(chuàng)作,作者需要有對(duì)歷史掌故的認(rèn)知,并能站在自己所處的時(shí)代背景上,對(duì)歷史和文化給出獨(dú)到的分析,創(chuàng)作出有文化意蘊(yùn)和文學(xué)氛圍的作品。比如寫《草原上的風(fēng)》,寫禪寺的《銅鑄之河》《鄉(xiāng)下人的南寧》《邊城和海》,寫桂西的壯族特色等。作者的立意與選材,都有著獨(dú)特的取向,思維空間在過(guò)去與現(xiàn)在間從容切換,于縱有千古橫及八荒中探求。作者立足當(dāng)下,融入歷史典故,又非簡(jiǎn)單的抒懷,而是以一名小說(shuō)家的獨(dú)具一格的審美情趣,細(xì)致的觀察與細(xì)膩的描寫,極具穿透力的筆觸,構(gòu)筑這些富有知識(shí)性、文化性又具有生命氣息和詩(shī)情韻味的散文。這樣的散文,可讀,耐讀,可細(xì)細(xì)品味。《西行五百里》感嘆西林的交通;《大地的眼睛》把樂業(yè)的天坑寫成了“天地間的一只眼睛”;《那鳳那山》“構(gòu)筑了人與自然最為和諧、最為瑰麗的風(fēng)景”……不一而足。
需要強(qiáng)調(diào)的是這一輯的大部分篇章里作家在區(qū)域敘事抒情寫意中傳達(dá)出很多壯族、壯鄉(xiāng)的地域文化象征意義。也許黃佩華在寫作的時(shí)候并不是有意為之,但在客觀上蘊(yùn)涵了這些象征意義。《這里的石頭會(huì)唱歌》對(duì)“山”“水”“石”的現(xiàn)場(chǎng)素描般的筆法使無(wú)數(shù)的經(jīng)典畫面躍然紙上。對(duì)于這樣的極具文化符號(hào)的記錄,讓讀者在閱讀的同時(shí)收獲更豐厚的知識(shí)性。
第三輯《食色江湖》里的美食,“凌云的狗肉”、廣西名片“粉”,還有嶺南以南的“食生”,是喚醒味蕾,是喚醒對(duì)一個(gè)地方或虛或?qū)崳蜻h(yuǎn)或近的記憶,“在我們生活的城市,食生是永無(wú)休止的,人們吃了河魚生又吃海魚生,然后再吃生龍蝦,吃生對(duì)蝦,吃生沙蟲,吃生泥丁,吃生蠔生貝......”(《城市食生族》),作家甚至還帶讀者吃到美國(guó),把在美國(guó)的吃喝描摹得妙趣橫生,不啻是一名作家吃貨,直至痛風(fēng)也在所不惜。
散文集《生在平用》有高雅的文學(xué)素養(yǎng)向度。作者不斷挖掘出一個(gè)新的視角和客觀的判斷,從多方面多層次書寫。在《邊城與海》中,寫說(shuō)走就走上了高速就直奔大海邊上;《我的高地情緒》大篇幅介紹桂西北的小說(shuō)里的人物原型、河邊的家鄉(xiāng)、紅河系列的作品,不同季節(jié)的各種姿態(tài),在桂西北在創(chuàng)作的情緒,這些思考是一名小說(shuō)家之魂,也是一名普通人之魂。
《生在平用》同時(shí)又有著歷史時(shí)空的深度和地域文化底蘊(yùn)的厚度。作者在《師長(zhǎng)與摯友》中說(shuō):“每個(gè)人都有屬于自己的一條人生路,而作為一個(gè)愛好寫作的人,我的路無(wú)疑是用書作為墊腳石,作為階梯,從遙遠(yuǎn)的桂西北一直鋪陳到遠(yuǎn)地他鄉(xiāng)”。作家黃佩華出生在平用,成長(zhǎng)在平用,他對(duì)平用厚重的筆觸去記錄歲月的沉淀,字里行間感恩壯族文化的孕育與滋養(yǎng)。世間所有的修行,莫過(guò)于悟道(發(fā)現(xiàn))且又能精準(zhǔn)地布道(表達(dá)),“向哲學(xué)要發(fā)現(xiàn),向文學(xué)要表現(xiàn)。”(蔡飛躍語(yǔ)),他用作家獨(dú)特的眼界去觀量,用心去創(chuàng)作,書寫家鄉(xiāng),書寫壯鄉(xiāng)的山山水水,讓原本文化底蘊(yùn)不濃厚的壯族小寨子蕩開枯朽再現(xiàn)新綠。所以,黃佩華的散文是他個(gè)人的超越也是作者情系故土、不忘初心的博大情懷的超越。基于此散文集《生在平用》是一部值得珍藏的散文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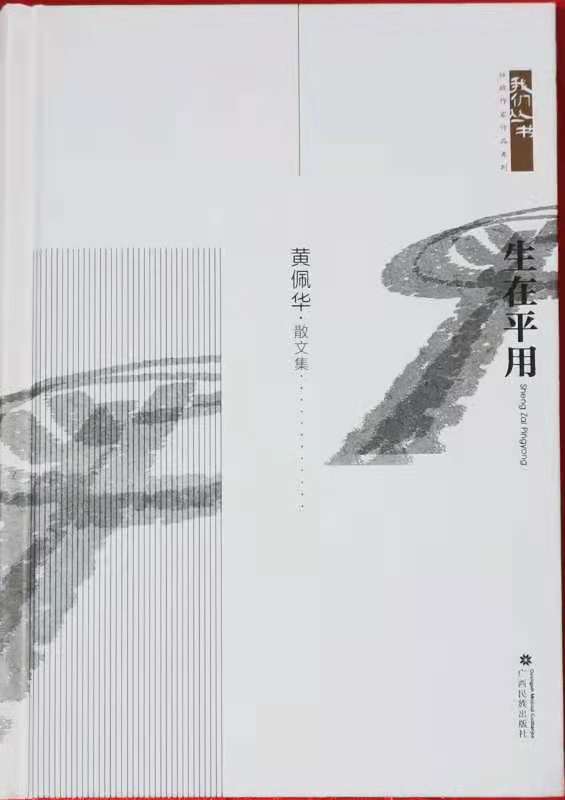


 純貴坊酒業(yè)
純貴坊酒業(y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