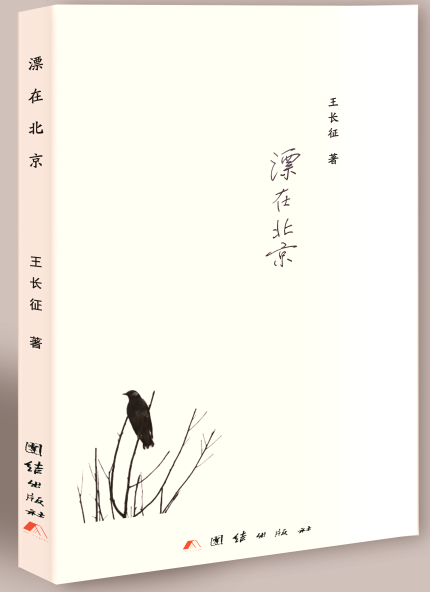
清晨與傍晚,隨著奔波的洪流,看一輛輛汽車、自行車、電動車,順著一條條或寬或窄的道路涌動向前,在地下,地鐵網路同樣載滿無數忙碌的面孔熙來攘往,竟莫名地想起讀過的王長征的詩集《漂在北京》。
《漂在北京》是王長征的第三部詩集。較之前的《心向未來》《幸福不期而遇》,《漂在北京》給我的記憶更深刻,準確地說,收入《漂在北京》的詩,更觸動我內心,使靈魂自動地安靜下來,平復有些紛雜的情緒,進入王長征營造的世界,心甘情愿地做他的世界的漣漪。
王長征每一部詩集,僅從詩集的書名而言,想必每一個讀者都和我一樣,能感覺到詩人對未來的無限憧憬,對幸福的希冀熱望,對事業的樂觀堅守。當無限憧憬、希冀熱望、樂觀堅守合在一起,毋庸置疑就是我們生存的時空中的生命之光。
二千多年前的希臘哲學家亞里士多德認為,只有在光中才有顏色,而黑暗則是無色的。我認為,詩就是世間萬物的光,因為詩,我們發現了世間的美好和丑陋,發現了生命的感知的冷暖。于某種意義上而言,詩是生命的孿生兄弟,并肩書寫了人類的燦爛文化。
《漂在北京》的“漂”字,絕非是一個異鄉人于某一個城市的專屬動詞。我們所有人,無一不是“漂”著的,漂在城市也好,漂在異域也罷,都是漂于世間的,漂于人類根據自身認識而設定的這一時間、空間之內。
同樣是漂著,王長征內心的豐沛,使得他的目光也變得更多維。他能看到“露宿街頭的孩子/手中攥著發濕的硬幣”,他能聽到“城中村‘飄出’贊美詩”:“他們是衣冠不整/流浪城市/被排斥的漂泊者……/手捧《圣經》/贊美自由高貴的靈魂”,當他看到溽暑中“睡在路邊的農民工”,他寫下“請你放輕腳步/不要驚擾/這些吧房子蓋得最高/卻住在最簡陋最低矮板房的人們”。當他看到“一位乞丐老婦”迎面走來,雖“選擇視而不見/怕被偽裝欺騙”,卻又由此而“憶起埋在鄉下麥田的親人”……當然也許這些都與他的職業有關,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歷史,自己的故事,自己的期許,而我們卻沒有理由沒有必要而以某種方式去窺探去挖掘。王長征在生活中、工作中遇到的人和事,借由他的看似無關痛癢的不經意的詩句,展現在讀者眼前的是活生生的、有血有肉、有苦有樂的多彩且五味雜陳的生命圖景。他用他獨特的云淡風輕看似偏于紀實的語言風格,帶領我們一同邂逅了他們,去感受“這些喪失激情的尋夢者/這些迷茫而憔悴的年輕人”的遠離故土,漂在繁華都市的萬般情愫。他用他的詩,把讀者拉進了他的生活空間,和他一起體味更多的生存意義。
生活是尋常而瑣碎的,在王長征的一首詩里,他寫道他“疼痛的手指”——“這是我握筆的手指/這是我寫詩的手指……我使勁扳著/自己疼痛的手指/使他們昂首挺胸/痛苦由我默默承受”。我想,疼痛的不只是他的手指,更有他善良敏感的內心。他有著和他詩中人物同樣的悲喜,也進一步地有著對漂泊境況的思考。也許無用,也許無奈,可當某人或某事觸及內心的時候,人是會不由自主的思考的。我們都會如此,只是并沒有將這種稍縱即逝的略顯深刻的思想記錄下來。
王長征是漂在北京的觀察者、創造者。北京這座古老的現代化都市。讓多少北京的土著也心存各種無奈的怨艾,讓更多的異鄉追夢人,將手捧著的夢中的愿景,在漂于此的歲月中,一次次地親手碾碎。王長征用一雙詩人的眼睛喚醒了生活的豐盈,即便在“難熬的寂寞”中,他也能“寫下燥熱的詩句/學習孤獨的生活”。這些詩,不是他刻意雕琢出來的,而是他自己內心深處的田野中生長出來的。他眼中的那些愁苦,那些掙扎,那些玩世不恭,那些無常,那些情欲和迷醉,都存在于真實的生命中,纏繞在每個人的命運里。而這些短暫的情感潮涌,在歲月里,慢慢地沉入每個人的生命之河的河床。
王長征的詩,會給讀者帶來沉默的剎那,繼而引起思索,世間萬象在他的詩中,無一不是源于他對生活的鐘情,無論多么艱難多么庸常,都是王長征用一顆詩心撞擊這個世界,在撞擊中迸發出絲絲領悟。他所秉承的質樸的詩藝,使真實的生活更真實更有溫度,也使他在異鄉漂泊的小,變成群體的與現實和命運抗爭的力量。
王長征快遞給我《漂在北京》的詩集的時候,是在今年的3月,正是新冠病毒瘋狂肆虐期間。春節前從北京回到老家安徽阜陽的王長征,由此不能按時返回他在北京的工作崗位。我打開快遞時,先想象著他在安徽阜陽的種種不安和焦躁,卻在翻開他寄來的詩集時猛然意識到:我的擔憂的無稽。詩集扉頁上是王長征的毛筆字,墨跡似乎未干:“風采三秋明月/詩意萬里春光”,看似簡單平淡的12個字,不是賣弄,不是套話,不花哨浮夸,而是透露著《漂在北京》作者的心路、心跡和心境,是看待這無常世間的淡然和多情,是他的純凈性情的悄然綻放。使我對這位年輕的90后詩人刮目相看。
《漂在北京》封底印有已故臺灣詩人洛夫對王長征詩歌的評價:“從王長征的詩里,我讀到他的根植于內心的鄉愁和善良,讀到了詩歌的骨頭和血脈,肝膽與魂魄,讀到了一位熱情洋溢的詩人自信與坦然,瀟灑與豪邁。”
依我看來,洛夫的話存在著些許缺憾——洛夫先生的為王長征的“畫像”是根據詩作,寥寥數筆,又想面面俱到地概括,便有了“應付”之嫌,忽略了王長征作為90后中國年輕一代所處的時代和這個時代孕育了王長征的詩句這一大背景,忽略了年輕一代中國詩人的文化從容和自覺,以及內心的細膩和敏感、孤獨這一特殊面貌。
《漂在北京》有一首題為《一位詩人》的詩,是這樣寫的:“他喜歡傍晚在附近的校園散步/捧本詩集認真閱讀/或尋找草叢里沉默的鵝卵石/充分享受這平靜的孤獨/與一棵樹對視/同一朵花交流/某個時刻面對泥土悄悄細語/不再理會生活的煩惱/眼睛如透明的鏡湖/他是這座城市河中一葉浮萍/漫無目的飄來蕩去/自從發現這幽靜一隅/再也不愿意隨波逐流”。
這“一位詩人”,不是別人,是王長征真實的“我”。無疑,《一位詩人》是作為90后年輕一代、作為這瞬息萬變不分晝夜忙碌著的時代的詩人,放下腳步短暫歇息時內心的獨白,或者說是內心世界對守望自我的一種堅持、一種“逃避”、“任性”式的剖析和思考。暫短歇息之后,他們又將以陽光般的笑容出發,去面對激烈甚至是殘酷競爭,去面對競爭中不可預測的困難、困擾、困惑。詩人王長征善于通過“與一棵樹對視/同一朵花交流”,在一切矛盾中自我紓解并釋然……
誠然,陽光般的笑容,不是王長征專有的。但從王長征身上,透過他的詩作,我們對接力中國詩歌的年輕一代詩人充滿期待和敬意。無論各種文化以什么樣的方式紛至沓來,他們以自己的熱愛,佑護著流淌了數幾千年的中國詩歌血脈,默默地傳承,發揚光大著,生生不息著。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