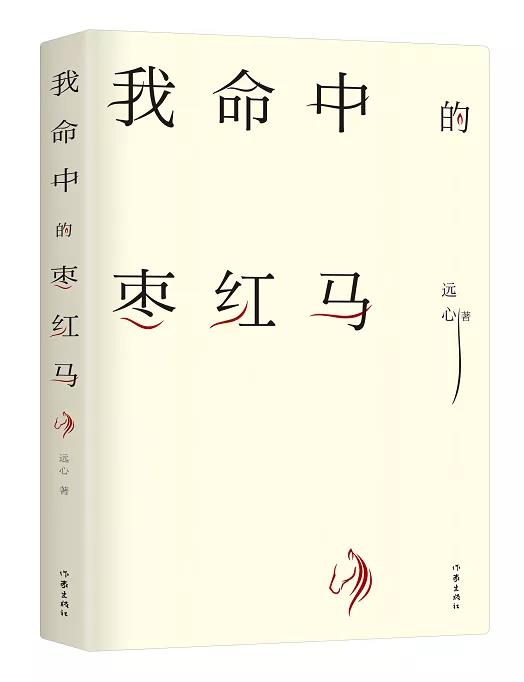
脫韁的蒙古馬
——讀遠心詩集《我命中的棗紅馬》有感
作者:土牛(江蘇)
或許,她就是草原的一匹野馬;或許,她就是象征自由的莽莽草原。
日前,收到遠心詩集《我命中的棗紅馬》,讀來不免有了這樣奇異的感覺。詩者,志之所之也。這本2020年中國作協重點扶持項目的作品,2021年8月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是一本以蒙古馬意象貫穿始終的游牧文化專題詩集,將一個草原兒女生活的場景、詩情、夢幻交織著帶給我們,靈性的文字,神性的思考,淋漓盡致展現的游牧文化,渾厚粗糲凸顯的西北風情,在一首首史詩式歌抒的片段中,引領著奔騰出別樣的生命體驗與感動。
認識遠心,是她離開生活二十七年的內蒙古高原轉戰江南開啟新征程之初。我們是魯迅文學院長三角中青年作家高研班同學,她性格熱情開朗,喜與同學小聚,酒品人品俱佳,如癡如醉高歌的天籟之音,常把大家帶進美麗的大草原。從詩集一百一十六首詩中,更充分體現了內蒙古的敦實豪放,赤子之心的遼闊情懷,呈現出集生態自然、寧靜純凈、清新雋永特質于一體的獨特詩風。
故鄉是親親爹娘一樣的叫喚。它能呼喊出美,呼喊出痛,呼喊出醉。作為蒙古草原長大的遠心,對內心擁抱的故土表現出的愛是極其厚重與癡迷的:“這就是我的土地,我的蒙古高原/八百年城墻飲醉了額爾古納河水/八百年屹立不語的科爾沁部敖包山/今夜,將我收攬入懷再沉睡千年”(《這就是我的土地》)。在草原,愛象征著博大遼遠,愛象征著奔跑狂野,愛象征著高亢嘶鳴。遠心原名趙娜,她用了這樣的筆名,似乎也昭示著草原兒女與眾不同的愛。這種游牧歷史滋養的文化,這種自然生存構筑的規則,潛移默化地給了詩人源源不斷的創作激情,以及對美好愿景朦朧曼妙的暢想,并借助熟悉事物與生活場景呈現出來:“來自科爾沁,科爾沁草原的風/風中奔跑的小黑馬/像頑皮的小駝羔,小狼崽,小駱駝/黑黝黝地拱我的額頭/又轉身跑去,把雄樹的楊花喚醒/一場楊花雪/小黑馬對著陰山嘶鳴……”(《科爾沁小黑馬》)。顯然成長在草原的記憶,一切和諧美好,小黑馬、小駝羔、小狼崽、小駱駝,有玩伴的深厚情誼,有風跑的歡聲笑語,有向往憧憬的嘶鳴,從而構建出一個并不單調妙趣橫生的純美王國。
詩集分六輯:《這就是我的土地》《如此雄偉的盛年》、《等待蒙古馬群》《趕著白云的走馬》《馬頭琴的嘶鳴》《寓言像一匹野馬》,都是詩家行吟草原,在內蒙古天大地大的家園,馳騁心靈與夢幻之間,自由意志、獨立精神最好的抒情與釋放。
家是草原,草原是家。應該說,草原養育了蒙古人,蒙古人帶給了茫茫草原勃勃生機。這種看似緊密邏輯關系的存在,放置到廣袤天地,又力顯出蒼涼、蒼白與空蕩。而詩人眼里的溫暖,往往超出普通人的想象:“到千里之外的敕勒川/一團耀眼天火/點亮蒙古包無邊的蒼穹/藍色蒙古高原,云河浩蕩/在燃燒的地平線上緩緩升起/應該打馬遠行久不歸的蒙古人/暮色里的背影無限延長……”(《暮色·背影》)。這樣原本單調凄涼的畫面,在這里成了攝影師抓拍的神來之筆,直抵人心柔弱處,美的陶醉,美的震顫,美的神往。這種不可思議的荒涼美境在詩篇《祖先的河灘地》又是另一番情趣:“那匹從阿爾泰山飛馳而來的神馬/眼里飄雪,落在克什克騰西拉木倫河北岸/一片老榆樹林和綠地的伊甸園/青春的叫喊在這里飄蕩……”
一首首激情澎湃的詩讀下來,感慨生命已融入了美麗的內蒙古大草原。而放牧的心仿佛成了脫韁野馬,草原成了無疆之域,伴隨詩人的詩情飛揚,伴隨風俗人情的歌舞飛奔。我們沐浴詩的世界,靈魂也接受著神圣洗禮:“蒙古人跨上上天賜予的神驥/奔流的河流才能泅渡流浪者”;“當我重返西拉木倫/在河水的濤聲中等待蒙古馬群/馬群在等待我//我命中的棗紅馬,閱盡大山大河大風暴/它是馬群的頭馬”……
馬是草原的驕傲,是追求,是力量,是速度,是自由,是風,是靈魂……在詩集《我命中的棗紅馬》中,棗紅馬或許就是詩人的全部理想,或許也引申著更多含義等待讀者去感受:“我一直在這里等你,我命中的棗紅馬/曾經的黑被你眼底的風情鍍亮”,“任何嘶鳴都不能牽絆你/我只有歌唱,拉響馬頭琴的兩根弦……”。
一千個人眼中有一千個哈姆雷特,一千個人也會讀出棗紅馬的一千聲嘶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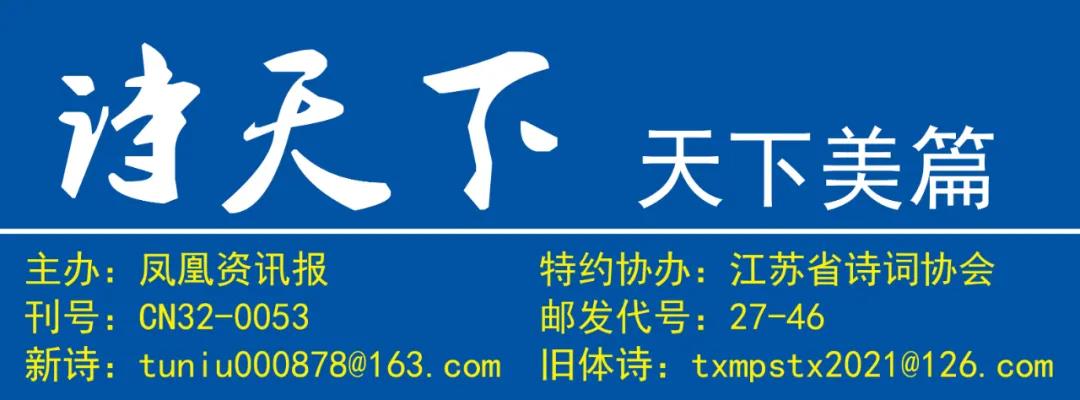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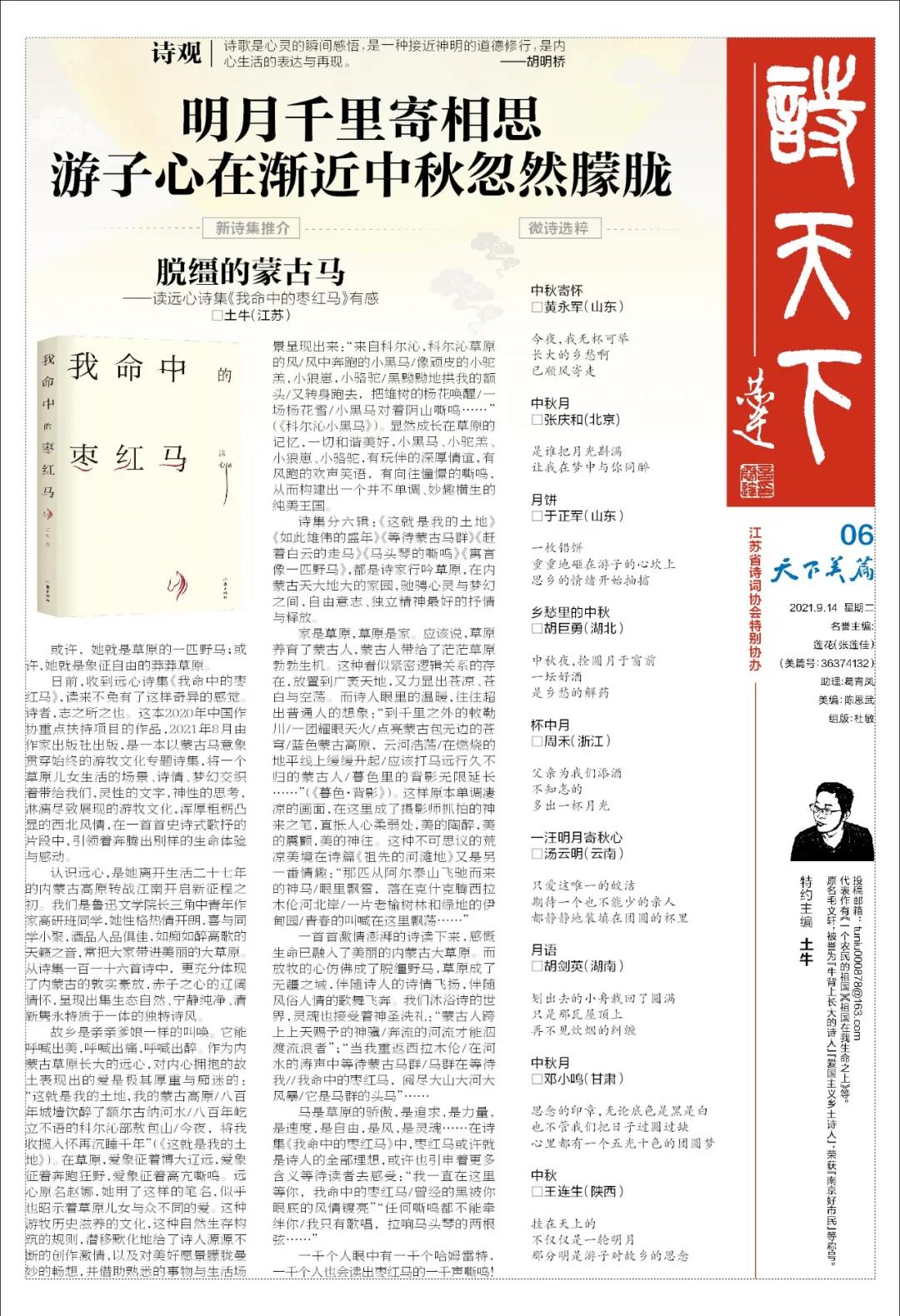
作者:土牛
來源:詩天下周刊
https://mp.weixin.qq.com/s/8pAFYtbkzT9VVTbwJc3Obg
來源:詩天下周刊
https://mp.weixin.qq.com/s/8pAFYtbkzT9VVTbwJc3Obg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