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山而居 田野作紀
——讀何萬敏的《涼山紀》
作者:沙輝
一
人之精神的生長,也如草木的生長,不僅有種子的產(chǎn)生等這樣的“因由”及發(fā)軔、發(fā)端,若要讓其茁壯,還需不斷對其進行培育。所以一種精神追求之結(jié)果的落實與獲得,甚至于一個觀點的取得與“立得住腳”,不僅有其種子之產(chǎn)生的存在和發(fā)端,更是不斷發(fā)酵、思考、培育和實踐的結(jié)果。何萬敏先生近年來成果不斷、著述不斷,也正是有其精神種子之存在和發(fā)端并不斷“培育”的結(jié)果,是他有“精神”生長和“奔跑的方向”與他的此種精神追求相互契合的結(jié)果:事物都有著內(nèi)在的因果、必然聯(lián)系。
何萬敏生長于大涼山,曾游學(xué)于重慶、求職于成都,后來由于某種精神的“感召”回歸大涼山。我認為這是他的涼山情結(jié)和“涼山書寫”的精神根基和知識儲備,是他的初心、“使命”的依仗。生于斯長于斯,所以心心念念,所以義不容辭回歸,這是他不停地行走于大涼山的山水之間、溝壑之處的精神根源;而重慶、成都的學(xué)習(xí)工作經(jīng)歷,在我看來實為他從事非虛構(gòu)寫作的某些人生閱歷與知識的儲備,是他打開視野時的其中某一扇窗戶。不管重慶成都、還是涼山內(nèi)外,何萬敏到過很多地方,見過許多世面、接觸過許多文化藝術(shù)界的人,然后俯身家鄉(xiāng)甘為從事于涼山知識文化界的一個耕夫。
在我看來,對于大涼山來說,對于大涼山的文化知識界來說,有沒有何萬敏這樣一個既有才華又如此勤奮努力、孜孜以求的文化人,其意義和重要性是極其不同的。“涼山所幸有此一人”的說法我曾經(jīng)用來形容過某些涼山文化界“幕后人”一樣的人,但是絕對不超過三個人。其中一個就是我們今天要談的何萬敏。在涼山,可以說,我們不缺形勝的山川,不缺諸如詩歌、音樂、舞蹈等方面的“自我舒展”型的人才,但是我們?nèi)狈Σ⑿枰缓笕藛T一般做出貢獻的人,我們?nèi)狈ψ杂X、自發(fā)地把我們的大涼山的風(fēng)物、地理、人情及人文歷史、自然稟賦進行深刻記錄、數(shù)十年如一日進行書寫的人。
在文化多元化的當下,碎片化和圖片化、視頻化的淺閱讀趨勢日益嚴重,系統(tǒng)化、深入化的文字記錄越來越顯得“費勁”而趨于退化、蛻化;再者,文化的深度化、行文的系統(tǒng)化和深入化,提倡者、號召者有之,躬耕者、踐行者少之,在文字的深入性、系統(tǒng)性上“既當指揮員又當戰(zhàn)斗員”者更是日漸稀缺。何也?文字工作苦也,更何況是系統(tǒng)化、長篇化(相對碎片化、淺表化而言)的文字工作?何萬敏作為長期從事文化(文字)工作的編輯,不僅完成了稿件編審等“分內(nèi)工作”,還日月躬行,以“第一現(xiàn)場”“第一手材料”的方式,在不停地全面深入記錄“涼山”。
可以說,何萬敏,是一個把“描寫大涼山”作為“己任”和“使命”的人。
二
于是,繼《光閃爍在你的枝頭》《住在涼山上》《涼山故事》等“記錄涼山”的作品集之外,《涼山紀》問世了。
在我看來,“涼山紀”三個字體現(xiàn)出何萬敏的一種“野心”或者說一種深切的意愿,那就是盡可能深入和全面地展現(xiàn)涼山、記錄涼山——這不就是他一貫的本意和愿望嗎?
紀,義同“記”,主要用于“紀念、紀元、紀傳”等,《史記本紀注》索隱曰:“紀者,記也。本其事而記之”。《涼山紀》,就是涼山記、記涼山,就是“本涼山其事而記之”。
《涼山紀》以非虛構(gòu)這個文體為統(tǒng)攬,串聯(lián)起人文、風(fēng)物、歷史、地理、文學(xué)、藝術(shù)以及文字、語言、服飾等地方文化、地域征候,使之成為融文學(xué)性、故事性、傳記性、知識性、民族性、地方性等為一體的類似于地方志的雜糅性讀物。這本書內(nèi)容縱橫交叉、涇渭分明又錯綜交織。它的縱線是地方性歷史和時間,橫線就是串聯(lián)起來的地方故事、風(fēng)土人情、地域癥候。
《涼山紀》作為一部紀實的非虛構(gòu)作品,有效避免了宏大敘事的視角和手法,而是以第一手材料、第一現(xiàn)場的手法和視角,糅之以自我的考察、考證、思考和適時、適當?shù)氖銓懀_到有效、真實和藝術(shù)性記錄之目的,同時見物、見景、見人,有溫度、有發(fā)現(xiàn)、有見解。這是何萬敏一以貫之的文風(fēng)。
“物”和“人”永遠是讓一個地方立體起來的基礎(chǔ)和站立、起跑的“雙足”、“雙翼”。除了深入挖掘和梳理、記錄涼山歷史地理、風(fēng)土人情、物產(chǎn)資源以外,對于涼山人文景觀、文化藝術(shù)的跟進式、緊貼性挖掘、記錄和闡發(fā),是何萬敏的所好和一貫“作風(fēng)”。
《涼山紀》圖文并茂,作者精心選擇了一些非常有代表性和史料價值的圖片作為插圖收入書中。我由此產(chǎn)生一個想法:用聲光、視頻等方式把這部書的內(nèi)容逐一展現(xiàn)出來,這何嘗不就是涼山的一幅畫卷、一部鮮活的歷史劇和宣傳片!
相對于本職工作而言,這是何萬敏的一種“額外的收獲”。而很多有成就之人所取得的成就,差不多都緣自于這樣的“額外收獲”。你看許多作家,除了很少一部分專業(yè)作家,他們的創(chuàng)作時間差不多都是在完成本職工作之余擠出來的,他們的著述,差不多都是在完成自己職業(yè)方面的本職工作之余抽時間完成的——他們的收獲,都是本職工作之外的“額外的收獲”。這樣的人,都是熠熠生輝的人,都是在干好本職工作之外,獲得另一番成就、取得“雙學(xué)位”的人。
何萬敏,相山而居,田野作紀。我想,這不僅是一份熱愛,到后來,這更多的是一份責任、一種擔當:我們所做的事,我們所堅持著做的事,到后來,都變成了一種習(xí)慣、一種責任、一份擔當與使命;不管出于熱愛還是義務(wù),做的時間久了,使命感、責任感也就油然而生、相生相伴了。于是,自發(fā)的行為也就成為了自覺的行為。
由此,何萬敏不斷地行走在涼山的山水間、自我的紙筆和鍵盤上。他有時走進涼山的胸膛,有時踩在了涼山的肩膀;有時埋頭進入涼山的文化肌理,有時舉頭仰望涼山的歷史星空;有時他也跟著振臂歡暢,但他更多的是獨思與紙上耕耘。
何萬敏,伴山水而居、而行走,以田野考察作涼山之紀。字里行間,見出何萬敏的赤子之心、考察之身影、考證之用力和奮筆與疾書的艱辛與快意,同時也可見出他淵厚的才情、廣博的學(xué)識和數(shù)十年如一日的讀書、思考、創(chuàng)作之并行。
由此,也可見何萬敏于涼山、涼山于何萬敏的彼此依附、彼此水乳交融之情和彼此貢獻、彼此成就之情形。
三
一篇文章或者一部著作,作為作者之猶如培育花草樹木一樣生長、生發(fā)和培育出來的“物事”、精神產(chǎn)品,都是自有稟性、自有體征、自有體味的。或大氣磅礴、或細膩入微;或鞭辟入里、或情深意長;或辛辣潑皮、或耐人尋味;或居高臨下、或平實娓娓;或快意恩仇、或家長里短;或張揚、或內(nèi)斂;或明理、或見性……不一而足,就像人各有異,文也各異。
縱然題材相同、甚至是同一個題材,不同的作者寫出來,結(jié)果的面目絕對是千人千面,文氣自有區(qū)別的。就像一道菜,食材同樣,但因手藝、調(diào)料不同,蒸、煮、燉、煎、炒、燜等做法迥異,最后上桌的結(jié)果也大相徑庭,所以各篇文章文氣殊途、文味各異。比如,有的是歷史氣的、有的是人文氣的、有的是文學(xué)氣的、有的是學(xué)理氣的、有些是書卷氣的、有的是武俠氣的,等等,不一而足。
作為一部記錄性的非虛構(gòu)作品,《涼山紀》不是閉門寫作中的書齋產(chǎn)品,它是行走的產(chǎn)物,是行走出來的,是從山川、河流和人文風(fēng)土里“走”出來的。它是屬于地理學(xué)、人文學(xué)、歷史學(xué)、史志學(xué)和紀實學(xué)的,同樣也是屬于文學(xué)類、文化類和民族學(xué)類的。它可以用來瀏覽、也可以用來細讀甚至是研讀:它可以作為故事、游記甚至是類似于奇聞異趣的讀物瀏覽,更可以作為了解涼山這一方風(fēng)華寶地的地方志類讀物來細讀,還可以作為深入了解和研究涼山人文地理、文化歷史的學(xué)術(shù)性、學(xué)理性資料進行研讀、辨析。總而言之,作者已用行萬里路、讀萬卷書的態(tài)度和實踐以及捉筆而為的行動,完成了《涼山紀》這部旨在記錄涼山風(fēng)土人文的著作,由此,作者已然完成了自我的“使命”,至于讀者的或瀏覽或細讀或研讀,則不再屬于作者的考慮范疇了。
在碎片化、娛樂化閱讀和自我“放縱”、自我降低精神追求及精神消費要求的時代,眾生刷屏抖音、快手之類,以為自己活得很“現(xiàn)實”,離現(xiàn)實世界很近,實則是被現(xiàn)實拋在了背面,離現(xiàn)實世界很遠;那些默默耕耘的人,那些埋頭苦干的人,那些似乎不在現(xiàn)實“面前”的人,看似隱逸了,隱沒了,實則是被現(xiàn)實牢記的人,他們才是現(xiàn)實的主人、擁有者。對于碎片化、娛樂化閱讀和自我“放縱”、自我降低精神追求及精神消費,《涼山紀》及其作者是逆向的,也是一種反叛和糾正,它及其作者何萬敏,以文化探尋和考察的行走方式及文化學(xué)者治學(xué)的態(tài)度,以文化視角的眼光、深刻的思考、細致的考證、全面的記錄,深刻而生動地呈現(xiàn)出了涼山文化的一面、人文的一面,使《涼山紀》成為與碎片化、平面化甚至是歪曲化相截然的傾于系統(tǒng)化、深刻化甚至是權(quán)威化的一部涼山紀、涼山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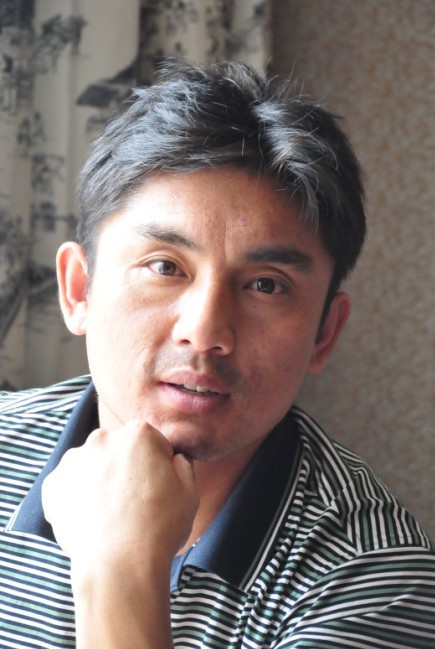
作者簡介:
沙輝,彝族,70后,中國作家協(xié)會會員,中國少數(shù)民族作家學(xué)會會員,四川省作家協(xié)會會員,涼山州文藝評論家協(xié)會副主席,鹽源縣作家協(xié)會主席。魯迅文學(xué)院第18期少數(shù)民族文學(xué)創(chuàng)作班學(xué)員。在《中國詩歌》《民族文學(xué)》《星星》《散文詩》《當代文壇》等發(fā)表詩歌和評論作品。著有“心”三部曲詩集《漫游心靈的藍天》《心的方向》《高于山巔隱于心間》,評論集《給未來以歷史的回音》、散文詩集《神靈的跨越》及人物訪談錄等作品待出版。


 純貴坊酒業(yè)
純貴坊酒業(y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