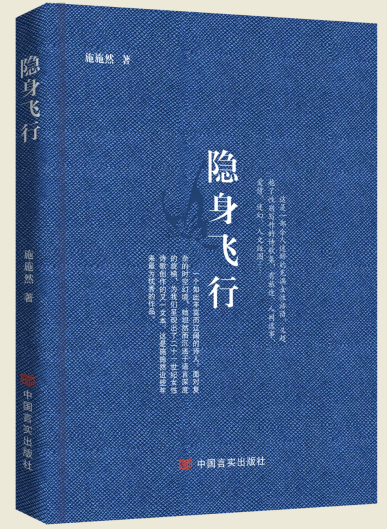
精神的漫游和語詞的飛翔
——評施施然詩集《隱身飛行》
作者:蒲素平
施施然是當下極具特色和品位的一個詩人,具有一定的標本評析價值。她的詩歌中有一種自我趣味的映照和精神的擦拭,精神的漫游,使她不斷探尋生命意識的飽滿和寫作的秘境,這從她最近版的詩集《隱身飛行》(中國言實出版社2022.1)可見端倪。
《隱身飛行》分《戒律》《想和你在愛琴海看落日》兩輯,收入詩人近5年創作的詩歌,這給我們研究、評析施施然的詩歌提供了一種便捷之徑。在《隱身飛行》中,展示出施施然探尋詩歌秘密之途的奇崛別趣,這一方面呈現出她詩歌品質的自覺構建意識,使她找到并沿著一條自我藝術之路不斷探索前行。其中,她一直試圖探尋到現代漢語如何跨過意義的容器,到審美深處開掘。另一方面,她以個性化的語詞,以細節的探幽,豐盈的表達和語詞陌生化的重新組合方式,使詩歌成為她傳達生命經驗的一種有效方法,并完成了自我審美意識的構造和張揚,使寫作成為與內心交流的一種有效工具。在《宿命》中,呈現出對精神的拷問和不斷探尋,寫作上使用了矛盾背反的形式,使這首短詩隱含的意義深長起來。詩中的“回歸和出走,圓滿和打破,建立和破壞,打碎和融合,砍伐和重鑄,愛和恨,廢墟和造物”等等,這些互相矛盾的敘述語詞迎面相撞,顛覆性的反差,突顯出了詩的內部張力,把原本熟悉的固化的詞義,向不同的方向延伸,呈現出一種強大生命力對沖。《戒律》寫的開闊而幽秘,深邃,詩人出筆從“女人著斑斕外衣,牛仔褲,骨肉均勻”開始,完成一種松弛的表達,一種自我視角的,生活化的再現。接著陡然是“她受夠了世間悲歡,漸漸斂起了/身體里的孔雀//僧人打赤腳,持蒲扇,穿紅袈裟/并列走來一路以僧伽羅語小聲交談”,這種巨大反差在輕松和不經意間完成,可見詩人對詩歌寫作的掌控力,而寫作的掌控力是檢驗一個詩人是否成熟的尺子。寫作絕不是一味的放,“收”在某種意義上難度更大,在寫到感情時處理法則是控制,而不是泛濫。把情感打碎重新發酵,讓情感產生新的情感。這一如艾略特坦言的情感規避:"詩不是放縱感情,而是逃避感情,不是表現個性,而是逃避個性。《死亡是一種教育》寫的極有趣味,有著個人化的情緒表達又有著普世精神的關懷,收斂中彌漫出淡淡的,個人化的,小的抗拒、干擾和懷疑。《死亡并不意味著消失》寫到,“清晨,萬物被第一縷秋陽照臨/施工隊的嗡鳴聲也如期/穿窗而進,不遠處/一座新的醫院正在半空中形成”,“更遼闊的生,分布在宇宙中/如同愛脫離了時間的結構”寫的干凈利落,有著現場感的自然,又有著向生命深出的探幽。
“海面上空翻滾的云,生命中曾壓抑的激情/像土耳其葡萄累積的酒精度/需要在某個時刻炸裂/相愛,相恨/再灰飛煙滅。原諒我,一邊愛你/一邊放棄你/鯨魚在落日的玫瑰金中躍起/又沉進深海漩渦的黑洞/那失重的快樂啊,是我與生俱來的/孤獨”(《想和你在愛琴海看落日》)。施施然是一個擅長寫愛情的詩人,由于女人與男人身體結構的差異性,造成女人比男人更加敏感和多思,她一旦調動了身體的內在感知系統,想象的豐富性和突兀感,陡峭的刺痛之美,令人驚嘆。在詩中,詩人手持情感的刀鋒沿著語詞的光芒,不斷地向內心的深淵處,向更深層行進,直至完全被吞噬,形成一種無法言說的深和空。唯美主義有一種觀點:“不是藝術模仿生活,而是生活模范藝術”,這觀點大抵可以用來說施施然的詩歌。“一切太激烈的事物/終逃不過戛然而止的命運/它也曾無辜地吞噬船只/將他們永遠吸納進海底/像那些我們錯手失去的人/被深埋在心底”(《印度洋》)。從某種意義上說,詩歌就是一種隱喻,這是因為詩歌不僅僅指向自己,也指向他人(他物)和他人(他物)背后所隱含的意義。詩人把強烈的情感,用平靜的口吻說出,把光不動聲色投進平靜的水中,使光在水中折射進一種相對應的客體之中,使主體和客體產生一種內在的相對關系,使詩歌的意義指向海洋中冰山。詩人華茲華斯說:“詩是強烈情感的自然流露,它起源于在平靜中回憶起來的情感”。生活中,人們說話的時候,常常通過語詞接近所指對象的意義,詩人則把視線放在語言本身和語言背后。也就說,日常說話說的是物理意義,重在實用。詩人重點通過語詞本身和語詞重新組合后產生的內在的新指向,形成多重意義,物理意義則不再重要。成熟的詩人一旦掌握一種詩歌的寫作密碼,就會一方面深挖,另一方面又堅決規避重復。施施然的愛情詩《風與愛情》《你是愛我的》《愛情》《鏡中》《枯山水》等等則是不斷地轉,通過一次又一次的轉,折射出身體和內心的不同層面的映像。“根據物質不滅定律/我們在世界上任何一個角落/吹到的風/都是同一場風”(《愛情》)。我記不請你的樣子了/但我不會忘記/有一些愛,在時間庭院里禪寂“(《枯山水》)。“我看見你柵欄里忍耐的豹子/眼中噴吐的怒火//讓怒火淹沒我吧,抓牢/進入,就讓不可控的一切塑造我//夜這么深,人世總是不長不短/我愿以刀尖,挑取蜜”(《鏡中》)。
西川說到施施然的詩歌時說:“換個角度說,她展示出了一股英豪之氣。而她本質上是一個細膩的,講究品位的人。”在《春日,陽宗海》《西柏坡》《袁》《只有空茫的大雪配與我對飲》《暖泉古鎮的兩位老人》《漢字之詩》《世相》《人類必將死于內訌》中,施施然詩風突變,安靜中突然出現一把大刀,準確果斷地砍向生活,盡顯剛毅、嘹亮之風。生活中的施施然,細膩、婉約,對品質有著極高的要求,她的詩歌創作曾經在這種精致、唯美上下過功夫,也形成了她一個階段的詩歌特征。近年來,她通過題材的拓寬和對生命體驗的不斷覺悟和認知,使自己在詩歌修行這條路上走的方正而快捷。優秀的詩人都是一個詩歌的覺悟者,有效完成了語言和生命體悟的組合,就是說語言和情感的體悟是不可分離的,是一個整體,無法說清是誰成就了誰。往往是一個人帶著自己的獨特體悟去尋找語言,尋找的過程就是詩歌產生的過程。或可以這樣說,生命體悟的呈現過程,就是詩歌產生的過程,而語言恰恰等候在那里。施施然的詩歌語詞特點明顯,漸成一種飛翔之勢,這也使得她形成自己詩歌面目的重要一環。本雅明說:“所有的語言都在自身中傳達自身”。“他們一言不發,在往來人群的注視下/歲月已將他們打磨成一對默契的齒輪//互相咬合,熟知對方的進退/當他們還年輕的時候/該較量的,已經完成”(《暖泉古鎮的兩位老人》),詩中有了前面的鋪墊,后面突然一句“該較量的,已經完成”,讓詩歌的意義產生無限歧義和張力。“我們沿著陡階,越往下走/越接近時間的深處”(《與女作家夜游吳堡黃河》)。“我們都沒說話,短短的沉默中/我們快速地走完了一生”(《雨中》)。清晰明了的語詞,素樸得不顯山水,然而,語詞行走中,在一個詩句的拐彎處,一轉身,詩歌卻突然拔地而起,飛于空中!這大約就是我們常說的,語詞的生命力從本質上,來源于使用者主體精神的激蕩和語詞本身重新組合產生的意外效果,從而成就了一首詩。
縱觀《隱身飛行》,正如書的封面所言:這是一本令人迷醉的充滿女性話語,又超越了性別寫作的詩歌集,有旅途,人間軼事、愛情、迷幻、人文版圖……
作者簡介:
蒲素平,中國作家協會會員,河北評論家協會理事,河北詩歌研究中心研究員,畢業魯迅文學院高研班31期。獲第三屆孫犁文學獎、首屆賈大山文學獎特別獎,第六屆中國詩歌發現獎等。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
————————————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