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城》專評
禁錮與飛翔
——淺談顧艷新作《樓下》
作者:李揚(yáng)帆
《樓下》是作家顧艷的一篇新作,發(fā)表于《長城》2022年第5期。“知識女性”一直以來是顧艷筆下的一類重要女性形象。在不久前的一篇小說《歲月親情》中,她書寫了一位知識女性在各種社會身份之間的糾纏,想要騰空卻發(fā)現(xiàn)自己被周身纏繞,羈絆她的不只是倫理親情、孝悌責(zé)任,更是在種種身份之間難以周旋的境遇,是個體的“自我”與“他者”的沖突與失衡。然而,在《樓下》這篇小說中,同為知識女性的安米則顯得自由豁達(dá)很多,雖然她也曾困頓于家庭瑣屑,但這篇小說中的女性形象就顯得從容輕盈很多了,旅美華文作家的身份不僅為顧艷小說提供了異域的發(fā)生空間,也賦予了她另一種話語和言說方式。
不同于《歲月親情》近乎寫實(shí)而鋪陳的散文筆法,《樓下》的語言風(fēng)格內(nèi)斂而克制,作家采用第三人稱近乎零度敘事的敘述視角,隨讀者旁觀了安米的生活片段。同是寫女性在家庭中的身份、角色,《樓下》將矛盾沖突聚焦在安米與丈夫?qū)O小陽構(gòu)成的小家庭,寫異國背景下看似尋常夫妻生活中的平靜與波瀾。
這部小說的特別之處,在于作家顧艷以敏銳的視角關(guān)注到了陪讀這一社會現(xiàn)象,以及這一群體的生活狀態(tài)、內(nèi)心世界,和由此觸發(fā)的波瀾與火花。小說中,安米赴美攻讀博士學(xué)位,丈夫?qū)O小陽辭去國內(nèi)的工作赴美陪讀,安米獲得了一份大學(xué)助理教授的教職,丈夫小陽則在家?guī)Ш⒆樱紶栐诰W(wǎng)上教教孩子們畫畫,沒有多少收入。國內(nèi)男主外女主內(nèi)的傳統(tǒng)家庭分工在安米和小陽家完全顛倒了過來。小陽身體不好,在家庭中沒有地位,時(shí)不時(shí)還要忍受安米的咄咄逼人的冷嘲熱諷,他只能默默承受著、忍受著,因?yàn)閷W(xué)不會英語即便出門也難以和他人交流。
顧艷在這篇小說中刻畫了一個經(jīng)歷著生活和精神雙重匱乏的男性角色,男子氣概在這個男性角色中消失了,小陽成為了一個社會邊緣人,在異國首都華盛頓,小陽是一個被社會和家庭拋棄的人,因此他常常自卑,正如他有時(shí)對安米說:“我曾經(jīng)是個身體虛弱的兒童,后來是個身體虛弱的青年,現(xiàn)在是個身體虛弱的中年人了。再下去,我這輩子就完了……”安米在家中對小陽頤指氣使,小陽在家中就像小媳婦兒一樣生活,頹廢、窩囊、不被重視、沒有地位。不平等的家庭地位、不一致的步調(diào)、失衡的夫妻關(guān)系使他們終究只能湊合著過日子,表面看起來波瀾不驚的生活,實(shí)際上暗潮洶涌,雙方都在一定程度上精神出軌。
安米的心思,被偶遇的小她十來歲的華裔年輕人“綠毛”牽動了,他年輕、搞怪,他的身份、職業(yè)對于安米來說是一個謎,綠毛的出現(xiàn)如同生活中的驚鴻一瞥,給安米的平靜乏味的生活注入了一絲新鮮感,安米需要的正是這種新鮮的活力。而孫小陽因?yàn)樵诩依餂]有地位、個人價(jià)值沒有得到充分認(rèn)可而對安米產(chǎn)生“報(bào)復(fù)心”。在這種報(bào)復(fù)心的驅(qū)使下,他碰到了樓下的華裔女婦人王莉莉,在幫王莉莉把書柜從地下車庫扛到客廳的過程中,小陽感受到了來美陪讀九年未曾有過的成就感。安米和小陽的這段婚姻,注定失敗的原因在于雙方的需要都沒有被滿足。在安米眼里,小陽成天無所事事、頹廢窩囊、身體虛弱,可以說是一無是處。在小陽眼里,安米仗著掌握家里的經(jīng)濟(jì)大權(quán)和大學(xué)教職的社會身份,對他頤指氣使、不留顏面,毫無女人性。兩人步調(diào)不一致,又缺乏相互尊重、崇拜與認(rèn)可,因而只是湊合著過日子,終究是同床異夢。
顯然,綠毛和王莉莉的出現(xiàn)只是加速其婚姻破裂的催化劑。陪讀這一行為本身就是以一方的無條件犧牲為代價(jià)的。然而和諧、平等的夫妻關(guān)系,并非一方為另一方犧牲,而是雙方在平等基礎(chǔ)上步調(diào)一致的良性發(fā)展。顧艷對孫小陽形象的書寫,實(shí)際上道出了陪讀這一現(xiàn)象中暗藏的家庭性、社會性危機(jī)。無論陪讀的一方是夫妻還是父母,陪讀者在異國環(huán)境下面臨的處境是相似的。對語言和環(huán)境的不適應(yīng)、放棄自己一部分家庭屬性或社會屬性、精神上的孤獨(dú)和不被理解。這類群體應(yīng)該被看到、被重視,他們的物質(zhì)生活和精神生活應(yīng)該被充實(shí),他們的存在不應(yīng)該是為了另一個人而存在,他們的價(jià)值需要得到發(fā)揮和肯定。
顧艷對這一題材的發(fā)掘,體現(xiàn)其目光的敏銳性。對這一群體的關(guān)注和書寫,表現(xiàn)出了作家對時(shí)代和社會的自覺介入。作為海外流動華人的一份子,顧艷對這一群體在異國的經(jīng)歷及可能面臨的問題有著切膚的了解,而作家的身份和知識背景又使她獲得了一種游離者的視角,使她得以與被敘述者保持一段審視的距離。因此,相比《歲月親情》,中篇小說《樓下》雖不乏想像性的虛構(gòu),其敘述顯得更為客觀而冷靜,作家通過這個故事意在描繪海外華人的生活狀態(tài)、心理狀態(tài),引起讀者對陪讀這一邊緣群體的重視和對這一社會現(xiàn)象的關(guān)注。
小說中的安米形象同樣值得關(guān)注,如果說顧艷在《樓下》中塑造了一個貧弱的男子形象,是對傳統(tǒng)男主外女主內(nèi)傳統(tǒng)的顛覆的話,女主人公安米的形象塑造同樣也是一個顛覆。小說中的安米雖是接受了高等教育的知識女性,但在家庭生活中,她說話刻薄、態(tài)度強(qiáng)硬,在家里擁有絕對的權(quán)威。家庭中心由男性傾斜到了女性,男女的家庭地位和價(jià)值分工,仍然處于一個失衡狀態(tài)。在安米與小陽的對話中,似乎不無幾分古代悍婦的樣子,全然失卻了現(xiàn)代高等知識分子該有的模樣。女子氣在安米身上被削弱了,從某種程度上說,安米是以扮演男性的方式來獲得了家庭的統(tǒng)治。
除了性格上女子氣的弱化,在外貌上顧艷也埋伏了一筆,她寫道:“來美國后,安米的穿著不是掉了一個檔次,而是很多。她越穿越隨意,大部分時(shí)間都是一條西褲,一雙平底鞋,再加上T恤和外套。”這一筆,標(biāo)志著安米在外貌形象上也逐漸弱化了自己的女性特質(zhì)。
然而,《樓下》的精妙之處,在于小說家并沒有將這個角色塑造得平面化,那些游離的部分,才是小說的微妙之處。比如,小說家緊接著寫道:“因此,她非常懷念上海生活的日子。那些曼妙多姿、豐姿綽約的上海女人,才是女人中的女人。”在類似的敘述中,主人公的形象逐漸立體起來。《歲月親情》中,“我”也曾是穿著旗袍豐姿綽約的女人,面對母親的衰老,“我”不禁感慨:“從母親身上,我發(fā)現(xiàn)一個女人的變化是不知不覺的。”在安米的回憶中,我們也不禁揣測,是什么改變了安米,使她變成了現(xiàn)在的模樣?是異國求學(xué)的艱辛、是人在客鄉(xiāng)的自我保護(hù)、是面對零零總總平淡生活瑣屑的疲憊,還是辛苦養(yǎng)家的經(jīng)濟(jì)重?fù)?dān)?小說中早已有了鋪墊和注腳。
小說的結(jié)局以安米和小陽的離婚收束,曾挑逗兩人生活之弦使其心生微瀾的王莉莉和綠毛,也終究只是萍水之交,漂移出了他們的精神生活。他們不過是日新月異的華盛頓生活里的一個過客。不同于《歲月親情》血濃于水無法割舍的親情和華夏民族深重的文化傳統(tǒng),作者將小說《樓下》的背景置于首都華盛頓,不僅是作家自身一部分生活觀察的再現(xiàn),更是在這個小說中表現(xiàn)了美國文化傳統(tǒng)中的無根感,城市人精神上的懸浮感和漂浮感,以及在快速發(fā)展的城市生活里,人與人之間的隔膜和日漸緊張的城市資源和空間設(shè)置帶來的幽閉感和壓力感。在這種語境下,人與人匆匆相遇,也匆匆告別。在告別了小陽痛快淋漓地哭了一場后,“她的眼前,忽然出現(xiàn)了一條五彩繽紛的彩虹”,她仿佛與過去的生活告別,一個嶄新的未來等著她去創(chuàng)造。小說的結(jié)尾,安米的事業(yè)蒸蒸日上,當(dāng)小陽給安米發(fā)出想要重歸于好的信號時(shí),安米回信道:“忘卻過去,就是為了更好的生活。”
如果說《歲月親情》中的“我”仍深深牽絆于親情、家庭與事業(yè)之間的纏繞的話,《樓下》里的安米已經(jīng)有了解開束縛、自我松綁與過去說再見的決絕和勇氣。顧艷立足于生活現(xiàn)實(shí),用或?qū)憣?shí)或虛構(gòu)的筆法道出了當(dāng)代女性正在面臨的一些難題和困境、正在承受著的精神負(fù)重,以及在此過程中的壓抑和扭曲。伍爾夫在一百年前就說過女性要有一間“自己的房間” 女性需要自己的空間和時(shí)間,女性的獨(dú)立方式從擁有一間自己的房間,即獨(dú)立而自由的靈魂開始,剔除掉女兒、妻子、母親、教授等社會身份,女性首先應(yīng)該做自己,這比任何事都重要。顯然,安米正在往這條路上前進(jìn)。
兩個小說雖立足于不同的社會現(xiàn)實(shí)語境,但都凸顯了女性在逆境里的智慧、堅(jiān)韌。《歲月親情》和《樓下》里的“我”,和安米不過是各自生活里默默承擔(dān)起生活重?fù)?dān)的個體。她們有各自的弱點(diǎn)和局限,她們并不完滿,但都立體生動。她們是生活著的人,對這兩個人物形象的塑造,體現(xiàn)了作家顧艷的敏銳和功力,同時(shí)也飽含了作家對女性該有的理想模樣和生活的追尋和探索。而在這種探索中,我們也看到了重新回歸寫作的顧艷,對自己九十年代以來的一貫風(fēng)格的承傳和接續(xù)。
正如作家自己所言:“從前對寫作的追求是一種智性表達(dá),在重新恢復(fù)寫作后,該以一種什么樣的方式來發(fā)現(xiàn)和表達(dá)呢?”這是她要思考的問題。在這兩篇近作中,我們也看到了顧艷的探索和努力,《歲月親情》中綿密鋪陳的生活寫實(shí)與《樓下》客觀克制的旁觀想象,讓我們看到了作家在處理不同題材時(shí)迥然不同的敘述方式,以及回歸后的顧艷駕馭多種寫作題材的能力。
顧艷的寫作以女性入手,又超越了女性敘事。除了對當(dāng)代女性精神生活的關(guān)注,《歲月親情》中對老年癡呆患者群體的關(guān)注和《樓下》對海外陪讀群體的關(guān)注,不僅反映了她對社會邊緣群體的關(guān)注,表現(xiàn)出了作家的社會意識和承擔(dān),也向我們展示了回歸后的顧艷在面對新的寫作現(xiàn)實(shí)的活力。
李揚(yáng)帆,浙江大學(xué)中國現(xiàn)當(dāng)代文學(xué)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海外華文文學(xué)研究、中國當(dāng)代詩歌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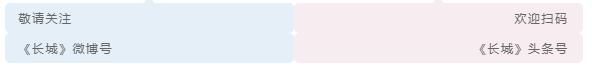

作者:李揚(yáng)帆
來源:長城
https://mp.weixin.qq.com/s/yFxIceP0Dwi_cB_BazhFpg
注:本文由顧艷推薦發(fā)布
——————————



 純貴坊酒業(yè)
純貴坊酒業(y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