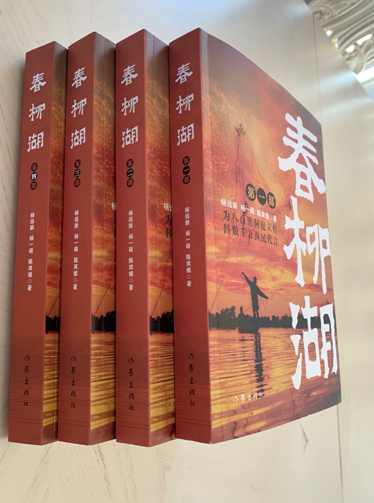
長篇小說《春柳湖》(全四部)
《春柳湖》講述閃爍人性光輝的婚戀故事
作者:丁萍
我兩次細讀240萬字的長篇小說《春柳湖》,最受感染的是書中主人公黃春江與蘆玉湖的婚戀故事。是一個偶然的機會,讓這對本不相識的少男少女在春柳湖的鯉魚灘上相逢。就像是命運特意的安排,或者是他們的前世本就是一對戀人,讓他們來人間一趟,重續前緣。
那是春天一個風和日麗的下午,少女蘆玉湖來到了鯉魚灘,她把風箏拋向空中,一邊奔跑,一邊放出手中拽著的絲線,風箏借著風勢越飛越高,像從湖邊蘆葦叢中飛起的魚鷹,翱翔在天際。看著風箏在她的操縱下,或左或右,忽上忽下的在天空中漫舞,姑娘的心一下被幸福的潮水溢滿,玲瓏般的笑聲灑向鯉魚灘,讓湖畔的柳枝低頭,令湖里的魚兒跳躍,她沉浸在無比激動的天地里。陽光也從云層中探出頭來,分享著她的快樂。
“歡樂總是乍現就凋落,走得最急的都是最美的時光。”因為她手里的風箏線拽得太緊了,突然間線斷了。這也好像對她暗示著什么。究竟暗示什么?她也說不出。做夢也不會想到他的生命旅途中會發生一場變故。那時無奈和沮喪一下鉆進她的心頭,爬在她的臉上,眼睜睜看著風箏飛離她越來越遠,飛向楊柳梢頭,飛向藍天中,急得眼淚流淌,焦急中四下張望。突然一個高大的身影從她身旁跑過,向風箏飛走的方向追了過去,眼看風箏就要越過柳梢,跌落進湖水,此時那身影高高躍起,一伸手抓住了即將飛走的風箏。姑娘懸著的一顆心落了下來,小跑過去迎著轉身而來的少男黃春江。兩人面對面地站著,彼此都沒有說話打破這陽光下美好的沉靜,她看他高大帥氣,英俊瀟灑,透著一股迷人的陽剛之氣。他看她亭亭玉立,婀娜身姿,如同眾荷之中盛開的一朵蓮花,一雙會說話的眼睛,清澈明亮,映在小伙的胸膛上。
至此,倆人暗生情愫,把愛的種子播進了心里。于是,一段曠世奇緣,一個凄美的愛情故事在春柳湖拉開簾幕,在洞庭湖上流傳。
人生的道路上無非是為了追求兩件事,一是為了事業,承擔社會的責任,二是為了愛情,完成生命的延續。
黃春江始終把對事業的追求放在第一位。他之所以成為春柳湖的重要人物,就是因為在他心目中,革命事業高于一切。他從春柳湖十二個孤兒中脫穎而出,一步步走向事業的巔峰。他的一生可謂是波瀾壯闊,跌宕起伏。先是在繼父黃經海的熏陶下走上革命道路,從春柳湖大隊的民兵班長做起,加入中國共產黨,擔任黨支部委員,最終挑起了黨支部書記的重擔。他一直帶領春柳湖漁民建設社會主義新漁村。他們在絕代堤、鯉魚灘、罶口筑堤挽垸。從無到有,從漁民日守河坡夜守灘,一家一條破爛不堪的漁船,吃住在船上,喝的是帶有血吸蟲病毒的疫水,經常挺著大肚子風里來、浪里去、捕魚為生。因血吸蟲病感染平均年齡活不過四十歲,在春柳湖的絕代堤上到處是墳塋,滿目蒼涼,埋葬了無數的怨魂。到春柳湖建起了漁民別墅區,結束了漁民一家一條船的歷史,岸上定居。建起了醫院、學校、公園、村辦企業、魚類科技館及魚類研究院。漁民走上了自主創新之路,實現了建設新漁村的夢想。
而黃春江與蘆玉湖的美好愛情卻出現了波折,沒有他的事業那么順風順水。他與蘆玉湖的愛情遭到了縣委工作組的反對,組長嚴東華直接干預。原因是蘆玉湖出身不好,她是舊社會漁霸徐銘烈的外甥女,與她結婚會影響黨的形象,而黃春江是黨培養的干部,根正苗紅。在那個特殊的年代,是堅決不允許的。這也就導致了黃春江與蘆玉湖的結局令人唏噓。 嚴東華為了斬斷黃春江與蘆玉湖的戀情,直接指派蘆玉湖與匡世宏結婚。匡世宏也是春柳湖的漁民,也是十二個孤兒之一,因為自身條件不好,一是他患有嚴重的血吸蟲病,導致個子矮小,肩不能挑,手不能提,二是家窮底子薄,用他的話說:張起一坨卵,撲到卵一坨。窮得巴鍋。他不想禍害別人。所以他一直處于單身。當幸福突然降臨,他又不得不接受。
就在匡世洪與蘆玉湖結婚的前夜,蘆玉湖與黃春江來到蘆葦叢中訴說相思之苦,情不自禁地擁抱在一起,也把她堅守了十八年的心交給了黃春江。用作者的話說:“那是一場天崩地裂的愛,那是一場摧枯拉朽的愛,那是一場排山倒海的愛,永遠鐫刻在兩人的心中。”
蘆玉湖和匡世宏結婚那天,她表面上顯得很平靜,內心卻翻江倒海,縱觀人世間,誰又愿意和一個自己不喜歡、不真愛的人生活在一起呢?她盡管身不由已,但她絕對不能讓愛情成為交易,成為犧牲品。倔強的蘆玉湖為了捍衛自己的尊嚴,守護自己的愛情,等參加婚禮的人剛剛散去,毅然決然選擇了服毒自盡。
嚴東華決定當天掩埋,匡世宏不肯,說什么也得守護她一夜。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因毒藥過期失效,蘆玉湖醒來了,重獲新生。她被匡世宏的行為感動,表示愿意與其結為夫妻。但是匡世宏理解蘆玉湖,知道她心里只有黃春江,一生只愛黃春江。他奉勸蘆 玉湖乘黑夜離開春柳湖,遠走他鄉,以后可能還有機會和黃春江一起雙雙入洞房,拜天地。蘆玉湖拜別匡世宏,消失在蘆葦深處。匡世宏復原棺材,將其安放在已經挖好的墓穴里,并象征性的立了一塊墓碑。
在蘆玉湖離去之后,黃春江經不住梅秋華的狂熱追求,兩人結為夫婦,夫唱婦隨,生活和美。只是每每在深夜,黃春江都會夢見蘆玉湖,并呼喊著她的名字。一年后,蘆玉湖產下一女嬰,這是她和黃春江愛情的結晶,也是她生命的延續。她為了讓女兒過上好日子,將其包好,悄悄放在了黃春江、梅秋華居住的屋檐下。這事驚動了春柳湖,漁人們爭相領養這個可愛的女嬰。可聰明透頂的梅秋華對女嬰的來歷心里有數。她當場給女嬰取名黃芬芳,收為已養。在以后漫長的歲月里,她給予黃芬芳的愛,遠超她親生的幾個孩子。
對于蘆玉湖的死而復活,黃春江蒙在鼓里并不知情。每年的清明節都會來到蘆玉湖的墳前,歲歲清明雨茫茫,看著長滿青草的墳頭,正像他的思念一樣茂盛。總忘不了她離別時眼中的淚,滴落在他的心上,忘不了她哀怨的目光,纏繞在他的心頭。
有時他總在想:那風箏為什么要斷線呢?如果不斷,就沒有我奮不顧身的為你追趕,也不會躍上柳梢為你把風箏拽下來,更不會傻傻地站在你面前,盯著你如水般清澈明亮的雙眸,讓你羞紅了臉頰,像陽光下盛開的荷花。如果是我轉身離去,如果我不和你說話,如果我不牽你光潔柔軟的手,你就不會離去而有這座墳墓。也就沒有那撕心裂肺的相思常掛心頭。也就不會像如今夜夜歸來,都在夢中呼喊著你的名字。我這孤獨孤苦的心,該安放在哪里?你又在何方?可知我的苦愁,你能感應到嗎?都說兩個相愛的人,心能連在一起而心生感應。也許過不了多久,我就會來陪你,讓我們的周圍開滿鮮花,讓湖畔的魚鷹來這里安一個家。我們一起看日出、看朝霞,看湖畔的楊柳青青,看遠去的白帆點點,看歸航的漁民滿心歡喜,走進他們新建的家。
黃春江對這段感情處在深深的自責和內疚之中,幾乎不能自拔。對此,梅秋華心里像明鏡似的有數,但她看破不說破,反而要求自己對黃春江傾注所有的愛。幾十年夫唱婦隨,堪稱典范。然而,就在他倆步入老年,距生命終點已經不遠的時候,也就是黃春江、梅秋華從定居美國的女兒黃芬芳那里探親回國之時,梅秋華斷然決定:與黃春江離婚。黃春江不答應。兒女們反對。可梅秋華誓不回頭。她寧可自己孤苦度日,也要在晚年成全黃春江與蘆玉湖的姻緣。而黃春江不知究里,離婚后他心里很苦,二段感情一次婚姻,就這樣離他而去,伴隨他的是漫長的夜與無盡的思念。 黃春江孤苦時總是會佇立在洞庭湖畔,曾經與蘆玉湖相會的蘆葦叢默默的流淚。他看著滔滔不絕的洞庭湖水,看著飛翔在天際的魚鷹,總是會想起她曾涉足過的地方,是否正留有她的身影、她的痕跡,或者她留下的一縷香風。
其實,自從蘆玉湖重獲新生,十月懷胎生下女兒黃芬芳托孤,就駕駛著一條漁船,時而生活在春柳湖周邊,時而生活在西洞庭湖上,那雙柔美的眼睛時刻關注著春柳湖,關注著她心里的黃春江。她始終相信老天給了她這段情緣,就一定會有重逢的時候。所以,她一直單獨生活,心里只裝著黃春江一人,癡癡的等待。每到日落都會站在船頭,伴著夕陽朝著春柳湖的方向,呼喊黃春江的名字。也會經常來到她與黃春江約會的蘆葦叢,重溫她與黃春江的過往,點點滴滴在心頭浮現。這種時候,她就會露出甜蜜的笑容和無限的向往。她也會托魚鷹帶上她的思念,在他行走的沿途,安放在他的身旁,讓他時時想著在這個紛繁的大千世界,還有一個人時時想著他,牽掛著他的一切。
也正是她時刻的關注,她知道黃春江離婚了,也正是她時刻的關注,感動了上蒼。這天,當黃春江午后騎著摩托車從縣城返回春柳湖,經過兩水一堤時,被他視為已出的義子柳水生,擔心自己販賣毒品的行為被黃春江告發,便使出毒招,將黃春江撞進了湖水里,以達到殺人滅口,保全自己的目的。隱藏在蘆葦叢中的蘆玉湖對發生的這一切看得真真切切,及時地救起了黃春江,幾十年的等待,終于與她朝思暮想的愛人在一條漁船上相會了。她感謝上蒼給了她這個機會。她把船藏進蘆葦深處,對準黃春江的嘴,嘴對嘴地做人工呼吸。黃春江發出一聲嘆息。蘆玉湖欣喜若狂,又哭又笑,發出大海般的呼嘯:“天啦!我的天啦!你終于把他還給我了!”
黃春江脫離了危險,四目相對,彼此心中燃起了思念已久的火焰,一下子回到了追趕風箏的年輕時代,倆人緊緊相擁而泣,任誰再也無法將他們分開。
這是一場曠日持久的愛戀,這也是春柳湖上美麗而凄涼的愛情故事。因風箏牽引,一條紅線貫穿整個作品,也因蘆玉湖救起黃春江而達到高潮。幾十年漫長的等待,他想她,他戀她。她也想他,她也戀她。他把感情埋在心底,默默地承受。她把感情植于骨髓,苦苦的等待。幾十年,恍若一場夢,但又不是夢。這場三個男女的婚戀,有分有合,有合有分,分分合合,合合分分,無不烙下時代的印?,無不閃爍人性的光輝。可謂回味無窮。
2022年11月18日于長沙麓谷
 本文作者丁萍近照
本文作者丁萍近照
作者簡介:丁萍,男,59歲,湖南漢壽人,現在長沙市獵鷹駕駛有限公司工作,曾經在《滄浪》《桃花源》《小溪流》《主人翁》《星星詩刊》《湖南婦女報》等發表小說、詩歌數十篇。近期由“作家網”“正揚網”“走向”“資江文化”等平臺發布的評論《<春柳湖>給我靈感》《讀<春柳湖>給我情感》《淺嘗<春柳湖>的民間特色》《淺析<春柳湖>的愛情故事》,散文《我與<春柳湖>作者的文學之緣》,詩歌《在雨季》等,受到社會各界的好評。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