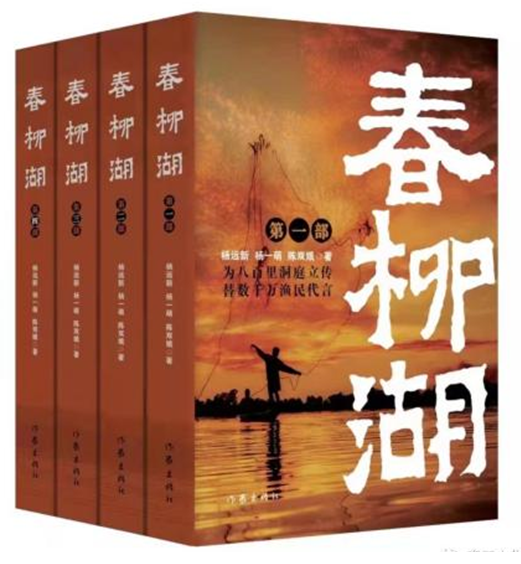
春柳湖演奏歷史的傳唱(評論)
作者:丁萍
長篇小說《春柳湖》(全四部) 翻開《春柳湖》,我在首頁記下了這么一段話:小說演繹了文字無法述說的過往,也延續了光陰灑在路上的痕跡。我很奇怪這書中的人和事,就像在我的記憶深處流淌了多年。我出生洞庭湖畔,飲湖水,食魚蝦成長,或多或少了解家鄉的歷史和家鄉的山水。當我品讀楊遠新、楊一萌、陳雙娥共同創作的《春柳湖》這部240萬字的作品后,讓我更加全面而又清晰地了解了家鄉洞庭湖的巨變進程。
一部好的文學作品,除了它本身的文化內涵,那就是文學作品的地方特色,包含純文字語言與方言俚語的對接,民間歌謠的傳唱,民間故事的演繹等等。這些都是民間文化的精髓,通過口頭的形式流傳下來,有的可以追溯到上千年的歷史,也代表了一個區域的興衰榮辱。讀《春柳湖》這部作品,就有很多來自于民間的典范,其中有一首痛心的民謠《養女莫嫁打魚郎》和一首革命歌曲《井岡山,多么妙》,反復出現于書中,二者聯系起來,就像一支時代進行曲,在洞庭湖的歷史舞臺上反復奏響,久遠傳唱。
每當春柳湖新漁村建設遇到困難,士氣低落,人心不穩時,漁民們就會唱響這首民謠和革命歌曲,以此來激發斗志,堅定信心。每當攻克難關,取得勝利,喜獲豐收時,漁民們同樣會唱響這首民謠和革命歌曲,以此來敲響警鐘,繼續奮進。我每每讀到這兩種場景時,眼淚就會忍不住地流下,心情久久不能平靜。心里也會情不自禁地哼起這首民謠和這首革命歌曲。
中秋節的那天,春柳湖的漁民本來聚在一起歡度節日,可誰知一場秋洪從天而降,打破了節日的氣氛,滔天巨浪奔騰而來,以輾壓一切的兇猛氣勢,摧毀漁民居住棲身的蘆葦棚,打翻捕魚的大小船只,卷走春柳湖上的一切生機。有逃得快的立在灘頭,看著漂浮湖面的家什,還有各種家禽家畜等隨著波濤沉浮遠離。有逃得慢的跌進湖水,在波峰浪尖上沉浮撲打,哭聲、嘶喊聲、浪濤奔騰的轟鳴聲響成一片,一幅凄慘的景象又一次在春柳湖上上演。
面對這突于奇來的洪峰,春柳湖大隊黨支部書記黃春江表現得極其沉著冷靜,一邊組織漁民群眾搶救生命及財產,一邊快速地劃著他的五斗小船沖進浪濤中,奮力劃向落水被卷走的兒童。他此刻的心里只有一個愿望,就是搶救生命,挽救生命,不讓一個生命從自己的眼前消失。
在他的指揮和帶領下,終于從波濤洶涌的洪水里把幾位失水的兒童救上漁船,但他們卻沒有一絲劫后余生的興奮,看著眼前的場景,就像有一塊巨石壓在每個人的心頭,讓每個人都感到無比的悲觀絕望。緊接著又一個噩耗傳來,一個年輕不到三十歲的寡婦方立珠被洪水吞噬生命,丟下了不滿三歲的幼童。剛為方立珠開過追悼會,把她埋葬在絕代堤的墳塋,又傳來漁民柳絮濤患急性血吸蟲病死去的噩耗。“船就是家,家就是船。天作蓋,地作被。水是命,命是水。得過且過,活一天算一天。”這就是當時廣大漁民生活的真實寫照。雖然推翻了吃人肉的漁霸,迎來了新社會,廣大漁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但洪水泛濫,血吸蟲肆虐成災,受各種條件的制約,讓漁民剛升起的一點希望又降到了冰點。這怎不令漁民感到雪上加霜,無一不流下辛酸的淚水。
面對一幕幕凄慘的場景,面對一張張絕望的面孔,黃春江心里五味雜陳,有一個聲音在他心里呼喊,那就是實現連改定居,走捕養結合,建設社會主義新漁村的道路。于是他用那低沉嘶啞的嗓子,領頭唱起了那首痛心的民謠:
娘呀娘呀娘呀娘,
養女莫嫁打魚郎。
漁霸吃人蟲吸血,
黃腫大肚擺成行。
日守河坡夜守灘,
十天九日餓肚腸。
男人大肚遭慘死,
孤兒寡母去逃荒。
全體漁民合著他的韻律一同唱響,唱出了春柳湖漁民辛酸的歷史,唱出了他們千百年來生離死別的命運,唱出了長期處在“退水一片荒,漲水淹屋場,瘟神冒送走,下水就遭殃”的惡劣環境。低沉而嘶啞的歌聲漫過了春柳湖的上空,越過了堤邊的楊柳林,壓過了洞庭湖洶涌的波濤。那是對命運的抗爭,那是對幸福生活的憧憬,那是一腔熱血的沸騰,那是從骨子里不服輸挺起脊梁的精神。
窮則思變。春柳湖漁民想改變,求改變的愿望極為迫切。黃春江身為大隊黨支部書記,抓住機遇,因勢利導,他帶領黨支部委員、黨員,走進蘆葦棚,踏上捕魚船,訪問漁民群眾,傾聽他們的心聲,特別是向老一輩漁民取經。最后確定了建設社會主義新漁村的道路。即在鯉魚灘筑堤建垸,捕魚和養魚相結合,實現漁民捕魚有船,居住有房的連改定居新生活。
既然確定了目標,就要付諸行動,光嘴上說而不行動,一切都是空談,有了行動才能達成共識,才能實現目標。擺在春柳湖漁民面前的就是抓住秋冬季節,湖水干涸,洞庭湖各灘頭都露出了水面的時機,搶時間筑堤建垸,同時對血吸蟲進行土埋、火燒、藥殺,全面徹底消滅之。每一個漁民都不會忘記,他們的親人挺著大肚,被血吸蟲病奪去生命的場景。特別是有的親人不堪忍受病疼的折磨,不愿連累凄風苦雨中的家庭,用一種極端的方式,即削尖了的竹筷,刺穿自己的肚子,結束苦難的生命。那是人生無望,走投無路的選擇。黃春江十二歲時親眼看著他的父親大肚炸裂,肚中腹水奔涌而出,他拼命的想把那薄如紙片的肚皮合攏,可怎么也做不到,只能眼睜睜的看著父親撒手離他而去。從此,他成為春柳湖的十二個孤兒之一。
要想把事業做成,達到目標,許許多多的困難和障礙擺在前面。特別是人的思想很難統一,有的思想僵化安于現狀,一家人一條船,繼續水上漂泊,過那種自由散漫慣了的生活。有的思想像墻頭草,左右搖擺不定,生怕干不好又遭受洪水的肆虐,沖垮堤壩,吃力不討好。面對這種情況,黃春江就想到義父黃經海教他唱的那首革命歌曲:
井岡山,多么妙。
濃霧迷鎖,山上望去好似大海的波濤。
井岡山,多么妙。
那時季,快槍只有兩百多條,
還有那一萬人拿著梭鏢。
我們的毛委員,
他有一肚子的革命道理把群眾教。
朱總司令,
一條扁擔,
二百里路去把糧挑。
井岡山,多么妙。
我們艱苦奮斗,才能夠有今朝。
井岡山,不要忘了。
黃春江和春柳湖的漁民每當遇到困境和挫折,都會唱起這首革命歌曲,每次唱起都會令他們熱血沸騰,激情澎湃,渙發起戰天斗地的力量。用黃春江的話說:我們不能看著腳背走路,要看得長遠一點,現在吃苦不光是為了自己,更是為子孫后代造福。井岡山時期的紅軍那么艱苦,在黨的領導和毛委員的帶領下,硬是憑二百多條槍和一萬多把梭鏢發展起家,逐步壯大,粉碎反動派的圍剿,長征二萬五千里,打擊日本侵略者,消滅蔣家王朝,解放全中國。他們一步步走來,不怕流血犧牲,用生命換來今天的新生活。春柳湖的困難和當初井岡山遇到的困難相比較,僅僅是滄海一粟,我們有什么理由畏懼困難,不努力向前拼搏,實現新漁村建設的宏偉目標呢?! 以黃春江為首的黨支部充分發揮戰斗堡壘作用,將春柳湖的漁民組織起來,團結一條心,擰成一股繩,在鯉魚灘上筑堤十二華里,建起了愚公垸,養殖池星羅棋布,旱地瓜果飄香,水田稻谷金黃,別墅連排接棟,醫院、學校、公園、各類加工廠、漁類科研所,應有盡有,形成了現代化的新漁村體系。
由此可見,是這首痛心的民謠,警醒春柳湖漁民痛定思痛,牢記使命;是這首革命歌曲,激勵春柳湖漁民不忘初心,方得始終;這是奮進的號子,這是歷史的傳唱。
2022年12月28日于長沙麓谷
 本文作者丁萍近照
本文作者丁萍近照
作者簡介:丁萍,男,59歲,湖南漢壽人,現在長沙市獵鷹駕駛有限公司工作,曾經在《滄浪》《桃花源》《小溪流》《主人翁》《星星詩刊》《湖南婦女報》等發表小說、詩歌數十篇。近期由“作家網”“正揚網”“走向”“資江文化”等平臺發布的評論《<春柳湖>給我靈感》《讀<春柳湖>給我情感》《淺嘗<春柳湖>的民間特色》《淺析<春柳湖>的愛情故事》《<春柳湖>講述閃爍人性光輝的婚戀故事》,散文《我與<春柳湖>作者的文學之緣》,詩歌《在雨季》等,受到社會各界的好評。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