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蘇軾詩學思想的九對關系
作者:鄒海燕
摘要:蘇軾是我國文學史上大的大家,詞開豪放之先河,文以“唐宋八大家”而著稱,書法乃“宋四家”之一,繪畫又是文人畫的代表,可謂是在詞、文、書、畫等方面才華卓絕、成果豐碩的一代之文豪。而且蘇軾一生所留下來的詩歌超過二千余首,在詩歌創作方面也有不少的佳作問世。雖然沒有專門針對詩學理論著書立說,但我們還是能夠從他的一些題跋、詩序、隨筆等作品中,總結出他的詩學思想。在此從蘇軾對文學的本質、文學創作構思等方面的觀點,梳理出蘇軾詩學思想的九對關系,并結合他的作品,作簡要的分析。
關鍵詞:蘇軾詩學思想;九對關系;文與道;認知與實踐;形式與內容;
導言
縱觀蘇軾一生對文學藝術的追求和實踐,以及在儒道釋三家思想的影響下,其文學創作和詩學思想主要圍繞文學的發展規律,以及傳承和發展歷史上對文學藝術創作相關理論,并對這些理論注入他自己獨到的見解和分析總結。在這里筆者歸結為他詩學思想的九對關系。一是“文”與“道”的關系,二是“道”與“藝”的關系,三是“出”與“入”的關系,四是“實”與“虛”的關系,五是“法度”與“變通”的關系,六是“自然之工”與“人為之工”的關系,七是“才情”“才氣”和“才力”的關系,八是“幸”與“不幸”的關系,九是文學與其他藝術的關系。這九對關系,涵蓋了蘇軾對文學創作的主客體的思考,形式和內容的認知,意境的創造,以及恬淡、意味深遠的審美意識等詩學理論的方方面面。他對于文學創作、藝術構思等方面的觀點也深深地影響著后世的詩學理論者,如楊萬里、王若虛等,尤其是他提出的自然之工和人為之工,“常形”與“常理”,“法度”與“變通”等觀點,對后來者批評江西詩派、前后“七子”等文學流派的詩學思想,對呂本中的“活法”說、王若虛的“元氣”說,以及嚴羽的“妙悟”說等皆有一定的影響。
一、“文”與“道”的關系
“文”與“道”的關系是我國文學史上,千百年爭論不休的話題,也是每個時代文人學者們,爭相要說明白、講清楚,卻又無定論的一對關系。“文”和“道”的關系,其實就是文學的“社會價值”與“審美”之間的關系。前者注重文學的社會功效,主張文學為社會政治服務,而對文學的審美價值持可有可無的態度。這樣的“文”與“道”關系的爭論起源于儒家對“詩言志”[1]的肯定,《典論·論文》[2]中對“文”的界定,以及儒家價值觀“三立”[3]說和司馬遷“發憤著書”實踐論[4]等文學創作目的,同時,又有人不斷地提出了“詩緣情”[5]等注重文學審美價值的對立觀點,所以便出現文學史上,不斷有呼喚“文以鳴道”[6]、“文以載道”[7]和主張“童心”[8]、“性靈”[9]、“自然”的“文”與“道”關系爭論和各種觀點的出現。
1.蘇軾主張文“有為而作”
受儒家思想和出仕的需求,蘇軾在“文”與“道”關系中,提出了“有為而作”[10]的觀點,即主張文的“社會功效”。他指出“詩需要有為而作”[11],反對沒有社會價值的詩文創作,比如“無為無補于世”。這里的“有為”和“無為”正是蘇軾詩學思想,對于文學社會價值,即“道”的肯定。
但是,蘇軾主張“有為而作”卻又并非是絕對肯定“道”的方面,他所謂的“道”與后世的“陳朱理學”的“道”有著根本上的不同。
理學家之“道”,完全忽略了文學審美功效,只注重文學社會功效,也就是陳頤提出的“作文害道”、“學詩妨事”[12],以及理學家們提倡的“存天理、滅人欲”[13]的有“道”無“文”的絕對化的“道”。
蘇軾的“道”乃是自然之道,也就是劉勰在《文心雕龍·原道》中所指的“道心”和“神理”[14],即萬事萬物的規律和相互之間的聯系。《日喻》[15]中指出:
南方多沒人,日與水居也。七歲而能涉,十歲能浮,十五能沒矣。夫沒者豈茍然者?必將得于水之道者。
此處的“水之道”變就是蘇軾對“道”這一概念的理解,也就是他對于“文”和“道”關系的認知,與道學家所謂的“道”的最大區別。也就是他主張的“有為”中,所要反映的“道”。
2.蘇軾提倡文“求物之妙”
在蘇軾的詩學思想中,除去文學的“社會功效”,同時并重的還有文學的“審美功能”。他在文學藝術的創造和構思中,提倡“求物之妙”[16],即在對萬事萬物的規律認知的基礎上,要有作者自身對于文學形象和藝術構造的“妙悟”。
“妙悟”一詞最早是佛語,大意是佛家弟子對于佛理的參悟,后來引入文學之中,并在嚴羽那里得到了發揚光大。其實,蘇軾所指的“求物之妙”也是對客觀事物認知的偶然感悟的審美體驗,也就是西方文論中所提出的“靈感”。靈感即是創作主體對客體的瞬間感悟和認知,主要在于主體感性的第一反應。蘇軾稱之為“妙想”,在他的《次韻吳傳正枯木歌》[17]中,蘇軾就明確提出了“古來畫師非俗士,妙想實與詩同出”。
“求物之妙”、“妙想”和“妙在筆墨之外”[18]主要是蘇軾對于文學藝術構思的一種方式,在其詩學思想之中,對于文學藝術技巧的論述還很多,比如第二要講的“道”與“藝”的關系,便是他對文學藝術的追求,也就是他對文學“審美功效”的肯定。
3.“文”與“道”關系體現在他的文學實踐之中
縱觀蘇軾一生,其文學實踐,皆沒有脫離他對“文”與“道”二者關系的認知。從他詩《和劉攽韻》[19]中“歲惡詩人無好語,夜長鰥守向誰親”,可以看出蘇軾詩學思想中對“道”,即“以詩為諷”,“有為而作”的詮釋。據清代歷鶚《宋詩記事詩》“明道雜志”條所載“蘇惠州以作詩下獄,再起。遂編歷侍從,而作詩每為不知者咀味,以為譏訕。”另記載蘇軾被貶錢塘時,在與好友潞公道別時,潞公說:“愿公至杭少作詩,恐為不喜者誣謗。”[20]而因為蘇軾是重“道”,也致使他多次遭到貶謫,甚至下獄危及生命。“烏臺詩案”[21]等人生變故,但卻并沒有改變他對文學“道”的認知。而他的詩作也大部分都體現了他的政治理想、人生抱負和對事物的認知。
另一方面是他對文學藝術構造的不懈追求。蘇軾對文學創作的“自然”之美,以及他對陶淵明詩歌所呈現的“淡雅”“悠遠”“韻味”的審美意識非常的推崇,尤其到了晚年,他寫了大量的和陶詩,詩中盡量追尋陶詩的“恬淡”“自然”之美。
舉蘇軾詩《和陶答龐參軍六首》并引[22]中的“種茶”一首來說明其追求藝術審美構造。
松間旅生茶,已與松俱瘦。茨棘尚未容,蒙翳爭交構。天公所遺棄,百歲仍稚幼。紫筍雖不長,孤根乃獨壽。移裁白鶴嶺,土軟春雨后,彌旬得連陰,似許晚遂茂。能忘流轉苦,戢戢出鳥昧。未任供春磨,且可資摘嗅。千團輸太官,百餅衒私斗。何如此一啜,有味出吾囿。
這首詩,蘇軾借用了陶淵明的《歸田園居·其三》[23]“種豆南山下”的藝術表現手法。詩題以“種茶”,全篇以發現茶苗、移栽種植、培育、喝茶為詩歌的演進軌跡,雖然是很平淡的一件小事,卻讓蘇軾寫出了他的詩味,關鍵在于前后兩對。詩人以“松間旅生茶,已與松俱瘦”開頭,交代茶苗生長的地方,道出了茶和“松”一般的品格,最后詩人寫到“何如此一啜,有味出吾囿”這一句又與前面遙相呼應,令人讀之意味無窮。
雖然,蘇軾刻意想要學陶詩的恬淡和悠遠,卻與陶詩的意境各異。即便遠離了“廟堂之高”,[24]但卻并不代表詩人真正做到了“居江湖之遠”。即便是他想要逃開仕途經濟,卻逃不開他已經形成的文學的“文”與“道”的詩學思想,這也深深地影響著他的創作。即便是“種茶”這樣的閑情逸事的詩歌,他也不忘把自己對于“言志”的意識添加進去。“松之瘦”卻并不能掩蓋其“高潔”,“一啜茶”,也能喝出“吾囿味”。
二、“道”與“藝”的關系
關于蘇軾“道”與“藝”的關系,主要是主體對客體的認知,以及在認知的基礎上轉化為文學創作的技巧之間的關系。所謂的“道”便是上一段提及的劉勰《文心雕龍·原道》中的“道心”和“神理”,即萬事萬物的普遍規律。而“藝”既是主體對客體的反映所具備的一種能力。曹丕在《典論·論文》中稱之為“氣”,[25]陸機提倡“緣情”、劉勰《文心雕龍·情采》謂之“情采”,[26]皆是創作主體所具備的一種應對客體的獨特藝術構造的方式和方法。
1,蘇軾提倡“有道有藝”
在《書李伯時山莊圖后》,[27]蘇軾指出“有道有藝。有道不藝,則物雖形于心,不形于手”。這里的“道”是指劉勰所說的“道心”和“神理”。創作主體即創作者對“道”的充分認知,能夠使其對“道”的附在體客觀事物了然于心,從而能夠為創者者提供文學創作的基礎。但是如果創作主體沒有掌握一定的藝術技巧,即蘇軾所謂的“藝”,就很難使其“道”呈現在文學之中。相反,即便創作主體有一定的技巧,即“藝”,也很難創作出好的文學作品,這就是蘇軾所說的“有道有藝”。
“形于心”和“形于手”,是蘇軾對客觀對象認知,以及將文學創作對象呈現在作品中的一種說法。在他看來,文學所構思的藝術形象,是基于創作主體對客觀對象認知的基礎上,也就充分地表明,他對于文學創作的認知在于寫實,但卻又很清楚地認識到,文學的寫實,和現實社會的實際,是不同的,需要通過創作主體的再次加工。也便是從“形于心”,到“形于手”的藝術構造的過程,而這個過程最主要的便是對于“藝”的把握和理解。
“有道有藝”,既是蘇軾對于“道”和“藝”二者關系的認知,同時也是蘇軾對于文學反映什么?文學構思的來源等問題的探討。
2.蘇軾主張“道”“藝”并進
蘇軾認為對于客觀事物的描寫和文學意境的構造,在于對于客觀對象的深入了解和全面掌握,也就是對客觀對象的充分認知。但在認知的基礎上,想要把所要描述的對象變成能夠打動人的文學作品,還需要創作主體,即作者在“藝”方面的用功。
他對秦觀文學創作的評價中指出“技進而道不進,則不可。少游乃技道兩進也。”這里的“技”,與上面提到的“藝”是同一個概念,有異曲同工之妙。如此看來,蘇軾很明確地認識到文學和現實生活兩者關系。
現代文藝理論認為“所謂藝術的真實,是以生活真實為基礎,通過概括、集中、提煉出來的具體生動的藝術形象,表現出社會生活的某些方面的本質和規律性。”[28]在蘇軾對于“道”和“藝”關系的認識中,我們可以看出,現實生活,即蘇軾的“道”,而文學作品是對現實生活的反映。同時蘇軾又指出現實生活反映在文學藝術作品中是需要通過“藝”或“技巧”來實現的。這種觀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現代對于文學來源于現實生活,但同時文學卻是主體對客體對象“技藝”加工的結果。
蘇軾詩學思想對“道”和“藝”兩者關系的認知,在另一方面也展現出他對文學和其他科學之間的認知,雖然沒有具體界定文學和其他科學,但卻從兩者關系中,區別了文學與其他科學。為后來者,在辨別文學和其他科學的爭論中,提供了一個有利的論證。
3.“道”與“藝”體現在他的文學創作中
在蘇軾的詩歌創作中,涉及很多的對客觀事物的描寫,從春夏秋冬的時令變換,到春花秋月、夏荷冬雪的感悟;有西湖白堤的楊柳依依,也有西湖和西子的相遇;嘆山河之壯美、惜晚照之余輝;借風雨之無常、念命運之飄搖等等,皆是詩人對萬事萬物了然于心,重“道”的結果。同時,詩人也通過自身文學素養和才力,把一首首看是寫景的詩,在他的藝術構思之下,展現出別樣的意境。我們還清晰地記得“竹外桃花三兩枝”[29]給人的早春萌動,難以忘懷“大江東去浪淘盡”[30]的蒼茫和雄渾。這些都是他對“道”和“藝”兩者關系的深刻認知之下,給我們留下的永遠感懷的美好詩詞。
在此舉蘇軾《和子由記園中草木十一首》[31]的最后一首詩歌,來作簡要賞析。
野菊生秋澗,芳心空白知。無人驚歲晚,唯有暗蛩悲。花開澗水上,花落澗水湄。菊衰蛩亦蟄,與汝歲相期。楚客方多感,秋風詠江蘺。落英不滿掬,何以慰朝饑。
詩人把秋天的景物凝結成為詩中的意象,野菊、暗蛩、空悠的山澗,以及靜謐、安然的小溪,這些是詩人形之于心,對秋天之道的認知。而芳心、時已晚、歲無期,楚客被秋風、屈原餐落英,皆是文人對得到皇帝賞識、感傷時光流逝、頌揚屈原的高潔品行的一些意象的截取,并把這樣的景和作者在“藝”方面的把握和貫穿,構造了一個別樣的秋景和別樣的情懷,讓悲秋喪時者與獨憐幽花者,以及倍感命運仕途不暢者,心生同感,引起共鳴。
三、“出”與“入”的關系
“出”與“入”的關系,是古代的哲學家對宇宙萬事萬物存在認知的一種方法,尤其是道家講求的“坐忘”和“心齋”[32]對后世文人在創作之中尋求靈感,達到一種空靈的狀態,尋求文學作品所展現出的一種空悠和化境的意境之美有著深刻的影響。在劉勰《文心雕龍·神思》[33]中,就很詳細地論述了想要收獲思維的愉悅,需要具備深刻的思想意識,就需要人之精神與物同游,達到神思的境界。劉勰提出“寂慮”和“悄焉”[34]的方式,也便是莊子所提出的“坐忘”和“心齋”方式的另一種說法。
1.蘇軾主張“靜”和“空”
“靜”和“空”是蘇軾對道家“坐忘”、“心齋”認知方式的一種繼承和實踐。他在《送參寥師》[35]中
明確指出“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靜空”是觀物主體清空自己內心所有的俗情俗事,達到道家要求的“坐忘”。同時,通過靜下心來,讓自己的心遠離躁動和不安,達到凝神靜氣的一種無我狀態,以待物入心,即道家講求的“心齋”。通過“靜空”的方式,從而達到“其神與萬物交,其智與百工通”[36]。也就是說蘇軾提倡“靜空”的思維方式,其目的是要達到深入萬事萬物內部,了解萬事萬物的基本規律,也就是前面所提及的“道心”和“神理”。只有對“道”了然于心的情況下,才能自然而然了解百工之間相互融匯貫通的地方,達到劉勰所謂的“旁通而不滯,日用而不匱”[37]的認知境界。“靜空”的方式,是蘇軾在對事物認知“入”方面的見解,也就是要認識萬事萬物,比如深入其中。
2.蘇軾主張“觀身臥云嶺”
蘇軾認為,要想“了群動,納萬境”[38]是需要主體進入“靜空”的一種“神與物交”的思維狀態,以“閱世走人間”進入其中,但同時也要“觀身臥云嶺”[39]從神思的狀態中走出來,方能夠使詩歌的創作達到一種“至味”的狀態。也就是上面提到的“形于心”到“形于手”的一種創作過程。當創作主體以“靜空”的狀態進入客觀對象,與客觀對象交相呼應,并產生深刻認知之后,作者還要從這樣的狀態中走出來,以主客相對獨立的方式,把自己的認知運用到詩歌的創作之中,從而使詩歌的味道達到極致。
如果只是進入其中,而不能走出來,就會像是蘇軾在《題西林壁》中所說的那樣“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40]深入廬山能夠讓詩人更加親密地與廬山接觸,但想要認識廬山,還得需要詩人走出來,離開廬山,借助詩人的一些“藝”的方式,才能夠真正成為詩人認知下的廬山。
3.“出”與“入”的關系體現在蘇軾的創作實踐中
“出”與“入”的關系,也是蘇軾對于客觀事物的認知和文學藝術構造兩者之間關系的一種認知,他用思辨的方式,把創作主體和客觀對象之間的聯系進行了形象的分析,同時,在蘇軾大量的寫山水、懷古、游歷等文學題材的創作實踐中,也很好地體現了思維到創作過程的經驗和感受,并指導他“出”與“入”的詩學思想認知的形成。
在此舉蘇軾《癸丑春分后雪》[41]這首詩,來與大家分享蘇軾對于“入”與“出”的認知。
雪入春分雀見稀,半開桃李不勝威。應慚落地梅花識,卻作滿天柳絮飛。不分東君專節物,故將新巧發陰機。從今造物尤難料,更暖須留御臘衣。
這是寫一種乍暖還寒體驗的一首詩,時令已至春分,但一場春雪來襲,讓原本有些鳥語花香的早春,變得沉寂。而這樣的春雪,在鳥語花香,春色萌動中更顯美麗,讓深入其中的人沉醉。詩人正是親身領略了這樣一場春雪的美景,方然用如此神來之筆地勾畫出這樣的一副春雪圖,簡練地抓出了雪中鳥語花香的消減,以及飛雪為春天增添的另一份美麗,來表達了詩人對春雪勝景的喜愛。詩人又把節令的自然變換,原本是可以掌握,卻又難料的認知,來道出“更暖須留御臘衣”,也就是即便晴天也要備一把雨傘,早做準備以防人生路上的變故。
四、“實”與“虛”的關系
我們這里探討的“實”與“虛”的關系,是指文學藝術創作中的“實”與“虛”,也就是文學審美范疇的藝術真實性的問題,以及創作主體對客觀事物藝術化構建的“虛”的問題。文學藝術的“實”是怎樣的一種實,虛構卻又是在什么程度上的虛,一直都是文學創作者所探討的問題。文學的虛實關系,在古代文論中,探討的人并不多,也沒有明確地探討它們之間的關系,只是在一些零星的有關文學“意象”方面進行了探討。而對虛實探討最多的是明清小說評論方面,也就是對史傳小說中“史料”和“文學創作”之間的探討。但“虛實”關系作為文學構思的基本因素,在古代的一些詩學思想中也可見端倪。
在古代文學創作中,詩歌和賦便是對“虛實”關系的最早探討,“詩歌言志”、“賦者陳事”,[42]詩歌是以“在心為志,發言為詩”[43]的藝術加工的過程,來對詩進行界定,展現了最初“虛”的狀態,而賦“以眼所觀”“按圖所述”來展現對客觀事物的描述,便是所謂的“實”。至后來,受儒道兩家的哲學“虛實”范疇的影響,又有“自然”以為實,“意”“神”為虛,“窮形盡相”[44]為“虛實”關系的認知等,皆對后世文學在美學“虛實”構造之中,有一定的影響。
1.蘇軾的“常形”、“常理”觀
蘇軾所謂的“常形”和“常理”觀,是對客觀事物外在和形態和內在規律的一種認知。他認為:“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水煙云,雖無常形,而有常理。”[45]從他的論述中,“常形”、“常理”都是客觀事物實際的存在,也就是在文學創作中,所要描寫的客觀對象的屬性,抓住了事物的“常形”“常理”,就能夠對事物的形態和規律了然于心,也是每一位關注現實的作家必須具備的一種能力,當然也是一位高超的畫家所要具備的能力。
在《凈因院畫記》中,雖然蘇軾提出“常形”和“常理”是對繪畫這種藝術的論述,但縱觀蘇軾的創作和對詩學理論的見解,也就是文學與其他藝術之間有著相同之處。很多時候他都以繪畫等藝術來討論文學創作的各種方法,“常形”和“常理”用在他的詩學思想上,便是對“實”的論述。
2.蘇軾的“寫生”與“傳神”觀
在蘇軾《書鄢陵主簿所畫折枝二首》中,[46]他指出“邊鸞雀寫生、謝昌花傳神”。蘇軾把繪畫這種藝術手法,分為了“寫生”和“傳神”兩種,即“寫實”和“寫意”。歷來我國國畫以大寫意和小寫意為繪畫藝術創作的主要手法,而“寫實”的工筆畫,并不被一些畫家所看好。引入文學創作之中,“寫生”是對客觀事物的真是描寫,而“傳神”這是在“常理”基礎上的虛構。
比如蘇軾的“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47]雖是提畫詩,但也是春景的描寫,以“移情于景”論之,是把情放在客觀的景物之中。但在筆者去蘇軾老家實際考察之后,用“移情于景”來評論這首詩,并不恰當,而真正的是“移景于情”。在蘇軾的老家的確是“竹林外有桃花”,而緊挨著的是一個池塘,但是卻并看不到江河之類的。而蘇軾所見的惠崇的畫,和他對家鄉竹外桃花及池塘春水的景物的印象,把“春江水暖鴨先知”這一組和前一組意象的結合起來,是詩人“移景于情”的一種創作方式,也是詩人“傳神”即“虛構”的一種創作方法。
3.“虛實相生”構成了蘇軾詩歌意境構造的提煉與集中
對于如何把握客觀對象和主觀創作的藝術需求,蘇軾的“常形”、“常態”觀,以及“寫生”和“傳神”觀,非常客觀地對二者進行了論述,也構成了他詩學思想中“實”與“虛”關系的基本認知,并呈現在他的文學創作實踐中。他對于意象構造的獨特性,在于他詩中同種意象的提煉和集中,給人一種化境的美。
下面來看蘇軾詩《舟中夜起》,[48]他所選取的意象和眾意象所構成的意境。
微風蕭蕭吹菰蒲,開門看雨月滿湖。舟入水鳥兩同夢,大魚驚竄如奔狐。深夜人物不相管,我獨形影相嬉娛。暗潮生渚吊寒蚯,落月掛柳看懸蛛。此生忽忽憂患里,清境過眼能須臾。雞鳴鐘動百鳥散,穿透擊鼓還相呼。
寧靜的夜晚,微風吹動菰蒲的蕭蕭之聲,在房間中的詩人以為外面正在下雨,然而實際的情況卻是開門所見的月光鋪滿了湖面,這里用實寫。之后舟入驚鳥驚魚,以及夜釣、看月,皆以一種“移景于情”的虛寫。看到外面的月光與水交相輝映的美景,想到獨自居于臨近湖畔的孤寂,讓他產生了極大的孤獨感。為了表達這樣的孤獨感,詩人借夜釣時候,船驚棲鳥和劃水驚動魚兒的動,與夜之靜,得到了物與人不相管,而我獨歡愉的這種情感。同時,詩人借月兒西沉、蛛網接在水草上的景致,晨鐘驚動百鳥,擊鼓相互呼叫的喧鬧,傳遞出整夜無眠,憂患時光流逝的悲時傷世的情感。
詩人對于靜夜孤舟獨釣的經歷、以及入秋有之的湖水的漲落、曉月西沉等生活和自然經歷,這些實景了然于心,而由實景所傳遞的情感,卻由想象中的動靜結合和時空轉換的虛寫,表達出來。正因為他對現實生活的了如指掌,所以在圍繞“舟中夜起”這樣一個中心,來創作這首詩的時候,他就能夠提煉出能夠支撐這樣一個主題的意象,并把有關的意象集中起來,形成了一種詩歌的化境之美。結合蘇軾對“虛”“實”關系地認知,不妨也大膽地推測一下,在寫這首詩的時候,詩人不過是真正感受到了開頭的那樣的實景,而以此實景,結合大量的虛景,創作了這首詩。
五、“法度”與“變通”的關系
在我國文學的發展的過程中,“變”與“不變”是一對相互矛盾,不斷被文人爭論的一組關系。自從儒家講求“尊經”和“法度”,以及“溫柔敦厚”的詩教以來,尤其是儒家思想成為我國的正統思想的情況下,遵從“法度”一直以來都是文人們追尋的一種創作標桿。劉勰在《文心雕龍·宗經》篇章,明確提出了要以古代的經典為宗,稱經是“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49]并對宗經文學之優點給予了闡述。在宗經方面各個朝代都提出了所宗之經典的內容,從最早的“三墳、五典、八索、九丘”,[50]到“四書五經”,[51]可見古人對于經典的追從,也可見“法度”對于文學創作的重要性。
但另一方面,大家又開始主張“變”,覺得應該以人心和情感的自然流露,來創作真性情的文章,方是文學最高的審美追求。劉勰一方面強調法度,另一方面也提出了“夫設文之體有長、變文之數有方”,[52]也就在宗經基礎上的“求變”。但如宋時江西詩派、明代的前后七子、桐城派等文學家和文學流派,既代表了一個時代或區域的文學創作思潮,同時也強調嚴格遵從法度,另一方面如呂本中、嚴羽、李贄、王士禛、龔自珍[53]等一大批的文藝理論者又主張“變”,而拋棄法度。
“變”與“不變”的關系,可謂是貫穿了中國文學發展的始終,也是諸多文藝理論者不斷探尋和辨別的一對關系。
1.蘇軾的法度
在上面,對蘇軾“常形”和“常理”觀的探討中,蘇軾對外在事
物不變的形狀稱之為“常形”,對沒有固定形態,但有內在規律的,稱之為“常理”,在蘇軾的詩學思想中,“常形”和“常理”就是他所講求的法度。在論述他的“常形”、“常理”觀的時候,蘇軾指出“以其形之無常,是以其理不可不謹也。世之工人,或能曲盡其形,而至于其理,非高人逸才不能辨。”[54]相比于眼可觀的“常形”,心方能觀的“常理”,才是才華卓絕的人要辨別認知的“法度”。也只有這些所謂的高人逸才,方能夠抓住事物的法度,產生深刻的認知。
蘇軾主張文學虛實結合,虛和實的文學意象的構建,是在對事物的充分認知的基礎上。所謂遵從“法度”其實也是蘇軾詩學思想對于文學藝術的基礎性條件,也就是對萬事萬物的“道”的認知,這在前面已經論述,不再贅述。
2.蘇軾主張“出新意”
蘇軾的“出新意”也就會是他主張文學藝術構思和創作在遵從
“法度”的基礎上,追求“變”的一種理論認知。在對畫圣吳道子的畫進行評論時,蘇軾指出“道子畫人物,如以燈取影,逆來順往,旁見側出,橫斜平直,各相乘除,得自然之數,不差毫末,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謂游刃有余,運斤成風,蓋古今一人已。”[55]在這里蘇軾對吳道子畫的出神,“出新意于法度”的創新做了高度的評價,也就是他主張在法度上的創新和變通。
同時,蘇軾在評論自己的書法時也說:“吾書雖不佳,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56]可見蘇軾對于書畫藝術的構思和創作上,注重“新意”,也就以看出蘇軾在文學藝術的構思和創作上追求“獨創性”和“求變”的一種態度。他在《詩頌》中說“沖口出常言,法度去前規。人言非妙處,妙處在于是。”[57]
3.“法度”與“變”在蘇軾創作實踐中的體現
在后世對蘇軾的詩歌和詞的評價中,喜歡用“以文為詩”、“以詩為詞”來評價他的詩歌創作和詞的創作。雖然說“以文為詩”和“以詩為詞”[58]也遭到了后世的詬病,但卻能夠看出,這也是蘇軾在宋人認為“詩必盛唐”[59]的認知下,宋人該如何把詩寫好的一種“創新”的方法。當然“以文為詩”的宋詩寫作方法并非單指蘇軾,在其“以議論為詩”的風氣下,“以文為詩”也并非蘇軾的獨創,只是他得到了“以文為詩”的精妙而已。再說,在詞的創作上,雖然范仲淹、歐陽修、晏殊等幾位宋初的詞家,也寫一些豪放情懷的詞,但終沒有逃出詞為艷科的窠臼。而真正開啟豪放詞風的是蘇軾,而且是形成了詞“自是一家”的獨創風格。
下面選蘇軾的《西江月·野照彌彌淺浪》[60]這首詞,來看他“以詩為詞”的創作風格。
野照彌彌淺浪,橫空隱隱層霄,障泥未解玉驄驕,我欲醉眠芳草。可惜一溪明月,莫教踏碎瓊瑤,解鞍倚枕綠楊橋,杜宇一聲春曉。
這首詞是蘇軾在黃州,春夜游蘄水,在酒家飲酒醉后,至一溪橋上,解鞍曲肱而臥,解酒祛乏時,見月光蒙眬,山川影隱,景色醉人,而寫的一首詞。整首詞給人的感覺是非常的雅,其意象的構建和用詞都非常的雅致。詞人對于詞中意境的巧妙構思,如同寫詩一般,把最具特色的意象都聚集起來,橋下潺潺流動的溪水、天空隱約可見的云翳,自己醉眼迷茫中的感受等,給人化境般的詩歌韻味。雖然是填詞,但詞人的詞如同寫詩一般,韻味悠長,給人以意境美。
六、天然之工和人為之工的關系
文學創作的“天然之工”和“人為之工”主要是針對文學的形式和內容,在形式上,主要表現在語言和辭藻上,“天然之工”提倡語言和辭藻的澄澈和干凈,相反“人為之工”是主張語言的華美和雕琢;而在內容上,“天然之工”崇尚個人才情的激發和靈感的迸發;“人為之工”去注重引經據典,追求“字字有出處”,[61]即學習臨摹古人。
“天然之工”和“人為之工”自古以來,文學界都爭論不休,也無定論。崇尚“天然之工”的喜歡“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62]的文學審美,提倡“童心”“性靈”的詩學思想等;而主張“人為之工”的,如賈島、孟郊[63]這樣以練字、苦吟的作者,及“點石成金、脫胎換骨”,[64]“文必先秦”“詩必盛唐”[65]這樣的文學流派和文學集團等。尤其是在宋明理學的主導下,文學面臨著越來越政治化的緊縮的形式下,“自然之工”和“人為之工”成了元明清時期,詩學者們爭論的焦點和相互批評的主要方面。
1.蘇軾主張“自然之工”
在《次韻吳傳正枯木歌》[66]中,蘇軾指出“天公水墨自奇絕,瘦骨枯松寫殘月。”這里的“天公水墨”便是指“自然的文章”。同時他還提出“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67]這里的“天工”也便是“自然之工”。劉勰在《文心雕龍·原道》篇詳細地論述了天地人“三才”[68]文章的表現方式,而這些“文章”又是“天地人”的自然之道。蘇軾自出“天公水墨自奇絕”便也是對“天地”自然之道的精妙的贊嘆。也正是他主張文學創作的“自然之工”。
另一方面,蘇軾非常推崇陶淵明和柳宗元山水詩中的淡雅、意遠和自然之美。在儋州的時候,蘇軾寫了100多首的和陶詩,在這些詩歌中,展現了他對自然的詩風的追求。在他晚年總結自己創作經驗的《答謝民師書》[69]中說:“所示書教及詩賦雜文,觀之熟矣。大略如行云流水,初無定質,但常行于所當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文理自然,姿態橫生。”這里的“行于所當行”和“止于所不可不止”是蘇軾遵循自然之道,講求自然之工的一種詩學思想。同時黃庭堅稱他的詩“時一微吟,清風颯然,故同味者難得爾。”(《答李端叔》)[70]“清風颯然”是黃庭堅對蘇軾“自然”詩風的評價。
2.蘇軾不反對“人為之工”
雖然蘇軾崇尚“自然之工”,但卻并不是完全按照自然來做文章,而且講求“無法之法”。蘇軾提出“無法之法”是基于他對“道”的認知之上的,這里的“無法”是在“道”之上的“無常法”,也就是上面他提到的他對“法度”和“變通”這間關系的辯證認知,在此不復述。“無法之法”便是按照自然之道,加以作者“創新”的運用,從而使文學作品既有“自然流暢”,毫無雕琢的審美內涵,同時,也具有文學藝術的韻味。
蘇軾在《文說》[71]中說“吾文如萬斛泉源,不擇地而出。在平地滔滔汩汩,歲一日千里無難;及其與山石曲折,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當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是而已矣。”這段話表明了蘇軾崇尚“自然之工”,但同時又不反對“人文之工”。而“自然之工”如“萬斛泉源”可“一日千里”,是“隨物賦形”而“不可知”,但“可知”者是“行于當行,止于不可不止”。蘇軾在這里所指的“不知”和“知”,是他對“人為之工”的認知。也就是“自然之工”可以讓創作者“形于心”,而“人為之工”可以讓創作者“形于手”。
3.蘇軾寫景詩中的“自然之工”和“人為之工”
在蘇軾眾多的詩作之中,寫景詩占了很大的比例,一方面是由他的仕途所決定,家在四川,應考在汴京,為官卻是東南西北中,[72]這讓他能夠走遍祖國的山川河流,為他寫景詩奠定了經眼的基礎,另一方面在于他詩學思想中對“道”的認識和把握,也就是他所提倡的“自然之工”。同時,還在于他對于“人為之工”的認知,是他的寫景詩,意境豐滿,情景交融,韻味十足。雖然他對陶靖節和柳河東山水詩歌非常推崇,但東坡的寫景詩,卻與他們不同,而有他自己的風格。
下面舉他的《新城道中二首》[73]之一,來看他的寫景詩的藝術風格。
東風知我欲山行,吹斷檐間積雨聲。嶺上晴云披絮帽,樹頭日初掛銅鉦。野桃含笑籬笆短,溪柳自搖沙水清。西崦人家應最 樂:煮芹燒筍餉春耕。
這是一首寫雨后初晴西山的景物,詩人從遠處的天空云層,太陽和山林,寫到近處的野桃籬笆和溪水、楊柳。意境的構思非常的巧妙,比喻用得非常的恰當。詩歌首句注入了濃烈的主觀色彩,接著又淡化了主體的存在,以白描手法,春山雨后初晴的精致描寫得清新舒雅,既有自然之美,又有人間之相。最后一句表達了春雨來得及時,去后農事之樂的農家氣息。寫景并非完全自然,參入了詩人的思想情感,使得詩歌讀起來韻味十足。
七、“才情”、“才氣”和“才力”的關系
“才情”、“才氣”和“才力”在語義上并沒有多大的區別,后世在評價前人時,尤其是評價具有文學方面“才華”的人的時候,也并沒有加以區別,而且三個詞也大多混用,并沒有進行嚴格的區分。在這里,我把三者提出來,是鑒于蘇軾詩學思想的認知。
我們在此所談論的“才”,主要針對的是“文才”,即文學藝術創作的能力,其他的便不多做議論。中國傳統文學中對于“文才”尤為重視,自古以來國家對文人士大夫的重視是非同一般的。文人士大夫既是國家的棟梁,又是政治、經濟、文化等各項事務的參與者和決策者,他們在中國古代發揮著巨大的作用,尤其是中國文學的中流砥柱。文人士大夫占據了中國古代文學的主流,是不容爭辯的。
在此提及文人士大夫的地位和影響力,其目的是在于說明分清“才情”、“才氣”和“才力”的關系是很有必要的。中國古代有很多“三歲能詩”、“七歲能文”的天才式的文人,比如蘇軾同時代的晏殊;[74]也有經歷世事滄桑,詩才和詩風卓絕的一代文豪,如“詩仙”李白。在傳統對于文人的評論中都少不了對他們天賦異稟的“文才”,和后世創作的“文采”的雙優加以盛贊。但區分先天和后天的“文才”,有利于探討研究對象在詩學思想上的認知。
提出的“才情”、“才氣”和“才力”便是對“文才”的先后天的一個區分。“才情”來天生的“文才”,《文心雕龍·明詩》[75]中,提出“人稟七情,應物斯感,感悟吟志,莫非自然”。之所以用才情來表示天生的“文才”,也在于此。“才氣”便是指后天的“文才”,《孟子·公孫丑》篇說“我之言,我善養浩然之氣”。可見氣是需要養。曹丕《典論·論文》[76]中提出了“文氣”說,最早把哲學的“氣”與文結合起來,并指出了“氣有清濁”,同時“氣”不可借出和傳給其他人。從這里可以看出,氣是需要后天的培養,以及每個人的“氣”是不同的,用以概括后天“才氣”的人,更為合適。
而先天和后天的“文才”的綜合,形成了“才力”。“才力”并非筆者發明的,在古代即有之,司馬遷在《報任安書》[77]中,就指出“所以自惟,上之不能納忠效言,有奇策才力之譽”。這里的“才力”便是指“奇策”能力的多少和大小,多少和大小是對“文才”綜合能力的概定,所以以“才力”比較合適。
1.蘇軾對“才情”、“才氣”和“才力”的綜合認知
在蘇軾的詩學思想中,并沒有明確論述這三者的關系。但是從他對“道”與“藝”的關系的論述和認知中,我們可以看出,“形于心”是他對“道”的認知,是文學創作的前提;而“形于手”是他對“藝”的認知,是文學創作的條件。“形于心”一定程度上是蘇軾對先天“才情”的認可和提倡,而“形于手”也是對后天“才氣”必要性的認同。
在蘇軾的時代,圍繞在他身邊的文人又被稱之為“蘇門六君子”、[78]“蘇門四學士”“蘇門后四學士”[79]的弟子,這些人在當時也是非常有名氣的文人大家,比如黃庭堅、秦觀等。但蘇軾并沒有把他們都統一起來,用一種詩學理論,來形成自己的獨立的文人團體,如黃庭堅所影響下的“江西詩派”,[80]三袁的“公安派”,[81]“前后七子”[82]等等,他們皆以一種詩學理論,來形成自己理論相關的文學團體。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蘇軾詩學思想對“文”與“道”,“道”與“藝”,“法度”與“變通”等關系的客觀科學的認知。
最令人樂道的是蘇軾為了說明個人“才力”積累,需要主體的主動認知這個道理,他在給山東舉子吳彥律所寫的《日喻》,[83]開篇就說:“生而眇者不識日,問之有目者。或告知:‘日狀如銅盤’。”扣盤而得其聲。他日聞鐘,以為日也。或告之曰:‘日之光如燭’。捫燭而得其形。他日揣籥,以為日也。”,這個故事蘇軾主要是為了說明,個人對于“道”的認知,需要的是自身的實踐和親生體驗,方能得到真正的感受。但是從另一方面,卻反映出蘇軾對創作主體“才情”的肯定,以及對后天“才氣”培養的自主性的認知。
2.“才情”“才氣”兼具的一代文豪
蘇軾一生在“詩、詞、文、書畫”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后人無
可望其項背的,更有甚者稱之為“雅文學的終極者”,也就是說他是中國文學史上最后一個雅文學的集大成者。蘇軾所留下的詩歌有2千余首,詞作近300闋,以及卷帙浩繁的大量散文、筆記體等文章,是有宋一代,無人企及的一座高峰。他對后世文學創作和詩學理論建都有著及其深遠的影響。
他提倡的“無法之法”是對后世呂本中“活法”詩學理論建設的基礎,呂本中提出“活法”以糾正江西詩派“脫胎換骨”、“點石成金”詩學理論的過分模擬和晦澀難懂詩風。他對蘇軾給予了盛贊,稱:“自古以來語文章之妙,廣備眾體,出奇無窮者,唯東坡一人”。[84]同樣提出反對江西詩派詩學理論的嚴羽,受蘇軾“妙想”和“神思”的影響,提出了“妙悟”[85]的詩學理論。王若虛在蘇軾詩學思想和文學創作的影響下提出了“元氣”和“自得”觀,[86]他對蘇軾非常推崇,“東坡文中龍也,理妙萬物,氣吞九州,縱橫奔放,若游戲然,莫可測其端倪。”(王若虛《詞話》),清代著名評論家劉熙載、[87]郭紹虞[88]等也對東坡的詩進行了高度的評價,并對他們的詩學理論的形成有著積極的影響。
以上是傳統詩學理論比較有影響的理論者對蘇軾詩學思想傳承和發展,以及對他文學作品的評價。在這些評論中我們可以看出,后世主要是對蘇軾尊崇自然之道,又提倡文學創作技巧“藝”,即“有法度”,又“變換莫測”進行了評價。這些好的評價,一是得益于蘇軾“才情”、“才氣”雙優下,無尚“才力”反映在其文學創作中,所留給后世的名篇佳作;再就是蘇軾詩學思想中對“文”與“道”、“道”與“藝”、“實”與“虛”等關系的客觀認知,對后世詩學理論發展的作用。
3.“風格各異”、“變換莫測”,“才力”十足的蘇軾
蘇軾在文學創作上,一方面形成了他獨特的詩學思想,同時,對于文學的認知,又在很大程度上提升了他文學創作的能力。也就是說他所擁有的“才情”讓他具備了與常人更加敏銳的視覺,和對宇宙萬物的認知能力,而善于養“才氣”的他又在不斷的文學創作的實踐之中,總結了大量的經驗,即他對文學規律的認知。這兩方面造就了“才力”十足的蘇軾。
下面以《江城子·乙卯正月二十日夜記夢》[89]為例,看風格各異,“才力”十足的蘇軾。
十年生死兩茫茫,不思量,自難忘。千里孤墳,無處話凄涼。縱使相逢應不識:塵滿面,鬢如霜。
夜來幽夢忽還鄉。小軒窗,正梳妝。相顧無言,唯有淚千行。料得年年腸斷處:明月夜,短松岡。
這是蘇軾悼念亡妻的一首感人肺腑的詞。上片前三句,以“不思量,自難忘”,便激起了多少人對于思念亡人的同感。對于逝者的思念,并非是刻意為之,而是和著每天的呼吸,在醒著和夢中,無處不在的一種相思。接著以“無處話凄涼”來闡述生者獨自一人,歷經人間滄桑的凄涼,再緊扣首句“思念生死兩茫茫”,來感嘆陰陽相隔的一對戀人,哪怕是在夢中相遇,都是分離長久的無可奈何。真可謂是繼潘岳“悼亡妻”[90]之后,最痛徹心扉、感人至深的一首詞,也成為傳頌千年來的名篇佳作。
以豪放著稱的蘇軾詞風,沒想到其婉約綺糜的情感,也寫得如此動人心弦。可見“鴻懿”之“才力”非他莫屬。
八、“幸”與“不幸”的關系
我們常說“詩人之不幸,詩家之大幸”,這是后世評論者用于評
價古時仕途上的不暢,文學上卻成就卓絕的文人。這里的“幸”與“不幸”是指古代文人士大夫在政治仕途上的“達”和“窮”。孟子在《孟子·盡心章句上》中指出“窮則獨善其身,達則兼濟天下”。[91]這句話也成為了儒生們人生信條,影響了以儒家思想為正統思想的封建王朝。同時,把這個當做信條的文人士大夫,每當遇到仕途坎坷,人生理想抱負無法實現的時候,多以“窮”這樣的境況來自喻。也就出現了很多在政治仕途上失意之后,從文學創作中尋找內心平衡的情況。儒家“三立”說,以及從司馬子長開始提出的“發憤著書”說,也在很大程度上,形成了失意文人對于著書立說的風氣,似乎也成了我們后世在研究古代文人時的美談。
1.蘇軾仕途上的“不幸”
蘇軾在《自提金山畫像》中,[92]對自己的一生做了總結,他說“心似已灰之木,身如不系之舟,問汝平生功業,黃州惠州儋州”。這里提到的“黃州惠州儋州”是蘇軾被貶謫的三個地方,也是蘇軾仕途“不達”,人生最為失意的“不幸”時期。貶謫黃州,消磨了蘇軾四年(1080年—1084年)的美好時光,再貶惠州(1093.10—1097.4)和儋州(1097—1011),又是五年多的時間,這時候蘇軾已經是50多歲[93]的年邁之軀。縱觀他的一生雖然年紀輕輕,才華就名動京城,但是真正作京官的時間(1069年—1071年)[94]并不長久,比起他在外為官實在是不值得一提,但這短短三年是蘇軾仕途的“達”的時期,同時也使他卷入了黨爭之中,為之后的不幸種下因的時候。在貶謫黃州惠州儋州時期,蘇軾不僅是以“戴罪之身”謫居這三地,受到當地主要官員的監視,而且他的生活非常的拮據,在黃州還在營區以東的山坡開荒種地,以解決生計問題。為了自嘲,也表達他對人生不幸的曠達,他為自己取號“東坡”。[95]
蘇軾的一生,在仕途上一直都處于貶謫的狀態,而他的政治抱負,與當時王安石為代表的“革新派”和司馬光為代表的“守舊派”皆有不同,這對在新舊斗爭激烈的趙家王庭的蘇軾而言,注定了他一生的仕途的不暢和人生的不幸。也是他人生以“窮”的方式,造就了他在文學創作道路上的“達”。
2.蘇軾繼承了歐陽修的“窮而后工”的觀點
蘇軾受其師歐陽修“窮而后工”詩學思想的影響,在對“幸”與“不幸”這對關系的認知中,他也主張“窮而后工”。在他的詩《病中大雪,數日未嘗起觀。虢令趙薦以詩相屬,戲用其韻答之》中說:“有客獨苦吟,清夜默自課。詩人例窮騫,秀句出寒餓,庶以躡郊賀!”[96]這里蘇軾以“詩人例窮騫,秀句出寒餓”來表達自己對于“窮而后工”的認可。同時,蘇軾也提出了“非詩能窮人,窮著詩乃工”。[97]
在理論上,蘇軾以“窮而后工”來看待“幸”與“不幸”的關系,在實際創作中,他也是這樣來踐行的。據蘇軾編年詩歌的統計,在汴京任職這三年蘇軾的創作不足20首,而在這前三年的鳳翔任職期間他創作的詩歌是130多首[98]。在黃州的四年卻是他是個創作在數量上和藝術上都雙豐收的時期,這段時間他無論是在詩歌的創作上,還是在詞、賦、隨筆等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功。我們所熟知的那首《念奴嬌·赤壁懷古》,[99]以及《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100]還有他的一些展現他詩學思想的隨筆和政治見解的散文等等,在這個時候都呈現出數量上和質量上的雙優。
尤其是在謫居海南的儋州的時候,蘇軾在對詩歌創作的意境等方面,有了更加深刻的認識,這段時間他以和陶詩,在創作中尋找一種化境的審美追求。
3.蘇軾“不幸”時期,文學創作的“大幸”時期
正如蘇軾對自己人生所作的總結中提到的那樣,他的人生的功業“黃州惠州儋州”,這是蘇軾仕途政治的“窮”的時期,也是他人生的“不幸”時期,但卻是他在文學藝術創作中的“達”的時期,正真是他的“功業”之所在,也是他“幸”之所在。
下面舉《定風波·莫聽穿林打葉聲》,來看蘇軾謫居黃州時候的文學創作和精神狀態:
莫聽穿林打葉聲,何妨吟嘯且徐行。竹杖芒鞋輕勝馬,誰怕?一蓑煙雨任平生。
料峭春風吹酒醒,微冷,山頭斜照卻相迎。回首向來蕭瑟處,歸去,也無風雨也無晴。
早春,風雨中帶著寒意。穿林而來的瀟瀟春雨打在樹葉上,詞人卻并未被這樣的風雨所嚇住,而是一邊吟嘯,一邊慢慢前行。吟嘯[101]是魏晉名士,最為美談的一件事情,也是魏晉風流的一種標志性的的行為,包括竹林七賢的阮籍就是一位善于吟嘯的名士。此處用吟嘯,也表達了詞人如魏晉這些風流人物一般,暢達和通透。下面用竹杖、芒鞋、蓑衣等農夫的穿著,來表達自己即便困頓,依舊積極樂觀的心態。也正好說明了詞人謫居黃州的時候,并沒有因為仕途政治的“不幸”而一蹶不振,沉淪失意,而是以一種積極的狀態,哪怕春寒料峭,哪怕風雨瀟瀟,哪怕回望過去一昏暗,到此刻,對于詞人而言已不關風雨,不關晴。這種“也無風雨也無晴”的心態,正是蘇軾能夠很好地面對自己人生起伏的一種悟性,也是對人生沉浮,應當以一種豁達的心態來對待的認知,更是他對儒家千年來,所賦予的“窮”與“達”二者關系的認知。
九、文學與其他藝術的關系
先秦文學所呈現出的文學特征主要是文史哲不分家,和口頭文學向書面文學過度的時期。這也是文學萌芽初期所呈現的一種狀態,文史哲不分家,也是文學領域內各種關系相互爭論不下的主要原因。隨著魏晉南北朝時期,文學自覺的到來,系統性的文學論述面世,文學漸漸成為了獨立的學科。縱觀劉勰的《文心雕龍》對文學體裁分類就可以看出,他對文學的界定是廣泛的文學概念。正如他對文學所下的定義,文學乃“人文”[102]也;只要是出于人之性靈,“心生而立言,立言而文明”,[103]便就是文了。所以他把封禪、章奏、史傳、檄移等應用型的書體也也稱之為文,這就使后世關于文學范疇內的各種關系出現爭論不休,沒有定論的根源。
同時受到上古時期“歌樂舞”三位一體的影響,文學和其他藝術如書畫等也有著密不可分的關系。尤其是在詩歌意境的構造,以及文學藝術的生成等方面都形成了相互借鑒,互相闡釋的現象。比如我們常見的是以畫為詩,為畫提詩等,皆是文人雅士樂此不疲的事情,同樣以畫論詩,也是詩評中常有的現象。
1.蘇軾喜以畫論詩理
縱觀蘇軾詩學思想的基礎,大部分借助于對繪畫藝術的闡述,他認為詩和畫之間,有著相同的藝術構思和意象的生成。如他在《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104]之一中所說:“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這里的“天工”也就上面論述到的“自然之工”,而在這首詩的結尾,蘇軾點出“誰言一點紅,解寄無邊春。”是借以評價王主簿畫中以一點紅來代表無限春的藝術創造,來論述詩歌取其“意”,而非取其“形”。
同樣在蘇軾《凈因院畫記》[105]中,也用評畫以論詩,他說:“余嘗論畫,以為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木,水波煙云,雖無常形,而有常理。”也就是上面提到的蘇軾詩學思想中“法度”的理論。
另一方面,他又以詩歌來評價繪畫藝術,比如《王維吳道子畫》[106]中,他指出“吳生雖妙絕,尤以畫工論。摩詰得知于象外,有如仙翮謝樊籠。”這里的畫工是蘇軾詩學思想的“人為之工”,有雕琢之嫌,而“象外”,則又是蘇軾詩學思想所主張的“常理”。同時,他又稱王維“味摩潔之詩,詩中有畫。觀摩詰詩,畫中有詩。”[107]
而且,蘇軾也借書法、音樂等藝術,來闡釋他的詩學思想,他在評論古代書法大家,如王羲之,他說其書法“蕭散簡遠,妙在筆墨之外”,所謂妙在筆墨之外,是蘇軾詩學思想中對于“言外之意”的肯聽。同時他借用陶淵明“無弦琴”,指出“破琴雖未修,中有情誼足”,[108]主張“言有盡而意無窮”的美學追求。在《石鐘山記后》一文中,蘇軾說:“錢塘東南,皆有水樂洞,巨石巖中,皆有自然宮商。”[109]“自然宮商”既是這段描述后面提到的“乃知莊生所謂天籟”。這也是蘇軾借音樂,來論“自然之工”詩學理論的一種方法。
由此觀之,蘇軾在書法、繪畫上的造詣成就了他詩學思想理論的基礎,同時,詩學思想在某種程度上,又影響著他在書法、繪畫藝術上的精進。
2.詩歌、詞賦、散文不同文學體裁的關系
后人常常把“以文為詩”、“以才學為詩”,[110]來總結蘇軾詩歌的藝術特色,雖然客觀實際,但卻遭到了后世一些文人的詬病,批評他詩歌好議論,比如黃庭堅就說他的詩“長篇需曲折三致意,乃成文章”。[111]一些人也對他喜歡“工字”、“用典”,賣弄才學的詩歌風格表示不滿。即便如此,在某種程度上反映了蘇軾對詩歌和散文這兩種不同文學體裁,具有他自己的獨到的認知。自古以來,認為文學體裁之間有著明確的界限,所以劉勰在為文學體裁分類時,進行了很細致地舉證。但蘇軾卻打破了這種界限,讓他的詩歌也具有散文般可議論的特色,但卻又并沒有把詩歌寫成散文。
另一方面,是蘇軾在詞的創作中,運用了詩歌創作的藝術風格。比如意象的提煉和集中,詩歌話的語言等等,讓詞真正脫離了“艷科”和“綺麗”的詞風。在評蘇軾詞的時候,后人常以“以詩為詞”來進行概括,但正是這“以詩為詞”,成就蘇詞的“自是一家”。[112]而且成就了他在宋詞創作中豪放派的高峰的地位。
3.各種藝術皆通的蘇軾,堪稱“雅文學”最后一人
蘇軾在書法、繪畫、音樂等藝術方面的造詣,以及他在文學上詩詞歌賦,散文隨筆等方面的成就,可謂時各種藝術皆通,縱觀后世,在無一人能夠與之比肩。堪稱為中國文學史上“雅文學”最后一人。[113]他在文學和書畫藝術上的成就,在于他對二者關系的客觀科學的認知。同時,也在于他不按“法度”,懂得“變通”的詩學思想。無論是他的詩學思想還是他的文學和其他藝術的創作實踐,兩者都是相輔相成,互相促進,又相互影響。他可謂是一位在文學和其他藝術上雜類旁通的第一人,奠定了他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在此舉蘇軾詩歌《飲湖上初晴后雨》[114]來看蘇軾如畫境般的詩,和詩歌中的畫:
水光瀲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欲把西湖比西子,濃妝淡抹總相宜。
這是蘇軾詩歌中的名篇,也是古人描寫西湖的壓軸之作,后世不復再有人超過他的這首詩的佳作。為此后人也把西湖稱之為“西子湖”。詩人以蕩舟湖上的視角,看西湖周邊雨后初晴,及晴后雨來的動態的景致。詩歌把繪畫的光感、色彩,以及詩歌藝術的比喻糅合在一起,既給人眼前有畫的感受,又給人以詩味十足的感受。難怪后人見到此詩時,便放棄了寫西湖。[115]
綜上所述,以上從九對關系中,粗淺論述了蘇軾詩學的基本思想,同時也通過蘇軾的一些具體的作品,對蘇軾詩學思想進行了說明。其中尚有很多的不足之處,但卻是很全面地反映了蘇軾對于文學是什么?文學的價值和藝術構思,文學與客觀世界的關系,文學與其他藝術和學科的關系,文學的審美等問題的思考。這些問題也是我國文學史上,從文學誕生開始,諸多文人學者探索、探討和論證的問題,但卻是爭論不休的問題
在當今看來,這些問題涉及文學的本質、形式、內容等主要問題,而且這些問題用當今的辯證唯物主義思維方法來解決,是沒有爭論和誰主客的問題。其實這樣的思維方式,在蘇軾的詩學思想中,已經得到了很客觀的回答。受儒家中庸思想的影響,蘇軾在論述自我的詩學觀點的時候,也以比較中正的態度,不偏不倚,始終在各對關系中,找到彼此存在的平衡點。比如文與道的關系,蘇軾站在了道的基礎上,卻并沒有完全偏向道,而且客觀地認識到了文學內在的特點和規律,使其文既沒有失去道的需求,同時保留了文學自身的特色。在“法度”和“變通”這對關系上,蘇軾首先是對“法度”進行了界定,承認了法度的存在,但同時,又以“變通”發展的觀點,來繼承和發展“法度”。這種辯證的處理文學范疇內各大關系的態度,既是蘇軾中庸思想的體現,也成就了他對文學的認知,取得了文學上的成就。
作者介紹:鄒海燕,女,漢族,文學碩士,西藏大學文藝學博士生,拉薩師范高等專科學校語文和社會科學系教師。主要研究方向:民漢文學;漢藏詩學。
①《尚書·虞書·堯典》提出“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八音克偕、無相奪倫、神人以和。”儒家“詩言志”主要是強調詩歌表達個人的志向。
②《典論·論文》由三國時期魏文帝曹丕所著,是我國文學史上第一部文學批評專論,由清代的沈陽孫和馮翼輯,提出了“蓋文章,經國之大事,不朽之盛事。”
[3]“三立”說,最早見于《左傳》(襄公二十四年),魯國大夫叔孫豹出使晉國,回答晉執政范宣子關于“不朽”問題時,他回答說:“大上有立德,其次立功,其次立言,雖久不廢,此之為不朽”。
④“發奮著書”說最早源于屈原,屈原在《九章·惜誦》中提出了“惜誦以至愍兮,發奮以抒情。所作忠而言之兮,指蒼天以為正”。其后司馬遷在《史記·太史公自序》中又對這一理論進行了強化和闡述。在對古之發奮著書的名人舉例之后,他發出了“此人皆有所郁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
⑤“詩緣情”由三國時期陸機提出,在他的《文賦》中,明確提出了“詩緣情而綺糜,賦體物而瀏亮、碑披文以相質、誄纏綿而凄愴、銘博約而溫潤……”
⑥“文以鳴道”是唐代“古文運動”的發起人韓愈,對古文寫作的一個明確的要求,也是文學為政治服務的一種價值取向。
⑦“文以載道”是宋理學派,對于文學即理學認知的主要觀念,宋·周敦頤在《通書·文辭》中提出“文所以載道也。輪轅飾而弗庸,徒飾也,況虛車乎。”與韓愈提出的“文以鳴道”又很大的不同。兩者都提出文學的社會功效,但韓愈并未否定文學的自身價值和規律,而后者卻完全把道和文當做一體。
⑧“童心”說是明代李贄詩學思想的主要論點,他主張文學創作的“自然”和“真情”,提出了“夫童心者,真心也”觀點。以此對宋明理學為代表的官方正統思想進行批判。
⑨“性靈”說是清代袁枚詩學思想的主要觀點,主張詩歌抒寫真性情,他提出了“詩者,人之性情”的觀點,是對“詩緣情”及“自然天工”等文學內容認知的繼承和發展。
⑩蘇軾:《蘇軾集》(卷一)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提柳子厚詩》“詩需要有為而作,用事但以故為新,以俗為雅,好奇務新,乃詩之病也。”
?蘇軾:《蘇軾集》(卷一)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書黃魯直詩后》。
[12]《二程語錄》卷十一,(清·張伯行 訂)載程頤之答問語“問:‘作文害道否?’曰‘害’;問‘詩可學否’曰‘既學時須是用工方和詩人格,既用工,甚妨事’”。
[13]《二程遺書》(卷二十四),程頤指出“人心,私欲,故危殆;道心,天理,故精微。滅私欲則天理明也。”
[14]劉勰:《文心雕龍》(戚良德注說)2008年3月第一版,《原道》篇:“贊曰:道心惟微,神理設教。”“道心”即天地人三才之道的精髓,“神理”即神奇奧妙的道理。
[15]王水照:《蘇軾》上海古籍出版,1981年12月。
[16] 《達謝民師書》《蘇軾集》(卷四) 黑龍江人民出版社 2005年11月,“求物之妙,如系風捕影。”
[17] 《蘇軾集》(卷一)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
[18] 《書黃子思詩集后》“予嘗論書,以為鐘王之跡,蕭散簡遠,妙在筆墨之外”是蘇軾寫給黃孝先的一篇序跋,黃孝先字子思。《蘇軾集》(卷一)(中國古代名家詩文集)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
[19] 【清】歷鶚輯撰《宋詩記事》(一),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1983年6月。
[20] 潞公,宋文彥博(1006.10.23——1097.6.16)的別稱,字寬夫,號伊叟。汾州(今山西介休)人,北宋著名的政治家、書法家
[21] 《宋詩記事》載“元豐二年乙未,先生四十四歲。七月太子中允權監察御史何大正、舒亶,諫議大夫李定,言公作為詩文,謗訕朝政及中外內臣僚,無所畏憚。國子博士李宜之狀亦上。七月二日,奉圣旨送御史臺根勘。二月十八日皇甫遵到湖州追之。”
[22] 《蘇軾集》(卷一)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
[23] 《歸田園居》是陶淵明的組詩,共五首,(種豆南山下)是第三首,也是備受后世文人學者所推崇的一首詩歌,全詩以恬淡、悠遠的意境,深受后來者的喜歡。王國維在《人間詞話》中,以“無人之境”的意境美,對其大加贊揚。全詩“種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晨興理荒穢,帶月荷鋤歸。道狹草木長,夕露沾我衣。沾衣不足惜,但使愿無違。”
[24] “廟堂之高”和后面的“江湖之遠”皆取之蘇軾中秋節,在密州(今山東濟南)寫給其弟子由的一首懷念詞中,即《水調歌頭·丙辰中秋,歡飲達旦,大醉作此篇,兼懷子由》,也是中國古代文學史上寫秋月最好的一首詞。與張若虛《春江花月夜》,寫春月最好的詩,并稱。
[25] 【清】沈陽孫 馮翼輯:《典論·論文》,指出“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于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氣”作為哲學概念,在先秦諸子中皆有提及。
[26] 劉勰:《文心雕龍》(戚良德注說)2008年3月,《情采》篇指出“夫鉛黛所以飾容,而盼倩生于淑姿;文采所以飾言,而辯麗本于情性。”劉勰對于文章是否華彩取決于創作主體的“性情”,這和陸機提倡的“詩緣情”有異曲同工之妙,同時也是蘇軾對于“藝”,即文學藝術構思技巧方面的追求,有著共同之處。
[27] 蘇軾:《蘇軾集》(卷四)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書李伯時山莊圖后》是蘇軾為北宋著名畫家李伯時的畫《山莊圖》所作的一篇文章,李伯時李公麟(1049—1106),號龍眠居士,安徽舒州人。
[28]《歷代書論集萃》(四)(宋代部)蘇軾《書論》《跋秦少游書》“少游近日草書,便有東晉風味,作詩增奇麗。乃知此人不可使閑,遂兼百技。技進而道不進,則不可,少游乃技道兩進也。”
[29]蘇軾:《蘇軾集》(卷一)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288頁。《惠崇春江晚景二首》之一,“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這首詩蘇軾在再度回京做官,從常州過登州至汴京的途中,所見惠崇所畫的兩幅畫,所作的兩首提畫詩。
[30] 王水照:《蘇軾》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2月。元豐三年(公元1080年),蘇軾抵達黃州,開始了4年之久的謫居黃州的生活。在黃州蘇軾三詠赤壁,創作了千古名篇《念奴嬌·赤壁懷古》“大江東去浪淘盡”是這首詞的開頭句,另外兩篇是《前(后)赤壁賦》。
[31] 蘇軾:《蘇軾集》(卷一)(中國古代名家詩文集)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第43頁
[32] 莊子思想對“道”認知的方法,“坐忘”即“墮肢體,黜聰明,離形體去知,同于大道,此謂坐忘”,也就是拋出身體和既有觀念的束縛,融入自然宇宙之中,尋求大道的方法。“心齋”即“若一志,無聽之以耳,而聽之于心,無聽之于心者,而聽之于氣。聽止于耳,心止于符。氣也者,虛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虛。虛者,心齋也。”心齋也就是用虛空之心去感知自然萬物。分別出自《莊子·內篇》(人世間)和(大宗師)兩篇。
[33] 劉勰著:《文心雕龍》(戚良德注說)2008年3月第一版,《神思》開篇指出“古人云,行在江海之上,心存魏闕之下:神思之謂也。”“神”即“神與物游”,思即“思理為妙”。神思便是要真正進入事物內部,體會事物之間的規律和關系。
[34] 劉勰著:《文心雕龍》(戚良德注說)2008年3月第一版,《神思》篇提出“文之思也,其神遠矣。故寂然凝慮,思接千載;悄焉動容,視通萬里。”劉勰認為文學的規律和關系,比自然宇宙的物更遠,所以想要達到對文的認知,就要通過“寂然”和“悄焉”的寧靜空虛的方法。
[35] 蘇軾:《蘇軾集》(卷一)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187頁
[36]《書李伯時山莊圖后》《蘇軾集》(卷四)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蘇軾為李公麟畫《山莊圖》所作的一篇文章。李伯時即李公麟,號龍眠居士,安徽舒州人,北宋著名畫家。文中全句:“居士之在山也,不留于一物,故其神與萬物交,其智與百工通。”
[37] 劉勰著:《文心雕龍》(戚良德注說)2008年3月第一版,《原道》篇“故知道沿圣以垂文,圣因文而明道;旁通而不滯,日用而不匱。”即了解了天地萬物以及人文知道,就能夠觸類旁通,用之不竭。
[38] 《送參寥師》,《蘇軾集》(卷一)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187頁,“欲令詩語妙,無厭空且靜。靜故了群動,空故納萬境。閱世走人間,觀身臥云嶺。咸酸雜眾好,中有至味永。詩法不相妨,此語更當請。”
[39]《蘇軾集》(卷一)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253頁,全詩“橫看成林側成峰,遠近高低各不同。不識廬山真面目,只緣身在此山中。”
[40] 同上
[41] 同上:87頁。
[42] “詩歌言志”,即“詩言志”,《尚書·堯典》“大舜云:‘詩言志,歌永言’”。“賦者陳事”:劉勰《文心雕龍·詮賦》指出“賦者,鋪也,鋪采摛文,體物寫志也。”
[43] 《古典文學——毛詩序說》(八卷)(清)洪范撰,續四庫全書 復印本。“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嘆之,嗟嘆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
[44] 東晉的陸機在其文論著作 《文賦》中指出“雖離方而遁圓,期窮形而盡相。”
[45]《凈因院畫記》《蘇軾集》(卷四)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余嘗論畫,以為人禽宮室器用皆有常形。至于山石竹林,水波煙云。雖無常形而有常理。”邊鸞,唐代畫家,擅長繪畫花鳥草木,中國花鳥畫獨立成科過程中的重要人物。趙昌,北宋畫家,工書法、繪畫,擅長花果。此二人見于《中弄過古代畫家匯總》。
[46] 蘇軾:《蘇軾集》(卷一)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309頁《書鄢陵主簿所畫折枝二首》其一“論畫以形似,見與兒童鄰。賦詩必此詩,定非知詩人。詩畫本一律,天工與清新。邊鸞雀寫生,趙昌花傳神。何如此兩幅,疏淡含精勻。誰言一點紅,解寄無邊春。”
[47] 《惠崇春江晚景二首》之一,《蘇軾集》(卷一)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288頁。全詩“竹外桃花三兩枝,春江水暖鴨先知。蔞蒿滿地蘆芽短,正是河豚欲上時。”
[48]《蘇軾集》(卷一)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
[49]劉勰:《文心雕龍》(戚良德注說)2008年3月,《宗經》開篇“三極彝訓,其書言經。經也者,恒久之至道,不刊之鴻教也。”
[50]劉勰:《文心雕龍》(戚良德注說)2008年3月,《宗經》篇“皇世《三墳》,帝代《五典》,重以《八索》,申以《九丘》”。
[51]“四書”:指《大學》、《中庸》、《論語》、《孟子》,“五經”指《詩經》、《尚書》、《禮記》、《周易》、《春秋》,“四書五經”皆是封建王朝用于選拔人才的教學典籍。
[52] 劉勰:《文心雕龍》(戚良德注說)2008年3月第一版,《變通》篇指出“夫設文之體有常,變文之數無方。何以明其然耶?凡詩賦書記,明理相因,此有常之體也;文辭氣力,通變則久,此無方之數也。”
[53] 張少康:《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下卷) ,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8月。呂本中的“活法”,嚴羽的“別裁、別趣”,李贄的“童心”說,王士禛的“神韻”說,袁枚的“性靈”說,皆是對文學“法度”說的否定,提倡“多變”且來自于創作者真性情的創作
[54]《凈因院畫記》,《蘇軾集》(卷四)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
[55] 《書吳道子畫后》,《蘇軾集》(卷四)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元豐八年(公元1085年),蘇軾為史全叔收藏的吳道子的畫所作的一篇題跋。
[56] 蘇軾:《論書》之“自論書”《蘇軾集》(卷四)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
[57] 同上
[58] 王水照:《蘇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126頁 十三(豐富多彩的文學創作)
[59] 嚴羽:《滄浪詩話》,《詩辨》認為“夫學詩者以識為主,入門須正,立志須高,以漢魏晉盛唐為師,不做天寶開元一下人物。”
[60] 王水照:《蘇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
[61] 宋黃庭堅在《答洪駒父書》中指出:自作語最難,老杜作詩,退之作文,無一字無來處。該后人讀書少,故謂韓杜自作詞語耳。
[62] 李白:《經亂離后天恩流夜郎憶舊游書懷贈江夏韋太守良宰》,前一句是“覽君荊山作,江鮑堪動色。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飾”
[63] 蘇軾在《祭柳子玉文》中指出“元輕白俗,郊寒島瘦”。“郊寒島瘦”指的是晚唐詩人孟郊和賈島,兩人以簡嗇孤峭的詩歌風格著稱,后人也用此來形容耳二人在詩歌練字方面的執著。
[64] “點石成金、脫胎換骨”是宋黃庭堅的文藝觀點,在《答洪駒父書》,他指出:“古之能文者,真能陶冶萬物。雖取古人之陳言如翰墨,如靈丹一粒,點鐵成金也。”
[65] 《明史·李夢陽傳》“夢陽才恩雄鷙,卓然以復古自命。弘治時,宰相李東陽主文柄,天下翕然宗之,夢陽獨譏其萎弱,倡言文必秦漢,詩必盛唐,非是者弗道。”,李夢陽明朝人,“前七子”之首。
[66] 《蘇軾集》(卷一)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397頁
[67] 《書鄢陵王主簿所畫折枝二首》同上,309頁。
[68] 劉勰著:《文心雕龍》(戚良德注說)2008年3月第一版,《原道》篇說:“惟人參之,性靈所鐘,是為三才”。結合前面談及的天文、地章,稱之為“天地人”三才。
[69] 王水照:《蘇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2月,第 123頁。
[70] 同上,第119頁。
[71] 文說》是蘇軾所寫的一篇書札,短短70余字,總結了蘇軾對文學創作的認知,以及對自然之工和人為之工兩者關系的認知。《蘇軾集》(卷四)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
[72] 王水照所著的《蘇軾》,對蘇軾的一生分了十一個階段,即家庭和早年生活,出入仕途,在汴京,從杭州到湖州,烏臺詩案,謫居黃州,調赴汝州,又到汴京做官,四任知州,再貶惠州、儋州,對他一生的人生軌跡做了簡述,從西到東,從南到北,又包含了中原汴京。
[73] 王水照 :《蘇軾》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第133頁
[74] 《宋詩·晏殊傳》“晏殊,字同叔,撫州臨川人。七歲能屬文,景德初,張知白安撫江南,以神童薦之。”
[75] 劉勰:《文心雕龍》(戚良德注說)2008年3月。
[76] 【清】沈陽孫,馮翼輯:《典論·論文》指出“文以氣為主。氣之清濁有體。不可力強而致。譬諸音樂。曲度雖均。節奏同檢。至于引氣不齊。巧拙有素。雖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氣”作為哲學概念,在先秦諸子中皆有提及。
[77] 【清】吳楚才《古文觀止》 吳調候選編,中華書局,1987年1月。
[78] 王水照:《蘇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第41頁。黃庭堅、秦淮海、晁補之、張耒、陳師道、李廌(zhi 至),稱之為“蘇門六君子”。
[79] “蘇門四學士”,指“蘇門六君子”的前四位,即黃庭堅、秦淮海、晁補之、張耒。“后四學士”指寥正一,李禧、董榮、李格非。
[80] 張少康:《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8月,第40頁,江西詩派是以黃庭堅為師,遵從黃庭堅“點石成金、脫胎換骨”詩學理論,大多與黃庭堅有親戚關系,也是他的學生。
[81] 張少康:《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第163頁,“三袁”指明代湖北公安縣袁宗道、袁宏道、袁中道,以散文創作著稱。
[82] 張少康:《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8月,第136,明代文學流派。前七子以李夢陽、徐禎卿為代表,后七子以李攀龍、王世貞為代表。
[83] 王水照:《蘇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2月,第43頁。
[84] 呂本中:《童蒙詩訓》,轉引張少康:《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第53頁。
[85] 張少康:《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第92頁
[86] 張少康:《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王若虛在《詞話》中對蘇軾和黃庭堅詩風進行了對比,并高度地評價了蘇軾“自然之工”的藝術風格,提出了自己“元氣”與“自得”的審美觀。
[87] 劉熙載,在他的著作《藝概》的(詩概)篇中指出:“東坡詩,善于空諸所有,又善于無中生有,機括實自禪悟中來,以辨三昧而以為韻言,固宜其舌底瀾翻如是。”轉引張少康:《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第94頁。
[88] 郭紹虞在《滄浪詩話以前之詩禪說》一文中對稱東坡的《琴詩》是“妙語解頤已近禪悟”。轉引張少康:《中國文學理論批評史》北京大學出版社,2005年8月第一版,第95頁。
[89] 王水照:《蘇軾》 上海古籍出版,1981年12月第1次印刷,第139頁。
[90] 潘岳(241—300)西晉時期文學家,“泰康文學”的主要代表。字安仁,又稱潘安。有《悼亡詩》三首,為紀念亡妻盧氏所作,傳達了情深意切的感情。出自《晉書·潘岳傳》。
[91]新編諸子集成系列,《四書章句集著》(孟子集注 卷十三)(宋)朱熹 集注 中華書局,1983年版。
[92]《自提金山畫像》,是北宋徽宗建中靖國元年(1101),蘇軾從謫處儋州遇赦北返,途中路過金山寺,看到李叔端十年前給他畫的相,在寺廟主持的小心保管下,依舊在,有感而發所作的一首詩。
[93]蘇軾生于1037年1月8日,到1093年10月貶謫惠州,已經是56歲高齡。王水照:《蘇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2月。
[94]以上年代考證,皆出于王水照《蘇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2月。
[95]王水照:《蘇軾》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2月,第65頁。蘇軾為自己取號“東坡”的軼事,乃出自本書“謫居黃州”的敘述。
[96]王水照:《蘇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2月,第16頁。
[97]蘇軾:《蘇軾集》(卷一)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一版,118頁。《僧惠勤初罷僧職》。
[98]王水照:《蘇軾》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2月,第24頁。
[99] 王水照:《蘇軾》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2月,第69頁。
[100] 蘇軾:《蘇軾集》(二)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
[101] 吟嘯,即清吟長嘯,《世說新語》(十八章)(棲逸)篇記錄阮籍吟嘯的軼事。言“阮步兵嘯,聞數百步。蘇門山中,忽有真人,樵伐者共傳說。阮籍往觀,見其人擁膝巖側。籍登嶺就之,箕踞相對。籍商略終古,上陳黃,農玄寂之道,下考三代盛德之美,以問之。屹然不應。復敘有為之教,棲神導氣之術以觀之,彼猶如前,凝目不轉。籍因對之長嘯。良久,乃笑曰:‘可更作。’籍復嘯。意盡,退還半嶺許,聞上啾然有聲,如數部鼓吹,林谷傳響。顧看,乃向人嘯也。”
[102] 劉勰:《文心雕龍》((戚良德注說)2008年3月,《原道》篇說:“惟人參之,性靈所鐘,是為三才”。
[103] 劉勰:《文心雕龍》((戚良德注說)2008年3月,(原道篇)提出“惟人參之,性靈所鐘,是謂三才。為五行之秀,實天地之心。心生而言立,言立而文明。”
[104] 蘇軾:《蘇軾集》(卷一)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309頁。
[105] 蘇軾:《蘇軾集》(卷四)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
[106] 蘇軾:《蘇軾集》(卷一)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
[107] 《東坡題跋·書摩詰<藍關煙雨圖>》,《蘇軾集》(卷四)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
[108] 蘇軾:《蘇軾集》(卷一)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第360頁。全詩“破琴雖未修,中有琴意足。雖云十三弦,音節如佩玉。新琴高空張,絲聲不附木。宛然七弦箏,動與世好逐。陋矣房次律,因循墮流俗。懸知董庭蘭,不識無聲曲。”
[109] 蘇軾:《蘇軾集》(卷四)黑龍江人民出版社,2005年11月。
[110] 宋嚴羽:《滄浪詩話》(詩辨)篇指出:“近代諸公乃作奇特,解會逐以文字為詩,以才學為詩,以議論為詩,夫豈不工?終非古人之詩也。”
[111] 王水照: 《蘇軾》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年12月,第134頁。
[112] 蘇軾《與鮮于子俊書》中說“近卻頗作小詞,雖無柳七郎風格,亦自身一家。”
[113] 宋后的元明清時期,元曲、明清小說皆為俗文學的代表,這個時期也是俗文學取得巨大成就的時期,而蘇軾代表的雅文學“詩詞”,再也沒有人超過他。加之他在書法、繪畫等藝術上的造詣,更是無人能及。
[114] 王水照:《蘇軾》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12月,第30頁。
[115] 南宋武衍在其《正月二日泛舟湖上》中寫道“除卻濃妝艷抹句,更將何語比西湖。”武衍,字朝宗,原籍汴梁(今河南開封),南渡后寓臨安(今浙江杭州)清湖河。
本文由史映紅推薦發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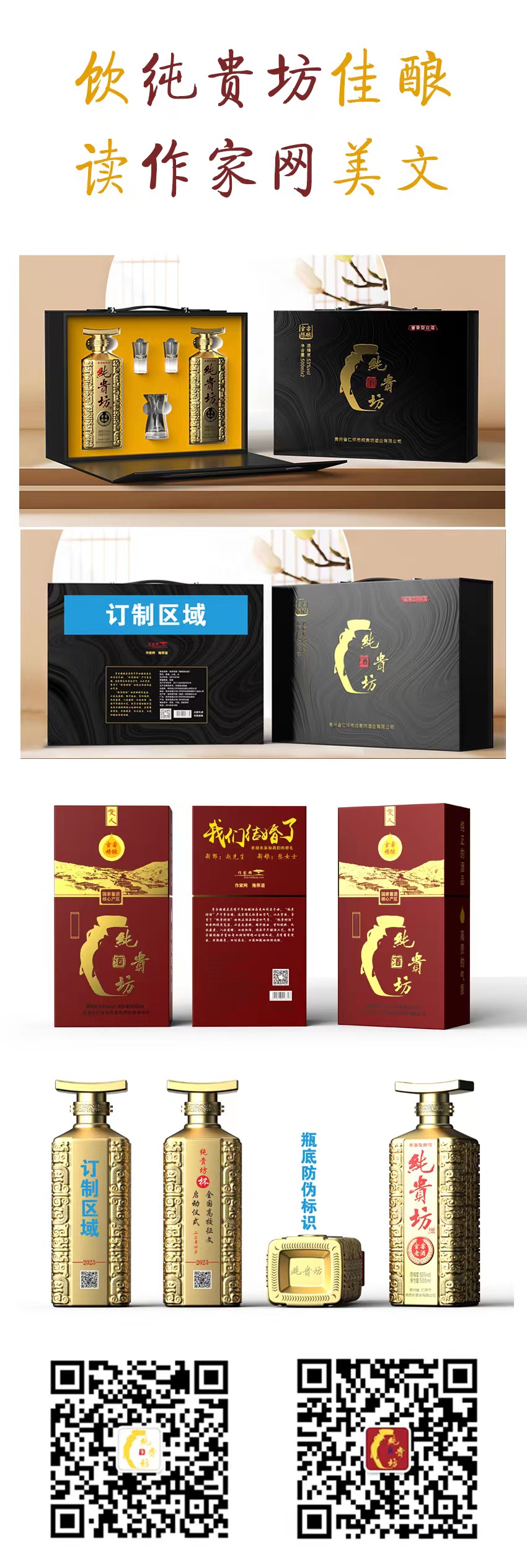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