擦亮青眸讀苦詩
作者:梧葉
編了幾年詩詞,其中見得多的是七律。七律難寫,難在出新意,更難在有分量。一般習作者稍能注意起承轉(zhuǎn)合就不錯了,至于中間的兩聯(lián)對語,只講究對得上,難得有新意有內(nèi)涵;首尾兩聯(lián)則更是敷衍成句,公式化收結(jié),缺乏意味。這讓我想起一些名家巨擘的七律。他們的律詩對句固然精巧奇特,最主要的還在于內(nèi)涵的分量。你看,楊萬里《南溪早春》開頭便是“近家五度見春容,長被春容惱病翁”,一個“惱”字即奠定了全詩的感情基調(diào),猶如一個沉實的秤砣,壓住了虛飄而起的秤桿子。詩詞高手葉嘉瑩女士寫于1942年的一首《秋草》,起句便是“西風掃盡一年痕,迢遞王孫客夢昏”,你看這個“掃”字,何等著力。這都應證了古人說的“起句當如爆竹,驟響易徹”的道理;起句爆響,引人驚而疑之,疑而往之,想不讀下去都難。
蘇軾說得已經(jīng)夠清楚的了:“詩以奇趣為宗,反常合道為趣。”又說,“陶彭澤詩,初若散緩不收。反復不已,乃識其奇趣。”開頭固然不都講究奇特,亦有平中見奇、淡里著味的。反常與合道不妨是相輔相成、陰陽表里,總的得有個尺款。怎樣得來趣味,即在正常的思維情勢下怎樣獲得反常的意趣效果?清代史震林說了:“趣者,生氣與靈機也。”可惜的是,許多人并不解這生氣與靈機,只把它當做靈感與天分。其實,只有經(jīng)歷過大起大落、大悲大苦、大患大難的人,才能將才情化為眼前風景與筆底煙嵐;而“為賦新詞強說愁”的所謂詩家詞客,即使在開篇布置好了玄境與飾景,到了頷聯(lián)頸聯(lián)必然如泄了氣的皮球,再也蹦跶不起來,更別說縱橫捭闔、謹開緊合了。深諳此間至理的詩人多矣,蘇軾當屬其中最杰出的代表。他的《和子由澠池懷舊》寫道:“人生到處知何似?應似飛鴻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鴻飛那復計東西。”這般灑脫和豁達,這般率性和超拔,注定了東坡居士的人格和詩風。苦到極時詩自甘,人生悲歡曲中論。韓愈、柳宗元、李商隱、劉禹錫、歐陽修等人莫不如是。
歷代評論家論詩,多在詩味。大凡詩之味道,可與飲食同,甜酸苦辣咸五味俱存焉。甘之如醴,淺嘗可矣;酸溜如醋,大可開胃;辛辣如姜,暢快淋漓;苦冽如藥,開竅醫(yī)愚;腥膻汗血,悚然駭然……這里撇開其他,單說苦味;撇開古時,單論現(xiàn)代。
苦吟,是一段漫漫長途,是詩人錐心泣血的自然流露,是中國詩詞傳統(tǒng)的一道風景。盡管這苦,有身之苦、心之苦、情之苦、志之苦、病之苦諸般,但一經(jīng)入詩,便有耐嚼耐品的魔力,便有感動感化的內(nèi)蘊。我們先來讀讀弘度(劉永濟,歷任東北大學教授、武昌武漢大學教授兼文學院院長,浙江大學、湖南大學及武漢大學語文系教授,湖南文聯(lián)副主席。文革中被打成“反動學術權(quán)威”,1966年含冤去世)的《老去》:
老去空驚世變新,眼中紅紫不成春。
酒觴自覆非關病,客座長虛始覺貧。
九奏何心娛醉帝,百靈低首拜錢神。
昏檠兀對茫如夢,又聽西風起白蘋。
讀者首先被震駭?shù)囊苍S是那個“驚”字。自然,尋常年月度,老去不須驚,若“驚”者,自是未識已老之人。世界在變化,在革新,人若跟不上,必當驚醒亦或驚訝了。但是,春去了,興淡了,友朋少了,盛氣衰了,錢權(quán)棄了,欲望滅了,更為重要的是,作為一名學者,不能發(fā)揮自己的學術作用,不能為人民做事為國家出力,這才是真正的“老”,老得泫然,老得無奈:他是在警醒后來人呢,還是真地把人生當成了夢?全詩句句言孤苦,卻不著一苦字,只見世道渾濁、小人當?shù)溃娙藨嵍磺C而不撓的獨立人格卓然在茲。
茶余飯后,檢索了一些現(xiàn)當代詩人的錦繡七律,合為一卷,暫且命名為《七律摭萃》,上自孫文秋瑾黃興,下至活躍在今天詩壇上的詩人們。選編的原則就是一個“新”字:有的屬于思想新,有的則是創(chuàng)意或構(gòu)思巧妙,還有的是意象新、視覺新、語言新。然而,無論是哪方面的新,都不是無病呻吟之作,都只是摧撼肝腸的作品。簡單地說,是母蚌之珠,是樹疤之淚,是詩人苦吟的結(jié)晶。比如聶紺弩《散宜生集》中的七律,在表達方式上就別具一格,他把白話寫成了極為典雅的格律體,讀來令人解頤解氣,過目難忘;但是看過之后就笑不起來了,只有和淚的喟嘆與沉痛的哀惋。且看那首《又作搓草繩調(diào)王子夫婦》:
冷水浸盆搗杵歌,掌心膝上正翻搓。
一雙兩好纏綿久,萬緒千頭繾綣多。
月下一牽情更篤,風流欲綰日西矬。
幾生修到荒原草,炕土蓬窗兩任過。
又如《削土豆傷手》:
豆上無坑不有芽,手忙刀快眼昏花。
兩三點血紅誰見,六十歲人白自夸。
欲把相思栽北國,難憑赤手建中華。
狂言在口終羞說,以此微紅獻國家。
在北大荒凄風苦雨的日子里,詩人以苦為樂,把日常枯燥苦累的農(nóng)活化成了幽默詼諧的詩行,字字見性,語語平易。“幾生修到荒原草”“以此微紅獻國家”,語似閑吟,意卻凝重,言外之意,促人沉思。
與聶紺弩先生相比,老舍的詩同樣不乏這般自嘲自諷的意味。因為他們追求自由的人格是那么地相似,而堅守品格操行、剛正不阿的秉性又如此地相同。《端午》其二云:
小江腳短泥三尺,初試新鞋來去忙;
迎客門前叱小犬,學農(nóng)室內(nèi)種高粱;
偷嘗糖果佯觀壁,偶發(fā)文思亂畫墻;
可惜階苔著雨滑,仰天躓倒?jié)M身漿!
小江是老舍的小孩子,詩人看到6歲的孩子“仰天躓倒?jié)M身漿”時的情狀,內(nèi)心何等負疚而不安,但是生活在戰(zhàn)爭煙火中的窮困文人,為了迎接好友的到來,就連孩子也自顧不暇了。
再如沈祖棻的《一夕》:
一夕純鱸寄夢思,秋風何事滯天涯。
病多倚枕殘更后,路遠扶筇日落時。
燕壘蜂房俱可羨,烏頭馬角總難期。
朋交幾輩成新鬼,猶自音書隔故知。
讀到尾聯(lián)兩句,我們自然想起魯迅的“忍看朋輩成新鬼,怒向刀叢覓小詩”,也必然想到詩人的夢和病是由何而起的了。詩中意象諸如純鱸、秋風、病體、殘更、遠路、落日,都形成了一個烘托哀景的整體,而在頸聯(lián)的對比中,更顯“音書隔故知”的痛苦和無奈。這一聯(lián)的“烏頭馬角”典故也用得自然得體,烏頭白,馬生角,典出《史記˙刺客列傳》,喻不可實現(xiàn)之事,加深了“隔故知”的現(xiàn)實性與鐵律感。
我們可以列出大量這類苦吟之作,足可以證明它們是動人心魄的好詩:
如許傷心家國恨,那堪客里度春風。(秋瑾《七律一首》)
入夜魚龍都寂寂,故山猿鶴正依依。(黃興《回湘感懷》)
金輪轉(zhuǎn)劫知難盡,碧海量愁未覺寬。(呂碧城《瓊樓》)
嘆息故園多鶴唳,懶從滄海看龍爭。(李烈鈞《過金陵舟中晚眺》)
憑欄無限憂時淚,如此湖山號莫愁。(張恨水《由北平到南京有感》)
三年攬轡悲羸馬,萬眾梯山似病猿。(高旭《擬石達開致曾國藩詩五首》)
不覺肺肝生白露,空憐河漢失流暉。(鄭孝胥《望月懷沈子培》)
夢里關河聞唳鶴,兵間身世寄飄蓬。(鄧拓《寄語故園》)
閑愁大豈三杯了,世味寒從一葉知。(熊東遨《謝袁第老新春賜詩元韻》)
……
文末,以岳西詩詞學會老會長王業(yè)記先生一首七律作結(jié),其中摹寫王澤翰老師臨終苦況,難道還不催人淚下?《二〇〇五年六月二十九日王澤翰老師在中小閱卷猝歿,感而有作》:
漫云馬革裹尸還,忍對蠶僵蠟燭殘。
生入校樓批試卷,死無棺柩殮衣冠。
人嗟人道時時變,官答官腔事事難。
桃李誰思悲坐帳,教師能不覺心寒?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quán)發(fā)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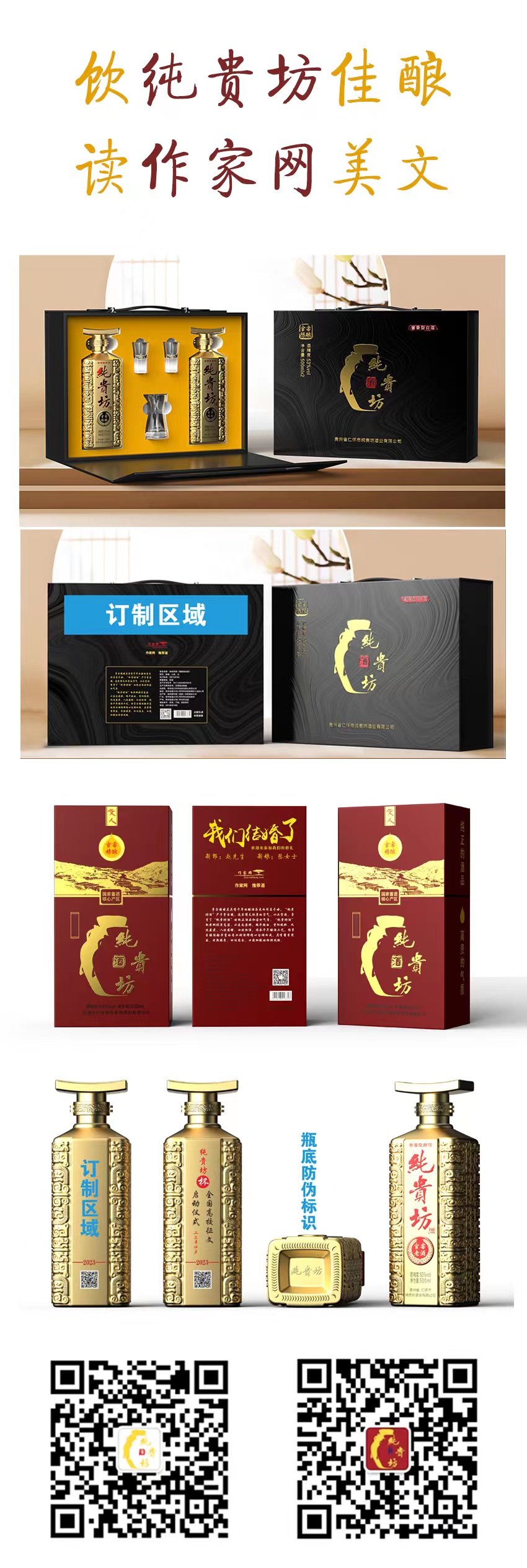


 純貴坊酒業(yè)
純貴坊酒業(y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