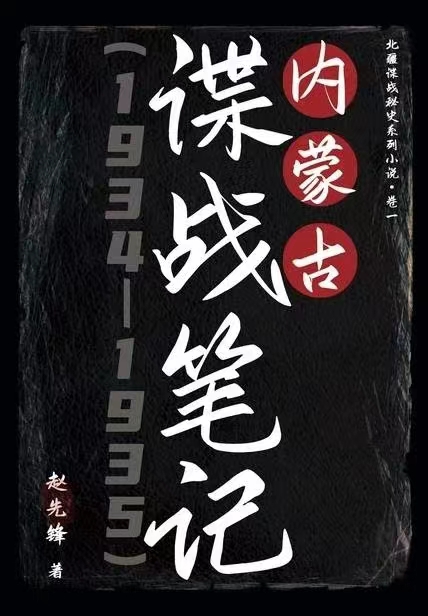
在大鷹爪下記事
——讀趙先鋒長篇小說《內蒙古諜戰筆記》卷一
作者:許氶
首先我要說,作家趙先鋒的長篇小說《內蒙古諜戰筆記》驚艷了我。
提到趙先鋒,一定繞不來北疆大地,他像一匹耐力持久的蒙古馬,總是奔走在充滿閃電的夜晚,而所踏過的腳印更是讓人出其不意,我們都稱其為北疆地域的“文學燈塔”;這點絕無吹噓之意。當我讀罷這部將北疆物事和歷史悄然結合的諜戰小說后,心中竊喜,隨后禁不住拍手叫絕,文字內里崎嶇,大量的歷史背景和鮮明的人物以及小說中的奇景奇觀堪比一場好萊塢巨片,活脫脫被這個“燈塔”照亮了。很亮,在這海的盡頭即草原的地方,這位既是詩人又是小說家,近年來又同時搞起電影事業的人,操刀老本行,顯然無意中開辟了另一條敘事蹊經——“公路諜戰小說”,或說這是首部中國的“公路諜戰小說”,僅從這點來看,就足以讓更多的讀者去細品。
讀這部小說,就是在走一條驚險的路,因為故事本身的翻山越嶺和長途跋涉,帶著讀者領略北疆地域獨有的自然和人文屬性,同時結合抗戰和邊疆諜戰特有的視覺效果,更是將這部小說的閱讀趣味擴大化。例如開頭,從莫斯科郊外的夜晚說起,直接拉長了敘事本身的空間距離。讀者沿著主人公的軌跡穿過草原、戈壁、大漠、河流、丘陵,也會跟著一度冒汗,這正能體現出趙先鋒在行文上嫻熟的技巧處理。小說就是說話,甚至故事大于敘述,趙先鋒的這部劇本式小說無疑模糊了傳統小說的抒情色彩,持續加大人物間的對話,通過大量的對話將閱讀小說的過程提升到看美國大片的視覺和聽覺過程,整體上更像夾帶了3D效果。當然這種強烈畫面感的支撐和趙先鋒的詩人身份不無關系。這里不得不提到趙先鋒的詩人身份,和這位“文學燈塔”認識之初,因為詩歌,他總能用自己文字中最強的光照亮一片土地的死灰,甚至足以割裂年齡的界限,讓彼此的靈魂火燒火燎,即便最深的夜也同樣激昂著。
語言是詩人的匕首,也是小說家的刺刀,趙先鋒的語言足夠鋒利,純粹詩性的語言更是給這部小說帶來別致的想象。例如在描述老駝頭對赤胡狼群中寫到:一只赤胡狼半個時辰就能吃完一頭牛,兩排白茬茬的、鋼釬一樣尖銳鋒利的牙齒能把人一口攔腰咬斷。它們喜歡嚼牛脖子、羊脖子、人脖子,不管什么脖子。它們餓瘋了的時候,狂奔的蹄聲如悶雷滾過水面,渾身散發的血腥氣,就算是一座山也要被它們撞碎兩塊巨石。實話說,類似這樣的句子恐怕國內再尋不出第二人來,這是經過幾十年來詩歌化語言訓練后的結果,短短幾句便可看出趙先鋒的性格,痛快、火焰般劇烈燃燒著,他仿佛不僅在寫一只赤胡狼,更像在寫自己,一種不多見的沖擊力和對生活的熱度。或者說這是生長在北疆地域的詩人獨特的經驗體質,情感和共情力,某種程度和詩人溫古的“在大鷹爪下簽名”類似。語言是趙先鋒的匕首,一位坐在酒桌深處的詩人,比失戀的人更易醉,趙先鋒不會醉,或說很少醉,亦或說他的醉是一種詼諧,是用海浪般的語言不斷擊打的天際。語言說到湍急處,必會產生詩意的浪花,趙先鋒的語言就像懸崖邊湍急的大河,總會閃出一層又一層浪花,這點上吻合小說的情節,急促有致,最終他獨特的語言輕松駕馭素材的優勢就露出來了。
當然,除過敘事和對話,趙先鋒以景寫事的能力也毫不遜色,例如:一只豹鴉盤旋在馬王溝的上空。半天了,既不飛走也不停落,王景農歪著腦袋盯了它很久。他將物象用到極致,他精準地敘述著細節,這種語言的奇觀和底色正是他詩人身份的再度體現。除此之外,這部小說的主線亦崎嶇,所涉及的文化之龐雜,歷史之交錯足以看出趙先鋒有著龐雜的知識體系和閱歷。尤其是小說后半段中,主人公意外發現的疑似成吉思汗陵確定是煤田,全身而退之前引爆了瓦斯,從而消滅了日本特務頭子,更是峰回路轉,頗具神秘性,這也正是這部北疆地域的公路諜戰小說中的獵象和奇景奇觀之一。
回頭審視,這是一部立意獨特的小說,里面夾雜的種種事件足夠有趣,文學性和文本質量亦是上乘,這是趙先鋒給這片土地做出的又一個靈魂工程的巨大貢獻。愿文學燈塔常亮,在那些杯與杯碰撞的日子里,眾神選擇了彼此的敘述對象,趙先鋒算其一。
作者簡介:許氶,90后,陜西人,詩人,動物營養學青年學者,屢獲全國詩歌大獎,現居呼和浩特。
微信讀書閱讀鏈接:
微信讀書9月聯合出品精選書單鏈接
https://mp.weixin.qq.com/s/m86FIpbZ-JxCiXjl3e605g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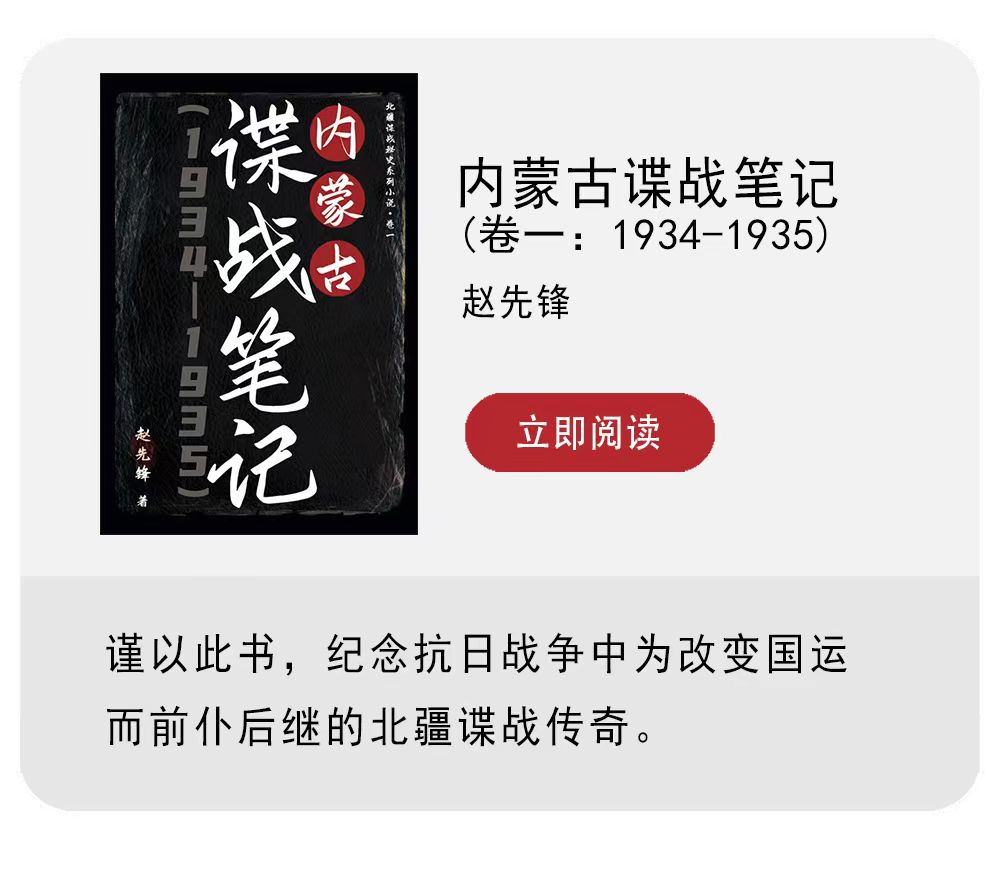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