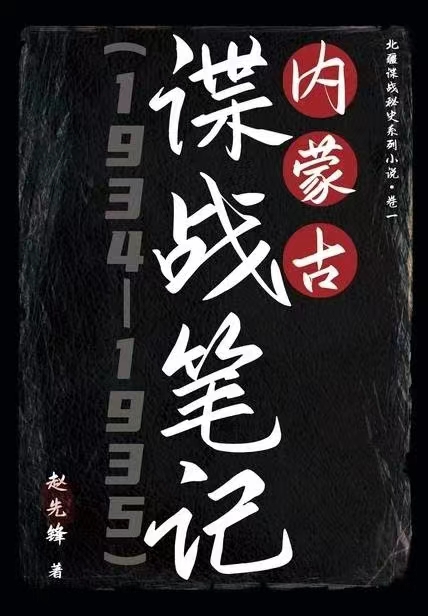
萬里北疆圖
——趙先鋒的《內蒙古諜戰筆記》
作者:閻錫四
前些日子,著名作家孫甘露的那本名為《千里江山圖》的長篇小說,獲了第十一屆茅盾文學獎,這個小說寫的是發生在上世紀三十年代上海的諜戰故事——中共地下黨組織為保護中共一位重要領導人轉移出上海,和國民黨特務斗智斗勇,并付出了巨大的犧牲。孫先生以前是先鋒小說家,可以說以晦澀和異端的表現方式著稱,二十年后,他在質、數雙量上的側重點,以及從文本技術上,非常中規中矩了;開句玩笑話,孫先生已不復當年之勇。這兩天,我碰巧讀到了內蒙古作家趙先鋒的一部長篇小說,也是寫諜戰故事的,發生地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末北疆(俄境、蒙古和內蒙古一線上),竟然令人有耳目一新的感覺。
中國的影院和電視、視頻平臺上,諜戰片(劇)一直保持著不錯的票房和收視率,比如諜戰片《風聲》《懸崖之上》等,比如諜戰劇《潛伏》《暗算》《風箏》《懸崖》《黎明之前》《偽裝者》等,一位出品過多部諜戰劇的影視公司老板說過這樣一句話,(大意)諜戰題材是永不過時的朝陽產業。這說明,在中國諜戰題材是個成熟的文藝類型。
趙先鋒的這部長篇小說命名為《內蒙古諜戰筆記》,乍一看,走的是“廁所讀物”的商業路子,但讀過之后,發現若不是囿于題材的限制,作者呈現的其實是個純文學文本(據說,這是一個網文版本,還有純文學版本),敘事、語言、修辭、結構、對話等都做得不錯,有美國作家科馬克?麥卡錫、斯坦貝克和前蘇聯作家肖洛霍夫的風格。其實,趙先鋒從上世紀九十年代初一直以筆名趙卡在從事詩歌、小說和隨筆批評寫作,現實主義和具有先鋒性質的文本在他的筆下并行不悖,但突然殺出個諜戰類型而且是獨樹一幟的公路諜戰小說,著實令人吃驚不小。
眾所周知,近二十年來的諜戰媒體作品幾乎集中于那幾個城市:北京-如電視劇《北平無戰事》;上海-所有聚焦在極司菲爾路76號的作品;重慶-如電視劇《風箏》;哈爾濱-如電視劇《懸崖》《和平飯店》;天津-如電視劇《潛伏》,等等。諸方狂喜過后,忽視了這里面有個審美疲勞問題,所以至少近三年來乏見還有高收視率的諜戰片(劇)。
諜戰作品問題的結癥,從趙卡的《內蒙古諜戰筆記》這部長篇小說就可以得到啟示:從諜戰類型里再細分類型,即從城市(密室)諜戰轉向公路諜戰。
應當說,“北疆”這個領域對大多數人來說太陌生又太神秘了,無論歷史還是地理,但在作者那里,就有了講故事的巨大彈性,作者也因此強調,“北疆”概念在小說里具有不可取代的獨特性。由此,我們可以想到科馬克?麥卡錫的墨西哥平原和肖洛霍夫的頓河,在時代生活與個人知識經驗上,大師啟發了作者的強勁想象力。
作者的“雞賊”(原諒我不禮貌地用了這個詞)主要表現在敘事信息密度極強的故事奇觀上,從結構、人物、對話和場景轉換上看,作者絕對有改編成影視的意圖,一旦將小說變成影視,將來呈現給人們的肯定是視聽奇觀。也就是說,小說的影視化效果,是作者故意為之。
小說講了一個秘密轉運戰略物資的故事,從俄境的恰克堡到中國的延安,曲線行程近萬里。故事是雙線講述的,一條走人,一條走物;走物的駝道又分出一明一暗兩條來,使得小說的公路性質極具張力,甚至敘述結構也有了某種隱喻的功能——走上歧途。
作者寫這本書之前應該是做了大量的功課,但這些功課并沒有支配他的寫作,也就是說,地方性知識不能以知識的方式和想象力競爭,這是作者的基本認知。由此,我們看到,這本書里的歷史、地理地貌和民俗背景,有可能是假的,或者說,被作者篡改了,或被重新杜撰了。“篡改”和“杜撰”,是任何一個抱有雄心的作家的一項基本素養,目的在于迫使讀者讀的時候信以為真;在羅伯特?麥基那里,體會這些看似合理的東西,則是另一番面目:“一個作家為什么要在虛構事件上對我們進行誤導呢?原因有二:強化可信性,強化好奇心。”
這本書的內容糅雜,覆蓋面也夠大,故事跌宕起伏,好讀,但深度上略有欠缺;所以我更愿意認為它的影視改編價值大于原著的出版價值,因為歷史、諜戰、戰爭、公路、冒險、尋寶等任一元素類型均可放大,從故事體量和內容跨度方面看,尤其適合電視劇或網絡劇。但改編電視劇或網絡劇的話,“節奏”的強化是一個重點。比如,以人物帶動節奏,尤其是,在內容強化方面最好是削弱主角光環強化周邊人物。這個想法是劇集的,即為每一集核心人物不同,在內容創作方面,針對主角及周邊人物的功能性和事件作用進行強化,從而單集以事件核心人物作為主角啟動故事,其中不排除配角和反角形成單集主角概念。此設定在故事展現方式和劇集概念方面的新穎度可以做出新的高度,并在整體觀感上和核心故事的驅動上更為飽滿。
扯遠了。一句話,這本書的故事有明確的 IP 養成基礎及系列影視作品開發價值。
很長時間以來,內蒙古的文學是被邊緣化的,由此,有時我們不得不感嘆內蒙古作家不被各方重視的命運,一種文學史的自卑就不可避免地發生了,而如何克服自卑又是個問題;是啊,這就是命運。我所知道的趙先鋒,以前是寫純文學作品的,在全國各種期刊上發表了五十多篇中短篇小說,也獲過重要的的文學獎項,但他在業內的名聲竟然來自文學評論,這就有點令人匪夷所思了。這部小說是他的第一部長篇,而且是類型的,看來趙先鋒在對自己的寫作進行了一次極為重要的也極為艱難的轉型,就是具有文學底蘊的類型小說;我還知道的是,他的偶像雖然有肖洛霍夫、托爾斯泰、科馬克?麥卡錫、斯坦貝克、馬爾克斯等,但也有類型小說大師喬治?馬丁和肯?福萊特,這樣就可以解釋他的轉型了。
需要強調的是,趙先鋒的《內蒙古諜戰筆記》不是歷史小說,按圖索驥式閱讀會讓人誤入迷宮,曾經有讀者跟趙卡探討他小說里的人名、地名和相關歷史上的事件,他都一概答復為他所有的小說全是虛構,甚至明明是真實的人名、地名,他也堅決不承認是真實的,稱那純屬巧合。他如此執拗,不接受對號入座式的閱讀規則,定是有著不可為外人道的某些隱秘緣由;或許,他希望他的文本還有其他可能的闡釋。
無論從歷史上看還是從省域行政建制上看,內蒙古的建區(省)史是嶄新的(可追溯烏蘭夫“單刀赴會”的英雄事跡),內蒙古的文學起步比較晚,所以我前面說過可能內蒙古的作家存在一種文學史的自卑,文學史的自卑其實就是作家的自卑,但這種自卑并不愚鈍,畢竟內蒙古以雙語(漢語和蒙古語)形式涌現出了那么多的詩人和作家。但若做個簡單地描述,我是不忌憚使用集體主義語氣這個現象概念的,特征太鮮明了。上世紀八十年代后期九十年代初期內蒙古的文學的確出現過一陣小高潮,后就迅速滑落到了低迷期,直到以趙先鋒為代表的若干70后作家在最近十年內的崛起。
基于“北疆”概念的地域寫作,是內蒙古一些作家包括本書作者發現的一大法寶,此地面積巨大,環境亦險惡,猶如一幅萬里北疆圖,而以趙先鋒這一類作家,內心里都駐扎著一個尤利西斯,在歸返文學的伊薩卡島途中總能化險為夷。就如眼下這本公路諜戰小說《內蒙古諜戰筆記》,作者將他的類型觀念發展成了一種地域寫作美學體系,比方說,在故事敘述的進程中,他會有意彰顯某時某地的實物場景,并從中挖掘出奇觀性的特征,令人嘆為觀止。
我聽說這部小說兩年前在愛奇藝平臺下的一個影視小組手里駐留過,不知什么原因(或許是疫情)無果了,最早的IP定位是“中國版的《權力的游戲》”和“抗戰版的《長安十二時辰》”——如果是“中國版的《權力的游戲》”,重點強調多線程同時推進、多人物命運軌跡、多地形畫風跨越、多情節節奏變換;如果是“抗戰版的《長安十二時辰》”,則強調事件與人物同時推進、時間炸彈分秒必爭、錯綜復雜撲朔迷離、多重勢力詭詐漫天。我認為兩者的開發方向都是不錯的。如今,這部小說由杭州沙發娛樂機構重點包裝打造“中國公路諜戰小說第一書”概念,我相信書會引發閱讀狂潮,作者也會被他的讀者談論。
作者簡介:閻錫四,來自網絡,信息不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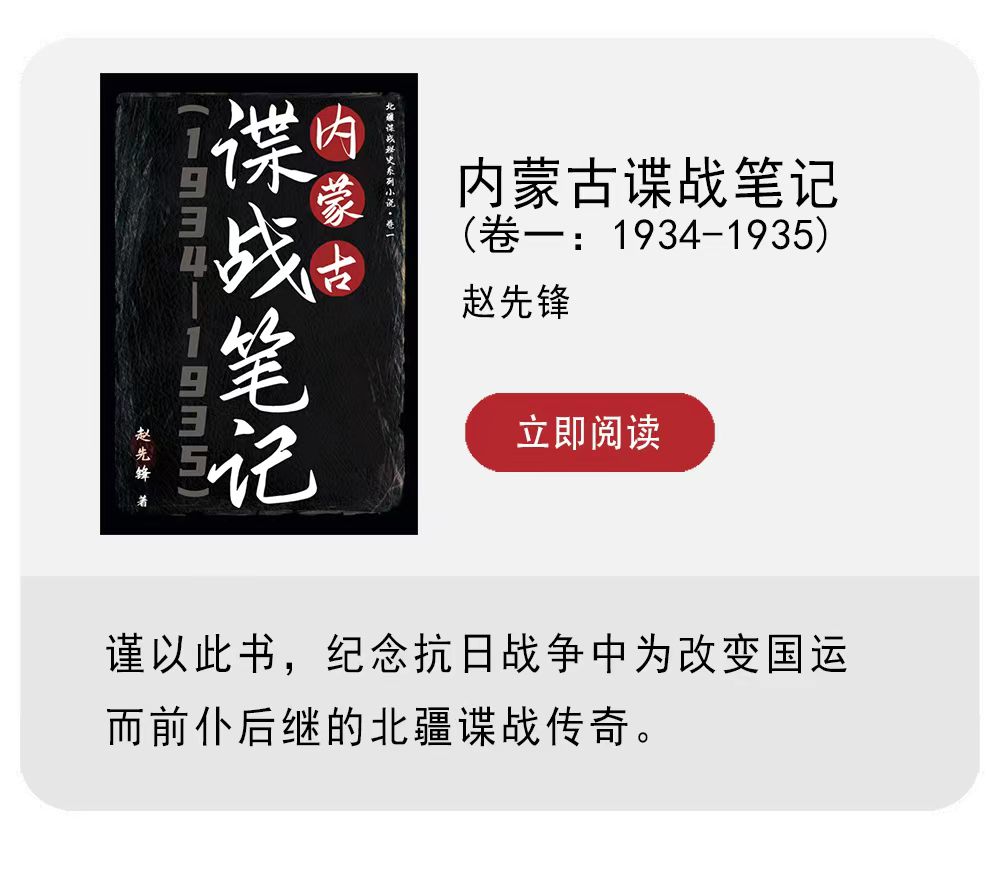
附:
微信讀書閱讀鏈接:
微信讀書9月聯合出品精選書單鏈接
https://mp.weixin.qq.com/s/m86FIpbZ-JxCiXjl3e605g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