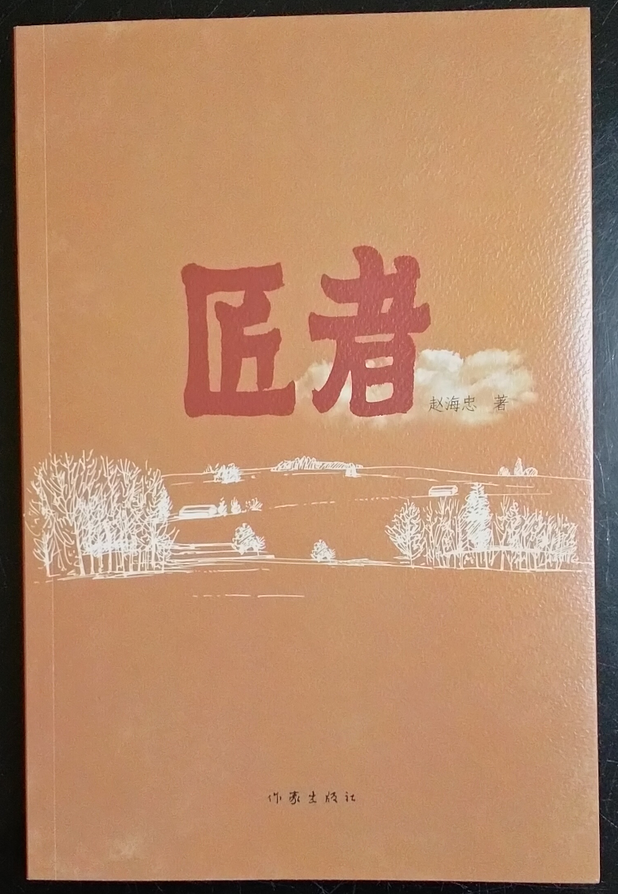
形散神凝花落草原
——小說《匠者》與《呼蘭河傳》比較閱讀
作者:王美珍
二月份剛剛讀完蕭紅的《呼蘭河傳》,三月份又拜讀了趙海忠教授的新作《匠者》,懵懂之中產生了想把這兩部作品放在一起比較的沖動:這兩部作品產生的時代不同,表現的社會主題迥異,但在寫法上,筆者認為有相似的地方。作為一名高中語文老師,因前有各位大咖專業的評價珠玉在前,我只有另辟他徑,把自己粗淺的認識綴成文字,見笑于諸君。
《呼蘭河傳》是女作家蕭紅1940年創作于香港的小說,反映了北方小城呼蘭河20世紀20年代的社會風貌和人情百態。小說《匠者》是趙海忠教授出版于2023年12月的長篇,反映烏蘭察布草原80年間的歷史變遷。
兩部小說有明顯的不同。
一是篇幅長短。《呼蘭河傳》共七章,21萬字;《匠者》共22章,34萬字。
二是敘述視角。《呼蘭河傳》采用兒童視角和成人視角交替的敘述方式,兒童視角回憶了“我”的童年生活,困惑著人們加諸小團圓媳婦兒身上的一切;成人視角介紹了呼蘭河城的社會風貌和風俗人情:東二道街、西二道街、十字街、大泥坑,跳大繩、唱秧歌、娘娘廟大會等。而《匠者》則全部使用第三人稱全知視角。
三是內涵意蘊。《呼蘭河傳》表現封建社會的保守、落后和愚昧,封建觀念對人們思想的桎梏,對平凡普通命運的踐踏。《匠者》則全景展現了烏蘭察布草原的一代匠人勤勞踏實、善良淳樸、在技藝上精益求精的精神內核,處處展現勞動之美。
下面重點談談兩部小說的相近之處。如果說《呼蘭河傳》是一幀照片,那么《匠者》則是現代版“清明上河圖”,二者最大的相似之處就是散文化的構思和行文方式。
一、人物塑造的散文化。《呼蘭河傳》重在描繪呼蘭河城的社會風貌和人情百態,不以塑造典型人物為目的,只在五、六、七章集中描寫了小團圓媳婦兒、有二伯、馮歪嘴子三個人物。而這三個人物,也最終成為作者批判的社會環境的一部分。且三個人物的故事互不關聯,各自獨立,體現了濃濃的散文意味。在人物塑造方面,《匠者》主要人物十幾個,次要人物幾十個。根據他們從事的職業,大約一章寫一個匠人,沒有刻意突出哪一個匠人,每個人的故事都可獨立成篇。每一個匠人的故事短而精,性格上較少變化,大多屬于“扁平人物”,就像散文的一個段落。然而可貴的是,作者塑造的二十幾個人物個個來歷不同,身形各異,卻又性格鮮明,呼之欲出。這都歸功于作者對鄉村匠人生活的極端熟悉和對農村平凡瑣碎日常的細致體察,以及進行創作時的高度藝術提煉。
二、情節處理和結構設置的散文化。兩部小說都淡化情節,可稱為“非情節化”小說。不講究開端發展高潮結局,不設置起承轉合、跌宕起伏的情節。《呼蘭河傳》一二章是對呼蘭河城風情風俗的描繪,三四章是我對童年的回憶,突出“我家是荒涼的”。五六七章分別介紹小團圓媳婦兒、有二伯和馮歪嘴子,各章體系獨立。《匠者》的獨立性更明顯。除了三畫匠、七鼓匠、賀大頭媳婦兒和三干頭媳婦兒幾個人物不連續地貫穿全篇,其他人物都各自在自己的章節里完成自己的故事。如二板爹、古車豁子、李大爺、釘盤碗兒等人。二者都充分具有散文“形散”的特點。在結構設置上雖類似于中國古典小說的章回體,但不同于章回體的是,它的情節前后不勾連,一章就是一個人物的橫截面,不同的橫截面共同繪制出呼蘭河城和烏蘭察布草原的民俗風情畫卷。
當然,《匠者》個別人物也介紹他的“歷史”,比如三畫匠和七鼓匠,除了開頭前兩章重點介紹二人的沖突以及和解,在其他各章中,還穿插交代了他們的幼時經歷和上學趣事,直到結尾的“上海之旅”,從而完成了這兩個人物的成長史。由于人物眾多,在這么長的篇幅里、在不同的章節里讓人物故事連點成線,連線成面,這仰賴于作者縱橫捭闔的駕馭和布局故事的能力,讓人嘆服。
三、寫作技巧的散文化。由于兩部作品在篇章上可以獨立成篇,所以在寫作技巧上也追求散文化的情調。在寫到地理環境、世態人情時,語言簡練,不用濃墨重彩渲染。
《呼蘭河傳》在寫到呼蘭河城的結構、街道布局時語言平淡質樸,如話家常,北方小城在讀者的眼前仿佛一幅簡筆畫。《匠者》更是如此。比如開頭的描寫:“塞外鄉間,跑動著各種手藝人,這些手藝人不同于其他農民,一技在身,在村里的身份僅次于干部。普通百姓,自己辛苦勞動,秋天分全年口糧,手中很少有活錢。養豬賣幾十塊,過年前給孩子們做一兩件新衣。夏秋季節賣雞蛋、兔子,買醬醋油鹽、針頭線腦。”語言簡凈,幾乎再不能刪去一字。給人閑散又凝練、輕松又疏放的美感。文中很少使用長句,語言像生活一樣樸實。畫物寫人多用白描,三言兩語,惜墨如金,但人物形神畢肖,如在目前,猶如中國畫的寫意。
當然,兩部小說中也有工筆細描。《呼蘭河傳》寫小團圓媳婦時,關于跳大神和洗熱水澡的描繪,筆墨之細,揭露之深,令人嘆為觀止。《匠者》寫到匠人們的勞動過程時,也是精雕細刻,充滿了勞動的美感。比如,寫好女巧靈剪紙,“時而,這兩只手猶如一對戀愛的麻雀,纏在一起,嘰嘰喳喳,頻頻點頭,小小的嘴把紅紙啄破。時而,這兩只手恰似一對新識的燕子,空中翻飛追逐,親昵試探,那是雙手變換著角度和手法,或扎,或剪;或大曲線鉸法去瓤,或小幅度花切出毛。該留下的留下,該剪掉的剪掉。眾人屏住呼吸,紙屑掉落炕席,有雪花飄落般極其細微的聲響。有幾片紙屑染了靜電,粘在貓狗身上,貓狗試了幾下去不掉,也就懶得去動它”。描寫精細到角度、手法,甚至掉落的紙屑粘在貓狗身上的細節,都躍然紙上。勞動過程充滿了美感、和諧、輕巧,與巧靈的形象水乳交融。
小說結尾也充滿散文的意味。《呼蘭河傳》的結尾,寫馮歪嘴子的兩個孩子,“給他東西吃,他會伸出手來拿,而且小牙也長出來了”,“微微一咧嘴笑,那小白牙就露出來了”,戛然而止。純粹的白描,沒有任何刻意的修飾,仿佛故事才剛剛開始。《匠者》的結尾,“手藝人知道,在那個山谷褶皺,杏林之東,有杏村”,毫不經意的結尾,散淡而自在,多么疏放的收束。
散文的特點是“形散神聚”。從形上來說,《匠者》二十二章各自獨立成篇,風采各異;那么,她的神是什么呢?筆者是這樣理解的:杏村是本文物質上的神,靈魂上的神是對烏蘭察布這片土地、土地上的人、土地上衍生出的鄉土文化的真摯熱愛。
當然,小說的語言也有值得稱道之處,大量方言的點綴,讓人忍俊不禁的同時,仿佛重回童年時代;她又分明是一部烏蘭察布方言教材。
總之,趙老師的小說《匠者》,除了小說的厚重,長詩的意蘊,更具散文的 “形散神凝”的落落大方,自由而又節制,粗獷而又細膩,就像一朵繁花降落草原,讓烏蘭察布這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重新走入大眾的視野。
向那些勤勉耕耘、書寫歷史的匠者致敬!
作者王美珍,烏拉特前旗一中。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