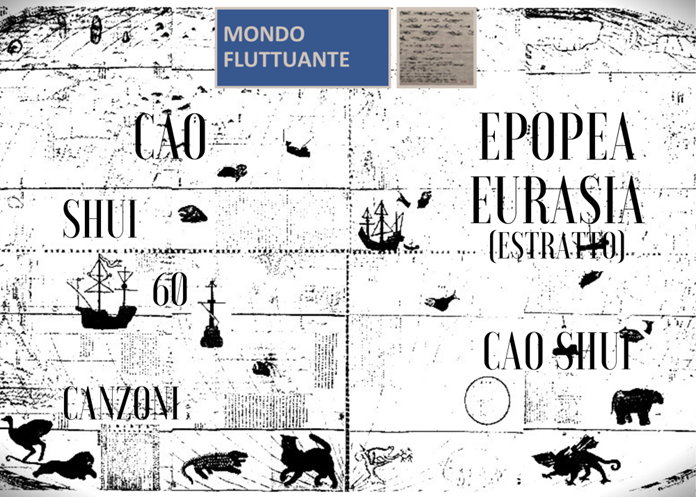
《亞歐大陸地史詩》:共同的基礎、共享的根源和普世的精神
作者:瑪利亞·特蕾莎·德·多奈特(美國)
曹誰/譯
“2008年9月1日,我果斷辭去了《西海都市報》的職務,開始了我一直計劃的一次行走:從青海出發,南到西藏,北到新疆,這兩個中國最神奇的地方。在我看來,昆侖山以北的新疆沙漠和昆侖山以南的青藏高原是亞歐大陸的陰陽中心……在我看來所有的山都從這里開始,所有的山也都從這里結束。”(曹誰,第94頁)中國著名作家、詩人、編劇曹誰的上述表述,為更好、更全面地理解其出版的《亞歐大陸地史詩》的精神、意圖和內容鋪平了道路。
我們已經通過曹誰的作品《帝國之花》認識了他,這是一本由意大利花達西亞出版社翻譯出版的三種語言的詩集,我很高興也很榮幸能閱讀和評論。正如我在那次評論中所解釋的,“閱讀、解讀和回顧曹誰的《帝國之花》并不容易,但卻異常迷人,同樣令人興奮”,“偉大的文化、深刻的感悟、平等的分析能力和360度觀察世界的能力,在這部文學作品中脫穎而出,成為曹誰詩學的旗艦。”(德·多奈特,2023)
正如我們即將看到的那樣,《亞歐大陸地史詩》的特點是,元素在其敘事發展中發揮了根本作用。
首先,這部作品的真正主人公是位于美索不達米亞的亞歐大陸,“曾經是人類自由的夢境”(第14頁)。根據歷史記載,人類文明起源于這一地區。此外,人們經常提到巴別塔和帕米爾高原,后者是位于中亞的山脈,與天山、喀喇昆侖、昆侖、興都庫什和喜馬拉雅山脈交界。
曹誰似乎有意或無意地將帕米爾山作為一種隱喻,甚至作為即將實現的新巴別塔的預兆,巴別塔重建,至少在象征意義和文化意義上,是他文學作品的最終目標。
正如曹在這部作品中所解釋的那樣,“史詩是一個民族集體精神的象征。今天,史詩的存在早已消失。我們面對的是一個世界而不是一個民族。我們生活在科學而不是神圣的故事中。我們用自由詩而不是格律詩。”因此,現代史詩的理念面臨著前所未有的合法性危機。這部史詩最初是一種原始的文學形式。在里面,它包含了一個描述整個民族發生的故事……”(第13頁)“今天,我們沒有神圣的故事,也失去了民族語言的節奏感。然而,正因為如此,詩歌似乎已經回歸了合法性……我們今天面臨的不是個人國家身份,而是地球公民身份。從這個角度來看,我們的世界需要為我們的時代創造或恢復一種‘偉大的史詩’。”(第14頁)
因此,在《歐亞史詩》中,曹誰感到有必要收復失地。他的史詩融合了古代和現代的參考、神話、故事、象征、真理、夢想和幻想,從南到北,從東到西,從地到天;它的目標是“建立或宣布一個具有共享圖像或元素或‘客觀對應物’的象征系統,以傳達我們的精神和世界的本質。”(第14頁)
隨著巴別塔建造后語言的誕生,人們向東和向西分散。他們開始用不同的語言交談,使用不同的符號和圖騰,但每種文化和文明中總是有相似之處或共同之處。因此,后者將表明一種共同的基礎、共同的根源和普世的精神,盡管時間流逝,甚至數千年,這種精神從未消失。
盡管流傳給我們的古代歷史的一部分現在被解釋為“神話”,但還是出現了一些問題:為什么幾千年來,我們的祖先堅定地將它們視為真理,而恰恰相反,如今許多人懷疑它們的真實性,寧愿將它們看作神話,而不是童話?盡管歷史的特點是一個文明戰勝另一個文明,一場又一場戰爭和征服,數百萬人不幸喪生,但我們難道不應該坐下來思考這樣一個事實:我們可能確實有一個唯一的起源,從而證明我們實際上都是兄弟姐妹嗎?對歷史事件的描述和不同文明的平行敘事鼓勵讀者找到這些至關重要問題的正確答案。
這本書經常提到的第二個重要方面不僅與陰陽有關,還與火的象征有關,火可能代表毀滅和創造,甚至凈化,水、地和天在中國文化中至關重要。它們都有多種應用和意義——從文學到象征,從隱喻到超越。
這部作品突出了人類的殘忍,其詩句指向了人類對自然和野生動物的統治,對生命的神圣性沒有任何考慮或尊重:
兇手像正常人一樣在人群中尋找目標
……
行惡的人享有榮光
行善的人潦倒死去
(《太陽,請將我喚醒(陰)》第49頁)
它強調了人類已經習慣的環境的反常和矛盾:
野狼朝白羊走去
屠夫朝馬匹走去
惡人朝好人走去
我們朝黑暗走去
(《太陽,請將我喚醒(陰)》第49頁)
因此,邪惡在地球上統治世界,而人類卻在黑暗中盲目前行。
在曹誰的詩歌中,總是有一種深深的孤獨感,并得到強調。這不僅僅是與他人身體距離的問題,更重要的是精神距離的問題。這是“生活的痛苦”(le mal de vivre),即充分意識到,盡管可以說我們都在同一條船上,但我們每個人都是如此獨立,被自己的痛苦死死鎖住:
無論走到何處都只有我一個人
眾人都那么遙遠
我發現中心的位置總是空的
我已無法離開這個位置
……
我發現我始終都在那個最空的地方
這孤寂的世界
四圍都是無所事事的人
中心總是空的
我這一生無法擺脫的空寂
(《獨孤誰(陽)》第49頁)
曹誰認為,其他重要的主題是知識和意識:它們在生活中都是至高無上的。然而,根據作者的說法,我們不應該依賴他人來獲得它們。我們可能會激勵人們,并同情他們對知識和意識的困惑和渴望,但最終我們每個人都應該找到自己的方式來實現這一目標。
詩人的主要任務之一是將這一切揭示出來。然而,只要集體意識還沒有充分意識到詩人信息的內在和深刻的意義,人們就會一直走在“迷霧”中,聽到他的“遙遠的回聲”。(《亞歐大陸的形體二》第54頁)
在他的詩歌中,也出現了一種深深的無歸屬感和生活的荒誕不經:
我的頭一半在內一半在外
我的身體一半在大地一半在天空
我熟識的人還在等我,我已經永遠離開
……
去的終將來,來的終將去
這一切又有什么區別!
(《斷頭臺》第51頁)
在他的整個作品中,曹誰顯然希望為更好地理解規范我們世界的動力,那同樣讓人類和所有造物受苦受難的動力,并試圖幫助人們理解和想象新事物的可能性,這種可能性可能會以兄弟情誼、世界和平和愛全人類的精神統一起來。
從頭至尾地追隨曹誰的寫作,確實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他的寫作需要全神貫注,不要迷失在他使用的許多敘述、細節、隱喻以及歷史和地理參考中。 后者在數千年中從一種文化跨越到另一種文化,盡管中心仍然是亞歐大陸,并包含各種文明和信仰,特別是人類歷史上前赴后繼的古代世界大國。
一次閱讀他的作品可能很有挑戰性,但絕對令人興奮和著迷,對于那些喜歡挖掘多元文化并對古代歷史充滿熱情的人來說,這更是一種回報。可以說,兼收并蓄、多才多藝的人會找到“面包充饑”。相反,那些思維方式更線性的人,盡管仍然對閱讀和欣賞曹誰的作品感興趣,但可能需要更多的時間和耐心來閱讀并充分享受它。在個性特征和思維方式方面,“兼收并蓄”或“線性”并沒有錯。這只是我們大腦如何工作的問題,我們對此無能為力。它存在于我們的DNA中。
因此,無論我們喜不喜歡曹誰的文學創作,我們都不能不承認他是一個人,是一個作家,是一位有著深厚文化底蘊和人文底蘊的作家、詩人和編劇。 我們衷心希望他能夠實現建造新巴別塔的目標,至少在文化上是這樣。(完)

瑪利亞·特蕾莎·德·多奈特簡介
瑪利亞·特蕾莎·德·多奈特(Maria Teresa De Donato),美國著名的博士、作家、詩人、記者、博主、心理治療師。在意大利“永恒之城”羅馬出生并長大,后來移居美國。她在小學的時候就出版了自己的作品,在羅馬的Scuola Superiore di Giornalismo學院攻讀新聞學,后來獲得美國博士學位。她精通英語、德語、意大利語3種語言,熱愛世界多元文化,是多元文化的大愛使者。在歐美國家數家雜志、期刊、媒體設有專欄,讀者遍布歐美。她出版了許多書,包括《生活——花園傳統中的精神之旅》(2016);《更年期——我一生中最美好的歲月》(2018);《感官的海洋——一個虛構的故事》(2019);《失蹤的謎題——自傳歷史譜系小說》(2019);《不同視角下的自閉癥——塞薩爾的成功故事》(2019);《生活與環境的故事集》(2022)等。她采訪過全世界無數大人物,榮獲無數國際大獎,曾獲得“總統文學卓越獎”。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