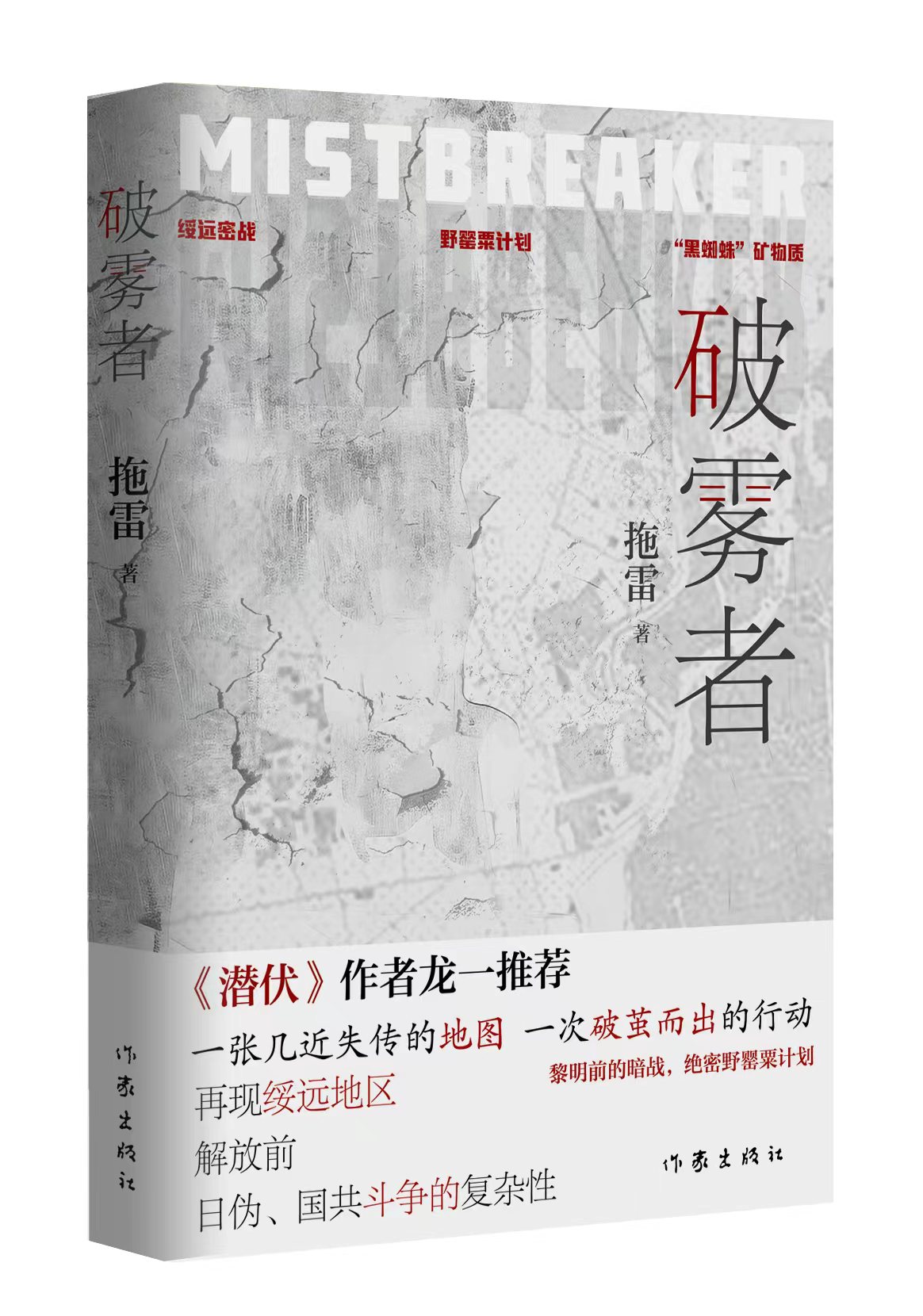
《破霧者》:鮮為人知的故事
——拖雷長篇諜戰小說《破霧者》
作者:趙卡
毋庸置疑的是,到目前為止,剛出版不久的拖雷長篇小說《破霧者》是內蒙古第一部諜戰小說;無論對作者本人而言,還是對內蒙古本土而言,這部長篇小說,毫無疑問是一個標志性事件:作者獲得了類型寫作的勝利;內蒙古會引發持續的關注和熱議。
我和拖雷是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中后期結識的,那時他正年輕,像突然冒出來似的,因發表了幾篇小說而在我們當地小有名氣,并被寄予文學上的厚望。我當時在寫所謂的先鋒詩,不過小說倒是讀過一些,和他能聊到一起,并建立起了彼此在文學上的信任。拖雷最初是以短篇小說登上文壇的,大概在2012年,他在《草原》雜志發表了他生平最重要的一個中篇小說《叛徒》,為他后來入局諜戰小說埋下了伏筆,所以,我們今天看到的這部《破霧者》,據我所知,在格局上比他以往任何一部(泛)諜戰小說更宏大,且不局限于單純的歷史趣味。
故事起始于一次抓捕行動事故——抗戰時期的歸綏特務科,受日本人節制,在一次抓捕敵人的行動中,“我”被一顆子彈擊中頭顱,慶幸沒死,但失憶了;后面的故事,就是“我”失憶后發生的故事。這種開頭的小說,頗有近年來網文的味道,作者創造出了一個虛擬的實景,把某些看起來不相干事件排列到一起,為了呈現一種時間順序上的關系,以便營造出與現實對弈的懸念性來。
諜戰小說,通行的做法是第三人稱敘述,有意思的是拖雷竟然使用了第一人稱,按他的說法,是這樣為了順手,殊不知諜戰題材小說若用第一人稱,視角就太逼仄了,會給作者增加處理的難度。他這是寫作上的蠻勇之舉,站在懸崖邊上的自加壓力,才讓我們看到了一個令人回腸蕩氣的北疆諜戰故事,與云耶山耶的城市諜戰故事區別開來。
《破霧者》的故事發生地,是在歷史上已經消失了的塞北四省之一的綏遠省,當時省會歸綏市就是今天的呼和浩特市,諜戰題材的這個地理元素之所以對作者不利,是因為不像上海、重慶、哈爾濱、北京這些諜戰品牌城市對讀者來說是熟悉的,而綏遠省、歸綏市對人們來說卻是陌生的——立省立市時間太短。這對拖雷的市場化努力帶來了巨大的阻力,他不得不像赫塔·米勒那些作家一樣,讓書寫風格跟地方性表情一樣獨特,所以我們在這本書里看到了大量的天氣和有名有姓的大街小巷。
整部小說的核心是圍繞一個日軍的“野罌粟計劃”展開的,故事背景有原型。其實從晚清開始,一直到抗戰期間,日本人就派出各種名目的地質、考古和人類學考察隊,在內、外蒙古進行地質考察和田野調查,比如著名的人類和考古學教授鳥居龍藏。小說里的故事發生在上世紀三十年代末四十年代初,一支日本科考隊在蒙古高原西部意外罹難了,由此泄露了日本人的一個罪惡勾當,他們在尋找一種可制造生化武器的原料代號為“黑蜘蛛”的礦物質;自此,包括中共、國民黨、汪偽、蘇聯人、日本人、蒙政會等各方力量展開了對“野罌粟計劃”的角逐。
作為類型小說,在主題定義上,故事從開篇不久就奠定了大家對日偽特務科的李明義——也就是“我”——的情感基礎,“我”作為“破霧者”,作者對他的角色設計是從內在意識出發的;包括情感預設,他有心理陰影,老是做夢,他和惠子的若即若離的關系,等等,確保了故事貼著主題。“我”的出場頗具戲劇性:失憶;因為當下諸多的諜戰小說在情節上已形成了浮詞套語,故“失憶”梗我以為是拖雷的打草驚蛇之筆,也是對自身局限性的一種反撥。從那一刻開始,一個在試圖回憶和講述障礙間掙扎的另類情工形象誕生了。
常規諜戰小說和諜戰劇的經典城市是上海、北京、重慶和哈爾濱等這種地方,事實上厚和特別市(日軍占領歸綏市后改名的)在那個年代也是一個間諜云集之處,日軍設立了很多特務機構和一些所謂的公館,比如羽山公館、徐田公館、山本公館、公奇公館、金田公館、三田公館和原田公館以及酒保公司等,拖雷對歷史的鉤沉和厘清頗費周章,最終以獨到而大膽描述成為內蒙古諜戰小說第一人。
這種小說的難度,對拖雷來說,當然是和當前其他諜戰小說家比,在于燒腦情節設計和專業知識的應用。燒腦情節設計需要合理的邏輯,就是說故事的各個關鍵節點都要有充足的說服力和邏輯依據,不能讓讀者挑出硬傷來,而專業知識,說實話,大家都沒干過特務,只能靠查資料。
那就只能使出傳統的看家本事了。拖雷寫小說,優勢在于通過刻畫復雜人物形象來講故事,像《破霧者》里的李明義,有著矛盾的性格特點,讀者在他的夜與晝兩個層面上感受到來了他的痛苦和掙扎;惠子的情感起伏和矛盾心理,崔板頭的草莽江湖氣,反派人物候忠孝的雙面不忠和殘忍,日本特務頭子本田麻二的狡詐與下流,宋德利的反復無常,等等無一不是豐富而立體的。寫人物而非聚焦故事,用細節和情感描寫,拖雷有效地避開了諜戰小說的模式化寫作和套路。
在此之前,我讀過孫甘露的長篇諜戰小說《千里江山圖》,并和拖雷探討過一個純文學作家的類型小說轉型之路,不得不說,其基本文學素養以確保讀者在閱讀時不會產生突兀或強制的不快觀感。如今拖雷的這個轉型剛剛開始,至少在主角人物上,他創造了一個失憶/記憶的矛盾沖突,引發了讀者的緊張感和好奇心;這就叫意難平虐心情節,以在陷入困境中揭示主角的過去經歷而非簡單的故事沖突,我們就可以在這個失憶/記憶的意外性上研究作者使用的懸念和引人入勝的結構。
以拖雷這部《破霧者》諜戰小說始,我認為像上海、北京、重慶這種大城市很難再挖掘出引人入勝的故事了,至少給我的啟發是,地方上太多失落已久的諜戰故事太值得我們去打撈了,鮮為人知的故事在歷史結束之前的位置,必將成為下一撥諜戰小說或影視的風口。
注:原標題為《鮮為人知的故事:記憶是如何與現實對弈的》
原載于《北海日報》
作者簡介:趙卡, 1971年生于內蒙古,作家、編劇,現居呼和浩特。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