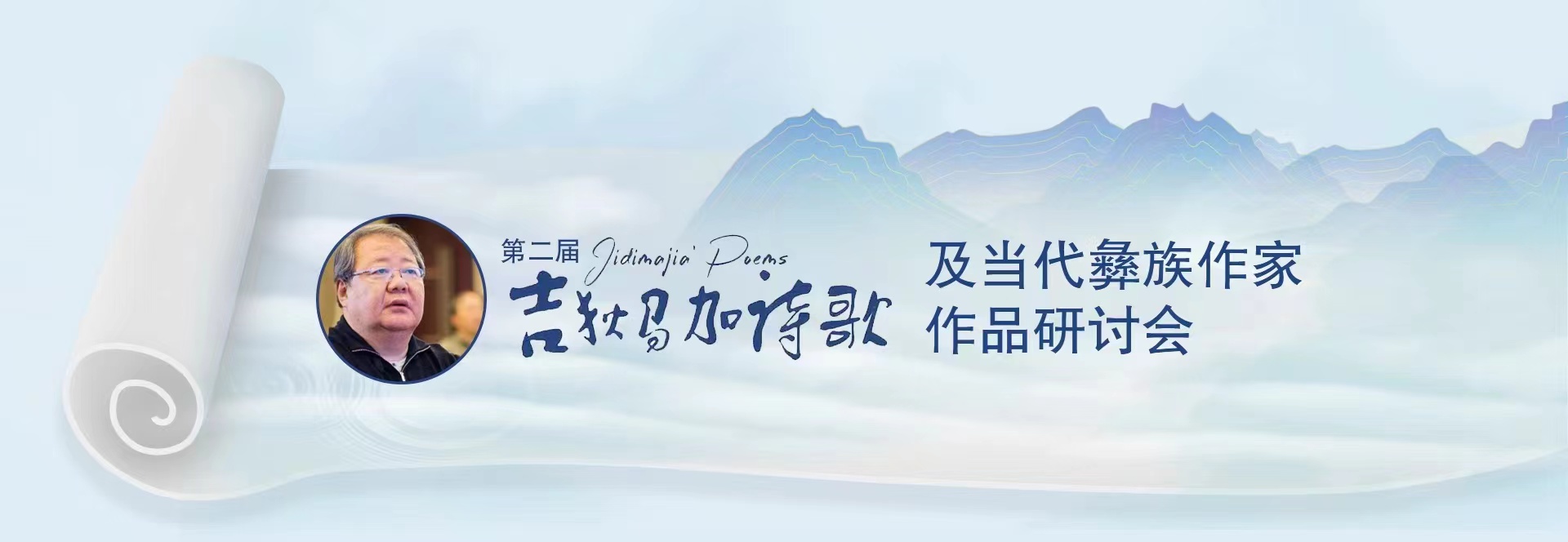
對于吉狄馬加詩歌的一些認識及吉狄馬加詩歌特質初探
——2023年4月在昭通學院“第二屆吉狄馬加詩歌及當代彝族文學學術研討會”分組討論會上的發言藍本
作者:沙輝(彝族)
引 言
雖然彝族是一個創造了輝煌燦爛的文化、為世界文明貢獻了自己力量的古老而堅韌的民族,并且也是一個以詩歌作為自己文化靈魂之一的民族,但是,直到吉狄馬加在彝族漢語詩歌界的崛起,才得以讓這個民族的詩歌產生了一個不僅在本民族內也在世人面前公認的彝族詩歌領軍人物、世界性詩人。作為一個崇尚英雄主義的民族,卻因為諸多原因,致使“詩歌英雄”的欠缺一直成為這個民族文化歷史上的一個“例外”,而吉狄馬加在新時期的成功崛起,填補了彝族沒有“詩歌英雄”的文化心理空白,使其英雄崇拜的主題內容得到了很好的并且是具體的補充,成為連接一個詩歌民族的歷史與當下和未來的具有大胸襟大情懷的世界級詩人。
對于如此豐富、立體、駁雜的和卓有成就的詩人進行全面性、綜合性評議是有難度的,而這幾年,我試著寫了幾篇關于吉狄馬加詩歌的評論,例如《吉狄馬加和吉狄馬加詩歌:一個民族的時代記憶》《思想的光芒,語言的魔力,人類茫茫精神星海中的一團焰火——從<遲到的挽歌>談談吉狄馬加詩歌的藝術魅力》《試論吉狄馬加作品的“文化性”——以長詩<應許之地>為例》《網絡時代背景下的彝族音樂高地和引領——試論吉狄馬加詩歌(歌詞)對于彝族音樂的意義和貢獻》《對于生命的悲憫,以及關于精神歸家路上的詩——讀吉狄馬加<關于二十一世紀的詩(組詩)>》等,所以就此綜合一下這幾篇文章的一些主要觀點,姑且取個《對于吉狄馬加詩歌的一些認識及吉狄馬加詩歌特質初探》的標題,以一個彝族寫詩者和評論者的角度,特此與大家分享討論。
一、《吉狄馬加和吉狄馬加詩歌:一個民族的時代記憶》里的幾點內容(主要有5個方面)
1、我在那篇文章提出的主要心得和觀點之一是:吉狄馬加是彝族詩歌的集大成者,吉狄馬加詩歌現象提振了彝族詩歌的創作信心和創作熱情。
其實這應該是一個共識,吉狄馬加作為一個當代中國著名的少數民族代表性詩人和具有廣泛國際影響力的詩人,是彝族詩歌的集大成者,他對于彝族漢語詩歌的帶動引領作用是不言而喻的。
詩歌因子滲透于古往今來的每一個彝人的生活中和骨血里,在彝族人的歷史中,在婚喪嫁娶等各式場合,彝族人都是以詩歌的方式或者說是詩化的語言進行對話、交流和賽辯斗智的,但不管是彝族的典籍、史詩,還是克哲爾比(彝族詩化諺語)等其它詩歌形式,差不多都為集體創作,在吉狄馬加之前,彝族雖然是一個具有悠久的文化燦爛的文明的古老民族,但并沒有產生過具有巨大影響力的詩人。這里面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比如因為彝族生活和地理上的歷來處于邊緣和封閉狀態,比如彝族口耳相傳地承載和傳承民族文學的方式,比如彝族的詩歌、典籍幾乎都為集體創作,都是集體智慧的結晶等,阻礙和制約了在彝族的歷史上產生家喻戶曉、載入史冊的具有巨大影響力的個體詩人。這雖然可以理解,但對于像創造了享譽世界的十月太陽歷、世界六大古文字之一的古彝文等輝煌燦爛的文明并且以“詩歌民族”引以為豪的一個民族,難免是使人感到一點遺憾的。直到吉狄馬加在彝族漢語詩歌界的崛起,才得以讓彝族詩歌產生了一個不僅在本民族內也在世人面前公認的彝族詩歌領軍人物、世界性詩人。雖然不能說吉狄馬加結束了一個“彝民族集體運用母語創造經典”的時代,——需要補充說明的是,因為眾所周知的全球一體化浪潮,很難想象彝民族在我們這樣一個時代還能一如既往以母語集體創作的方式創造出猶如《勒俄特依》《瑪姆特依》或者是《查姆》《阿細的先基》一樣的經典、史詩,——但應該可以說吉狄馬加開啟了彝族詩歌走向世界、把一個古老的詩歌民族帶進世界視野里的全新時代。從這一角度而言,吉狄馬加是彝族詩歌的集大成者,同時也是彝族漢語詩歌寫作取得巨大成功的典范,是使一個民族——彝族的詩歌連接起傳統和現代、使處于當下的時代對接上上一個時代又能很好地開啟以后之時代的詩人。
我在這里想強調的是,吉狄馬加對于彝族漢語詩歌的帶動引領不是通常意義下的帶動引領,而是吉狄馬加的詩歌創作和所取得的巨大成功是作為一種詩歌現象提振了彝族詩歌的創作信心和創作熱情的。彝族是一個詩的民族,但是在吉狄馬加這一代人之前,這主要是針對彝族的彝語詩歌和彝語的詩性、彝語的詩歌化情形而言的;而大家知道,彝語和漢語不管是在語法表達上還是在還是作為語言的精神背景的風俗習慣等都分屬于兩個體系,說這個的意思也就是說,彝語和漢語之間的轉化是存在一定難度的,而何況是詩的轉化。所以,是因為有了以吉狄馬加為代表的他們的詩歌創作形式、詩歌風格以及情感抒發路徑、精神的成功轉化和“轉述”、詩歌經驗的獲得和成功,才使彝族詩歌寫作者切身感受到原來彝族詩歌可以是這么寫的,彝人的精神世界可以如此以詩歌的形式得到轉化和“轉述”,可以如此向更多的人、更廣闊的外部世界進行有效地自我表達,才深切感受到它的普世價值意義并深受感召與鼓舞,使彝族漢語寫作變得充滿信心和自我期待。我就曾經對諸如《古里拉達的巖羊》中例如“雄性的彎角,裝飾遠走的云霧”這樣神奇而又十分貼切于大山里的巖羊毅然昂立于大石上的栩栩如生的形象感到驚奇不已,而應該做過類似的仿寫。
2、我在那篇文章提出的另一個主要心得和觀點是:吉狄馬加和吉狄馬加詩歌的存在,填補了彝族“英雄崇拜”中的“詩歌英雄”空白。
其實這個觀點的在上面的討論中已有所涉及,我在這里想強調一下的是,稍微熟悉彝族文化傳統的人都知道,彝族是一個具有英雄崇拜主義精神的民族,是一個崇尚英雄、注重信仰的民族,可以說,彝族文化在很大一個程度上就是“信仰文化”:比如畢摩文化——是在對畢摩文化的信仰基礎上建立起來的;比如彝族的萬物有靈說——彝族人覺得不管是石頭、樹木、小草還是河流、山頭之類,萬物都有一個類似于靈魂的神靈在護佑著它本身;又比如彝族對火、鷹等等圖騰文化的崇拜,也都歸屬于“信仰文化”的范疇。這些文化都不排除是在精神信仰的基礎上發展起來的。這在彝族的英雄崇拜類型故事傳說和精神領袖崇拜類型故事傳說中得到充分印證:在崇拜對象中,駿馬是達嶺阿宗,雄雞是瓦布多幾,家狗是克巴丹毅,青蛙是斯惹巴貨,人類英雄是半人半神的支格阿魯,畢摩大師是畢阿史拉則,機靈有辯才猶如阿凡提的有碩郭克惹,美女的典型有呷嫫阿妞、布阿史嘎歪等等,而對于詩歌,或許是因為彝族的傳統和古典詩歌主要形式為集體長時期共同創作,沒有產生過真正意義的、盡人皆知的“英雄”。“詩歌英雄”的欠缺,一直是英雄崇拜主義的彝族歷史上的一個“例外”。在此意義下來討論,吉狄馬加在新時期的成功崛起,填補了彝族沒有“詩歌英雄”的文化心理空白,使視詩歌為生命的彝族在談論彝族詩歌的個體性現象時不至于乏善可陳。
3、我在那篇文章還提了這么一個心得和觀點:吉狄馬加是一位站立于自己民族母親寬廣的肩膀上放眼世界的真性情詩人。
關于這個心得和觀點,我是這樣描述的:吉狄馬加具有最為深沉的情懷和博大的胸襟,他的深沉,來自于背后那個歷經苦難卻又堅韌的民族,來自于腳下那片大山大河大平原中神性而成為詩人“永久的迷戀”的土地;他博大的胸襟,是父性的山川所賦予,是母性的江河所恩賜,更是他“民族的眼光”世界的視野所決定。他的一切思想和情懷的獲得,都是他對“民族”和“世界”這兩個既“隔離”又融合、既“獨立”又彼此包含的概念的深切感悟。他對自己的民族、對生命與和平自由等真善美的事物具有著內在性的、與生俱來的鐘愛。吉狄馬加的詩歌,是艾青的名句“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淚水,因為我對這片土地愛得深沉”式的深深的愛。毫無疑問的是,吉狄馬加首先是民族的,然后才是世界的。是彝族這位古老而年輕、具有博大精深之文化底蘊的、飽經滄桑又煥發新顏的偉大母親養育了這個世界級的民族詩人。可以說,沒有彝族這樣一個民族,沒有吉狄馬加自身對彝族傳統文化的深厚積淀和深深思考,就不會有這樣一個成為中國少數民族代表性詩人的吉狄馬加。關于對自己民族的愛,關于自己民族所具有的詩性特征給自己帶來的滋養,關于對自己所熱愛得使之熱淚盈眶的那片土地的濃郁情結,關于對自己的創作所背靠的文化底蘊和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創作情感、創作靈感和創作熱情的來源,我們在吉狄馬加的詩歌、訪談、創作談以及演講等其它言論中能夠輕而易舉捕獲到明確的信息。
4、我覺得吉狄馬加是一個生命意識非常強烈的詩人,所以這個觀點我在后來的評論中也有反復提及。
在這里,我還是很樂意提一提我在當時寫的這樣的內容:彝族是一個正視死亡的民族,在我很小的時候,我很不理解那些老者說到(自己的)死亡為什么總是那么坦然,他(她)在談論自己的死亡就像是在談論下一頓飯吃什么好那樣正常和簡單。在彝族諺語中也有“人死正常,猶如圓根葉子落”(季節到了,圓根的葉子就會一層層變黃、枯萎,這樣的說法是指向世上新人換舊人那層意思的)、“老者正當死,幼者正當玩”(意思是老人死去是合情合理的、自然的,幼者愛好玩耍也是合情合理的、自然的)。在吉狄馬加的詩中,除了對大地和家園意識的抒寫——“我曾經歌頌過土地和生命”(《獻給這個世界的河流》),以及顯示出他站立在母族的土壤放眼世界的對人類的精神關懷,還有他對母親和孩子這樣一對“關系”熱衷于闡述(《自畫像》:“孩子留下你的名字吧,在這塊土地上,因為有一天你會自豪地死去——題記”“我是一千次葬禮高潮時/母親喉頭發顫的輔音”,《我愿》:“彝人的孩子生下地,母親就要用江河里純凈的水為孩子洗浴——題記”“當有一天我就要死去……這時讓我走向你/啊,媽媽,我的媽媽/你不是暖暖的風,也不是綿綿的雨/你只是一片青青的/無言的草地……讓我干干凈凈的軀體/永遠睡在你的懷里”)等等以外,對生命的死亡這一意象,也多有涉及。關于這點,我們不引用詩歌——那多了去了(如前面所引用到的)——我們先來看他在他的創作談里談到的:“我寫詩,是因為我很早就意識到了死”“我寫詩,是因為我的父親已經死了,我非常懷念他”(《一種聲音——我的創作談》)。而這些,都是直指人類的精神母題的,是詩人對生命源自何方歸于何處的母源性課題的思考。吉狄馬加在作品中顯示出的對母性(土地、母親、民族)的熱愛和依戀,本來就是“溫情”的,是“溫情”的行為;死亡雖是個令人恐怖的詞匯,在他的抒寫中卻一點沒有陰森恐怖的氣息,相反,它充滿一種“生命的撫摸”的力量。這雖然與彝族的向死而生觀相互一致,卻有著本質的區別:彝族傳統的“死亡觀”是樸素的順應自然的哲學觀點,而在吉狄馬加這里,更多的是對生命的珍愛、憐惜、熱愛和贊頌。
5、我在那篇文章還提的又一個心得和觀點是:吉狄馬加的寫作是“精神性”的寫作,情懷的和深沉的寫作。
我當時是這樣寫的:不管是吉狄馬加對生養自己的那片土地、家園的深情抒懷,還是他對民族的文化和精神以及對整個人類的精神關懷性抒寫,抑或是他在當下更多地對于人與自然生態和人類的生存發展的書寫,都指向并抵達一種精神上的蒼茫遼遠,都是“精神性”的寫作,情懷的寫作,他的這樣的寫作最終都會落到“實在性”“現實感”這樣的精神底座上。
吉狄馬加的詩雖然有時候因為彝族文化在某些方面中具有的巫術色彩而多少顯得有些魔幻、高深,但其實他的語言并非是晦澀的。敦實、博大、溫厚、深沉、深邃、幽遠、厚重、大器(注意,我這里是“大器”而不是“大氣”),成為他詩歌和詩歌語言的特征,他的詩歌是平實中的深邃、現實中的魔幻,是“近”中的“遠”,是“遠”中的“近”。閱讀吉狄馬加和吉狄馬加的詩,我們只有從“去接近一個偉大靈魂”這樣的角度出發,這樣才能真正理解他的詩歌、走進他的精神世界。
(此文發表于《當代文壇》2016年第6期,發表時有所刪減;節選并以《吉狄馬加的寫作是精神性寫作》為題發表于《草堂》的2017第1期)
二、《思想的光芒,語言的魔力,人類茫茫精神星海中的一團焰火——從<遲到的挽歌>談談吉狄馬加詩歌的藝術魅力》里的幾個內容
在這篇文章,我以閱讀《遲到的挽歌》的心理感受作為切入點,結合“自我”的平時閱讀經驗和體會,從民族學、歷史學和詩學的角度試圖闡述吉狄馬加詩歌的藝術氣質內涵及其獨特性,認為僅從吉狄馬加思想的光芒、詩歌語言的魔力,醇正而恒定的詩人的抒情性品質,超脫的生死觀的思考和始終如一的注目這三個維度考量,也顯示出了吉狄馬加詩歌足夠的藝術魅力和精神能量,充分體現出它獨一無二的藝術特質和卓越的藝術貢獻。
1、我在那篇文章里說:不可否認,吉狄馬加的詩歌具有某種厚植于民族傳統精神文化下的“超越性”和魔力。超越性具體體現在他的思想性、精神世界上,即他的思想性與精神世界讓他的詩歌作品具有了某種超越性,而與一般的詩人自然區分開來;他的詩歌獨有的魔力則不僅體現了他的思想與精神世界,同時也體現了他的詩歌作品背后那片熱土包羅著包括畢摩文化在內的神秘氣息以及吉狄馬加詩歌的高超藝術性,比如語言和修辭自身帶有的那種張力和深沉、深邃、廣博。如果沒有了這樣的超越性和魔力,吉狄馬加的詩也就不成為公認了的吉狄馬加的詩。當然,我深信不疑地認為,這一切都源于他所植根于的博大精深的母族文化以及他的人類性視野和自身異于常人的深層思考與體悟,以及將深層思考、體悟和創作實踐相結合的身體力行。每次閱讀吉狄馬加的詩歌,我都會有一種別樣的“詩歌閱讀感受”(具體地說是一種“震顫”)穿透我最隱秘而平時輕易不會得到觸碰的身心之處,這種感受根本不同于閱讀其他詩人,不是那種簡單的愉悅、腦洞大開的快感,不是那種同作者一道“完成”一種高超的語言智力游戲、成功走出或說穿越作者的語言迷宮之后的獲得感,也不是那種豁然開朗、恍然大悟般的精神“妙悟”,也不僅僅是思想得到“開光”一般領悟甚至是同作者一道受到“神啟”般完成其中語詞的“精妙”、藝術表達的“精微”,以及深切感受到博大精深的精神內涵、深邃的思想和精神陶冶給自己帶來的有關思想和精神的獲得,讓人如此透徹地受到心靈的顫動、精神的震撼、震顫和浸禮、滋養。
2、我在那篇文章里談到:在我看來,吉狄馬加和吉狄馬加的作品,是具有詩歌英雄主義的。從吉狄馬加一生的詩歌創作歷程和成就及精神追求圖譜來看,可以說吉狄馬加是具有“英雄情結”的。然后,我還想強調的一點是,彝族原本就是一個崇拜英雄的民族,彝族的“德古”[ 德古:彝語,指彝族傳統社會中的智者和賢達,是德高望重、具有威望的民間糾紛調解師。]“冉闊”[ 冉闊:彝語,即勇敢的人、英雄。]等等這樣一些生活中司空見慣的詞匯本來就是具有強烈感情色彩并經常被長者、族群和彝族傳統精神作為正統、“主流精神”的象征和載體進行育人塑性的,吉狄馬加作為成長于如此環境并向彝族文化傳統深入汲取精神養分的詩人,這樣的影響想必是耳濡目染并且深遠的。
關于英雄主義思想,在吉狄馬加這首作為一個兒子獻給父親的深情懷念之作,作為他借此向養育他成長、作為精神臍帶的先輩和民族,向所有正義的生命致以崇高敬意的長詩《遲到的挽歌》里的內容,我們也可見一斑。這里由于篇幅,不再贅述,大家想具體了解的,可以具體閱讀《遲到的挽歌》,也可以在我那篇評論了看看我咋論證的。
3、我在那篇文章里還談到這么一個意思,就是認為語言是具有魔力的,語言可以使一個人“生”(在精神上絕處逢生),也可以使一個人“死”(在“魔咒”中使人痛不欲生甚至選擇死亡)。只是語言的魔力的表現形式,可以是“眾口鑠金”,可以是可畏人言,也可以是詩的語言或詩的語言一般的語言,還可以是催眠師般的語言魔術、詛咒師的語言魔方。語言的魔力的層級由語言的“精致度”“密度”和“連綿度”幾個方面聯合作用下所達到的層級而決定。三寸不爛之舌的游說,軍隊出征前的演講,誓師大會上的動員,道與釋,巫術,咒語,儀式,思想,安魂曲,莫不與語言有關,或者說,它們無一不是建立在語言的基礎上的。
語言的魔力,不僅在如上所說之處展露無遺,還在如彝族的送魂經、喪禮上各種儀式中體現得淋漓盡致(具體的例證此處略去)。
《遲到的挽歌》作為一首悼念父親的遲來的挽歌和一首回顧父親“光輝的一生”、頌揚生命至高無上的贊美詩、頌詞,甚至也算是一曲安魂曲,同時藝術化地“詳敘”了父親生前和去世的一些特別的過程和場面,而在閱讀中,我們在詩歌作品的語詞上、意境上、節奏上、長度上等等方面很容易地感受到它類似于“送魂指路經”一般的韻味——那綿長而具有魔力一般的語詞,它本身簡直就是一部“經書”,念之讀之,那種好似向冥冥中不斷念念有詞而連綿不絕的念誦給我們帶來全身心的肅穆,讓我們深入感受語言自身那種攝人心魄一般的魔力(所引用的詩句此處略去)。而這,又何嘗不是作者念念有詞“念頌”出來或者讓我們念念有詞“念誦”出來的、向天而吟的一曲遲來的、與父親亡靈進行“最后的”道別的“送魂經”呢?!
4、我在那篇文章里談到,吉狄馬加具有醇正而恒定的詩人的抒情性品質,吉狄馬加可謂是中國詩歌界真正意義的最后的抒情詩人。 在當今之中國詩歌界,吉狄馬加是最有“定力”的一個詩歌創作者。一是自80年代初開始詩歌創作以來,吉狄馬加一直筆耕不輟至今、持續保持了旺盛的創作熱情并且成績斐然;二是吉狄馬加雖然也學習借鑒西方以往和當下的優秀作家詩人的成功經驗,但他一直以來地以中國的、民族的甚至是地域的傳統文化作為自己文化精神背景和基座,堅持民族性、現代性、世界性有機自然融合,而不是丟棄中國傳統而進行意識流、后現代之類的“潮流”寫作、實驗寫作;三是吉狄馬加篤定地從事著詩歌寫作,而不隨著時興進行跨文體、跨文本寫作,或步入小說、散文、詩歌等通吃行列。四是當下的中國詩歌是以去抒情、敘事化、口語化的寫作一統江山,并且當下流行將詩歌、小說、散文等進行雜糅、面團一般糅合的“打破文體限制”寫作,而吉狄馬加一直以來以飽滿的熱情、激情和純正嚴肅的態度進行詩歌創作,并且一直保持著詩歌固有的“抒情”元素,一以貫之保持著中國詩歌醇正的抒情傳統。從某種意義上而言簡直可以稱得上是中國詩歌界最后的“抒情詩人”。
說到詩歌的抒情性,我一直以為“抒情性”應該是詩歌的基本屬性之一,過去如此,現在也應該堅持,雖然它的表現形式可以是外顯的,也可以是內在的和隱秘的。吉狄馬加卻可謂是中國詩歌界真正意義的最后的抒情詩人,他在堅守著中國詩歌的“正道”和“醇正”,通讀他的詩歌作品之后你會發現,他的作品無不或隱秘或明顯地是抒情性的。比如《遲到的挽歌》就是,抒情的基調鋪滿全詩,使其深沉、深情、高遠,具有了一種撼人心魄的震撼力。
陳寅恪曾說過這樣的話:歐陽修寫《新五代史》,用一本書的力量,使得一個時代的風尚,重返醇正。我眼中的吉狄馬加,也是一直以本文如上所說的三個維度和自己不斷的精神追索、孜孜以求以及不倦的抒寫,保持了中國詩歌相關層面和中國詩歌“一個時代風尚”的醇正,或讓其重返醇正。
(此文發表于《山東文學》2021年第1期,后收入吉狄馬加長詩《裂開的星球》《遲到的挽歌》評論集《世界的裂隙成果詩人的心臟》)
三、《試論吉狄馬加作品的“文化性”——以長詩<應許之地>為例》里的一些內容
在這篇文章里,我主要談到了吉狄馬加在這首長詩了談到的一些“有趣”的創新手法(比如對于帶有彝語音譯性質的詞語如“啊諾蘇”“嚯羅啵羅”的運用之類),這里因為篇幅省略不做具體談及,我們這里主要談談那篇文章里談到的吉狄馬加詩歌作品具有的“文化性”:
吉狄馬加進行創作,無一不是踩住“現代”做兩樣事:回望歷史與傳統、思考并放眼未來。由此,他的作品不僅僅屬于“文學”“詩歌”,也屬于“文化”范疇,它的精神實質、它的內容和“卷起”的思想風暴,也是屬于文化的范疇的。他是踩住“現代”、站立在“現代性”之上,放眼傳統、放眼未來、放眼精神與文化,并對其進行審視的這么一個詩人。吉狄馬加的詩歌情結、文學情結和民族情結、家國情結可以說是與生俱來的,是他的精神的一部分并且是重要組成部分。因為他的這樣的“全域性”視角,他的胸懷民族、胸懷家國的人類性審視眼光,因為他的人類性眼光、作品的文化性特質,他的作品與一般人的作品因此而自然區別開來,他的作品的辨識度與全球性影響力因此而得到確立。林賢治說“真正的知識分子,需要具備一種公共立場,關注人類的重大事務,那些生死攸關的所在”“精神性的具備,首先得有精神生活和精神空間”,吉狄馬加無疑是具備公共立場的,文化立場的,是關注人類精神傳統和命運未來的,“他的作品是直接和人類命運相關的”。他不僅“有精神生活和精神空間”——更多地體現在他對民族傳統文化的諳熟和深度認可、信任以及蜜蜂吸花粉般的不斷吸取和“深挖”,他的作品就是精神性、文化性的直接映射和體現。我們當下許多人的作品,都先天不足地缺乏了一種“全域性”視野、博大精深的胸懷和大的架構、文化性的眼光。面對紛繁多變的世界,面對紛繁快節奏的現代生活,“匆匆人間,再難顧及他人”,全球化與后工業時代,我們許多人的精神都自動化和適應性地矮小了、“現代化”了、自我化了,最多就剩下歷史角落里的父親或許還在空無對象地喃喃自語……在我們真實的精神世界,回望傳統、回望我們的祖先與來路,在傳統之外,在迷茫的當下,誰還可以作為我們的父親帶我們回去?這是一個非常值得思考的問題。
就像許多偉大的經典作品自身就是當時之文化的產物,也是人類文化的某種密碼和承載體(理解當時的文化、理解人類文化,這些偉大的經典作品無疑是最“靈便有效”的鑰匙),吉狄馬加的詩歌同樣是“當時之文化的產物”“人類文化的某種密碼和承載體”,包括他的詩歌和他的其它作品(如評論、演講稿)天然自帶某種強有力的文化氣息、文化魅力、文化底蘊即文化性。除了“博大精深”、“人類性眼光”“在連接起傳統與現代的致敬傳統中彰顯現代性”是我一直以來對吉狄馬加作品的總體印象和評價以外,吉狄馬加作品所具有的“文化性”,是我這幾天才“明了”起來并能有所簡要說明的一個方面。——那些偉大的作品和作家,往往都因為體量太大、涵蓋太廣,是極不容易作出簡單簡要的概括的。而在我感覺到的他的博大精深、他的歷史性人類性眼光和他的在傳統中包蘊現代性之外,我一直以來閱讀他作品時那種道不清說不明的感覺原來就是他的作品具有的“文化性”。就像他的作品具有其它那些特質而迷人、而具有了很強的個性和辨識度,我以為,他的作品的“文化性”,同樣是他的深厚文化底蘊、精神大格局的產物,是他的作品之所以迷人和具有很強個性和辨識度的重要一個特征。
(此文發表于《川觀新聞》2022年8月29日,后被《四川日報》在2022年10月14日的“天府周末.西嶺雪”欄目以頭條形式推出)
四、《網絡時代背景下的彝族音樂高地和引領——試論吉狄馬加詩歌(歌詞)對于彝族音樂的意義和貢獻》里的觀點
在這篇文章里,我試圖通過一些“現象”的梳理加上一定的論證,就吉狄馬加詩歌(歌詞)對于彝族音樂的意義和貢獻,即吉狄馬加詩歌(歌詞)對于促進彝族音樂的“高地建設”“高品質追求”的引領作用和貢獻進行初步的探究討論。我主要從“詩與歌的聯姻歷史關系,試論吉狄馬加詩歌(歌詞)與音樂產生聯系的必然性,以及它對于彝族音樂的特殊貢獻”“以吉狄馬加詩歌(歌詞)形成的音樂作品為例,談談詩與歌結合之下所能產生的廣泛傳播作用及社會影響力”“詩與歌在彝族精神生活中交融互生,精英文化是引領帶動、是文化保護傳承的先行者和有生力量”這么詩歌方面進行了梳理和論證,因為限于篇幅,不再具體轉述,我們就以那篇文章的“內容提要”來做個概要式的了解:
眾所周知,網絡和自媒體的普及為大眾文化、個體創作的平臺建設和傳播提供了開天辟地的便利,不過由于“篩選”機制和“沉淀”效應的大大降低,以及網絡特別是自媒體對于“及時性”“娛樂化”的追求,致使網絡世界里的藝術作品“高山流水與靡靡凡音齊駕并驅,陽春白雪與下里巴人并肩共存”,網絡時代下包括音樂在內的文學藝術泥沙俱下的現象極其明顯。在這樣的時代背景下,討論文化和文學藝術特別是主流文化和文學藝術的“提高站位”,為新時代之精神文明建設、精神高地建設提高“段位”和自我要求、強化引領作用,顯得至關重要。當下,彝族音樂同樣是“高山流水與靡靡凡音齊駕并驅,陽春白雪與下里巴人并肩共存”,而吉狄馬加的詩(歌詞)對于彝族音樂的“拔高”和引領性作用是極其明顯的。對于吉狄馬加的詩歌成就,有目共睹;而他的詩歌(歌詞)對于彝族音樂的貢獻和帶動引領作用,也理應引起關注。以吉克曲布、奧杰阿格、瓦其依合、賈巴阿叁、彝人制造、太陽部落等為代表的當下彝族音樂主力,積極將承載著濃郁的彝族文化元素和內涵的吉狄馬加詩歌轉換形成音樂作品,他們善于在吉狄馬加的作品中獲取靈感、將由此獲得的靈感和吉狄馬加作品相結合、彼此“共生”,從而創作出獨特的音樂作品,有力推動了彝族音樂的高水平高水準發展。這是除了已經“顯化”的彝族詩歌、彝族音樂之外,又一可喜的彝族“文化現象”。
(此文發表于《民族文學》2023年第2期,后被其公眾號2023年2月18日推出)
五、在《對于生命的悲憫,以及關于精神歸家路上的詩——讀吉狄馬加<關于二十一世紀的詩(組詩)>》里討論到的
在這篇近作,我主要從吉狄馬加回望又前瞻、當下又“傳統”的詩歌精神實質,試圖論證他的作品也是基于對一切生靈的悲憫(這個悲憫非悲天憫人之悲憫,而是大愛博愛和強烈的生命意識下的悲憫)而一直走在精神的“歸家”的路上的精神內涵和實質:
“他站在自己建造的山頂,將思想的風暴吹向宇宙。”只要我們認真考察、樂于考察,我們就會發現,吉狄馬加的詩歌,幾乎無一不與“傳統”相關,我在這里所說的“傳統”,不僅僅是指傳統文化、傳統精神和文化傳統、精神傳統,而主要是指相對比較廣義一些的文化和精神,那是一種博大的、寬廣的、以人為本的、具有厚實的思想高度和精神內涵、表征的行為。統觀吉狄馬加的詩歌,他的生活環境雖然是城市的、現代化的,他生活在中國的現代化大都市那么多年,他卻沒有單一的、單純地禮贊過城市生活、現代化生活,沒有單一地、單純地書寫現代性,而是時時以審視的、回望的和前瞻的眼光,來讓文字承載自我的精神世界對于外部世界和心靈世界的本能反映。吉狄馬加的詩歌總是給我們一種“非常可靠”的印象。這種“非常可靠”不僅僅基于對一個成熟詩人、杰出詩人的信賴,更在于他的詩歌在思想和精神高度下所體現出來的“有意義性”。而這個“有意義性”的直接體現就是,他的作品是具有人類精神性乃至于是人類文化性的。當下的中國詩人,包括中國頂級詩人,所缺乏的不是詩歌的技藝、技法和藝術性、創造性、創新性,而在于精神的博大、思想的深沉、情感的沉郁。而這不僅需要非凡的才華、執著的前進和孜孜以求,更需要宏闊的視野、博大的胸襟、胸懷天下的精神和哲人思考哲學般的深入和掘進。對于如此“大師的行徑”般的作為,我覺得更多的需要依賴于“先天性”,依賴于“天生”的稟賦——我這里所說的天賦不是指我們通常意義下的智慧,而是更傾向于智性的、精神性的方面。不必忌諱地說,在波詭云譎、眼花繚亂、時代之潮流滾滾向東的現代性面前,在人之精神傾向于“矮化”的時代背景下,如此“大師一般的存在”是極其稀缺的。或許他們的詩歌寫得那樣精致、精美和迷人,但是,精神和思想的精深度,仍然是一大梗阻。而吉狄馬加,似乎“天生”地就跨越過了這樣的“梗阻”,而成功樹立起了自我的精神譜系、詩歌坐標,從而做出了自己的詩歌貢獻、“確立”了自己與眾不同的辨識度和不可替代的詩歌地位。
(此文后來發表于川觀新聞2023年6月12日,后被四川文藝網203年8月14日轉載——2024年7月13日補記)
整理于2023-4-16
(全文發表于涼山州彝學會刊物《涼山彝學》203年刊)

作者沙輝近照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