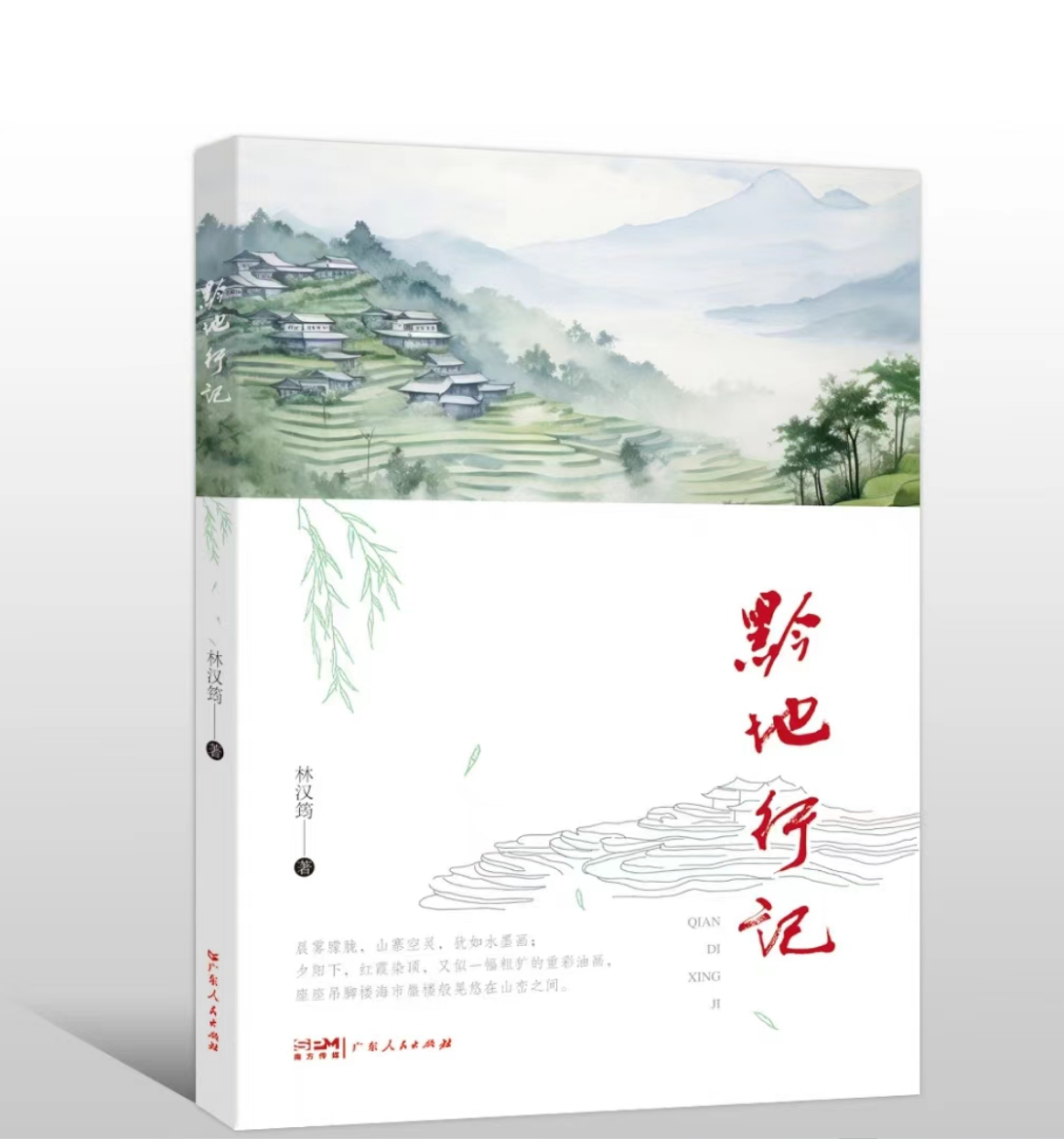
黔地圣徒筆下的山鄉巨變
——評林漢筠散文集《黔地行記》
作者:黃清
作家林漢筠最新出版的散文集《黔地行記》(廣東人民出版社2024年4月),這是他在東西部協作貴州銅仁德江掛職時創作的一部書寫黔地歷史的文化散文集,收錄了28篇散文,近20萬字。在東西部協作期間的艱難工作是可想而知的,他不辱使命,用文化的擔當,給黔地一份滿意的答卷。作為一部校本教材,以一份厚重的文化盛宴交給了黔地的孩子們,讓他們了解自己生活的環境,了解本地的文化古跡,了解人文景觀、歷史故事和文化名人。他抱著這樣的情懷去熱愛,去抒寫云貴高原的光彩。
冰心說,成功的花,人們只驚羨她現時的明艷!然而當初她的芽兒,浸透了奮斗的淚泉,灑遍了犧牲的血雨。林漢筠的成功是用無數汗水匯聚而成的。寫作是一件苦差事,特別是他的作品中蘊含著豐富的文化知識,歷史知識。把厚重的文化播撒的時候,就像閃耀在夜空的星光,照亮了人們前進的道路。他是黔地文化瑰寶的守護者,筆下的人物都閃耀著歷史的光華,生生不息,薪火相傳,永不泯滅。本文將從其代表作《潮砥之砥》《觀儺》來品析他作品所表現的藝術個性。
一、以民族精神的圖騰展現人物的精神面貌,表現文章的主旨
文化散文從美學角度來說,一般是立足在新時代的高度,用現代眼光重新關照歷史人物和歷史事件,從中挖掘新的文化內涵,適應新時代發展的形象和意義。在這個大變革之時代,鄉村振興,百千萬工程的山鄉巨變主題,在林漢筠的掛職期間抒寫的地域文化散文中就已經融合了這些元素。如《潮砥之砥》,開篇人物閃亮登場,又有懸念,粉面含春威不露,朱唇未啟笑先聞。“穿過一段名叫潮砥的水域。這兒,有一塊巨石嵌著四個大字——‘黔中砥柱’。后來因下游蓄水,巨石被淹沒于水中,可這四個大字,如同它的主人,像五百余年前的落筆那樣,把一條江照得敞敞亮亮”。[注釋2:林漢筠:《黔地行記》, 廣東人民出版社2024年4月版,第165頁。]它的主人,指的就是明代思南府水德司人田秋,從這個歷史人物展開,將歷史背景與人物命運,黔地環境緊密相連。田秋作為文章的核心人物,其求學、回鄉、題字、以及后來的仕途經歷,都被生動地描繪出來,使讀者能夠深入了解這位歷史人物的性格、抱負和成就。文中引用北宋史學家范祖禹“崖谷吐吞成霧雨,蛟龍戰斗作風雷”的詩句,增加了文章的歷史厚重感,也展現了田秋對先賢的敬仰和效仿之心,這是時代所需要的永不過時的精神品質。
《潮砥之砥》的標題意象開闊,象征深刻。“潮砥”是一個地名,而“砥”在古漢語中常用來比喻堅定的意志或基石,有磨石、磨礪之意,有中流砥柱、砥礪前行之旨。“面對朝廷的麻木不仁,田秋痛心疾首,他要‘我以我血薦軒轅’,守護綠水青山,捍衛國家利益”“這一站,就站起了巍巍烏江兒子的擔當。改革,是要付出心血甚至生命代價的”。田秋,是一個不撞南墻不回頭的人,在世俗面前,只認一個死理,像半山公那樣,“天變不足畏,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用上疏,吹響改革的號角;用行動,向天下奉獻一顆赤子之心。[注釋3:林漢筠:《黔地行記》, 廣東人民出版社2024年4月版,第178頁;第175頁。]這些文字以田秋痛心疾首說明對朝廷不作為的憤怒,對山鄉環境遭到破壞、國家利益受損的深切憂慮。這種憂慮,正是山鄉巨變主題的重要組成部分,即面對傳統觀念和現實困境,如何尋求突破和變革。“以我血薦軒轅”的誓言,將田秋的形象塑造得高大而悲壯。以鮮血為代價,這是借用魯迅《自題小像》里的詩句,誓將一腔熱血報效祖國。這種無私奉獻、勇于擔當的精神,正是山鄉巨變所需要的正能量和動力源泉。
在《觀儺》一文里,儺戲是中國古老的文化,是起源于農耕時代的圖騰崇拜,并逐漸發展成為具有地方特色的劇種。儺戲文化中蘊含著豐富的美術思想、象征意義。林漢筠通過具體的故事情節和人物形象來探討人性的復雜性和多面性,將人的內心渴求與儺戲的神性和人性交織在一起,展現人性的光輝與陰暗、善良與邪惡,公正與偏私,權力與義務等問題。
林漢筠寫孝道的儺戲,結合多年前在鄉下全村人給七十歲的母親做生日時的情景,孝是人類至上的主題,是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根本。《關公斬蔡陽》,透著古老而詭異氣息的儺面,如同神靈一般被敬畏。“徹膽長存義,終身思報恩”,元人羅貫中筆下的關公,是正氣正義的化身。他,激濁揚清,匡扶正義,勸善懲惡,重情重義,義薄云天。關公精神的核心在一個“義”字,“福則祈之,患難則呼之”,天下無不頌其德,供其祠,成為民間對正直忠義的英雄崇拜,祈望護國佑民的情感寄托。儺戲故事中,關羽殺的壞人還很多,久而久之在人們的心目中關羽就成了專除害人妖怪的神。關羽在疲憊不堪的情況下依然堅持與蔡陽交戰,并最終將其斬殺,這體現了他堅定的信念和非凡的勇氣。在“山鄉巨變”的過程中,鄉村和農民同樣需要這種勇氣和決心來面對各種困難和挑戰,推動鄉村的發展和變革。儺戲也成為了我們這個時代的一種非遺物質文化遺產,一種供人民生活娛樂的文化,說明我們這個時代已經是幸福的時代。
二、精巧而富有個性的表現手法,讓人物形象更加鮮明事件更有意蘊
《潮砥之砥》的巧妙寫作手法,描繪了黔中大地的山川之景和人文情懷,成功地塑造了一個鮮活的歷史人物形象,傳遞了積極向上的精神力量。“惡風橫江,卷浪萬丈”“江中,巍然聳立著一鷺鷥巨石,面平如砥”,文章對烏江潮砥水域的自然景觀進行了細膩的描寫,不僅展現了烏江的險峻與壯美,也烘托了田秋當時的心境和情感。“那天,這個被尊稱為唐鑒公的人站在三門峽上,面對傾落九天的波濤,望著矗立如柱的三座峭山,喊出‘砥柱詩’來,又讓世人多了個‘三門峽砥柱’之謂。想到這里,田秋整了整衣袖,招呼同伴,提筆揮墨,一氣呵成,寫下‘黔中砥柱’四個剛勁有力的大字,又不忘落款寫道:甲申歲孟春月吉旦,西麓田秋題”。[注釋4:林漢筠:《黔地行記》, 廣東人民出版社2024年4月版,第166頁。]通過對田秋在潮砥題字的場景描繪,文章將田秋的豪情壯志和黔中大地的山川之景相結合,使讀者能夠感受到他內心的激蕩與澎湃,這是巨變了的鄉村,這是時代的脈搏。
田秋與其他歷史人物(如三閭大夫、共工)的不同選擇,凸顯了他堅韌不拔、勇于擔當的精神品質。“黔中砥柱”四個大字就是象征田秋,以及他所代表的黔中大地的精神圖騰,這種象征手法使得文章的主題更加鮮明和深刻。“他是烏江的兒子,烏江懂他,大山懂他”等富有哲思的句子,既表達了人與自然的和諧共生,也揭示了人性中的堅韌與執著。在敘事節奏張弛有度,在敘述田秋的故事時,既有緊張的情節,如烏江行舟遇險,也有舒緩的描寫,如回憶求學歲月,這種張弛有度的敘事節奏使得文章讀起來既引人入勝又耐人尋味。
林漢筠的每一篇散文都是沉甸甸的。《觀儺》一文,作者開篇以回憶的方式,敘事與情感的交織,將讀者帶入一個充滿溫情與童趣的鄉村場景。他通過母親追趕自己聽“響樂聲”的情景,不僅描繪了童年的歡樂,也流露出對母親深深的愛與懷念。這種親切的敘事,使得文章從一開始就具有了很強的感染力,吸引力,引出下文對儺文化的探究和思考。通過哥哥的轉述,非常親切地讓讀者了解了什么是儺,“儺是古代驅疫降福、祈福禳災、消難納吉的祭禮儀式。人們出于對神謙恭和畏懼,儺藝師便戴上面具。于是,人、神、巫、鬼攪和在一起,就有了一種精神寄托”。[注釋5:林漢筠:《黔地行記》, 廣東人民出版社2024年4月版,第109頁。]儺戲表演的生動細節描繪,也是作者擅長的手法。“抓力虎”的形象被描繪得既矮小又精瘦,但他的表演卻能讓全村老少為之傾倒,這種身形與品質的對比,增強了文章的戲劇性和可讀性。“響樂聲”不僅代表了鄉村的娛樂活動,也象征著村民們對精神生活的渴望和追求,充滿了豐富的意象與象征。“看似筆直,卻一路嘻嘻哈哈地走著、流著”,這種擬人化的手法賦予了小河生命力,使讀者仿佛能親眼見到那條活潑流動的小河,而“小河”則象征著時間的流逝和生活的變遷,它見證了村莊的興衰、人們的悲歡離合和家鄉的巨變。
林漢筠的語言極富有個性,他善于運用簡潔明快、深沉厚重的語言來描繪鄉村的日常生活和風俗人情,同時又不失文學的韻味。“人們放下褲腳,在河里頭簡簡單單地洗一下腳上的泥巴,就朝著‘響樂’聲的地方走去。”這句話既寫出了村民們樸實無華的生活方式,又表達了他們對“響樂聲”的熱愛和向往。對“儺戲”的詳細描述和解釋,讓讀者了解這一古老藝術形式的歷史淵源和文化內涵,表現了深厚的文化底蘊,吸引讀者對傳統文化在現代社會中生存和發展的關注與思考。
林漢筠運用對比與反襯,將“宛平”(京南門戶,歷史名城)與穩坪這一默默無聞的小鄉鎮進行對比,突出了穩坪的隱蔽與不為人知;將山莊的奢華與山寨的簡樸進行對比,突出了山寨人民對儺戲的深厚情感和熱愛;將現代都市的喧囂與儺戲的靜謐進行對比,強調了儺戲作為傳統文化的獨特價值和意義。同時用“浩瀚的地名之中”反襯出穩坪的渺小與不易察覺,增強了文章的層次感和深度。“雨,是一個婉約的詞語。它,可以從山頭的石縫里探出頭來,從那人的寨子的土瓦里張揚火煙,從寨口的古樹里宣告季節。”“迎接他們的,又是一場抬頭仰望、低頭思索的大雨”擬人化的手法將雨賦予了生命,仿佛它在主動地探索、張揚、宣告,增強了語言的生動性和畫面的形象感。“穩坪,也是一個婉約的詞語。這個黔地小鄉鎮,像飄落的一粒細雨,藏進深山之中”。[注釋6:林漢筠:《黔地行記》, 廣東人民出版社2024年4月版,第111頁。]用“飄落的一粒細雨”的擬人化形容,既展現了其地理位置的偏僻,也賦予了它一種靜謐、溫婉的氣質。“一粒細雨”,象征穩坪在歷史長河中的渺小與不起眼的,但正是這樣的地方,卻蘊藏著豐富的文化底蘊和獨特的風土人情,有了鮮明的對比和深刻的隱喻。“夜,慢慢地沉去;雨,緩緩地飄來;近處、遠處的燈,將山莊的雨夜拉上一道絢麗的彩虹。”“開紅山”是定,是靜,是鎮,如同山寨的古樹;而“下火海”則是動,是喧囂,是歡騰”,[注釋7:林漢筠:《黔地行記》, 廣東人民出版社2024年4月版,第122頁。]這些句子運用了排比、對偶等修辭手法,不僅句式整齊,節奏感強,而且富有韻律美,增強了文章的可讀性和感染力。
“雨,像寬大無比的海,用優美的線條,牽出天朗氣清,牽出春和景明。它,無時不在向天、地暗示著,花朵,明月,驕陽,牛群,歡唱”。對新時代鄉村景色的描寫,一草一木,一花一樹都是透著時代的氣息,這是偉大的時代,這是幸福的時代,這里的鄉村發生了巨大的變化。
作為嶺南作家,林漢筠以全新的視角審視黔地文化,他通過行走“他鄉”的描述,展現了東西部協作的文學成果,就像他在《結龍橋,打開世界的鑰匙》說的,“橋,水梁也;水梁者,水中之梁也”,他為兩地文化交流搭建了橋梁。
《黔地行記》的出版對東西部協作文化交流和烏江地域文化研究具有重大現實意義。它不僅促進了粵黔兩地的文化交流與合作,還加深了人們對黔地文化的了解和認識。同時,該書還為推動當地經濟社會發展提供了文化支撐和精神動力。
林漢筠說:“我做了黔地的圣徒,與這座新城達成了默契,與這座山寨形成了共識。”[注釋8:林漢筠:《黔地行記》, 廣東人民出版社2024年4月版,第004頁。]觸摸她的體溫,感悟她的文化,傾聽她的故事。抒寫著這個時代的美好,記錄著新時代的山鄉巨變。
作者系廣東省樂昌市高中語文高級教師。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