寧靜而孤獨的精神旅行
——談吳投文詩歌創作
文/幽林石子
湘籍批評家、詩人、湖南科技大學教授吳投文,主要從事中國新詩研究。他在進行學術研究的同時,潛心創作,且收獲頗豐。吳投文性格溫雅,喜好安靜,他的許多詩歌也呈現濃烈的孤獨感與神秘性。近年來,吳投文的詩歌正引起學界的關注,有多位評論家陸續發文研討他的詩歌。吳投文三十年的詩歌創作,進入了中年的豐盛期,在當今詩壇產生了較大影響。
吳投文的代表性作品有《雪雁》《你說什么都是什么》《雷聲》《月夜》《山魅》《空白》《一個人的影子生涯》《收獲季節》《葬禮》等,這些詩歌開辟了深邃的思維路徑,彰顯語言的開闊性與耐讀性。吳投文的詩歌創作已經脫離了靈感寫作的初期軌道,大多是非常克制而成熟的智性表達。在他的詩歌中,孤獨、隱忍、詭異三條動脈經常清晰地浮現,體現了詩歌語言的精確性與靈魂深度。
吳投文在詩集《看不見雪的陰影》的自序中闡明了自己對寫作的猶豫,而讀者恰恰從這種猶豫中感受到他對詩歌的敬畏。因為不需要落入器皿,所以在沉默中堅守。即使面對冰天雪地,也獨自享受寧靜而孤獨的精神旅行。正如一只在空中翱翔的大雁,翅膀壓低了雪的身影,凝視大地,思緒遼遠。這似乎是靈魂創作的象征性意象,亦是詩人自我銘刻的烙印。比如這首《雪雁》:
一場大雪降下我的孤獨
那種緩慢下降的孤獨
一片片打濕我的肺
和骨頭
所有的溝壑和陷阱
都被填滿
所有的孤獨
都忍不住顫抖
那些雪地上的墳丘
像倒扣的黃金天堂
此刻,我經過它們
為曾經忽略它們而羞愧
我的目的地
始終沒有到來
我迷戀的那些事物
像愛人一樣消失
這首《雪雁》語言幽僻而孤寂。詩中“雪雁”是不平凡的活性圖像,并非簡單樸素的自然意象,卻更深地反映出詩人所在的某種生命狀態與理想精神。此刻,雪雁與詩人同時融入飛雪的閃光中,使人想起鈣質豐富的碑。在冰涼的雪地里,沒有誰比詩人更理解一只雪雁,而雪雁也隨著飛雪撲入詩歌的故鄉。詩中有這樣的詩句:“一場大雪降下我的孤獨/那種緩慢下降的孤獨/一片片打濕我的肺/和骨頭/所有的溝壑和陷阱/都被填滿/所有的孤獨/都忍不住顫抖/那些雪地上的墳丘/像倒扣的黃金天堂”, 此刻最醒目的是生活的律動,驛站起伏,漣漪奔波,跌跌撞撞。這里的“下降”并非跌落,卻意味著一種腳踏實地的心徑,而“孤獨”卻乘坐收獲的歡欣。就好像鮮花踏緊大地,卻張大嗓門,極力向高空呼喚。這是一種沉甸甸的寂靜的美,一種奇妙而僅可獨享的意境,卻使人隱隱作痛。而這種體驗不斷輪回,直至浮起一個個黃金似的墳丘。“此刻,我經過它們/為曾經忽略它們而羞愧”,這時不僅有燈的亮光,也有茫茫白雪的輝煌淹沒某種失落與憂傷。答案令人欣喜,不但在白雪中飄飛,還在黃金的天堂里成熟。詩人微笑著融化記憶中的冰凌,以蔥蘢的詩情,鋪展潔凈的才情。而這曾經是在無意中被忽略的,執著與自信是非常珍貴的精神之鈣。“我的目的地/始終沒有到來/我迷戀的那些事物/像愛人一樣消失”,詩人的指尖始終按在熱情的脈博上,靈魂的律動真誠回應心臟。他有足夠的熱情培育他所經過的風景,也以最好的方式修剪枯枝敗葉,愛人始終陪伴著他綴于綠葉叢中。
吳投文深情熱愛著詩歌,他曾說:“詩歌像火焰一樣在風中猶豫著,它的余燼隨風飄散,但它內在的熱度卻帶給我們致命的溫暖。”也正是這種具有時代意義的寂靜的事業,掀起了筆墨的一派生機。變換的季節真誠而飽滿,一層一層在深處的憂愁里流動,果實安靜而深沉。我們再看他的另一首作品《秋風起》:
秋風起,我從閣樓里下來
敲鐘,一下兩下叮當
蟬聲的羽翼稀薄
西風來得早哇
有人撞上南墻不回頭
獨自嘆息
草木抵住最后的凋零
卻是一個恍惚,又一個恍惚
掩飾果實的遲疑
我鐘愛這些發黃的草木
那么脆,天空晴朗
少婦走過庭園里落葉的嘀咕
我和一只蝴蝶的魂有什么區別呢?
舞一下,又一下
河水在遠處靜靜地閃光
梯子已成朽木,我只有沉默
螞蟻爬上一節
就有一節的恐慌
這首詩曾刊發于《長江叢刊》2018年8月號上旬刊,也被中國詩歌網評為“每日好詩”。此詩深受讀者的喜愛,筆者細讀了多次。詩中多條隱形的思想秘道與堅固的精神橋梁交織,加強了詩歌的空靈感與神秘性,耐讀性強。
細心的讀者可以認為,此詩是人生的綠葉與果實間所作出的沉穩的呼應。初秋,是起風的時候了,歲月的色彩又深了一些,而“我從閣樓里下來”。這里并不需要說明,下樓時有沒有人陪伴。這時候詩人已步入中年,他正以成熟的步履緩慢地行走在生命的秋天里,秋風吹著安靜的頭發。“敲鐘,一下兩下叮當”,這是來自時間深處的鐘聲。在初秋的風里,有一種緊迫感油然而生,這一定是詩人在為自己敲鐘。歲月匆匆,還有很多事在未來等待,而過去的其實也還可以更完美一些。趁現在精力充沛,抓緊時間,好好部署。“蟬聲的羽翼稀薄”很自然地運用了通感手法,從聽覺上的“蟬聲”轉移到視覺上的“羽翼”,有效提升了意象的靈巧性與新奇感。這里借“蟬聲的羽翼”隱喻平生的業績,而“稀薄”便成為一個謙詞。實際上,一些深深淺淺的笑容一直融化在生命中,而愿望也已達成綿延的幽徑。
“西風來得早哇,有人撞上南墻不回頭,獨自嘆息。”這一節“有人”一詞用得妙,使整小節進入一個迷幻的境地,延伸了詩歌的想象空間。我們先不去追問此人是誰,但一個“撞”字已經清晰告訴我們,他遇到阻力了。這正意味著可以見到真實而微妙的磨礪中的光影,那片光影會越來越成熟,越來越優秀。艱難與困苦盡管是滄桑之河,心境如彈簧一樣總能把持該有的尺度,夜里噙淚經常成為一種光明的習慣。
每個人都是作為獨立的個體而充實人間的,喧囂反而會使我們感到莫名的孤寂,而草木也一樣。當一片葉子在自然的舞池中歌唱久了,她也會失落地飄向大地,風也抵不住生、老、病、死的宿命。“草木抵住最后的凋零,卻是一個恍惚,又一個恍惚,掩飾果實的遲疑”,此處詩人用非常形象又充滿哲思的語言,暗示了生命的起起落落。果實的成熟是芬芳之后的歸宿,那是一種圓滿的隕落。正因為是隕落,所以期盼再多一點“遲疑”的心思,多一些繽紛的歌舞與美好的過程。
在感嘆光陰匆匆的同時,悄然回眸,又倏然明朗。“我鐘愛這些發黃的草木,那么脆,天空晴朗,少婦走過庭園里落葉的嘀咕”。 從創作技藝上來講,“落葉的嘀咕”運用了活性的通感手法,同時也運用了擬人手法。嘀咕著的落葉是引人深思的鮮活的自然情境,它不僅勾勒出真實的生命狀態,同時反映出這種狀態下的某種落寞與不舍之情。黃葉飄零,秋天蕭瑟而神傷,幸有詩歌與摯友的陪伴,給生活帶來了生機與希望。在我們的生活當中,總會遇見許多美好的事物,而這也恰恰是不可或缺的詩意。
對于步于中年的詩人來說,他們大多褪去了青春的星火,他們緩慢地抒情,安靜地呈現。“我和一只蝴蝶的魂有什么區別呢?舞一下,又一下,河水在遠處靜靜地閃光。”橫向的生活,精致而美好;縱向的生命之舟,靜靜地飄向時間深處。“梯子已成朽木,我只有沉默。螞蟻爬上一節,就有一節的恐慌。”這一小節中“梯子已成朽木”與開頭“秋風起,我從閣樓下來”相呼應。當我們揚起韌性之帆,季節越來越深,而“朽木”終將浮出歲月的水面。瓜熟蒂落,而“我”所遇見的小螞蟻,他神情恍惚,也于恐慌中遇見“我”游移而疲憊的眼神。
這首詩的藝術手法多用通感、象征、隱喻、抑揚結合、首尾照應等。創作時思想沉穩,詩歌語言詭異,指向陌生化,充滿神秘性與滄桑感。是一首聲、情、景高度融合,語言高度凝煉的上乘之作。
詩人作詩其實是一件非常艱難的事,要盡力排除生活鎖鏈的束縛,在一個夢幻般的理想空間里,提煉精神的藝術雨露,營養自身,也潤澤他人。當某種純粹的優美的幻象被現實的颶風攪擾的時候,有一種揪心的憂慮漫過心臟,使人不得不重新回到希望的夢境中,求取內心的平靜與快樂。實際上,真誠的詩人都是孤獨的思想者,吳投文亦如此。我發現他對每一首詩的創作要求都很高,語言新奇,善于吊詭,且感情深厚。文字間流動著智性而奇特的靈光,而憂傷亦是他鞭撻社會與人性陰影時的心靈印記。我們再來讀他的這首《月夜》:
我路過夜晚的樹下,風一陣陣吹起
遠處的巖石慢慢從地上升起
在空中凝聚,合為一體
它的圓形發出光,愈來愈亮
樹林沐浴在光潔的銀色里
我放慢腳步,踩著小徑上的枯草
像一個老人把一生的心事收起
咀嚼空濛中草屑的余香
此刻,我渴望永久的寧靜
在獨自的矚望里返回內心的訓誡
鳴蟲遲疑著撥響呼吸的節奏
我閉上眼睛,暴露在光芒的箭矢中
風持續地吹著樹林的翳影
我躲避偶爾從額前飄落的樹葉
心里顫動著異樣的渴望
像一枚果核分泌赭黃的火苗
詩歌《月夜》取自靜謐的生活場景,是內心愿景的巧妙延伸。不難看出生命的蔥郁,月色的深沉。詩題用詞簡潔,卻點破生命的玄機,令人遐想。詩中夜色籠罩了現實的生活圖景,希翼伴隨失落影響著斑駁的心靈,咬緊牙關,收納季節深處的飽滿與枯黃。詩歌第一節起步舒緩,意蘊開闊。詩中的“巖石”是月亮生動的隱喻,而“巖石”既優雅,又鋒利,并能筑起秋天的凌厲。此時,月亮端起幽光,緩緩出場,月亮的步履與詩人的步履互相映照。遠處的事物越來越近,而經過的事物又越來越遠。自然的情愫遇上安靜的靈魂,小徑、枯草、鳴蟲、翳影、樹葉都以各自的方式,觸摸詩人眼里的悲歡。現在最喜歡做的事是把心事收起,在廣袤的空間,分泌果實的欣慰與微笑。
在吳投文的情感詩中,語言大都比較含蓄,講究場景的分寸感、意境的隱秘性,這與他平素溫和內斂的性格不無關系。在詩歌創作中,吳投文擅長運用陌生化、通感等藝術技巧,使讀者產生新奇的閱讀體驗。比如這首《你說什么都是什么》:
你握著我的手
顫抖著,不容易握住
我與你對視,緩緩轉向世界的靜止
空氣碰撞空氣
敞開的門擋住你的背影
風把光線晃得稠密,讓我站住
你說什么都是什么
我們握著手
站在彼此的黑暗中低泣
詩歌第一節就自然地運用了通感手法,完成陌生化的技巧,比較隨心又有新意。全詩沉穩中流露情感鏡頭的方向感,在深邃中體現出一種自然的憂郁美,語境柔和而寧靜,克制又朦朧。讀者能從詩中直線感受到兩團緩緩追逐的青春之云,似有雨滴纏綿于天地之間,而落腳時舒緩輕柔,揉熱了細膩的地心。詩題“你說什么都是什么”等同于“你說什么就是什么”。一朵云溫文爾雅,百般呵護心儀的另一朵云。愛著就會順著,順著就已寵著,連錯誤的雨點也顯得清純可愛,藍天為此撐開幸福的顏色。當共同的草地長滿含羞的綠眼睛,透過抒情的暖陽,彼此目光交織,草木葳蕤,只是還沒有放走眉尖的蕭蕭斑馬。一種深沉的情感摒棄了小我,一片天足以滑翔豐滿的羽翼。“緩緩轉向世界的靜止”不需要說出,就默默把微妙的風景捕獲。因為距離產生美,只需要“空氣碰撞空氣”,留存溫軟的想象,讓空氣與空氣升溫,或許親密接觸。反正“敞開的門,永遠會擋住你的背影。”你不會離去,甜美的想象充滿彈性。所以“風把光線晃得稠密”,陽光充足,溫情濃厚,即使飄遠也心存念想,互相牽手,于彼此的夜色中深情啜泣。
吳投文的詩歌精煉而深邃,生活現場感濃烈,引人深思。詩歌有體現社會舞池陽光、溫暖、燦爛的一面,也有抒發內心苦痛、傷感、無奈的情感一角。甚至在深入人性細小的一隅時,就掏出了沉重、混濁而充滿異味的一把泥濘。我們再讀吳投文的另一首詩《雷聲》:
夏天的雷聲使草木在雨中
震顫,閃電像一道鞭子
抽打活著的人們
所有匍匐在地上的事物
再一次伏得更低
這時,在孤寂的森林中
動物們驚恐地聚集在一起
它們有自己的思想
閃電每一次照亮它們的眼睛
它們就站得更高一些
詩中的“雷聲”實際上是一種鞭策。如果潔靜的天空對大地的渾濁不滿,如果大自然的良善對人心的阡陌質疑,閃電與雷聲便會及時提醒眾生,尤其要“抽打活著的人們”。那些細小的事物通常謙遜地“匍匐在地上”,它們普遍擁有一種簡單低調的自然美,貼緊大地感受離合與悲歡。相比人類,動物更善于自由發聲,它們對周圍的事物保持絕對的真誠,具有質地純正的生活,使我們能感受并欣賞到不被包裝的生長藝術。它們終生說不出合適的言語,但“它們有自己的思想”,理解閃電的暗語。容易表露的真性情使它們比我們更接近真、善、美,自由的靈魂已深入人類無法企及的精神領域。
對詩歌心存敬畏是真詩人常有的精神狀態,他們因淚花的動蕩而流下微笑,或許感動于周圍的塵埃與星光,或許被自已感動。在遠處的天涯,每個人都可以飲漢語之泉滋養生命,而每個人都需要樸素的事物打開精神原鄉,并喂養心靈的村莊。再看吳投文收錄于《土地的家譜》中的一首詩《收獲季節》:
靈魂系在稻尖上的愛人
挑一路叮叮當當的汗珠
走過鐮刀剛殺伐的田野
――暮色呼喚你回來
燈光亮處的家屋
升起一彎愛情的月
愛人一生走過許多路
總在回家的時候
油然想起白米飯的香味
――白米飯喂養大的阿寶
是從她身上結出的果實
愛在溪邊放牧海星星的童話
親近泥土遠離詩歌的愛人
一生與稻穗相依為命
锃亮的鐮刀代表她的心
――在風中欲語還羞的稻谷
沿著被汗水依戀的道路
和你一起回家去
這首詩鄉土氣息非常濃厚,應是吳投文早期詩歌創作的成功之作。筆者把它放在本文偏后的位置,是因為詩中隱含“出發”的激情,同時布滿“憩息”的溫馨,“收獲”的風景亦愉悅了心靈的平原。詩中奇崛的想象與真情文字,非常感人。吳投文把此詩放在詩集《土地的家譜》的前面,可能因了某種特殊的意義。《收獲季節》的表象是一曲深情的鄉村田野戀歌。詩中的“愛人”是一位單純、質樸、勤勞的女子,她可能讀書不多,但有一顆真誠善良的心,長年親近田野,與稻穗相依為命。她勞動的果實裝滿愛情的彎月,喂養著詩人的情懷與遠方。詩中的“愛人”實際有一種第三人稱的指代意義,更具有“母親”的隱喻性成份。母親小小的身影平凡而美麗,在溫馨中編織米粒的深情,使阿寶產生深深的依戀。母親一天勞作之后,詩人也放下案頭的筆。暮色緩緩升起,小小的家屋亮起溫暖的燈光,照著一家相愛相親的影子。
母親的腳步從一片田野進入另一片田野,稻穂用謙卑丈量著兩路深深的腳印。母親用一粒米的飯香喂養阿寶和詩人的情懷,卻經常在辛勤中忘記自己的饑餓。阿寶深情地依戀著樸實而詩意的田野,融合溫暖的親情。深愛母親的阿寶,用心靈的語言歌唱母親的汗水與收成。母親是一位幸福的農家女子,正是這位用生活與身體寫詩的女子,讓詩人懂得了生活的真諦,理解生命之根。
吳投文早期詩作還有一首《葬禮》:
永恒的愛人,你一如既往的足音
行走在莊稼的莖脈里
你這樣回到泥土深處
深情如赴戀人的幽會
――咿呀之聲的嗩吶
吹成一調無望的喚歸
殉難的愛人,你傾盡一生的汗水
喂養瘋長如林的莊稼
再挽一把鐮走進田野
收割一穗一穗的炊煙
(如今,銹鐮掛在墻壁上
握鐮人的背影因風化蝶)
――嗚咽之聲的笙簫
奏一管不忍重歸的鄉愁
幸福的愛人,你一生眷戀的泥土
深情地浸過你的頭頂
莊稼影里古典的村莊
紛紛揚起清明時節的煙雨
――鏜嗒之聲的陣鑼
送你到泥土深處的家園
這近似于生命轉折中的一個晴天霹靂。因為曾經勞動的身影深深沉進莊稼,所以知道熱愛田野的親人,與泥土一起長成了一道滄桑的風景。讀者能聽到輕輕的嘆息在整首詩中回響,悲哀的簫聲為她曾經的背影奏響“不忍重歸的鄉愁”。一道刺眼的閃電,剎那間閃過新生的田野,稻子在寒風中為“離別”奏響憂傷的挽歌。整首詩給人一種心靈被撕裂的感覺,疼痛漫過每一個詞語,下起紛紛揚揚的清明雨。詩歌給人的真實感令人震憾。在哀婉的歌聲中,詩人把“永恒的愛人”“ 殉難的愛人”“ 幸福的愛人”呈現于相同的泥土家園,卻體現了勞動與憩息、堅守與離別、幸福與悲傷的生命羈旅。而今,佝僂的背影不再深入莊稼,“殉難”是一種勇敢的別離,更是幸福的呈現與懷念。 “愛人”因“殉難”使笙簫嗚咽,季節因永恒使莊稼重歸,這是一種真實的向死而生的生命歷程。莊稼因葬禮起死回生,繼而郁郁蔥蔥。縱觀全詩,詩人的想象足可以假亂真,情節的虛擬能力超凡脫俗,鄉愁之痛深入骨髓,深入人心。全詩在自然舒緩的語境中,鋪陳鄉村的平凡景象,體現出深厚的故鄉情懷與緬懷情緒。
(原載《文藝生活》2023年第4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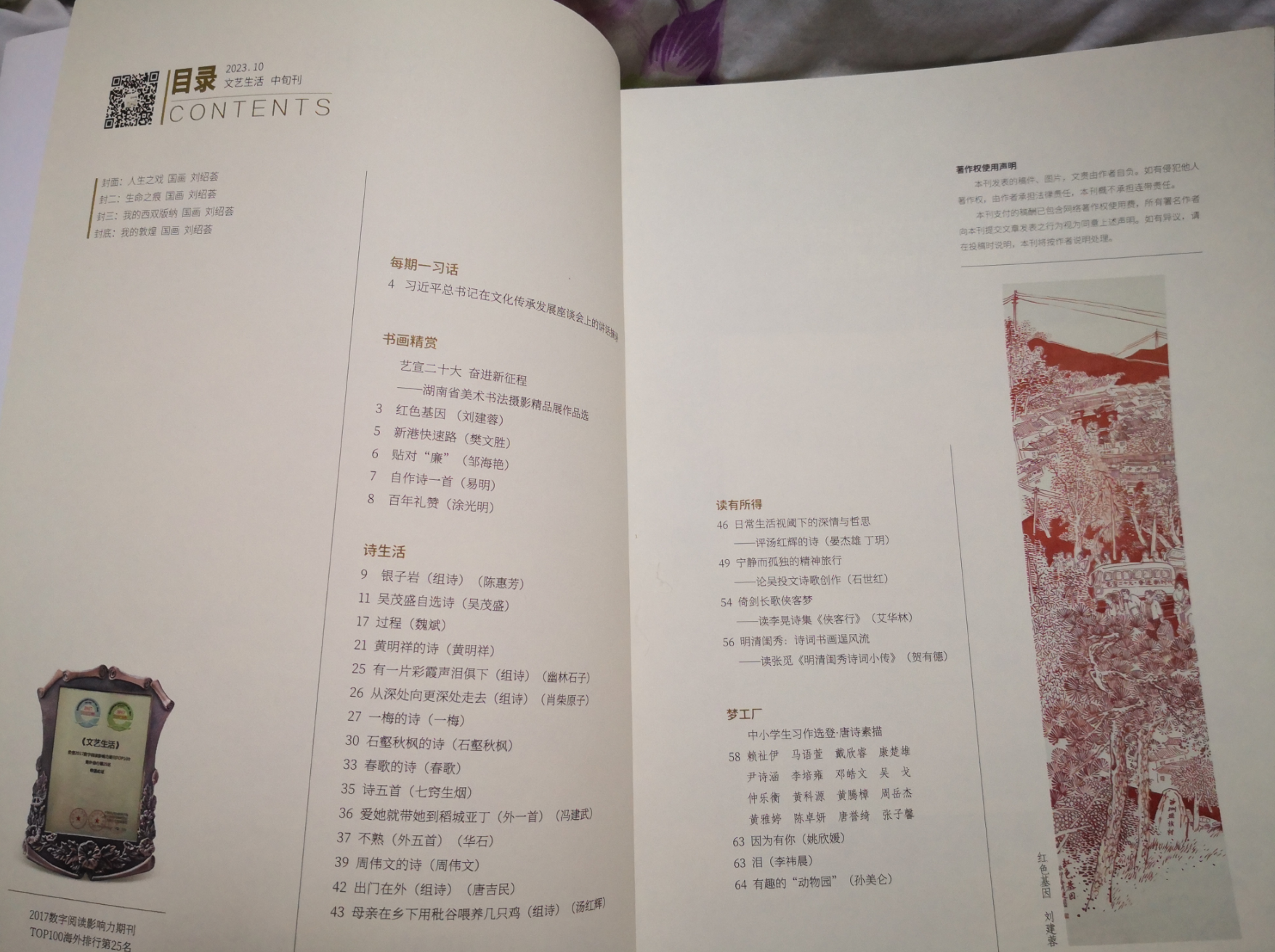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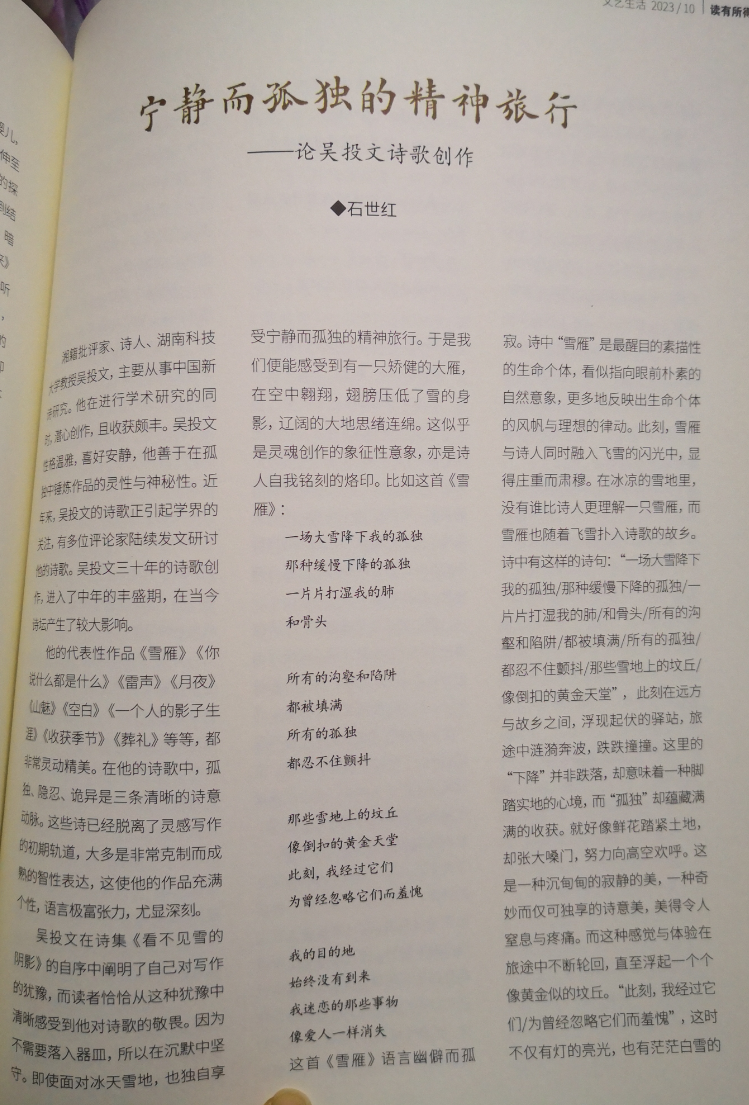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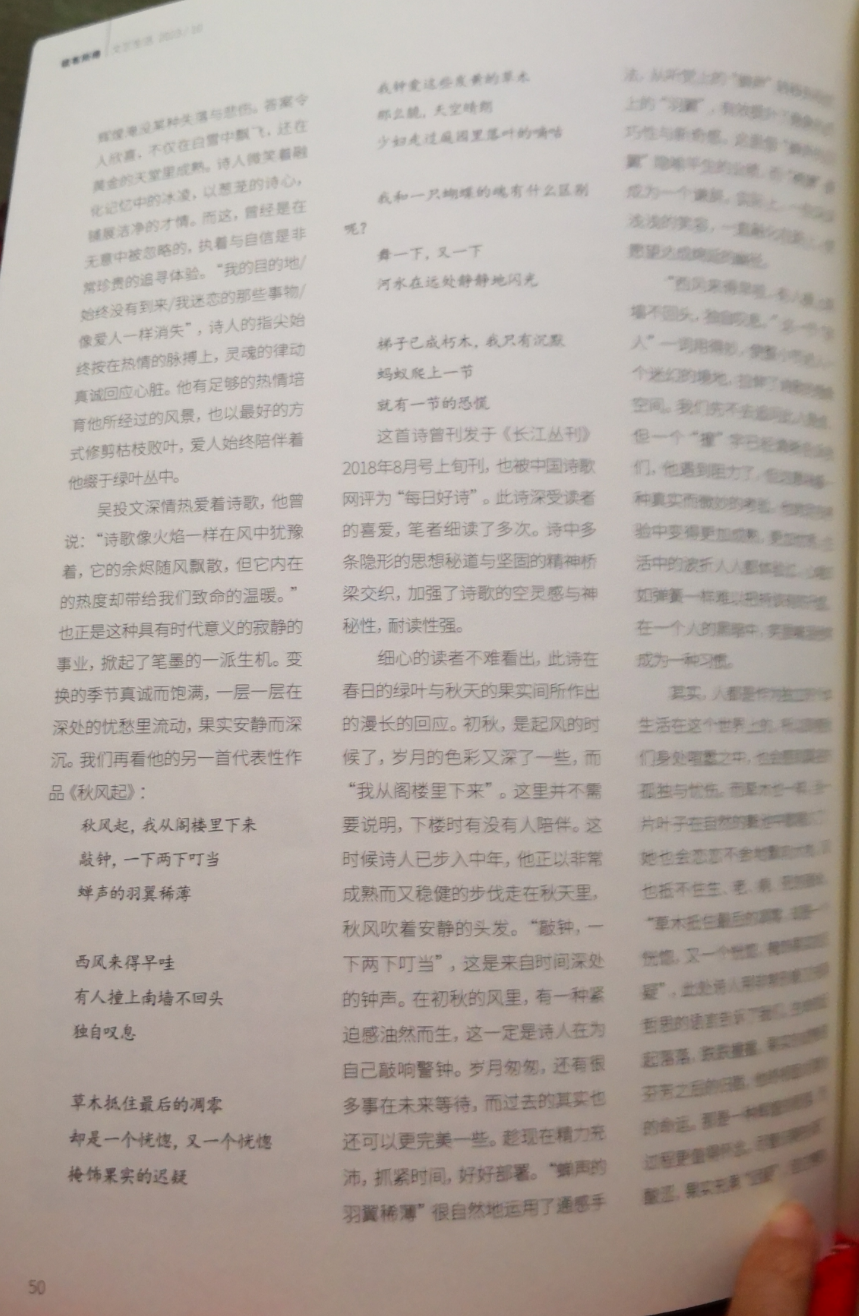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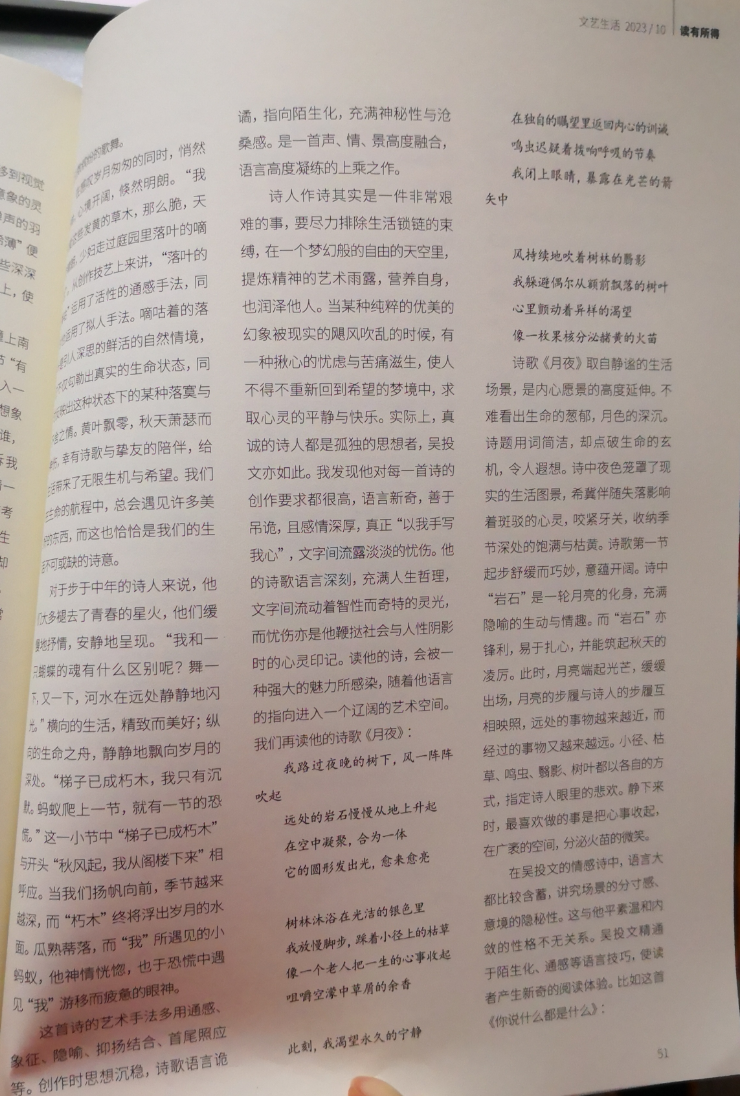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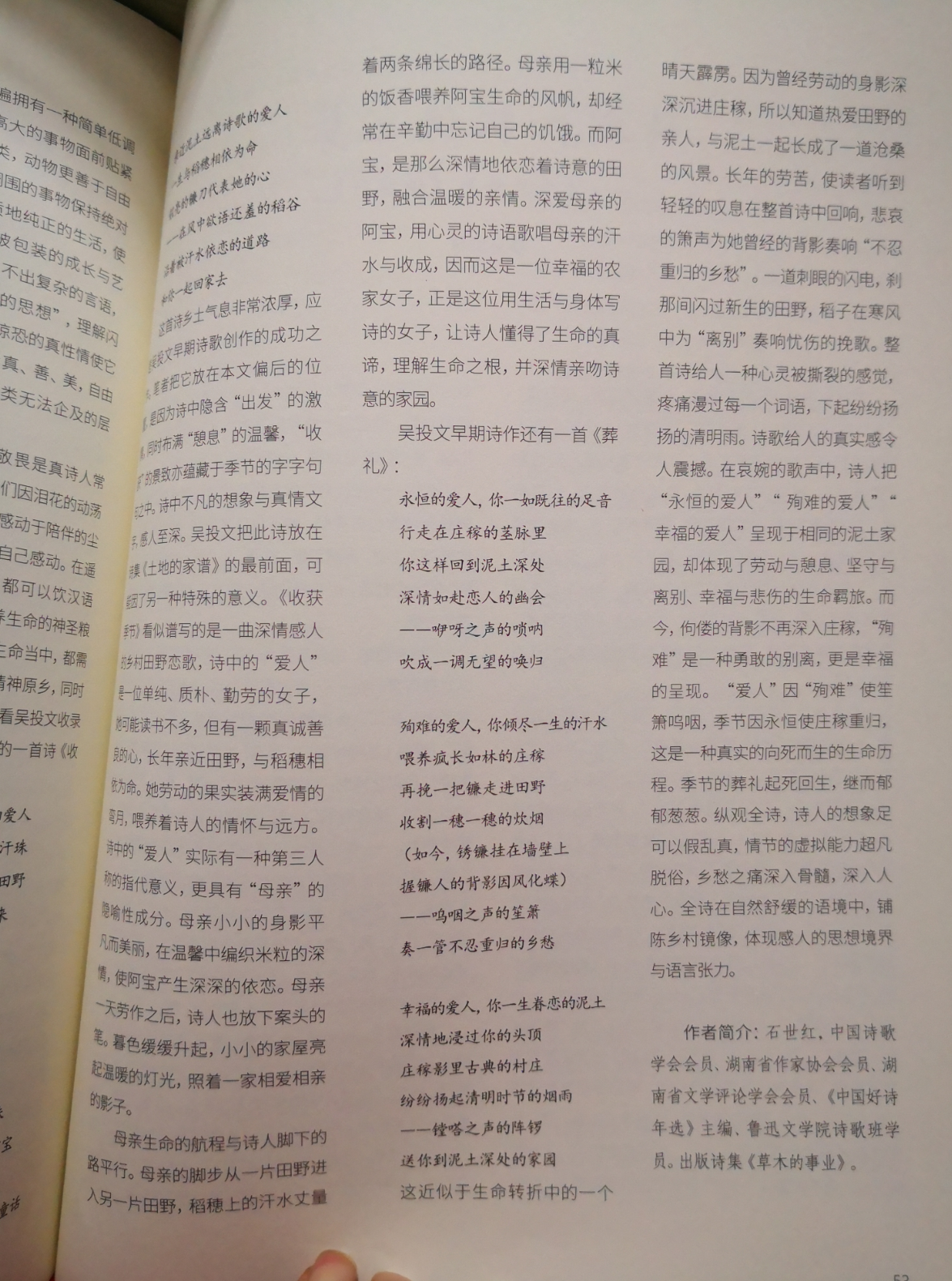

【作者簡介】幽林石子,實名石世紅。中國詩歌學會會員,湖南省文學評論學會會員,《星星》詩刊2023年度特邀評論人。魯迅文學院湖南詩歌班學員,《中國好詩年選》主編。湖南省作家協會、音樂家協會會員。湖南省新鄉土詩歌研究會理事,寧鄉市作協、音協理事。近七百首(篇)詩歌、評論、散文發于《星星》《詩林》《綠風》《散文詩》《湘江文藝》《文藝生活》《小溪流》《草堂》各級報刊。有作品被《青年文摘》轉載。出版詩集《草木的事業》。文學創作業績被《星星》《鴨綠江.華夏詩歌》《中國詩人》《湖南日報》《湖南文學藍皮書》《長沙晚報》《今日寧鄉》等紙刊收錄或報道。有詩作被譯成英語推介到國外。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