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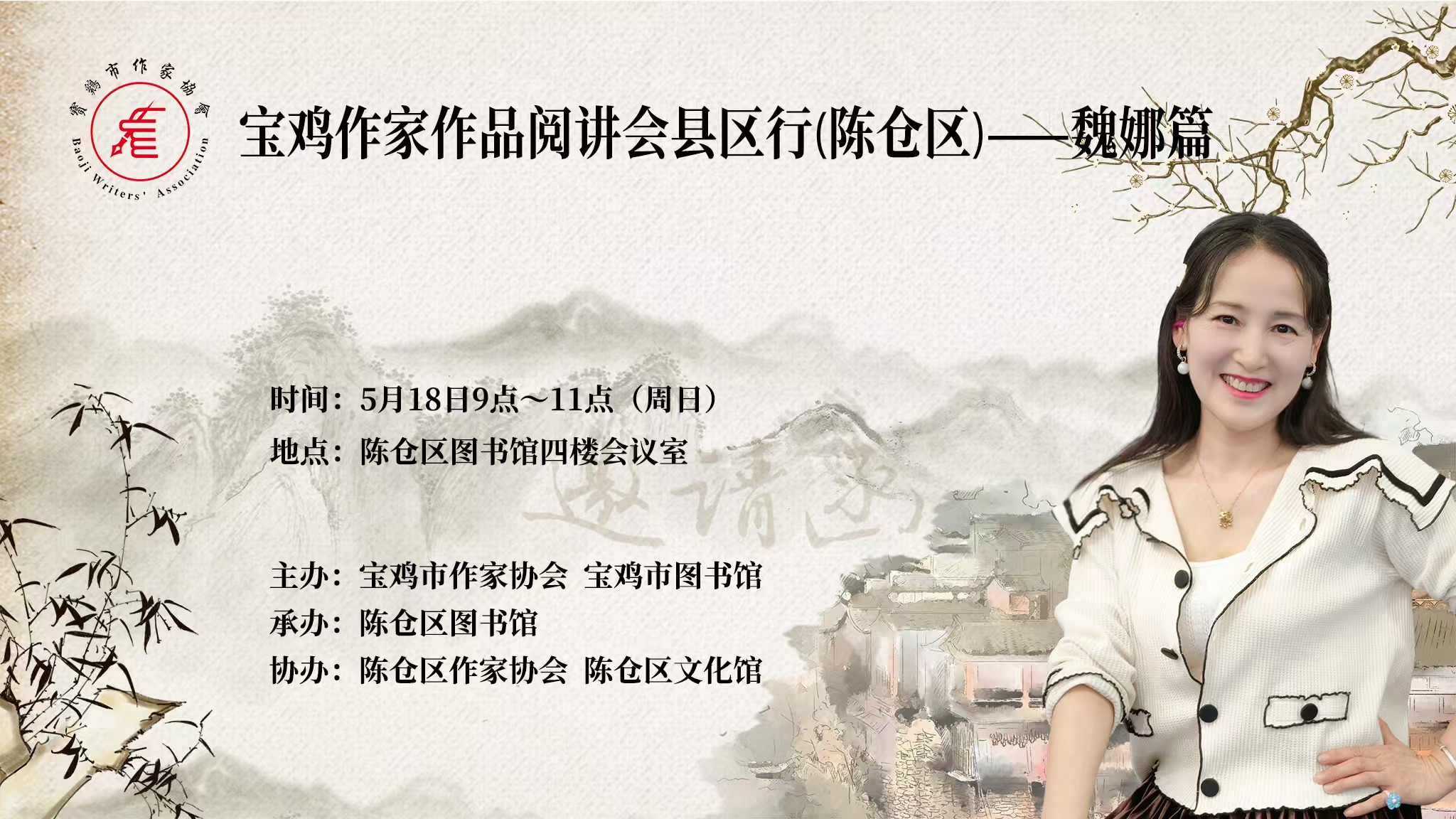
現實關照與理想之境的詩性抵達
——魏娜詩歌的藝術格調
作者:郁楓
重讀魏娜的詩集《低語》,突然獲得了一種震撼和力量感。這是我現在日常閱讀中很少有的一種閱讀體驗。說起來,魏娜的詩集《低語》是和我的詩集《秋天最末的憂郁》是一同在我市著名詩人白麟老師的攛掇下由寧夏黃河出版集團寧夏人民出版社出版的。而且,次年我們倆一同獲得了“六維?首屆寶雞作家協會文學獎”詩歌獎。必須承認,由于當時的心浮氣躁,無法沉下心來完整的閱讀魏娜的詩集,制度了其中的一部分。當今天因為要對她的詩作進行評價的時候,不得不沉下心認真的閱讀并思考。至此,我才發現自己當年的浮躁竟然錯過了閱讀一本優秀詩集的良好機會。
《低語》的優秀,在于它的詩體文本從頭至尾都呈現出詩歌所具有的語言優美、思想敏銳、結構新穎、節奏明快、藝術手法多樣的諸多特點,使人能讀出韻味、讀出感受,讀出對現實的人文悲憫,讀出積極向上的鼓舞感。
我覺得,《低語》就像是一部娓娓道來的悲憫敘事,具有詩歌的小說化或者散文化的傾向,始終保持著一種疾徐由我、悲喜自渡、吐納決絕、快意恩仇的清新自然,表達了詩人熱愛眾生、直視苦難、同情弱者、溫暖他人的悲憫情懷。
詩歌的美,在于意境、在于節奏,在于思想、在于語言的創造。基于這一切,就自然而然地形成詩人獨有的藝術格調。美國著名作家房龍在他的《藝術》里寫道:“任何一種藝術,本質上都是個人感受的體驗。所以,藝術天生就是超凡脫俗的,是超出塵世的一種美好情感的東西。”每一種藝術,都有他自身的特點和創作原則和創作規律,我們總是在以一種模仿和借鑒的方式,用自己占有的素材,以某種特定的體裁表達自己對世界的看法。詩歌亦如此。如果一位詩人喪失了自己對生活敏銳的覺察力和熱愛,既是掌握了再精致的寫作技巧,他都不能寫出打動人心的詩歌。在我讀《低語》的時候,我深切的感覺到這一點。我以為詩人的責任,就是在關照現實的時候,表達自己明確而堅定的立場,并給讀者一種善良溫暖的精神指向——只有以詩性能夠抵達的理想之境。
現在,我想就魏娜詩集《低語》來簡單評述魏娜詩歌的藝術格調問題。
所謂的藝術格調是藝術作品所表現出來的美學品格與思想情操,所反映的是藝術家的綜合修養與審美能力,是衡量作品價值的重要標準之一。詩歌作為文學藝術的一個門類,它的格調應該不超出藝術格調的定義。魏娜詩歌的格調在于品性天真爛漫、在于內心的善良溫暖,在于對世界對生活的熱愛有加和對苦難的隱忍承受。當然還有形式上的別出心裁、指彼而言他、有悲喜而孤單煎熬,有愛恨而自我消解等等特點。她總是出其不意的架構一個詩歌現場,而又措不及防地留下一幢“爛尾樓”;她總是營造出一場盛大的愛情故事,卻又戛然而止的拆穿了內心的希望;他總是敏感于生活的點點滴滴,卻又將絲絲縷縷的牽腸掛肚深藏心底。我有時候認為,要立體的描摹出現實中的魏娜是困難的,因為她總是以詩意的變化莫測,將人生打扮的精彩紛呈,激情四射。
我想了很久,覺得魏娜的詩歌格調問題,必須從如下幾個方面去理解:
一.以卑微視覺與生活對話,寫出蕓蕓眾生的愁苦悲喜。在這一點上,魏娜作為生活的親歷者,她用心觀察底層大眾的喜怒哀樂、卑屑無助,看透了民生的無奈和掙扎,她把作為詩人的真誠和悲憫,一并交還給生活,交換給讀者,給人很強的代入感,也為讀者找到審美的出口。我們來看《真心話》這首詩:
他一生卑微,無所成就
一次酒后,他很認真地說:
我此生的愿望
就是做一個好人
中年以后,他無文憑無技術
把寶全壓在了股票上
有一次酒后,他目光潮濕的對妻子說
“我懂女人的虛榮。有生之年
我一定讓你過上你要的那種生活”
現在,他急于得到這份保安的工作
對對面試他的人說:“雖然我外形不好,
但你放心,人品絕對沒問題”
就是這一首詩,一下擊中了我。她把一個人的幾十年,或者一生的理想和困境活脫脫地展示給人,在愿望、股票、保安等詩眼里,詩人給了我們一個經歷挫敗,仍然堅持自己“人品絕對沒問題”。這種構思技巧提高了詩歌的段落跨度,對一個人一生的困境做了做大限度的留白,增加了詩歌閱讀的沉浸感。同類型的詩歌還有《自己人》《一張老照片》《紅木炕柜》《公交車上》等等,他都是利用一些小故事,營造出眾生百態,襯托出人性的善良與自省,使人產生一種不羞于剖析自身的快慰。
二.視角向下,讓自己成為底層生活的代言人。魏娜的時,給人一種“野蠻生長”的自由恣肆,無拘無束,口無遮攔,表現出一種大無畏的豪放與成熟、或者生澀。有時候覺得他所寫的生活就在眼前,有時候又覺得她所寫的對象就藏在我們身邊,也許是你,是我,是她自己。在《乳房》這首詩中寫道:
母親懷我時,多數時候處于饑餓
生下的我,同樣饑餓
因此,對于乳房沒有依賴和溫暖的印象
女兒一哭,我的奶水就溢出來
女兒使出吃奶的勁吸吮,一身汗。
我疼出一身汗。奶水不夠
乳頭上被吸吮出血泡,而后結痂
如此反復,整個哺乳期
現在我的乳房失落,下垂
沒有同感,沒有幸福感
我時常對鏡端詳蒼老的她們
懷念那些豐滿的日子
這首詩巧妙的利用三代人對乳房的對照關系,寫出了時代的變遷,寫出日常生活里被人忽略的幸福。在與人類生存的“根性”層面,隱喻了生活的廣闊空間,將生活的廣闊性聚焦在點的層面上,聚焦在人的不易言說的“隱私”上,用三代人對乳房的態度,襯托出對生活的態度。詩人以很平常的生活范式,展現出了母性的偉大和美好。這是詩人非常成熟的寫作技巧,看是刻意,實則是審美意識的自然而然、情不自禁的理想表達。
在《穿壽衣》《火葬場》《第一爐》《生命的煙火》等詩篇里,作者以“走到這里,路就走到了盡頭。”“走到這里,情就走到了盡頭。”“走到這里,我就走到了盡頭。”“走出這里的我們,余生的第一天,才剛開始。”“82歲的她,坐在床邊。腳下的空氣很冷。”“百年之后,站著的,不過是兩座墓碑”,“那盞疼痛的燈,她印證了我的罪孽深重。”這些詩句,都隱含了生命的必然走向死亡,死亡中又隱含著新生命的誕生成長,在自然和必然之間,隱含的是對生命無常,人生苦短的哲學思考。
三.創作意境之美,在無限可能中讓詩歌抵達理想之境。也許,魏娜的詩歌寫作并沒有這樣形式上的桎梏,但他對國內外詩人優秀詩歌的閱讀,肯定豐富了她對詩歌深層內核的理解,提升了他對詩歌寫作的技巧。她將自己的精神內質,通過詩句逼近理想之境,那種博愛、寬厚和善良,是人類的希望之境,是詩歌的理想之境,她努力地實踐著,創造著,詩性抵達文字營造的自由、博愛、真誠、正義的價值之域。現如今,我們人類總是在不斷的逃離生活的現場視域,又在不斷地在詩意的理想之境尋求精神的升華,尋求自我安慰。敘利亞詩人阿多尼斯說過:“詩歌是天堂,但它永遠在語言的疆域流浪。”魏娜以語言的歧義性和信手拈來的意境之美,為讀者營造了詩歌的通感。讓我們可以有眼淚,可以有愛憎,可以哭或者笑,但只要心中有愛,就一定會在善良的感召下,努力地生活,努力地活著。這就是詩歌的力量,它只會在沉默中爆發,或者在沉默中滅亡,但它的眼睛是雪亮的額,即使死,也死不瞑目。順便說一句,只有通讀了《低語》篇章,才能知道魏娜的詩歌之美,藝術之美,精神之美,技巧之美。
最后,要對魏娜的詩歌指出兩點不足:、
一.詩歌的小說化、散文化寫作,導致了句子的密致和缺少間隙,影響了詩作的節奏感和知覺延伸。在《清明祭奶奶》《緣分是星星在夜空閃了閃就各自消失》《在時光涼了的茶水里》《絕堤的思念》等篇章里,因為敘事的拖沓,影響了詩歌的節奏,形式上的講故事和散文化寫作痕跡明顯,影響了詩歌的形式美和意象美。書法關于章法的一種說法叫做“密不透風,疏可走馬”,對詩歌寫作同樣適用。
二.注意回避詩歌語言的隨意性和口語化。詩歌的口語化會使詩歌陷于平庸和缺少個性。使詩歌疏離于詩歌的特性語境,必然詩歌的陷于“大眾化”和弱化詩歌的辨識度。
以上,是我對魏娜詩歌寫作格調的粗淺認識。由于學識修養所限,難免掛一漏萬。不足之處還望作者和文友批評指正。
2025.05.16
【郁楓簡介】
郁楓,本名范宗科。男,生于陜西省寶雞市鳳翔區。中國作家協會會員。陜西省作家協會會員,陜西省書法家協會會員。寶雞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兼秘書長。著有詩集《生命的顏色》《在陽光的側立面》《秋天最末的憂郁》,隨筆《走進詩經》,長篇小說《熱土》《塵囂》,散文集《煙火依然》,中短篇小說數十篇。在《延河》《雪蓮》《回族文學》《詩選刊》《上海詞刊》《散文詩》《》《中國藝術報》《陜西工人報》《西安晚報》《華商報》《文化藝術報》《寶雞日報》《秦嶺文學》《中國作家網》《光明網》《人民智作》《作家網》等報刊、雜志、網絡平臺發表詩歌、散文、小說、文學評論60余萬字。短篇小說《握不住的光》獲《延河》2023年度小說榜單一等獎。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