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對話楊黎:平面與廢話
——我們這個時代的詩歌(對話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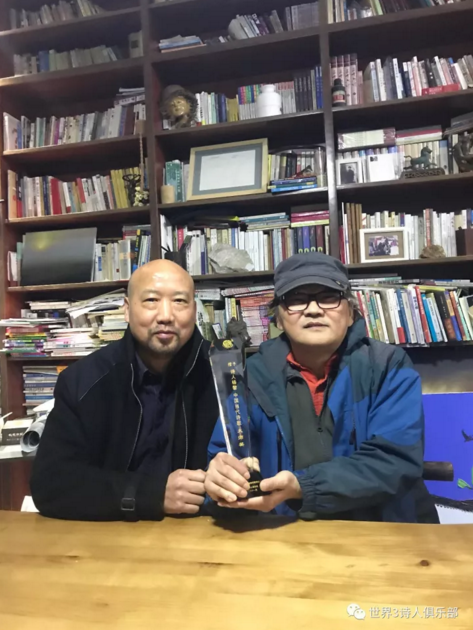
北魏(左)與楊黎

楊黎簡介
楊黎,男,當代詩人和作家,第三代詩歌運動代表作家,廢話寫作理論構建人。
《橡皮:中國先鋒文學》雜志主編,“橡皮文學獎”創建人。出版有《小楊與馬麗》《錯誤》(詩集)《燦爛》(專著)《一起吃飯的人》(詩集)《我寫,故我不在》(文集)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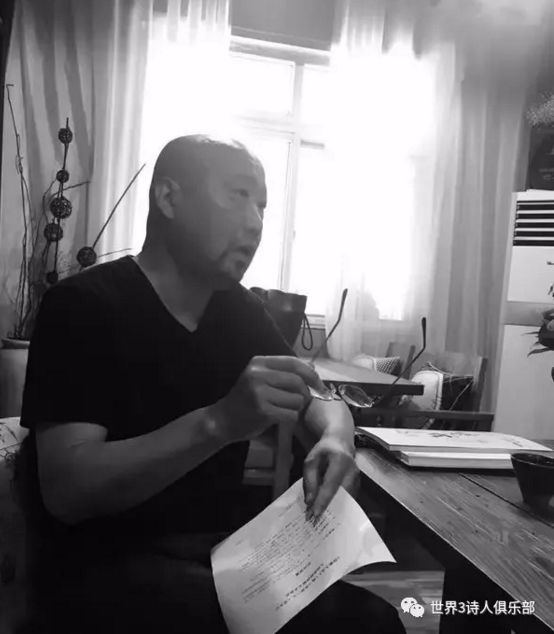
北魏簡介
北魏,詩人,第三代“杰出詩人獎”獲得者,《世界3》先鋒詩歌主編,現居蕪湖。“平面寫作”理念提供者和倡導者,“平面寫作詩歌小組”召集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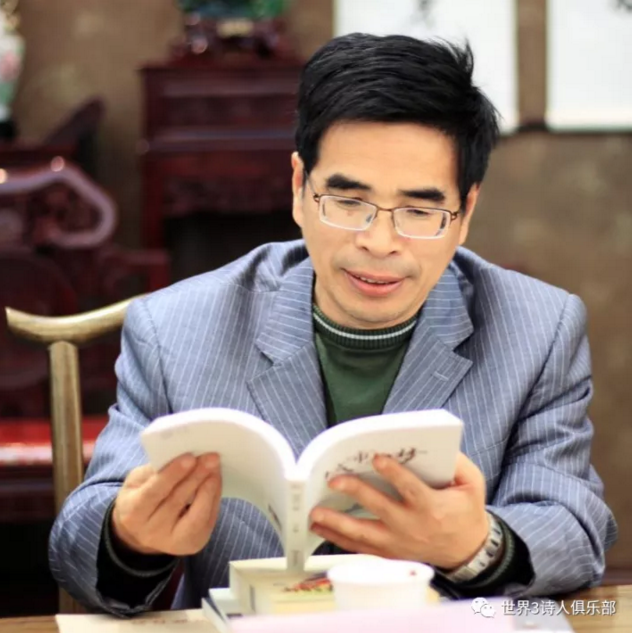
楊四平簡介
楊四平,男,1968年生,安徽師范大學教授,博士生導師,中國新銳詩歌批評家,華夏文化促進會顧問,東西方詩人聯合會主席。
———————————————————————
對話錄
北魏:這次交流會比較湊巧,我們沒有想交流會和新詩百年有什么關系,但是碰上了。我剛才在想,新詩百年,如果從1917年到2017年,真正發生在詩歌內部的,也只有四分之一的時間,是中國新詩在詩歌內部發生和變化的。為什么這么說呢?從現代詩意義上看,也就是從上個世紀三十年代末年到四十年代初,這個時候中國漢語詩歌才出現真正意義上的現代主義詩歌,給我們帶來了另外的一個詩歌面貌,這就是新批評派的成員瑞恰慈和燕卜遜等人,他們在當時的中國大學任教,把外面的幾乎是最新的詩歌觀念理念引進到中國。這些在西南聯大的詩人們在新批評派引入的思想觀念影響下,我們看到了卞之琳,看到了穆旦等人,就這么三四年,中國新詩一步躍入了現代,后來到臺灣的紀弦、痖弦以及羅門、洛夫這些人基本上是這個繼續。再算下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中國的朦朧詩與第三代,這個時間我算一下也就六到七年時間。但是從2000年開始到現在的17年,這個時候中國的新詩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這個17年加上前面的十年,所以我說只有四分之一的世紀,這個里面有我的理解,如果可以這樣理解的話,我們今天在這個所謂百年新詩發展過程中,做的這個交流也就不那么別扭了。
第二個是今天是個好日子,昨天還在下雨,現在在出太陽。下雨和出太陽又能說明什么呢?它不會影響這個交流如期進行。很多人在意當代詩歌不受關注了,他們可能認為不受關注了就沒有寫作的意義了,我不同意這個說法,這也是不太正常的想法,我以為該寫的還會寫,而且會寫得更多、更好,這個今天在這就不多說了。今天的這個交流如果能有同學得到一些領悟與影響,這次活動就是有意義的,即便沒有,今天的這個交流也是有它的必要性的。本周二我們《世界3》出了楊黎的專號,本周六就開始了這次交流活動,這是這次交流活動的動因。
今天交流活動第一項是頒獎,頒獎之前我多說兩句。韓東提出了“詩到語言為止”,影響了很多人。我個人對“詩到語言為止”的理解是認為韓東提出的一個形而上的理念,事實上他的作品是形而下的,非常當下的,因此他的這句話我以為是他的寫作觀念和努力的方向。第二個對中國詩歌產生動力的我認為是多多。多多提出“詩是無中生有”。所以你始終看到他在“與詞搏斗”,詩寫到這份上,我是不好評價的,事實上他這樣寫也是很多人的寫作,對詞語的追蹤以及命名,在語詞間尋找詞語,對于多多,我是近而遠之的,請理會我不說為什么。第三個影響了詩歌發展走向的這位詩人,今天我們把他請來了,他的觀點是“詩從語言開始”。他提出:詩是沒有的東西。和多多的無中生有不一樣,他的是有中生無。關于詩是沒有的東西。待會我們請他自己來進行闡述。從2000年開始,他把中國詩歌固有的形態進行了徹底的顛覆,從好的方面說叫蒸蒸日上,從壞的方面說是烏煙瘴氣。我認為這么表達與形容他都是可以接受的,沒有善與惡之意。這個得有今天的嘉賓——廢話理論的構建者來進行深度闡述。下面歡迎廢話詩人楊黎先生。
楊黎:謝謝,謝謝中國當代口語詩歌研究中心、世界3,我假裝不激動,實際上是很激動的。安徽這個地方跟我很有淵源,我基本上是從安徽這個地方走出來的。雖然我不是安徽人。我的第一首成名作就是在1986年的安徽詩歌報上發表出來的,叫《冷風景》。從此以后,我就成了著名青年詩人一直到現在,我的另一個大獎也是在安徽得的。詩歌報在1988年的中國探索詩大獎賽,我得了第一名。今天時隔三十年,我又到了安徽,被授予中國當代詩歌大師獎,我覺得是我的一個新的開始。上次是著名青年詩人。這次就是我的大師的開始了。韓東說我是一代宗師,我很高興,但我改了一個字,我說我是一代中師,中間的中,中間的意思。謝謝!我很高興。
楊四平:楊黎老師我在學習的時候,他就影響了許多人,這次獲獎是當之無愧的。為了活躍當下的詩歌氛圍,所以我們把他邀請過來,進行面對面的交流。下面是平面與廢話的長江論劍。
北魏:對頒布“中國當代詩歌大師”這個稱號,我們是很慎重的。我們認為一個詩人,當然他首先最主要的任務是寫詩,但你詩寫得再好,也只能是一個詩人,你可能是一個大詩人,但不是大師。艾略特稱龐德為匠人,偉大的匠人,可能就有這方面的考慮。大師是一定要有理論的,沒有理論他不能影響匯集很多詩人,沒有理論他不能影響惠及他人,那怕他“禍害”他人也行,我這樣說有些極端,非常的個人化,甚至很主觀,但今天我卻以為我是站在客觀立場上說這話的。“大師”是這樣的,很多人在他的理論的影響下,會在寫作上發生根本性的變化。下面就請廢話詩人楊黎先生談談廢話理論。
楊黎:我覺得有一點,北魏談到了,大師不僅要有作品,還要有理論,我挺喜歡這句話。我這個人有個特點,干一件事情,我不搞清楚,我就不想干了,甚至吃飯,我覺得我不會因為餓了才吃飯,有一次我差點餓死,吃飯這個事成了我童年的陰影。我不太喜歡一些詩歌青年和詩歌老年,他們寫了一輩子詩,總說我是在寫我的感覺啊,他總覺得振振有詞的,我一般不和這種人說話,我關鍵是,要探討,要追問,要搞清楚,我為什么要寫詩?我原來想成為哲學家,但后來我發現詩人比哲學家能獲得更多,所以我覺得還是詩人好。
說到廢話,在1986年我和我朋友們一起創辦了非非主義,那時我很年輕,和在座的同學差不多大,22、23歲左右,那時候非非形成了三派,一派是周倫佑,他是主編,也是故事派。第二派是藍馬,他是我們的理論家,第三派是我,我是里面的第一詩人,我跟他們有共識也有差異,周倫佑是后現代主義,藍馬是前文化哲學,而我是以詩為主體的語言派,我那個時候的主體的語言觀念就是建立在語言哲學這個上面。那時候我還小,也不可能建立什么,但非非那時候我們三人達成的共識,逃離文化逃離價值逃離意義,那種逃離價值的主體是周倫佑,逃離文化的主體是藍馬,逃離意義的主體代表是我。到后面非非分手,我與何小竹、吉木狼格、小安等在一起,首要觀念就是超越語義,我就想語義這個東西把我們束縛得太緊了,像繩索一樣,我們為什么不能掙脫它呢,就這個簡單的思考就構成了我們的第二次批判。我整個90年代底就考慮得這個問題,搞了個5000言,最后一句話,說出了我對詩歌最終的領悟:詩啊,言之無物。言之無物在過去的大家的腦子里面,都是受批判的,你寫得什么嘛,言之無物,這卻是我寫作追求的,最高境界。到了新世紀,隨著我理論的成熟與文字的成熟,終于到了有了互聯網,通過互聯網不斷地碰撞交流爭吵,從大家的抬愛與認同下,有一群人形成了橡皮,也就是橡皮寫作,從廢話里面,過往的15年里,出了很多新聞事件。在中國這個當代生活里面,除了沒有余秀華大,但趙麗華事件、烏青事件、羊羔體事件也超出了一般的社會事件,我非常喜歡北魏提出的禍害這個詞。
楊四平:我來說一下這個禍害,應該是糾正了詩歌的一些方面,以往的詩歌過多關注了詩歌的所指,把詩言志與詩無物連起來,這個無物怎么連呢,楊黎提出來這個廢話。我還說一下,楊黎剛才說,為什么我們要寫詩?在宋代,寫詩可以考公務員,入仕途,今天不行。而且在社交場合,也是很流行的娛樂。到了互聯網時代,好像只有一種,就是自己和自己對話。所以我們今天的詩歌,它的公共性,在慢慢得弱化。
北魏:楊黎剛才很謙虛,他說他是中師,我說中師那是中學老師——開個玩笑啊。他是謙虛了,一代宗師可以和大師相類,可以這么講。之前有很多人問《世界3》是什么意思,這個問題我答了無數遍,今天借這個機會我再答一遍,答之前我想說我的一個觀點,就是不要太注重比如意義啊意思啊這些東西,你就把它看作一個名字,它其實就是一個名字嘛。《世界3》是什么意思不重要,《世界3》在做什么比它名字重要一些。我們知道物質世界是第一世界,精神世界是第二世界,世界3就是傳說的靈魂世界。我理解靈魂世界和世俗世界,可能就隔了一張紙,你敲一敲,可能它就破了,世界3的原意在這,就這么多,你也不要多想,多想還是那么多。我剛才說這次這個大師獎的大師,他必須是要有理論的,否則只能是大詩人,不是大師。我剛才還說要想成為大師,必須要有理論,而且這個理論是要惠及他人的,或者你禍害他人也行,一群一群的惠及或禍害。前不久我在“安徽當代口語詩歌大展”里說到神奇,就是那個化腐朽為神奇,實際上,我非常反對這樣的,它好像又在跟你說“人定勝天”這樣的胡話,杜甫也說過“語不驚人死不休”這樣的話,天天在那里想神奇,緊皺眉頭,一定非要搞出雷聲出來,為什么不能像平時那樣么?中國人對化腐朽為神奇很推崇,這個很不好,也是很功利的。說不上壞,但也好不到哪里去。作為一個神奇的東西,是很功利的。你自己神奇了,你原來的也就沒有了。曹寇一篇重讀讀紅樓的文章里,說盛世和衰世,盛世是制度化的固化的,也是腐朽的,盛世產生不了大詩人,他說得頭頭是道,他說盛世里面可以產生小說家。我說化腐朽為神奇,不如說倒過來說——“化神奇為腐朽”,因為腐朽是自然的、日常的、人人的、也是生命的,如果有什么東西是永恒的,這永恒的里面一定有腐朽,而神奇一定不在里面。
下面我談談平面寫作。平面寫作是我在安徽當代口語詩歌大展提出的。2000年后,中國詩歌發生了很大的變化。許多詩一寫出來就成了舊詩,無效的詩。回過頭來,我看了我八十年代寫的東西,那時候沒有口語這個概念,我習慣叫脫離書寫腔調的東西叫“口頭詩”。84年前我寫了不少這樣的“口頭詩”,很多人都說不是詩。那個時期寫詩也很瘋狂,之后下海,上岸,再下海再上岸,最后還是覺得詩好玩些。詩這個東西是你自己逗自己玩,沒有別的說道。說寫詩為玩詩不好聽,其實就是自己和自己玩,玩到最后你非常的孤獨你又非常的自豪,這孤獨和自豪都是你要接受的,這沒有什么好說的,這個里面有很多矛盾的東西,人生也不過這樣吧。楊黎的廢話寫作,非常有刺激。口語寫作,簡單的講就是說話,往復雜方面講還是說話。你怎么說的你就怎么寫下來,就行了,因為這個語言是你自自然然的,是你還沒有作態之前本來的樣子,而詩本身就是要這個本來的樣子,這樣你的自在性自生性都有了,你的詩不會差到哪里去。剛才云虎兄說楊黎你的東西看不見技術,實際上技術被楊黎隱藏了。平面寫作就在這么大的背景下產生的,當然我們還在探索的路上。我就提出了五去四化,第一個就是去語義,我認為詩歌的語義,即那個所指,是背離一首詩的產生的。語義往往把一首正在寫的詩,引到了詩的反面。這就是為什么要“去”它的原因。楊黎說的廢話,我認為也是在這個層面上說的。廢話就是廢除你語言里面那些所謂“有用的東西”,剩下的那些看上去“無用的東西”,別人認為沒用的,那其實就是詩。第二個去語感,很多人反對,這樣說吧,完全在一首里去掉語感是不可能的,只能降低它對一首詩生成的左右,為什么這樣講?因為語感直接導致慣性寫作,一旦一個人在慣性寫作,基本上就可以確定他的寫作正在無效。第三個去意識,也有不少人反對,有人一寫詩就正襟危坐,提醒自己是在寫詩,那意思是你別打擾我,我非常反對這個意識。寫詩的時候,完全可以有人打擾,一打擾,你也完全可以把這個打擾寫到詩里。接下來說去經驗,好像詩歌是經驗的,經驗是詞語詞匯不斷累加,一個人經驗多了,反而是束縛,好像詩沒有經驗詩就輕,你想過沒有,你的經驗很多都是別人的,我不反對在一首里寫你的經驗,我反對的是你把別人的當自己的。第五個是去深刻,這個就說到柏樺,他寫的詩注重互文性,后面有許多注釋,你搞不清他寫詩是為了注釋,還是注釋是為了詩,用知識寫詩也可以,就像我們吃糖果,糖果在嘴里,在化,你才感覺到甜,當化到你的肚子里的時候,這個時候,知識不只是知識,可能是知識化成別的東西了。這個是五去,五去后是四化,因為時間有限,我說一下,讓更多的時間留給楊黎先生。“四化”第一個客體化;第二個表象化,表象即本質,我們今后有闡釋性文章;第三個是流水化;還有一個是關聯化,世界是關聯的,人也是關聯的,詩人袁魁對關聯化寫了篇關聯化初探,寫得很好,大家可以看一看。我對平面寫作就說到這。
楊四平:讓我們交給時間,不管是平面化還是廢話。就像李白杜甫,其實當時最出名的是白居易,但現在沒誰說白居易在李白杜甫之上。我們說:明月松間照,清泉石上流。我們的廢話和平面,可能就像這大音希聲大象無形。作為詩人來說,回到這里,怎么呈現,這個詩歌里面有個時間和結構的問題。面對當下互聯網復雜的環境,我們日常怎么處理這種時間和結構呢,一種非常張揚的,還一種是非常內斂的,時間變得非常緩慢,所以我們關注流水這個問題。
北魏:下面我們請楊黎說說吧。
楊黎:還是大家一起說吧,我們一起交流。
北魏:大家舉手提問吧,楊黎到蕪湖來是第一次,我是在蕪湖,你們隨時可以和我聯系,現在主要是向楊黎提問,向大師學習的一個好的機會。
陳云虎:剛才我關注到一個細節,剛才北魏兄說掃二維碼,我在找沒找到,我發現楊黎也在找,我覺得這個詩就像二維碼一樣,很有意思。
同學:能否就具體的文本來探討廢話理論呢?
楊黎:我和北魏先生的平面理論不太一樣的是,我更少的不太有具體的有關的設計,有次我被朋友問,什么叫廢話詩?我說第一我不知道什么是廢話詩;第二我沒提出過這三個字,我說得是:詩就是廢話。我這個詩不是指我的詩,也不是指誰的詩,我是指整體的詩。我是從這個本質上面去描述它,所以我沒有說的具體的例子。如果說具體的,我就舉我自己的,我1988年在詩歌報得獎的那首《撒哈拉沙漠上的三張紙牌》,這三十年被人解讀無數次。沒有人說出我到底說得是什么。我想說的就在這首詩上,就是在撒哈拉沙漠上,我看見了三張紙牌,一張新一點,一張舊一點,一張打開的,這個什么意思呢?我說不知道,因為我沒想過它有什么意思。我,你覺得我是什么意思嘛。我只是寫了這樣一件事,也許它不經意地引發了你們另外的想象、追問一樣。
胡偉偉:我想問下楊黎先生,我們國家是有審查制度的,在這種情況下,詩人如何處理現實文本呢,前蘇聯有阿赫瑪托娃、索爾仁尼琴、帕斯捷爾納克等,為什么中國和前蘇聯環境很相似,卻沒有出現這些類似的詩人呢?
楊黎:我對你提到的三個詩人,沒有像你想象的那么喜歡他。我認為在我周圍,在當代至少有20個詩人比他們優秀。他們僅僅是名氣沒有他們大,如此而已哦,楊教授提到杜甫活著的時候沒多大名氣,所以說你現在用他們有諾貝爾背景的人來說這個問題,不能讓我信服。我基本上也不敢妄加評論,而現實影響發表,不影響寫作。我的著名詩篇《打炮》也沒發表過,但它在網絡上很多,我想,就是孔夫子刪了許多好詩,刪是一個理想主義者和專制主義者共同擁有的愛好,而我既不是理想主義者也不是專制主義者。所以限制僅影響發表,不影響寫作。
楊四平:《廢都》也曾是禁書,但現在被解禁了,它并不是賈平凹寫的最好的作品。一些公共事件會讓作品受到更多關注。蘇聯一個是政治原因一個是宗教原因,造成了這些詩人的苦難。
胡偉偉:德國當代漢學家顧彬說過,中國當代的漢語是受過污染的漢語。德國納粹之后許多作家又開始重新學習語言進行寫作,請問楊黎先生,顧彬先生說的這個觀點你怎么看。
楊黎:我都不知道顧彬是用德語說的還是用漢語說的。實際上他說的是外行人的話。他實際上是不懂這個,我對這種漢學家,實際上是有看法的。他不像我們那些中國的精英,因為學外語的都是精英,中國以前學外國人學西方人,都是一些聰明人,但是漢學家么,我很早之前就拒絕過和漢學家進行交流。我認為他們是精英群里面,那些不容易找工作的,學那些冷門,他好找工作,他并不是所謂的文學家寫作者,甚至不是對文學有愛好的學文的人,我覺得有很多這些見過的漢學家,我探討他們的前世今生,你怎么學漢語呢,你會發現,他們是不懂的。寫作都是要出淤泥而不染么,語言的污染,能污染到什么呢?語言的污染最大的污染在這里,比如你們都崇拜真而瞧不起假,這是語言價值提示的重要性,所謂的廢話,就是要廢除語言的意義,要廢除語言的價值批判。語言的價值批判,也是對人類最大的束縛,從這個角度去看,我們談價值。我認為文革帶給我的,恰恰是語言的解放,沒有帶給我的污染。顧彬這個人我也很知道,1992年他是吹捧我的,后來他認識了歐陽江河,成了他的粉絲,鞍前馬后的,成了反對我的,如此而已,沒有水平,他說的一些話,中國小說都怎么怎么樣,他說這個人不懂外語,就寫不好小說,這個話好搞笑的嘛,他至少懂得兩門外語嘛,他連一句話都說不好,曹雪芹呢,他普通話都不懂,不也寫出了《紅樓夢》。所以說他這個理論是非常沒有學術水平的。
楊四平:這個里面有個背景,這些漢學家有個歐美的背景,認為我們中國是個第三世界國家,他們是排斥這個意識形態,是有政治的眼光的批判的。還是封建時代的思維,所以講出這個話。
楊黎:他這個漢學家,能讀懂中國當代詩歌嗎?能讀懂歐陽江河的嗎?我都持懷疑。他不是對藝術品對作品有判斷的。他看不懂,很麻煩。他那個懂,是什么呢?
北魏:前段時間我還與牧野說到顧彬,他說他去聽了顧彬的一個講座,聽到一半就聽不下去了。我說顧彬對中國詩人和詩歌了解很有限,他甚至還停留在上世紀九十年代之前,有些話看上去很嚇人,其實他的很多觀點都是想當然的,也就是說是很有問題的,他的很多比較也是靜態的。好了,今天我們不是在開顧彬的討論會。我想說翻譯同一首詩,一個詩人的翻譯和一個普通翻譯人的翻譯,是完全不同的,翻譯差距是很大的。好,繼續。
同學:請問楊黎老師如何看待詩壇里面的圈子與互相吹捧。
楊黎:我覺得有個圈子挺好的,為什么呢?互相吹捧是個好事,人與人之間的鼓勵,是非常好的風氣。氣味相投的,是共同成長的,如果經常吵架的,我個人是不喜歡的,我建議找氣味相投,你漂亮我聰明,很好的,我喜歡朋友圈勝過喜歡微博。微博是這個世界,這個世界對我沒多少關系,我不是個陰謀家,不是想稱王稱霸的人,那么我要那么大的世界干嘛呢,我就喜歡一個小小的朋友圈,它使我活得自在,安逸,舒服,挺好的。
同學:請問楊黎老師,中國詩歌講究美學,尤其古典詩歌,包括戴望舒和張棗,我想問下口語詩歌它有美學嗎?如果有它體現在哪些方面呢?
楊黎:我是一個不使用口語詩這個詞的人,在這點我與北魏先生有不同看法,我認為沒有口語詩,如果這是口語,那什么不是口語,難道僅僅是它寫在紙上的就不是口語嗎就是書面語嗎,還是僅僅因為它的內涵,那么這個內涵是什么呢?我認為這是一個中國當代詩歌的誤區。什么叫做現代漢語?如果給口語一個表述,它是什么呢?就是現代漢語。剛才提到的戴望舒和張棗,一個是膚淺的一個是假裝高深的。實際上不是這么簡單。美,都在追求美,但美與美不一樣。魯迅先生說過:焦大未必愛林妹妹。在我心目中,戴望舒的詩真的不美,在美學層面上,如果有一等美二等美三等美,有點美很美非常美美得一塌糊涂,那戴望舒僅僅是小美,通過節奏的起伏形成的小美,在我們內行來看,他的美比不上張棗,但張棗的美也是很差的。這個也是觀念了。追求美是美的天然的本性的追求,但你以為在口語中爆粗口是美或什么是美,那我告訴你那不一定是美,那可能是別人告訴你的,是你被教育的結果。你是在這個教育里面成長起來的,而不是天生的。
同學:請問楊黎先生,你的廢話理論下,你如何評價誰寫得好誰寫得不好呢。
楊黎:我曾有句話說:廢話面前人人平等。實質上,沒有好和壞的標準,廢話里面寫的不好的詩,可能在別人眼里是好的詩。你認為好的詩對我可能是不好的詩,所以這個世界沒有好詩與壞詩這個主體。
同學:那么沒有價值的東西就會被淘汰掉,人們認為不美的東西。
楊黎:戴望舒恰恰相反,孔子編詩的時候不是按那個標準,他是按他的溫柔敦厚,仁義禮智信的價值標準來編詩,我一直很絕望的是,我想看到300首以外的詩。但是你所標榜的淘汰制度非常殘酷地把那2000多首詩給刪除了,我不知道誰給他的權利,但我現在看不見了,中國就是有這個愛好,這個愛好就成了他們要把他們認為壞的敏感詩給遮蔽了,但是結果是什么,被刪除的2000多首詩,是真的寫得不好嗎?
楊四平:所以要有考古,發掘出被埋藏在故紙堆里的好東西,好詩。都是一樣的,讓它們重見天日。
袁魁:我想問下楊黎老師的創作習慣,我看見你在中午吃飯的時候,隨手就寫出三首詩,我想知道這種創作習慣是你一開始就有的還是慢慢摸索出來的。
楊黎:這種是有手機可以寫作之后就有的,和以前正兒八經趴在寫字臺上是不一樣的,腔調口氣都變了,挺好的,技術革命,我相信用鋼筆寫出來的和用毛筆寫出來的肯定不一樣。用打字機打出來的和手機寫出來的,肯定不一樣。它的自然屬性越來越豐富。就寫長篇來說,還是需要時間的,像工作一樣,我個人還是喜歡像工作一樣的,哪怕可以很隨意地寫。
阿爾:我注意到楊黎老師的詩,有出神狀態。我想知道,是人在寫詩,還是神在寫詩?
楊黎:我意識很清醒地是,我在寫作。可能有人有這種能力,超能力。我認為我是沒有出神的能力。有的人是有點虛構。
北魏:噢,我來介紹一下,阿爾,來自安徽宿州,詩人,平面寫作核心成員。陳云虎,江蘇揚州人,也是我們平面寫作核心成員。汪倩,安慶詩人,也是安師大畢業的。坐在邊上的許光,宿州人,我們平面寫作核心成員。胡偉偉,在蕪湖,經常有稀奇古怪的想法。詩也很尖銳。坐在邊上的是風兒,盧麗娟,安徽著名詩人,蕪湖詩院院長,《世界3》編輯部主任,平面寫作核心成員,最近半年來詩風大變,正在往平面化發展。再坐在邊上的是袁魁,著名詩人,楊黎說他是平面虎將。楊黎老師每天三四首,他現在每天一兩首,正準備寫五六首,他也是我們《世界3》副主編。我再介紹,楚風,蕪湖隱藏的詩人,很內斂,東西非常淡,也是我們平面寫作核心成員。平面寫作從發起到現在還不到一個月,成員已發展到50多人。攝影的叫若塵,風兒的女兒,非常優秀,每次活動她都義務的攝影主持。好,大家繼續提問。
同學:請問楊黎老師,你記得你寫的第一首詩嗎?寫詩有沒有一些技巧,可以鍛煉出來。
北魏:我想說一下,我之前說過詩歌無技巧,但在達到這個無技巧之前,你必須要不斷地練習,到一定程度,你要漸漸忘掉與消解掉這些技巧,看似無技巧,實際上處處都是有技巧的。它有很多技巧在里面,你一句話兩句話說不清楚。你說的第一首詩,實際上,我是記不住我寫的第一首詩,但我記得我寫得很滿意的第一首詩,任何詩人說,這是我的第一首詩,你不要相信啊,這可能是他寫的第一百首詩,都不止。
楊黎:這個絕對了,我真的記得我寫得第一首詩,而且寫得也不好,只是我不告訴你而已哦。現代詩的第一首我還是記得的。北魏老師說得高深了,我說怎么寫一首詩,我有一句名言,古人是沒有這個焦慮,古人很簡單的,他們偷懶,把文章分成韻和散。我們現在搞復雜了,什么叫詩呢?困惑就出來了,我教你一個和古人一樣偷懶的方法,我發明的一個:分行就是詩。分行是對人的一個提示,我告訴你這就是詩,而不是文章不是通知不是書信不是應用文。我說我請你吃飯,如果我是分行的,那你不要相信,我是在寫詩,如果你真的跑來了,呵呵。如果我發你個短信,你可以來。這個分行的,就是詩。記住。
同學:請問老師,現在的寫作是不是有化丑為美呢,就是審丑。
北魏:平面寫作還是關注“真”的,這個“真”不是真理的真,是事物本來樣子的。這個事物本來樣子它可能是美的,它也可能不是美的,這除了美是變化著的,還因為“真”很多時候是“看不見”的,這個被我們自己遮蔽的“看不見”,可能是人有什么想法的一種動因,寫詩可能就是這個動因之一。美有很多公共性,附加在上面的東西,對我們的寫作會產生影響。詩歌與美關系,和詩歌與真的關系一樣重要。實際上人性美和丑很多是在道德層面講的,與詩關系不大。我不贊成“天問宣言”里說的,它說的大概意思是,一個壞人是寫不出好詩的。詩史早就證明,“壞人”在當壞人的時候,詩寫的比“好人”要好的例子很多,不必我在這里得罪故人。
楊黎:其實這點我和北魏有不同看法,我是喜歡美的,顏值決定一切。我不強調不喜歡真,真是什么?假又是什么嘛?為什么真的就比假的好呢?為什么假的就比真的差呢?為什么真就值得驕傲呢。我有時間和北魏交流一下。美,因為它是絕對的,所以它才是有層次的,這個層次是逐漸靠近的,由簡單到復雜,再由復雜到簡單,這個你應該是有學過的吧。
北魏:今天這個交流會非常成功,講了很多,這里面很多東西你馬上能感悟到,還有許多在今后寫作中,你靈光一閃,也會突然感受到。謝謝大家,謝謝同學們,謝謝詩人楊黎。最后一項,簽名售書合影,楊黎與束曉靜的《寫一年》,謝謝大家。
20171118
(本文為整場對話精選,非全錄,若有錯漏,歡迎指正,謝謝理解!)

蕪湖詩院合影(前排左一 北魏 楊黎 陳云虎 楚風 ;后排左一 風兒 袁魁 許光 阿爾 (攝影:若塵、林黎)

攝影:風兒、若塵、林黎
錄音:胡偉偉
錄音文字整理:袁魁
審閱:北魏、楊黎


我們不定義先鋒詩歌
我們只展示先鋒詩歌文本
主編:北魏
常務副主編:袁魁
副主編:丑石、趙東、沙馬、阿爾、梁震
編輯部主任:風兒
設計總監:上谷阿凡
定期推出日:每周二
投稿郵箱:shijiesan618@163.com
https://mp.weixin.qq.com/s?__biz=MzUxNjEyMTYzMQ==&mid=2247484210&idx=1&sn=b0409dbbb5868044f536a452f3f1db79&chksm=f9ad7642cedaff547c3417ef30e84babd21ee29b39f58c3ee4ae56304cc3de4bf5acc8c638dc&mpshare=1&scene=1&srcid=1127LPOdMhCmA4KTMYBuG94R&pass_ticket=bKlxM58%2FIKLqDwtJITtKYd1fa9vciq%2BNe7jzyJCPVZBzHsymjO3N0ikoM%2FzUi%2BlT#rd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