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中的世界
——《光年》詩劇會報導

“世界中的世界”《光年》詩劇會于2017年11月25日在北京虞社演藝空間舉行,同時進行的活動還有良閱城市書房授牌典禮。出席《光年》詩劇會的嘉賓有《光年》主編戴濰娜、《光年》出品人劉明清,翻譯家顧彬、王家新、趙振江,詩人周瓚、朵漁、冷霜、陳家坪、蔣一談、王東東、葉美。2015年中國成語大會總冠軍、詩人、《詩刊》編輯彭敏主持了這場詩劇會。

詩人周瓚首先上臺朗誦了兩首詩,一首是自己的作品,一首是加拿大詩人瑪格麗特•阿特伍德的譯作。讀者在她低沉而略帶憂傷的嗓音中,總能想起虛虛實實的往事,也能夠從中得到一些撫慰。主持人彭敏認為,在中國當代文學史上,民間刊物一直取得了很多成就。有想法的詩人遏制不住沖動,從上個世紀八十年代、九十年代以來,很多著名的民間詩刊一直陪伴著中國詩歌成長,比官方詩歌刊物對于當代詩歌的發展,助力和作用更加強烈。而詩人周瓚創辦的《翼》詩刊也發揮了這樣的作用。

翻譯家趙振江朗誦了詩人加西亞•洛爾卡和曼努埃爾•岡薩萊斯•普拉達的詩作。在談自己對詩歌翻譯的體會和看法時,趙振江認為逐字逐行地翻譯詩歌,肯定是行不通的。就詩歌翻譯而言,他同意墨西哥詩人帕斯的觀點:“翻譯與創作是孿生行為”,區別在于“詩人開始寫作時,不知道自己的詩會是什么樣子;而譯者在翻譯時,已經知道他的詩就應該是眼前那首詩的再現。”在詩歌翻譯中,詩歌翻譯要像創作,而詩歌創作不要像翻譯。

顧彬上場時,主持人彭敏稱他為中國詩歌的知音。據顧彬透露,他于1943年第一次來到北京,那是文革時代。他很喜歡去臥佛寺,并在那兒寫了很多很多詩。他為觀眾朗誦了其中的一首詩作《在櫻花谷》。

今年10月份,王家新與顧彬在歐洲有一個朗誦之旅,因為他的德文詩選和克羅地亞文詩集的出版。他為觀眾朗誦了他在飛機上寫的一首詩《飛越阿爾卑斯》。最令人興奮的是,王家新為觀眾朗誦了一首茨維塔耶娃的《約會》,這是他1993年在倫敦時候的譯作。這首詩的翻譯對他很重要,是他第一次與茨維塔耶娃真正意義上的相遇。“愛就是忠實于相遇”,因此,他覺得自己必須要把它翻譯出來。

《光年》出品人劉明清早年寫詩,后來以詩人的情懷出版了各種詩歌類的圖書和學術書籍。《光年》創刊號的題目叫“詩歌共和國”。劉明清為觀眾朗誦了其中一首巴勒斯坦詩人馬哈茂德•達爾維什的作品《在這塊土地上》。

葉美新近要出版一本詩集《塞壬史》,她為觀眾朗誦了一首同題詩。葉美與《光年》有一種很深的緣分,編輯第二期時,她參與到了編輯工作中。她一直被《光年》所吸引。就像時尚教母戴淮娜一樣,這本雜志很先鋒,很時尚。封面、欄目、版式,都是她心目中一本成功翻譯雜志的標準。本次活動主題“世界中的世界”,出自葉美即將出版的譯著書名,作者是英國詩人史蒂芬•斯彭德。所謂世界中的世界,意味著我們要有一種面向世界的眼光。

彭敏稱冷霜是一位謙謙君子,對他們一批當時還在上學的80后詩人有非常多的幫助。冷霜為觀眾朗誦了一首自己的詩,和一首翻譯的詩。在詩歌寫作的說明中,冷霜敏銳地談到了燭火的囑托。翻譯也如同燭火的傳遞和應答。多一些翻譯,就會少一些黑暗。

對于活動海報中《世界中的世界》,朵漁發現排版很有趣味:世中世,界的界,橫批:光年詩劇會。這種發現是誠實的,但這種誠實同時也會帶來一種意外的幽默。

當戴濰娜上場時,彭敏稱她為“光年之母”,他形容《光年》是一本性感的雜志。因為性感,戴濰娜想到了一個現象,那就是維多利亞時期,那些貴族們用一整套從頭到腳的穿衣方式來對抗當時剛剛興起的平民趣味。某種意義上,寫詩可能跟穿衣服是一樣的。一群思想馬戲團里的演員,每天早上為創作新的詩行而醒來,為一個靈敏而杰出的句子奮斗終身。這種奮斗,跟鏡子前的奮斗一樣,都是試圖用一種精致的節奏撼動粗鄙的現實。享受語言的人,能享受更深層的親密關系。詩劇會活動的現場也是非常性感的,戴濰娜希望在此刻,所有的朋友跟我們的詩人一起形成了一個從審美到智識到情感的共同體,性感共同體。

陳家坪在演講中表達了,《光年》是一本非常重要的雜志,希望能在一個公共的空間里讓詩歌參與社會文化批評與對話。《光年》雜志有一種傳播新文化新觀念的責任和使命,這種使命也來自于五四時期,整個西方文化參與到中國進入現代文明社會的建構。結合自己的詩歌創作經驗,陳家坪談到了詩人巴列霍對他人生發展的影響,以及翻譯對他思想成長的影響。最近他拍攝完成了一部紀錄片《孤兒》,里面充滿了詩性邏輯。基于自身的生存背景,他為觀眾朗誦了兩首詩《街燈》《父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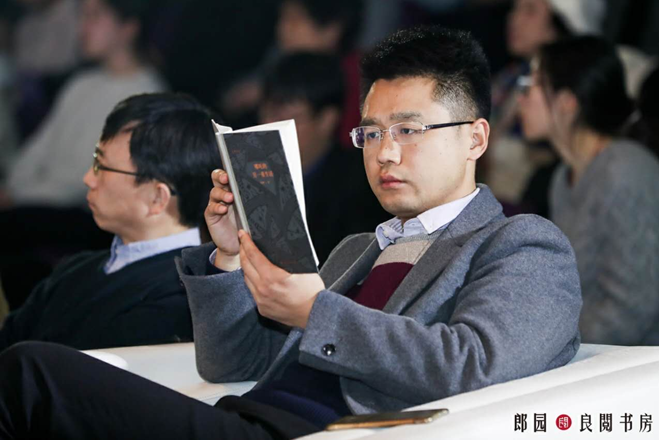
在80后高學歷化、學者化的詩人當中,王東東是出道特別早,如今依然屹立不倒的詩人。他以上課的方式給觀眾講解了他的詩歌寫作來源,也給觀眾介紹并朗誦了一首英語詩人艾德文繆亞的詩。對于現代詩精妙的意象體驗,王東東與觀眾做了一個最好的分享。

通過《光年》這個名字,蔣一談想到了時間這個概念。“世界中的世界”,世界是佛教用語,大家也都知道,世是時間,界是空間,世界即時空。作為人類,我們在地球上生存,其實每一個人都是逗留的人,但是有一句詩性的話是這么說的:我們在這個世界上逗留的時間越長,我們就會被剝奪得越多,我們想逃離,但只有一樣工具和認識能成為我們的擺渡人,能把我們抽離開這個荒誕的世界,這個工具和認識就是時間。太陽的光抵達地球的時間為八分鐘,人類只有這八分鐘的時間,但是在這八分鐘里,我們并不知情太陽已經毀滅。這是一個荒誕的想象,荒誕有一個孩子,它的名字叫憂郁。在我們這個時代,憂郁的人正越來越多。最后,蔣一談為觀眾朗誦了法國詩人勒內▪夏爾的一首詩《我入住痛苦》。

中國自白話文運動以來,漢語的更新在多大程度上借助了翻譯西方譯的力量?我們如何在新世紀創辦一本既在內容上追求思想先鋒,又在面貌上尋求性感,時尚的翻譯詩刊?如何在人人淪為“低端人口”的緊迫現實面前再次復活世界文學的整體話語?面對這些思考,以“世界中的世界”為主題的《光年》詩劇會,邀請嘉賓和前來聆聽的觀眾產生了相應的互動與探討。
來源:光年 詩劇會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