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啟代在母親節(jié)周永詩集
《吶喊》座談會上的發(fā)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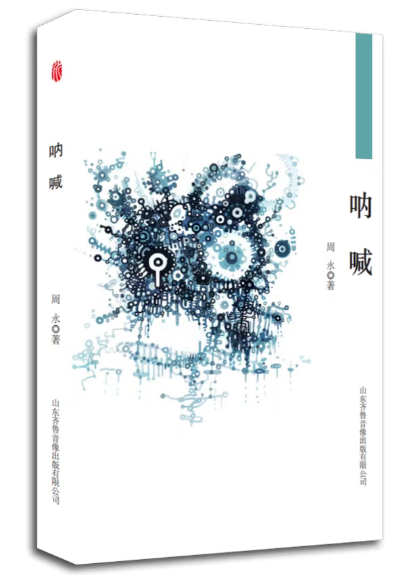
各位師友好,今天是母親節(jié),首先向天下的母親致敬。我們都是母親的孩子,詩歌是我們的孩子,因此,今天也是我們的節(jié)日。從另一個角度說,詩歌誕生在詩人的手上,但詩人與詩歌不是輩分的差異,而是母(父)子同心的生命同體、精魂同源,從這個意義上講,不帶有詩人情感和精神基因與密碼的詩歌對于人類是沒有真正意義的。
今天很高興見到老朋友,又認(rèn)識幾位新朋友。在坐的耿建華先生、李炳峰先生、趙林云先生、宋俊忠先生等剛剛參加了第四屆長河文學(xué)獎的系列研討或頒獎晚會,其中周永和散皮的詩集都有專題研討,高連剛、楊福成、路小曼在會前會中會后都參與了很多工作,活動是各位師友兄弟姐妹共同協(xié)助的結(jié)果,在此一并表示感謝。
研討會之后召開分享會,角度不一樣,實(shí)質(zhì)沒有變,都是圍繞作品進(jìn)行剖析解讀,批評中有分享,分享中一樣有批評。周永先生說趁熱打鐵,所以今天我們再進(jìn)行一次樣本分析和分享,爭取經(jīng)受不斷淬火之后能發(fā)現(xiàn)鋼、鍛造出鋼性的詩句和詩篇。
周永先生的這些詩我都熟悉,包括每一首詩的寫作背景和過程。作為好朋友,我見證了他從最初的《詩海揚(yáng)帆》到《走過雨巷》,再到這本《吶喊》經(jīng)歷的過程。可以說,從充滿青春暢想的詩歌愛好者到略帶浪漫氣息和滿滿鮮花掌聲的抒情歌者走到今天充滿憂思和深沉的詩性書寫,周永走過了創(chuàng)作的三個階段。《吶喊》那首詩出來大概是2016年一個暮春的午后,那天他突然發(fā)燒,我正在馬武寨山的巖石上靜看山下喧囂的人間,從手機(jī)上讀到他發(fā)來的這首詩,我很為他高興,當(dāng)時就激動地回復(fù)他,告知他終于邁進(jìn)了詩的門檻。這個轉(zhuǎn)變并非突然,從觀念的逐步轉(zhuǎn)變開始,他大概經(jīng)歷了已經(jīng)至少一年多的自我煎熬。否定一個舊我并不容易,走出一個新我一樣難。有了這第一步,他應(yīng)當(dāng)有著相當(dāng)長時間的寫作噴發(fā)期了。這七八年來,收集在這本詩集里的作品絕大多數(shù)都是這一階段寫出的。《吶喊》是標(biāo)志性的,《我的影子活得比我好》是標(biāo)桿性的。這本詩集是他代表他目前詩歌創(chuàng)作水平的一部書,反復(fù)研討和分享,我想周永是想誠懇地聽聽他們的意見,受些激勵,領(lǐng)悟些點(diǎn)播,注意些問題。他是想明年完全退休后決心寫出更好的東西。這種雄心和抱負(fù),我是贊賞和支持的。
下面就說一下我對這本《吶喊》的粗淺看法,別人在研討會說過的我就不重復(fù)了。我覺得周永的創(chuàng)作是在三個維度展開的,這決定了他的題材走向——盡管我在詩學(xué)思考上非常謹(jǐn)慎使用這個概念,因?yàn)樗菀桩a(chǎn)生歧義和被誤讀。一是作為生活之子的周永,他積極地行駛著而不是扮演著教師、兒子、丈夫、父親、兄弟、朋友等不同的角色,沉入既深,體味也就真切,他寫父母的詩有十首,特別悼念母親的詩,讀之讓人心痛,這一點(diǎn)與那些終日生活在生活軌道之外的詩人不同;二是作為自然之子的周永,他用詩筆忠實(shí)地記錄著自己的生命足跡,從韓國首爾、到泰山、黃河、大明湖、馬套、泗水之濱、聊齋城里、兗州礦業(yè)等等,他都有詩章出來,事實(shí)上,自然之子的詩人是帶著赤子之心的純凈和文化之心的體驗(yàn)來締造詩歌的建筑,因此,這些帶有紀(jì)游特征的詩歌實(shí)際上是自然其外文化其內(nèi),是文化之子在大自然面前的傾情表露;三是作為精神之子的周永,那首《吶喊》奠定了他這本詩集《吶喊》的精神底色,他看生活和社會的目光開始有了審視、批判的銳利,說到底,詩歌喚醒了他作為一個現(xiàn)代詩人和知識分子的良知和正義感,逐漸由傳統(tǒng)文化中的仁愛之心升華為現(xiàn)代文明理念的悲憫情懷。從他開篇的《漢字》到最后的《書法》短詩十六首,貫穿著有二十二首涉及到書法的詩歌,都寄寓著他對文化、文明、社會現(xiàn)實(shí)的思考和叩問,這些詩他寫的比較放得開、寫作時狀態(tài)也比較好。總而言之,這三個維度的展開體現(xiàn)了周永詩歌由小到大、由外及里、由實(shí)及虛的探索軌跡和美學(xué)走向,沿著這樣的路徑走,不斷超越自己和自己設(shè)立的目標(biāo),才能寫得越來越好。
也就是說我們對詩集《吶喊》連續(xù)進(jìn)行研討和分享,是為了助力周永不斷突圍,找出優(yōu)點(diǎn)和不足,助力他不斷趨向更好更高的寫作境界,并不是說這本詩集已經(jīng)多么了不得——這本書對于他個人詩歌創(chuàng)作而言的確是這樣的,但我相信周永自己也會把它放到整個漢語新詩的創(chuàng)作大背景上來考察。我也講三條:一是用語偶有生澀,不能整體上給人渾然一體的感覺,這種生澀不是來自詞語和詩意的張力本身,而是沒有化透;二是蛻變的痕跡明顯,有人說桑恒昌先生和我的影子都有,這很難免,作為桑先生的學(xué)生和我的朋友,周永研讀我們的詩歌文本要多得多,也用心得多——非常慚愧,我的詩歌也還缺點(diǎn)多多,這個我自己知道。試舉一例,他寫到“爹娘,給我一雙手/師傅,幫我長成兩支筆”很容易讓人想到桑先生的“我的肩上長出一桿槍/我的手上長出一支筆”。好在作為學(xué)生他長出了兩支筆,比老師的多了一支(笑)。從另一個側(cè)面看,這不是壞事,人的詩歌觀念和精神立場變化后,蛻變是一種新生;三是因?yàn)橹苡肋@些年擔(dān)任著勞動職業(yè)技術(shù)學(xué)院的很多繁重的工作,又在書法上用力專注,說實(shí)話,很多詩歌具有蹁躚之痕,不少急就章,有些是我當(dāng)時逼出來的。我曾經(jīng)說過,做詩人是生命中的意外,好詩也是寫作中的意外,有時**是能寫出好東西的。他已經(jīng)寫出了一些好詩,但要走得路還很長、提升的空間還很大,這也是我們分析他的創(chuàng)作得失的意義所在。

最后再與大家分享一下上個月在北京一個文化論壇的發(fā)言,那次發(fā)言的題目叫《詩人的修養(yǎng)》。我個人認(rèn)為詩人的修養(yǎng)問題是一個亟待提出并要十分重視的問題。我在發(fā)言最后曾強(qiáng)調(diào):做一個合格的新詩人,需要從三個方面考慮。一是詩人應(yīng)當(dāng)建立自己的歷史感,具有歷史意識。歷史感的缺失很容易與精致的利己思維合流,會讓我們毫無擔(dān)當(dāng),擔(dān)當(dāng)意識是使命意識的具體體現(xiàn)。歷史感來源于我們對人類苦難經(jīng)驗(yàn)的體察和對現(xiàn)實(shí)社會的關(guān)注。錢理群教授所說的“精致的冷漠和世故的清醒”不該成為我們現(xiàn)代人的集體人格面相。有人說我們?nèi)狈π叛觯诂F(xiàn)代社會,我們可以重新建立自己的信仰。西方詩人有自己的信仰,我們作為現(xiàn)代人應(yīng)當(dāng)在全人類的文明成果之上建立自己對藝術(shù)和人生的信仰,作為一個有著“士”的精神傳統(tǒng)和“道”的文化血脈的傳人,我們信仰的建立應(yīng)當(dāng)首先從建立歷史感切入。二是詩人應(yīng)當(dāng)培育自己的公共性自覺。真正的詩來源于生命的必須,作為現(xiàn)代詩人,寫作上要體現(xiàn)公共性——這是個性風(fēng)貌的基礎(chǔ),偉大的藝術(shù)一定有它們的共性,其中作為詩人的公共性自覺就是應(yīng)有的共性,藝術(shù)個性如果不包含那些人類共有的精神和美學(xué)成果,這樣的個性是沒有意義的。人格和詩格的統(tǒng)一,正是張清華教授所倡導(dǎo)的上帝的詩學(xué)的要義之所在。思想觀念的現(xiàn)代化說明我們是現(xiàn)代人,人格和詩格的合一才是我們作為詩人的證明。公民都有沉默的權(quán)力,詩人則有為公共事件發(fā)言的道德義務(wù)。三是詩人應(yīng)當(dāng)體現(xiàn)出專業(yè)品質(zhì)。在技術(shù)主義盛行的當(dāng)下,我所謂的專業(yè)品質(zhì)是建立在精神品格之上的詩人角色定位。這當(dāng)然包含對詩人藝術(shù)經(jīng)驗(yàn)和寫作技巧的要求,但我更強(qiáng)調(diào)精神的濃度和厚度,更看重是否有著歷史感和公共關(guān)懷的質(zhì)素,是否很好地將自我化入無我之境,體現(xiàn)出一種卓爾不群的藝術(shù)精神和自由意志,是否在更高的意義上熔鑄了良知、智慧與勇氣。具備了這樣的修養(yǎng),然后去生活、觀察、思考、寫作,這種存在和行為本身就是藝術(shù)使命之所系。
我就不展開說了,但愿不屬于畫蛇添足,因?yàn)檫@是周永——包括我們,都需面臨都在面臨的課題。正如周永的詩句所言,剩下的日子,還是讓筆說話吧!
啰嗦到此,謝謝大家!
2023年5月14日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quán)發(fā)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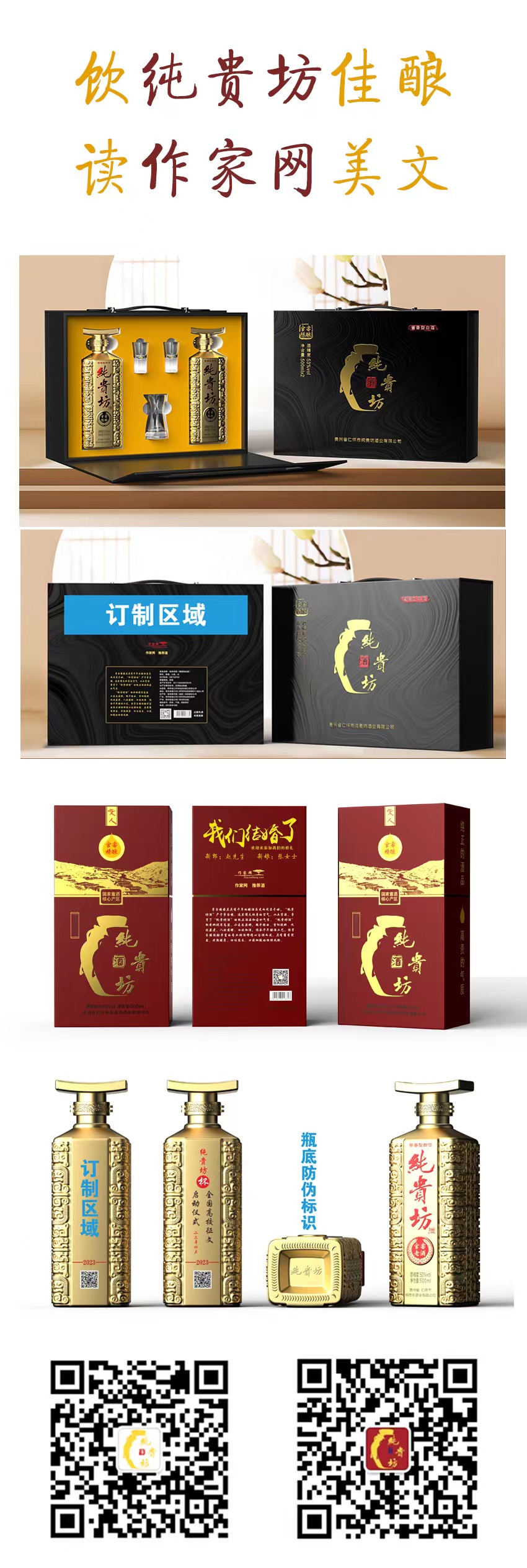


 純貴坊酒業(yè)
純貴坊酒業(y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