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從延安來》
延大 夢想開啟的地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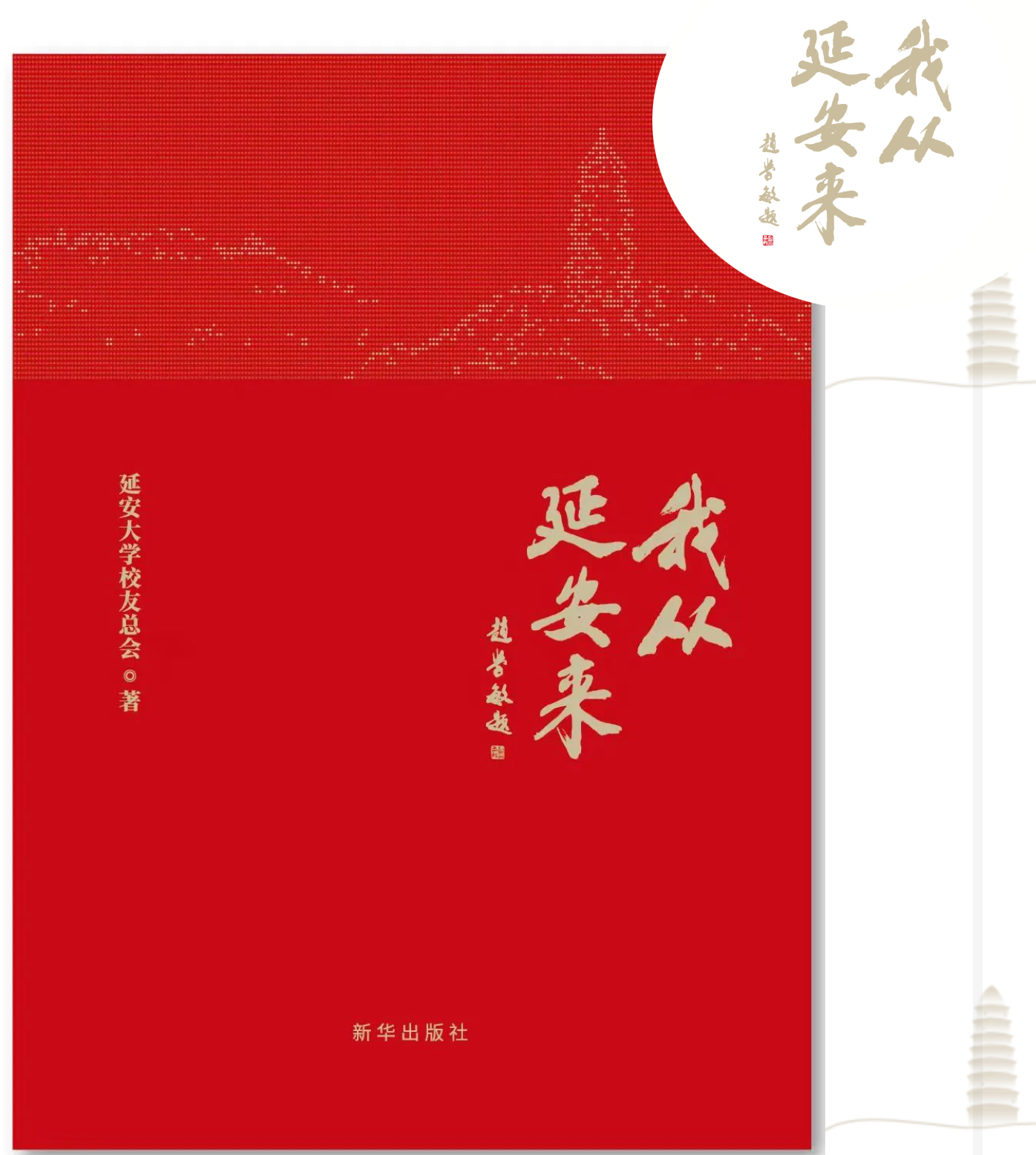


忽培元,祖籍陜西大荔,1955年生于延安,1981畢業于延安大學中文系。中國作家協會會員,全國傳記文學創作與研究專家指導委員會委員,第四屆、第五屆中國傳記文學學會副會長,中國書法家協會會員。2016年5月被國務院聘為國務院參事。
主要作品有:文學傳記“蒼生三部曲”《群山》《長河》《浩海》,《耕耘者——修軍評傳》《百年糊涂——鄭板橋傳》《難忘的歷程——延安歲月回訪》《劉志丹將軍》《謝子長評傳》《閻紅彥將軍傳》等;長篇小說《雪祭》《神湖》《老腔》《鄉村第一書記》;中篇小說集《青春紀事》《家風》,中短篇小說集《土炕情話》;散文集《延安記憶》《人生感悟》《毛頭柳記》《大慶賦·鐵人銘》《地耳集》《生命藤》《京密河札記》《秦柏風骨》《山秀珍》《義耕堂筆記》;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和詩集《北斗》《開悟集》等。
《群山》《耕耘者——修軍評傳》分別獲第一屆、第四屆中國傳記文學優秀作品獎(長篇);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獲中華鐵人文學獎。作品被譯成英文、俄文在國外出版。反映當代生活的長篇小說力作《鄉村第一書記》由作家出版社出版,改編成電視劇《花開山鄉》,在央視一套黃金檔熱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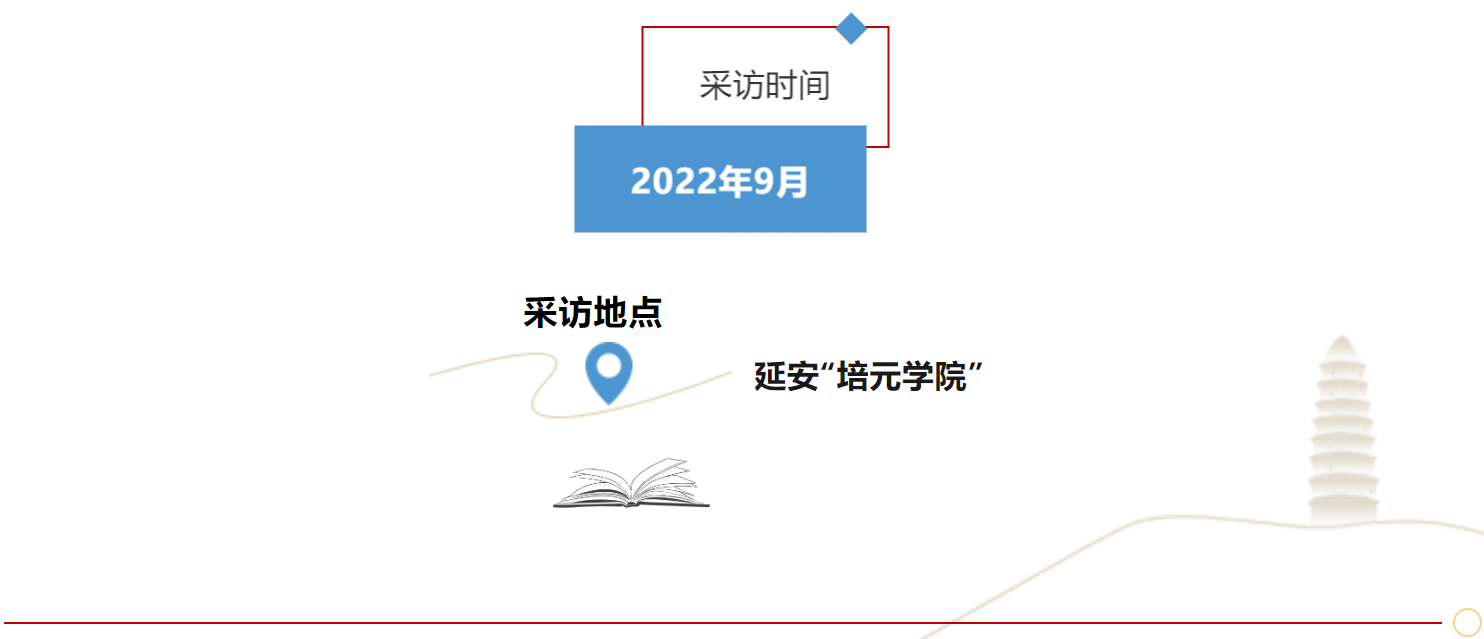
1977年,中斷了十余年的中國高考制度得以恢復。這年冬天,570萬來自各行各業的青年,懷揣著奮發的意氣、滿腔的抱負,以及對科學文化知識的無限向往,走進了高考考場。時年二十三歲的忽培元正是他們中的一員。在經歷了被稱為“史上最激烈的一次高考”的競爭后,忽培元走進了夢寐以求的延安大學的校門。
延河水、土窯洞
給予我樸素而深刻的人生啟蒙
1955年,忽培元出生于延安的市場溝口,這里是延安時期的新建商業街,屬于城鄉結合地帶。他的父親忽聚田是一名將自己的一生奉獻給陜北水利事業的知識分子。在百廢待興的年代,為讓自己所學應用于實際、支援革命老區建設,畢業于西北農學院的父親,主動申請從西北軍政委員會水利部,下到當時現代水利設施幾為空白的延安地區,參與水利建設,發展農業灌溉生產。自此舉家遷徙,扎根陜北。
那時候,延安沒有一畝灌溉田,農民靠天吃飯,廣種薄收。忽培元的父親和他的同事們是第一批在黃土高原上建壩修水渠的人。作為高級水利工程師,父親測量設計、參與施工直到工程通水,把一畝畝旱地變成水田,讓農民從效益很低的勞動中解脫出來,也為貧瘠的陜北大地增添著綠色。
忽培元的父親勤奮、儉樸,對待工作嚴謹、認真,幾乎年年都被評為勞動模范,《人民日報》《光明日報》曾對他的事跡進行過長篇報道。父親是那個時代知識分子的縮影,他們沒有功利得失的私欲,只有奮不顧身的熱情,他們用堅毅、辛勞、心血和汗水詮釋了新中國一代知識分子的責任和理想,也在年幼的忽培元心中樹立起一個無私奉獻的榜樣。而母親的勤勞和善良,更像一面鏡子,照得忽培元的心中亮堂堂的。從父母身上,忽培元得到了很好的家風傳承,擁有了一生恪守的品質涵養。“踏實勞動、踏實做人、踏實做事,這是父母留給我最寶貴的財富。”忽培元說。
上世紀50年代,陜北的經濟水平還很落后,物資相對匱乏,忽培元一家的生活十分艱苦,經常忍饑挨餓。三四歲時,在回鄉政策的號召下,忽培元隨母親回到物資相對寬裕的關中老家——大荔縣安仁鎮下魯坡村生活過一段時間。雖然時間不長,但老家給年幼的忽培元留下了十分深刻的印象。在他的童年記憶里,天氣晴朗時,站在老屋后院那棵老棗樹下,可以望得見南邊的華山和東邊的黃河水。在這個黃河畔上的古老村莊,忽培元曾用兒童那充滿好奇的目光和心靈,感受故鄉新鮮而神秘的一切,感知傳統農民勤勞、質樸的本色……
小時候,忽培元的父親常年駐工地,住帳篷。回到延安的很長一段時間里,父親的工地在哪,家就搬在哪。在忽培元的記憶中,隨著父親工作的每一次調令,全家就帶著為數不多的家當,拉著簡陋的架子車,在陜北四處遷移。城郊的窩棚、教堂、廢棄窯洞……都曾是他們的家。就這樣,在一次次的舉家搬遷中,忽培元經歷了從兒童到少年的學習與成長,更面對了困難時期的饑餓與艱辛。但在知識分子父親和勤勞賢淑的母親的培養和熏陶下,在那個不注重文化知識的年代,忽培元各項學業和活動都走在了前面,他的心中也有了一個上大學的夢想。
然而那是個特殊的年代。在知識青年上山下鄉的澎湃浪潮中,高中畢業后的忽培元被分配到延安郊區的川口公社插隊落戶,他也只能把大學夢深深埋藏在心底。他還記得那是1973年的一個寒冷的冬日,父親用自行車把他和不多的行李送到了川口,從此他的生活開啟了新的一頁。
陜北農村歷來苦焦,但對于吃慣了苦的忽培元來說,在川口,他并沒有感到絲毫的陌生困頓,而是仿佛回到了曾經生活過的關中老家一樣,充滿了歸屬感。在這片干旱貧瘠的土地上,他和鄉親們一起上山下地,春天播種,夏天除草耕耘,秋天弓著身子把沉甸甸的莊稼由山里背到莊里的場上碾打……很快,他就成長為日工分十分的莊稼把式。
一年后忽培元不僅入了黨,還被鄉親們推舉擔任了大隊黨支部書記,成為了全縣最年輕的基層干部。那時他剛剛十九歲。“全村一千多口人,把你當成‘黨派來的親人’看待,你的一舉一動,都代表黨組織,擔子有多重,只有挑擔人自己知道。那時白天苦干一天,夜晚躺在炕上翻來覆去睡不著,心里盤算著,怎樣才能讓老百姓豎大拇指。”忽培元說。為了讓川口的百姓脫貧致富,他將大隊的一千多口人、兩千多畝地劃分成四個作業組,定地塊,定勞力,定生產資料,定產量,到年底根據任務完成情況獎罰。事實證明這個方法很不錯,群眾也滿意。此后,這位年輕的大隊一把手,還帶領大家搞起了多種經營,在兩千多畝川地中間修了個百頭豬場。這樣一來,使得村里沒有糞臭味、干凈衛生的同時,也為田地積攢了肥料。“這樣的田是高產田,那時延安縣的種子都是由我們生產大隊供應的。”忽培元自豪地說道。
延大
夢想開啟的地方

插隊五年后,忽培元被招工到了西安鐵路局安康分局。可就在他準備向著那條在別人看來穩定平坦的道路行進時,恢復高考的消息傳來。“統一考試、擇優錄取”,一個“考”字,猶如一聲號令,蕩滌了“讀書無用論”的污流,為正待復蘇的中國大地吹來了第一陣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春風。同時也喚醒了忽培元心中沉睡了多年的大學夢。
積聚十三屆的考生、荒廢十年的學業、一個多月的備考時間,使許多報考者猶豫、徘徊。由于信息閉塞,忽培元對高考的政策并不十分清楚。有人告訴忽培元,只要報名考試,無論考上考不上,都得放棄工作。可即便是這樣,命運不再取決于他人,不再由出身和關系決定,而是掌握在自己手中。離開校園多年的忽培元,毅然報了名,并開始了夜以繼日的復習備考。
1977年冬天,關閉了十一年的高考考場重新敞開大門,570多萬年齡懸殊、身份不同的考生涌進考場。幾乎所有考點門口都拉起了這樣一條橫幅,上面寫著:祖國,請您挑選吧!
1978年春天,忽培元被第一志愿延安大學中文系錄取。延安大學,這所坐落于楊家嶺下、延河岸邊的高等學府,是中國共產黨創辦的第一所綜合性大學,對于忽培元來說,有著神秘的色彩,令他充滿了向往。“延大是光榮的大學,是黨中央、毛主席在延安時期親自創辦的培養革命戰士的大熔爐,當時的名氣和地位可想而知。”忽培元說。
邁入大學校門的忽培元無疑是激動與振奮的。作為恢復高考后的第一屆學生,77屆學生中的多數人和忽培元一樣有著上山下鄉或招工入伍的經歷。飽受知識斷層和精神困惑的這一批學生,經歷了百里挑一的選拔,擁有了改變命運的機會,因而格外珍惜這來之不易的學習時光。“那時候我們每個人對待學習都非常刻苦,幾乎人人都會抓住一切時間看書,經常是十一二點才離開教室。”忽培元回憶著大學的時光,他還記得同窗好友魏久堯經常是最后一個離開教室的。“那時候延大是在全省范圍內招生,全班五十三名同學分別來自陜北、關中、陜南,大家雖然生活習慣不同,年齡跨度也很大,但也許是因為有著相同的經歷,也有著共同的目標,所有同學關系都相處得很好,很多同學即使畢業幾十年也沒斷了聯系。”
當時的延安大學辦學條件還十分艱苦,整個校園里只有一棟樓,既是教學樓,同時又是圖書館;學生宿舍安置在校園內的兩排窯洞里;學生食堂也是學校的大禮堂,沒有桌椅,大家就在地上蹲著就餐。最常見的伙食是白菜土豆燴菜,偶爾能看見豆腐,大家都會爭相傳告。“雖然生活條件艱苦,但同學們都能很快適應環境,加上大家也都一門心思想著讀書與學習,大部分時間是在教室度過的,所以生活條件就顯得并不那么重要。”忽培元回憶道。也是從那時起,延安大學艱苦樸素的作風,就深深地鐫刻在了每一名延大學子心上。
更令忽培元感到欣喜和自豪的是,延安大學雖然坐落于經濟發展相對落后的陜北,條件較為艱苦,但當年的師資力量卻相當雄厚。中文系的教師中,除了有畢業于復旦大學的包永新教授,從西北大學調來的宋靖宗教授等,還有多位畢業于或曾任教于著名高校的教師。恢復高考前,這批優秀的教師多年無法正常教學;恢復高考后,他們總是盡可能地將己所學毫無保留地教給學生。
“人們總是很難忘懷影響了你的精神世界與人生方向的好老師,且隨著歲月流淌而日愈清晰。延大中文系學習四年,最大的偏得就是遇到他們這些飽學敬業的先生。”忽培元曾多次在文章中回憶過這些令人敬重的老師,其中就包括教古典文學的高振忠先生、教古漢語語法修辭的趙步杰先生、教寫作課的馮力平先生、教古典戲曲的宋靖宗先生和趙云天先生,以及教文藝理論的包永新先生等。“他們的思想活動和創造力或許難免受到某種時代影響或局限,但是他們的克己奉公與刻苦鉆研的品格卻成就了精神的高尚與靈魂的干凈。他們身上體現出的貌似訥言敏行,其實更是‘我將無我’的更高境界與新君子風度。這種為人師表的‘身教’,對我們的影響,應當說遠遠超越了知識的‘言傳’。”忽培元在文章中寫道。
包永新教授是上世紀50年代由上海復旦大學中文系畢業后,自愿報名來大西北支援祖國建設的,教文學理論。在忽培元的記憶里,無論冬夏包永新先生來上課,總是穿著可體整潔的淺色中式衣衫,頭發梳理得一絲不茍。他走路的姿勢和面部表情永遠嚴肅而溫和謙恭。給人的印象,格外的莊嚴凝重、熱忱謹慎。忽培元課余時間喜歡與好友結伴到包先生窯洞里請教。那孔小小的石窯洞既是先生的家也是他的辦公室,里面除辦公桌書櫥和簡單家具外,幾無余物。他還記得先生每次都要用糖果清茶招待他們這些學生。談話多數圍繞教學內容,也包括當時的文藝創作、文學現象和文學新人新作。
“包永新先生的認真嚴謹、言之有據、一絲不茍、潔身自好的治學態度與自我修為,至今清晰銘刻在記憶里,深刻地影響了我的人生。使我在任何環境、任何世風之下,都保持和把握住讀書人的是非底線,與為人處事及治學的定力。”忽培元在紀念包永新先生的文章中寫道。
“當時我們身處陜北,信息閉塞,思想也較為保守。是老師們的教導和培養讓我們這些本是地上跑的人可以‘飛起來’。”忽培元說,“多年來,無論走到哪里,面對誰,我都會自豪地說我的母校是延安大學,是母校塑就了我們人生奮斗的底色,是母校賦予了我們前行的力量。延大,是我夢想開啟的地方!”
文學
是我對這個世界的責任與義務

恢復高考使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價值觀和社會風尚重新在社會上形成。當校園內學子們如饑似渴地求知時,校園外同樣掀起了讀書熱,一時間文學青年找到了心靈的港灣,沉浸在文學世界中,文學熱潮就此興起。而對于忽培元來說,文學夢的萌發更是在此之前。
之所以愛上文學,忽培元說可能是從陜北那漫長的冬夜里,聽母親所講的那些瑣碎但無比吸引人的故事開始。故事里的喜怒哀樂、人際關系、人物命運,總是牽引著他的思緒,讓童年的忽培元在還不知道文學是什么的時候,就埋下了文學種子;而知識分子父親對待知識、對待文字的執著,也深深影響了他的人生觀、價值觀的形成,也讓他懂得知識的力量能夠讓人受益終身,無論何時,都要多閱讀、多思考、多動筆;后來上了小學正值“文革”期間,一個偶然的機會忽培元發現了學校存放“禁書”的地方,那一時期看了很多名著,又碰到一位很好的啟蒙老師,教他怎么觀察生活,怎么真正讀懂書;當然最重要的原因還有忽培元從小生活在革命圣地延安,從小他的周圍就有好多當過兵、參加過早期紅軍赤衛軍的老黨員、老紅軍,他們口中的紅色故事,也深深地吸引著忽培元……總之,忽培元就這樣愛上了閱讀,愛上了寫作,開始認真觀察生活并記錄下來,從此一發不可收拾。
學生時代的忽培元就打下了很好的文字基礎。在農村插隊時,他就已經開始寫一些與鄉村有關的文章。進入延大之后,忽培元全面系統地學習了中國古代文學、中國現代文學、文學理論、現代漢語、寫作等課程,更是有了海量的閱讀積累,為他日后的創作奠定了堅實厚重的基礎,也使得他少年時就埋藏在心中的文學夢也漸漸清晰了起來。延大時期,忽培元曾多次在《延河》《延安文學》等雜志上發表文章,并且和愛好文學的同學一起創辦了中文系的文學刊物《原草》。這本薄薄的文字刊物,從征稿、編輯、刻板、油印到發放,都由學生自己完成。忽培元主要負責文字編輯工作,這本雜志也為他后來的文學創作起到了影響。
1981年忽培元從延大畢業后,先后在中學語文教師、雜志社編輯的崗位上工作過,還擔任過縣、市級重要領導崗位,后調國務院研究室工作,擔任國務院參事。無論他身在何方,身居什么崗位,他始終求真務實,開拓進取,一步一個腳印。無論日常工作多么繁忙,他對文學的追求與熱愛,從來沒有改變。
忽培元認為社會工作和文學創作就像是他的“兩畝地”,而他則像一個真正的農民一樣,多年來一直辛勤地耕耘著這“兩畝地”。在忽培元四十多年的從政生涯中,他走到哪里,寫到哪里。每當有新作品問世,大都與他此前或眼下的任職有關,因而他的作品,大多能聯系實際,注重調查研究并做出深刻的思考。除了諸多的文學作品,他還寫了大量經濟社會調查研究報告。“文學,是我對這個世界的責任與義務。”忽培元說。
青年時期,他寫自己插隊時的所歷所感,集結成鄉村敘事系列作品《土炕情話》《青春紀事》;延安工作期間,他寫延安的革命傳統,寫自己在延安工作和生活中的切身體驗,收錄于散文集《延安記憶》;在擔任馬文瑞同志秘書期間及在陜、甘、北京等地采訪了許多西北老同志,掌握了大量真實情況,搶救了寶貴的歷史資料之后,他寫就長篇傳記《群山》《長河》《浩海》,還著有《劉志丹將軍》《謝子長評傳》《難忘的歷程——習仲勛在陜北》《閻紅彥將軍傳》,和反映陜北將軍賀晉年、吳岱峰等大量的革命歷史人物的特寫;在潼關工作期間,他寫了反映農村社會問題的長篇小說《雪祭》;到大慶工作后,他創作了6000多行的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此外,他還組織編寫了至今是研究延安歷史和文化重要資料的《新延安文藝叢書》,以及獲得大慶開發和建市以來文化發展特別貢獻獎的《大慶文藝精品叢書》(18卷);在擔任國務院參事期間,他更是廣泛調研、深入采訪,寫下了反映鄉村發展的長篇小說《鄉村第一書記》,由其改編成的電視劇《花開山鄉》也被搬上了央視熒屏……豐厚的生活經驗和長期擔任縣、市地方官員的歷練,無疑為忽培元的文學創作提供了取之不盡的源泉。
忽培元的好友、著名作家陳忠實曾評價忽培元的文學創作時說:“忽培元的文學作品,總是從生活出發,從現實出發,即使寫歷史生活,也有當下生活體驗的融入,給人以厚實、親近之感。”
黨政工作和生活角色、社會角色,讓忽培元成為一個真正的生活者。“那段時間的積淀太重要了,某種程度上打破了作家下去體驗生活、深入生活這種概念。你要是一個真實的生活者,而不是去觀察、去體驗,你要真實地泡在生活中。”忽培元說,“在生活的過程中,我接觸各種矛盾,解決各種矛盾,扮演各種角色,從不同的角度觀察不同的人和事物,這些可以讓我的生活經歷不斷豐富。但你還得是個有心人,需要從藝術的角度上來看待生活,把生活中的瑣碎講述出來,重新提煉生活再升華成文學藝術作品。所以有人說,我白天的工作時間像是在體驗生活,晚上的個人時間又變成了一個作家。”忽培元至今都有一個習慣,無論工作多么繁忙,他都會在早晨五點多起床,堅持晨起寫作。
忽培元曾在一篇自序中寫道:“苦戀文學,如同摯愛哺育過我的陜北土炕和米酒,那情分真正是與日俱增。”自上世紀70年代忽培元開始業余文學創作,在繁忙的工作之余,他始終以飽滿的創作激情和高度的社會責任感筆耕不輟,在小說、詩歌、傳記文學和散文等領域均有建樹,現已先后出版書籍三十余部,發表文字千萬字以上。其中,《群山》《耕耘者——修軍評傳》分別獲第一屆、第四屆中國傳記文學優秀作品獎(長篇);長詩《共和國不會忘記:大慶人的故事》獲中華鐵人文學獎。多部作品被譯成英文、俄文在國外出版。
故鄉
是浸潤生命的情感源泉
多年來,忽培元在文學的土壤里勤奮耕耘著,幾乎每隔幾年,就會有一部厚重的作品問世。2018年底由作家出版社出版發行的《鄉村第一書記》,就是這樣一部沉淀深厚之作。
《鄉村第一書記》講述了鄉村第一書記白朗帶領干部群眾腳踏實地破解一個又一個難題,保衛綠水青山,因地制宜發展新農村經濟,建設美好家園的生動故事。其中,主人公白朗的形象,不僅綜合了忽培元的眾多采訪對象,更有取材于他在延安川口插隊的經歷以及此后參與對口幫扶延川縣文安驛鎮梁家河村的體會……雖然小說的寫作歷時三年,但素材的積累與構思跨越了近半個世紀。
小說出版后,引起了廣泛的關注與反響,被認為寫出了第一書記駐村工作的酸甜苦辣,是一部貼近現實、深接地氣的現實主義佳作。同時,被評論家譽為“是一部多側面塑造新時代共產黨員新人形象的具有教科書意義的優秀文學作品”,“在當前扶貧工作和鄉村振興實踐的深入研究探索和某些方面具有‘破題性’意義的思考和藝術再現”。小說出版至今,已發行十幾萬冊,在寧夏和河南的一些地方,鄉鎮干部和第一書記更是人手一冊。就在全面打贏脫貧攻堅戰收官之年,由《鄉村第一書記》改編的電視劇《花開山鄉》在央視一套黃金時段熱播,該劇在讓人們看到新時代中國農村變化發展的同時,再一次引發了人們對鄉土情懷的思考。
實際上,忽培元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都著重寫鄉土情懷。目前,他剛剛完成的長篇小說《同舟》,就是繼《鄉村第一書記》后的又一部書寫鄉村的力作。全書56萬字,通過講述一個特殊的民族融合村——同舟的故事,反映了當代陜西秦嶺腳下黃河之濱一帶的農村變遷。
無論是在延安成長、生活、工作,還是后來到省城,到京城,再到大慶……忽培元的生命之根、情感之根、思想之根、文學之根都始終深扎在延安,深扎在陜北這塊紅色土地上。土窯洞、毛頭柳、老黃牛,犁地、攔羊、背莊稼,吹嗩吶的老漢、放牛的孩童,陜北民歌的真摯純美蒼涼,陜北傳統農民的性格特征和精神氣質,始終是他敬重與歌詠的最初音符和基調。
對故鄉的眷戀之情不僅體現在忽培元的文學作品上,還體現在他的繪畫作品上。他的繪畫多樸拙,在樸拙中滲透著蒼茫之氣。黃土山巒、窯洞村落、童子牧牛、山里的五花羊和攔羊老漢、村道上犁地歸來的黃牛和陜北漢,都是他繪畫作品中常見的意象。他曾在文章中寫道:“故鄉黃河灘涂和陜北的黃土溝壑,是我的生命源頭和藝術根脈所在。我就像一只風中不安分的風箏,無論升降起落,身后總有一條看不見的線牽扯著,難分難舍。一閉上眼晴,就看得見那么一架山或一條河,一座小院兒或是幾孔窯洞。記憶深處的童年之夢,故鄉與親朋記憶,這是浸潤我們生命的情感源泉,是永遠都叫不醒的人生夢境……這就是鄉愁,是關于故鄉的親密話題,是我們一生都沒完沒了的思念與牽掛,是隨時都想回歸其間的精神家園,更是我們靈魂的歇息之所,足以讓你心緒沉靜下來的一種撫慰與規勸。”
從插隊知青到大隊書記,再從縣市公務員到國務院參事,忽培元的視野在不斷拓展,思考也在不斷深入。但無論走到哪里,走出多遠,他心中總是裝著故鄉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并且隨著時間的沉淀與深刻冷靜思考后,這些關于家鄉的記憶與思考總是召喚出他更多創作的靈感,而在創作的字里行間他也把對故鄉的感情回饋給了那里的土地和鄉親父老。
無論是小說、詩歌、散文,還是紀實文學,忽培元的創作一直根植于生活和人民的厚土,延續著傳統文脈,帶著陜北家鄉的泥土氣息,律動著詩性、情趣、火花與骨氣。忽培元所敬重的著名詩人賀敬之曾這樣評價忽培元:“他對文學事業的熱愛,對革命前輩及其業績的崇尚,以及刻苦努力學習寫作的精神,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是一個熱情勤奮、思想堅定、很有責任感和使命意識的黨員作家。在他的人品和作品中,洋溢著崇高理想和堅定信念的力量。”
母校
是每一位延大學子的底氣
距離1981年忽培元從延安大學畢業,已經四十年之久。四十年來,忽培元卻從未和母校真正分開過。多年來,他無論走到哪里,無論在何處任職,始終時刻關注著母校的發展,常常惦念著母校的恩師和同學。和故鄉一樣,母校同樣是他筆下的取之不盡、用之不竭的寫作之基和力量之源。
“回想起全國恢復高考后榮幸考入具有光榮歷史的延安大學,當時的喜悅之情難以言表,記憶猶新。”忽培元說,“在延大中文系四年學習,如羔羊之承哺,似小樹之沐陽,影響奠定了我一生的思想傾向、知識基礎和投身文學事業與為社會精誠服務奉獻的堅定理想志趣。如今回顧,羔羊已老,小樹既壯,可當年的各位恩師或早已作古,或垂垂老矣。好在代代皆有才人出,名校名師多后賢。一日為師終生為父,母校之恩,難報萬一。”
幾乎每次回延,忽培元都會抽時間與同窗好友相約去母校走走看看。談起母校的變化,忽培元感受最大的就是硬件設施的不斷改善和院系建設的不斷突破。他說以前延大雖然名氣大,但校園狹窄,基礎設施簡陋,在很多人眼中甚至有點“湊合”。而今延大在幾屆領導班子的接力奮斗下,在全體師生的努力下,校域范圍不斷擴大,校園建設和教學設施得到不斷改善,校園環境也得到了大力的提升。同時延大的院系建設得到不斷突破,使得延大已由一個以師資培養為主的師范院校,變成了一個真正意義上的綜合大學,而且在全國具有很大的影響力。
多年來,延安大學也時刻關心關注著忽培元的發展,每次遇到校慶等重大活動都會向他發出邀請,并且還聘任忽培元為文學院的客座教授。忽培元時常回母校開展講座,與小校友進行面對面的交流。他的講座內容有關于寫作的心得,也有關于就業形勢的思考,更有紅色黨史故事。他為校友們講自己的文學歷程和人生感悟,說的最多的就是“我們首先要意識到,能夠在延安大學這所具有光榮革命歷史的高校上學,這是自己人生的一次機遇和榮耀,不管走到哪里,母校就是我們的底氣。”
2022年的一個秋日的午后,在延安市寶塔區川口鎮馮坪村“培元書院”,我們又見到了忽培元。此次回延,他帶著歷經近半個世紀的作品與跨越大半個中國的鄉愁,自籌資金為曾插隊落戶五年的第二故鄉建起了書屋。他想通過自己的努力,讓這里的村民可以隨時享用文化大餐,為這里的孩子心中埋下文學的種子,并且希望能夠帶動和影響更多的人熱愛文學、熱愛故鄉。“作家與鄉村,亦即作家與時代,永遠同呼吸、共命運。”忽培元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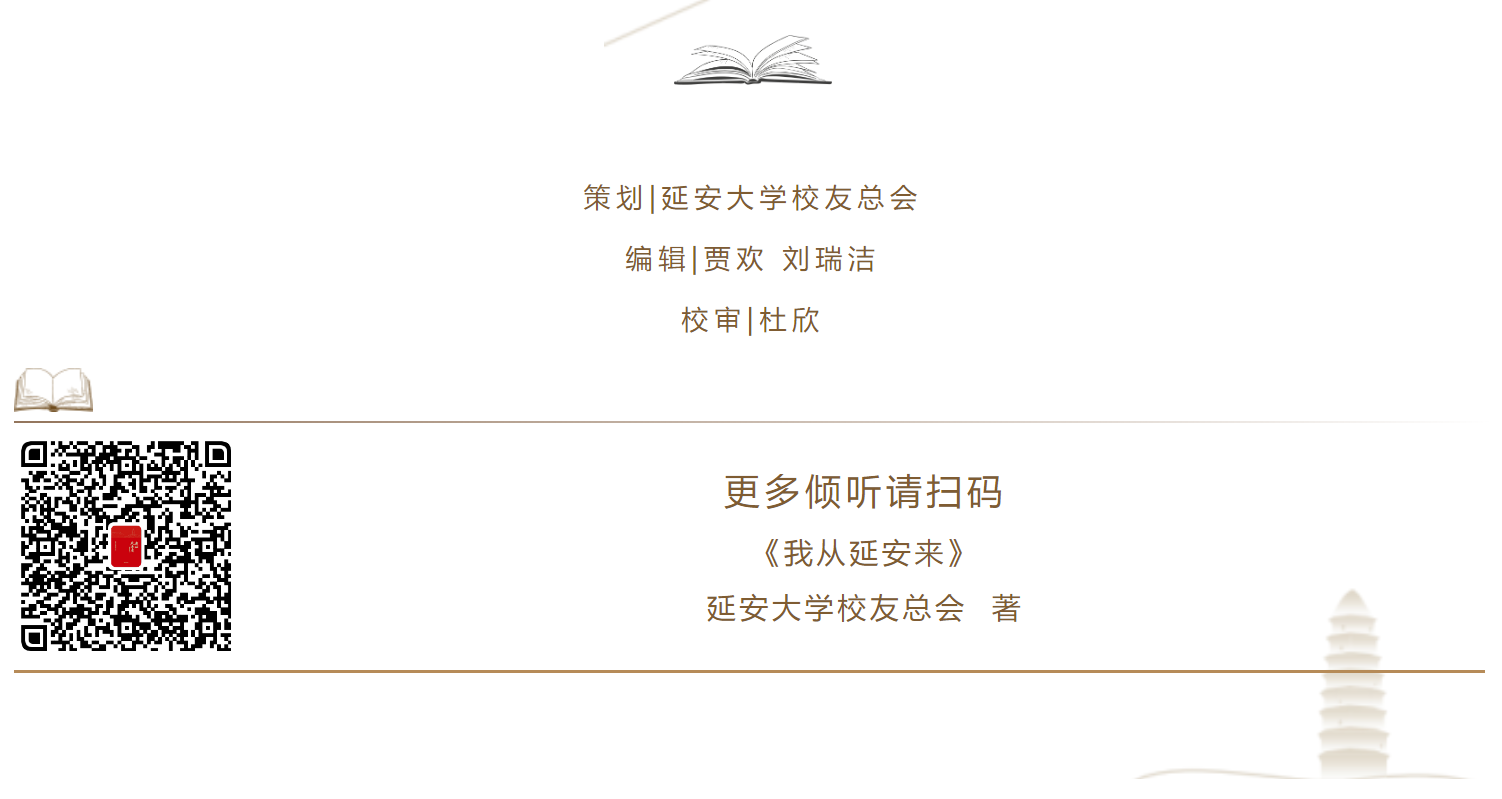
來源:延安大學校友總會
https://mp.weixin.qq.com/s/jaYSPph-NYGtxdhugiYmMw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