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詩歌概念”地域書寫的再界定
——以葉延濱、耿占春、卞之琳、沈浩波、樹才、詩豪天詩歌的北京書寫為例
●楊青雲(《北京詩歌概念書系》特邀撰稿人)
在當代中國詩歌的坐標系中,北京始終是一個無法繞開的“精神地標”。它既是三千年建城史、八百年建都史的歷史容器,又是現代文明與傳統基因激烈碰撞的前沿場域;既是國家意志的象征空間,又是無數個體生命的棲居之地。當“地域書寫”成為詩歌研究的重要維度,北京詩歌的特殊性便愈發凸顯——它不僅是對一座城市的景觀描摹與經驗記錄,更是民族文化記憶、現代性焦慮與精神主體性建構的集中呈現。本文以葉延濱、耿占春、卞之琳、沈浩波、樹才、詩豪天的詩歌為核心文本,從“空間表征—精神投射—語言建構”三重維度考辯北京詩歌概念地域書寫的內涵邊界,重點探討其如何以地域為錨點強化民族文化主體性,并為漢語言的現代性轉型提供詩性支撐。
在進入具體文本分析前,必須先厘清“北京詩歌地域書寫”的核心界定——它并非簡單以“北京”為題材的詩歌集合,而是以北京的地理空間、文化肌理、歷史記憶、社會生態為載體,實現個體經驗與公共精神、地域特質與民族共性、傳統基因與現代意識交融的詩歌創作。其界定需緊扣三個維度:
北京的地域空間具有天然的“雙重性”:一方面是永定門、鐘鼓樓、故宮、中軸線等承載著皇家氣象與歷史厚重的“傳統空間”;另一方面是CBD、城中村、地鐵線路、移民社區等彰顯著現代節奏與生存壓力的“現代空間”。北京詩歌的地域書寫,正是通過對這些空間的詩性轉化,將物理空間升華為文化空間。如詩豪天《北京中軸線》中“永定門的垛口銜住第一縷晨曦/七百多年的光陰從磚縫里簌簌落下來”,并非單純描寫永定門的建筑形態,而是將其轉化為歷史時間的“具象載體”;沈浩波《雨中抒情》里“阜成門的空氣指數/每天嚇我一跳”,則以阜成門這一具體地點為切入點,折射出北京現代都市的生態焦慮與生存困境。這種“空間詩化”,是北京詩歌地域書寫的基礎前提。
北京作為首都的特殊身份,使其地域書寫天然具有“超越性”——個體在這座城市中的生命體驗,往往能折射出整個民族的精神狀態。葉延濱《中國》中“不,可尊敬的小姐,對于我的祖國,長城——/只不過是民族肌膚上一道青筋/只不過是歷史額頭上一條皺紋”,看似是對“長城”這一傳統符號的解構,實則是通過對民族象征的重新認知,建構現代中國的精神主體性。這種“個體發聲—民族回響”的邏輯,同樣體現在北京詩歌的地域書寫中:樹才《安寧》對住宅小區日常的凝視,暗含著對現代都市人精神歸處的思考;耿占春《當一個人老了》對生命困境的追問,折射出轉型期中國人的存在焦慮。可以說,北京詩歌的地域書寫,始終在“個體”與“民族”的張力中尋找精神共鳴點。
北京詩歌地域書寫的終極價值,在于為民族語言提供新的表達可能。北京方言(如兒化音、京腔詞匯)雖可為詩歌增添地域色彩,但北京詩歌的語言貢獻遠不止于此——它通過將北京的歷史語境、文化特質融入漢語言表達,讓民族語言既扎根傳統又貼近現代。卞之琳《魚化石》中“你我都遠了乃有了魚化石”,以極簡的語言承載著時空錯位的哲思,這種語言張力的營造,與北京“傳統與現代并存”的文化特質高度契合;詩豪天《北京中軸線》將“九三大閱兵”“申遺成功”等現代事件與“太廟柏枝”“社稷壇五色土”等傳統意象并置,實現了語言的“歷史縱深”與“當下在場”的統一。這種語言實踐,讓北京詩歌的地域書寫超越了“地域本位”,成為民族語言現代性建構的重要路徑。
北京詩歌概念文本解構六位詩人的北京書寫與主體性建構
六位詩人的創作橫跨近百年(卞之琳創作于20世紀30年代,沈浩波、樹才為當代詩人),其北京書寫呈現出不同的側重點,但核心都指向“地域特質與民族精神的融合”,尤其是通過強化北京地域的輝煌主體性,為民族語言注入新的生命力。
(一)葉延濱《中國》:民族符號的重構與北京精神的隱性呼應
葉延濱的《中國》雖未直接描寫北京,但詩中對“長城”的解構與“中國”意象的重塑,與北京作為“民族精神樞紐”的特質形成隱性呼應。長城作為中國的象征符號,其地理起點雖不在北京,但北京作為元、明、清三朝都城,始終是長城所代表的“防御文化”與“民族認同”的核心承載地。詩中“年輕的我——高昂的頭,明亮的眼,剛毅的體魄”所建構的“現代中國”形象,與北京從“帝王之都”向“現代首都”的轉型軌跡高度一致。
這種呼應的深層意義在于:葉延濱通過解構傳統民族符號(長城),打破了對“中國”的刻板認知,而北京詩歌的地域書寫,正是需要以這種“解構—重構”的邏輯,打破對北京“皇家氣派”的單一想象,挖掘其現代性的精神內核。《中國》所彰顯的“民族主體性”,為北京詩歌的地域書寫提供了精神坐標——北京的輝煌,不應僅僅是歷史的輝煌,更應是現代中國精神的輝煌。
(二)卞之琳《魚化石》:時空錯位中的文化張力與北京語境適配
卞之琳的《魚化石》創作于1936年,雖無明確的北京指向,但詩中“我要有你的懷抱的形狀/我往往溶于水的線條”所體現的“融合與疏離”“存在與消亡”的辯證關系,與北京的文化語境高度適配。20世紀30年代的北京,正處于“傳統帝制終結”與“現代文明涌入”的轉型期:故宮的紅墻與胡同的灰瓦間,滲透著新舊文化的碰撞;文人的堅守與西方思潮的沖擊,構成了復雜的精神圖景。《魚化石》中“你我都遠了乃有了魚化石”的“時空凝固感”,恰是這種文化轉型期的詩意表達——舊的文化形態雖已“遠去”,卻以另一種方式(如魚化石般)沉淀為民族文化的基因。
從北京詩歌地域書寫的角度看,《魚化石》提供了一種“間接書寫”的范式:不必直接描摹北京的景觀,只需捕捉與北京文化特質同構的精神內核,便能實現與地域的深層對話。這種書寫方式,拓展了北京詩歌地域書寫的邊界,使其不再局限于“題材綁定”,而是走向“精神同構”。
(三)耿占春《當一個人老了》:生命困境的追問與北京的歷史重量
耿占春的《當一個人老了》以哲性筆觸書寫生命的荒誕與困惑:“當一個人老了,才發現他是自己的贗品/他模仿了一個鏡中人/而鏡子正在模糊”。這種對“自我存在”的追問,與北京這座城市的“歷史重量”形成了奇妙的共振——北京承載著太多的歷史記憶,每一個生活在這里的人,都仿佛在“歷史的鏡子”中尋找自我,卻又時常陷入“鏡中模糊”的困境。胡同里的老人見證了城市的變遷,卻可能在現代化的浪潮中感到自我迷失;年輕的北漂者追逐夢想,卻可能在歷史與現實的夾縫中失去方向。
詩中“他的自我還沒誕生”的焦慮,正是北京現代性轉型中個體精神狀態的縮影。耿占春的書寫,將北京的“歷史重量”轉化為個體的“精神壓力”,又通過對這種壓力的追問,觸及了民族文化中“自我認知”的深層命題。這種“以個體生命觀照地域精神”的方式,讓北京詩歌的地域書寫更具人文深度。
(四)沈浩波《雨中抒情》:移民視角下的地域認同與民族情感
沈浩波的《雨中抒情》以“北漂”的移民視角,撕開了北京“輝煌”背后的生存真相:“我已習慣了在塵土中奔走/風沙襲擊著我的眼睛”“我竟無端地想起遠在故鄉的父母/呵,白發的雙親,你們可知道,遠在北京的兒子此刻的心情”。這首詩的價值在于,它打破了北京書寫中“宏大敘事”的壟斷,以個體的“異鄉感”與“鄉愁”,建構了更真實的地域認同。
北京是一座典型的“移民城市”,據統計2023年北京常住人口中,非本地戶籍人口超過800萬。這些“移民”的存在,讓北京的地域特質中天然包含“疏離與融合”的矛盾。《雨中抒情》中“失去了我的南方/失去了我的故鄉/失去了故鄉連綿的雨水”的失落,與“就將留居京城”的選擇,正是這種矛盾的體現。而這種個體層面的“地域認同困境”,又折射出整個民族在現代化進程中的“文化根脈焦慮”——當無數人離開故鄉涌向大都市,如何在“現代”與“傳統”“異鄉”與“故土”之間找到平衡,成為民族精神建設的重要命題。
沈浩波的書寫,讓北京詩歌的地域書寫從“宏大敘事”落地到“個體經驗”,既展現了北京的“包容性”與“殘酷性”,又通過個體的情感共鳴,強化了民族情感的凝聚力。這種“接地氣”的地域書寫,讓北京的“輝煌主體性”不再是空洞的符號,而是充滿人間煙火的生命體驗。
(五)樹才《安寧》:日常景觀的詩化與北京的精神歸處
與沈浩波的“焦慮”形成對比,樹才的《安寧》聚焦于北京的日常景觀:“汽車開走了停車場空蕩蕩的安寧/兒童們奔跑奶奶們閑聊的安寧/我想寫出這風中的清亮的安寧/草莖顫動著咝咝響的安寧”。這首詩以細膩的筆觸,捕捉了北京現代化進程中“被忽略的寧靜”,為北京的地域書寫提供了“溫情視角”。
北京不僅有CBD的繁華、地鐵的擁擠,更有住宅小區的閑適、街頭巷尾的煙火。樹才的書寫,打破了對北京“快節奏”“高壓力”的刻板印象,挖掘出地域空間中的“精神歸處”。詩中“占據我全身心的,就是這”的篤定,既是對“安寧”的珍視,也是對現代都市人精神需求的回應——在歷史的厚重與現代的喧囂中,北京依然為個體保留著“詩意棲居”的可能。
這種書寫的意義在于,它讓北京的“輝煌主體性”更具溫度:北京的輝煌,不僅在于歷史的厚重、現代的繁華,更在于它能為每一個生命提供“安寧”的棲居之地。這種“日常詩化”的實踐,豐富了北京詩歌地域書寫的情感維度,也讓民族語言的表達更貼近生活本真。
(六)詩豪天《北京中軸線》地域符號的整合與民族精神的具象化
詩豪天的《北京中軸線》是北京詩歌地域書寫的集大成之作。詩人以中軸線為線索,將永定門、鐘鼓樓、萬寧橋、故宮、天安門、太廟、社稷壇等核心地域符號串聯起來,構建了一幅“歷史與現代交融”的北京精神圖譜:“永定門的垛口銜住第一縷晨曦/七百多年的光陰從磚縫里簌簌落下來”“天安門的旗桿直插云端/紅旗展開時像一片燃燒的霞”“北京中軸線是一根穿線的針/把南與北/古與今/都串在北京詩歌的上面”。
《北京中軸線》以中軸線為詩性錨點,將北京七百年的歷史厚重、當代的時代氣象與《東方紅》的精神隱喻熔于一爐,既是北京詩歌地域書寫的典范之作,更以其獨特的詩學建構,樹立起北京詩歌精神高度的旗幟。這首北京詩歌跳出了單純的景觀描摹,讓中軸線成為串聯古今、勾連個體與民族的精神紐帶,其對北京詩歌概念的詮釋與拓展,具有不可替代的文本價值。北京中軸線不是簡單的地理坐標,而是北京城市文化的“脊梁”,詩豪天精準抓住這一核心意象,讓詩歌從一開始就扎根于北京的地域基因。這首詩的核心價值,在于將北京的“地域符號”轉化為“民族精神符號”:中軸線不僅是北京的地理脊梁,更是民族文化“南北貫通、古今傳承”的象征;九三大閱兵、申遺成功等現代事件與太廟祭祖、社稷壇五色土等傳統意象的并置,彰顯了民族精神的“延續性”與“時代性”。詩中“每一個字/都帶著古城青磚的厚重/瓦的滄桑/和人的溫度”,正是北京“輝煌主體性”的直接表達,這種主體性,既扎根于歷史的厚重,又彰顯著現代的活力。
《東方紅》的隱喻是《北京中軸線》的詩學靈魂,它為北京詩歌的地域書寫注入了鮮明的精神底色,實現了地域文化與民族精神的深度共鳴。社稷壇的描寫是這一隱喻的集中體現:“社稷壇的五色土沉默著/青紅白黑黃五種顏色/砌成大地的五臟/也砌成《東方紅》歌聲的聲聲嘹亮”,五色土是中國古代對土地的認知與敬畏,代表著東、南、西、北、中五方疆域,是民族生存的根基;而《東方紅》作為從陜北傳唱至全國的革命歌曲,是人民對領袖、對新中國的贊頌,是民族精神的象征——詩人將五色土與《東方紅》并置,意味著北京詩歌的地域文化與民族精神同根同源,地域書寫的內核正是民族文化的傳承。
“古人們把對土地的敬畏捏進泥土里/讓五谷的香從土里鉆出來”,這句看似樸素的描寫,實則暗含著“土地與人民”的關系:古人對土地的敬畏,本質上是對生存的敬畏、對人民的重視;而《東方紅》的核心精神,正是“為人民謀幸福”,這種內在邏輯的契合,讓《東方紅》的隱喻不是生硬的植入,而是與地域文化自然融合。“歌吟了千年的《東方紅》/比北京詩歌的紅/更紅/更鮮艷”,這里的“紅”是精神的顏色:北京詩歌的“紅”可能是故宮紅墻的紅、紅旗的紅,而《東方紅》的“紅”是革命的紅、人民的紅、信仰的紅,它更鮮艷、更有力量,因為它承載著民族從苦難到輝煌的奮斗史,是北京詩歌地域書寫中最厚重的精神底色。
尤為重要的是,《北京中軸線》與葉延濱《中國》形成了“相映成趣”的呼應:《中國》通過解構傳統符號建構現代民族精神,《北京中軸線》則通過整合地域符號具象化民族精神;前者是“抽象到具體”的升華,后者是“具體到抽象”的提煉,二者共同指向“民族精神主體性”的建構,也為北京詩歌概念的命名提供了核心文本支撐。
北京詩歌概念理論建構的命名邏輯與語言貢獻
基于上述文本分析,我們可以明確“北京詩歌”概念的命名邏輯,并厘清其對民族語言現代性的貢獻。這一概念的成立,并非基于“題材地域化”的簡單歸類,而是基于“精神地域化”與“語言地域化”的雙重支撐。
(一)北京詩歌命名邏輯以“地域精神”為核心的三重統一
北京詩歌概念的命名,需實現“三重統一”:
1. 歷史與現代的統一:如《北京中軸線》所示,北京詩歌的地域書寫必須扎根歷史(永定門、故宮等傳統符號),又直面現代(九三大閱兵、都市生存等現代議題),在歷史與現代的對話中彰顯地域精神的延續性。
2. 個體與民族的統一:如沈浩波《雨中抒情》、葉延濱《中國》所體現的,北京詩歌需以個體經驗為切入點,通過個體的情感共鳴與精神追問,折射民族的集體意識與精神需求。
3. 空間與精神的統一:如樹才《安寧》、耿占春《當一個人老了》所實踐的,北京詩歌需將物理空間(住宅小區、胡同街巷)轉化為精神空間,實現地域空間與精神空間的同構。
這三重統一的核心,是“地域精神”的提煉——北京詩歌的本質,是“以北京為載體的民族精神詩化表達”。只有緊扣這一核心,“北京詩歌”才能成為一個具有學術價值與詩學意義的獨立概念。
(二)北京詩歌語言貢獻為民族語言注入“地域基因”與“時代活力”
北京詩歌的地域書寫,對民族語言現代性的貢獻主要體現在兩個層面:
1. 地域基因的融入:通過將北京的歷史語境、文化特質、生活經驗融入語言表達,讓民族語言更具“文化厚度”。如詩豪天對中軸線、五色土等地域符號的詩化運用,豐富了民族語言的意象體系;沈浩波對“阜成門空氣指數”“工體球場”等現代地域經驗的書寫,讓民族語言更貼近現代生活。
2. 表達范式的創新:在傳統與現代的碰撞中,北京詩歌探索出了新的語言表達范式。如卞之琳《魚化石》的“哲性隱喻”,將抽象的時空思考轉化為具象的詩歌意象;葉延濱《中國》的“符號解構”,打破了傳統民族符號的固化表達;樹才《安寧》的“日常詩化”,讓平凡的生活場景成為詩意的載體。這些創新,為民族語言的現代性轉型提供了詩性范例。
正如題目所強調的,北京詩歌“強化北京書寫的輝煌主體性”,其本質是通過地域書寫強化民族文化的主體性;而這種主體性的強化,最終會“進入我們漢語言的血液中”,讓民族語言在扎根地域文化的基礎上,更具生命力與影響力。
從卞之琳的《魚化石》到詩豪天的《北京中軸線》,從葉延濱的《中國》到沈浩波的《雨中抒情》,北京詩歌的地域書寫始終在“歷史與現代”“個體與民族”“空間與精神”的張力中尋找平衡,最終建構起以“輝煌主體性”為核心的地域詩學。這種詩學,不僅是對北京這座城市的詩意記錄,更是對民族精神的鏡像呈現——北京的歷史厚重,是民族文化積淀的縮影;北京的現代轉型,是民族復興的見證;北京的個體悲歡,是民族情感的共鳴。
“北京詩歌”概念的界定與命名,不僅為詩歌研究提供了新的視角,更重要的是,它彰顯了地域書寫對民族語言現代性建構的重要價值:當詩歌扎根于具體的地域文化,其語言表達才會有堅實的文化根基;當地域書寫上升到民族精神的高度,其詩學價值才會有更廣闊的輻射空間。從這個意義上說,北京詩歌的地域書寫,既是“北京的”,也是“民族的”;既是“歷史的”,也是“未來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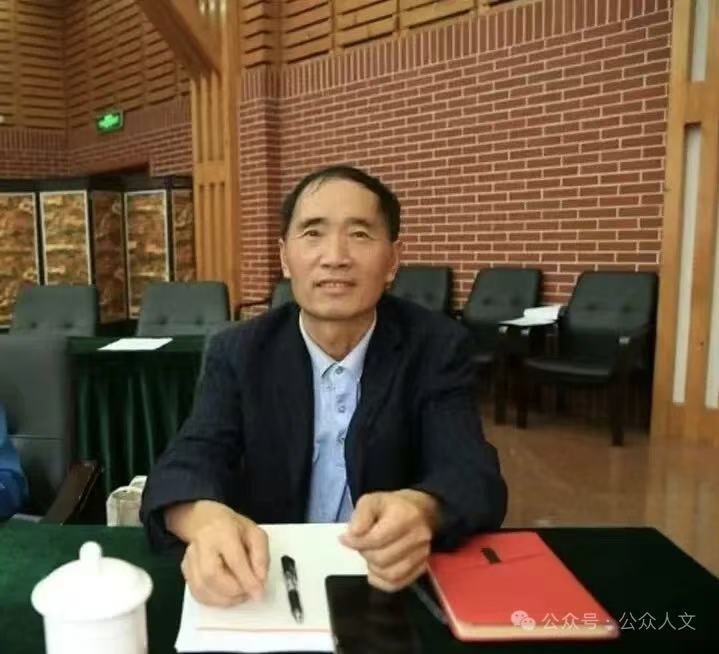 楊青雲 近照
楊青雲 近照
【作者簡介】楊青云,曾用名楊曉勝,筆名梅雪、汝愚等。常駐北京。著有《范曾論》《范曾新傳》《孔祥敬詩論》《周恩來研究》《范曾詩魂書骨美學思想窺探》《賈平凹美術論》《李德哲美術論》《北京虎王馬新華新論》《忽培元淺論》《王闊海新漢畫初探》《北京詩歌概念書系上部》《櫻花結》長篇小說等。現為范曾研究會會長,北京周館籌秘書長兼《周公研究》新媒體總編。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