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詩歌”的詩學建構及精神譜系重釋
——以葉延濱、梁小斌、安琪、藍藍、馬新華為例
●楊青雲(《北京詩歌概念書系上卷》特邀撰稿)
當詩歌成為一座城市精神的鏡像,“北京詩歌”便不再是地域標簽下的文本集合,而是承載著中國近現代文化基因的詩學共同體。在當代詩歌語境中對“北京詩歌概念”的系統命名與詩學建構,本質上是對“京派精神”的再發現,這種精神既植根于北京作為政治與文化中心的歷史積淀,承襲了“皇帝詩學”所蘊含的宏大敘事意識與文化擔當,又在當代詩人的創作實踐中轉化為直面現實、堅守理想的使命自覺。它不是封閉的地域詩學,而是以北京為樞紐,連接傳統與現代、個體與時代的精神載體。
葉延濱、梁小斌、安琪、藍藍、馬新華五位詩人,以各自獨特的創作軌跡勾勒出當代北京詩人群像的多元維度:葉延濱以“寓言書寫”解構時代話語的虛妄,梁小斌用“日常鏡像”叩問歷史創傷的余溫,安琪借“城市覺醒”張揚個體生命的鋒芒,藍藍憑“生命痛感”傳遞人文關懷的溫度,馬新華則以“紅色意象”錨定文化根脈的厚重。他們的作品共同印證:北京詩歌的詩學高峰,正在于將“京派精神”的宏大性與個體書寫的具體性相融合,將“皇帝詩學”的文化底蘊轉化為介入現實的精神力量。
筆者旨在通過深度剖析五位詩人的代表作品,梳理其詩學特質與創作邏輯,進而建構“北京詩學”的理論框架,重釋北京詩歌的精神譜系。這一研究的核心旨歸不僅是為“北京詩歌概念”提供學理支撐,更是為了彰顯命名背后的使命意識,推動北京詩人明確自身作為“京派精神”傳承者與創新者的角色,以更系統、更整體的姿態向詩歌界與批評界展示以北京為中心的詩學實踐與精神內核。
解構與警示:葉延濱的“寓言詩學”與京派批判精神
葉延濱的詩歌始終保持著一種“局內人”的清醒與“旁觀者”的冷靜,詩人既深植于北京的文化語境,又能跳岀具體場景的局限,以《老寓言》為代表的作品構建了一套直指時代本質的“寓言詩學”。這種詩學既是對“京派精神”中批判傳統的繼承,也暗合了“皇帝詩學”所要求的社會關懷與警示意識,成為北京詩歌批判維度的重要支撐。
《老寓言》以“一個人在路上邊走邊撒謊”開篇,瞬間將讀者帶入一個充滿悖論的時代場景。撒謊者的話語極具迷惑性:“用的每個詞都很正確”“出名門,名家論,名言典”,甚至“貼有包修包換的證書”。這里的“正確”并非真理意義上的正當,而是被權力話語規訓后的“合規”——那些來自權威體系的“名言”“證書”,為謊言披上了“合法性”外衣,使其如“鋼軌一樣鋪向天際”,形成不容置疑的壓迫性。
葉延濱的敏銳之處在于精準戳破了時代話語中“形式正確”與“本質虛假”的裂痕。在北京這座全國話語生產與傳播的中心,話語既可能是思想啟蒙的工具,也可能淪為權力附庸的載體。當“正確”成為衡量話語的唯一標準,真理便被形式所遮蔽,謊言便有了橫行的空間。詩人以“寓言”的形式將這種異化具象化,既避免了直白批判的局限,又保留了批判的鋒芒,這種“舉重若輕”的批判智慧,正是“京派精神”的核心特質之一:不糾纏于具體事件的是非,而是抓住時代的精神癥結,以詩性隱喻完成對普遍問題的反思。
詩歌結尾“滿嘴跑火車就是這么跑的/只是,坐上車的人都沒回來”,將批判的視角從“撒謊者”轉向“盲從者”。“坐上車的人”象征著被虛假話語裹挾的群體,他們沿著“鋼軌”般的謊言前行,最終卻走向了“沒回來”的絕境。這里的“沒回來”不僅是物理意義上的失蹤,更是精神意義上的迷失。當個體放棄獨立思考淪為話語的附庸,便失去了與真實世界對話的能力,最終被謊言吞噬。
葉延濱的警示背后是“皇帝詩學”所延續的文化擔當。傳統“皇帝詩學”雖以帝王視角為核心,卻始終蘊含著“為生民立命”的責任感;葉延濱則將這種責任感轉化為對普通個體的精神關懷,不僅批判制造謊言的權力機制,更希望喚醒被蒙蔽的大眾。這種“警示意識”使他的寓言詩學超越了單純的批判,具備了引導精神走向的積極價值,也為“北京詩學”奠定了“批判與建構并存”的基調:批判的目的不是否定,而是為了重建更真實、更健康的話語生態。
葉延濱的寓言詩學之所以屬于“北京詩學”的范疇,關鍵在于其批判始終緊扣北京的文化語境與精神特質。先生筆下的“謊言”不是地域性的小伎倆,而是具有全國影響力的時代話語;先警示的“盲從者”,也不是某個特定群體,而是身處話語中心場域中的所有個體。這種“立足北京,觀照全國”的視野,正是“京派精神”區別于其他地域詩歌精神的核心所在——北京的文化地位決定了其詩歌必須承載更廣闊的時代關懷,而葉延濱的寓言詩學,正是這種關懷的詩性表達。
創傷與救贖:梁小斌的“日常詩學”與京派人文底色
梁小斌的詩歌始終扎根于北京的市民生活,詩人以《雪白的墻》為代表的作品,將宏大的時代苦難濃縮于“雪白的墻”這一日常意象中,構建了充滿人文溫度的“日常詩學”。這種詩學既體現了“京派精神”中對個體命運的深切關注,也延續了“皇帝詩學”中“以小見大”的敘事智慧——從一面墻的變遷中,窺見一個時代的精神創傷與救贖的可能。
詩歌開篇以孩童的視角切入:“媽媽,我看見了雪白的墻。早晨我上街去買蠟筆,看見一位工人費了很大的力氣,在為長長的圍墻粉刷。”這里“雪白的墻”是工人勞動的成果,是“不要在這墻上亂畫”的樸素叮囑,帶著純粹的日常感。但隨著詩意的推進,墻的意象逐漸沉重:“這上面曾經那么骯臟,寫有很多粗暴的字。媽媽,你也哭過,就為那些辱罵的緣故,爸爸不在了,永遠地不在了。”
“粗暴的字”直指歷史中的暴力話語,而“爸爸不在了”則將話語暴力與個體悲劇直接關聯——一面墻的“骯臟”與“雪白”,背后是一個家庭的破碎與一個時代的傷痛。在北京的胡同里、街巷中,這樣的墻比比皆是,它們既是城市空間的組成部分,也是歷史記憶的載體。梁小斌沒有選擇宏大的歷史場景,而是從最普通的一面墻入手,將歷史創傷植入日常場景,這種書寫方式正是“京派精神”的重要特征:不追求史詩般的壯闊,而是從北京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中提取時代記憶,使詩歌更具真實感與共情力。
詩歌的情感在結尾處達到升華:“比我喝的牛奶還要潔白,還要潔白的墻,一直閃現在我的夢中,它還站在地平線上,在白天里閃爍著迷人的光芒,我愛潔白的墻。永遠地不會在這墻上亂畫,不會的,像媽媽一樣溫和的晴空啊,你聽到了嗎?”
孩童對墻的情感從“看見”升華為“愛”,并作出“永遠地不會在這墻上亂畫”的承諾。這個承諾不僅是對工人叮囑的回應,更是對創傷的反思與救贖,“不亂畫”意味著拒絕暴力話語,守護墻的“潔白”,本質上是守護人性的純粹。而“像媽媽一樣溫和的晴空”則將個體承諾擴展為對時代的期許:希望未來的世界如晴空般溫和,不再有暴力與創傷。這種從個體出發的救贖意識,體現了“京派精神”中的人文底色:北京詩歌的精神力量,不僅來自對時代的批判,更來自對人性的堅守與對未來的希望。
梁小斌的“日常詩學”為“北京詩學”注入了獨特的精神價值。它證明北京詩歌不必依賴宏大的政治符號或歷史意象,也能承載厚重的時代主題;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個體的細微情感,同樣可以成為連接歷史與現實的紐帶。這種詩學將“皇帝詩學”的宏大關懷落地為對每個普通生命的尊重,使北京詩歌的精神譜系更具溫度與厚度——它關注帝王將相的歷史,更關注平民百姓的命運;它書寫城市的宏大變遷,更書寫個體的心靈軌跡。
覺醒與張揚:安琪的“城市詩學”與京派先鋒意識
安琪的詩歌帶著鮮明的“北漂”印記,詩人以《北京之春》為代表的作品打破了傳統北京書寫的沉重感,以充滿張力的語言書寫北漂詩人的精神覺醒,構建了極具先鋒性的“城市詩學”。這種詩學彰顯了“京派精神”中的先鋒意識,北京不再只是歷史的載體,更是個體夢想的舞臺,而“北京詩歌”則成為詩人自我實現的宣言與城市精神的注腳。
詩歌開篇即勾勒出典型的北京城市空間:“春天在永定門外等我,我從十四號地鐵冒出頭,楊柳樹已抽出嫩綠葉芽兒,摩的米師傅年輕,拉著我過陶然亭,過先農壇,來到金泰開陽大廈。”這些空間元素極具代表性:“永定門”“陶然亭”“先農壇”是北京的歷史地標,承載著城市的文化記憶;“十四號地鐵”“金泰開陽大廈”則是現代北京的象征,代表著城市的快節奏與機遇。
安琪將歷史與現代空間并置,構建了“傳統與現代交織”的城市語境。對于北漂詩人而言這些空間不僅是地理坐標,更是精神符號,“從十四號地鐵冒出頭”象征著從迷茫、困頓中覺醒,主動擁抱城市;“過陶然亭、先農壇”意味著接納北京的歷史文化;“來到金泰開陽大廈”則代表著融入城市的文化場域,找到自己的位置。這種對城市空間的詩性解讀,體現了安琪作為“外來者”對北京的獨特認知:北京不是封閉的文化堡壘,而是開放的精神家園,它既尊重傳統,又擁抱創新。
詩歌的核心意象“春日熊熊”以反復詠嘆的方式出現:“春天從一本詩選沖出來迎接我,它說,詩人,我已讀過你的詩。春日熊熊,春日熊熊,能點燃春天的人都是了不起的人!”“春日熊熊”既寫出了春天的生命力,也彰顯了詩人的自信與激情。在安琪眼中,詩人不是城市的邊緣者,而是“點燃春天”的創造者,是城市精神的塑造者。
這種對個體價值的張揚打破了傳統北京詩歌中“個體服從時代”的敘事模式。安琪筆下的詩人,不再是歷史的旁觀者或受害者,而是主動介入城市、創造價值的主體。這種“主動介入”的姿態,正是“京派精神”中先鋒意識的體現:北京作為全國文化前沿,始終吸引著有夢想、有鋒芒的詩人,而這些詩人則以自己的創作賦予城市新的精神內涵。從“五四”時期的新詩革命到當代的先鋒詩歌運動,北京始終是詩歌創新的策源地,安琪的“城市詩學”正是這一傳統的詩學延續。
安琪的“城市詩學”拓展了“北京詩學”的內涵與邊界。它證明“京派精神”不僅包含批判與關懷,更包含創新與突破;“北京詩歌”不僅是本土詩人的陣地,更是所有在北京追尋夢想的詩人精神的共同體。這種詩學回應了當代北京的城市特質——開放、包容、充滿活力,為北京詩歌的精神譜系注入了新的活力。同時它也為“北京詩歌概念”的命名提供了時代依據:北京詩歌必須緊跟城市發展的步伐,吸納多元的創作力量,才能保持旺盛的生命力。
痛感與堅守:藍藍的“生命詩學”與京派精神韌性
藍藍的詩歌雖不刻意強調地域特征,卻始終浸潤著“京派精神”的底色,詩人以《我的財富》為代表的作品,以極簡的語言書寫生命中的苦難與堅守,構建了直擊靈魂的“生命詩學”。這種詩學沒有宏大的城市意象,卻蘊含著“京派精神”中最本質的韌性——在苦難中保持溫柔,在有限的生命里堅守愛與尊嚴,這種韌性正是北京詩歌能夠穿越時代、歷久彌新的精神密碼。
詩歌開篇即顛覆了“財富”的傳統定義:“我的財富頂端那失敗的鉆石,我最大一顆珍珠里最初的貧困。”“失敗”與“貧困”本是生命的缺憾,卻被藍藍轉化為“鉆石”與“珍珠”般的財富——“鉆石”的堅硬對應著苦難的磨礪,“珍珠”的溫潤象征著苦難中的成長。這種轉化不是對苦難的美化,而是對苦難的超越:詩人坦然承認生命中的痛感,“我哆嗦的手腳,壓扁的深夜,我那燒成白灰的一綹頭發”,卻不被痛感吞噬,反而從中提煉出生命的價值。
在北京這座快節奏高壓力的城市,每個人都可能經歷“失敗”與“貧困”,都可能遭遇挫折與痛苦。藍藍的詩歌沒有回避這些痛感,而是以一種平靜、堅韌的態度面對它們。這種態度不是消極的妥協,而是積極的抗爭,將苦難轉化為財富,將痛苦轉化為力量。這種對生命的深刻理解,體現了“京派精神”中的成熟與厚重:北京詩歌經歷了不同時代的考驗,早已超越了單純的情感宣泄,形成了直面苦難、堅守希望的精神傳統。
詩歌結尾“我呼吸,在人間不會停留太久,我愛,并為此終生受苦……”將詩意推向高潮。“不會停留太久”承認了生命的有限性,而“我愛,并為此終生受苦”則彰顯了生命的無限性——愛與堅守超越了時間的限制,成為對抗苦難的精神支柱。這種堅守不是悲壯的吶喊,而是平靜的抉擇,帶著一種歷經滄桑后的從容與堅定。
藍藍的“愛”是廣義的,它包含對生命、對他人、對世界的關懷,這種關懷正是“京派精神”中人文傳統的核心。從老舍的小說到汪曾祺的散文,京派文學始終帶著濃厚的人文關懷;而藍藍的詩歌則將這種關懷延伸到對生命本質的追問,使“北京詩學”更具精神深度。同時這種堅守也暗合了“皇帝詩學”中“生生不息”的精神內核,無論時代如何變遷,對生命的尊重、對愛的堅守永遠是人類精神的底色。
藍藍的“愛”是廣義的,它包含對生命、對他人、對世界的關懷,這種關懷正是“京派精神”中人文傳統的核心。從老舍的小說到汪曾祺的散文,京派文學始終帶著濃厚的人文關懷;而藍藍的詩歌則將這種關懷延伸到對生命本質的追問,使“北京詩學”更具精神深度。同時,這種堅守也暗合了“皇帝詩學”中“生生不息”的精神內核——無論時代如何變遷,對生命的尊重、對愛的堅守永遠是人類精神的底色。
藍藍的“生命詩學”具有超越地域的普遍價值,它證明“北京詩學”不僅能書寫北京的城市故事,更能回應人類共同的生命困境。這種詩學為北京詩歌贏得了更廣闊的共鳴空間,也使“京派精神”成為具有普遍意義的精神符號——韌性、堅守、人文關懷,這些特質不僅屬于北京詩人,更屬于所有在苦難中追尋意義的人。同時,它也提醒北京詩人:只有扎根人性的普遍需求,才能創作出真正具有生命力的作品;只有堅守精神的底色,才能使“北京詩歌”始終站在時代的前沿。
根脈與共振:馬新華的“意象詩學”與京派文化擔當
馬新華的詩歌深耕北京的文化根脈,他以《香山楓葉的紅》為代表的作品,以“香山楓葉”為核心意象,將個人創作、城市精神與文化根脈緊密相連,構建了充滿文化自覺的“意象詩學”。這種詩學既是對“京派精神”中文化擔當的踐行,也將“皇帝詩學”的宏大意識轉化為對北京文化根脈的堅守與傳承,為“北京詩學”注入了厚重的文化底蘊。
詩歌開篇即奠定文化書寫的基調:“他放下畫虎的筆轉而蘸取香山的秋,墨盤里朱砂與赭石相撞,迸出《東方紅》底色寓言的北京。”“畫虎”的傳統技藝與“香山的秋”的地域意象結合,“朱砂與赭石”的傳統顏料與“《東方紅》底色”的時代精神碰撞,使“香山楓葉的紅”超越了自然景觀的范疇,成為連接傳統與現代的文化符號。
馬新華對“紅”的闡釋極具深意:“他說‘畫紅,不是涂胭脂,是山魂里滲岀的血,是晨光吻過的骨血,是北京的風吹老了歲月,卻吹不淡的赤誠’。”這里的“紅”不是表面的色彩,而是北京的“山魂”與“赤誠”,是代代相傳的文化精神。香山是北京的文化地標,楓葉的紅是北京秋天最鮮明的符號,而馬新華則賦予這一符號更深厚的文化內涵:它是胡同墻根被曬暖的霜色,是鐘鼓樓檐角挑著的余暉,是《北京詩歌》躍動的心跳。這種將地域意象與文化記憶深度綁定的書寫,精準捕捉了“京派精神”中對文化根脈的珍視,北京詩歌不僅要書寫城市的當下,更要承接城市的歷史,讓文化基因在詩行中延續。
詩歌的創作過程被馬新華描繪為“筆鋒轉陡,如香爐峰的脊背,淡墨鋪出霧,濃墨壓成巖,最紅的那幾片,懸在枝椏,像未熄的星火”。這里的“筆”既是繪畫之筆,也是詩歌之筆;“香爐峰的脊背”既是香山的地理形態,也是北京文化的精神風骨。詩人以筆墨為媒介,將自然景觀與文化精神融為一體,實現了“筆與魂的共振”——“魂”既是香山的山魂,也是北京的城魂,更是詩人的文化魂。
這種共振的本質,是詩與城的共生:北京為詩人提供了文化滋養,從胡同的煙火到宮殿的莊嚴,從歷史的厚重到時代的鮮活,都成為創作的素材;詩人則以詩歌為載體,為北京的文化注入新的生命力,讓香山的紅、鐘鼓樓的韻,通過詩行被更多人感知。馬新華在詩中寫道“讓每道紋路都通向山魂的根”,正是這種共生邏輯的詩性表達——詩歌的紋路與城市的根脈相通,才能真正成為城市精神的代言。
馬新華的“意象詩學”,彰顯了“京派精神”中最核心的文化擔當。在全球化語境下,城市文化逐漸趨同,北京詩歌的使命之一,便是守護本土文化的獨特性。“香山楓葉的紅”之所以能成為文化符號,正是因為它承載了北京獨有的歷史記憶與精神氣質——這種“紅”不是抽象的色彩,而是具體的文化場景、鮮活的生活體驗、厚重的歷史積淀。
這種擔當,也是“皇帝詩學”宏大意識的當代轉化:傳統“皇帝詩學”以“天下”為關懷對象,當代北京詩人則以“城市文化”為守護目標,通過對地域意象的詩性建構,讓北京的文化根脈得以傳承。馬新華的創作證明,“北京詩學”的文化厚度,不僅來自對傳統的繼承,更來自對傳統的創新,將古老的文化符號與當代的詩歌語言結合,才能讓北京文化在新時代煥發生機。
結語:為中國當代詩歌的繁榮貢獻“北京力量”
梳理葉延濱、梁小斌、安琪、藍藍、馬新華的創作實踐,我們得以清晰地勾勒出當代北京詩歌的精神譜系:這是一條以“京派精神”為核心,融合批判與建構、關懷與先鋒、韌性與擔當的脈絡。葉延濱的“寓言詩學”以批判為刃,剖開時代話語的虛妄,奠定了北京詩歌的現實品格;梁小斌的“日常詩學”以人文為底,從個體命運中窺見時代創傷,賦予北京詩歌溫度與共情;安琪的“城市詩學”以先鋒為旗,在城市空間中張揚個體精神,激活了北京詩歌的創新活力;藍藍的“生命詩學”以韌性為骨,在苦難堅守中追問生命本質,深化了北京詩歌的精神深度;馬新華的“意象詩學”以文化為根,在地域意象中錨定精神血脈,厚重了北京詩歌的歷史底蘊。
這五位詩人的創作,共同印證了“北京詩歌概念”命名的必要性與緊迫性。這種命名不是簡單的地域劃分,而是對一種詩學傳統的自覺認領,對一種精神使命的主動承擔——它昭告詩歌界與批評界:北京詩歌早已形成具有獨特氣質的詩學體系,其“京派精神”既承襲了“皇帝詩學”的宏大關懷與文化擔當,又融入了當代的現實意識與個體精神,是中國當代詩歌不可或缺的重要力量。
對于北京詩人而言,這種命名意味著更明確的使命自覺:既要扎根北京的文化土壤,從城市的歷史與現實中汲取素材;又要跳出地域的局限,以更廣闊的視野觀照人類共同的精神困境;既要繼承“京派精神”的優良傳統,又要勇于突破創新,為北京詩歌注入新的時代內涵。
從本質上看“北京詩歌”的詩學建構與精神譜系重釋,最終指向的是中國詩歌的當代發展——以北京為樣本,探索地域詩歌與時代精神的結合路徑,尋找傳統文脈與當代創作的銜接點。當北京詩歌以“京派精神”為旗,以“北京詩學”為綱,它必將以更系統、更整體的姿態,在全國詩歌版圖中彰顯獨特價值,為中國當代詩歌的繁榮貢獻“北京力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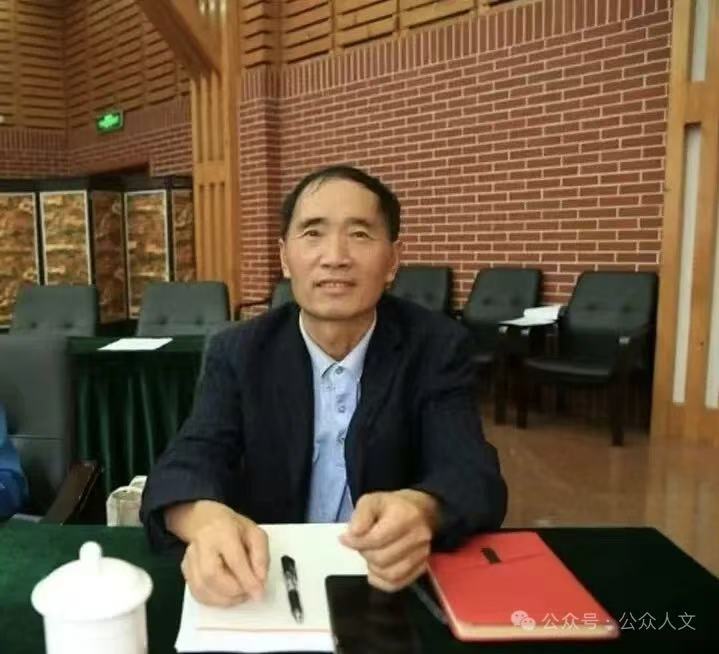
楊青雲 近照
【作者簡介】楊青云,曾用名楊曉勝,筆名梅雪、汝愚等。常駐北京。著有《范曾論》《范曾新傳》《孔祥敬詩論》《周恩來研究》《范曾詩魂書骨美學思想窺探》《賈平凹美術論》《李德哲美術論》《北京虎王馬新華新論》《忽培元淺論》《王闊海新漢畫初探》《北京詩歌概念書系上部》《櫻花結》長篇小說等。現為范曾研究會會長,北京周館籌秘書長兼《周公研究》新媒體總編。
(注:本文已獲作者授權發布)


 純貴坊酒業
純貴坊酒業




